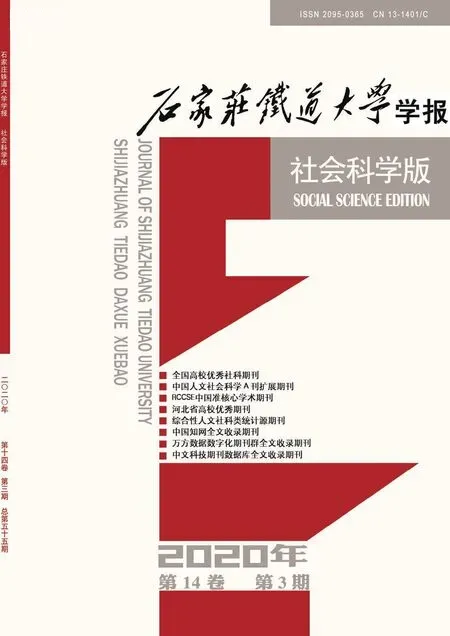论王梵志诗中的悲剧
——基于悲剧美学的理论
黄 炬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悲剧原是西方戏剧的一种体裁,其源头是祭祀仪式中的酒神颂歌。亚里士多德奠定了悲剧情节、演出时限等理论基础,并被后世不断发展成一门延伸到了其他文学体裁中的系统文艺理论和美学原理之一。“悲剧”一词的内蕴也逐渐超出了戏剧等文艺作品创作、接受的理论范畴,成为不幸事件和引起接受者痛苦、哀伤、恐惧等悲感情绪的一般代名词。作者和接受者在创作和欣赏悲剧时与悲剧事件保持着一段审美距离。这段审美距离使得作者心中原有的,以及接受者心中被作品激起的悲感得到升华——“以悲剧的痛苦唤醒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唤起对人生、生命、社会、历史的反思。”[1]
中国戏剧虽然没有系统的悲剧理论,绝大部分也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即便是《窦娥冤》《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已悲感十足的戏剧也并没有西方那种浓重的悲剧色彩,鲁迅等人严厉批评了古典戏剧的这一创作倾向。没有系统的悲剧理论虽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一大缺憾,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悲剧意识。中华民族的童年是早熟的,我们心中社会、历史、人生的沧桑感由来已久。叔本华、别林斯基等人将悲剧作品奉为文艺的巅峰,而我们,从来都不缺这样的佳作。在诗歌理论领域,钟嵘多以“哀怨”“凄怆”等悲苦之词评诗,被他列入上、中品的诗人大多都以悲苦为主要的艺术特色,足可见其以悲为美的艺术眼光。在诗歌创作方面,王梵志的诗虽被学术界定义为通俗诗,但读来悲感浓郁,十分沉重。他一生坎坷,饱经沧桑,敏锐地感受到了初唐安定繁荣局面背后的种种悲剧。
一、人生悲剧
叔本华等悲剧美学家认为悲剧就是真、善、美的毁灭,假、丑、恶的凸显。随着对悲剧认识的不断深入,美学家们意识到悲剧不一定是要让诸如普罗米修斯这种至善至美被毁灭,也不一定要像英国文学那样热衷塑造大批撒旦式的邪恶形象。相反,普通生活中的善、恶、美、丑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悲剧,这也是莱辛市民悲剧的理念。王梵志的诗中就抒写了这样的悲剧。
(一)假、丑、恶的凸显
他的一些诗描写了守财奴的凄凉结局。“病困卧着床,悭心犹不改。临死命欲终,吝财不忏悔。”(《受保人中坐》,本文中的王梵志诗均引自《王梵志诗辑校》)[2]这可谓是对此类人最典型的刻画。《大有愚痴君》中的守财奴用尽心思,贪敛了不少钱财。然而转眼间便撒手人寰,钱财被奴婢随意挥霍。更有甚者,在《撩乱失精神》中,妻子被人霸占,儿女被人任意驱使,自己百日斋祭过后便被淡忘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而这对于那些奴婢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至于谁是主人似乎并不重要。“不免贫穷死”正是王梵志对这些守财奴最辛辣的嘲讽,他们在物质上什么也带不走,精神上更带不走别人的一丝关怀,死后的“贫穷”一至于如此!诸如此类的诗歌还有《愚人痴涳涳之一、之二》《有钱惜不吃》《见有愚痴君》等。叔本华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为意志,万物为意志追求不息,而且永远得不到满足,这是世间一切痛苦的根源。这些守财奴在意志的驱使下盲目地为财生,为财死,他们的人生是浑浑噩噩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
贫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生产力、政策制度、战乱等社会性因素外,个人勤勉与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家中渐渐贫》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懒妇形象:好吃懒做,饮酒无度,无所事事;越穷越生孩子,越生孩子越不肯劳作;有件光彩的衣服就大摇大摆地出去攀比一番;又喜欢搬弄是非,十分讨厌。又如《朝廷数十人》:这些懒汉整日和一群狐朋狗友鬼混;喜欢高谈阔论,而实际上一无是处;任意驱使妻子儿女,却连温饱都不能满足他们,连自己的父母都引以为耻;诗人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人:“日月甚宽恩,不照五逆鬼!”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是人类的生物本能,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这导致了“本我”与理性冲突的悲剧。
王梵志的诗也表现了一些家庭伦理的悲剧。“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造作庄田尤未已》)亲情竟然如此冰冷,简直不堪直视;父母缩衣节食将儿女养大,儿女动辄就怒怼父母;一些儿子娶了媳妇就嫌弃父母老丑,完全忘记自己是在父母的怜爱下长大的;儿子畏债自杀,父母担罪;其他如妒妇破坏家庭,继母漠视继子等,也都有所表现。
英国文学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说:“生活中真正的悲剧往往以毫无美感的形式出现,它们给我们的感受无异于一切鄙俗的事物。”[3]财奴、逆子等鄙俗、丑陋人事的凸显,表明真、善、美等有价值的事物失落,而这何尝不是悲剧性的呢?
(二)人情之美与生命苦短的矛盾
悲剧美学认为,悲剧就是要把真、善、美等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爱情的幻灭又何尝不让人扼腕痛惜呢?“花帐后人眠,前人自薄福。”(《平生歌舞处》)在鬼使的催促之下,人间那一个个歌舞相乐的家庭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死别的悲剧。“夫妇相对坐,千年亦不足。”(《夫妇相对坐》)然而,死神一朝降临在头上,即便是腰缠万贯也赎不回对方的生命。斯人一去,空留得台镜生尘,剪刀蒙锈,哀痛难止。“情欲、感情、愿望、认识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而是构成着人类天性的财富,一切人共有的东西。因此,谁具有更多的普遍事物,谁就更富有生命。”[4]别林斯基话里的“生命”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追求是人类普遍的特质,举案齐眉,你侬我侬,夫妻间这种缠绵不尽的人情美,对爱情超越千年,超越生死的强烈愿望的人性美,迸发出了崇高的生命之美。王梵志笔下爱情崇高的生命之美与瞬间幻灭的巨大落差充分展示出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二、命运悲剧
基于命运的神秘感所激起的对人生的怅惘和迷惑,千百年来,从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直至现在,哲人们不停地探索着命运是什么的问题:宗教的宿命论、谢林的必然与自由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偶然说……
从《差着即须行》一诗来看,王梵志相信名字、官职、钱财、衣食等都是命中注定的,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运命随身缚,人生不自觉”(《运命随身缚》)、“运命满悠悠,人生浪聒聒……饶君铁瓮子,走藏不得脱”(《运命满悠悠》),王梵志这种个人命运的无力感和悲感也通于西方《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悲剧,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悲剧观。在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中,命运女神是主宰一切的,就连众神之神的宙斯也都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这是宿命论的体现。
王梵志对命运进行了诗意的表达。他虽身在佛门却并没有陷入宿命论的漩涡之中,他是以超出生死的哲思来审视命运的归宿:“身如大店家,命如一宿客。忽起向前去,本不是吾宅。”(《身如大店家》)个人的命运在生死之间飘忽不定,谁也不知道自己今生将会住进什么样的店家(人的躯壳),也不知道在这个店家里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生风景。而个人的命运终究是要离开的,只不过是暂时寄宿在上面而已,命运是如此的难以捉摸!他有时候以轻松的笔调来抒写命运的真谛,内蕴却十分的深厚,很难说这是唯心还是唯物:“自生还自死,煞活非关我……若不急抽却,眼看塞天破。”(《自生还自死》)生不由己,死不由己,个人生命的“消长”维持了人类的平衡。同样,就命运而言,有人幸福就有人不幸,有人失意就有人得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上面还存在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我们绝对不能认识它。”[5]我们上面存在着的这种东西——命运,维持着万事万物的平衡,个体只能服从它,任其宰割。相对于古希腊人停留于命运表面上的悲感来说,王梵志的探索又进了一步。王梵志对命运的哲理性思索并没有消解掉其中的悲剧力量,如果仍以王梵志的哲思来探索全人类的命运反而显得更加沉重:相对于宇宙的浩瀚,我们人类显得如此渺小,我们与宇宙中的其他事物同样存在着“消长”的关系维持整个宇宙的平衡,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该怎么办?该何去何从?
西班牙思想家乌纳穆诺曾说过:“凡是属于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而不只是非理性的;同样,凡是理性的事物都是反生命的。这就是生命之悲剧意识的基础。”[6]王梵志对命运的沉思正是反理性的典型表现。他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甚至不确定它到底存不存在,只是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似乎确实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戏弄着人生,操控着生死。人类的命运观本身就是一个反理性的东西,对命运的恐惧也只不过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千百年来,王梵志和无数的哲人一样,以反理性的行为去探索一个反理性的东西,讲不清楚又似乎摆脱不了,悲剧意识弥漫在他们的心头,也带给了全人类。
三、社会悲剧
“中国古典悲剧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广阔性,悲剧性格的多样性,悲剧根源的深刻性,是西方古典悲剧所不及的。”[7]211早在2600多年前,《诗经》中《魏风·硕鼠》《魏风·伐檀》《小雅·采薇》等诗就已经开始抒写底层民众的历史悲剧性了。而西方古典文学,往往热衷于塑造像普罗米修斯这样为人类幸福献身的悲剧“巨人”,到了19世纪,文坛才有意识地将笔头转向批判现实主义,刻画普通民众,抒写小人物的悲剧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悲剧观将悲剧文学的创作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主张突出悲剧的历史真实性,是对社会悲剧美学的重大贡献。悲剧作家和理论家们认为社会悲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环境、人际关系、悲剧人物。王梵志的诗描写了一幅幅封建制度压迫下的社会底层生活画,很好地体现了社会悲剧美学。
(一)社会环境
作为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是社会悲剧的直观表现。“批判现实主义的悲剧作家们,从大量的社会现象中意识到‘社会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命运’这一铁的法则。”[7]189
隋炀帝横征暴敛,肆意挥霍民力,最终玩火自焚。初唐统治者吸取了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相对减轻了百姓的一些负担,并创造了一个治世——贞观之治。初唐统治者在隋朝租调制的基础上创制了租庸调制。每丁每年纳“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8]。此外,每丁须为中央政府服正役二十天,或者为地方政府服数十日的杂徭,如果不想服役也可以输税代替。经韩国磐先生的推算,通常情况下,交纳租税后“每年还缺少一个半月以上的口粮”[9]。如果再算上各项生活开支以及力役的话,农民的生计其实是极为窘迫的。然而,陆贽却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一文中称赞租庸调制云:“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以之厚生,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10]4748“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11]一些统治者打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旗,堂而皇之地剥削百姓,对民生疾苦无动于衷,这不正是封建社会的悲剧性吗?二十天的正役似乎影响不大,然而有时候来往的行程就花费了大把时间,严重耽误了农作活动。“一人就役,举家便废”[10]1570并非虚言。《旧唐书·马周传》有言:“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12]
租庸调制实施的基础是均田制,它具有国有和私有的双重特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高宗、武后时期吏治的腐败,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之租庸调制按人头而不是按实际土地占有量的收税办法,使得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王梵志的《富饶田舍儿》和《贫穷田舍汉》把这一社会背景下的贫富差距对比得十分鲜明。
府兵制是时代悲剧的另一大根源。府兵制起源于西魏,唐太宗时达到了鼎盛。此项制度从三丁之家抽取一人服兵役,府兵“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徭”[13],此外还需要自备驮马、衣食、兵器等军用物资,这对于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来说,无疑是又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人际关系
“社会悲剧特别重视交待悲剧人物的社会性,而最能体现人的社会性的是人际关系”[7]193,直接体现在压迫剥削与被压迫剥削的关系上。对于那些交不上赋税的百姓来说简直就是噩耗。一些地方官吏趁机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祸害乡里。《独自心中骤》记录了一个兵勇逼税场景,这些强盗公然欺男霸女,可恶至极。“脱衣赤体立,则役不如羊……命绝逐他走,魂魄历他乡。”(《身如圈里羊》)兵役、正役之下的百姓真是还不如牲口呢!牲口好歹还能有皮毛遮风挡雨有所归依,而从役者无端沦为孤魂野鬼。百姓为地方政府所服的杂徭又名轻徭,但也未必见得这一项徭役有多轻。“官喜律即喜,官嗔律即嗔。总由官断法,何须法断人。”(《天理为百姓》)难免会有一些地方败吏“不依令式,多杂役使”[10]428,更不用说借法巧立名目,敲榨百姓了。王梵志的《当乡何物贵》大胆揭露了这些丑行:乡里区区刀笔小吏利用手上的一点职务之便就可以竞相奔走钻营,何况一乡之长呢?难怪诗人不禁感叹:“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
“天下恶官职,不过是府兵。”(《天下恶官职之一》)王梵志抨击府兵制的残酷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天宝三载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有言:“成童之岁,即挂轻摇,既冠之年,便当正役。”[10]3150对一些男丁来说,成童(十六岁至二十岁)服轻徭,再加上成丁后四十年的兵役,这几乎就是终身服役了。唐代前期战争频繁,在四十年的戎马生涯里又有多少人能够活着退役?而且,这些职业军人“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8]6895,很难得到优待。“王役逼驱驱”(《人生一代间之一》),王梵志也揭露出了那些非人的待遇。
存在主义哲学家布贝尔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我与你、我与它,我与它的关系是把对方当作完全客观的,可以操纵和利用的物,这体现出的是人性的毁灭。从王梵志诗中所揭露出的,对百姓的压迫剥削来看,统治者显然是把百姓当作他们营建宫室、开疆拓土的工具了,像牛马那样。
人际关系上的社会悲剧性也间接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黑格尔认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与人民对自然“人”(应有的各种生存需求和权利的人)的渴望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悲剧性的。由于社会阶层和社会环境的差别,自然的“人”实际上是被社会的人扼杀了,“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异化了。亲情的异化更是触目惊心。相当一部分人不惜把重赋重役抛在父母身上,四处苟且偷生,为了生存,有的甚至六亲不认,为非作歹。《天下浮逃人》云:“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南北踯纵横,诳他暂归贯。游游自觅活,不愁应户役。无心念二亲,有意随恶伴。”亲情的异化是有其根源的:环境使然!正如《奴人赐酒食》之言:“户役一概差,不办棒下死……何为抛宅走,良由不得已。”
(三)悲剧人物
王梵志自己就是一个悲剧,步入中年后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四处化缘求生,贫病交加的他甚至不觉料想到自己将死于沟壑,为豺狼所食,《一生无舍坐》倾诉了这一悲剧。他有时候甚至强烈地呼嚎生命的苦难:“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我昔未生时》)这又何尝不是万千百姓的痛苦心声呢!
恩格斯的悲剧美学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4]。“差科取高户,赋役数千般。”(《当乡何物贵》)在这个痛苦的时代里,富裕的家庭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剥削,这便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环境。经胡适、郑振铎等先生的考证,王梵志家里早年生活还比较富裕。后来很有可能是由于赋役的剥削导致破产,最后空无一物,穷困潦倒,于是只好皈依佛门。经历了人生剧变的他有时候反而感到很庆幸:“他家笑吾贫,吾贫极快乐。无牛亦无马,不愁贼抄掠。你富户役高,差科并用却。吾无呼唤处,饱吃长展脚。你富披锦袍,寻常被缠缚。穷苦无烦恼,草衣随体着。”(《他家笑吾贫》)环境迫使人物行动,他以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抒发了自己空无一物,了无牵挂,尚能得过且过的“悠闲”心态。这种扭曲的心态是社会悲剧最好的见证。
府兵制也制造了不少悲剧人物。丈夫一去永别,妻子守活寡不说,还得在家里没有必要劳动力的条件下独自抚养儿女,生计十分艰难,以至于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妇人应重役,男子从征行。”(《相将归去来》)《观内有妇人》一诗,从“眷属王役苦,衣食远求难”来看,写的就是府兵制下的家庭境况。诗中的这位女子贫病交加,无力应对其他赋役,更何谈为征夫寄去衣食!于是只得投身道观,凄惨度日。
马、恩认为悲剧人物应该集进步与腐朽落后于一身。佛教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互相利用的关系:佛教依附统治者得以生存,统治者利用佛教的宿命论、因果报应论来麻痹民众的反抗意识,以便达到剥削的目的。王梵志50多岁时才皈依佛门,但他四处化缘求斋,并没有严守佛门条律。结合他对宿命论的怀疑来看,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宿命论、因果报应论者,再从他对唐代赋役制度的抨击来看,还体现出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但他诗中贫富贵贱命中注定的佛教思想比较浓重,这又是他腐朽落后的一面。这种双面性不仅表现出了悲剧和悲剧人物的历史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展示出了悲剧的震撼力:诸如王梵志这样的悲剧人物分明已经看到了现实社会的不合理之处,但自身腐朽落后的一面决定他们根本找不到出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以及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被毁灭。
四、“死亡艺术”
王梵志讽刺秦皇、汉武求仙访道的蠢行,他心里弥漫着“生活本身的无价值、个人的有限生命的无价值”[15]的悲剧意识。爱情、生命不得长久;命运的魔爪无计逃脱;功名、财富又带不走;懒人、不孝子等庸人的生命更是如此的污浊。他眼中充满了这些不堪的事物,于是生发出了“万世淡无味”(《共受虚假身》)的消极心理。王梵志悲剧意识的另一方面是看遍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痛苦。“早死无差科,不愁怕里长。行行展脚卧,永绝呼征防。”(《生时同毡被》)上有各项赋役的压榨,下有地方官吏的欺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忽起相罗拽,啾唧索租调。贫苦无处得,相接被鞭拷。生时有痛苦,不如早死好。”(《可笑世间人》)至于那些交不上租调的百姓,等待他们的将是官府的无情鞭笞,如此痛苦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又如《你道生胜死》,写的是府兵制下军人饥肠辘辘的痛苦呻吟和希望慈母别给这条生命的哀嚎。王梵志这些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恶生乐死的悲观情绪,正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堪称是人间地狱,生不如死。
他的诗堪称是“死亡艺术”,其毕生三百多首诗中,有一百五十余首是直言死亡的,这在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他看透了人生、命运、社会的各种悲剧,但又找不到出路,彷徨,迷茫,于是只好宣扬“死亡艺术”来呐喊,来唾弃,来反抗那个时代。“因为只有死亡才能清除尘世间的污秽和耻辱,除此之外,别无良策。”[16]
王梵志诗的“死亡艺术”是全面否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近乎叔本华的悲剧学说。“你从何处来,脓血相和出。身如水上泡,暂时还却没。”(《狼多羊数少》)他以生之痛苦和死之须臾作对比,极力突出生命之苦短。“纵得王公候,终归不免死。”(《本是达官儿》)达官贵族的后代不仅出身好,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但终究难免一死。“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工匠莫学巧》)他奉劝工匠放弃技艺,它只会奴化人格,受人剥削。因为唐律规定:“诸丁匠岁役工二十日。”[17]“只见生人悲,不闻鬼唱祸。”(《生即巧风吹》)生死之间来去匆匆,有几人参悟到了六道轮回之苦?那些凡夫俗子只是恋生悲死而已,何曾看得到死后的悲苦!人人都渴望长命百岁,但他有的诗,如《百岁有一人》,却宣示这并不见得是件好事。佛教称人生在世要遭受五阴之苦,活的越长就意味着要经历更多的这种苦难。佛教认为人世间的恶人死后会被打入最苦的阿鼻地狱,使其受尽折磨,王梵志的这首诗却声称长命之人死后也会被打入阿鼻地狱,居然连死后的意义也被他否定了。
佛教并没有完全使他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与现实的矛盾反而搅乱了三观,创伤了精神,逼得他堕入了虚无主义的漩涡。“虚无主义带着渗透骨髓的阴冷,传递着社会的悲哀引发人们心里的哀鸣”[18],我们不禁感叹,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是要有多么失望才至于完全否定人生的价值和生死的意义。王梵志和哈姆莱特等悲剧形象一样,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精神上极其痛苦。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的苦难和死亡”是最惊心动魄的悲剧[19]。但“精神上的毁灭也可能看来是悲剧性的”[20],而且更像是彻彻底底的悲剧。精神上的悲剧是人生、命运、社会等各种悲剧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