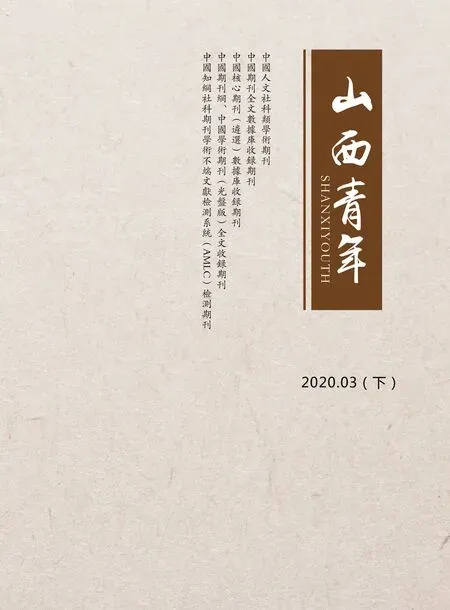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精准脱贫
肖文婷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由“救济式扶贫治理”“开发式扶贫治理”不断走向“参与式扶贫治理”的治理模式,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现阶段,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减贫脱贫的难度越来越大,急需转变过去的扶贫模式,解决贫困区域发展的滞后问题。社会治理进一步丰富了精准扶贫的内涵,不仅要扶贫,更重要的是脱贫,推动脱贫开发工作建立有内生动力、上下结合、内外互动、多方协调的脱贫长效机制。社会治理的引入,革新了我国传统贫困治理的格局,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调整新的社会权力分布格局和以社会系统组织整合理论看待问题的视角,对于改变片面强调整体利益而漠视公民个体因素的传统贫困治理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一、社会治理理论的内涵和在精准脱贫应用中的合理分析
精准扶贫作为贫困治理最重要的内容和手段,直接关系减贫的有效实现,更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社会治理视角和精准扶贫有高度的契合度,不仅在目标上存在着内在统一性,而且在实践结构上的同构性也颇为相似,都注重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转变到社会资本的过程,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发展和社会资本的不断开拓,为脱贫攻坚的实践模式创新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多元扶贫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一词不仅体现多个权力中心之间连续有机的协调,也体现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协同参与的内在意义;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则是遵循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以多元主体间共同合作和参与为基础,理性的选择和配置社会资源,以人为本的原则满足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需求;将社会治理引入精准脱贫,除了政府机构,还包含更为广泛的社会组织,这些主体共同承担扶贫工作。社会治理制度的强制性是其政策有效实施的刚性特征,这种“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契合程度是社会治理制度的一大优势所在。
社会治理理论注重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当前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我国贫困治理已经跳出了单纯的物质供给阶段。社会治理理论强调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支持网络中,使得人们的社会行动能够实现的一种社会资源,通常表现为信任和规范等,这些资源可以为贫困人口带来便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它们获取资源的成本。社会治理理论认为精准脱贫的人口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现有的扶贫工作应当不断推动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再到社会资本的转变。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减贫对象的内生发展动力。社会治理理论在精准脱贫中的应用,不仅注重协同共治,积累社会资本,更强调减贫对象的内生发展动力。贫困人口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足才能达到脱贫的目的。社会治理理论认为贫困治理不仅有外生式扶助,内生式的发展是更关键和更根本的治理,尽管外部的资源投入对精准脱贫的帮助尤为重要,但是贫困人口内部的自助性发展是实现精神和物质脱贫的必经之路。
贫困群体参与和共享是树立减贫主体发展意识的重要途径。贫困人口被动接受救助的局面,让他们成为减贫主体之一。由此,贫困治理不是简单的投入和帮扶的模式,而是外部条件的有效输入和内部资源的充分挖掘相结合。
二、社会治理视角下脱贫工作面临的问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国的减贫成效有目共睹,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高度赞誉。但脱贫工作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贫困治理主体结构、贫困治理的社会资本、减贫对象的主体发展意识三个方面。
贫困治理主体结构有待改善,实现精准脱贫的工作中,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统筹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大包大揽”。贫困地区的独特资源和经济优势缺乏灵活的模式来激发其实现有效的市场化。非政府组织助力精准脱贫,可以发挥独特的专业优势,打破现有政府“单兵作战”的减贫模式,丰富贫困治理中“政府—贫困群体”的单向结构,推动贫困群体之间多层次的良性互动;在宏观上减轻政府行政和经济压力,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扮演掌舵者的角色,总体规划和掌控扶贫方向;微观上来说,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主体之一,激发社会承担主体责任的同时,与政府产生协同效应,创新发展新的减贫项目。
贫困治理的社会资本短缺,一是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贫困的弱势群体难以获得或无法利用制度保障来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必须改革和完善贫困地区的教育和文化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医疗体制,满足贫困区域整体的基础性发展需要;二是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力不够,制约了这种资本支持的作用和效果,解放和激发社会组织的发展动力,丰富民间组织的活动方式成为一个突破口;三是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意识薄弱,因此要提高贫困人口实现自我内在的发展动力,不断积累贫困群体的独特社会资本存量。要实现精准脱贫要由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向社会资本范式转变。提高减贫对象的社会资本占有,是新时代我国精准脱贫制度变迁的重要路径。
减贫对象的主体发展意识不充分,现有的脱贫政策以扶贫主体为中心,输送物质和服务达到减贫脱贫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贫困主体被动接受各项优惠政策享受脱贫,经济上脱贫后较少关注贫困人口自身的发展能力和致富的可持续能力,这也是造成返贫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能否在今后长期的发展中稳定脱贫还是值得考量的。脱贫真正的意义是在于培育贫困对象的主体活力和能力,通过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形成内源发展的主体,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脱贫队伍中,与区域环境相结合,才可能实现可持续脱贫,有效减少脱贫后的返贫现象。将贫困治理内源式发展和外生式输入相结合,使得我国现有的贫困治理体制既有赖于外部资源的有效输入,更有赖于减贫对象内部的自发展。
三、社会治理视角下精准脱贫政策创新
参照社会治理的理论精髓,精准脱贫是政府、市场、社会、民众等多主体合作的共治模式。社会治理视角引入精准扶贫,对我国的减贫事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调整多元贫困治理格局的同时,凝聚、重塑、合理分配社会资本,并且着重强调发展减贫主体的内在动力,提升自我发展意识,实现精准脱贫。
政府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有机统一,这与公民治理理论所提出的“多元社会主体对一个独立的国家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谋而合。庞大的贫困人口基数和复杂多样性的致贫原因对政府单一扶贫体制提出挑战,客观上要求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民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反贫困行动中,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减贫主体相关多元化模式,这种社会协同参与的精准脱贫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参与减贫事业,理清政府、社会、市场和公众之间在脱贫事业中的主体关系,打破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隔阂,夯实脱贫攻坚的成效,为脱贫的精准性打下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值得肯定的是,现有的脱贫攻坚行动呈现了结对帮扶的和多主体参与的效果,但参与深度和广度仍然有待提升,贫困农户和市场机制的能动性潜力尚未发掘出来。
社会资本和制度保障的双重驱动,“资本理论研究者认为,物质、人力与社会三种资本的积累顺序不同,这三种资本积累在不同时期也会显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需求”。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社会资本的表现一般是人口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国家政策和规章制度、社会组织及社会参与程度等。国家制度和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贫困主体拥有制度赋予的权利来保障自我生活的基本需要,抗衡致贫因素的困扰,为了防止漠视贫困群体和减轻制度孤立贫困群体的现象,建立和完善针对贫困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加大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对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积累有显著的作用,依靠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发展贫贫困地区的三大产业,拉动经济发展水平。激发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提高贫困人口社区参与程度,对丰富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有重要帮助,同时改革和完善贫困地区的教育和文化建设,提高减贫对象的文化素养,在拥有社会资本的同时懂得如何使用,从而提高自身的能力。
自我价值和公共利益的共同提升,精准脱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民生政策,贫困地区和人口经过政策“输血”这一系列的制度有效的缓解了贫困,但是贫困治理对象依旧被看做是“可怜人”和“弱势群体”,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和扶持。在社会治理取向看来,精准脱贫的工作机制应当消除这种无形的“社会排斥”现象,重视贫困群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构建社会融入为目标的扶贫工作机制,而且强调对扶贫对象实施集体认同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现代培育”。减贫对象自我价值的认同与中央所提出的坚持源头治理、根本消除贫困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贫困治理必须从“外部输血”转向“自身造血”。这也在另一方面对精准脱贫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不仅要“扶贫”更要“扶志”,在精神上实现脱贫,脱贫攻坚的内生发展动力才能真正提升,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回馈社会,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贫困主体自我发展的实现都有赖于贫困地区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充分发掘地区资源优势,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学习生产技术和技能。提高减贫对象主动性作为,促成贫困地区内源式发展的格局,实现可持续脱贫,建立健全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四、研究结论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脱贫的任务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也更加紧迫,总结以往的脱贫经验,结合最后阶段的任务,社会治理理论框架下的脱贫工作更能体现多层次、长效性的脱贫特点。社会治理理论主要从内涵与精准脱贫有内在契合性,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发挥社会各界扶贫主体的层次性和不同的功能,以及关注脱贫主体的自我效能,由扶贫到脱贫的彻底转变,最终使得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不返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