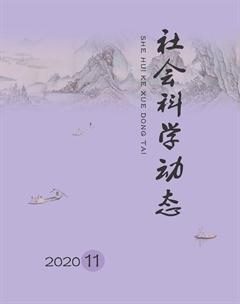汤养宗的诗歌:包容的姿态与新质的追求
汤养宗是当代汉语诗坛中葆有持久文本创新力和语言创造力的诗人之一。四十年来,他坚持在鲜活的民间场域中寻找资源,坚持精神的自我探寻,不断拓展自己诗歌的艺术空间。2018年,他的诗集《去人间》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可以说,《去人间》既是诗人自我更新的显证,也是当代文学语境变化的写照。
一、口语叙述中的抒情传统
20世纪90年代初,汤养宗因“海洋诗”闻名诗坛。进入新世纪以来,汤养宗在接受西方现代理性逻辑和语言理论的同时,又创新性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建构了以叙述句为主干的话语体系。开阔、复杂的诗歌叙事革新了以往汉诗写作中的精雕细琢、高言大志的积习,极大地开拓了诗歌写作的空间。
林庚先生说:“正是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其为诗的国度。”① 抒情无疑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特征。汤养宗则认为,“叙述依然是在抒情,但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抒情,而是文字与阅读之间的平等交换,把才情的另一头托付给阅读,使阅读成为第二次创造”②。他以戏剧化、情境化、白描等艺术手段介入,并以叙述与体验聚合把读者从遮蔽的状态中“唤起”,这种“唤起”不再依赖诗人主观强烈情感的输出,而是返回事物自身,从叙述语言中营造诗歌肌理间的情感表现张力。比如《平安夜》:
窗前的白玉兰,身上没有魔术,今夜平安。
更远的云朵,你是可靠的(说到底,我心中也没数并有了轻轻的叹息)未见野兽潜伏,今夜平安。
云朵后面是星辰,仍然有恒定的分寸,悦耳,响亮以及光芒四射的睡眠。今夜平安。
比星辰更远的,是我的父母。在大气里面坐着
有效的身影比空气还空,你们已拥有更辽阔的祖国
父亲在刮胡子,蓝色的。母亲手里捏一只三角纽扣那正是窗前的花蕾——今夜平安。
悼亡诗自古有之。汤养宗这首悼念父母的诗在现代时空观念的影响下,凸显出一种独特的面貌。他从窗前的白玉兰联想到遥远星辰,再到天国父母,最后回到窗前,构建了一个环形的时空结构,诗人把天国的父母置于其中,虚实相生的细节叙述,戏剧场景式的还原,实现父母在时光深处与万物的永恒同在。“今夜平安”的反复咏叹,歌唱式的结构使口语叙事形成强烈的韵律,传达出诗人对人世最深情的祝福。这种手法在他的《空气中的母亲》《没事做》等作品中也多次出现。汤养宗把古典节奏、韵律元素揉入现代口语叙事诗,使得现代诗的抒情有了更坚实的质地。
古典诗词中的“互文”、白描语言等修辞手法也在汤养宗的口语叙事中得到承续。如“从无中生有的有/到装得满满的无”(《光阴谣》),“深也十多年,浅也十年多/我在外头,父母在里头”(《清明余语》)等,互文修辞在诗歌里大量使用,赋予文本流动的语感,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汤养宗擅长用白描短句,简洁传神,或古典长短句节奏,“春日宽大,风轻,草绿,日头香/草木欣荣,衣冠楚楚”(《春日家山坡上帖》),或用叠字形成音节反复,“又一路向东。向东。向东。汇入在,南中国海”(《中国河流》),这些白描语言新奇而雅洁,在音乐的节奏中控制并推动主体情感的发生变化。
汤养宗的诗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拒绝了抽象的悬空式说教,以鲜活、传神的口语叙述筑就其诗歌坚实的细节肉身,为阅读者提供了细致、可靠的情感元素,这是汤养宗中国传统诗歌观念在西学激活之下的探索,也是对现代文明中人的复杂情感的一种呼应。
二、“人间”在场者的生存追问
“我”在众多篇目中的出现是汤养宗诗歌的一大特色。以“我”的身体面对事物和经验,并以此获得观察世界和进入内心的角度,从而使诗歌创作始终保持在生活的第一现场。“我”的生活立场和“诗人”的文本立场之间的对话交流,使汤养宗成为一个不断向内探寻和追问的“人间”在场者。
上世纪90年代末,經济形态的多元化和社会身份的分层化促使新的文化语境的生成,个体的日常抒发与世俗审美消费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面对众语喧哗的大众审美,单一的诗歌文本表达已经无法表现繁复驳杂生活的丰富性。因此,汤养宗不断地突破主体抒情的风格与视角,转向生活事象与“我”并存的多维文本写作。如《断字碑》(2008):
雷公竹是往上看的,它有节序,梯子,胶水甚至生长的刀斧
穿山甲是往下看的,有地图,暗室,用秘密的呓语带大孩子
相思豆是往远看的,克制,操守,把光阴当成红糖裹在怀中
绿毛龟是往近看的,远方太远,老去太累,去死,还是不死
枇杷树是往甜看的,伟大的庸见就是结果,要膨胀,总以为自己是好口粮
丢魂鸟是往苦看的,活着也像死过一回,哭丧着脸,仿佛是废弃的飞行器
白飞蛾是往光看的,生来冲动,不商量,烧焦便是最好的味道
我往黑看,所以我更沉溺,真正的暗无天日,连飞蛾的快乐死也没有
诗人以“看”为联结点,让雷公竹、穿山甲、相思豆、绿毛龟、枇杷树、丢魂鸟、白飞蛾这类事物与“我”并存,代表了“看”的不同视角。上与下,远与近,甜和苦,光与暗,在相悖向度上的四组对抗形成诗歌张力,平衡了诗人内心的复杂争议,并指向生存范畴内斑驳复杂的疼痛。正如诗人所说的,“这是一种具有分裂性质的写作,它催发了事物内在隐秘性的多向度呈现”③。
随着诗人的向内探寻,这种复杂生存感受的书写开始转向更广阔的生命探寻和本质追问,比如《父亲与草》(2011):“我父亲说草是除不完的/他在地里锄了一辈子草/他死后/草又在他的坟头长了出来。”“我”的在场照亮了父亲的生存经验,来自父亲劳动经验的徒劳和来自“我”亲眼看见的徒劳,使诗人的文本立场应声而出,即徒劳无功的荒谬感。但是,到了《光阴谣》(2012),虽然“我”身处“竹篮打水”徒劳式的生活场景中,但是“我反复享用着自己的从容不迫。还认下/活着就是漏洞百出”,这个立场甚至是一种“顺从”或“欣然领命”。由此可见,潜藏在诗歌文本立场之下的不是诗人对命运的嗟叹,而是转向个体的对抗精神“从得曾从未有,到现在,不弃不放”。
作为“人间”在场者,诗人认识到存在的荒谬与苦难,但他似乎更强调个体抗争的精神,追求在坚定对抗的过程中显示生命的光辉。“天下没有不可公开的地址,哪里都是一堆/残羹冷炙”,但是“不死的依旧是我们身上的艳骨”(《举人》),在不断向内挖掘和追问的过程中,诗人在更高层面上与世界达成和解。
三、以诗论诗的书写策略
以诗论诗,是汤养宗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书写策略。在他的诗歌中,往往交织着两条线索。一是以各种艺术手段介入的诗性书写,二是反观写作自身的思辨书写,形成了诗歌的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这两个层面在诗歌中并非以固定的姿态呈现,而是以动态的方式相互交织、相互关联,形成诗歌形式和内涵上的完整。
发现和寻找两个层次之间的关联性词汇,是进入这类书写的通道之一。比如在“我管写字叫看管/一只或一群,会嘶鸣”(《象形字》),“我归顺自己的文字,会写诗、热恋着自己手中的母语,血对上血一般对人说/请你闻一闻我身上的香气,汉语散发出来的香气”(《在汉诗中国》,“我节省,一直靠自己很小的方言读字/靠舌头下的喃喃自语”(《我的舌头我的方言》),这些诗歌几乎都指涉到“字”“词语”这些字眼。表层上它们从专业指称变成书写的对象,深层上则是反思古典诗词向现代诗转变所带来的文化上的演变、生存及新的可能性,并明确中国诗歌的根脉是深藏在民族、民间的骨血之中。此外,“大象”“线条”“蒙面人”等这类隐喻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关联性词汇,隐秘度更高。“大象”暗喻传统经典的诗歌写作,“线条”喻指多维叙事的形状,“蒙面人”喻指诗人努力探寻的诗歌秘密,等等。对这些关联词汇的深度理解,正是打开汤养宗多维诗歌的秘密钥匙之一。
以寓言诗话实现诗人创作态度的自我构建,这是理解汤养宗诗歌的另一条通道。文本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有很多,但作家的创作态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从《纸张》(2001)到《立字为据》(2011),再到《悬崖上的人》(2013),在诗歌里躬身自省使汤养宗重新恢复了一个作家对文字的敬畏与担当,进而构筑其诗学审美精神中最坚实的质地。“我立字,相当于老虎在自己的背上立下斑纹/苦命的黄金,照耀了山林,也担当着被射杀的惊险”,“立天地之心,悬利剑于头顶,严酷的时光/我不怕你,我会先于名词上的热血拿到我要的热血”(《立字为据》),掷地有声的寓言式图景中潜藏着一个对作品质量有着高度要求的创作者的态度。这份凛然与自信是基于诗人长期艰苦卓绝的诗学探索,“他们在悬崖上练习倒立,练习腾空翻/还坐在崖边,用脚拨弄空气,还伸出舌头/说这里的气温适合要死不死”,透过这个寓言图景的表层,诗人与古往今来的精神探险家有了相似的姿态,他们在精神上彼此交融,相互坚定“倒立于崖顶,在那里试一试冷空气/我的决绝九死一生。那迷人的深渊”(《悬崖上的人》)。
在变幻万千、纷繁复杂的现實生活面前,诗歌创作是选择世俗趣味的迎合,还是以出色的文本创新实现对社会精神的审美引导?汤养宗选择了后者。多年来,他的诗歌以不断追求新质的包容姿态面向“人间”,从而获得了感受世界的丰满,逐步呈现出艺术的成熟。
注释:
① 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② 汤养宗:《一个人大摆宴席》,见《汤养宗集1984—2015》,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页。
③ 汤养宗:《去人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286页。
作者简介:许陈颖,宁德师范学院语言与文化学院,福建宁德,35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