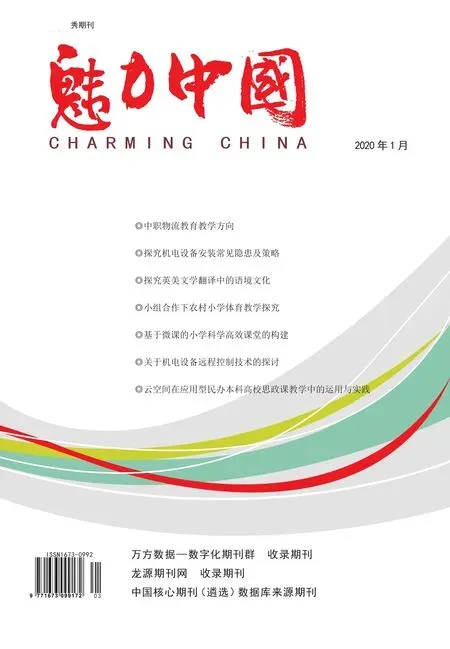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华旭科
(浙江省慈溪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慈溪 315300)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一直是一个不为人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立法依据和理论研究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来,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才在我国逐渐展开,并在这短短几年间以爆发态势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信息被非法传播和使用的案件层出不穷,侵犯个人权利,危害人们的尊严和自由,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大数据时代下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刑法等所构建的法律体系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也实为必要。
一、大数据时代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现状
个人信息这一法律保护体系始于刑法。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由于信息交流的媒介的原因,对个人信息的侵害相对较少。因此,我国的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对此类犯罪并未通过刑法条文进行规定,直到《刑法修正案(五)》才首次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写入刑法条文。2005年《刑法修正案 (五)》的修订,首次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但只是限于对信用卡保护条款,即第177条规定的“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为了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修订,将“犯罪主体由特殊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增设了从重处罚的规定,并将本罪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了七年有期徒刑”。刑法的准确、顺利实施离不开相关民事制度的支持,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逐步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制度,以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二、我国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之完善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良好的沟通与协调,发挥刑法的谦抑性
在合法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应当形成一种平衡的张力,在价值冲突下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这也正是秩序、正义与自由、效益等价值之间冲突的表现。“刑法保护社会关系中最具有公共性和重要性的利益,使得刑法的适用具有最后性”,既作为整个法律规范体系有效性的最后保障而存在,也作为其他法律部门力度不足性的补充而发挥作用,因此,刑法的谦抑性成为制定司法解释与司法适用的基本指导精神。
(二)通过行业自律,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收集和使用是个人信息开发和利用的两个主要环节。通过行业自律对行业内涉及的个人信息行业进行行政指导。引导重点行业和龙头企业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制定个人信息开发和利用规则。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管理机制,节约社会公共管理成本,努力从源头上进行管理,并将刑法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最后屏障。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进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门立法,明确个人信息概念和范围、信息主体权利义务、信息保护的原则、罪名体系和要件以及法定刑等内容规定,对于解决我国信息保护难题、保障信息安全秩序有重大意义。
(三)清晰界定行为方式,明确划分行为后果
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某类新型犯罪行为,应当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归类总结,提炼出最一般的行为模式,给予刑法评价。本文认为,对于何谓情节严重的考量,应当在参考与本罪具有等值性法益的犯罪基础上进行。本罪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民主权利的客体之内,并位于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之后,因此,它的情节危害性与上述各罪具有相当性,可以考虑将多次侵害个人信息、滥用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给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重大财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致使某一领域的社会秩序混乱以及其他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重大利益损失的行为认定为情节严重,使司法工作人员在适用本罪时有具体的参考标准,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情节严重中的情节,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的情节,只要有一方面情节严重,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应构成犯罪。”
(四)健全我国现行的法制体系,注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国际效力
为了适应新常态,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适当修正公民人权保护有关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的保护条款。在民法刑法以及相关法律的内容修改中,更加明确界定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细则和侵害行为构成的违法犯罪的惩罚措施。使得我国的社会会主义法制建设与时俱进,内容进一步完善,体系更加健全,不断增强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能力。
三、结论
针对大数据时代的公民个人信息侵害行为越来越多,违法犯罪手段不断更新,在实施法律保护方面存在相关内容有较多盲点和空白的情况下,进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公民个人信息侵害的刑法保护研究,符合社会发展和法制体系健全的需要,对有效保护公民的人权,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有积极的作用,希冀构筑起民事、行政、刑事立体化的规范体系。大数据时代为个人信息的盗用倒卖和非法使用提供了许多便利优势,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因此,要在刑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修正过程中,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条款,作最详尽的表述,明确犯罪主体和客体的确定方式和条件,力求做到保护有方,打击到位,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显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