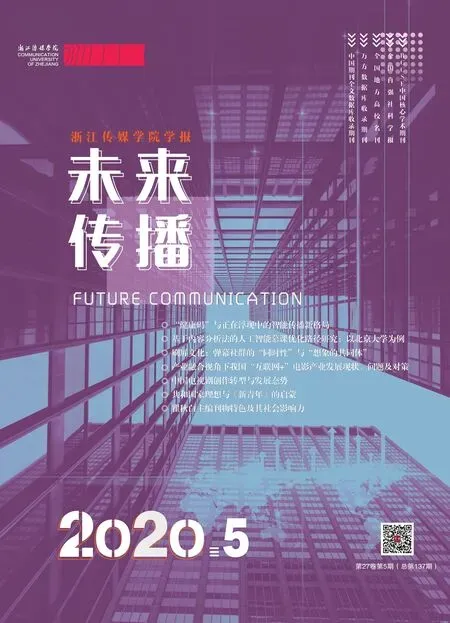中国电视剧创作转型与发展态势①
严 勤
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戏剧与影视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电视剧年度蓝皮书》,通过网上近10万人次的投票,以及学界业界50位顶尖专家学者(1)50位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如下:陈奇佳、陈犀禾、陈晓云、陈旭光、陈阳、戴锦华、戴清、丁亚平、范志忠、高小立、胡智锋、皇甫宜川、黄丹、贾磊磊、峻冰、李道新、李跃森、厉震林、刘汉文、刘军、陆绍阳、聂伟、彭涛、彭万荣、彭文祥、饶曙光、沈义贞、石川、司若、王纯、王丹、王一川、吴冠平、项仲平、姚争、易凯、尹鸿、俞剑红、虞吉、张阿利、张德祥、张国涛、张卫、张颐武、赵卫防、周安华、周斌、周黎明、周星、左衡。的最后票决,共推选出2019年中国电视剧10大影响力作品,它们分别是:《都挺好》《长安十二时辰》《在远方》《小欢喜》《庆余年》《外交风云》《破冰行动》《陈情令》《老酒馆》《奔腾年代》。这些入围的电视剧,既有献礼新中国70周年的革命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外交风云》,也有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行业巨变的现实主义题材剧作《在远方》《奔腾年代》;此外,都市题材剧《都挺好》《小欢喜》,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陈情令》,年代剧《老酒馆》,涉案剧《破冰行动》等,均以其丰富的故事内涵以及高标准的制作完成度,激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和收视狂潮。与此同时,在新媒体技术日趋成熟的背景下,诸如先台后网、台网联动以及先网后台等多种播出模式的探索,都为互联网语境下中国电视剧的传播拓展了新的空间。中国电视剧创作,正从产业化以来的数量增长转型为新时代的高质量增长。
一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信息,2019年全国生产完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共254部10646集。这些剧目中,现实题材剧依旧唱主角,共计177部7004集,分别占总部数、总集数的69.69%、65.79%;历史题材剧目共计73部3475集,分别占总部数、总集数的28.74%、32.64%;重大题材剧目共计4部167集,分别占总部数、总集数的1.57%、1.57%。[1]
为了更清晰地厘定国产电视剧的发展态势,我们不妨从近来备案公示的电视剧数量中寻找端倪。从备案公示的部数来看,2018年较2017年的变化不大,2019年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其备案部数较2018年下降22.2%,总集数下降24.8%。与此同时,相对于2018年,2019年生产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数量同样呈现下滑态势:总部数下降21.7%,总集数下降22.6%。近三年获准发行的电视剧平均集数分别为:2017年42.9集/部,2018年42.5集/部,2019年41.9集/部,平均每年缩短0.5集/部。
很显然,2019年电视剧供给侧改革仍然在进一步深化。2018年纳税风波和收视率造假给国内的影视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资本热钱因此迅速撤退。据统计,2019年以来,关停的影视公司达1884家。[2]资本市场中,电影第一股华谊兄弟营业利润为-375797.29万元,比2018年同期下降337.09%;(2)详见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快报。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首次出现年度亏损,2019年亏损约12.95亿元。(3)详见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预告。产业调整带来的冲击与阵痛体现在电视剧生产与创作中,则是2019年电视剧产量与总集数与2018年相比下降近三成,打破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
耐人寻味的是,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近年来卫视平台收益也日渐下滑。2019年第一季度,“新剧仅占所播剧目的二成左右,和一季度拍摄制作的电视剧数量相比,更是仅占13.8%。”[3]据统计,2019年黄金档电视剧有实力维持高比例首轮播出率的仅北京、东方、江苏、湖南、浙江和山东6家卫视,大多数省级卫视已无力支撑购剧成本,往往采购播出二轮、三轮甚至多轮剧作,因此加剧了全国电视剧的供需矛盾,中国电视剧产量下滑,是行业冲击导致的被动调整。同时,中国电视剧追求高质量的作品创作,说明制作公司力图通过内容创作的品质提升以赢得自救与突围。
二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诸多献礼片展播中,创新成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基调。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外交风云》首次将镜头全方位地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间波澜壮阔的外交历史,可谓填补了该题材的创作空白。剧作浓墨重彩地抒写了诸如炮击英国“紫金石号”、毛主席访苏、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周恩来访非、中法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尼克松访华、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当前中国在“后全球化时代”中践行“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剧作所叙述的这段历史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中学时期的历史教科书,还是新闻、纪录片等影像资料,都对这段历史进行过非常翔实的记载与描述;但是,通过电视剧创作如此全景式地展现这段历史还属首次。这段历史跨越年代之长、涉猎事件之多以及人际关系之复杂是以往的重大题材电视剧未曾经历的,尤其是如此众多的领袖人物的汇聚一堂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上也尚属首次。该剧所面临的创作与审查的双重压力可想而知。编剧马继红在多个场合都曾提及:外交题材对很多创作者来讲,那是一个令人仰止的高地,那是一片让人寒颤的禁地,但同时它又是一片散发着迷人芬芳的圣地。[4]
马云在《无处不在:快递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曾指出:“快递企业从零开始,短短几年内已经有7家上市公司,这是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是数百万名风里来、雨里去的快递员的付出,是所有物流从业者的共同努力。正是这样一群普通人,撑起了全世界最庞大、最复杂的物流系统,撑起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在传统商业模式中,行业经销商的层次壁垒,限制了绝大多数人的创业可能,互联网时代的快递业则打破了行业的屏障,每个人都有可能借助互联网和快递实现自己创业的人生梦想。电视连续剧《在远方》以敏锐的艺术触觉,在国产电视剧中第一次将镜头聚焦于创造中国互联网经济奇迹重要力量的快递行业,“剧作在叙述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创业史的同时,将人物故事与时代洪流融合兼顾,把个人的创业传奇,升华为时代的精神象征。”[5]剧作在勾勒宏大时代背景的同时,并非孤立地叙述“非典”“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等历史事件,而是巧妙地将铭刻这个时代记忆的历史事件与个人的命运相结合。如在“非典”时期,走家串户的快递业面临严峻考验,但是主人公姚远不但没有退却,反而与命运抗争,咬牙给员工加工资,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当然,《在远方》的时代精神,更重要的则在于编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快递这一物流经济模式所带来的人们日常生活状态和思想精神层面的巨大冲击和改变。姚远所经营的快递业从不规范的草根团队发展到与国际电商相爱相杀的大公司,所折射的恰恰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创业传奇。
电视剧《奔腾年代》,聚焦于新中国电力机车这一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行业题材,努力展示一代知识分子尊重科学、勇于创新的奉献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剧作在男女主人公这一人物关系的架构上,借鉴了“欢喜冤家”这一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出身于资本世家、毕业于西方名校的年轻工程师常汉卿,与平民出生、从朝鲜战场上凯旋归来的战斗英雄金灿烂,两者在文化修养乃至性格上显然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两人在开始相遇时充满了一种喜剧性的碰撞与误会;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金灿烂开始被常汉卿对科学技术的执着、严谨和爱国奉献精神所打动,而常汉卿也日益被金灿烂的热情、善良、淳朴性格所吸引。在正常的生活轨迹中两个原本不可能相互理解的年轻人,却因为建设新中国的电力机车而相识相亲相爱。值得注意的是,《奔腾年代》在叙述新中国发展史时,并没有回避历史的敏感话题,而是以其艺术的勇气直面历史。剧作中留苏归国的政治部主任冯仕高,痴恋金灿烂而不得,转而以各种“帽子”打压常汉卿,并不顾科学精神,盲目追求高速度,酿成电力机车因温度过高而燃烧毁坏的大祸,冯仕高甚至因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可以这么说,《奔腾年代》或许在创作上仍有可进一步商榷之处,但是剧作在讴歌时代进步的同时不失对历史的反思力量,其所达到的艺术敏锐度和思想高度,是近年来国产电视剧中极为罕见的。
作为著名编剧高满堂“老”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力作(前两部分别为《老农民》和《老中医》),电视剧《老酒馆》在开拍之初,就广为瞩目,正如导演刘江所言,“高满堂这是把压箱底儿的宝贝拿出来给我拍了”。作为“老”字三部曲的压轴之作,《老酒馆》延续了高满堂作品一贯的平民史诗的风格,但是,不同于前两部剧作以“农民”“中医”为名的个体聚焦,《老酒馆》着眼在“酒馆”这一封闭空间里的人物群像叙述。剧作以1928—1946年的山东大连为背景,讲述了以陈怀海为首的关东山淘金者,来到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大连好汉街开酒馆谋生的故事。在剧作中,老酒馆恰似一方戏台,各色人物轮番登场。陈怀海们在这儿迎来送往,以“酒、菜、人”待八方客,见证了一个动乱年代的恩义江湖。《老酒馆》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剧作通过贯穿的角色人物以大量细节连缀成多线索的交错叙事,来带动情节的发展。这种叙事策略,与以老舍原作改编的电视剧《茶馆》颇为相似。《老酒馆》中,以陈怀海为首的主线人物,与三爷、雷子、亮子、老蘑菇、半拉子等人物一道,将老警察丛队长、侠盗金小手还有贺掌柜贺义堂等人的故事缝合起来,描摹出一幅幅生动丰富的民国时代的世俗风情画。
三
近年来,都市题材剧可以说一直都是收视的热点,涌现出了《蜗居》《我的前半生》《美好生活》等爆款级作品。电视剧《都挺好》,聚焦于原生家庭给个体生命所带来的相互折磨和心理创伤这一话题,所塑造的苏大强这一电视剧荧幕上罕见的“问题父亲”形象,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长期以来,诸如《激情燃烧的岁月》《父母爱情》《父爱如山》等电视剧叙事文本,父亲基本上占据着核心的权威位置;但是,在《都挺好》这部剧中,苏母却占据了强势的主导地位;作为父亲的苏大强,则处处遭受妻子的压制,一切都要看苏母的眼色行事,基本失去一家之主的位置。在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时,苏大强往往选择逃避。苏明玉遭受来自哥哥和母亲不公平的对待,试图从父亲苏大强那里获得帮助时,苏大强却转身离开。苏大强能力的欠缺,体现的是其父亲形象的失能;妻子过世后,苏大强一改往日在家中唯唯诺诺的形象,倚仗父亲的身份在几个子女之间搬弄是非,甚至无止境地勒索子女,其行为已经近于失德。很显然,《都挺好》苏大强这一形象引起的广泛争议,无疑是意味深长的。正如有评论指出,“家庭剧中,父亲几乎是不可缺少的男性符号形象。然而,缺位的父亲、无力的父亲却消解着传统父权制逻辑下父亲形象的权威。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对父亲身份的焦虑,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现代社会父亲的退化、父职的空缺。”[6]
电视剧《小欢喜》延续了《小别离》的主创班底,同样聚焦于三个家庭在应试教育背景下的喜怒哀乐,以应试教育为视角探讨都市社会家庭的亲子关系命题和社会关系。因此,从《小别离》到《小欢喜》,其矛盾冲突的戏剧内核没有变,改变的只是剧中孩子们的年龄,由一群中考生变为了高考生,剧作的矛盾也因此显得更为尖锐。在这个意义上,《小欢喜》可以说是《小别离》的2.0版。一般认为,由于传统文化、就业竞争和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国内中考、高考的应试教育,通过高强度、高竞争、高控制的题海训练,以及追求升学率的高压管理,迫使每一个人都在这种应试机器中超负荷地高速运转。因此,《小欢喜》之所以在国内引发话题争议,不仅在于该剧描摹出一幅高考语境下中国式家庭“浮世绘”,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激发了改革开放以后参加高考的第一代,在“第一次做父母”之后,在“高考”这一历史与现实的场域中,如何与孩子相互博弈、共同成长。《小欢喜》以小事件、小人物和小情爱的视角展开叙事,直面早恋、性教育、自杀、抑郁等敏感话题,以小视点折射出了家庭生活的日常悲欢,从中年危机、二胎、职场风波、卖房、租房、离家出走等这些看似俗套的情节中挖掘出一种温暖人心的情感底色。小说原著的作者鲁引弓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小欢喜》不渲染焦虑,这是创作前我们就达成的观点。我们要从纠结着的高考家庭中去寻找一些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小小欢喜’,从苦中找到解开问题的钥匙,给大家温暖一下。”[7]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信念,该剧虽然直击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焦虑与痛楚,但始终带着小小的欢喜,充满着对生活真实、友善和美好的向往。
近年来,网络剧制作逐渐呈现出高端化、电影化、工业化的发展态势,形成了“高标准、高规格、高投资、大场面、全明星”的高概念制作模式和创作追求。投资高达6亿的大制作《长安十二时辰》,在制作上运用了互联网思维,“对相关大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对于预设观众采取有预谋的“定向爆破”。据历史文献记载,唐代长安城实行宵禁,唯有上元节全城解禁联欢。《长安十二时辰》以此为逻辑起点,注意借鉴美剧《24小时》的叙事模式。剧作的叙事假定主人公张小敬必须在十二个时辰之内缉拿恐怖分子,才有可能解救长安城里的黎民百姓。在这样的语境中,《长安十二时辰》中反复出现的日晷镜头,强调由于时间流逝而日益扑朔迷离的案情和日益焦灼的人物情绪。随着张小敬的办案历程,剧作将镜头深入长安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冷暖色调来分隔现实和回忆的时空,构建出一个立体的大唐“长安”气象,既让观众目睹了大唐盛世的繁华与喧闹,也让观众窥探到辉煌灿烂后面的暗流涌动、阴暗绝望。由于剧情本身主题宏大、线索错综复杂,《长安十二时辰》在展现狼卫破坏长安城这一主干线索的同时,还穿插叙述了林相府、元载与王毓秀、闻染等众多人物的副线脉络,从而与主线形成了一种节奏的变化。主线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前推进的同时,副线以日常性甚至是抒情性场景来控制节奏。这种多线并进的叙事方式,将错综复杂的线索在网状结构的情节中铺开,以建构一种忽明忽暗的叙事张力。在时空的处理上,剧情以现实时空为主体,嵌入崔六郎带入狼卫的时空、旧历23年烽燧堡战役的时空、闻无忌在世时的时空等过去时空。这些过去时空,主要通过现实时空中人物的回忆来插入。例如,随着案件的推进,张小敬的多次回忆,让原本人物、情节关系复杂的烽燧堡战役线索变得更加清晰,从而实现了过去时空事件与现实时空正在发生事件的相互照应。
从玄幻小说衍生而来的玄幻剧,业已成为中国网络剧的新类型。当前流行的玄幻剧,其时空观、种族观和生死观所架构的世界观,明显继承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同时又结合青年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结构加以改造和创新。玄幻剧将古老东方神秘文化与现代的审美想象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魅力。2019年热播的《陈情令》,改编自“墨香铜臭”的小说《魔道祖师》。《陈情令》的改编不仅保留了原著小说中的众多“名场面”,还借助剪辑手法给予受众一定的想象空间。电视剧本身融合了重生、修仙、武侠、鬼怪等多种猎奇元素,但也注入了丰富的现实寓意。由于原著具有明显的“耽美”情结,《陈情令》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采取了“双男主剧”的叙事模式,一方面保留了原著那种若有若无的暧昧之感,满足“她”经济下女性观众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刻意地将双男情感升华为兄弟之情,体现出网剧对主流文化的妥协与认同。应该承认,《陈情令》改编策略,契合了网剧分众化、多元化的审美体验,结果不仅在国内引发了收视狂潮,而且作品远销泰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多国荧屏,并被Netflix收购海外发行权。
作为搭上2019年全年古装剧末班车的《庆余年》,是一部改自于网络同名穿越小说的网剧。剧作将小说原有的穿越想象,改写成文学专业学生的小说创作,以此保留小说原著的穿越审美意味。剧作中主人公范闲这一人物塑造,之所以充满戏剧的张力,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私生子,为解决身世之谜而身不由已地卷入了皇家的权力斗争,具有鲜明的悬疑风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带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储备,却意外地闯入古代江湖而“玩转”历史。剧作以“现代思想与古代制度的碰撞”为论点,以“假如生命再活一次”为主题,不仅完整保留了原著架构在范闲这个人物身上的现代元素,更是在电视剧的开篇就点名了该剧的意义所在。该剧的主题可以引用第一集的一句话进行概述:“每一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想过重活一次,因为人生总是有太多遗憾,所以这故事真正的意义是珍惜现在,为美好而活。”
因为网剧崛起,网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构,传统的先台后网播出模式逐步让步于网台同播,甚至先网后台。如《亲爱的,热爱的》于2019年7月9日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首播,并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播出;《破冰行动》于2019年5月7日在爱奇艺播出,5月10日在央视八套播出;《庆余年》首播于腾讯视频、爱奇艺,然后在浙江卫视播出……可以预见,随着5G时代的来临,网台互动和媒体秩序变更,都将深刻影响中国电视剧的题材形态、内容创作和传播方式。2020年疫情的爆发,在院线电影整体沉寂近5个月之久的日子里,更是凸显了电视台和网络平台传播的独特优势。网络独播的《我不是余欢水》《鬓边不是海棠红》、网台同播的《如果岁月可回头》《清平乐》等剧作的流行,都意味着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与传播,正处于一个深度变革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