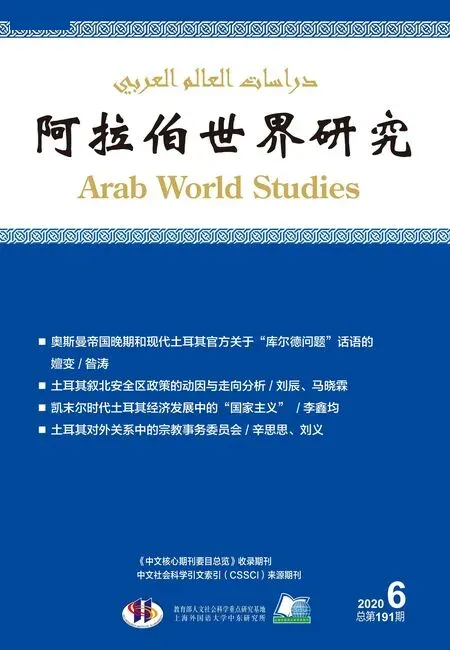奥斯曼帝国晚期与现代土耳其官方关于“库尔德问题”话语的嬗变*
昝 涛
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3)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02,p.121.在福柯看来,话语不只是涉及内容或表征(representation) 的符号,而且被视为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也就是说,虽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问题不仅仅是运用特定符号指称事物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更多、更为复杂的关系与实践,话语理论就是要揭示和描述这种复杂性。(4)Ibid.,p.54.福柯的话语理论着力于分析话语的对象、陈述、概念与主题选择等是如何进行的,它们的顺序、对应、位置、功能和转换是怎样发生的,进而揭示隐藏其后的权力—知识共生关系。(5)Ibid.,p.41.关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参见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1-122页。
在土耳其,尽管“库尔德问题”很重要,但长期以来它并非一种明确且客观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至少存在两个层次:一是客观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即认定库尔德问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存在,进而从现实问题的不同角度去切入和讨论;二是主观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即对所谓“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对某个问题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对相关问题基于不同视角的看法和话语,这些话语不只是对所谓客观存在的“库尔德问题”的符号性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某种符号/话语建构起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权力—知识关系。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这表现为握有更多权力(包括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对“库尔德人”与“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建构和处置。也就是说,话语必然会反映出主体力图以何种方式或政策来对待和处理客体,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实践)或说(表述)。因而,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话语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政治—权力实践的建构和表达。
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现在,土耳其国内形成了多种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认识(6)土耳其学者阿尔坦·谭总结了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五种认知路径:(1)不存在库尔德问题;(2)库尔德问题是一个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3)库尔德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4)库尔德问题是一个种族认同问题;(5)库尔德问题是一个国族问题。参见Altan Tan,Kürt Sorunu,Istanbul:Tima Yaynlar,2014,pp.15-16。和话语。对这些认知和话语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本文仅从较为有限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观察、描述与分析。同时,本文更为关注话语的转变而非具体的政策过程,故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详细分析,对具体的事件和过程则作相对简略的处理。
一、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人世代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7)关于库尔德人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参见Michel Bruneau,Küçük Asya’dan Türkiye’ye:Aznlklar,Etnik-Milli Homojenletirme,Diasporalar,translated by Ayhan Güne,Istanbul: letiim,2018,pp.148-149。,今天则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个国家境内。库尔德人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诸多差异,部落库尔德人和没有形成部落的库尔德村民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显著不同;库尔德语的两大主要方言之间几乎无法沟通;库尔德人还存在逊尼派、什叶派、耶济德人(Yezidiler)(8)耶济德派(Yazidism)是一种很古老且独特的一神教,靠其内部的圣人口传,在很多方面与中东地区的其他宗教存在共通之处,包括密特拉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参见Nadia Murad,The Last Girl,New York:Tim Buggan Books,2017,pp.5-6。之间的宗教差别。经过民族主义的洗礼,尽管各种差异仍然存在,但库尔德人现在已经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


19世纪后,为应对国内外民族主义威胁,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发展出一种可以被视为国族主义的“奥斯曼主义”(Osmanlclk)。(14)关于奥斯曼主义,参见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3-126页。简言之,就是开始赋予帝国境内的臣民们平等的公民权,所有人不论宗教或民族出身,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不能说这种主张没有吸引力,但从历史大势来看,民族主义已然兴起,而奥斯曼帝国由于自身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落后,越来越无力应对国内外的危机和威胁,因此帝国改革派所提出的这种主张和政策也无法挽救帝国。奥斯曼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项错误的政策,更大程度上是大势所驱。在奥斯曼主义之外,帝国晚期还发展出了一种主要是针对穆斯林民众的泛伊斯兰主义。这种主张出现的背景在于,俄国和欧洲列强不断以宗教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尤其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基督教领土的丧失,相应地境内穆斯林人口比重迅速上升,加强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也就日益重要了。(15)昝涛:《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3期,第101-102页。
19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这要求终结帝国中央与边缘那种传统的松散状态,过去“因俗而治”的政策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也意识到,以游牧—部落生活方式为主的库尔德地区,作为帝国的边缘向来就是不稳定因素。因而,如何掌控和利用这股力量,就成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改善地方治理时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16)如杜贵(Duguid)所言,“库尔德人是这个地区的潜在危险因素,需要做的是,要么完全镇压它;要么就纵容和讨好它,同时还要维持对其宽松的监控。”转引自Selim Deringil,“From Ottoman to Turk: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in Dru Gladney,ed.,Making Majoritie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22.就库尔德地区来说,奥斯曼政府自“坦齐麦特”(17)原意为“改革”“整顿”,指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时期以来,越来越不愿意让库尔德人实行“自治”,但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导致习惯了自治的边疆地区出现了反抗和叛乱。1840年~1847年间,库尔德地区就出现了叛乱。(18)Latif Tas,“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516.帝国政府进行了镇压,并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到19世纪80年代,库尔德人的半自治地位不复存在。
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年~1909年)出现了强调锻造帝国主体人口的论调。这种论调主张以土耳其人为核心,逐渐将其他穆斯林人口吸收进来,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等,这个主体人口将成为帝国可靠的元素,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锻造这个主体人口的两个途径就是教育和参军。(19)Selim Deringil,“From Ottoman to Turk: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pp.220-221.帝国政府之所以努力同化库尔德人,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就是,库尔德人长期被认为是“潜在的土耳其人”(müstakbel Türk)。(20)转引自Latif Tas,“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517.
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创立的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哈米德军团(Hamidiye Alaylar),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利用和拉拢库尔德人对抗亚美尼亚人的产物。(22)除了巴尔干地区,挑战帝国权威的内部非穆斯林分离主义的重要势力是亚美尼亚人,俄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也很大。Selim Deringil,“From Ottoman to Turk: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pp.222.当时,随着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情绪逐步高涨,东部地区日益不稳定,哈米德二世在库尔德人中组织了一个非正规军军团,目的就是让他们来协助帝国稳定当地秩序。(23)Caroline Finkel,Osman’s Dream: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p.502.在历次镇压亚美尼亚人的运动中,库尔德人的哈米德军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帝国政府的另一个考虑是,通过赋予库尔德人权力来约束他们,并期待其更加效忠于中央政府。(24)Ibid.此外,帝国依然坚持传统上排斥和打击什叶派的做法,逊尼派库尔德人的哈米德军团会被鼓动去打击什叶派的库尔德人。(25)Latif Tas,“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517.这再次表明,在对待不同族群时,宗教差异对奥斯曼帝国至关重要。帝国的目标始终是将库尔德人吸收为可靠的、能够维系帝国的力量,也就是拉拢和利用库尔德人。
从哈米德军团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晚期针对库尔德人的政治话语主要还是宗教性的,其政策框架是奥斯曼主义,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系奥斯曼帝国。有学者认为,哈米德军团这一体制设计具有双重影响,首先,在帝国晚期强化了库尔德人的部落认同,从而延缓了其民族意识的发展;其次,部落学院的教育以及在战场上的经历,培养了一批具有开阔视野的库尔德人精英,为后来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做了人员上的准备。(26)Selim Deringil,“From Ottoman to Turk: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p.226.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哈米德二世之后,改哈米德军团为部落军团(Airet Alaylar),但也有青年土耳其党的重要人物考虑把军团的名字改为“乌古斯军团”,这反映出土耳其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上升。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奥斯曼帝国针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是土耳其化,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只是外衣,实行土耳其化才是实质。关于此类观点(27)参见Latif Tas,“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p.499-500.,笔者认为此论有失偏颇,原因在于,虽然长期来看土耳其化可能是一个趋势,但维系奥斯曼帝国、强调伊斯兰的团结并不只是口号,而是帝国晚期政治精英的真实目标。或许可以说,19世纪末以后,土耳其化在发展,但在20世纪初阿克楚拉写作《三种政策》(28)Yusuf Akçura,Üç Tarz- Siyaset,Ankara:Türk Tarih Kurumu Basmevi,1976.的时候,土耳其化还没有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
二、土耳其民族运动期间的“库尔德问题”
到20世纪初,族群之间的差异更加清晰,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也在发展。被送到伊斯坦布尔接受教育和监视的库尔德精英们,在接触到民族主义思想之后,也发展出以对库尔德斯坦土地认同为基础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并成立了多个库尔德人组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库尔德精英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库尔德进步与互助社”(Kürt Teraki ve Teavun Cemiyeti),但随着大战的爆发,这些库尔德精英也上了战场,其组织趋向涣散。战争结束后的1918年12月17日,“库尔德进步与互助社”的部分成员参与创立了著名的“库尔德斯坦复兴社”(Kurdistan Teali Cemiyeti)。该组织在库尔德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巨大反响,一些著名的库尔德家族人士、宗教人士以及教育界人士都参与其中。该组织的目标是“捍卫库尔德人的利益”与“支持民族事业”。(29)Felat Özsoy-Tahsin Eri,Öncesi ve Sonrasyla 1925 Kürt Direnii,Istanbul:Peri Yaynlar,2007,pp.28-29.除了库尔德斯坦复兴社,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库尔德人的组织相继建立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虽然库尔德精英已经有了库尔德民族认同,但他们在政治主张上却是分散的,有的希望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有的则支持奥斯曼帝国哈里发,在广大库尔德民众中,民族主义更不是主流。由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主要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离库尔德地区太远,即使他们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也没有多大政治影响力,更多地从事社会和文化活动。有学者因此认为,库尔德斯坦复兴社很难被视为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组织。(30)Felat Özsoy-Tahsin Eri,Öncesi ve Sonrasyla 1925 Kürt Direnii,Istanbul:Peri Yaynlar,2007,pp.29-30.

当时,土耳其民族主义人士对帝国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是有清楚认知的,但捍卫帝国统一是主流,库尔德人是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在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内部,争论主要是围绕“奥斯曼”“土耳其”“穆斯林”这几个身份而展开。19世纪末期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日益上升,也在安纳托利亚的革命阵营中有明显表现,突出体现在“土耳其”身份的使用。革命阵营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故意采取了模糊策略,避免让这些争论削弱自身的团结和力量。(33)Howard Eissenstat,“Metaphors of Race and Discourse of Nation:Racial Theory and State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in Paul Spickard,ed.,Race and Nation:Ethnic System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4,pp.239-256.即尽可能地把不同表述并列放在一起,以满足团体身份的多样性。因此,其在使用“民族”(millet)一词时加上了多样化的定语,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和“穆斯林”等等。最常见的则是把“土耳其”与“穆斯林”一起使用,以使大多数人都能满意。尽管他们对这些术语的具体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可以达成共识,即安纳托利亚的斗争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是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带有“圣战”的色彩,这正是当时的话语选择所欲达到的效果。在更具宗教色彩的话语之下,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库尔德的民族身份,都暂时退居了次要地位。
在1920年5月1日一次激烈的议会辩论中,来自锡瓦斯的代表埃米尔帕夏(Emir Paa)力图说服其他人放弃“土耳其(人)”这一术语,因为他觉得“土耳其(人)”不能体现安纳托利亚革命运动的广泛性。而有的代表则认为他在玩文字游戏,有的则说“土耳其(人)”与“穆斯林”是相等的,没有必要放弃,但是埃米尔帕夏说:“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建立了哈里发制度……我要求我们不仅以土耳其的名义行动,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以土耳其人的名义聚集在这里。我请求你们,说穆斯林甚至是奥斯曼人要比说土耳其人更为合适。在我们的故乡有高加索人、车臣人、库尔德人、拉玆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人民。让我们不要以一种分裂的方式来言说,那将使(这些群体)被排除在外。”(34)Howard Eissenstat,“Metaphors of Race and Discourse of Nation:Racial Theory and State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in Paul Spickard,ed.,Race and Nation:Ethnic System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4,p.246.
实际上,埃米尔帕夏所提出的关于民族身份与国家关系的问题非常重要,但在当时只能以回避的、妥协的或者模棱两可的方式解决。针对埃米尔帕夏所引起的争论,凯末尔一方面承认并非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被包括在他们所宣称的民族边界内,另一方面他宣称革命运动是安纳托利亚所有穆斯林的运动,包括高加索人、库尔德人、拉玆人和其他很多群体。凯末尔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也回避了埃米尔帕夏的关切:如果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捍卫“穆斯林”的权利,那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土耳其人”这个词?(35)Ibid.,p.247.
凯末尔对民族身份问题采取不争论的态度,实际上是为了平息无谓的争论,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上来。(36)笔者无意暗示凯末尔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建立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明确意识。实际上,在独立运动早期,凯末尔很少使用“土耳其人”(Türk)这个词,即使他偶尔说到“土耳其”(Türkiye),也是在与“奥斯曼帝国”同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民族身份问题一直以模糊不清的状态存在着。1920年9月,在一场有关让非穆斯林志愿者参加国民军的辩论中,“土耳其人”被等同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这个词语对立使用。(37)Howard Eissenstat,“Metaphors of Race and Discourse of Nation:Racial Theory and State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p.245.同年10月,在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中,有一个议员发问道:“难道土耳其人与穆斯林不是同一回事吗?”一位代表这样回答:“当一个人说自己是土耳其人的时候,他就是穆斯林……欧洲人也把伊斯兰世界称为土耳其啊。”(38)Ibid.,pp.245-246.欧洲人的确长期把奥斯曼帝国称为土耳其,而土耳其这个词在欧洲人那里也经常是被等同于穆斯林/伊斯兰的领土。因而,在“土耳其等于伊斯兰世界”这样模糊的意义上,这一回答被多数人所接受。
但在民族主义迅速上升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构建中的民族身份问题所引发的争议日趋无法回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土耳其民族主义最终占据了上风。1920年9月13日,凯末尔和部长委员会共同署名提交了一个包含三十一条内容的新宪法草案。该草案开始的“目标与原则”部分共包括四条,其中第一条中有“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用语,即原来“大国民议会”的名称前加入了“土耳其”(Türkiye)(39)1920年1月,凯末尔谈到威尔逊的计划时,提到土耳其国家就用了“Türkiye”一词。参见Enver Ziya Karal,ed.,Atatürk’ten Düünceler,Ankara:ODTÜ Yaynclk,1986,p.3.一词。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建立或者已经被建立了,它的名字就叫“土耳其”。在此过程中,反对者曾力图用“奥斯曼帝国”来取代“土耳其”,但他们没有成功。
但是,当时拟定宪法的秘密委员会(Encümen-i Mahsus)反对凯末尔等人的做法,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这一术语在委员会宣言中得以保留,但在宪法文本中未出现“土耳其”一词;在1921年1月10日通过的新宪法第三条中,“土耳其国家”(Türkiye devleti)也仅使用了一次。1921年宪法宣布大国民议会的目标是“苏丹—哈里发的独立与解放,以及祖国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40)有关1921年宪法的论述参见November 10,1994 State Ceremony Speeches and Atatürk and Turkish Identity Panel,Translated by Serap Kzlrmak,Ankara:Atatürk Research Center,1999,pp.34-36。“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词首次出现在宪法中是土耳其建国后的1924年了。
考虑到“土耳其”一词具有与伊斯兰世界等同的模糊性,其种族—民族主义的特性也并不是那么强烈。但当其涉及到土耳其穆斯林与非土耳其穆斯林的分类时,它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特性就必然会凸显出来。在土耳其的语境下,国名虽然是土耳其(Türkiye),但族名被统一为土耳其人(Türk),这就意味着,非土耳其人的其他族群日益难以被接受。这种内在矛盾不是今天才被人所知的,在历史上确定国名和族名之时,那些当事者对此就已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历史(暂时)没有沿着多元主义的道路前进。这是后来土耳其很多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而当代土耳其正处在努力调整历史轨道的时期。
从民族认同的视角看,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主要面对的是土耳其民族主义。(41)土耳其民族主义其实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国族意义上的,即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的问题;二是种族意义上的。Türk原本是作为一个种族-族群的名称,同时也被土耳其官方确定为国民身份,即土耳其人或土耳其国民。换言之,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库尔德问题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历史与现实政治框架。因此,要了解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首先必须对土耳其民族主义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42)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参见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基于种族特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土耳其人是奥斯曼帝国境内获得民族意识比较晚的群体。如前所述,直到奥斯曼帝国事实上已经崩溃的独立战争时期,“土耳其”一词还只是在模糊的意义上被使用,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当时也未成为普遍的共识,它只是当时部分精英秉持的思想观念。
土耳其民族意识的出现,一方面涉及到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其他的穆斯林,因为族裔意识是在对比的情境中建立的。如前所述,在独立战争期间,库尔德人的身份已被认识到,同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有人反对使用土耳其这一概念和身份,而土耳其与库尔德等身份是并置的。正如当代土耳其学者所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恰纳卡莱战役以及民族独立战争中,库尔德人是维护国家统一的,西方的煽动并没有影响到这一点。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凯末尔等将领与库尔德人一起工作,强调“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共同奋斗”,在1919年的埃尔祖鲁姆会议的决议中提到,包括库尔德地区的东部省份不能从奥斯曼帝国分裂出去,强调与库尔德人是“亲兄弟”(öz karde)关系。(43)Felat Özsoy-Tahsin Eri,Öncesi ve Sonrasyla 1925 Kürt Direnii,p.54.第一次大国民议会与1921年宪法中提到,库尔德人是国家平等的伙伴、光荣的公民和主人。(44)Mahmut Akpnar,Kürt Sorunu ve PKK Nereye Gidiyor?,Ankara:Edge &Elhan Kitap Yayn 2015,p.24.在当时,凯末尔等人使用的是土耳其,在指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时,他们用的也是领土—人民意义上的土耳其国民(Türkiye halk),而不是具有种族特性的土耳其人(Türk halk)。这都说明当时土耳其的政治话语还是可以(暂时)平等地认识和对待库尔德人的,并承认库尔德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是土耳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一部分。
三、凯末尔主义的“库尔德问题”话语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1924年宪法与第二次大国民议会不再提库尔德人及其语言、文化和权利,不再把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并列,而是只提“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民族”。1924年宪法第88款指出,“土耳其人民(Türkiye ahalisi)不论宗教与种族之差异,在公民身份上都被接受为土耳其人(Türktlak olunur)”(45)Altan Tan,Kürt Sorunu,p.16.。当时有议员质疑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是否可以被称为土耳其人,建议不用土耳其人,而是使用更具国族性质的土耳其国民,但这个主张最终还是被否定了。最终被坚持的主张是,除了土耳其人之外,国家不承认其他的民族(millet)。(46)Altan Tan,Kürt Sorunu,pp.16-17.这成为此后多年土耳其官方针对库尔德人的正式话语。

可见,随着民族斗争形势的好转以及后来统一民族国家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之前较为平等地对待库尔德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具有种族特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占据了上风,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这成为土耳其官方对库尔德问题的主流话语。

除了正面地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强调土耳其的单一民族特性之外,库尔德人的行动也强化了这种趋势。由于将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捆绑在一起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苏丹—哈里发,尤其是哈里发所代表的宗教统一。随着苏丹制和哈里发制的废除,库尔德人的梦想破灭了。共和国建立之后,关闭宗教学校、字母改革、强制土耳其语教育等猛烈的世俗化措施使库尔德人受到了巨大冲击,而库尔德人最反对的就是新国家废除和改变了宗教机构与原则。换言之,这些现代化变革打破了库尔德人与新国家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纽带,相对封闭和传统的库尔德人难以接受新的国家秩序。
不断发生的库尔德人叛乱使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更加强化了单一民族国家的主张和政策,并在单一国族认同之外排斥其他的亚身份,除了土耳其认同之外,库尔德、拉兹、切尔克斯等认同都被认为是需要被废除的错误的观念。而“土耳其史观”和“太阳语言学说”等官方支持的伪学说,也同时服务于否定或抹杀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土耳其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1876~1924)曾经提出的理论在此时被利用和宣扬,即库尔德人其实是对自身没有认识的土耳其人,他们是“山地土耳其人”,而且绝不接受库尔德语。(49)Michel Bruneau,Küçük Asya’dan Türkiye’ye:Aznlklar,Etnik-Milli Homojenletirme,Diasporalar,p.211.关于土耳其官方坚持此种话语的原因,有学者解释为当时激进的西方化改革遇到了阻力和反抗(50)Kemal Kilici,“Minority/Majority Discourse:The Case of the Kurds in Turkey,” in Dru Gladney,ed.,Making Majorities,pp.238-239.,而库尔德人的反抗是最令人头疼的,因此针对库尔德人的话语不是种族认同问题,而是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对峙,其目的在于推倒阻碍现代化的反动落后势力,为国家的进步扫清障碍。事实上,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起义在当时也的确是主要围绕宗教问题,而不是以库尔德主义为中心的。(51)Mahmut Akpnar,Kürt Sorunu ve PKK Nereye Gidiyor?,pp.24-25.

到了多党制时代,尽管有关库尔德人的一些禁忌被取消了,但对库尔德人权利的限制仍然持续存在。1960年的军人政变后,虽然军方主导颁布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但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还是罢黜了很多库尔德领导人。政变后上台的军人总统杰马尔·古尔塞勒(Cemal Gürsel)曾为一本力证库尔德人其实是突厥人的书撰写序言,他强调,“世界上能够被称为‘库尔德人’的具有独立身份的种族是不存在的。”(54)Altan Tan,Kürt Sorunu,p.17.军政府还通过新的法律,把很多村庄的库尔德名字改为土耳其语名字。随着自由主义宪法的实施,库尔德领导人针对军方的高压政策迅速出现反弹,尤其是一些新出现的组织具有更突出的库尔德种族特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组织更加热衷于讨论库尔德人的种族属性,但它们更为关心的还是阶级问题。土耳其官方很快转向了对左翼运动的镇压,但左翼运动对库尔德问题的关注极大地影响了很多库尔德人的族属认知。(55)Kemal Kilici,“Minority/Majority Discourse:The Case of the Kurds in Turkey,” in Dru Gladney,ed.,Making Majorities,pp.240-241.
1980年,土耳其共和国发生了第三次军人政变,军方痛恨之前政治和社会领域发生的动荡与分裂,转而强调基于凯末尔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国家统一,这相应地打击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表达和主张。军方的立场清晰地体现在其主导制定的1982年宪法中,政府采取的包括括禁止使用库尔德语在内的针对性举措,都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口号下进行的。为了打击库尔德认同,军方还复兴了20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些伪学说。(56)Ibid.,p.242.政变后上台的军方领导人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与古尔塞勒的观点并无二致,他强调了库尔德人就是“山地土耳其人”的既有说法,表示他们生活在雪山上,因走路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才被称为“库尔德”(Kürt),并称库尔德人主要是从中亚来的。(57)Altan Tan,Kürt Sorunu,p.18.
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坚持保守的话语和立场,但这并不能否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也无法阻止人们讨论这一问题。除了左翼的重要角色之外,一些重要的土耳其领导人如厄扎尔(Turgul Özal)、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等人,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6月,厄扎尔称自己很可能有库尔德血统,这最终为土耳其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开辟了道路。1991年4月,对库尔德语的禁令被取消。(58)Kemal Kilici,“Minority/Majority Discourse:The Case of the Kurds in Turkey,” p.243.在厄扎尔时代,他重启了一个新的国民身份方向,即不再将国民称为土耳其人,而是土耳其国民,即在国名的基础上,把土耳其的公民和国民身份定义为“来自土耳其的人”,这才是真正公民或国民意义上的土耳其人。甚至有人建议干脆把土耳其国名改为“安纳托利亚”。当然,这种界定此时仍处于争论之中,受到了来自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挑战,被指责为分裂土耳其国家。

德米雷尔的这个总结非常重要,他以过来人和亲历者的身份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土耳其共和国官方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话语及其变化。即在1990年前土耳其共和国并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而德米雷尔改变了这一状况。当然,这不包括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因为在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凯末尔党人最初是承认库尔德人存在并积极争取库尔德人的。德米雷尔解释说:“我说‘库尔德人之存在’时,指的是有库尔德人,我是说我们接受这一现实。这说明了什么呢?也就是说存在库尔德人,但他们是土耳其国民(Türk vatanda)。无论如何,土耳其人并没有必要都来自突厥种族(Türkrk)。当然也有属于突厥种族的土耳其人,但土耳其这个词有超越于种族涵义之上的意思。这是一个民族的名字(milletin ad)。而这个民族的定义并不依靠于种族。土耳其民族的含义即在于此。”(61)Ibid.
库尔德地区一直也是土耳其国内无法忽视的欠发达地区,从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角度说,是需要重点投资和关注的对象。因而,从发展或经济的角度来重构库尔德问题也成为另一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它关注的是国家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投入。这一点由于不直接涉及民族认同问题,不再赘述。
四、正发党的库尔德“新思维”
历史地看,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做出最重要改变的就是2002年上台执政至今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62)关于其具体立法和政策,可以参见Ioannis N.Grigoriadis,“Türk or Türkiyeli?The Reform of Turkey’s Minority Legislatio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Ottomanism,”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3,No.3,2007,pp.423-438。而正发党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话语并不是一致和连续的。作为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发党偏好于通过强调伊斯兰话语争取库尔德人的选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的确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除了强调宗教因素作为共同纽带外,正发党还强调自身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受害者身份,“我们也是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军队的受害者,我们的受害程度并不亚于库尔德兄弟。一旦我们掌权,我们的优先选择就是对国家重新定义,解构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63)转引自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问题的演进》,第24-25页。这种话语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争取选票的需要,而真正掌握了政权之后,正发党需要做的更多。在话语建构方面,2005年埃尔多安的重要演讲代表了正发党当时的库尔德新政策。
2004年,土耳其总理办公室下属的一个工作委员会——“少数族群与文化权利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主要主张是建议使用土耳其国民这个身份符号,使其成为国族认同,而土耳其人则降低为一个族群身份。该报告自然还是招致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但得到了大量媒体、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64)Ioannis N.Grigoriadis,“Türk or Türkiyeli?The Reform of Turkey’s Minority Legislatio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Ottomanism,” p.425.在此基础上,2005年8月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土东南部重要城市迪亚巴克尔发表了其“民主宣言”,这可以称得上是土耳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新思维”。在迪亚巴克尔演讲之后,土耳其国内舆论界对埃尔多安的“新思维”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赞扬欢迎者有之,批评抗拒者有之,充满期待者亦有之。值得关注的是,埃尔多安演讲一周之后,库尔德工人党(PKK)宣称“单方面停火”一个月,以等待政府的新政策。此后土耳其舆论界的反响更为强烈,一时间各种评论和争辩风起云涌。
只有了解埃尔多安的“新思维”以及土耳其国内对此产生的不同意见,才能理解当前土耳其人在解决国内少数族群问题及反恐问题上的话语和主张,以及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感知当代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 “更多的民主”:埃尔多安“新思维”的提出
2005年8月12日,埃尔多安访问了土东南部重要城市迪亚巴克尔,这里是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核心聚居地,也是齐亚·格卡尔普的出生地。埃尔多安在这里发表了被土耳其媒体称为“民主宣言”的著名演讲。在土耳其人看来,该演讲的发表意味着土政府对解决库尔德问题以及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主义问题提出了“新思维”。埃尔多安的演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强调库尔德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重要问题。埃尔多安说,“(库尔德问题)不仅涉及到我们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所有问题都与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无论他们是突厥人、库尔德人、拉兹人、阿布哈西亚人,还是切尔克斯人。这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含义。”
第二,强调必须通过建设性的思维来解决库尔德问题。埃尔多安主张,要在共和国原则与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更高的民主、更多的权利和更大的繁荣来解决这一问题。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将继续深入下去,直到每个公民都感觉到自由,“我们将永远不会让民主衰退。”
第三,强调必须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埃尔多安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旗和我们的共和国是神圣的,我们以此为荣。暴力和恐怖主义是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而且我们将永远不会宽恕它们。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诉母亲和父亲们,我们这个国家将使你们的孩子免受恐怖主义之苦。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才是你们要找的、解决你们问题的人。”

虽然埃尔多安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还讲了很多其他的细节,但重点就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埃尔多安访问迪亚巴克尔的两天前,他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15名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这次会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产生了一些争议,但在土耳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这是国家高级领导人首次公开而诚恳地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
(二) 关于“新思维”的争论

虽然埃尔多安的演讲具有突破性且十分老练,但依然出现各种争议和批评意见。在经历数天的喧嚣之后,土耳其国内开始从他热情洋溢的演讲中冷静下来,媒体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例如,《国民报》(Milliyet)的一篇评论指出,埃尔多安的演讲是“危险的调情”。作者认为,埃尔多安并不明白问题所在,而“对手(指库尔德政治组织)却十分明白,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期待,即大赦、语言教育、降低选举条件、清除政治限制、向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开放政治参与道路……”(67)Melih Ak,“Tehlikeli Flört,” Milliyet,19 2005,sayfa 14.。《自由报》(Hürriyet)的涂番·图兰赤(Tufan Türenç)也列举了库尔德政治组织的要求,并质问埃尔多安在演讲前是否经过深思熟虑。他还对埃尔多安有关将库尔德工人党与爱尔兰共和军作类比表示批评,“爱尔兰共和军停止恐怖主义活动,乃是英国多年来坚持抵抗他们的结果。土耳其的领导人应该明白,在涉及国家重大问题时,他们必须三思而后行。”(68)“Press Scanner:From the Columns,” Turkish Daily News,August 20,2005.其实埃尔多安为自己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并不是如有关评论家所说,库尔德工人党可以无限地提出要求,如果埃尔多安做不到的话,就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反对党坚持其一贯的批评思路。土耳其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领导人拜卡尔(Deniz Baykal)严厉批评了埃尔多安的“新思维”,称政府当前的反恐政策是错误的,民主的方式决非答案。关于库尔德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土耳其的问题,土耳其专栏作家费克莱特·比拉(Fikret Bila)的一篇文章分析得很透彻。比拉指出,现在库尔德人的重要政治组织实际上都与奥贾兰有密切关系,那么,他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土耳其呢?“……土耳其共和国要么给予库尔德人想要的独立公民权以及(宪法)立法权,要么不给。前者意味着,他们合法的身份认同被接受下来。共和国的文化存在与政治主权有赖于库尔德人的认可。这种认可必须依赖于相互间合法的保证。”(69)Fikret Bila,“Kürtler Açsndan Nasl bir Türkiye?,” Milliyet,19 2005.
2005年8月20日,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单方面停火”一个月,以作为对埃尔多安“新思维”的回应。但土耳其国内关于反恐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土耳其人普遍反对与恐怖分子谈判。2005年前后,土耳其国内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军方为代表的“强硬派”,他们认为对付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坚定的决心进行武力打击,直至消灭恐怖分子。除军方之外,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坚持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决不能与恐怖主义妥协,更不能与之谈判。二是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民主派”,他们认为恐怖主义不只是个军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主义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库尔德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更深入的民主化”。(70)“Kürt Sorunu Benim Sorunum”.
继1993年土耳其领导人公开承认了“库尔德现实”(Kurdish reality)之后,此次是土耳其总理第一次力图说出全部的事实,即土耳其存在“库尔德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埃尔多安演讲中所说的“国家的错误”,遭到有关评论的质疑。埃尔多安所说的“国家的错误”,实际上是指以前官方不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是错误的,从逻辑上来说就是否定了凯末尔的政策。
埃尔多安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提法,遭到土耳其前总统德米雷尔的批评,埃尔多安认为他所谈的问题与以往领导人的表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德米雷尔并不这么看。德米雷尔表示自己以往的话语是:“我们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71)“Kürt Realitesini Tanyoruz”.,而埃尔多安的提法是“存在库尔德问题”(72)Ibid.。德氏认为,他的说法与埃尔多安的提法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他没有将库德人视为问题:“在种族上,您可以说自己是突厥人、库尔德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而在此之上的身份乃是土耳其人,即属于土耳其民族。区别就在于此。但是,当以‘库尔德问题’代替了‘库尔德人之存在’时,您就是在说另一个问题了。您把民族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接受了。从这个角度看,我所说的与埃尔多安讲的不是一回事。”(73)Ibid.
在迪亚巴克尔的讲话中,埃尔多安说:“迪亚巴克尔跟安卡拉、埃尔祖鲁姆、孔亚以及伊斯坦布尔一样重要。每个国家都会犯错误,忽视以前所犯的错误决非一个大国应该做的事情。一个大国和一个强大的民族是应该能够面对它的过错并以更强大的姿态面向未来的。这是我们的政府所坚信的。”“我曾经因为引用了一首诗而入狱,我那时就相信我向我的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在那个信息中我说:‘我没有对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或者愤怒。这个国家和这面旗帜是我们的。纠正这些错误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有些人问我,‘库尔德问题将何去何从?’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74)“Kürt Sorunu Benim Sorunum”.埃尔多安还表示,忽视一个问题将意味着不尊重整个民族,每一个公民都理应从政府那里获得最好的东西。国家在东南部的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教育。在演讲的最后,埃尔多安说:“我将以一位诗人的诗句(75)这个诗人名为贾希特·塔兰奇(Cahit Taranc),诗名为《我想要一个国家》。来结束我的演讲,这位诗人曾呼吸过迪亚巴克尔的空气。”(76)“Kürt Sorunu Benim Sorunum”.
(三) “新思维”之后
埃尔多安上台时曾经对库尔德选民许下宏伟的经济发展愿景,但是这些目标大多没有兑现,与中东部土耳其人聚居的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之虎”的新兴城市相比,库尔德地区的发展乏善可陈。实际上,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政府多年来是希望解决库尔德问题的,甚至曾准备与库尔德工人党实现全面和解。可以说埃尔多安的“新思维”开启了与库尔德人的十年和解进程。但这个所谓的“和解进程”遭到了多方压力,最终双方都失去了耐心,和解走向失败。
2005年之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还在库尔德问题上提出过一些重要的“话语”或政策。2009年,土耳其政府公布“库尔德开放倡议”(Kürt açlm),该倡议对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权利等作出了某些保障性规定。(77)“The Kurdish Opening in Turkey:Origins and Future?,” Carnegie,December 1,2009,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09/12/01/kurdish-opening-in-turkey-origins-and-future-event-1494,登录时间:2020年10月22日。2011年11月23日,埃尔多安在议会进行了1个小时的演讲,公开承认并为土耳其政府20世纪30年代所杀害的近万名库尔德人道歉。(78)“Turkey PM Erdogan Apologises for 1930s Kurdish Killings,” BBC,November 23,2011,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5857429,登录时间:2020年10月22日。与本文提到的“新思维”关系最密切的是2015年3月23日埃尔多安在新落成的总统府就民族和宗教关系发表的重要演讲。(79)“Kürt Sorunu Yoktur;Kürt Kardelerimin Sorunlar Vardr,” TCCB,March 23,2015,https://www.tccb.gov.tr/haberler/410/29843/kurt-sorunu-yoktur-kurt-kardeslerimin-sorunlari-vardir.html,登录时间:2020年10月20日。埃尔多安从1071年的曼齐克特战役谈到20世纪初的土耳其独立战争,回顾了土耳其族同库尔德族长期形成的兄弟情谊,指出两个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关系。埃尔多安通过这篇演讲正式“收回”或者“修正了”他的“新思维”演说中的提法。他表示,自己在2005年讲的是“库尔德问题”(Kürt meselesi),土耳其不存在“库尔德难题”(Kürt sorunu)(80)根据当时的土耳其新闻报道看,埃尔多安讲的就是“库尔德难题”(Kürt sorunu)。,库尔德人在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包括土耳其族在内的其他公民也会遇到,并不因民族身份而具有特殊性。库尔德族是共和国诸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各个民族的首要身份应该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埃尔多安明确指出,民族是聚合在“同一片屋檐下”各个种族的共同体概念(Millet,her türlü etnik unsuru aynçataltnda toplayan bir kavramn addr),“土耳其民族”包括土耳其、库尔德、切尔克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等36个民族。埃尔多安进而提出“四个独一”理念,即“一个民族、一面旗帜、一个祖国、一个国家”(Tek Millet,Tek Bayrak,Tek Vatan,Tek Devlet)。
从“新思维”提出至今,埃尔多安党人的库尔德问题话语出现某种逆转,或者说是收缩,这与形势变化有关。收缩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向主体民族的主流观念靠近和调整,把“库尔德问题”说成是“库尔德事务”就是最重要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尔多安党人回到了凯末尔主义的老路上,共和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单一民族(族群)话语,已经转变为超越狭义族群身份,进而强调广义国民身份(Türkiyeli)的话语。这种话语的源头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但比较多的讨论应该是在厄扎尔时代,而在埃尔多安时代,这已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趁机崛起,库尔德工人党将其重要力量转移到了叙利亚。(81)王新刚主编:《叙利亚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版,第102-103页。土耳其一方面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的政治主张,不承认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支持叙利亚北部反对派武装与叙政府军抗衡;另一方面土耳其仇视和警惕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认为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都是“恐怖组织”。(82)同上,第100页。2015年7月,埃尔多安明确表示不接受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建国。与其同时,“民主联盟党”呼吁中东地区所有库尔德人保卫再次受到“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科巴尼,随后库尔德工人党也进入叙利亚支援“民主联盟党”,土叙两国的库尔德势力开始更为显著的合流。(83)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一些叙利亚库尔德人试图联合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以获得后两者的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土耳其尤其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主张。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叙利亚库尔德人最终走上与其他两国库尔德人不同的道路,即在承认国家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寻求自治。参见王新刚主编:《叙利亚发展报告(2019)》,第110页。
在国内人民民主党(HDP)崛起,以及土叙库尔德人合流的大背景下,埃尔多安政府开始出手打击国内外库尔德势力。2015年,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持续十年的所谓“和解进程”破产。在为期两年的停火结束后,土耳其政府表示不会再与库尔德工人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土耳其官方对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话语重新回到了国家安全优先的轨道。
总体来看,埃尔多安在2005年的主张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它仍代表了土耳其对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和话语的重大进展。正发党时期,虽然奥斯陆和平进程和伊姆拉勒和平进程都失败了,但也留下了厚重的历史遗产,代表了当代土耳其人在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上的积极探索。
五、结语
土耳其是库尔德人口最多的国家,库尔德人在土耳其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其占据了土耳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数量高达1,470万人左右。(84)“Son Nüfus — Dünyada toplam kaç Kürt var?,” Rudaw,June 15,2016,https://www.rudaw.net/turkish/world/150620169,登录时间:2020年10月25日。尽管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土耳其人就试图同化库尔德人,但并没有实现,反而强化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库尔德人的存在一度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他们的身份被抹杀和压制,但这个问题无法永远地隐藏和搁置下去。在进入民主化时期之后,土耳其必然要面对库尔德问题,以往被压制的这一问题就逐步凸显出来。
从历史视角来看,土耳其政府为解决库尔德问题做了很多尝试,先是强硬同化,后来采取民主和发展的策略。正发党政府尤其强调运用民主的手段,口号就是“用更多的民主解决民族问题”。从结果来看并没有成功,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既涉及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同时又触动了主体民族的敏感神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从国族主义向认同政治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或许是一个日益强调多元主义的时代难以摆脱的宿命。但土耳其又有其特殊性,尤其是表现在族称和国民身份上的长期混同。争论的各方各执一词,孰是孰非,难有定论。
福山指出,身份政治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国家和世界造成了巨大伤害,并呼吁重建国族认同以应对这一挑战。(85)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Vol.97,No.5,2018,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tribalism-francis-fukuyama,登录时间:2020年10月25日。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是近代历史的两个重要主题。前者主要是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其扩散带来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并直接导致传统帝国纷纷崩溃与解体。然而,一族一国这样的民族主义逻辑并没有随着传统帝国的消失而失声。因为世界上只有200个左右的主权国家,而能够被称为民族或族群的群体却成千上万。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对峙格局暂时淹没了民族主义这个“病毒”的扩散,但在过去三十年里,以民族-宗教为载体的认同政治又在世界各地纷纷崛起,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也说明,既有的民族国家体系消化民族问题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困境。因此,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反思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特别是其在此问题上的话语演变及其得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