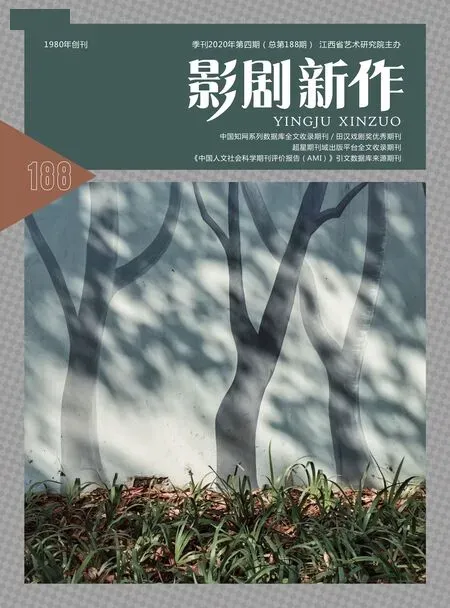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互文性结构
周重横
2020年8月,红色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江西艺术中心连演三场,场场爆满,足见其人气和票房号召力。这部出品于2018年,由上海歌舞团精心打造的革命历史题材舞剧,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满堂喝彩,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培养了众多的粉丝。同时,它还获得了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可以说是既赢得了奖杯,又赢得了口杯。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从艺术上说,也许从互文性角度可以一窥其中成功的奥秘。
互文性一词首先是由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词语、对话和小说》(Word,Dialogue and N o v e l)中使 用“互 文性”(intertextualité)这一术语的,她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后来罗兰·巴特把它发扬光大,将其运用于文化符号学研究。互文性理论给我们的提示就是认为文本是开放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动态转换的过程。文本在文化环境中不断地生产和消费,读者的接受和感受文本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文本不断地获得新的含义。文本获得意义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用互文性理论来解读《永不消逝的电波》,是红色经典不断地得到阐释,在不同时代不断获得意义的过程。
一、构建不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
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前,就有产生于不同年代的不同艺术形式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最早的是电影版《永不消逝的电波》,它出品于1958年。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硝烟尚未散去,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素材由国家安全部一位了解李白烈士生平的人士提供的,经过编剧艺术加工而成,因此影片片头字幕的编剧用的是一个化名。电影的导演王苹曾经在旧上海生活过,对旧上海的生活场景十分熟悉,主演孙道临为了拍好李侠这个角色,向老地下党员请教,力求形神兼备,刻画的形象要能让人信服。电影现实主义的视角与英雄主义的情怀,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十分吻合。通过电影版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我们可以领略到那个年代精神的纯粹、信仰的纯真。
电视剧版《永不消逝的电波》出品于2010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故事有了新的解读,赋予了新的内涵。当时的荧屏上流行“潜伏”的主题,《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作为地下工作者与“潜伏”主题相吻合,编创者看到了其中的流行元素,进行了艺术再创造。这一版的故事在李侠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上下足了功夫,刻画细腻,内容丰富,充分发挥了电视剧故事容量大的优势,并填充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代的流行与思考。此外,总政歌舞团在2011年出品了歌剧版本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出品于2019年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时代背景下献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作品,它突出的是艺术气质与地域特色,全剧制作精美豪华,利用了影像的手段辅助叙事,舞蹈动作唯美动人,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要。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全剧既延续着对于英雄的崇敬与赞美,也张扬着新时代精神下的文化自信。全剧给人以坚定凝重感,有一种直逼人心的力量。正如剧中所言:唯爱与信仰永存!舞剧版《永不消逝的电波》把谍战、地下斗争升华成爱与信仰的力量,找到与当下观众对话的契合点。剧中的原型李白烈士就义的时候,距离上海解放仅剩7天,他倒在了黎明的前夕。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利用舞剧的形式来纪念他,引领观众走进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与那个年代进行对话,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同年代的“互文结构”。它如同一声声电波,在两个时代间传送,这就形成了深远的历史质感。
二、构建不同艺术形式间的互文性
从电影、电视剧到歌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构成一个链条,形成相互阐释的互文性结构。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充满了惊险,通过惊险气氛的营造来突出李侠的勇敢与机智。它的冲突的中心在于李侠去上海获得并向中央发报报告日蒋勾结阴谋的情报。它的斗争是没有战壕没有炮火的地下战线隐秘的战争。片中的李侠性格深沉,动作从容,“深沉”成为他身上突出的特点,这种“深沉”不仅体现在行事的沉稳上,还体现在他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体现在他对党的忠诚、对人民深沉的爱上。他的这种性格,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他作为隐秘战线上的报务员,作为无名英雄,其从容不迫的个性,是在血与火中考验出来的。同时,他对待同志亲切温厚,对待妻子爱恋有加。电影作为影像的艺术,它的叙述完整清晰,交待了李侠离开延安的恋恋不舍,每个情节观众都能看得清楚明白。电影用了明暗两条线索,一条明线是敌我残酷的斗争,一条暗线是李侠与何兰芬的情感线。在电影的前半部分,突出的是李侠与何兰芬的感情;电影的后半部分,突出的是斗争。两个部分的前后景互换,正是电影的巧妙之处,有张有驰,焦点不同,观众的感受就不同。“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是李侠最后留下的话,也成为了经典独白,在以后的作品中被一再提及。
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内容更为丰富,扩充了情节,把斗争扩充到整个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的整体格局中,在人性的刻画上下功夫,尽可能地去深入英雄的内心世界,努力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英雄。面对不同时代的观众审美需要,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注重人物的多面性与丰富性,挖掘情节的内涵与深度,做到了既遵循传统的精神,又有新的突破。虽然在一些问题的探索方面,做得并不完善,但为后来的改编提供了借鉴。
在编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前,编剧罗怀臻就反复观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从中寻求灵感与突破。他说:“剧本创作之初,当我重新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时,我觉得这个故事确实缺少舞蹈性,舞剧的演出必须把故事发生的空间打开,所以我设计了几个电影里没有出现的重要场景:第一,是李侠由杂货铺的小老板变身为报馆职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报业很发达,几十个人坐在一个大厅里办公,就像今天的职场,演员可以在其中完成舞蹈。第二,我设计了一个上海的旗袍店,里面五光十色,能够体现上海女性的风情,但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报联络点。第三就是石库门,李侠夫妇的重要活动场所。这就是剧作家带着思考给舞剧编导提供的腾挪空间。人物的身份变了,由杂货铺的小老板变更为报馆职员,特地为舞蹈设计了新的场景 ──上海旗袍店,这些巧妙的设计为舞蹈开创出了新天地,为舞剧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报馆的场景设计既可以突出旧上海的地域特色——报业的发达,也可以为群舞腾挪出空间,制造出迷离的气氛。旗袍能彰显东方女性的独特气质与不一样的美,能给舞剧带来新的样貌和辨识度,让观众一看就明白,这讲的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罗怀臻这样表述舞剧“电波”的艺术气质 :一种阴郁的,但是同时里边又有一种温暖的东西 ;是城市既是猎场、深林,又是七情六欲的一个现场。这也是我们对一座城市的真实印象。舞剧既阴郁又温暖的艺术气质的形成得益于报馆与旗袍店的巧妙的场景设计与美轮美奂的舞剧设计。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形式侧重于惊险性,利用影像的剪辑与巧妙的前后景处理,营造跌宕起伏的氛围,突出了英雄“深沉的爱”。其电视剧形式侧重于人性的刻画,试图还原英雄的方方面面,让新时代的观众更容易去接受。而舞剧形式突出艺术气质,塑造迷离气氛,它克服了舞剧拙于叙事的缺陷,用独特精到的视角与身体语言,讲述了英雄的痛苦与忧伤,也讲述了英雄的豪情与无畏。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形成了一个网络,互为影响,互相成全。有的观众因为看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想去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有的观众看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意犹未尽,就想着去看电影与电视剧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却有相同的基调,那就是对于英雄的赞美。李侠对党忠诚,对人民充满深沉的爱,这是不同形式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一以贯之的人物特点。意义的形成就是不同形式的艺术间接力,一环扣着一环,传统得以继承,革命精神不灭。
三、构建不同舞蹈语言的互文性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部谍战剧,跌宕起伏,充满悬念,舞剧为了充分还原原剧的气氛,巧妙设计符号化的舞蹈语言,符号化的身体语言间构成了一张象征之网,互相间映衬补充,形成了互文性的空间。上海弄堂的幽深,裁缝店的紧张,繁荣的街道,繁忙的报馆,都用身体语言来实现。
剧中的独舞都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人物特点。李侠的身份是地下工作者,他每天隐瞒自己的身份,周旋于不同的人之间,敏捷的反应与过人的胆量都是他身上的特质,所以他的舞蹈动作设计得干脆利落,快速连贯,让人感觉一触即发,是一种随时准备着的状态。兰芬端庄朴素,不管服装设计还是舞蹈设计,突出的是她的东方女性特有的美与她性格中的温柔体贴。她是李侠的亲密战友与爱人,她的舞蹈灵巧轻盈,与李侠的舞蹈形成了良好的对比,一阳一阴,一刚一柔,让观众感觉他与她之间的世界是自洽的,他与她的爱是真挚美好的。女特务柳妮娜的舞蹈表现了盛气凌人同时又外强中干的气质,她的装扮偏男性化,体现着权力与攻击性。
剧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双人舞就是回忆双人舞。舞剧借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出现了不同的双人舞,宁静深情,含蓄蕴藉,表达了革命夫妇在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非同一般的爱情。
剧中的群舞营造了气氛,给人以视觉的唯美享受。剧情的开端,黑衣人撑着雨伞,不停地在雨中穿梭的群舞营造了阴森的气氛。黑衣人的群舞成为一种基调,在后来的舞蹈中不断地间插出现。旗袍店的群舞既展现了敌我斗争的紧张激烈,又表达了旧上海特有的风情。《渔光曲》群舞是整个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之一。这段舞蹈是从兰芬引火做饭中生发出来的,这属于她的“白日梦”。 一群女子身穿旗袍,手拿蒲扇,款款而舞,这是对人间烟火、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与眷恋。
总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利用独舞、双人舞、群舞,组成了一个舞蹈的“互文性”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