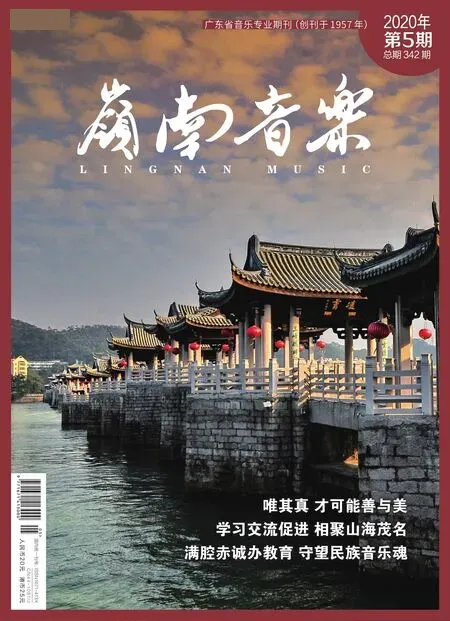生命体验与音乐艺术(上)
——曾健音乐创造本体论
文|
生命体验,显示出生命之严峻性与可能性。体验乃生命意义之不断感悟,在此不断感悟之中,本体之思考,撕裂时间母胎而把握到永恒。思考是从虚无中透射进来的澄明之光,它照亮了人生之现实世界。艺术创造,即对自己存在体验之反思与领悟。
对于从事一生音乐艺术创造的曾健先生(为叙述之便,下文均略去先生之称谓)来说,体验就是一种人生境界,身处其中,人因秉持回忆、想象、激情、温爱而将有限之生命,带入出神状态之中。曾健的此种本我体验性或体验的本我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一个永远体验与探索之过程,知识与理性乃至逻辑推理,并给我们提供现成的人生答案,答案只在每个人的寻找与探索之中,在于把握那震撼我们灵魂的人生重大困境和对生存处境的深切洞悉本真之揭示中。我们只是人生最高问题的提问者,答案在生命的真切体验中,在亲身之经历、直接之感受、心灵之慰藉与唤醒之中,体验给予我们人生思考之起点,同时又使我们关心生命意义超过关心生命状态本身。
曾健的音乐审美艺术体验,就是他的音乐艺术创造本身之呈现。曾健的音乐审美艺术因体验的激情性而显示出他的悲、欢、苦、乐,因体验的原生性而无保留地坦露出创造者心中的每一丝波澜、每一阵颤栗、每一分虔诚。音乐关乎人生,这是曾健生命之表现与传达,它表达了音乐创造者曾健的本我体验,而且表达了他生命之本真。只有音乐审美艺术体验,才使曾健不断摆脱现实世界中之平庸、虚伪与成见,曾健是带着泪和微笑去体验生命与思考人生的。
体验即本我反思与探索,体验蕴含的是他面对人生终极价值关怀的问题与痛苦追问。人生经历曲折,然而音乐艺术家曾健受同一根本痛苦的驱迫而追寻着同一个大谜底,并窥见同一本真之境。体验是开启曾健音乐审美艺术本我论之钥匙,是音乐美学本我论之根基。体验关乎音乐家曾健人生之意义与音乐审美艺术之意义。因此,我们将曾健音乐审美艺术体验作为美学本我论之重要之维加以研究,并藉此追问体验与生命、体验与音乐艺术、体验与意义、体验与世界之同一关系的问题。无疑,此已构成曾健音乐审美艺术本我之轴心。
一、体验与生命:同构同质之共生性
体验作为曾健音乐审美艺术本我论范畴,是笔者在此独立使用之概念,其主要目的是考虑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体验者与其对象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主体全身心地进入客体之中,客体也以全新之意义与主体构成新的关系。此时,无所谓客体也无所谓主体,主客体之此种活生生的关系成为体验之关键。对象对主体之意义不在于是否可认之物,而在于对象上面凝聚了主体的客观化了的生活与精神。对象的重要正在于其对主体有意义,这就使主客体关系成了“曾健个体自己的音乐审美艺术世界”了。
体验关涉曾健的有限生命之超越与现实世界价值之探索。体验打开了人类与曾健,曾健与世界之障碍,使曾健的当下存在与人类历史相遇。在体验过程中,个体绝非一个超然物外、面对客体的纯粹“主体”,同样,对象也非外在于个体之纯然“客体”。处在体验之中的个体所体验到的是:我在世界中,世界也在我中。体验表明了有限生命世界关联中之存在性,从而具有了本我之意义。
体验关乎人的生存方式,即人生诗意化问题,深层体验总是关乎人本体属性之命运、搏斗与爱憎。体验就是曾健感性个体本身之规定性,就是要使自己直面人生之真,去解人生之谜。通过音乐审美艺术体验,去把握生命之价值,通过音乐审美艺术创造活动,去穿越世界晦暗不明之现象,揭示生命之超越性意义。音乐审美艺术体验与生命之诗意化,有着非此不可之联系。音乐审美艺术把心灵从现实之重负下解放出来,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通过音乐美学的诗意化媒介,从意志的关联中提取出审美价值内核,从而在此一现象世界中,诗意地创造出反映现实世界本质的音乐艺术作品。音乐艺术创造扩展了对创造者个体释放之效果,以及个体世界体验之视界,从而满足了个体者的内在之精神需求:当命运以及个体自己的选择,仍然将自己束缚在既定的世界秩序中时,创造者的想象使个体自己臻达他永不能实现的现实境界。音乐艺术开启了一个更高更强大的审美世界,展现出一种崭新的审美远景。
现实世界不是曾健认识的对象,它是由命运带来的直接性,由命运、爱憎、遭际、诞生、重负、祝福、悲悯等组成,只有担当实名之欢乐与痛苦,才能深谙现实世界之谜,而音乐人生者必被人生音乐艺术所笼罩。体验与生命,在曾健本我论上具有一种同构同质之共生性。
了解一个音乐家的创作与个性,先得知其人,了解他音乐美学思想之大体过程与决定性因素。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其个性就是这“成心”之主要方面,它会极大地影响一个音乐家的生活态度、行事方式与创作特性。
曾健的个性如果用树木来作比,那么就是说,他既有像春天的垂柳,婀娜披拂,给人一种柔和而温顺之感觉,又有像秋天之国槐,坚刚挺拔,望之森然,显示出一种严正而凛然之气象。
一个民族,只有摆脱了外在羁绊,并吸取人类文明之精粹,创造出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这个民族才能屹立在世界之巅;一个人,只有当他成为人格独立之人,精神自由之人,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家。在音乐艺术的精神王国里,音乐家就是自己灵魂的主人,就是自己的精神创造活动的绝对主宰。
曾健出生于1936年的江西南康。自古以来,南康就是沟通中原与南粤的必经之地,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在童年与少年时代之人生境遇中,显然埋藏着曾健的精神密码,也微妙地影响着他音乐艺术创作的内在深度。所以,现实中的曾健,常常在微笑的表情中带着凝重,使人隐约看见他童年生活留下之影子。1950年,曾健在部队开始了他的文艺工作。他说:“坚守中国魂,讲好中国故事,说好中国话,树立中国手风琴学派,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抵制洋垃圾,不被异化、矮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我终生的目标!当然更需要年轻人传承下去,把这面大旗举的高高的。共同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引自曾健微信聊天记录,以下相同者不再注明。)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音乐言论,是一个自信的音乐家的音乐艺术言论。这是一个音乐家彻底摆脱了外在羁绊之后的音乐艺术创造者的宣言。它显示着曾健卓尔不群的个性与充分成熟的音乐意识。它表达着这样的一种音乐美学认知:一个民族,只有摆脱了外在羁绊,并吸取人类文明之精粹,创造出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这个民族才能屹立在世界之巅;一个人,只有当他成为人格独立之人,精神自由之人,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家。在音乐艺术的精神王国里,音乐家就是自己灵魂的主人,就是自己的精神创造活动的绝对主宰。曾健拒绝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扰与控制,既拒绝过去旧的艺术教条之束缚,也拒绝现在新的“现代主义”的拜物教束缚。他扬弃盲目冲动之意志,而使具有历史性(即体验着的)生命获得了本我论之优先地位。生命不仅仅是生物进化中之一环,生物性之规定不能解放出人的生命之谜。生命非他,是有限个体从生至死之体验之总和,是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以思悟之的解谜过程。所以说,不是任何一个音乐家都有曾健这样的强大性格,都能像他这样,敢于以“独立”之姿态,对音乐创造提出挑战,敢于以自信之态度,与一个时代流行的音乐风气相抗衡。
如果说,我们的艺术曾经被外在力量之束缚与压抑丧失了活泼的个性与内在的激情的话,那么,曾健就是挣脱了此种束缚与压抑,显示出了一种强大的个性力量与艺术生命之能量。本我论问题即曾健生命底蕴之问题,生命底蕴问题即曾健体验之向度问题。他与世界迎面走去,因为世界是他的世界;他解释音乐文本意义,因为他是音乐意义之给出者;他了解他人之表现,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深切的表达者。感性个性个体之总体世界构成了他个体之生命世界。在此意义上,曾健的生命体验即意味着超越有限性之僵硬界面之全新过程。
因此,曾健非同凡响的音乐“宣言”,使人联想到普希金的那个振聋发聩的艺术宣言。曾健致力于让音乐“坚持中国魂,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手风琴学派”,并视为自己“终生奋斗之目标”。普希金则认为,诗人自己就是艺术世界的最高主宰。普希金在《致诗人》中说:“你是帝王:你要独立生活下去/你要随着自由的心灵的引导,沿着自由之路奔向前方/致力于结成那可爱的思想的果实,不要为你高贵的功绩索取任何褒赏/它们都存在你的心中。你自己就是最高的法官/你善于比谁都严格地评价你的劳作/严厉的艺术家啊,你对它们满意吗?”(沈念驹、吴笛主编:《普希金全集》第2卷.抒情诗,乌兰汗、丘琴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50页。)在普希金看来,诗人自己就是艺术世界的最高主宰,而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则意味着一切。也就是说,音乐艺术是一种高度自律的精神活动,是心灵翅羽最自由、最自在之飞翔。没有此种最高意义上的自由与尊严,任何艺术家都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然而,这样的独立而自由的音乐意识,曾健终其一生,至少在他创作生涯之绝大部分时间里,殆未尝有一念及之。曾健的主要音乐艺术理念,庶几都是从创作实践中来。曾健既是音乐的设计师,也是音乐创造的践行者。曾健既是音乐艺术战场上的拿破仑,也是士兵,是一个像拿破仑身后的名叫阿尔芒与巴蒂斯特的法国士兵一样的士兵。曾健的音乐艺术创造是服从自我意志的创造,是有“我”的创造,是“我”的情感、思想与现实世界经验渗透到整个作品中的创造。很多时候,在对应性很强的音乐作品中,音乐造型就是作者的精神之子,就是他的人格镜像与精神投影。20世纪70年代,曾健改编创作的手风琴独奏曲《我为祖国守大桥》,就体现着他自己的态度与性格。这首著名的经典音乐作品,是人类普遍性大于时代特殊性的创作,是开放的、包容的、多样化表达的创作,也是指向普遍性的音乐创作,因而是个性大于整体化的创作,是个性与普遍性相互融合的创作。在曾健的这首独特性很强的独奏音乐作品里,作曲家的造型是大于至少是等于时代的,而精神视野则是高于时代的。在这首音乐作品里,曾健的视野和思想,是超越了时代之精神边界,也是高于时代的平均值的,甚至显示出一种超越性与超前性。因此,曾健将音乐艺术的边界,拓展到了普遍性的人性之领域,又将自己的创作,切实地提升到了现实主义与艺术之高度。曾健赋予此作品以巨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任何一个演奏者,只要他有正常的音乐艺术的体验能力,只要他渴望了解真实的士兵和真实的士兵生活,他就会对《我为祖国守大桥》这部作品的曲作者产生强烈的兴趣,就会对这首作品产生强烈的演奏冲动。就此而言,流传近半个世纪的此首独奏曲,将会在人类音乐历史的长河里,吸引无数的演奏者,并赢得他们的信任、认同与高度评价。可见,曾健的音乐艺术与人类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以致于我们认为音乐艺术本体与人的本体同构,音乐艺术就是人的生存世界。由曾健这首经典音乐作品的创造与流传,可以欣慰地告诉我们,那就是:音乐艺术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并为了人而存在,音乐艺术的中心是人的生命形式,音乐艺术是人超越生命有限性而获得无限性之中介。人通过音乐艺术体验为中介向无限超越之时,时间之流向即发生了变化。在体验之中的时间,不再像日常生活时间是由过去走向未来,而是以未来朗照现在。人携带生命之全部过去与现在进入未来之中,并以未来消融全部时间,根据自我内心所体验过的内在时间重新构筑出一个新的时空境界。此种通过音乐艺术审美所把握到的无限境界,把感性个体引出有限性之规定与局限性之存在,使之与大同觌面。这是一个绝对超越时间的世界,刹那凝聚为永恒。曾健的奥秘即在于此达到时间之超越、顿悟的同一心境。而真正的音乐、真正的艺术就能将人导入此一全新之超验世界。
二、体验与人格:主客体之互动性
每一个音乐艺术家都有自己喜爱的音乐家。这些最受喜爱的音乐艺术家,通常就是对他们的创作影响最大的人。曾健最喜爱的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外音乐家,中国的音乐家有萧友梅、王光祁、华彦钧、刘天华、黎锦晖、张寒辉、黄自、冼星海、聂耳、马可、郑律成、贺绿汀、丁善德等;外国音乐家几乎囊括了欧美所有古典音乐艺术家,诸如贝多芬、莫扎特、海顿、巴赫、勃拉姆斯、大小约翰·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德彪西等,以及现当代的一些中外音乐艺术家,不论地域性或空间距离,就音乐艺术的美学精神讲,它们是没有距离的,他们都具有崇高的音乐精神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讲,曾健帮助国人音乐爱好者克服了音乐艺术上的某种神秘感、距离感与自卑感。对中国音乐人来讲,曾健意味着光荣和骄傲,也意味着信心和力量:咱们也有了一个曾健。在曾健七十多年来的音乐创作时间里,他既属于自己的时代,也属于个人与自己的故乡。当然,健全而自然的个性化创作,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使他获得了自己的生长契机与生存空间。
一个音乐家崇拜和热爱古今中外的大师,就会接受他们的影响。中外历代大音乐家对曾健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巨大的,这从他改编创作的一系列音乐演奏作品即可见出。可以说,音乐前贤对曾健的“精神素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音乐家的人格修养与自我人格,一个是音乐艺术修养与创作技巧。对音乐创作来讲,音乐家的人格有着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义。人格境界之高下,决定了其创作境界之高下。因为,人格意味着可靠的方向感,意味着健全的伦理精神,意味着良好的善恶美感,甚至意味着雅正的美学情趣。自古及今,没有一首经典的音乐篇章,没有一部伟大的音乐史诗作品,是人格卑劣的音乐家创作出来的。就人格修养与精神境界来看,曾健实实在在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当代音乐大家。他在部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七十余年,他的业绩被编入1988年由邓小平亲自题字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中国音乐家名录》一书中。1997年,第九期 《中华手风琴之最》中说,曾健是我国手风琴界“资深、业绩突出者”;曾健是“我国从事手风琴专职演奏时间最长(47年)、年龄最大(60岁)、演出场次最多(约4600多场)”的著名音乐家;曾健改编和创作了大量手风琴演奏音乐作品,其中《我为祖国守大桥》《吹起芦笙跳起舞》《飞速前进》《欢迎叔叔凯旋归》等已成为国内外业界经典作品。他自1996年60寿辰,开始用作曲软件在电脑上撰写了三百余首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渗透了他70余载的军旅生活体验,此乃真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李商隐诗句)啊!其中,为少年儿童也编创了大量的音乐作品,电子琴独奏曲《醒狮之舞》曾在全国获得金奖,在我国少儿艺术教育事业中作出卓著贡献。这是音乐家曾健最具智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些辉煌艺术成果,并不是哪一个音乐家都可以做得出的。曾健还举办了各种形式不同的青少年手风琴音乐培训班,亲自为学员上课与演奏示范,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他曾说:“艺术的传授首先是做人,要梳理正确的人生观。遵循前人教诲,在我的演奏、创作、教学工作中,着力以人为本:演奏接地气,创作雅俗共赏,教学先教做人。以此鞭策自己,拿起手风琴这个文艺武器,作为全身心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动力,这是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说,追求生命意义之明晰性必然遇到一个困境:音乐家必须思考别人无法思考的东西,即为了意义,他必须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种界限之两边皆加以思考。曾健也意识到了此种困境。故他不谈此种划界,而是让音乐艺术本身来“说话”,以音乐的审美造型来表达此种“界限”。这就是体验的一种指向意义之活动,坚持体验中主体客体相互融合之立场,指向主客体互动所产生之意义。此种意义绝不是外在于体验活动之超验之物,而是主体在体验中通过对主客体关系之自觉与自由之呈现,在主体总体精神活动中建构起来的。主体在音乐造型(对象)之全面占有之中,将造型加以生命化,从而保证其具有完满的充实性,并反证主体给出意义之深度。可以确认,体验主体确立自身意义之世界,是获得主体性地位之保证。这就是曾健的音乐思想,也是他触及情操、灵魂体验的音乐艺术世界。此种体验是曾健将自己的知、情、意与音乐世界及其命运之遭际融为一体,在主客体互动中返身透视自己精神之内海。这是曾健内在音乐审美意义之体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生命体验。
音乐是一种和荣誉关系密切的事业。追求荣誉是创造之动力之一。完全没有荣誉感的人不可能持久地热爱艺术创作。但是,追求真正的荣誉与追求虚名浮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曾健虽然在国际国内获得过数十次的各类音乐艺术大奖,但他的“成功”与“成名”,并不在言说中,而是重在创造实践中。无论怎样说,只要创作出划时代的经典作品,那就一切均在不言中了。如他的手风琴独奏曲《我为祖国守大桥》,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评价是“经典中的经典,是中国手风琴一张闪亮的名片!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在国际手风琴大赛现场演奏时,世界一流的手风琴大师们激动地举起手臂高呼:“中国!中国。”这些权威人士发出的赞誉之声,此皆实话,绝非虚语。曾健对于荣誉与经典的理解,是他生命体验和美学表达的基本方法,他不是借助逻辑推理,而是由个体生命体验进入艺术生命之中,让整体生命意识融合在一起。他与生命相关的音乐艺术现象,皆是借助于音乐的节奏、符号、语言渗透在一起的生命表达。因此,理解荣誉与经典之传达就是理解了生命,为了达到此种深层理解,曾健是通过他的音乐符号与音乐语言中介而感受其所表达的生命本体。是的,任何一位踏实的音乐家,尤其是集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一身的音乐家,皆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而是将自己的创作,视为一个漫长而艰辛的生命体验过程。虽然曾健的“七十年一个单元”,似乎有点过长,但将他的创作丰收期设定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应该是符合艺术家创作生命成熟与成功规律的。
音乐是一种和荣誉关系密切的事业。追求荣誉是创造之动力之一。完全没有荣誉感的人不可能持久地热爱艺术创作。但是,追求真正的荣誉与追求虚名浮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在人格修养与伦理精神上,曾健受到历代前贤大师之巨大影响。接受影响之程度,决定于对影响者认知之深度。曾健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有自己的体验历程。体验、理解与传承乃是进入人类精神世界之过程,音乐历史也由通过体验、理解、传承才成为自己的现实世界之一部分。如果没有理解,便不能构成音乐的历史,精神世界便是平庸与荒芜的,就谈不上生命之可能性,表达与意义都将不复存在。因此,体验与理解活动是曾健音乐审美活动质的规定性。他的音乐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集中体现了人类体验及其理解的本质。他对中外历代前贤的人格与德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在《敬幕孔子的音乐思想》一文中说:“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孔子的音乐观点有许多论述,如:‘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指社会风气的改变与人们心灵的净化,在此方面,什么东西都比不上音乐。圣人的音乐美学观,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炽热的智慧与光芒。让人敬佩与仰慕!孔子是从道德品格层面上来论述,印证着音乐对社会的推动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这是一位真真确确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曾健对这些贴近音乐人格和精神的创作态度的揭示是深刻的。亦由此才使他的体验与音乐艺术作品得以流传与延展,使作品具有了普遍性意义,使精神世界成为具有相关性和互通性之统一体,使音乐艺术史之审美阐释成为现实。为了音乐创作,为了熟悉所描绘的环境与音乐人物造型,他深入部队基层的战士生活中,像普通战士一样为“祖国守着大桥”,盱衡九州,唯此一人耳。
曾健的音乐艺术创作是一种面向外部世界的创作。他将音乐艺术关注的焦点集中到自己身上。曾健的审美意识与音乐艺术理念,已经达到那种真正开放和包容之境界,在他身上确确实实没有半点自私自利、自怨自艾之弊。对于那些缺乏他者意识的“私有形态”之“消极创作”来讲,曾健的音乐艺术经验,确实具有指示正路之意义与补偏救弊之作用。任何艺术作品,均是作者情感、思想与人格之镜像。即便在那些叙事性、甚至爵士音乐作品里,也有一个作者的形象融汇期间。曾健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音乐是正能量的传递,是情感的投射,是心灵的倾诉,是艺术的载体,是心灵的对话。是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心灵的净化,这是我70年来音乐生涯最重要的体验与总结。”这段话,从音乐创作之角度看,它无疑是深刻的。它揭示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音乐艺术美学真理:音乐作品是作者的精神之树结出的果实;一切形式的创作,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着作者的灵魂。因此,曾健在接受音乐前贤的艺术观点之同时,他也特别强调了音乐家对自己的人格造型与灵魂的塑造问题。他在自己内心筑起了这样一种自觉意识:音乐创作上的一切均决定于音乐家自己的人格,他坚持认为艺术创造的丰硕成果,均是生命体验之结果,也是人生之感悟,是全部的生活积累与艺术的提炼。他曾很形象地比喻过自己的艺术人生,他说:“何谓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琴、棋、书、画。人生犹琴,是指音乐艺术的跌宕起伏,喜怒哀乐;人生如棋,棋局难料,迎接挑战;人生似书,字体有宋、楷、行、草;字犹人,是性格的写照;人生若画,一幅画可以缤纷多彩,又可能是黑白颠倒;人生若行,走在旅途上,迎接艰辛,战胜困难。”因此,离开了音乐家的人生格调,很多事情都根本无法说清楚。所以,他在任何音乐场合,均反复强调“音乐是心灵的净化”这一理念。此一理念还告诉人们:音乐家创造音乐作品之同时,也在不断塑造着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对时代来说,比他所创造的任何艺术典型都更具有意义:因为在国家将面临需要大量有进取心人的时代里,作曲家的的音乐造型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典型。音乐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音乐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音乐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的人格形象。曾健清楚音乐家最应该具备的能力就是自省的能力、自我批判的能力、自我审视的能力,此一点,对于音乐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曾健的这些观点,包含着符合音乐艺术规律的真理性内容。因为,“一撇一捺人易写,一生一世人难做”(曾健语)。一个音乐家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与高尚之精神,他就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音乐形象;如果他没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他就不能深刻地审视自己,也不能深刻地审视自己的音乐作品。在创作音乐作品的时候,音乐家如果意识不到自我之存在,将作品看作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他者的世界,那么,他就有可能丧失创作的责任感,就有可能随随便便地创作,就有可能对作品进行话语歪曲。遇到接受者的不满意与质疑,他就会不停地辩解:这是音乐呀,是旋律需要那样啊,与我无关嘛。然而,在曾健看来,在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之态度与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反对那种完全排斥主观态度的“零度”(罗兰·巴特语)创作。在创作的时候,一个热爱生活之人,绝不会是没有态度之人,也不能满足于把自己的态度隐藏起来。在曾健看来,只有主体才能使整个体验活动成为主体精神的意指活动,任何主客体意义之建构或主体本我之反思活动,皆要建立在自我之澄明与自觉基点上,并在体验活动中与自我保持认同。主体是音乐审美体验活动的承担者及意义世界之禀有者。不同的意向行为方式将获得不同的意义构成,并在不同的意向行为主体方面得到不同的解释。在此,曾健是意向之发出者,正是在此种主体体验的意旨中,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是的,曾健体验的意向性是他永远处于主导地位,是在体验中被构造的意义成为对他而言之意义,他依持着自己的本真信念,而成为世界意义之转换者。因此,他坚持认为“音乐艺术是正能量的传递,是情感的投射,是心灵的倾诉,是审美艺术的载体,是心灵的对话”这一理念。在曾健的音乐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曲家之存在,可以分明地看见作曲家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他所创造的自我造型,是一个高尚作曲家的造型。他严肃地生活,严肃地思考,严肃地创作。曾健与音乐前贤一样,赋予音乐创作以神圣而庄严的性质。音乐前贤对曾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格境界方面,也见之于创作经验和音乐技巧方面。曾健通过作品之方式——用自己的作品向世人进行了具体的展现,同时,也通过言传身教之方式,告诉音乐爱好者如何进行音乐创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