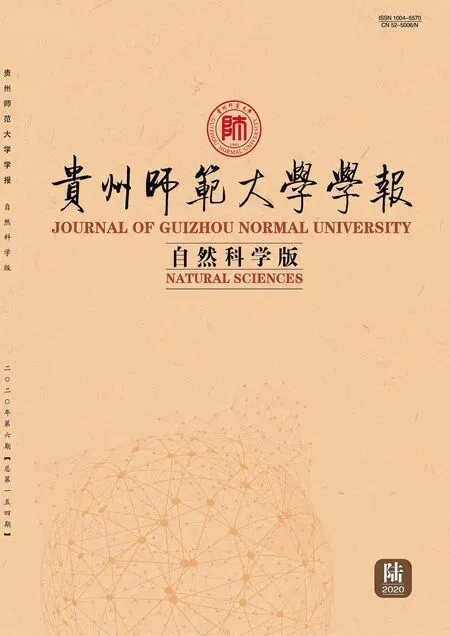夫妻依恋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希望和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
谢其利,宛 蓉,兰文杰
(1.贵州师范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贵州 贵阳 550018;2.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0 引言
追求幸福是个体毕生的重要生活目标,老年人也不例外[1-2],尤其是在农村老年人口数量众多的我国,探讨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因素更为必要[3]。婚姻是影响个体幸福感因素之一[1,4-5]。有研究显示,个体的婚姻质量在老年期达到巅峰[5-7],婚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也在老年期最强[8-9],婚姻状态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3]。但遗憾的是国内关于婚姻质量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报道却较为少见。
夫妻依恋从依恋理论的视角看待婚姻关系,夫妻依恋是指配偶之间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建立的一种特殊情感联系和内部工作模型,是成年人最为重要的特定依恋之一[10-12]。有研究表明,中国老年人夫妻依恋的3个维度(安全、回避和焦虑)与婚姻满意度呈中等程度的相关,表明夫妻依恋是衡量中国老年人婚姻质量的可靠指标[11,13]。婚姻依恋建立后对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有着长期的影响,拥有安全的夫妻依恋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态更好、幸福程度也更高[10-12,14-15]。可见,夫妻依恋可能是影响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夫妻依恋影响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希望是一种基于内在成功感的积极的动机状态,是个体相信未来事情会变得更好的信念,是“心灵之彩虹”[16-17]。希望高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也高[18-21]。希望的根源在于个体的过去和现在[17],如,成功经历是个体希望的重要来源、而重复失败则会导致个体逐渐失去希望[17,22]。此外,社会支持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希望[21,23]。可见,良好的婚姻对于成年人而言是意义重大的成功,良好的配偶支持可能是老年人希望的重要来源,安全的夫妻依恋可能是影响农村老人希望的因素。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夫妻依恋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希望,并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生命意义是指个体对人类自身及其存在的本质以及对那些自认为比较重要事物的感知、觉察[24-25],生命意义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关系极为密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等同于幸福感[24-28]。有研究显示,社会关系是生命意义的核心要素,是生命意义最为重要的来源之一,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更强[26,29-30]。婚姻关系作为成年人最为重要的亲密关系之一,拥有良好婚姻关系的个体也会拥有较强的生命意义感[28,30-31],依恋可能会通过生命意义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32]。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婚姻依恋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并通过生命意义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有研究显示,婚姻依恋可能和个体的希望关系密切,拥有良好婚姻的个体的希望水平更高[10,17,21-23]。希望与生命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是生命意义的一个主要成分[33],希望水平高的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也较高[18,34]。另外,生命意义又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关系极为密切,生命意义感强的个体更幸福[24,26-28]。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希望和生命意义可能会在婚姻依恋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具体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假设模型图Fig.1 Hypothetical model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55岁以上、配偶健在(含再婚)的农村老年人。2所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志愿参与调查的学生利用假期在贵州、湖南、重庆、四川、河南、云南等6省市(以贵州省为主)67个区县的农村地区通过方便取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共调查642名农村老年人,年龄在55~89岁间,平均年龄66.05±12.09岁,平均婚龄42.77±6.52年;男性357人(55.61%),女性285人(44.39%);受教育程度:文盲127人(19.79%),小学303人(47.19%),初中147人(22.90%),初中以上65人(10.12%)。
1.2 研究工具
1.2.1 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
采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11-13],原问卷包含18个条目,包含依恋安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3个维度(每个维度6个条目),5级计分(1=极不同意,5=极同意)。本研究中依恋安全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6,依恋回避维度的Cronbach’sa系数为0.81,依恋焦虑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67。
1.2.2 成人特质希望量表
采用Snyder等编制,陈灿锐等修订的中文版[17,35]。量表含2个维度(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各4个条目,4级计分(1=完全不同意,4=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希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路径思维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1,动力思维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
1.2.3 生命意义问卷
采用王鑫强等[36]修订的中文版生命意义感量表。量表含2个维度:寻求意义(4个条目)和拥有意义(5个条目),采用7级计分(1 =极不同意,7 =极同意)。本研究中寻求意义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69,拥有意义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1。
1.2.4 主观幸福感量表
由于研究对象为老年人,笔者选择题目较少且信效度高的“总体幸福感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问卷”测量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总体幸福感问卷 量表为1个自评条目(即,总体上我的生活是幸福的),7级计分(1 =极不同意,7 =极同意),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高,研究表明该条目能很好地衡量个体的整体主观幸福感[2]。
生活满意度问卷 由Diener等[37]编制,中文版由熊承清等[38]修订,量表含5个自评条目,7级计分(1 =极不同意,7 =极同意),量表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2。
1.3 调查程序
调查员由2所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志愿参与调查的学生担任,利用假期的时间入户调查;正式调查前由研究者根据调查手册对所有调查员进行个人调查的培训;调查前征得被调查者的同意并讲清楚指导语,有能力自行填写问卷的被调查者请其自行填写,不识字(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自行填写)的由调查员逐条将题目读给被调查者、请由其独立选择后由调查员将选项记录在量表上;填写完成后当场核查、回收问卷。
1.4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本研究首先从测量程序方面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控制:调查匿名进行、不同问卷计分方式进行适当的变换、部分条目使用反向计分。在进行数据正式分析前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0个,第一个因子解释15.68%的总变异,低于40.0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39]。
1.5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和AMOS 2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老年人夫妻依恋类型基本情况
将农村老年人的夫妻依恋维度分数转化成夫妻依恋类型以便更好地理解农村老年人的夫妻依恋风格[11-13]。首先对农村老年人在依恋问卷3个维度上的分数进行标准分的计算,然后采用Kmeans聚类法对夫妻依恋类型进行划分(聚类结果见表1)。

表1 农村老年人夫妻依恋类型聚类分析Tab.1 Cluster analysis of attachment types of rural elderly couples
由表1可见:安全型夫妻依恋,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上得分均较低,而在依恋安全维度上得分较高。表现为能自如地与配偶相处,遇事主动向配偶寻求帮助和支持,相信配偶能尊重、理解和喜欢自己;拒绝型夫妻依恋,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分数均较高,依恋安全维度分数较低, 表现为不习惯和配偶有亲密的情感联结,喜欢和配偶保持距离;焦虑型夫妻依恋,在3个维度上得分均较高,表现为不自信,担心配偶嫌弃自己,担心配偶不能真正理解自己。为了验证聚类结果的合理性,根据聚类的结果,以依恋维度为结果变量,以依恋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11-13]。结果表明,在依恋安全维度上,3种依恋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640)=444.12,P<0.001,η2=0.57;在依恋回避维度上,3种依恋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640)=420.64,P<0.001,η2=0.56;在依恋焦虑维度上,3种依恋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640)=368.09,P<0.001,η2=0.53。表明本研究聚类的结果是合理的。
2.2 不同夫妻依恋类型农村老年人希望、生命意义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检验不同类型夫妻依恋农村老年人希望、生命意义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夫妻依恋对农村老人希望、生命意义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1-13]。
表2表明,3种夫妻依恋类型农村老年人的希望、生命意义和主观幸福感(由总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得分合并而成)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表明:生命意义和主观幸福感方面,安全型夫妻依恋农村老年人显著高于拒绝型和焦虑型夫妻依恋农村老年人,焦虑型夫妻依恋农村老年人显著高于拒绝型农村老年人;希望方面,安全型妻依恋农村老年人显著高于拒绝型妻依恋农村老年人,焦虑型妻依恋农村老年人显著高于拒绝型妻依恋农村老年人。

表2 不同夫妻依恋类型农村老年人希望、生命意义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Tab.2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hope, life significa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with different attachment types
2.3 农村老年人夫妻依恋、希望、生命意义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表3表明,夫妻依恋的3个维度、希望的2个维度、生命意义的2个维度、生活满意度及总体幸福感的两两相关大部分显著。

表3 各研究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Tab.3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search variable
2.4 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中多个变量之间两两相关,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更为有效[40]。进行结构方程分析前先进行测量模型分析,检验表明测量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各因子载荷均显著(系数均在0.5以上,P值均小于0.001,见图2),表明观测变量较好地反映了所要测量的潜变量。
在检验包含中介变量的模型前,先检验夫妻依恋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夫妻依恋的3个维度均显著预测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β安全=0.56,β回避=-0.07,β焦虑=-0.24,Ps<0.01;累积解释14.40%的总变异)。然后用农村老年人数据拟合包含中介变量(希望和生命意义)的模型,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较好,χ2=693.47,df=237,χ2/df=2.93,NFI=0.87,IFI=0.91,CFI=0.91,RMSEA=0.04,但是模型中部分路径系数不显著,尝试逐步删除不显著的路径系数以使模型更为简洁,模型拟合结果表明最后的简洁模型拟合良好,χ2=505.96,df=180,χ2/df=2.81,NFI=0.89,IFI=0.92,CFI=0.92,RMSEA=0.04。2个模型的Δχ2=187.51,Δdf=57,Δχ2/df=3.29,P<0.01,表明2个模型间存在差异,且简洁模型的部分拟合参数更优,所以简洁模型为最优模型(见图2)。图2表明,在加入中介变量后,依恋安全的直接效应为0.19,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

注:A1-15是“夫妻依恋问卷”条目;Hope1路径思维、Hope2动力思维;LIM1意义寻求,LIM2拥有意义;SWB1总体幸福感,SWB2生活满意度;图中实线表显著的路径、系数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虚线表不显著路径、系数未在图中标出。图2 夫妻依恋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结构方程模型图Fig.2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ital attachment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2.5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检验希望和生命意义在农村老年人夫妻依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41],在原始数据(N=642)中抽取5 000个Bootstrap样本进行间接效应估计,结果表明(见表4):依恋安全→希望→主观幸福感的中介路径显著,该路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6/0.56=10.71%;依恋安全→生命意义→主观幸福感的中介路径显著,该路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27/0.56=48.21%;依恋安全→希望→生命意义→主观幸福感的链式中介路径显著,该链式路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4/0.56=7.14%。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Tab.4 Bootstrap analysis of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安全型夫妻依恋类型的比例低于不安全型夫妻依恋(拒绝型和焦虑型),和已有研究认为中国老年人夫妻依恋中安全型夫妻依恋占主要类型的结果不一致[11,13],与谢其利等[12]的研究认为农村留守老人安全型夫妻依恋比例较低、拒绝型夫妻依恋的比例较高的结果类似。农村老年人拒绝型夫妻依恋类型比例较高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在中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观念比较盛行,农村男性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承担对外的家庭活动,而女性老年人更多承担对内的家务、照看后代等活动,夫妻在共同劳作交流的时间较少,可能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情感和心理距离[42]。其次,本研究中的老年人的婚姻大多是非自由恋爱,而是通过媒人介绍而结婚,可谓先结婚后恋爱。其中部分老年人对当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婚姻不满意、也没有能在婚姻中进行相互适应,而是基于社会的压力和其他原因表面维持婚姻,但是夫妻双方的情感沟通较少,导致拒绝型夫妻依恋类型出现的频率较高[42]。
本研究表明,安全型夫妻依恋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拒绝型和焦虑型夫妻依恋的农村老年人,依恋安全维度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和考察夫妻依恋与孤独感、心理健康等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标的已有研究一致[12,14-15]。本研究在考察婚姻状态影响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安全的夫妻依恋是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来源[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为不安全的夫妻依恋类型,但焦虑型夫妻依恋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是显著高于拒绝型夫妻依恋的农村老年人的。其原因可能是,夫妻依恋类型的研究表明,焦虑型的夫妻依恋表明夫妻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还会顾及对方的感受、担心对方,只是在舒适度和自由度上不如安全型夫妻依恋,而拒绝型夫妻依恋的夫妻则是拒绝沟通、不考虑对方的情绪感受,采用回避的方式进行应对[11-13]。这一结果表明,拒绝型夫妻依恋是农村老年人最不理想的夫妻依恋类型。
本研究表明,安全型夫妻依恋农村老年人的希望显著高于拒绝型和焦虑型夫妻依恋的农村老年人,依恋安全维度与希望显著正相关,表明安全的婚姻依恋是农村老年人希望的重要来源。安全型夫妻依恋的农村老年人在日常的夫妻互动中相互理解,让老年人不断地体验到成功,这种成功感可能是其希望的重要来源[17,22],而不安全型依恋的夫妻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回避和焦虑、让老年人体验到重复的失败,可能会导致其希望的失去[17,22]。同时,安全型夫妻依恋类型的农村老年人能及时得到配偶的支持,而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也是提升老年人希望的关键因素[21,23],本研究进一步证实来自配偶的支持也可能是提升老年人希望的因素。
本研究表明安全型夫妻依恋农村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显著高于拒绝型和焦虑型夫妻依恋的农村老年人,同时依恋安全维度与生命意义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证实,婚姻这一重要的亲密关系是农村老年人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拥有安全的夫妻依恋的农村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更强[29-31]。但是,本研究的结果和国外已有的成人依恋与生命意义关系的研究也有所不同,国外已有研究认为安全依恋的成年人比不安全依恋类型的成年人表现出更多的拥有意义感和更少的寻求意义感[43-44],但本研究表明安全型夫妻依恋农村老年人的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均显著高于不安全型依恋的农村老年人,而其意义寻求和拥有意义一样和希望以及生命意义等积极结果正相关。这一结果和国内较多实证研究表明寻求意义与积极的结果呈正相关而不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负相关的结果类似[24,36],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结果[36]。
本研究结果表明,依恋安全维度不但直接预测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外,还通过希望和生命意义间接影响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部分验证了假设模型。研究结果证实,安全的婚姻依恋是农村老年人希望和生命意义的重要源泉[17,26,31],而且希望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命意义[18,34],安全的婚姻依恋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希望和生命意义并间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正如根据依恋、希望和生命意义的理论所推测,安全的婚姻依恋就像一个基地,让农村老年人获得希望、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10]。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意义的直接作用以及所发挥的间接作用均较希望的作用更大,这一结果和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生命意义感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的作用[25-28]。此外,已有研究认为依恋安全这一积极的维度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独有的、积极的维度[11-13],本研究的结果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相比较,依恋安全这一维度对中国老年人的心理积极适应有其独特的价值。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本研究是一个横断研究,只能在统计上证明中介效应和因果关系,后续研究应采用追踪范式进一步验证;由于取样的困难,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样本的代表性略显不足;本研究采用的是自评量表,无法完全避免社会赞许效应,后续研究应结合他评的方式加以改进。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是本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初步了解了农村老年人夫妻依恋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夫妻依恋3个维度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希望和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可为提高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