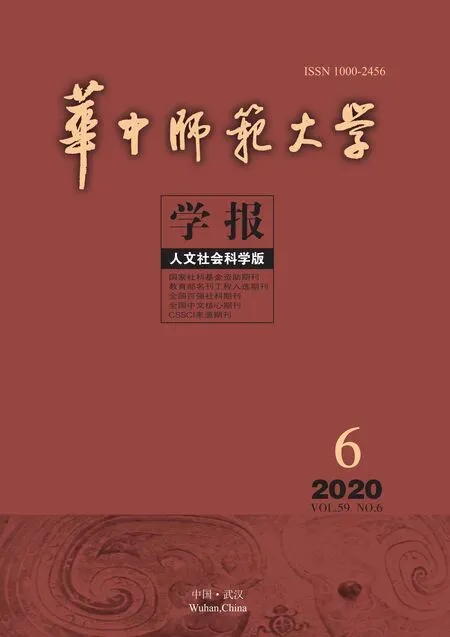王夫之《诗经》阐释的三个重要诗学命题
毛宣国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王夫之的诗学理论建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与《诗经》阐释密不可分。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很早就有所认识。20世纪30年代方孝岳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论及王夫之《诗译》《诗广传》等著作时就指出:“自来我国的文学,大家都认为源于《诗》三百篇,推《诗》三百篇为极则。但究竟‘三百篇’所以为万万不可及的道理,批评家都不过言其大概,而不曾有切实的指示。王船山的书,就是专为切实指示此点而作。”①方孝岳所说的“切实指示此点”非常重要,它说明王夫之的诗学理论是自觉地以《诗经》批评实践为基础的。方孝岳还以王夫之的“兴观群怨”理论具体说明了这一点,认为“他论诗,一切拿‘兴观群怨’那四个字为主眼”,一切皆是以《诗经》批评为准则,从“孔门的‘诗教’中阐发出来”②。方孝岳的这一阐释思路亦为后人所继承,如朱东润、郭绍虞等人论及王夫之诗学,都非常重视其对《诗经》批评特别是“兴观群怨”说的解读,甚至认为“此为其立论一大关键”③。20世纪末,宇文所安论及王夫之的诗学时亦紧紧抓住它与《诗经》阐释的关联,认为王夫之关于诗学的最犀利的批评和理论文字大多见于《诗广传》《古诗评选》等著作,这些著作“深深地植根于悠久而复杂的《诗经》学术传统,脱离了这个传统,它所讨论的问题就无法理解”④。王夫之的诗学大体可以从哲学、政教、审美三个方面展开。以“气”为本和“天人相通”的哲学观念构成了王夫之诗学的哲学基础,对《诗大序》以来政教传统的高度重视构成了王夫之诗学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王夫之诗学又是中国古代审美诗学传统的发扬光大者,其提出的一系列诗学命题,如“《诗》者,幽明之际”、诗道性情、诗乐为一、兴观群怨、情景、比兴、现量等,都有效地整合了传统诗学的政教与审美的理论资源,在政教与审美的张力中凸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价值。我们重点选择王夫之诗学中三个核心命题“《诗》者,幽明之际”、“诗道性情”、“兴观群怨”,对本源于《诗经》批评实践的王夫之诗学理论做具体阐释。
一、“《诗》者,幽明之际”
“诗者,幽明之际”是王夫之在《诗广传》中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它见于《诗广传》卷五《周颂·论昊天有成命》篇:
惟《昊天有成命》可以事上帝,于戏!微矣!礼莫大于天,天莫亲于祭,祭莫效于乐,乐莫著于《诗》。《诗》以兴乐,乐以彻幽,《诗》者,幽明之际者也。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抟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棲,故诗者,象其心而已矣。神非神,物非情,礼节文斯而非仅理,敬介绍斯而非仅诚。来者不可度,以既“有成”者验之,知化以妙迹也。往者不可期,以“不敢康”者图之,用密而召显也。……呜呼!能知幽明之际,大乐盈而诗教显者,鲜矣,况其能效者乎?效之于幽明之际,入幽而不惭,出明而不叛,幽其明而明不倚器,明其幽而幽不棲鬼,此《诗》与乐之无尽藏者也,而孰能知之!⑤
“幽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传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幽”可以说是幽暗、隐藏,没有开掘的事物,“明”可以说光明、显现、已经开掘的事物。“幽”与“明”也可以看成是有形与无形、显与隐之事物的统一。《周易》此话的意思是说,易卦所展示的世界与宇宙天地一样广大,创制易卦的圣人可以知道幽明显隐之道理。“幽明之际”中的“际”在《周易》中亦多次出现,如泰卦《象》辞中的“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坎卦《象》辞中的“刚柔际也”,可以理解为天地交会,阴阳会合之意,引申来说,也可以看成是宇宙万物的“际会”和“遇合”,看成是幽明两类事物存在着相互连接的时机、际遇。王夫之深通《易》理,他提出“《诗》者,幽明之际”的命题的目的是企望像《易》理阐释一样,通过《诗》来洞悉宇宙万物、天地人间的幽明显隐和无穷变化。
王夫之提出“《诗》者,幽明之际”的命题,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诗经》中的祭祀诗。《昊天有成命》是《诗经·周颂》中的一首著名诗篇,对于该诗的主旨,《毛诗序》解释为“郊祀天地”,但根据《诗》所表达的意思,朱熹所言“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的说法更为合理,也得到普遍的认同,姚际恒、方玉润等人都赞同朱说,著名学者杨宽所著的《西周史》也认为朱熹解释为祭祀成王之说是正确的⑥。王夫之则认为“惟昊天有成命可以事上帝”,而诗中“成王不敢康”的“不敢”一语非颂德之词,所以赞同《毛诗序》的观点,解释为祭祀天地而非祭祀成王⑦。不管对《昊天有成命》一诗主旨如何理解,“《诗》者,幽明之际”的命题所针对的对象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诗经》中的祭祀诗。祭祀诗是《诗经》的重要类型,它主要体现在《大雅》和《颂》中。周人重视祭祀,同时认为祭祀神灵非诗不可,诗歌可以在人和神之间建立联系,成为沟通神人的重要手段。“《诗》者,幽明之际”命题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提出来的。具体说来,“《诗》者,幽明之际”命题大体包含以下内涵:
首先,王夫之之所以重视《诗经》中的祭祀诗,与他对“祭祀”的本质理解相关。王夫之认为,祭祀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事神”而在于“治人”,在于“昭明德以格于家邦,人神之通,以奉神而治人者也,非仅以事神者也”⑧,这可以说是道出了祭祀的本质。既然如此,诗人写诗,祭祀神灵与祖先,其真正目的就不在于还原神的外在形象,而在于表现人如何在祭祀活动中受到神的精神感召,与神的心灵相通。《诗》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具有超凡功能,人们正是通过《诗》来感受神的存在,达到人与神的心灵相通。在这种心灵相通中,王夫之特别强调了诗人心理体验的重要性。神作为宇宙中神奇力量的体现,它是超自然的,其形象是“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抟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的,是无法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来感知的,它只能诉诸人们的心理体验。王夫之以《周颂》中祭祀文王和武王的诗说明了这一点。“‘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孰见之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孰闻之乎?”⑨,文王作为祭祀之神的出场,是人不能以目见和耳闻的,但如同目见耳闻,这正是祭祀者复杂神秘的心理体验的结果。“祀文王之诗,以文王之神写之,而文王之声容察矣;祀武王之诗,以武王之神写之,而武王之声容察矣”⑩,在祭礼与祭祀的氛围中,文王和武王作为神的形象,所具有的“肃以清”、“广以远”、“舒以密”(文王)和“昌以开”、“果以成”、“惠以盛”(武王)的特点,都不仅仅取决于“神”自身,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人们对于神的虔敬与崇拜,传达了人们对于神的神秘、微妙、复杂的心理感受。
其次,“《诗》者,幽明之际”不仅指向人与神沟通的超凡世界,它也是人世风云和社会治乱的反映。王夫之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的诗人,他对于时代兴衰和社会治乱有着特殊的敏感,所以他非常重视通过《诗》察人世之兴衰和社会之治乱。《大雅·嵩高》和《大雅·烝民》等诗,历来被人们视为“美宣王”之作,王夫之却认为“周之凌迟而东,其肇于宣王之世乎!《王风》之凌迟而《黍离》,其肇于宣王之雅乎!”,从这些诗作中可看到周朝衰落的苗头与趋势,所以他非常重视用《诗》来“知升降”和“知乱治”。他所提出的“《诗》者,幽明之际”命题也有这样的意味。他说:“《易》有变,《春秋》有时,《诗》有际。善言《诗》者,言其际也。寒暑之际,风以候之;治乱之际,《诗》以占之。极寒且燠,而暄风相迎,盛暑且清,而肃风相报。迎之也必以几,报之也必以反。知几知反,可与观化矣。”此中所言“际”不仅指天运四时的流动变化,亦指向人世间的动乱兴衰。“治乱之际,《诗》以占之”,它不仅说明了祭祀在中国古代政治和军事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说明了《诗》作为中国古代占筮(祭祀)文化精神的体现,在反映人世兴衰治乱规律,知晓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善言诗者,言其际也”,人们正是通过《诗》中所透露的端倪与信息,来觉察宇宙天地万物的变化和人世兴衰治乱,它不仅关系到人与神的沟通,不仅关系到宇宙天地的微妙变化,关系到从暄风、肃风中感知寒暑的季节转换,更关系到社会的兴衰治乱和民心民情的好坏。王夫之这一思想也是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继承。比如,汉代今文学家以灾异言《诗》,提出《诗》的“四始”“五际”说,其目的就是见微知著,“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即通过《诗》来察觉天地万物变化、社会兴衰治乱和王道政治好坏。所不同的是王夫之褪去了今文经学家以灾异言《诗》的神秘色彩,因而更加突出了《诗》“知乱治”“知升降”的本体存在及其参与时政、干预现实的功用。
再次,“《诗》者,幽明之际”命题突出了“乐”(音乐)在祭祀天地神灵、沟通人神过程中的作用。周人祭祀神灵,按王夫之的说法,要“采备五色,和备五味,乐备五音,臭备五气”,即包括“色”“味”“音”“气”多种因素,但只有“音”(乐),才在人与神的沟通中发挥最大作用。王夫之所说的“乐”与诗、舞是一体的,这也是中国早期诗歌的特点,诗乐一体,诗舞乐不分。不过,细加区分,诗与乐又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相对于“诗”,“乐”在沟通人神之际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他说:
乐为神之所依,人之所成。何以明其然也?交于天地之间者,事而已矣;动乎天地之间者,言而已矣。事者,容之所出也;言者,音之所成也。未有其事,先有其容;容有不必为事,而事无非容之出也。未之能言,先有其音;音有不必为言,而言无非音之成也。
又说:
今夫鬼神,事之所不可接,言之所不可酬。髡髴之遇,遇之以容;希微之通,通之以音。霏微蜿蜒,嗟吁唱叹,而与神通理,故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大哉,圣人之道,治之于视听之中,而得之于形声之外,以此而已矣。
在王夫之看来,神的世界是幽微不显的,“事之所不可接,言之所不可酬”,要将其敞亮,使人与神的世界贯通起来,“乐”的作用是最不可忽视的。乐具有“霏微蜿蜒,嗟吁唱叹”的特点,所以它“与神通理”。王夫之还指出了“乐”(舞)“未有其事,先有其容;容有不必为事,而事无非容之出也。未之能言,先有其音;音有不必为言,而言无非音之成”的特点,认为它超越了语言的局限性,在传情达意方面具有“诗”(言)所不具有的优势。王夫之这里所说的“音”指的是音乐,所说的“容”指的是舞蹈。相比“音之所成”的“言”(诗)、“容之所出”的“事”,“乐”(舞)更具有合于鬼神,感于性情,沟通天地万物之间的幽明的功能,即所谓“音容者,人物之元也,鬼神之绍也;幽而合于鬼神,明而感于性情,莫此为合也”。这也是王夫之为什么要提出“乐为神之所依,人之所成”观点的依据所在。因为只有“乐”才能进入到幽明隐显的神灵世界中,传达出人们对神灵的祈求与希望。
“诗者,幽明之际”命题对“音乐”作用的强调,其实不仅仅是针对“乐”,对于理解诗之本体存在也具有重要意义。不少学者谈到王夫之诗学时,都将“诗乐合一”看成其重要的诗学主张,认为它非常重视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比如提出“诗乐之理一”、“乐与诗相为体用”、“诗与乐相为表里”等命题,重视以“声情”论诗,等等。王夫之对诗乐关系的重视,续接了明代前后七子重视“诗乐”的诗学传统。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将对诗乐关系的理解置于“《诗》者,幽明之际”一类命题的理论背景下,王夫之的“诗乐合一”论便具有了与明代以“诗乐”为典范的理论完全不同的意义。“诗者,幽明之际也”,也就是说诗能贯通幽和明、人与神、有形与无形之世界,这种贯通与“乐”的特殊功用相关,但乐与诗并非是分割的而是一体的,其关系如萧驰所说:“‘诗以兴乐,乐以彻幽,诗者幽明之际者也’一语,实际上指出了入于幽又处于优位之乐与诗的关系:首先,乐因其更‘霏微蜿蜒’和‘入空’而比诗更具有超越性。然而,‘幽明之际’又明指处于优位之乐与诗并不隔绝,而可‘涵之于下’,即包容在诗里;同时,处于下位的诗,亦能‘际之于上’,即以具无言之神,不可见之色和希微清空为其至高境界。”这样,王夫之就以音乐为介质,将诗与乐统一起来,展示了隐含在幽明之际、隐显之际、天人之际、形上与形下世界中的诗歌本体的存在,将诗歌带入一个意义更加深远的世界。如果将这一命题放在中国传统的消弭形上与形下世界对立,追求时空一体、象外虚空的审美境界的理论背景下,则其在诗学史上的理论意义如萧驰所说:“‘际’既指出诗处于空间与时间艺术的际畔,言与‘不落言荃’和无言之声的际畔,处于‘指事造形’、执着感性与‘色相俱空’心灵世界的际畔,‘际’亦指出上述两个世界在诗中的交会和际遇。由此,他超越了前辈的以乐论诗,超越了李东阳所谓‘诗乃六艺之乐’的概念,比其所谓‘诗乐之理一’的意涵亦远为丰富。”“诗者,幽明之际”命题所包含的诗乐关系的理解,体现了王夫之《诗经》阐释所达到的哲学美学深度。
二、“诗以道情”
“诗以道情”,有学者将其看成是王夫之诗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不管能否作为逻辑起点,“诗以道情”作为王夫之诗学最重要的命题却是无疑的。《诗广传》开篇《论关雎一》就将“诗以道情”作为最重要的诗学观念提出来:
周尚文,文以用情。质文者,忠之用,情才者,性之撰也。夫无忠而以起文,犹夫无文而以将忠,圣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则将劝天下以匿情矣。

《关雎》是《诗经》中的第一首诗,也是历代人们最重视的诗篇,许多阐发诗学宗旨的文献都源出于对《关雎》的评价,如《毛诗大序》和朱熹《诗集传序》等。王夫之亦不例外。他选择《关雎》,将“诗以道情”作为其论的宗旨,可见对“情”的高度重视。《论关雎》没有直接运用“诗以道情”的话语,而是采用了“文以用情”、“是故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之类的表述,它实际上是“诗以道情”的另一种表述,其目的在于说明像《关雎》这样的诗歌是以情为本体的。类似的表述在《诗广传》中还有很多:“圣人达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琴瑟之友,钟鼓之乐,情之至也。百两之御,文之备也。善学《关雎》者,唯《鹊巢》乎!学以其文而不以情也。故情为至,文次之,法为下”;“天地不匮其产,阴阳不失其情,斯不亦至足而无俟他求者乎?均是物也,均是情也。君子得甘焉,细人得苦焉,君子得涉焉,细人得濡焉。无他,择与不择而已矣。……故曰发乎情,止乎理。止者,不失其发也。有无理之情,无无情之理也”,等等,都是将情感作为《诗》之本体,强调情感的重要性。情感不仅是评价《诗经》作品最重要的标准,也是评价整个诗歌作品的最重要标准。“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这些话不仅表明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而且也表明王夫之是以《诗经》为典范,将《诗经》与后代诗歌比较之后而明示诗之本体是“兆在人心”即抒发人的情感与性情的。
王夫之所言之“情”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诗广传》为例,按照袁愈宗的归类,可以分为白情与匿情、贞情与淫情、裕情与惉滞之情、私情与道情等类型。“白情”与“匿情”说的是有了真实情感应不应该表现的问题。“是故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白情”就是不隐匿,将内心的真实情感表现出来,像《关雎》那样,“‘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不匿其哀也。‘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不匿其乐也”,将君子对于淑女的真实情感没有任何隐藏地表露出来。在王夫之看来,只有将自己的情感真实地表达出来,才能“性无不通,情无不顺,文无不章”,符合人的本性和本心的需求。“匿情”则是相反,它是将人的真实情感隐匿起来,不让它抒发。若情感久久被压抑,得不到宣泄,其结果必然是“耽乐结哀,势不能久,必于旁流”,“迁心移性不自知”,即导致人的本性的迷失和人心的沉沦。
“贞情”与“淫情”、“裕情”与“惉滞之情”、“私情”与“道情”等,说的则是应该表现什么样的情感问题。“情上受性”,如果情以性为依归,就是“贞情”。《诗经》中的《静女》就是符合“贞情”标准的诗,它“情迫而有不迫,道有常而施受各如其分”,其所表现的情感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能用道德理性加以节制。“淫情”则是“情下授欲”,不能对人的情欲加以节制,不符合人的本性的情。《采葛》被王夫之定性为“淫情”之诗。它“以之思而淫于思,以之惧而淫于惧,天不能为之正其时,人不能为之副其望”,所表现出来的男女相思之情失去了节制和规范,不能给人以正确的价值引导,陷于个人私欲而不能自拔,诗的语气风格也过于迫切——“其词遽,其音促,其文不昌”,与王夫之所推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正和平之音相背离。王夫之对“淫情”的理解,反映了其在情感问题上维护儒家诗学正统的一面,他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看待情感表现的。不过,王夫之之所以否定“淫情”,是因为他看到,这种情感表现还属于一己私情的范围,若听任这种情感的放纵,只会局限在个人狭窄的情感中不能自拔。这也是王夫之为什么要否定“私情”和“惉滞之情”的原因所在。因为无论是“淫情”,还是“私情”和“惉滞之情”,在王夫之的眼中,他们在本质上都一样,属于一己之悲和一己之私的情感,都缺乏高远的社会理想与目标。王夫之追求的是另一种情感境界,即能反映时代兴衰、世道人心,广通天下,与大众同欢乐共忧患的“情”,即所谓“裕情”和“道情”。王夫之说:
周公之徂东山也,其忧也切矣;自东而归,其乐也大矣。忧之切则专以忧,乐之大则湛於乐。夫苟忧之专,乐之湛,所忧之外,举不见忧,而矧其见乐?所乐之外,举不见乐,而矧其见忧?独宿之悲,结褵之喜,夫何足以当公之忧乐,而为尔不忘邪?忧之切,乐之大,而不废天下不屑尔之忧乐,於以见公裕於忧乐而旁通无蔽也。
《诗经·豳风·东山》一诗表现了周公东征胜利归来能不以己之忧乐而废天下之忧乐,这种情感就是王夫子所主张的“裕情”和“道情”。王夫之对“裕情”和“道情”的重视,与其基本的哲学观念密切相关。王夫之曰:“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道心也;喜、怒、哀、乐,人心也。”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二者不可分割。在“性”与“情”关系上,王夫之总的倾向是“尊性以贱情”,因为性是先天固有的本质存在,属于道德本体方面的东西,情是后天的偶然性存在,属于个人私欲的范围,必须受到“性”的节制和礼义归化才有意义。不过,王夫之并没有否定“情”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就人的现实存在而言,情可见而性不可见,“故性之于情上见”,“性”必须寓于“情”中才能成为人具体的本性,“道心终不离人心而别出”,道心与人心、情与性必须统一起来,才有意义。正是基于“性”“情”关系的这一理解,王夫之高度重视情感在诗歌创作与欣赏活动中的意义,又不把情感问题泛化,走向滥情与纵欲的地步。王夫之的“性”“情”之辨,是以其“诗之教,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的教化哲学观念为基础的,同时又贯穿着以气为本、“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诗广传》卷三)的广大和谐的生命哲学精神,自然转向对于“裕情”和“道情”的重视。诚如唐君毅所说,王夫之重视气必然导致重情,他对于诗歌的贡献不仅在于言志达情之说,更在于“余情”范畴的创造与重视。唐君毅这里所说的“余情”与“裕情”相通,所指的均是一种与“气”相通、气力充沛的广大和谐的生命情感。这种情,如他所说,是人与万物共同拥有的本性的体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它绝非那种沉湎于个人欲望得失的狭隘的一己之情,而是具有天地同情之心,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群体之情。诗歌应该表现的即是这种情感。王夫之说:
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期为者,志也;念之所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动焉而不自待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人即无以自贞,意封于私,欲限于小,厌然不敢自暴,犹有愧怍存焉,则奈之何长言嗟叹、以缘饰而为文章之乎?
“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说明王夫之不仅重视诗歌的情感表现,而且遵循《诗大序》以来的以“志”统“情”的路线,将“情”与“志”统一起来,重视群体道德规范对“情”的引导与制约作用。在《诗广传》中,王夫之多次提到对“情”的规范问题,如“故圣人尽心,而君子尽情”,“情,非圣人弗能调以中和者也。唯勉于文而情得所正,奚患乎貌丰中啬之不足以联天下乎”,“交谤以成乎衰周,情荡而无所辑有如是。故周以情王,以情亡,情不可持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这里所说的君子尽情、正情和治情的问题,都是讲的如何用“性”和礼义教化来规范情的问题。其实,谈“情”与“性”的关系,也是谈“情”与“理”的关系。所谓“诗源情,理源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不因自得,则花鸟禽鱼累情尤甚,不徒理也”,“忧乐以理,斯不废天下之理”,等等,均是将情与理的统一看成是恒定诗歌情感价值的重要标准。不仅如此,王夫之还将“理”与“气”统一起来。“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从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凡气皆有理在”,王夫之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气化氤氲的结果,自然心、性、理也须从“气”上说。王夫之还引入“诚”的范畴解释“情”。他说:“诚者何也?天地之撰也,万物之情也”,“诚”即是天地之心和天地之情的体现。“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浡然兴矣”,“用俄顷之性情,而古今宙合,四时百物,赅然存焉”。诗人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情感,“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将个体情感与宇宙天地之情连接、打通。
“诗以道情”的诗学主张并非王夫之的首创,中国古代诗学历来有着“诗以道情”的传统,王夫之“诗以道情”诗学主张的提出,会通了“诗言志”“诗缘情”和宋代理学家的性情论等多种理论资源,同时也是其以“气”为本、“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人与天地万物一气贯通的哲学精神的体现,所以它对于中国古代情感诗学理论来说是一种丰富与发展,有两点至为重要:
第一,王夫之的“诗以道情”的主张,重视“性”对“情”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固然有着传统儒家诗学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王夫之对“情”与“性”关系的理解,是以“气”为本的宇宙论、人性论哲学精神的体现,所以在“情”的理解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是超越前人的。王夫之的“诗以道情”主张也是对明代文坛诗坛创作风气的一种回应。明代中后期受心学影响,出现了“尚情”的文艺思潮,这一思潮虽然具有将“情”从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下解放出来的积极因素,却又导致了明末纵欲、滥情等文艺流弊的产生,明代诗歌所取得的成绩甚少为人所称道,但其派系之多,标榜之风之烈却为历代所罕见。所以从明末清初开始,一些著名学者、诗论家如钱谦益、黄宗羲等人,都借助传统儒家的性情论诗学理论中“约情复性”“性为情节”观点来批评和纠正这一流弊。王夫之也不例外。不过,与时人普遍否定明代文学创作不同,王夫之只是否定明人纵欲、滥情风气,并不否定明人创作本身,也不否定“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他的“性情”“理欲”之辨以及“情为性节”、“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的一类主张,是在充分肯定诗歌表达真诚的情感,对各类情感做出辨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并没有破坏诗之情感的本体地位,由于有其“性情”和“理气”论的哲学支撑,反而深化了儒家诗学的情感理论,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王夫之的“诗以道情”的诗学主张是在天人之学的哲学背景下展开的,与其“气”之本体的哲学观念密切相关。“情”为“气”所贯通,人心与天地遇合,在心之广大与天地宇宙往来沟通中见出人之情感精神力量的强大,这便是王夫之所重视所追求的“情”。这种气—物—情相通的观念也可以说构成了王夫之情感诗学,特别是情景交融诗学理论的基础。在《诗广传》中,王夫之提出了一个气物相授、心与物相值相取的情感生成模式:
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
有识之心而推诸物者焉,有不谋之物相值而生成其心者焉。知斯二者,可与言情矣。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浡然兴矣。
王夫之所说的“阴阳”实际上就是“气”。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也化生出一个“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浡然兴矣”的有情世界。王夫之以“气”为本言“情”,认为“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将“情”看成是心与物相值相取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在言“情”与“景”、“心”与“物”不可分离的原初性、本源性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诗广传》描述《灵台》之诗的那种“天不靳以其风日而为人和,物不靳以其情态而为人赏,无能取者不知有尔……王适然而遊,鹿适然而伏,鱼适然而跃,相取相得,未有违也,是以乐者,两间之固有也,然后人可取而得也”的关系,它是宇宙世界本然存在的一种秩序与节奏,也是人纵浪于大化世界之中,涵容天道人伦,物理人情,与天地万物往来相授、和谐共生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中,不再存在着一个景触发情,情表现景,然后情景融合的模式,而是“言情则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响而执之有象;取景则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王夫之这样理解“情景”,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心物、情景理论的继承,而且赋予了中国古代“情景”理论新的内涵。在王夫之的诗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情中景,景中情”“景生情,情生景”“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即景含情”“取景含情”之类的表述,它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感物兴情的“情景”理论的,后者如刘勰所说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钟嵘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萧统所说的“睹物兴情”等,都是将物作为情的触发物,强调“情”因感物而生,将“情”看成是“物”的心理感应。而王夫之的“情景”理论则打破了情与景、心与物之间的限隔,强调“情”与“景”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的“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与人相通,情与景相互生成,万物如其本然地存在,呈现出生命最真实的状态。王夫之对“情景”的这些理解,无疑大大丰富了“情景”诗学理论的内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夫之“情景”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了中国“情景”诗学理论的完成者与总结者。
三、“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是《诗经》学史上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也是王夫之诗论中最重要的命题。“兴观群怨”命题最早由孔子提出来,主要是从学《诗》和用《诗》的角度阐发这一命题,目的在于通过“诗三百”的学习来提高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提高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其中涉及对《诗》的审美、认识、道德等多方面功用的理解。孔子之后,对“兴观群怨”进行阐释的最重要的代表是汉儒与宋儒。汉儒释“兴”为“引譬连类”,“观”为“观风俗之盛衰”,“群”为“群居相切磋”,“怨”为“怨刺上政”(孔安国、郑玄),着眼的是诗之教化功能,力图通过对“兴观群怨”的阐释构建一个讽谏批判现实、和谐社会人心的政教诗学模式。宋儒以朱熹为代表,以“感发志意”释“兴”,以“考见得失”释“观”,以“和而不流”释“群”,以“怨而不怒”释“怨”,虽然不失其教化立场,其侧重点却与汉儒不同,不重美刺讽谕的政治伦理功用,而重人的性情和道德修养,对“兴观群怨”阐释的情感心理意味也大大加强。与汉儒和宋儒一样,王夫之也非常重视通过“兴观群怨”的阐释来发扬孔门诗教思想。不过,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说的理论意义又非传统的诗教理论所能涵盖。王夫之是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又是传统诗学的总结者,他对“兴观群怨”说的阐释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试图在新的理论层次上将传统的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的诗说统一起来,使本源于《诗经》批评实践的“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超越狭义的《诗经》接受和道德评价范围,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观念,所以它涉猎的内容极为广阔,包括诗之本体,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诗之文本意义,诗的非功利性与功利性、诗之教化与审美的关系等。
王夫之论及“兴观群怨”的话语很多,《诗译》中有一段话,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其“兴观群怨”说的理论内涵: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是故延年不如康乐,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谢叠山、虞道园之说诗,井画而根掘之,恶足知此!
依据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夫之论“兴观群怨”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将“兴观群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看待。自孔子提出“兴观群怨”之说以来,阐释者虽多,但大多是将“兴观群怨”四字分训为四义看待,将“兴观群怨”割裂开来认识《诗》的功用,到了王夫之才把四者联系起来,充分揭示其内在的关联。对于王夫之的这一理论贡献,学术界已有充分认识。比如戴洪森认为王夫之这一说法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看法而“以兴、观、群、怨四者的联系、转化论诗”,叶朗亦指出只是到了王夫之“第一次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对它们内在的联系作了阐发,因而使后人有可能突破传统的狭窄理解,见到一个新的境界”。其实,王夫之将“兴观群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并不背离孔子“兴观群怨”说的基本思路。在孔子那里,“兴观群怨”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不同的是孔子是在春秋赋诗言志的基础上,突出了诗的政治教化功能,王夫之则是以情感为核心,将《诗经》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更加重视诗的艺术审美功能,所以突破了经生家解《诗》模式的理论局限。对此王夫之自己亦有明确认识,他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将《诗经》作品作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看待,在清代其他的诗论家那里也有体现。比如,方玉润谈到《诗经》的“赋”“比”“兴”手法运用时,就反对那种执定某章为兴,某章为比,某章为赋,将《诗经》作品强为分割的阐释方法,认为“夫作诗必有兴会,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则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谓比也。或一二句比,或通章比,皆相题及文势为之。亦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已耳,非判然三体,可以分晰言之也”。虽然方玉润与王夫之的阐释角度有不同,一是针对《诗》之兴、观、群、怨的功能,一是针对《诗》之赋比兴的方法,但他们都意识到《诗经》作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形象整体,反对经生强行割裂《诗经》作品并予以牵强附会阐释的做法。
第二,王夫之将“兴观群怨”称之为“四情”,认为诗歌“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突出的是情感作为诗之本体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体情”的过程中,“兴观群怨”的功能得以充分体现。不仅如此,王夫之还着眼于审美情感活动的规律与特点,对“兴观群怨”作为四种审美情感的内在联系予以揭示。比如,对于“兴”与“观”关系的揭示。“兴”是兴情,是人心的感通与之志气的激发;“观”是“观志”和“观风俗”,二者似乎不相关联。而在王夫之看来,“兴”与“观”是统一的,互相作用的。“诗之泳游以体情,情可以兴矣;褒刺以立义,可以观矣”,“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正是通过“兴”的情感感发,“观”才转化为一种艺术的认知,发挥其观志和观社会民情的作用。“群”与“怨”的关系也是如此。“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尽于言,可以怨矣”,“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因为情感的作用,“怨”与“群”才可以统一起来,发挥其“怨刺上政”及和谐人心的功能与作用。王夫之言“群”与“怨”还包含一种含义,“群”主要指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所以侧重于群体情感的表达,而“怨”则侧重在个体情感方面。王夫之虽然重视“怨”的情感表达,但是反对将“怨”局限在个人狭小的圈子内,变成个人戾气和一己私欲的情感表达,而是将“怨”的情感纳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中,将个体之情与群体意识统一起来,使“怨”与“群”情感表达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深广的艺术内涵。
第三,王夫之以“情”为中心阐释“兴观群怨”说,兼摄创作与欣赏、作者与读者两个方面。萧驰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观群怨”说的意义评价时,认为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或专注在作者方面,强调诗创作状态中审美的非功利性、非目的性与艺术的社会功利性的统一;或者着眼在读者方面,强调阅读对于作品意义的创造。其实,无论是从作者还是从读者任何一方面都无法把握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意义内涵。王夫之提出“‘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命题,说明他是高度重视读者在诗歌接受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以”是凭借,“可”是允许,意为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来把握诗歌作品的意蕴内涵。“兴观群怨”之说的要义也就是要读者不遵循固定的思维模式,不因循固定的思想情感来体验与感受作品,或“兴”或“观”或“群”或“怨”,“各以其情而自得”,使《诗经》文本的意蕴和和审美价值得到充分的开掘。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诗人创作的主体地位也是不能忽视的。离开了诗人所创造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读者的“随所以而皆可”,“各以其情而自得”的感受体验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对此,王夫之有着明确认识。他说:“‘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诗三百篇》而下,唯有《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这里所说的“随所以而皆可也”,显然不仅指向读者,更关涉诗人和作品价值评判的高下。“夫怨而可以群,群而可以怨,唯三代诗人为能”,王夫之这里所说的“三代诗人为能”,显然也是从诗人角度强调“兴观群怨”之说的意义。这也是王夫之提出“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命题的意义所在。“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但涵求的却是“作者用一致之思”,即必须在对作者用心和作品意蕴把握的基础上谈读者的“以情自得”,这实际上是强调读者的“自得”必须受到诗人创作作品意义内涵的制约与影响。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批评也表明了这一点。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哀乐的情感本来就藏在人的内心,只不过因为乐音的触发而表现出来,所以音乐本身与哀乐的情感无关。王夫之不赞成这一观点。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事与物不相称,物与情不相准者多矣”的情况,故难免出现“其音自乐,听其声者自悲,两无相与”的现象,但不能说成是“声无哀乐”,因为音乐的接受和欣赏中的“以情自得”同样要受到音乐本身情感内涵的制约影响,那种以为听者可以“坦任其情,而于物理之贞胜”,即以自己的情感取代音乐作品自身情感内涵的理解及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正是基于对作者与读者两方面情感表现的重视,王夫之提出了“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为风雅之合调”的观点,使“兴观群怨”各种情感因素有机统一起来,成为衡量和评价诗歌创作与鉴赏的最重要标准。
在“兴观群怨”的“四情”之中,王夫之非常重视“兴”的作用。他将“兴”看成是有识之心与天地间所有事物(天化)相值而相取的产物,并以《诗经·东山》的诗句来说明这一点。“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於今三年”,离别家乡已三年的征夫,当他看到栗薪上面累累的瓜果——那些曾经非常熟悉的事物与场景,感慨万分,蕴含在心中的情感自然喷发而出,就像“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那样,一切来的都是那样自然,没有任何矫情与造作,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兴”。它是天化与人心在仰俯之际相融相通,也是人的生命情感的流露与迸发。具体到诗歌作品中,就是情景互生、情与景的统一:“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王夫之言“兴”还包含一层含义,那就是诗人可以通过“兴”的情感感动来超越一己私情,使诗所表现的情感具有普遍社会意义与价值关怀。比如他说:“能兴则谓之豪杰……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力”,就具有这样的意味。正是赋予“兴”这样的内涵,王夫之才超越了传统儒家的诗教理论,由“兴”及“观”及“群”及“怨”,将“兴观群怨”说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谈到“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它与“现量”说的关系。王夫之重视“兴”,提出“现量”范畴,与他“诗以道情”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都可以看成是王夫之“性情”论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兴”和“现量”与一般言“性情”不同,它重视的是诗的情感自然感发和当下生成的意义。“现量”这个范畴来自佛学。“量”在佛学中是尺度、标准的意思,指知识的来源、认识形式及判定知识真伪的标准。现量即感觉,是感觉器官对于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没有加入概念的思维分别活动。王夫之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美学诗学转化。他认为,“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现量”的这三层含义,可以从审美感兴和审美观照意义上理解。“现在”说的是审美观照的时间性,它是当下生成的直接感兴,是不需要借助于过去的知识;“现成”说的是审美观照的直觉性,它是“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在瞬间直觉生成一个充满诗意的感性世界;“显现真实”即是说审美观照所显现的是事物本来面貌,是真实而非虚妄的东西。
王夫之不仅用“现量”阐释了审美观照的特点,他还将它广泛地运用在诗歌审美实践中。“即景会心”、“因情因景”即可以看成是诗歌创作中的“现量”。王夫之说: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贾岛的“推敲”故事一直传为诗坛佳话,王夫之则予以否定。原因在于他认为这种“推敲”只重视“形容酷似”,刻意思虑,让诗歌创作成为人力设计而非诗人情感自然感发的结果。他认为好的诗句如“长河落日圆”“隔水问樵夫”即是诗人情感自然感发、“即景会心”、“因景因情”的结果,即禅家所谓“现量”。王夫之的《诗经》著作中并没有直接出现“现量”这一术语,但是他对《诗经》作品的具体评论,如云:“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葛覃,劳事也。黄鸟之飞鸣集止,初终寓目而不遗,俯仰以乐天物,无惉滞焉”,“往戌,悲也,来归,愉也。往而咏杨柳之依依,来而叹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既是谈诗之“情”与“兴”,也是谈“现量”,它是以直接感兴的形式来表现人与万物的相融相通,这是一个美的世界,也是一个感性的、充满诗意的世界。王夫之重视“兴”,将“兴”看成是“现量”的题中之义,即是要将这样的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
以上,我们阐释了“《诗》者,幽明之际”、“诗以道情”、“兴观群怨”三个命题的理论涵义。这三个命题充分说明《诗经》阐释对于王夫之的诗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王夫之正是通过《诗经》阐释提供的丰富理论资源推动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
注释
①②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85页,第186页。
③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④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503页。
⑥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山西古交市非遗项目“岔口道情戏”自然传人王谷唤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