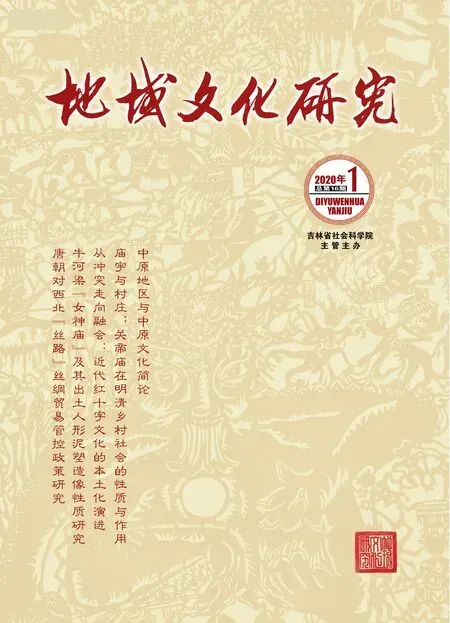清代地图与“哈尔滨”地名考证
高龙彬
“哈尔滨”地名①关成和:《哈尔滨考》,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内部资料,1985年;关成和:《哈尔滨考》,《地方史资料》第一辑,哈尔滨地方史研究所,1980年,内部资料;《阿勒锦村——哈尔滨地名考》,哈尔滨市图书馆内部资料,1977年;纪凤辉:《哈尔滨寻根》,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王禹浪:《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陈士平:《哈尔滨探源》,内部资料,2002年,等。黄锡惠:《“哈尔滨”地名考释》,《满语研究》2010年第1期;纪凤辉:《〈黑龙江舆图〉与哈尔滨地名》,《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纪凤辉:《哈尔滨地名由来与哈尔滨城史纪元》,《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石方、石恒林:《“模糊史学”视域下的哈尔滨地名考》,《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15期;石方:《哈尔滨地名含义新诠——从“模糊史学”的视域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梁爽、黄澄、王禹浪:《天鹅说——哈尔滨地名新探》,《学理论》2000年第10期;王洁:《关于〈“哈尔滨”地名考释〉中一处分析的商榷》,《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赵阿平:《哈尔滨地名的含义》,《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何报侠:《哈尔滨地名的由来》,《中国民族》1981年第8期;王禹浪:《哈尔滨地名之谜》,《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赵力:《松花船口吉江通衢——哈尔滨地名之我见》,《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6期;王昊:《智者的困惑——关于哈尔滨地名含义的争论》,《黑龙江档案》2018年第5期;孟烈、李述笑:《名城与城名——哈尔滨地名纵谈》,《黑龙江日报》2010年10月21日,等等。探讨是哈尔滨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亦是一个争论不休并至今悬而未决的难题。语言学关涉“哈尔滨”地名的来源,“哈尔滨”地名的满文、汉文、俄文与日文等的出现时间和历史演进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的课题。历史地理学关乎“哈尔滨”地理方位与地理名称的对应考证,不同历史时期“哈尔滨”的具体位置和不同行政区划的“哈尔滨”的称谓变化也是一项亟待进一步梳理的论题。清代地图的利用为“哈尔滨”地名研究提供了语言学与历史地理学相结合的“载体”。
一、与“哈尔滨”相关的清代地图概观
地图是一种史料,甚至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证据。这首先表现在地图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方面,其次地图也反映了一定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同时,地图亦是一种图像,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一种图像的表现形式。清代地图为研究“哈尔滨”地名探究提供了一个视角或路径。
与“哈尔滨”相关的清代地图:康熙满文的《康熙皇舆全览图》(1718);雍正满文《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乾隆汉文《乾隆十三排图》(亦称《乾隆皇舆全图》、《乾隆内府舆图》,1760—1770);同治汉文《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即《大清一统舆图》,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绘制,1863);光绪汉文《黑龙江舆图》(1890—1899)。
同时,笔者查阅了哈尔滨市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的相关古籍:《皇朝省直舆地各志》(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哈尔滨市图书馆藏书号211.1.2449。)《皇朝一统舆地全图》(清赵子韶绘,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石印,哈尔滨市图书馆藏书号211.1.4910。)《大清中外一统舆图》(清邹世治等撰,清同治二年湖北抚署景桓楼刻印本,哈尔滨市图书馆藏书号211.1.2711。)《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说》(清王尚德绘,清光绪廿四年,上海文贤阁石印,哈尔滨市图书馆211.1.1092。)与《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注》(清杨守敬、饶敦秩撰,清光绪廿二年注,哈尔滨市211.1.4734。)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外文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舆图指要》。此外,“文物出版社的三大册《中国古代地图集》,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编的《舆图要录》,飞利浦·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还有最近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编的《地图中国》。”①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160页。
葛兆光强调,“把图像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确实是很有趣的领域,但是,我觉得,很多研究图像的,常常有一个致命的盲点,这就是他们常常忽视图像是‘图’,他们往往把图像转换成内容,又把内容转换为文字叙述,常常是看图说话,把图像资料看成文字资料的辅助说明性资料,所以,要么是拿图像当插图,是文字的辅助;要么是解释图像的内容,是把图像和文字一样处理。”②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136页。让图像自己说话是一项深刻的命题。图像的意义首先是其所呈现的感官内容,其次是内容背后的内涵。“色彩、构图、位置、变形,这些图像的内容在文字史料中是没有的。如果分析图像的时候不分析这些,图像就还原成了文字,图像的特殊性就没有价值了,充其量是看图说话或是插图,是辅助性的说明。”③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140页。在研究时,图像的辅助性功用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升华,发掘与发现图像背后的意义。尽管针对不同的研究课题,然而作为图像史料的地图所呈现的内容是第一个认知层面。
二、关于地图中的“哈尔滨”相关地名考证
《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乾隆十三排图》与《黑龙江舆图》等清代地图,为研究清代政治史、文化史与区域史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满文或汉文的地图标识如阿尔楚库和屯、松阿里乌拉、哈尔宾等,是研究“哈尔滨”历史文化的重要信息。
满文《康熙皇舆全览图》中,阿尔楚库和屯、阿尔楚库比拉、松阿里乌拉,拉林比拉等地名和江河名称形象地描绘了该区域的情况。但是,没有“哈尔滨”字样。“和屯”即满语的城镇;“比拉”是河;“乌拉”是江。松花江“盖由松阿里转讹而来,昔满洲土人呼此江为松阿里乌拉,即天河之意,汉人则亦因之而称松花江矣。”①《盛京时报》,1936年09月09日,第7版。
满文《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中,除了阿尔楚库和屯、阿尔楚库比拉、松阿里乌拉,拉林比拉等地名和江河名称,在阿尔楚库比拉与拉林比拉中间的松阿里乌拉中出现了“扁岛”(满语罗马字母转写为tarhvn toho)。从地图“扁岛”标识的位置看,该地方是今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某处江心岛。但是,“扁岛”不是现太阳岛,也不是“哈尔滨”地名的来源。
纪凤辉论证,“哈尔滨”一词是满语“扁岛”之义。论据与地图、地理位置有关的是:“第五,《大清一统舆图》标绘‘扁岛’的方位。地名是历史上形成的,它的产生不是毫无意义和毫无根据的,而哈尔滨地理特征确为‘扁岛’在《大清一统舆图》中得到了最令人信服的又一证明。在《大清一统舆图》阿勒楚喀河和拉林河之间松花江江段中,只标有一处扁状的岛屿,而且这个扁状的岛屿与全幅地图标绘的整个松花江、黑龙江十数个较大的岛屿相比,其形状两端最尖,其分流两侧最均,其面积亦是较大者之一。特别是这个扁状的岛屿所标正对呼兰辖境的江北塔尔挥托辉(意为蛤蜊洼,详见《新晚报》1990年5月17日第3版),虽然没有标出‘哈尔滨’地名,但与今哈尔滨方位完全吻合,并突出了哈尔滨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这不能不是哈尔滨命名的根本起因。晚于《大清一统舆图》刊行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就是在这个扁状岛屿旁标有‘哈拉宾’字样,这不能不进一步说明哈尔滨之名的确来源于这片独具自然地理特征的扁状岛屿。”“第六,清代档案中有关哈尔滨‘扁岛’的记载。不仅清代地图如此标绘哈尔滨地形,而且清代档案记载与地图标绘相符合。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862年巡查松花江沿岸网厂,渡口官员报称:‘塔尔辉处江之北岸,原有渡船一只,对面江之南岸哈尔滨亦有渡船一只,其中有沙洲一道,两岸之渡各摆各岸’,这个岛屿便是《大清一统舆图》所标绘的与塔尔浑托辉相对的岛屿所在,是为呼兰与阿勒楚喀江中之分界。据查,哈尔滨江段南北渡船初于1777年相设,距1709年《皇舆全图》实测哈尔滨地形的时间仅差68年,进一步印证了这片岛屿的存在。满族除了用形容词‘扁’命名岛屿外,如‘哈尔费延岛’(见《吉林通志》第12卷第5页),还用‘扁’来命名山、河等名称,如‘哈勒费延山’(见《吉林通志》第18卷第23页)。‘哈勒费延河’(见《钦定盛京通志》第20卷第20页)。由此可见,满族用‘扁’命名并非鲜见。”②纪凤辉:《哈尔滨地名由来与哈尔滨城史纪元》,《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
《大清一统舆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都没有“扁岛”的标识。纪凤辉的说法是推断或推测。从任何时期来看,“哈尔滨”在地理形态上都不是扁岛。黄锡惠表示:“今天的哈尔滨以扁的形状得名,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已难考求。有的研究者将通名阑入专名而认为‘哈尔滨’系‘哈尔滨屯’之省,解释为‘扁岛’,非是。”①黄锡惠:《“哈尔滨”地名考释》,《满语研究》2010年第1期。此处还涉及“扁岛”与“太阳岛”的关系。(1906年《哈尔滨及其郊区规划图》,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67号哈尔滨市住建局城建档案馆)据《滨江尘嚣录》一书记载,太阳岛“位于松花江铁桥之西侧,隔江与道里相望,面积约四方里。”并且,“惟以位于江心,独得清凉之气,故夏季酷热之时,逐成为游人避暑之地矣。”②辽左散人:《滨江尘嚣录》,收入李兴盛主编黑水丛书第12种《东游日记·外十六种》(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7-978、978页。
关成和谈到,“关于太阳岛的解释,民间流传两种说法:一是太阳岛是个圆形的岛,故以太阳名之;一说独岛上的阳光显得格外地炎热,逐以其命为岛名。”满族渔民“最初把这个小岛称作Taiya⁃on,主要是指小岛附近的水域盛产鳊花。满语词汇taiyaon,在口语里是词中与词尾音——yaon联结成一个音节,因此同汉语的‘太阳’十分音近。”因此,“把满语的地名‘Taiyaon’说成‘太阳岛’,必是由这部分流传下来的。”③关成和:《哈尔滨考》,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内部资料,1985年,第145、147页。笔者认为,他的想法仅仅是一种推测。陈士平的记叙同样不具备学术意义,“太阳岛并非鳊花鱼。据说在很早以前太阳岛一带盛产鳊花鱼,因此,满族人称这里为tai yaon(太要恩)即鳊花鱼,tai yaon,久沿成俗就变成了太阳岛了。”其实,“太阳岛并不是满语,而是地地道道道的汉语。据一位老哈尔滨人说,约在80多年以前,太阳岛的位置并不在今天的太阳岛,而是指江中的一个长着柳丛的圆形沙滩。”④陈士平:《哈尔滨探源》,内部资料,2002年,第52页。
纪凤辉判断:“继《大清一统舆图》后,1876年杨守敬刊行了《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1906年,由杨氏门人熊会贞重校再版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首次在这个扁状岛屿旁标有‘哈拉宾’字样,这不能不进一步证明哈尔滨之名的确来源于这片独具自然地理特征的扁状岛屿。”⑤纪凤辉:《哈尔滨寻根》,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第57页。由中东铁路管理局编制的1906年俄文《哈尔滨及郊区规划图》与1910年俄文《哈尔滨平面简图》,都有《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中“扁岛”相对应的位置。
哈尔滨第一次庆祝国际五一劳动节也与该问题相关联。1907年5月14日,“俄历五月一日,哈尔滨商店、饭店闭店,工厂停工。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5,000多名中俄工人在中国船夫摆渡的帮助下过江,在哈尔滨松花江十字岛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阿勃拉莫夫在集会上号召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⑥李述笑:《哈尔滨历史编年(1763-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4页。据《盛京时报》的《哈尔滨·纪劳动会演说事》介绍,“阳历五月初一日,为劳动者纪念大会,无论为商界工界,上中下等社会,凡以劳动力得衣食住者,均于是日示威运动。俄历五月一日,哈尔宾埠俄国劳动者亦拟举行此会,然因俄长官不准,故未放在铁路租界举行,而至松花江北岸聚会,共集三千余人。”⑦《盛京时报》,1907年5月22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928年的《哈尔滨街市全图》显示,“太阳岛”与“十字岛”是两个不同的方位和称谓。这说明“太阳岛”与“十字岛”并不是同一个位置,亦不是同一个名称。“中俄工人在中国船夫摆渡的帮助下过江”与“松花江北岸聚会”等信息表明,中俄工人不可能在江心的岛屿集会,而是在松花江北岸现太阳岛聚集。因为不管“5,000多名”还是“三千余人”也说明,如此众多的人数亦不太适合在松花江的江心岛举行相关活动。
日本人绘制的1933年《哈尔滨市街全图》和1944年《哈尔滨市街图》中都有“太阳岛”的具体方位。①俞滨洋主编:《哈尔滨·印象》(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24、33页。日文版的《观光哈尔滨》的太阳岛位置与前两图相同。1944年《哈尔滨市街图》中的太阳岛已经出现断裂。《观光哈尔滨》的出版时间应该在1944年之前,因为该图太阳岛已经出现了侵蚀。这是地理学上潮汐的结果。松花江受潮汐作用侵蚀北岸。1946年《哈尔滨市街地图》中标有太阳岛字样,但是1944年地图中出现断裂的东部岛屿,在1946年地图中已经消失。剩余部分也因为同样原因最终消失。这就出现了以现在太阳岛的位置取代已经消失的江心岛的太阳岛名称。
《乾隆十三排图》中标有松阿里乌拉、阿尔楚库和屯、阿尔楚库比拉、拉林比拉等汉文地理位置,然而并没有“哈尔滨”等地名字眼。
同治二年(1863)的《大清一统舆图》中标有塔尔浑托辉、阿勒楚喀、哈勒楚喀河、拉林城等地名,但是没有关于“哈尔滨”的地名信息。
光绪十六年(1890)《黑龙江舆图》内容丰富,地图中不仅有“哈尔宾”“大哈尔宾”和“小哈尔宾”等重要的与“哈尔滨”地名相关的内容,而且还对一些地名的变迁进行了解释,如阿勒楚喀即阿尔楚库,即金史按出虎,北盟汇编作阿芝川。
纪凤辉著文:“笔者案查《黑龙江舆图》,看到距‘大哈尔滨’东南11 公里还标有‘小哈尔滨’字样,并在距‘大哈尔滨’西北31公里即靠近江边还标有‘哈尔滨’字样。另外在四方台至阿什河下口止的一段松花江南岸上,还依次有四方台、顾乡约屯、马架子沟、田家窝棚、苏家店、路家店、喇嘛屯、三棵树等村屯。值得注意的是,在松花江南岸方圆21公里内,由西北至东南几近一条直线上标示着哈尔滨、大哈尔滨、小哈尔滨三个地名。这不能不说明一个问题,即三者之中必有其一是哈尔滨的原址,而绝不可能都是哈尔滨的原址。”②纪凤辉:《〈黑龙江舆图〉与哈尔滨地名》,《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关于此段介绍,笔者将要商榷的问题,一是“11公里”“21 公里”和“31 公里”是怎么计算的?二是“哈尔滨”“大哈尔滨”和“小哈尔滨”的“滨”怎么不是地图中的“宾”?由“宾”到“滨”,不仅仅是字的不同。三是“哈尔宾”是如何突然出现在地图上的?
纪凤辉还概括了关成和《哈尔滨考》中的观点,关成和强调:“把古村名阿勒锦,按阿·伯方言的语言用汉字标出的哈拉宾正式改为哈尔滨,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官印《黑龙江舆图》上反映出来的,从此即成了该城名的定译”,阿勒锦村“当在马家沟河及阿什河中间的高地平原的北端,即《舆图》所示‘大哈尔滨’附近。按该图以方格计里的方法推算,‘大哈尔滨’约在和平乡的成发屯一带。”③纪凤辉:《〈黑龙江舆图〉与哈尔滨地名》,《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其中,“城名的定译”是纪凤辉对关成和观点的误读。
关成和在《哈尔滨考》一书中描述:“哈尔滨东部偏北和西部偏南地区多沼泽、洼地,远不如马家沟河及阿什河中间的高地平原更适于‘筑室’生息。并行的两河之间,特别是偏东处,是一个南北狭长的矩形地带。每当大雪封门时节,自海沟河北行,只有这条岗地最为通畅。据《黑龙江舆图》标示,阿勒锦村当在这条岗地的北端,即该图所示‘大哈尔滨’的附近。按《舆图》以方格计里的方法推算,‘大哈尔滨’约在和平乡的成发屯一带,该屯南与穆宗驻地、北与黄山①即荒山,今皇山。哨所相距各约十余华里。”同时,他表示,“古阿勒锦村的邻近地区,在《舆图》问世的前一年,已被帝俄筑路当局非法更名为松花江市,而该图在阿勒锦村故地一带着意标记‘大哈尔滨’四字,其目的无疑是在于通过重申当地的历史地名,以维护国家的主权。此举,不啻表示地名哈尔滨,就是女真语村名阿勒锦在这时的汉译。”②关成和:《哈尔滨考》,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内部资料,1985年,第22、23页。
据俄侨资料记述,“哈尔滨这个名称,就其起源有多种说法。俄人的说法是哈尔滨的称呼是来自一个不大的村落‘ХАО—ВИН’(哈奥-比恩),这一点可由长期从事远东旅行,并于1896年逆松花江而上深入中国东北的Е.Е.阿涅尔特的日记得以证实:最初在松花江两岸见到一些小树林,哈尔滨现址的下游4公里的南岸,有一个小村子‘ХАО—ВИН’(哈奥-比恩),距江边大约8—10俄里的高岗上,有一个田家烧锅(香坊),‘ХАО—ВИН’当年是阿什河的码头,距离该处约为45 俄里。1898年5月5日,田家烧锅及附近土地被铁路收买,作为码头及铁路工程局驻地。”③赵喜罡、郭秋萍编译:《他乡亦故乡——俄罗斯人回忆哈尔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据日本学者的研究,“1898年2月,决定选择铁路干线预定线和松花江的交叉点,作为铁路建设局的据点,并命名为松花江市。松花江是源于满语,意思是天河。可是不久,松花江市就按着当地的地名改称为哈尔滨市。在1900年制作的地图里就表明了‘哈尔滨市’,但车站表明是‘松花江’站。”④[日]越泽明著,王希亮译、李述笑校:《哈尔滨的城市规划》,哈尔滨市城乡规划局内部资料,2008年,第16页。这说明1898年之前,就有了“哈尔滨”地名,可解释1899年的《黑龙江舆图》中标有“哈尔宾”一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皇朝省直舆地各志》中的“吉林全图”里标有混同江、呼兰河、拉林、阿勒楚喀城等地名,然而亦是没有“哈尔滨”地名相关的标注。
三、“哈尔滨”:语言学与历史学的相遇
关于“哈尔滨”一词在档案中出现的时间,纪凤辉指出,“王尚德之子王连茹禀称:‘切自高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搬居拉林、罗金承领官网,并令按年交纳课税。’由此可证,‘哈尔滨’一词出现的确切时间,可以确定为1763年。”这是因为“1869年拉林协领永海呈称:‘案查拉林原于罗金、报门、烟墩、哈尔滨沿江一带设立官网,捕打贡鲜,应进鳇鱼、白鱼由来已久,已逾百年。’”但是,这个推断是没有根据的。在此之前,他还查阅档案,“窃因网户(王尚德)自道光二年(1822)间江水涨发,冬网碍难捕打。当经报明衙门,饬令于罗金、报马、哈尔滨等处设立鱼圈,修造渔船,着夏秋捕鱼上圈,备输贡鲜。由此确知,‘哈尔滨’一词至迟在1822年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说法是可行的。后来,他还“推断哈尔滨网场最初‘曾闲散满洲’的时间大致可在雍正年间(1723—1735)。与此同时,‘哈尔滨’这个名称必已出现。”⑤纪凤辉:《哈尔滨寻根》,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第46、46、45、47页。这还是臆断。这些源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并没有解决“哈尔滨”的最早出现时间问题,也没有证实“哈尔滨”地名与地理方位的统一问题。
在《哈尔滨寻根》一书中,纪凤辉没有利用《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三幅重要的地图。同时,他使用的《盛吉黑战迹舆图》《大清一统舆图》《拉林舆地全图》《黑龙江舆地图》与《哈尔滨草图》等都不是原图,为照图手绘,而且还有标识错误,如《大清一统舆图》(1865)的时间应为1863年,《黑龙江舆地图》(1897)改为了《黑龙江舆图》(1899)。
《哈尔滨指南》卷一总纲言,“哈尔滨三字系满洲语,译成汉文即打渔泡之意义或译为晒渔网三字。”①殷仙峰:《哈尔滨指南》,东陲商报馆,1922年,第1页。在1923年的《东省铁路沿革史》的《序言》中,编辑委员会尼罗斯提到,“回忆二十五年以前,松花江左右均圹土沙堤、荒凉满目,即本埠之香坊田家烧锅亦不过冷落一村,茅茨土舍。”②[俄]尼罗斯撰,朱舆忱译:《东省铁路沿革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据1929年出版的《滨江尘嚣录》一书介绍:“哈尔滨三字原系满洲之语,有谓为晒渔网之义,有谓为打渔泡之义,惜不佞不谙满语,不敢率然决定,但敢证其确为满语也。”③辽左散人:《滨江尘嚣录》,收入李兴盛主编黑水丛书第12种《东游日记·外十六种》(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3页。《哈尔滨特别市市政报告书》开篇讲:“哈尔滨为前清旗族晾网之地”。④《哈尔滨特别市市政报告书》第一册,内部资料,1931年,第1页。《哈尔滨四十年回顾史》⑤《滨江日报》(1938年9月—1943年2月)连载《哈尔滨十四年回顾史》。《滨江日报》是日伪统治时期在哈尔滨出版的半官方报纸,连载内容涉及地亩、行政、司法、江防、教育、工商、设治、交通考纪、电业电报、廿四节令、矿产事业、江堤船务、特区津梁、军政经过、公安警察、滨江市政、特别市、未来建筑、修建文庙、历代祭祀、外交宗教、古石古印等问题。记载:“哈尔滨距阿城九十里,原属阿双两县界地,水路通衢,为金之要地。”“当未筑中东路时归双城管辖,清光绪二十二年,俄人与我国订立合同,修筑铁路,始划分区域,别为道里,道外。道里曰哈尔滨(译义未详,或曰即晒网之义,未悉何考),道外曰傅家店以此地系南北通衢,有傅姓开店于此。”⑥《滨江日报》,1938年09月14日第3版。哈尔滨于“俄人筑路前,距今约三十年,固一片荒凉野场,共命名之来源,于汉义,绝无讲解。哈尔滨三字,原系满洲之语,有谓晒渔网之义,有谓为打渔泡之义,昔不佞不谙满语,不敢率然决定,但敢证其确为满语也。”⑦《滨江日报》,1938年10月02日第3版。从语言学角度看,“地名由语词构成,属于语言词汇的一个部分。作为语词,它除了有口头的字音和书面的字形外,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一定的词义。地名的语词性特征,主要就体现在这词义之上。”⑧干树德:《地名学与历史地图》,《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王坪在《哈尔滨半世纪》一文中指出:“‘哈尔滨’是满洲语,译成汉文是‘打渔泡’或‘晒渔网’的意思。由此可知哈尔滨原来不过松花江边一荒村。自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中东路兴筑以后,哈尔滨才慢慢地脱落原始本色。”⑨《生活报》,1948年5月26日第3版。哈尔滨报业发展史中曾经出现两份《生活报》。第一份“《生活报》创刊于1948年5月1日,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委托东北文化协会主办、专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4开4版报纸,5日刊”,“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当年12月6日,《生活报》迁沈阳出版。在哈尔滨期间共出版44期”;第二份“《生活报》由黑龙江日报社主办,1984年10月6(日,笔者注)创刊,4开4版,套红印刷,每周3刊。”(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报业广播电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3、104、121页。)第二份《生活报》发行至今。哈尔滨之历史,“发轫于西历1898年,旧俄帝政时代之建设中东铁路,辄以此间为侵略远东政策根据地,自是厥后扶摇直上。”⑩《盛京时报》,1936年08月06日,第7版。据1923年的《东省铁路公司成绩报告书并简明大事记》介绍,“本会(东省铁路历史委员会)详加推求以俄旧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本路副监工依格纳齐乌斯代表茹总监工由海参崴督率全部路员到哈视事之日,认为本路开始修筑之纪念日,较为适当。”①《东省铁路公司成绩报告书并简明大事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俄历的“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即公历的1898年6月9日。这是把俄历与公历的5月28日混淆。同时,需要梳理的问题是从“晒渔网”到“晒网场”的转变。
《哈尔滨探源》一书的结论是,“虽然哈儿宾与哈尔滨语音相同,但是,哈儿宾为女真语,而哈尔滨为蒙古语,音同义不同。”②陈士平:《哈尔滨探源》,内部资料,2002年,第60页。在《“哈尔滨”地名考释》一文中,黄锡惠得出肯定性结论:“今天哈尔滨地名之语源并不是什么‘女真语’,词源也绝非所谓的‘哈尔温’,语义更与‘天鹅’毫无关系。”而是“来自满语口语‘哈儿边’,其规范满语为‘哈勒费延’,汉意为‘扁’。”③黄锡惠:《“哈尔滨”地名考释》,《满语研究》2010年第1期。石方按照模糊史学的理论来分析:“‘扁状的岛屿’是指其形状而言,‘晒网场’是指其作用而言;先将其‘模糊’为‘形状与作用’,后将其‘清晰’成哈尔滨是满语‘扁状的晒网场’之意。”④石方:《哈尔滨地名含义新诠——从“模糊史学”的视域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辞海》亦说明,哈尔滨“原为一渔村,铁路通车后逐渐兴起,1932年设市⑤1932年设市,应该是哈尔滨特别市。哈尔滨历史上曾出现四次“特别市”:1926年11月第一次称“哈尔滨特别市”。1933年6月是第二次,此时为日据时期。第三次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将东北划分为9个省2个特别市,其中将哈尔滨定为特别市;第四次在1946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后。1947年6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布中国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方法,东北被划为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嫩江省、黑龙江省、兴安省九省。与现在哈尔滨行政区划有联系的是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嫩江省四省。笔者认为,不能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模糊地认识哈尔滨过去的行政归属。。‘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⑥《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894页。
小 结
“哈尔滨”地名的研究可能是我国城市历史研究的一个特殊个案,从地名的语言来源到地名的具体含义,从地理方位到名称变化,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争论可能还要继续下去。地图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作为图像史料的地图的使用,可以使“哈尔滨”地名的考证得以拓展和深化。新材料的挖掘和使用是历史研究创新的重要途径。历史研究是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问题。语言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历史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的探索,但是需要处理好主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