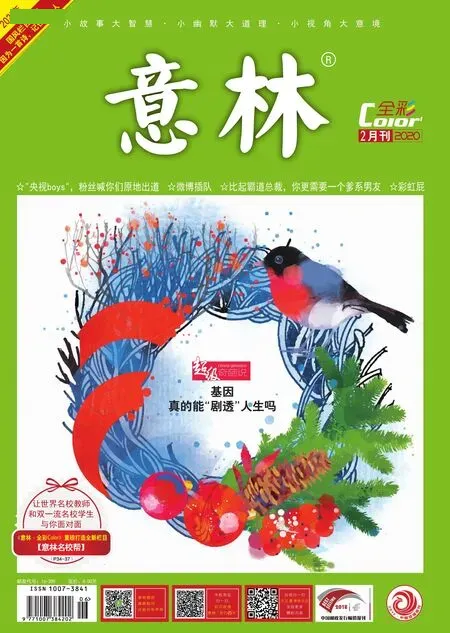少年与红鲤鱼
□连 生
孩童时代,有一年天气很冷,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太阳升起来了,河道的中间融化了,河水便顺着雾气流动起来。在村子里待不住的鹅、鸭们摇晃着来到河边,旁若无人地啄食着两岸的荒草,不一会儿,一双双脚丫儿都滑向河中央,随波嬉戏起来。
最早发现河面上有浮鱼的是于伯,他是位勤快的老人,每天总要起早到河边遛弯儿,当他看到河面上跌跌撞撞的鱼群时,他伸出手捉了两条。那些鱼徒劳地呼吸,再也没有挣扎的力气。于伯扔下自己抢网的渔具,一路小跑着回到了村子里。
河湾里又来了鱼鹰船,那些外乡人又来我们这里捕鱼了。黝黑的小船头立着几只鸬鹚,我们都习惯叫它们水鸭子。它们的喙可不同于家鸭那扁圆的嘴,它略带弯钩,恍如一支支专门捕鱼的利箭。捕鱼人一抖竹竿,它们如得了圣旨的士兵一样,一头扑向水面,潜入水底。一会儿,在附近的水面冒上来一只只机警的脑袋,有的噙了一条小鱼,有的一无所获,左顾右盼地观察之后,便各自争先恐后地潜入潜出了。这时的河面上热闹异常,人声、鸟声便在这河湾里弥漫飘散。
那些水鸭子脖子上都勒着一根儿细绳,那是捕鱼人害怕它们偷食,刻意绑上去的。那根细绳在我眼前晃动,还有那些气喘吁吁水淋淋的水鸭子。捕鱼人会在心情好时,丢给它们几条小鱼,可是,出来靠捕鱼谋生的他们很少心情好,我无数次幻想剪断那些套在水鸭子喉咙之间的绳子。但我不能靠近它们,假如我潜入水中伺机游近,往往一丝轻微的响动都会让它们惊慌失措,四散飞逃。捕鱼人的竹竿无情地横在我的面前,我择去头顶的杂草,浮出水面,和捕鱼人短时间对峙之后,便使劲吐上一口唾沫落败而逃。

河边已经有人在捡拾了,那些失去了平衡摇摇晃晃而来的鱼群,从我的眼前如醉酒般游过。我开始沿着河岸一路狂奔,三里外的水坝上,放干水的河床裸露着青黑的淤泥,捕鱼人穿着连身的皮裤,在水里来回地走动,不时扔上岸一条条巨大的鱼。他们的水鸭子不在这里,如今他们也不再依靠它们了,这条河里的鱼都要被捉完了,他们不再需要那些顺水而下的小鱼。一尾三尺长的鲤鱼跃出了水面,红色的鳍,晶亮的肚腹,它用力跳跃着,拍打着,躲避着那些在水中笨拙转身的人们。祖父曾经说,红鲤鱼是我们河湾的河神,保佑着这条河两岸居住的人们。在此之前我从未看见过红鲤鱼,它只生活在我和伙伴们的想象里。红鲤鱼是有灵性的,它不可能被人这么轻易地捉到。那条红鲤鱼在河床与天空之间不断地腾跃着,它用力拍打着红色的尾翼,一次次挣脱捕鱼人的围堵。河床中间的那片水面越来越小,红鲤鱼的一次次腾跃,显得力不从心,它的鳃边已开始流血……捕鱼人兴奋地吆喝着:“拿鱼叉来!”他们高举手中的鱼叉瞄准那尾红鲤鱼。
站在河岸上的我,看着那条红色鲤鱼,它在阴冷的冬日里,绽放着温和的暖意,炫目得令人不敢逼视。我飞身扑去,在我用手触摸到那光滑冰凉的鱼鳞之后,便昏了过去。当我醒来之后,已躺在自家的床上了,母亲生了一大堆火,正在烘烤我的棉衣。红鲤鱼呢?红鲤鱼呢?我问。母亲说,养在外面的水池了,还活着呢!“小哥醒了,小哥醒了!”一抬头,我的小伙伴都围在床边,花白胡子的于伯也来了,他抚摸着我的头说,傻小子,好样的!
抱在我怀里的红鲤鱼是属于我的。捕鱼人并没坏了规矩,他们的鱼叉在我纵身跃下之时,定格在冬季的空气中,他们不会想到一个少年会突然跃入水中和他们去争夺一条鱼,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一条稍大一些的鱼而已。看到穿着棉袄棉裤跳入水中的少年冻昏过去,他们还是感觉到一种畏惧。
“这小子像条鱼,贴着我的鱼叉飞过去。”他们惊魂未定,对我的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