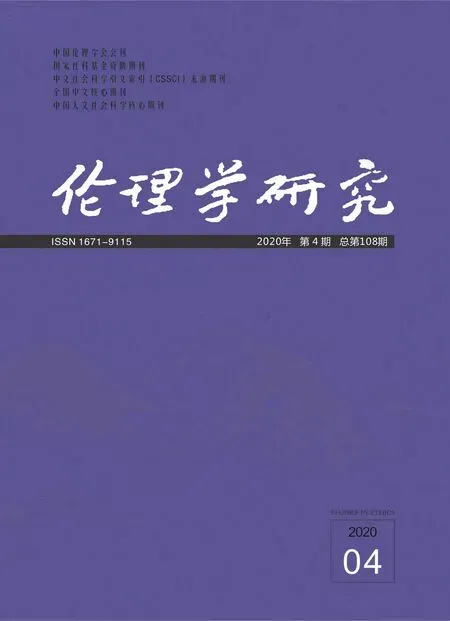《白虎通》“血缘情感”道德价值论证及其反思
冷兰兰
西周以降,宗法血缘制度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血缘”以及与“血缘”相伴而生的“血缘情感”,在表达着有限的个体自由意志的同时,更是成为社会统治意志的工具化存在,缔结出种种以“血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与“血缘”关系一起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被最大程度地运用于论证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白虎通》的成书便是基于这种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的需要。汉章帝时期,由于朝局飘摇、土地割据、外戚蠢蠢欲动、贫富分化等问题,对国家秩序、社会规范等进行系统的修订和重塑乃是当务之急。所以,《白虎通》看似是对五经进行修订,本质上却是对社会现实的理想设计。本文基于《白虎通》谈“血缘情感”的道德价值,对“血缘情感”的内涵主要从两个方面的关系来把握:一是血缘关系,即:人类因生育而自然形成的,具有生物性、社会性、遗传相关性的伦理关系,是人出生后第一次进入的人伦关系,也是与“别人”最开始、最原始的关系。同时也是最终造就“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1](P21)的一种决定性关系;二是血缘情感关系,在以“血缘”为核心的人人关系的交织与捆绑中,人与人“相连”的“家族式社会”得以建立,并以此为核心辐射形成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网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被凸显,形成了“同血缘”“不同情感”的血缘情感关系,以及由其衍生而来的“拟血缘”“同情感”的关系。其道德价值的论证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血缘情感“同质”天人关系
早在原始社会,受自然生产条件的限制以及认识能力的制约,神秘巫术、图腾崇拜、器物崇拜、祖灵崇拜成为人类对未知事物的一种“寄存式”想象,总是与人们生活中琢磨不透的东西混为一谈,极大丰富了“神明”或“天”的实体性内容,成为与“人”相对的一种神秘的客观存在,给予人们对未知事物更多的寄托与想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人们在现实的劳动生产实践中将某种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之物视为“祖先”或神明加以崇拜,认定自己的部落是受图腾或神明庇佑的后代,当有族群内的先人逝去时,便想象其是追随先祖神明而去了,形成了事实祖先被神化的伦理设定。如此一来,“任何家庭都有自己的祖先,祖先是神或者正在变为神,神作为祖先和父辈而被信仰着”[2](P19-22),这种人与神之间的链接,不再是个体人神之间的链接,而是从抽象性走向了现实性、普遍性,人神之间不再是冰冷的物我异质关系,而是现实的具有天然性、亲密性、特殊性的血缘关系,“物我关系”的“同质”找到了“质点”,并开始以此为线索从多个方面力证“物我同质”何以可能。像早期的“感生说”就认为,“ 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3](P101),所以降生了黄帝、炎帝、后稷、禹、汤等等。从本质上说,这种“物我同质”对后世“天人关系”的论证给出了两重暗示,一是人神之间有着天然的血脉传承关系;二是神或天也不外乎是“人”的另一种存在形态。
就实体形象而言,《白虎通》认为“天”与“人”都有着同样的血肉组织,只是以一种超乎人类的形式而存在罢了,延续《春秋繁露》的记载,认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4](P477)乍一看这种论调似乎有些没头没尾,纯粹是“天人相类”的比附,但事实上这种论证本身有其内在的逻辑,其逻辑起点就在于这种推测是基于人祖之间的“血缘”传承关系,也就是说这种论证是建立在已有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有了这层血缘关系,才衍生出“同类”相近的血缘情感,使当时的人们对“天”的实体形象的附会给予了情感上的允许。这才有了“天”之366 日以拟人之366 节小骨,天之12 个月比拟人有12 大骨,天之五行元素比拟人有五脏,天之四季比拟人之四肢,天之昼夜比拟人之醒眠,一个活生生的人形“天”得以塑造完成,也就完成了从“种”的特性上对“天”进行类的划分,显然“天”与“人”同类,“天”正是抽象意义上的“人”。“天”与“人”既然是同类,那么二者以什么样的关系状态存在呢?有证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4](P398)也就是说,天人之间是一种生养关系,不仅人的“形体”与天相副,人的“血气”“德行”“好恶”“喜怒”“寿命”都是承天而成,均是以祖先可能是“神”作为理论自信的,《白虎通》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在这当中,血缘情感发挥着情感认同的重要作用,在现实意义上为同质“天人关系”提供了情感意义上的群众基础,在理论上则提供了逻辑前提与逻辑线索的支持。
借助这种生养关系的天然性、权威性及伦理正当性,《白虎通》以“由此及彼”的手法论证了天与人的种种血缘联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天”与每一个人都是生养关系呢?显然并非如此。“天命”并非均等地降临在普罗大众身上,而是选择符合一定条件的人成为真正的天之子,也就是“天子”。对此,《白虎通》认为“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5](P2),且“ 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生 称王”[5](P43),“德合天地”的“人”才能成为天选之人,此人必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臣下谓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5](P47)。尽管“天子”的合法化身份在实际生活中总是以神谕或“兆”的方式得以预设,但却从血统上赋予“天子”与“天”直接的生养关系,这种直接的、天然的血缘关系预示着血统上的独特身份,更意味着“天子”的政权拥有着与生俱来的伦理正当性与合法性,“天子”由此拥有“天王感应”的特权。有了“天子”与天之间的关系范式,人间社会的人伦秩序建设也就有了理所当然的依据,那就是将这种血缘关系的传承继续向下延伸,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里就说到:“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4](P557),《白虎通》则进一步认定“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5](P4)。将“天子”与臣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同样以“拟血缘”的形式链接起来,通过“天子”将“天”的血统延伸至普通民众,使得“天子”又获得了统领人间纲常的权力。至此不难看出,“天子”如同神的代言人,上承天命,下统民心,拥有着近乎“神”的身份与地位。如此一来,天与天子、天子与臣民之间均以血缘为纽带,统一于同一个道德预设,政治秩序、人伦规范等也就以最有说服力和信服度的方式在全社会推广开来,使得政权分治者大多是“天子”的血脉族人,如子女、兄弟等,由周代“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内之邑”[6](P238),亦可见一斑。为了巩固、回应这种天人关系“同质化”的观点,《白虎通》又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着手,寻求着“天人关系”“同质化”的证明,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统一起来,形成彼此呼应之势,“天道”由此成为人们当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一是在人伦关系上基于血缘情感倡导“忠孝”观。基于血缘与血缘情感,将全社会人伦关系划分为“三纲六纪”,囊括了全社会应有之关系状态,使整个人类社会形成了以“家”或“宗族”为基本单元结构的组成,凝聚出近乎信仰的血缘关系及血缘情感关系,天道与人道实现了“忠孝”价值观的统一;二是在社会道德规范上基于血缘情感倡导“事天如事亲”[7](P966)。上至君臣下至平民百姓,均要对天地、山河、鬼神、先祖行祭祀礼,《春秋繁露》认为“天子不可不祭天也,无异人之不可以不食父”[4](P544),同时也“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下之礼也”[4](P543),在天祭与宗庙之祭冲突之时,主张以天祭为先。宗庙丧事重在“至哀痛悲苦”[4](P543)且三年不祭,而天子祭天就如同人赡养父母,人不可以一日不孝敬父母,天子同样不可以一年不祭天,将天祭与“人养父母”相提并论,充分运用血缘情感带来的“同理心”与“共情力”,既从意识层面强化“天”与“人”血缘关系的客观实在性,又从实践层面默化了天人关系“同质”的认知;三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上基于血缘情感倡导“如天之行”。要求农业生产要与上天的“四时”“八风”规律一致,人的作息要与“昼夜长短”相一致,君王一日四餐“平旦食”“昼食”“脯食”“暮食”要与其居中央管理四方的权威一致,行军打仗要与“天道一时生,一时养”[5](P209)相一致,而商旅军事活动“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5](P217)也是为了坚持“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5](P217)。这种实践性的“同质”化行为,是人民基于血缘情感的信任对“天”的模仿,对天道的遵循,虽然本质上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但取得了促进生产实践的现实成果,也就反过来强化了上天的“好生之德”,具化了天人关系“同质”的事实,从现实角度将“物我”关系或“天人”关系转化成了一种血缘情感关系或拟血缘情感关系。
二、血缘情感“拟亲”人伦纲常
中国古代以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生产为物质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更容易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地域、文化及风俗习惯,再加上交通条件等的制约,先民们很难进行长距离、跨地域的人际交往与生产生活,大多以家庭为单位结构群聚而居,且常常几代不移,易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家族生活及家族关系网络。因此,早在周代就形成了“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5](P394)的宗法结构,血缘及血缘情感成为宗法社会下的“万能胶”,《白虎通》以“拟亲”的方式,将整个社会以纵向为“纲”横向为“纪”的结构形态划分为“三纲六纪”,并生成与其相适应的尊卑等级关系,为夯实我国古代社会“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奠定了身份认同的坚实基础。
“三纲”是宏观意义上的人伦关系格局,从纵向角度使“天子”将天下人伦关系以“纲举目张”的方式形成了统筹。“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5](P373)君纲、父纲、夫纲的划分体现出三个层面的关系递进,在国家层面,人伦关系统归“君”与“臣”的关系;在宗族层面,统归“父”与“子”的关系;在家庭层面则归于“夫”与“妻”的关系。从“君”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父”还是“夫”都只是其统管之下的一个权力分支,都对“君”负责,君纲凌驾于父纲与夫纲之上,而父权又凌驾于夫纲之上,形成一种“闭环式”的关系链。在这个“闭环式”链条中,血缘情感关系是其得以形成的根本依据。就“君纲”而言,要求臣对君行“忠孝”之事,就是基于“拟血缘”关系确立的一种政治人伦关系。《白虎通》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方面,承继“天子”是为天之子的血缘事实,认为“帝者,谛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5](P45),以“天下所归”确立了“天子”在终极意义上的身份,即:具有生养天下的身份与能力;另一方面,从王者之所以会有臣民间接论实了臣民的“子民”身份,其原因在于“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虽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虽至灵,必有山川之化;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顺天成其道。……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5](P129-131)以天地与日月山川之间的关系为比拟对象,也就间接实现了把“臣”的身份类同于“子”的身份,把子对父的“孝”移为臣对君的“忠”,把父对子的权威转化为君对臣的无上权力,体现的正是如同父子一般的尊卑关系;“夫纲”是“父为子纲”的延伸,“夫者,扶也”[5](P376),夫妻关系构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血缘情感链接,以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血缘链接即“子女”为血缘纽带,同属于“拟血缘”关系,而“父纲”则是理所当然的血缘关系。概而言之,“三纲”都是以血缘情感关系或“拟血缘”情感关系为基础或前提的。当然其论述之辞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附会与神秘色彩。
“六纪”从属“三纲”,是从微观层面进一步理顺其他人伦关系的一种分类做法,所以“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5](P373)“六纪”关系依然是“三纲”的延伸,其依据不外乎是血缘情感或“拟血缘”情感。《白虎通》中有论:“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也。”[5](P375)其中“诸父”“兄弟”“族人”都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关系状态,遵“父子”纲;而“诸舅”“师长”“朋友”则无直接的血缘关系甚至无血缘,其中“诸舅”虽然是依夫妻关系的存废而存废,有一定的血缘联系,但更适合划入“拟血缘”之列。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父族对其势力安全的保护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出现了人为的远母族而近父族的现象,比如在《白虎通》“九族”篇中有言:“礼所以独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后,民人皆厚于末,故兴礼母族妻之党,废礼母族父之族,是以贬妻族以附父族也。”[5](P400)由此,原本属于“血缘”人伦的关系被置于“同志相助”的利益关系中,故从夫妇之纪;“师长”“朋友”则是完全无血缘关系的两种人伦关系,涵盖面甚广,且有其自身的内涵和建立依据。《白虎通·辟雍》篇中谈到“师长”关系时说到:“师弟子之道有三。《论语》‘朋友自远方来’,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视予犹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义教也,君臣之道也。”[5](P258)“师长”关系是最为特殊的一种关系,遵从“君”“父”“友”三重内涵,既要有“君臣”之尊,又要有“父子”之情,还要有“朋友”之义,其关键在于拟血缘的情感在起着链接作用;“朋友”关系同理师长关系,“朋者,党也。友者,有也。《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5](P376)讲究的是同门之谊、同好之情、志同道合,是以师长关系的存在为最初的前提,逐渐扩大化为志同道合的人,而志同道合的人的所学所识,又可归根于同宗同源的师长,由此也就使得朋友关系如同师长关系,是后天建立起来的拟血缘的情感在发挥着凝聚作用。
通过“拟亲”人伦关系,基本确立了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人伦秩序及规范,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以“拟血缘”为基础向外展开,其中最主要是以“父子”血缘关系为轴向外展开“家族生活”。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主要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而展开出去的,所有在这伦常关系中的人的行为都以父子关系为准则。”[8](P23)这意味着对人我关系进行血缘关系的模拟或类同,血缘之情也就转移到人我之情的建设当中,由此又形成了区域化的地缘文化、地缘关系,这种基于血缘情感而形成的人伦关系与人伦文化最具凝聚力和影响力,宗族所在之处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精神寄托之所,宗族文化或者说地域文化也由此具有强大的内生力,代代相传。哪怕到了当代社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同族成员在地理区域上逐渐分散,人们生活的社会逐渐从“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社会交往范围从时间、空间、地域上都被无限扩大,血缘情感或拟血缘情感却依然是个人开展新型社会关系的凭仗,现代人依然本能地基于传统“宗族乡村”式的社会结构,对血缘关系进行各种模拟,甚至不自觉地掺入地缘因素,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拟亲”关系的结合更加紧密,人际模拟的可能性更多,所涉及范围更广。如今天所说的同乡关系、邻里关系、“四海”概念、“同洲”概念、“地球村”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对个人而言,“拟血缘”能让个体在陌生的环境中感受到“人情味”,并因“亲人之情”而凝聚出更大的集体力量;对民族、国家发展繁荣而言,“拟血缘”情感有利于家国责任与使命的集体承担,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兄弟国家”等就是这种血缘情感的现实辐射。但是其缺点一样存在,那就是以血缘情感为链接的人伦关系偏重于感性层面的“共情”,却相对缺少理性的思辨,一旦“共情过度”就会导致“共情伤害”。
三、血缘情感“名定”资源分配
“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都是社会控制的结果。社会控制是实现社会秩序、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必需手段”[9](P140)。社会要正常运转必然意味着一些最基本的秩序性,如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精神资源等的分配须呈现秩序性,所以社会控制的范畴也大抵如此。在古代社会,“名”就充当了这样一种极具政治色彩的控制工具。纵观诸子典籍,我们能够看到,各家各派几乎都曾或多或少地讨论过“名实”问题,并且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如何处理好“名实”关系问题对国家治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白虎通》一书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汉代社会正面临着封建政权难以高度统一、诸侯纷争不断、土地割据严重、贵族权力膨胀、社会礼仪秩序混乱的局面,这恰恰是一个需要“治乱”的历史场景。所以,《白虎通》开篇论爵共十篇,从“上论天子为爵称”,到“制爵五等三等之异”,再到“妇人无爵”,而“庶人称匹夫”,最后到“追赐爵”“诸侯袭爵”以及“天子即位改元”,从官制角度对各种爵号、名号、人伦身份做出了宏观的安排,而其后的“号”“谥号”“名”“五祀”“三纲”等篇也都是围绕着“名”的划分及内涵展开大篇幅的阐述,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其“正名”以“正实”的政治目的,渴望通过“名实”关系的辩正来实现人们自我意志与自我身份的同一性认同。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深察名号”时指出的那样:“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4](P366)所以治国必先“正名”,方能“正一而万物备”[4](P156)。
“正名”何以具有这样一种权威的社会控制地位呢?一方面,“名”如同身份权利的伦理表意,基本规定了臣民社会个体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分配原则,偏向于理论或制度层面的建构,而“实”则是以“名”为指导的现实做法,是对“名”从现实举措角度做出的行动分解,侧重于实践意义上的构建,二者是类同认识与实践这对辩证关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名”与血缘情感相伴而生渗透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班爵制号”“制礼行仪”到“礼乐器物”的使用,都是既遵从“名”的规定又符合血缘情感的伦理规范,“名分”“位份”往往与人伦身份相统一。如“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5](P2),“帝者,天号也”[5](P71),“明位号天下至尊之称,以号令臣下也”[5](P47),天子的名、爵、号都来源于“父天”,臣民的“名”也就同此逻辑了。由此,“名”不仅成为社会道德规范的对象化标准,更是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资源分配的一般法则,现择其重点表现论述二三。
一是“名定”权力资源的分配。“三纲六纪”的确立,将“君”与“父”二者一开始就置于人伦血缘的“制高点”,从根本上保障了“君”“父”区别于其他身份角色的特权,并显著地表现在“名定”权力资源的分配活动中。一方面,“名定”权力资源的支配权。“君”“父”“夫”以“三纲”的姿态直接享有社会资源分配的决定权,带着“以父之名”的色彩,理所当然地享有各方面社会资源的最大占有权和决策权。对于君王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P142);而对于宗族的父家长来说,“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5](P376),父家长是宗族范围内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掌管整个宗族的资源分配,有权制定“家规”“家法”,行使父家长的权威;对于一家之主的“夫”来说,“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5](P376)。丈夫在家庭中享有绝 对的支配权,妻子处于从属地位,必须要“屈服”于丈夫,女性血缘被人为地“外化”为家族血缘的“外系”血缘,将血缘性别上的“男女区别”“名定”为“男尊女卑”,哪怕在同父同母的血缘延续中也保持着“儿尊女卑”“男贵女贱”的观念,儿子被看作权力的接棒者,负有延续家族血脉、继承并发展家族权力和财富的权利,而女儿只被要求学习从父、从夫及敬兄之道。另一方面,“名定”权力资源的分配原则。在王权继承、父权继承上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0](P2)的原则。《史记·殷本纪》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11](P76)这一记载比较直观的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即:权力资源的分配,视嫡直系血脉为尊,继而才是长者为尊,这是一种人为的基于血缘情感关系延伸而来的尊卑等级的设计。也就是说,尽管是“同血缘”,却有着“不同情感”,于是要以“名”来实现“直别”“长幼”之分,使“嫡”与“贵”并举,造成“嫡”“庶”之“实”的差异。《白虎通》便“律定”了嫡庶之间的这种继承权,认为“篡者何谓也。篡犹夺也,取也。欲言庶夺嫡,孽夺宗,引夺取其位”[5](P224)。把庶位欲取代嫡位的做法看作是“篡”,定性为不合法。
二是“名定”财富资源的分配。嫡长子继承权的确立意味着尊卑等级制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贯彻。秦汉以前,别子和庶子虽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却明显区别于嫡长子。如西周时期,财产与权位的继承权被一并给予了嫡长子,别子和庶子便无财产继承的可能。秦汉以后,政府为增加税收、积累财富,强令大家族“析籍”,为了家族稳定延续,家主降低了嫡长子的财产继承份额,“众子均分”逐渐成为家族财产继承的重要原则,但在实际履行中依然存在着嫡庶长幼差异。从《白虎通》论“封地”的差等化即可见曲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人大国称侯,小者称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5](P7-10)五等爵位是“名”,封地不同是财富资源分配的“实”,爵位的确立依据的是其与“天子”血缘关系的远近,近者为“公”,次第远之,则封地次第差异,从政治资源架构层面做出了尊卑等级的差异化表率。同时,女性在财富继承上始终被拒绝进入家族核心,如,“在室女”在家族财产继承上,额度就不能超过她应有的嫁妆。
三是“名定”生活资源的分配。生活资源涉及面甚广,如教化资源、婚丧资源、服饰用度资源等等方面。就教化资源而言,虽然都是明礼仪序长幼,不同身份的人受教育的场所格局、名称却不同,“‘雍’之为言壅也,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5](P259-260)。“庠者庠礼义,序者序长幼也”[5](P262),场所的不同明确标示着“名”的不同,对于百姓来说,受教化止于知礼仪序长幼,而天子则要行天下之仪则,诸侯也只要做到天子的一半才行,这其实已经决定了教化资源的分配必然存在着“实”的差等化;就婚丧资源而言,不同的人伦身份有着不同的名实资源差异,要“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5](P457)。既要遵守长幼有序的要求,又要遵从名份差别带来的婚丧财产分配的差异,以及婚礼丧葬使用物品配备的等级差异;在服饰、器物等用度上,均有相应的等级、品级和位份。如“古者淄衣羔裘,黄衣狐裘。禽兽众多,独以狐羔何?取其轻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其跪乳逊顺也。故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狐苍,士羔裘,亦因别尊卑也”[5](P433-434)。血缘情感带来爵位“名”的不同,服饰用度之“实”也就不同,本质则是生活资源的分配呈现出差异化、等级化与阶层固化的表现。
四、血缘情感“濡化”家国情怀
马克思曾说过:“古代各国的部落是按两种方式建立的:或按氏族,或按地区。”[12](P479)而在部落的建立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血缘因素,只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血缘因素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西方国家通过引入“自由主义”,不断消解着“种族主义”“家族主义”“教派主义”中的血缘因素,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血缘情感在政权中的作用。而中国却恰恰相反,从古老部落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建立,始终延续了“氏族”方式,并且不断强化宗法血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使中华民族“犹然一宗法之民”[13](P136),无论“家”单位还是“国”单位,都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政治组织,并且“把家族(仍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变成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而且把治家的原则奉为治国的准绳”[14](P16),整个社会靠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划定尊卑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治家与治国在本质上承袭着同一套文化规范与道德模式,形成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5](P119)这样一种“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
中国人在这种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情感认知的状态下,以发乎血缘情感为基础,移孝作忠,敬仰天下,经世致用,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文化观以及利益观,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形成了高度的认同与维护,有着互利共存、荣辱与共的认知、体悟和实践,是情感与理性的双重认同,不仅内化于心更是外化于行,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中国式的“家国情怀”,其核心则在于血缘情感在其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濡化”作用。而所谓“濡化”,不同于“社会化”或者“同化”等概念,它主要是指“在特定文化中个体或群体继承和延续传统的过程”[16](P286),强调的是一种“过程性”的养成与主观的自觉,对于一些需要“继承”或“延续”的特定文化或者传统而言,它能够集传播、内化、实践于一体,是一种以教化与学习的过程来同时实现文化延续、族群自立的独特方式,常与家庭及家庭教育相伴而生,如传统社会一贯认可的“子不教,父之过”就是明证,个人的观念、心理和行为习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并在家庭或家族文化的言传身教之下发生着变化,是家国情怀得以形成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是通过血缘情感“濡化”出共同的家国价值。天人关系的“同质”与人伦关系的“拟亲”,都使得血缘关系已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简单的属性关系,更多的则是道德关系、利益关系,忠君孝亲成为宗法血缘社会根本的价值取向,特别是西汉以后,“忠孝的制度化逐渐强化,忠孝一体逐步达成共识”[17],天子通过祭祀、“立宗庙”“称宗庙”“奉宗庙”“谒高庙”“承宗庙”等方式身体力行地表达了对先祖血缘的尊重与崇拜,既强化了血缘政权传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树立了“以孝治天下”的价值理念,上到“天”、天子,下到诸侯、百姓,都以“孝”和“悌”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使得人们对血缘关系的敬畏和尊重上升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白虎通》中用了较多笔墨对天子奉宗庙的行为进行描述,表达天子“不自专”的品格,从而传达出血缘情感上“孝”的德行,如“封诸侯于庙者,示不自专也”[5](P23),“所以戒非常,伐无道,尊宗庙,重社稷,安不忘危也”[5](P199)。“王者将出,辞于祢。”[5](P202)“天子遣将军必于庙何?示不敢自专也。”[5](P207)“天子亲耕以供郊庙之祭,后亲桑以供祭服。”[5](P276)“巡狩所以四时出何?当承宗庙”[5](P290)等等,但凡涉及到班爵、军事、农桑、德行等决策性事宜,天子均要履行告知“先祖”的义务,这种告知的方式具有极强的仪式感、示范性和情境性,对于引起臣民的共鸣和仿效进而产生认同具有着感同身受的直观刺激性。所以,在寻常百姓生活中,更是要尊崇礼法的规定履行着“孝”的义务,如,在丧葬活动中,子女尽孝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居外门内东壁下为庐,寝苫枕块,哭无时,不脱绖带。既虞,寝有席,疏食水饮,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练,舍外寝,居垩室,始食菜果,反素食,哭无时。二十五月而大祥,饮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庙,去丧之杀也”[5](P516-518)。这种生活常态化的道德场景,以伦理叙事的方式“濡化”着人们的认知与实践,使极端化的尽“孝”成为内蕴于父子至亲之间的一种天然的、必然的情感表达。不仅如此,天子还主张对有丧之臣给予宽恕与仁慈,认为“诸侯有三年之丧,有罪且不诛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罚”[5](P212)。“臣下有大丧,不呼其门者,使得终其孝道,成其大礼”[5](P529),这就进一步把“孝”转化为家国同构的共同价值底线,因此也就有了“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7](P926)之说。
而“忠”则是比拟于“孝”产生的道德承诺,《白虎通》中认为:“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5](P219)以拟血缘情感带来的“恩义”为纽带“移孝作忠”,将臣对君的“忠”和子对父的“孝”,理解为形式不同但内涵一致的血缘情感表达方式。但是二者之间的链接尚不止于此,而是体现在“过程性”的对接上。如,要实现伦理准则上的至孝,不仅要做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18](P5),更要做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18](P5),全社会由此形成了“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8](P6)的完整价值链条。从表面上看,是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孝敬父母联系了起来,将“事君以忠”作为实现“孝”的手段,“忠”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孝的践履。然而从本质上来看,这恰恰是构建起了一种价值“濡化”的全链条,突出体现了其“过程性”特征,这种价值链条将“人”的一生分成了三个价值层次的同时也分化成几个阶段,但始终被捆绑在血缘情感关系的要求之中。如:幼时得父母抚养,在家族成员的言传身教下,羊羔跪乳的血缘之孝是必然的信仰;得以长成,要“显父母”而“事君”,才能忠孝两全;成家立业,唯有做到既忠且孝的行为规范,方有终其一生的立身之本。这样一来,人生就是一个实现“孝—忠—孝”的动态化建设过程,而且,这种“过程式”、生活化的方式,不仅使民众在理性上对君主绝对服从,而且在感情上自觉形成了父权认同,将“君”和“国”等同了起来,君成为国的代表和象征,“忠君”即是“爱国”,一些族训中甚至直接主张“国难尽忠”,“忠孝”由此成为家与国共同的价值准则。
二是通过血缘情感“濡化”出共同的家国实践。在“家国一体”思想的指引下,统治者从制度层面打通了“忠孝”之间直接进行转化的通道,通过入仕制度开辟了家国命运同构的实践。《汉书》中多有记载“举民孝弟力田”“举孝廉”等做法:“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19](P66)“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9](P114)“举孝廉”是汉代察举制中的岁科之一,然,不仅岁科中出现“孝”的要求,在不定期的诏书中,也直言要求举荐“孝弟”者,例如,宣帝时期颁布的罪己诏中就有言:“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19](P175)同时,对于这种德行,皇帝还会给予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嘉赏,《白虎通》中就记载了将享有“宗庙之盛礼”美名的“秬鬯”匹配给有孝道的人,并赞叹到:“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赐以玉瓒,使得专为畅也。”[5](P307)在灾荒年间,皇帝还会赐以“田”“帛”“衣”“食”:“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19](P124)“赐……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19](P196-197)甚者,升官、受爵的制度中也取“孝”“悌”等作为考核要素,《白虎通》中有言:“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5](P289)“三年然后受爵者,缘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5](P28-29)以此,将个人的功名和个人“孝悌”血缘品德挂钩,使得个人利益、家国利益在现实意义上实现了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同样体现出“过程性”特征,那就是“孝悌”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洞的价值评判,它必须伴有长期的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更是一个运用血缘情感环境“濡化”认知的过程。与此同时,“天子”作为国家这个大“家”的家长,虽然享有被尽忠的权利,但也要为万民之表率,比如,天子日行、受教、受爵也必须遵守“孝悌”之道:“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陈孝悌之德以示天下。”[5](P248)“天子临辟雍,亲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5](P249)“天子三年然后再称王者”[5](P39)。所以天子在对待“子民”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以民为本”的义务,汉代贾谊对此阐述道:“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吏为贵贱。此之谓民无 不为本也”[20](P101)“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20](P105)。君臣之间由此结成了相互倚靠的利益共同体,天子在政治作为中也较多体现出了超越个体利益、以天下为重的精神,利于赢得民心,为激发民众自发自觉的情怀养成提供了大局趋势与濡化氛围。
结语
在“血缘情感”的生活现实下,个人价值与生活目标的实现寓于家国建设当中,个体“人”由此主动肩负起了多重道德责任:向上,有一种立“孝”名的使命感,爱戴父母、忠君爱国、向上向善;向下,有一种为子孙后代立“榜样”的责任感,言传身教、自强不息、成仁成圣。人们在个体的看似“无我”之中锻造出强烈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又在家国一体的“有我”中孕育出严于律己、敬业乐群、精忠报国等品格,使个体与家族、国家休戚与共,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凝练出中国人忠诚、孝亲、责任、友爱等特有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从未断流的中华文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白虎通》全书都在极尽说辞为“血缘情感”道德价值作合理辩护,并极尽运用之能事,企图以温情脉脉的“亲恩”掩饰宗法统治下“尊尊”的冷漠、腐朽与残酷。因此,对其进行反思也极为必要。
一是僵化的宗法血缘思维,导致个体命运被预设,禁锢了人的价值。如前所述,宗法等级制是一种以血缘为依据作出身份、权利乃至资源分配预设的制度,它并不考虑个体人的能动性,甚至压抑人的价值的主动发掘,如男尊女卑、女性“无外事”的设定,如嫡长子继承制的“先天性”,都是以血缘作为选择的唯一依据,它无法克服“统治能力的制度性下降”——“君主能力不仅会在终身专制的过程中出现波动,也会在家族继承的过程中出现波动,而世袭终身制则决定了散落在外的治国能力,无法通过政道化来防止这种波动”[21](P145)。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作了“身份”设定,个体命运几乎都是在被预设中走向终结,而家族、国家的发展只能寄望于“君统”“宗统”血脉的生殖能力抑或遗传基因的优劣,虽然具有偶发性、不确定性,但带来的却是皇权、宗权确定性的凌驾于人的选择之上,这使得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与法权上出现双重不平等,人我关系也处在被设定好的亲疏远近之中。某种意义上说,《白虎通》以拟血缘的方式“同质”天人关系,从根本上禁锢了人的价值与发展,是一种倒退的做法。
二是“拟宗法化”的三纲六纪,导致“子民人格”的形成,滋生了贪腐与剥削。“三纲六纪”是《白虎通》构建出的基本道德体系,它以宗法血缘制度为现实基础,通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全社会的人伦关系转化为一种拟宗法关系,促使“家”“国”一体化的社会政治秩序得以形成,也由此奠定了君权至上的“子民”社会的形成,全社会共通的身份就是“子民”,造就了一种以忠孝为核心的“子民人格”,在这种状态下,国民不是国民,只是臣子、庶民、黔首,他们最大的梦想无关自身、家族、国家的超越,只是被动的承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剥削和压榨。同时,“政治联姻”“血亲拟制”带来的稳固的血缘联系和利益捆绑,为徇私舞弊、裙带之风、贪污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家族势力日渐膨胀,家庭主义盛行,更是造就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政府与人民的“疏远”[22](P229-233)。
三是血缘共同体式的生活,导致“熟人道德”的膨胀,忽略了独立的“个体人”的道德需要。由于血缘共同体式的生活现实,个人习惯于把血缘关系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导致中国传统道德教化出现“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23](P177)的局面。《白虎通》所倡导的德性与德行始终服从于三纲的统领,也是囿于宗法血缘关系而论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由血缘关系推出法所形成的差序格局导致的是一种‘熟人社会’,形成的是‘熟人道德’”[24](P34-39),倡导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规范,始终将“人”置于血缘或拟血缘的社会关系中去认知和设定,使个体的“人”缺失了作为独立的“个体人”的自由和道德需要,“陌生人道德”抑或个体“人”的道德需要被忽略,比如当代道德建设中提倡的“尊重”“平等”“公正”等观念就严重缺失,在道德建设层面“人”的独立性受到遮蔽,具有道德狭隘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