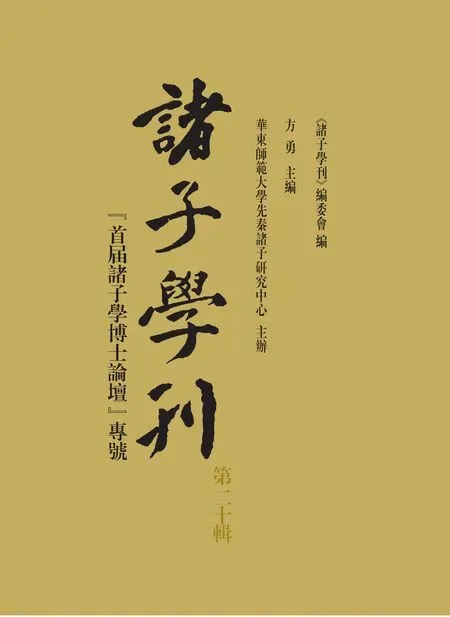浦江文脉的歷史傳承與當代發展
李小白
内容提要 浦江文脉作爲金華之學的重要分支,興盛於宋末以至明初。以師緣紐帶聯繫起來的浦江學人,其代際嚴明、傳承有序、理念合轍,雖受時代遷轉之影響,仍不失爲金華地區文脉傳承的典範地域。浦江文化不但存在明顯的脉絡化趨勢,還是江南文化轉爲中國文化重鎮不可或缺的貢獻者。宋元浦江學術的底色帶有濃厚的婺學色彩,後隨着朱學的傳入而匯流,藉由浦江學人與明初政治的結合,開出有明一代的文章之派。近代以來,賡續浦江子學傳統並能在復興傳統文化熱潮中推陳出新,則需要從學術歷程、治學脉絡及對諸子學現代學術形態轉化等多方面,對“新子學”理論的提出者予以考察。
關鍵詞 浦江文脉 婺學 新子學 方勇
浦江地處浙東婺州(今金華)北部,陳、隋以前爲烏傷(今義烏)之北鄙,隋開皇九年(589)爲婺州戍堡,唐天寶十三年(754)始設浦陽縣,五代吴越王錢鏐改爲浦江縣,至宋代厘爲上縣,元代爲下縣,仍屬婺州(1)康熙間修《金華府志》卷一《建制·疆域》,《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49册,上海書店1993年版,第16頁。。縣因浦江而得名,“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因以爲名焉”(2)柳貫《浦江縣官提名序》,《柳貫集》卷十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7頁。。浦江,亦名浦陽江,源出深褭山,爲吴越三江之一。新安江匯蘭江而爲富春江,經蕭山東江嘴與浦江匯流,入杭州灣而稱錢塘江,三江入海,浙江由此得名。浦陽江“以小絜大”而配三江,“到兹直達海,混混百川會”,雖小猶能達於海,終成一方勝概(3)柳貫《過錢清》,《柳貫集》卷二,第52頁。全祖望在《浦陽江記》中言及“浦陽江水發源義烏,分於諸暨,是爲曹娥、錢清二江。其自義烏山南而出者,道由蒿壩,所謂東小江者也,下流斯爲曹娥。其自北山而出者,道由義橋,所謂西小江者也,下流斯爲錢清。”曹娥、錢清二江皆曲折入海,“六朝皆以浦陽之名概之”(陳垣《鮚埼亭集批註》,《陳垣全集》第13册,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頁)。。配合婺州境内衆多佳山麗水,兼與周邊縣域壤地相接的地理優勢,爲士人彼此聲氣互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溝通平臺。是以在宋元之際,浦江人文尤爲興盛,湧現出諸如宋遺民方鳳諸儒,入元後浦江柳貫、吴萊、方樗、方梓,義烏黄溍,以及明初宋濂、王禕、胡翰、戴良,包括宋濂門人方孝孺等前後四代儒者,構成了以師緣爲主要紐帶的交相往來的學脉關係(4)學界多是將浦江作爲金華的一部分進行研究,較爲突出的論著有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歐陽光《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文史》1999年第49輯)、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及鄒艷《月泉吟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在討論浦江文脉中人物關係的問題上,筆者延續歐陽光、徐永明等關於這一時期婺州文學集團的代際劃分的方法。。經過宋元明初幾代作家的努力,浦江文化呈現出明顯的脉絡化趨勢,士人之間的代際傳承尤爲顯著,從這個意義上説,浦江文脉得以生成。梳理浦江文脉的文化内涵以及與諸子學傳統的歷史淵源,有助於重新認識具有典範意義的地方文化的歷史與現實。謬誤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 浦江文脉的學術底色
浦江人文興盛於宋元時期,尤其是在遭遇破國亡家之後,士風、士習一改此前所謂卑弱、雕飾的衰氣,情動於衷而形於外,南宋遺民在殘山剩水中以慷慨悲歌的姿態展現不仕蒙元的遺民意志。入元後,由於元廷長期不實行科舉,以防範猜疑的態度對待漢人及漢民族傳統道德文化,“以江南後服,猜防南人,視若殷之頑民”(5)屠寄《鄧文元等傳論》,《蒙兀兒史記》卷一百二十,1934年武進屠寄刊本。,並“視南方如奴隸”(6)孔齊《至正直記》卷三“曼碩題雁”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頁。,士人社會地位空前低下,殘酷的社會現實越發令江南士人懷念故國,將學術傳承和文化命脉視爲己任,文化自覺意識凸顯。由於元初統治集團漢文化水準低下,政府在文化上作爲有限,既乏促進文化發展之措施,又無主導性意識形態之干預,“視學校爲不急,謂詩書爲無用”(7)《廟學典禮》卷二《程學士奏重學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頁。,以至於“學校廢墮,儒風凋喪”(8)阮元主編《兩浙金石志》卷十四《元嘉興路儒人免役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48頁。,社會治理及思想管控也都處於較低層次,文化上是一種學在民間的自在狀態。考察大量元代文化史料,基本可以形成元代文人活動是較爲自主的認識,浦江士風在此影響下,越發呈現自由和昂揚的態勢。自宋末以至明初,浦江文脉前後相繼,以學緣爲紐帶,形成較爲明晰的學術傳承關係。分析這一時期浦江文脉的學術底色,不僅有助於梳理區域性文化團體内外聯絡的實際情形,亦能從時代思潮的角度,認識構成區域性文化團體的衆多成員内在較爲真實的精神世界,以及充分瞭解浦江文脉學術傳承的歷史情境。
(一) 浦江文脉的傳承
界定浦江文脉成員的一個簡單方法是從籍貫入手,劃分最爲核心的人員構成,但這極易出現忽略人物彼此間複雜的交往關係的問題。爲呈現歷史原本的複雜面貌,需要就人物交往的實際情形有所交代。浦江文脉的形成期和發展的高潮階段,在時間上縱跨13至15世紀初,即經歷了宋末、元代以及明初洪武、建文年間,前後四代人。歐陽光分析浦江文脉中人物彼此間的交往關係,大致分爲五種,即親緣、鄉緣、師緣、友緣、政緣(9)歐陽光《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文史》1999年第49輯。。戴良有言,“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姻親而托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遊從,或以友朋而密邇”(10)戴良《祭方壽父先生文》,《戴良集》卷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頁。。戴氏僅言及前四種,忽略了政緣,不過整體來看浦江學人之間這幾種交往關係,都可以集中到師緣上來。浦江毗鄰金華,學人借助師緣,彼此交流密切,宋元諸家之學彙聚於金華,金華諸學波及浦江。浦江、金華之間,朱學、吕學、龍川事功文章之學縱横於此,構成浦江文脉之中幾股重要的力量。借論述浦江學人的師緣之機,恰可梳理浦江文脉與宋學之間的淵源和這一時段浦江文風的遷轉。
初代的代表人物是方鳳(1240—1321)。遺民謝翱、吴思齊與方鳳相交莫逆,三人對浦江文脉的形成貢獻良多。方鳳,浦江人,字韶卿,一字韶父,又字景山,號岩南,因有堂名存雅,人多稱存雅先生。方鳳出身仕宦家族,其家自北宋初年便“簪纓蟬聯不絶,乃浦陽仕族之冠”(11)柳貫《仙華方氏譜序》,《柳貫集》附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42頁。,自幼接受傳統的儒家文化熏陶,“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者也”(12)柳貫《方先生墓碣銘》,《柳貫集》卷十,第268頁。。謝翱(1249—1295),字皋羽,又字皋父,福建長溪人,“讀書博學,宋季以古文知名”(13)鄭元祐《遂昌雜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曾爲文天祥幕僚,文天祥殉國後,謝翱奔走於浙東山水間,與方鳳結交而在浦江活動。吴思齊(1238—1301),字子善,一字善父,號全歸子,其家先是從處州麗水搬至永康,宋亡後,思齊隱居浦江。《宋元學案》將方鳳納入《龍川學案》,視爲陳亮一脉吴思齊之講友。因吴思齊宋亡後號全歸子,又稱“全歸講友”,方鳳、謝翱皆在其列。
如果説方鳳早年出遊杭州,積極科考,借機上書丞相,陳述禦敵治國之策時,不失不畏强敵的英勇之氣和敢於陳情、積極進取的爲國情懷,這與陳亮的事功之説有明顯的合轍之處,那麽在宋亡之後,由方鳳所作詩歌表現出的氣質更見其於事功一脉内在的精神契合。嚴格意義上説,方鳳並不屬於龍川一脉。受陳亮在婺州地區較强的影響力和自身一以貫之的精神氣質的影響,以及與吴思齊的密切關係等原因,黄宗羲將方鳳、謝翱視爲私淑龍川一脉之人,權以“全歸講友”稱之。宋濂曾言:“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淒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即杜甫)非耶?”由於方、謝、吴三人“皆工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比附《易經》所謂“同聲相應”之説,三人都可稱得上是“氣節不群之士”(14)宋濂《浦陽人物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六,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6頁。。
三人的風儀節操,頗爲時人推重,“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争親炙之”,使浦江在宋元之際成爲浙東地區故宋遺民嚮往、聚會、以氣節相互砥礪的所在。此外,儘管由於元初長期不舉行科舉和奉行民族壓迫政策,致使南士入仕之途狹窄、治生艱難,但也令士人“未有場屋之累”,少了科舉仕途之念,對待學問的態度便越發純粹,“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15)黄溍《送吴良貴詩序》,《黄溍集》卷十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頁。。方鳳等人又以所居浦江爲中心,流連山水,痛悼亡宋,“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郁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16)宋濂《吴思齊傳》,《宋濂全集》卷十六,第311頁。。實際上,元初士人無科舉場屋之學的負累,可一掃自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90)所謂“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的衰氣,進而回避儒學“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的弊端,棄場屋功利之學而使“文運大明”,“今其時矣”(17)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疊山集》卷六,《四部叢刊》本。。由科舉而造成的儒者無用的問題正因科舉不行於世而得到解決,儒者雖懷念故國,卻也由於這種無功利的自由獲得精神的釋放,能以更爲純粹的理念將不同個體組織起來。宋遺民有着不同於前代高蹈遠引的遺民形象,他們更具組織性和凝聚力。借助結社和彼此詩文唱和的組織活動,宋遺民試圖通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群體生活,共同面對元初江南嚴酷的生存狀況以及增加彼此相互扶持的精神力量。這種趨群結盟的意識使宋元之際的浦江文學集團有了存在的思想基礎,士人之間的聯繫也因此得以加强。
據徐永明考察,與方鳳同時代的浦江籍陳公凱、陳公舉弟兄、吴似孫、黄景昌等人,也曾在元初浦江區域文化的建設中發揮作用。其中陳氏兄弟、黄景昌等人都在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的征詩活動中有過突出表現,爲浦江文脉的創生發揮作用(18)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陳公凱之詩曾得月泉吟社第四十名,後爲月泉書院山長。陳公舉先爲浦江儒學教諭,後遷江浙儒學提舉,入大都應奉翰林文字,有《世經堂集》。吴似孫也曾擔任山陰儒學教諭(19)方鳳《方鳳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頁。。黄景昌“從方鳳、吴思齊、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其人“善持論,出入經史,衮衮不窮”,著作尚多,“不能備陳”,是一位多産的學者(20)宋濂《浦陽人物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六,第2266頁。。
清人吴偉業提到,“浙水東文獻,婺稱極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華隱者方鳳韶卿,與謝翱皋羽、吴思齊子善,賡和於殘山賸水之間,學者多從指授爲文詞”(21)宋濂《宋濂全集》附録吴偉業《序》,第2770頁。。方鳳偏重於詩文創作,在浦江組建詩社組織以凝聚遺民群體的同時,構築了門人學統的基本框架,“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22)蘇伯衡《申屠先生詩集序》,《蘇平仲文集》卷五,四部叢刊本。,其中像柳貫、黄溍、吴萊等對元代文風頗具影響的文章家都曾出自方鳳門下,“黄晉卿、吴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23)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57頁。。方鳳還曾爲吴氏家塾西席,指導吴氏子弟如吴幼敏、吴似孫等人,“里士吴明府渭,因與其伯兄弟辟家塾,延致先生吴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弄林水間”(24)柳貫《方先生墓碣銘》,《柳貫集》卷十,第268頁。。宋末戰亂之後,由於浦江地區原有的文化人物的努力和外部文化力量的加入,當地較爲迅速地形成了聯繫密切的區域文化勢力,文化傳統得以維持。
入元後,隨着宋元之際遺民的陸續凋零以及方鳳弟子的崛起,浦江文脉完成代際過渡。浦江文脉的二代人物如黄溍、柳貫、吴萊、方鳳子方樗、方梓等人活躍於元朝相對穩定的時期,他們的社會身份比之遺民色彩濃厚的前代發生了轉變。他們不僅接受了元朝統治和元朝官職,還與江西籍虞集、揭傒斯、范梈等人一道提倡所謂盛世文學,影響有元一代文風,“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説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25)戴良《夷白齋稿序》,《戴良集》卷十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頁。。方、吴、謝三人爲友,“開風雅之宗”,黄、柳、吴三人都曾出入方鳳門下,彼此有師緣又有親緣,爲“金華詩學極盛之一會”(26)朱琰《金華詩録·序例》,乾隆三十八年刊本。。考數人出身,所得浦江山水滋養甚多。黄溍弱冠即“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仙華之下”(27)黄溍《送吴良貴詩序》,《黄溍集》卷十一,第418頁。。儘管黄溍爲義烏人,但宋濂曾説“黄爲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28)宋濂《金華黄先生行狀》,《宋濂全集》卷七十六,第1850頁。。黄溍與浦江在地緣、師緣上的關聯之深由此可見。柳貫與方鳳先有親緣,後有師緣。方鳳夫人季氏,“於貫爲從表姑”,柳貫從小“親事先生”(29)柳貫《方先生墓碣銘》,《柳貫集》卷十,第268頁。,“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吴先生思齊、粤謝先生翱……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與三先生的師緣可謂深厚(30)黄溍《翰林柳公墓表》,《黄溍集》卷三十三,第1205頁。。吴萊是方鳳孫婿,年雖少而所得尤深,其力倡復古的文學思想對明代文章學的發展頗具影響,四庫館臣贊譽他“在元人中屹然負詞宗之目”(31)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七,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42頁。。從其弟子宋濂等人對明初文風的影響來看,並無誇大之處。
浦江文脉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是宋濂、戴良、鄭濤、張丁等人,在金華地區頗具影響的還有王禕、胡翰、蘇伯衡、許元、朱廉、吴沉、傅藻、童冀等人,其中以宋濂爲集大成者,有“婺中宿學,元末遺儒”之稱。這些人多是上一輩活躍於金華地區的文人學士的家族子弟或門人,彼此間或是同門學友,或是同鄉或姻親關係,浦江學人與金華士人之間的交遊在元末明初表現得尤爲突出(32)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第22頁。。由於元人突破了宋人學術門户森嚴的藩籬,走向融合匯通,他們轉益多師,使得學緣關係出現交叉和互動,不同學術派别在交匯融合的同時,學人的思想背景也呈現複雜化。宋濂早年轉益多師,其學術淵源深厚複雜,先後師事包廷藻、聞人夢吉、方麒、吴萊、黄溍、柳貫等人(33)陳葛滿《宋濂交遊考》,《浙江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宋濂重視師承授受,“終身稱述師門不少置”(34)陳婺《〈婺書〉整理與研究》,浙江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5年,第75頁。。如果從師緣傳承上看待宋濂的這些師長,他們皆可嵌入婺學的學術脉絡之中(35)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第24頁。。吕祖謙、唐仲友、朱熹、陳亮都有浦江籍的後學傳承,宋濂在經學、史學、古文、佛道等方面的精神成長歷程也可納入這些師緣學統之中。僅以方鳳一脉來看,宋濂在古文辭和事功之學上有陳亮、方鳳等人思想的印記,至於説宋濂“調和朱陸”的理學主張、經史觀念,甚至散文理論皆有與吕祖謙的觀點存在冥合之處。而且從金華整個學脉的發展來看,考察宋濂師長的學緣,皆可溯及吕祖謙、朱熹等人(36)宋克夫、熊愷妮《宋濂朱學淵源考》,《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熊愷妮《宋濂的吕學淵源與散文理論》,《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從這個意義上説,稱宋濂爲婺學的集大成者並不爲過。
隨着明朝的建立,宋濂及一群金華、浦江籍文臣對明初典章制度的建構,“一代禮樂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婺學在明初大放異彩(37)張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789頁。。憑藉朱元璋專制强力的推行,經過改造的婺學文化集團思想觀念在明朝版圖得以鋪開。宋濂及其後學,如子宋璲、弟子鄭淵、鄭濟、鄭洧、鄭格、鄭棠、鄭楷、鄭柏、樓璉、樓希仁、劉剛、趙友同、王紳、李耑、吴彦誠、章存厚、林静、黄昶以及寧海人方孝孺等人的努力,浦江文脉的第四代人物成型,其中以方孝孺成就最高,婺學亦臻至極盛。但由於明初强化思想文化的統治和靖難之役導致的王權變更,依附於建文帝的方孝孺慘遭明成祖屠戮十族,禍及孝孺宗族、弟子,浦江文脉遭遇前所未有的打擊。
浦江地區在宋元明初長達一百二十餘年的文脉傳承具有典型意義,可視爲區域文化衍生的代表。以師緣爲紐帶考察浦江文脉的代際傳承,符合宋代以後地域性士人群體重視文化傳承的歷史事實。歐陽光從宋元時期人物之間重視淵源授受和建立學統的角度,指出地域性文脉的建構是學統思潮的典型反映,同樣也是帝制時代集權觀念在文化領域的外化。而且,浦江文脉作爲婺學的代表,其成員學術淵源中有着强烈的理學化色彩。理學又恰恰是極爲重視“學統”的,理學家們對傳承是否正宗與純粹尤爲在意(38)歐陽光《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文史》1999年第49輯。。是以四庫館臣評介元代學術時有,“學脉旁分,攀緣日重。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39)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叙》,第1頁。。清人的批評指出了元代學術史的大致情景。需要承認,如果没有這種以師緣傳承爲紐帶,聚集區域文化之中形成人物之間的某種集合,那麽在風雨如晦的宋元之際和明初惡劣的政治環境之中,想要維持區域内文化的代際傳承恐非易事。不過,以師緣爲紐帶的浦江學人,並未構成嚴格意義上清人所謂的“務定一尊”和“見異不遷”的“黨派”弊端,實際情況是浦江幾代學人的學術傾向既有堅持也有變化,並不能用簡單、籠統的一句話可以概括。因此,從區域性文化團體内部學術淵源進行考索,或許能較爲準確地探明時代遷轉過程中,浦江文脉究竟發生了哪些具體而微的思潮轉折,從而有别於此前較爲籠統的文化概述。
(二) 浦江文脉的學術源流
元初,江南地區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文化挫折,儒學勢力一度跌至谷底。但婺州地處浙東一隅,借助與文化都會——杭州的地緣優勢,婺州儒學師教的氛圍依然濃厚,當地故宋遺民中有不少是吕祖謙、陳亮、朱熹等人的三傳、四傳弟子,如金履祥、胡長孺、吴思齊、石一鼇等輩,儒學的傳統一仍舊貫且呈現兼取各家的學術傾向。浦江學人中方鳳的後學,如柳貫、黄溍、吴萊、宋濂、戴良等人在元朝中後期勃然而興,儒學傳統未曾斷絶,儒學授受更加純粹,“小鄒魯”之名絶非浪得,“吾婺自東萊吕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40)宋濂《題蔣伯康小傳後》,《宋濂全集》卷三十九,第864頁。,甚至“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41)宋濂《贈何生本道省親還序》,《宋濂全集》卷二十六,第540頁。。包括浦江在内的婺州地區,彌漫着儒學的文化氛圍,形成爲人所歆羨的東南文獻之邦。
1. 理學
自宋元以來,婺州名儒輩出,人文薈萃,有所謂“小鄒魯”和“東南文獻之邦”的贊譽。溯及師緣,浦江學人與婺州儒者一道構成婺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浦江文脉也可視爲婺學的重要一支。婺學自兩宋之交由蘭溪范浚開其源,“范香溪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4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四十五《范許諸儒學案》,第1438頁。,經南宋吕祖謙、唐仲友、陳亮等人拓其流而臻至鼎盛。此外,婺學又得朱學滋養,後世稱爲金華四先生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皆是朱熹弟子黄幹在婺州的高徒。入元後,國家以程朱理學取士,黄氏在婺州的學脉被官方視爲朱熹嫡傳,在政府支持下獲得較大發展。
吕祖謙、唐仲友、陳亮三人之學對婺學的發展頗有影響,“宋南渡後,東萊吕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説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家”(43)宋濂《潛溪録》卷四《經籍考》,《宋濂全集》附録二,第2720頁。。其中又以吕學影響最大,“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吕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吕氏爲得其宗而獨傳”(44)黄溍《送曹順甫序》,《黄溍集》卷十一,第411頁。。吕、唐、陳三家學問側重不一,“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説齋氏以經學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45)宋濂《潛溪録》卷四《經籍考》,《宋濂全集》附録二,第2738頁。。唐仲友以經學起家,但後來因爲“嘗得罪朱子”而“宋史不立傳”,唐氏之學不傳,這點頗爲浦江學人所不平(46)宋濂《宋濂全集》附録二《潛溪録》卷四,第2706頁。。陳亮“事功之學”有别於朱熹、吕祖謙、陸九淵、張栻等人“談性命而辟功利”,“倔起其傍,獨以爲不然”,曾道“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47)宋濂《喻偘傳》,《宋濂全集》卷十六,第302頁。。陳氏之學在浦江文脉的二代、三代學人身上發揮了有别於初代學人的轉折性作用。基於對元王朝的接受,柳貫、吴萊、宋濂、戴良等師生都曾有過元王朝的官職,獲得名位,實現從布衣白身到士大夫的身份轉變(48)柳貫、吴萊、宋濂、戴良等人在元朝獲得的官職,像柳貫曾於大德四年(1300)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吴萊中舉後,舉上禮部,不利而退,後被薦調任萇鄉書院山長,未任而卒。宋濂早年參加元朝科舉,二十六歲曾到錢塘參加鄉試,不第。三十九歲應試鄉闈,仍不第。四十歲,因危素等人薦舉,擢宋濂爲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潛溪録》載《行狀》云“至正己丑(1349),用大臣薦,擢先生爲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宋濂全集》附録二,第2593頁)次年,入仙華山爲道士。戴良曾於至正二十一年(1361)被舉薦任奉訓大夫、淮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如果分析這種轉變的深層心理因素,龍川陳氏之學應於其中發揮了作用。從宋濂對陳亮所謂“皇帝王霸之大略”的推崇亦可窺其究竟。
浦江文脉頗受吕學、朱學影響。吕學爲鄉學,淵源有自。朱學在婺也有明確傳承。元中期推行科舉,以程朱理學爲選士標準,朱學由此大盛。朱、吕異同,前人辨析詳細,此處不贅,僅就一點討論,從中可見浦江學人爲學傾向。朱熹、陸九淵之學較偏於心性修養,大多數情況下諱言事功之學,“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而吕學則因重視史學,對事功並不排斥,又“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調和朱陸,主張心性修養應從現實的濟世安民的功業之中得以體現(49)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東萊學案》,第1653頁。。朱、陸之學重内輕外,重經輕史、重道輕文,重性理道德而輕事功,喜清談,鄙視具體實務的處理,有虚懸於現實之外的形而上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難免會在朱、陸之後産生流弊,影響其現實效用和具體評價。對此吕學予以糾偏,以吕學爲主要特色的婺學,取中庸之道,對文與道、經與史、性理道德與現實事功等問題予以同等看待,不取二元對立的價值判斷,而以融合、無礙的態度視之,所以我們看待浦江文脉的二傳、三傳學人在接受了元朝統治後,紛紛出仕,貫徹内聖與外王的儒家宗旨於己身,實現兩者的統一,從而符合孔門宗旨。這是重視求真務實、經世致用的婺學之所以能昌盛於元末明初的内在文化原因。
不過,從宋濂等人的叙述來看,元末吕學似已處於不傳的境地,吕學不傳引起浦江學人普遍憂慮。浙東之學自南宋乾、淳之後,理學以朱、陸、吕三家獨大,“三家同時,皆不甚合”(50)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東萊學案》,第1653頁。,宋濂稱“吾鄉吕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殁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絶,濂竊病之”(51)宋濂《潛溪録》卷四《經籍考》,《宋濂全集》附録二,第2035頁。。宋濂有志於繼承吕學,這點不僅從其文章著述之中多有表露,在其師緣學統上更爲清晰。南宋以來,“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徐僑)再傳而至黄文獻(黄溍)、王忠文(王世傑),一自王文憲(王柏)再傳而至柳文素(柳貫)、宋文憲(宋濂),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故謝山云‘四百年文獻之所寄’”(5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七十三《麗澤諸儒學案》,第2434頁。。排列宋濂的學脉關係,正是吕學的六傳,是“吕之嫡脉”(53)熊愷妮《宋濂的吕學淵源與散文理論》,《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吕祖謙之學最盛的兩條學脉又兼祧朱學,並開有明一代的學統,從這個意義上説,浦江學人於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明確了浦江學人在理學學統之中的位次,回過頭來就需要分析浦江學人幾個較爲突出的學術特點。在此之前,應先明確理學與經學的關係,方能較爲深入地理解浦江學人的理學底藴。作爲經學史上一種特殊形態的理學,理學是經學演變的邏輯産物,經學是理學的根柢,理學是從經學思想中升華得來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理學服務於經學典籍的詮釋(54)姜廣輝《論宋明理學與經學的關係》,《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顧炎武曾指出,理學即經學,是理學家將理學觀念加諸經學而呈現出的新面貌,本質上仍是經學,不講經學的理學難以稱得上是理學,所以説“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55)顧炎武《與施愚山書》,《顧亭林詩文集》卷三,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8頁。。宋元士人講經學,故其理學有根柢。朱、吕以義理闡釋經學,並有大量傳注類理學化著作存世,朱、吕後學同樣如此。
依着理學即經學角度觀察,浦江學人之中,舉凡柳貫、吴萊、宋濂等人皆有深厚的理學化了的經學底藴,這點淵源有自。宋濂曾在《浦陽人物記》中梳理浦江一地的學術傳承,“浦陽雖小邑,自宋以來以文知名者甚衆,大抵據經爲本”,充分表明浦江學人在經學方面的重視程度。其中若干典型代表如下:
1. 于世封: 能暗記六經、三史……晚乃著《易》《書》《詩》傳四十卷。著《春秋三傳是非説》二十卷。
2. 朱 臨: 從安定胡瑗遊……長樂劉彝,授《周禮》,又兼習水利。臨乃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唯臨得之爲精……所著《春秋説》二百餘卷。
3. 何敏中: 自少學《易》。
4. 吴克己: 窮經博古,尤邃於《易》。
5. 方 鳳: 善《詩》,通毛、鄭二家言。
6. 黄景昌: 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作《春秋舉傳論》……作《周正如傳考》……作《蔡氏傳正誤》……作《古詩考》。
7. 柳 貫: 受經於蘭溪金履祥……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
8. 吴 萊: 年四歲,其母盛氏口授《孝經》《論語》及《穀梁傳》,隨能成誦……年二十四,以《春秋》舉上禮部……著書有《尚書標説》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説》《胡氏傳考誤》未完。(56)參考《宋濂全集》之《浦陽人物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8~2270頁。
藉由上述臚列的浦江學人,便可瞭解他們在經學一道的側重。我們注意到像黄景昌、柳貫、吴萊、宋濂等人在理學的脉絡上皆有一席之地,而且經學一道在浦江也有深厚的文化傳承。舉《春秋》經爲例,浦江學人之中不僅自五代以後便有于氏一族在《春秋》一道上有所深入,北宋中期又有朱臨“優於經學”,其人學有統緒,也曾指出:“孔子没千有餘年,説《春秋》者皆膠於偏見……雖董仲舒爲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57)宋濂《浦陽人物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六,第2260頁。宋元之際,浦江學人關於《春秋》經的研究一直未斷,像黄景昌在《春秋》經的論述,不但能“據經爲斷”,消除學者對《春秋》三傳不知所從的疑惑,還撰述《春秋傳舉論》《蔡氏傳正誤》,以方便學者研究前人的《春秋》學著作。其他如朱恮、吴萊,曾以《春秋》中舉,朱、吴等人《春秋》經方面的著述或存或佚,都表明浦江學人在經學一道上的深厚底藴。至於説婺學的經學根柢,像前文所述的吕祖謙、朱熹、唐仲友、陳亮等輩不僅是學派的開山人物,其後學也無不根基於經學,進而闡釋自家關於經學典籍的理學化觀點,舍經學而談理學無異於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如果論及浦江學脉的集大成者——宋濂,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宋濂對經學也有着鮮明的立場,他將六經大義視爲“存心”“著書”“言談”的根本,尤其是在三十歲時突破對古文辭的熱愛,轉换了學問方向,更是堅定了他關於經學的認知,不僅“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58)宋濂《白牛生傳》,《宋濂全集》卷十六,第294頁。,還不厭其煩地在文章中肯定“經”的崇高地位。“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下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内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59)宋濂《經畬堂記》,《宋濂全集》卷十二,第225頁。宋濂關於經學的理學化認識還表現在“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虚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歎哉”的感慨之中,爲此提出符合理學傳統的治經理念,“唯善學者,脱略傳注,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60)宋濂《六經論》,《宋濂全集》卷七十八,第1878頁。。這是理學化了的治經方法,由此可知後世稱宋濂“六經皆心學”的觀念並不是虚言,同時符合理學專以心性爲宗主的學派特色(61)劉玉敏《六經皆心學: 宋濂的心學特色及其影響》,《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宋濂關於經學與理學“一而二,二而一”關係的直白論述,比起他的師長們則更爲前進了一步,重新提振了浙東心學在明代學術之中的影響。
2. 史學
如所周知,浦江學人關於史學的認知,頗受吕祖謙的影響。吕學向來以經史並重的面目示人,“東萊吕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62)吴萊《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全元文》第44册,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頁。,“金華之學,唯史最優”,但士人多以其“於經則不密察”苛評吕祖謙之學。事實上,我們注意到吕祖謙在經史一道頗有心得,他對《尚書》《左傳》等儒學經典的詮釋,不僅是“密察”經典的體現,更是其史學功底的展示。《尚書》《左傳》首先是作爲先秦史書而存在,而後經國家支持才升格爲經,成爲所謂“聖人之史”,宋濂不但指出“若《書》若《春秋》,庸非虞、夏、商、周之史乎?古之人曷嘗有經史之異哉”,又對士人苛評吕祖謙的説法予以指正,“凡理足以牗民,事足以弼化,皆取之以爲訓耳,未可以歧而二之。謂優於史而不密察於經,曲學之士固亦有之,而非所以議金華也”(63)宋濂《龍門子凝道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四,第2228頁。。
實際上,吕學針對經史關係的認識,宋濂曾以“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作爲總結吕學“粹然一出於正”的理學化了的經史觀(64)同上,第2212頁。。吕學經史並重的傳統對浦江文脉影響深遠,柳貫曾以《春秋》爲例,指出司馬遷作《史記》曾仿《春秋》義理,“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仿之以爲《史記》”(65)柳貫《金石例序》,《柳貫集》卷十七,第459頁。。用《春秋》之例,講明史學編纂的書寫問題。此外,柳貫還曾借給金華俞時中詩集作序的機會,指出時中詩“有關於世教,若《讀通鑒》諸作,真得史外傳心之要”(66)柳貫《俞器之詩集序》,《柳貫集》卷十七,第461頁。,其中“史外傳心”一語恰可反映婺學所重視的“史”,正是理學化了的“史”。義理史學重視以理闡史,以史證理,有以經御史的特徵,是宋元理學家以經入史典型手法的體現(67)湯勤福《義理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1期。。從浦江學人針對經史關係的叙述中,受義理史學影響的情況相當普遍。
前文提及吴萊曾以《春秋》經中舉,他自己也説“鄉予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68)吴萊《古職方録序》,《全元文》第44册,第35頁。,所以特别强調《春秋》經的歷史意義,“自魯史而爲《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爲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69)吴萊《春秋胡傳補説序》,《全元文》第44册,第38頁。。從義理史學的角度考察吴萊的理學化史觀,例證頗多,如其“《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點明《春秋》升格爲經的原因在於尊王(70)吴萊《周正如傳考序》,《全元文》第44册,第34頁。。又從《公羊傳》的角度揣度孔子作《春秋》的本意,即講求“當世盛衰離合之權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從而有别於“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的偏頗論調,同樣是吴萊“史外傳心”的典型思路。吴萊的史觀混合了他對儒經的態度,他辨析古之學《春秋》者“率論理而不論勢”,昧於時事變遷的具體情況,僅據儒經作教條式的理解,爲此吴萊指出“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用“理勢之相須”務實地處理具體事務。吴萊堅信此説並“非私見也,非鑿説也”,是“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71)吴萊《春秋世變圖序》,《全元文》第44册,第50頁。。吴萊還指出,《春秋》“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唯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72)吴萊《春秋通旨後題》,《全元文》第44册,第94頁。。如此一來經與史的關聯得到統一,而且吴萊這種重視理與勢辯證關係的見解影響到了他的弟子宋濂。從吴萊到宋濂關於經史認知的脉絡中可以瞭解到,二人不僅在經史關係認知上有承接關係,在具體的處世上也有相同之處。
宋濂曾從“聖人之史”的角度辨析經史關係,他説:“《易》《詩》固經矣,若《書》若《春秋》,庸非虞、夏、商、周之史乎?古之人曷嘗有經史之異哉?凡理足以牗民,事足以弼化,皆取之以爲訓耳,未可以歧而二之。”(73)宋濂《龍門子凝道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四,第2228頁。此説固然是爲解除旁人對吕祖謙“優於史而不密察於經”的疑惑,指出吕學經史並重的特點。從吕祖謙、吴萊、宋濂的學脉來看,浦江學脉充分繼承了吕學經史並重的傳統。
浦江學人在義理史觀的指引下,重視史法成爲題中之義。宋濂未出仕之前曾長期擔任義門鄭氏的西席,有較好的創作環境,曾撰寫《浦陽人物記》二卷。書中收録浦陽自唐末五代以來歷史人物二十九位,分忠義、孝友、政事、文學、貞潔五門,並且仿《通鑒》格式,分别進行頌贊,四庫館臣有“皆具有史法”的贊譽(74)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浦陽人物記二卷》,第523頁。。宋濂後來接受朱元璋聘請,出仕爲官,洪武二年(1369)受命總裁《元史》,二月丙寅開局於南京天界寺,八月癸酉告成,計一百八十八日。但順帝一朝三十六年史事無實録可徵,因遣使者四出采輯,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開局,七月丁亥書成上進,計一百四十三日,兩次修史,前後不足一年(75)方齡貴《元史叢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迫於時日,成書之速,疏漏難免,但宋濂秉承“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之者,尤非也”的理念(76)宋濂《大明日曆序》,《宋濂全集》卷二十六,第553頁。,使得此書在元代《十三朝實録》《經世大典》等書久佚的今天,仍不失爲元史研究的一手資料,其價值也隨着相關研究的深入而日益彰顯。
3. 子學
宋元之世是浦江文化的興盛期,其中特以宋季浦江方鳳等一批遺民作家群體最爲著名。宋元鼎革帶來天崩地解的社會變動,遺民群體在殘山剩水間所尋求的文化向心力正是要在風雨如晦之中立定脚跟,並以先賢自況,抒發遺世獨立精神的同時,借此平復因朝代更迭産生的文化失落感。元初浦江學人最爲人矚目的文化活動,便是曾由月泉吟社組織,以“春日田園雜興”爲主題的詩歌聯賽,仿科舉程式,以儒道合一的典型代表——陶淵明爲思接千載的吟詠對象,表明遺民之於元廷的不合作態度。細究宋元之世浦江學人在諸子一道上的思想内涵,不但需要溯及他們身後學術傳承體系之於諸子的態度,還要聯繫其個人針對諸子的觀照,由此考察諸子學如何成爲構成浦江學人精神世界重要内容的歷史原因。
遺民精神的源泉來自於老莊。遺民方鳳與吴思齊、謝翱等人藉由詩社組織遺民活動,不僅提振了浦江乃至金華當時衆多遺民的士氣,更對浦江文脉的形成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浦江詩風到方鳳時,“浦陽之詩爲之一變”(77)宋濂《浦陽人物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六,第2266頁。,方、吴、謝三人的詩文風格可視爲針對南宋衰弊已極詩風的一種反動,有開新的作用。這是從詩風變遷的角度,指出方鳳等人歸隱浦江仙華山之後的詩文氣質變化産生的作用。然而,細細考察方鳳的詩作,構成其思想底色的不單單有儒學,更有老莊之學的印迹,甚至佛教思想也能從現存的作品中有所體現。
面對亡宋之後的殘山剩水,遺民們的詩酒聚會、遊山慟哭等活動,皆被賦予了某種慘痛省思的内涵與行動隱喻。寄情山水詩酒成爲遺民破國亡家後抗節不屈的某種象徵。宋元之際,浦江學人大多有遠遊的經歷,透過山水、詩文排遣因個人遭際而招致的怫鬱、痛恨、懷戀以及艱於治生、親友别離的尷尬與無奈。閲讀方鳳的詩文集,其中不乏藉老莊、禪理以遣懷的詩句,透露出方鳳與諸子之學的深刻聯繫,從“人生本來浮”(《遊寶掌山寺》)看世事無常,借“大觀物物齊”“吾心太虚闊,倘然萬象具”(《寄柳道傳黄晉卿兩生》)臻至莊生齊物的妙悟,因此説出“盆歌疏達慕莊生”(《止所吴公挽歌辭》)、“手把《南華》讀一過,詩思徒湧如春波”(《答柳道傳餉筍》)之語,也就不難理解彼時方氏的心境與曠達。至於説“不惜逍遥投杖屐,何妨磅礴解衣冠”(《九日同皋羽子善遊白石龍湫用杜老九日藍田韻》)之句,更可見方氏受莊子影響之深。如何從破國亡家的切己苦痛中挣扎而出,僅僅從空疏的理學中尋求安心之所顯然不合元初的社會現實,於是來自莊學的精神慰藉便顯得尤爲重要。
對宋濂在《浦陽人物記》中提到方鳳“性不喜佛、老”的説法應予以保留。理學家對待諸子學乃至佛道的態度,大多是秉持拒斥的態度。宋初邢昺在《論語疏》中立場鮮明地説:“異端,諸子百家之書也。”出於對儒家經典的維護,諸子百家之書的遭遇可以想見。孟子所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的教誨,理學家服膺不止,紛紛以正統自居,拒斥“異端”。如果説兩宋是理學道統建構並行之廣泛的時代,那麽前文提到元代便是不同統系脉絡互相融合的時期,而且由於元代並未認真對待漢人學者提出的道統與文統之説,前代由官方和知識界重視的道統、文統等統系便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下移。嚴格意義上的辟除“異端”缺乏明確的現實意義,諸子之學在學者的視域中呈現不同於前代的色彩,即便是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婺學也在元代中後期出現研究諸子學的風潮,這是宋代理學家始料未及的。
如果藉由前文提及方鳳所傾向的龍川陳亮之學,那麽從陳亮本人對待佛老的立場就可瞭解龍川後學的態度。陳亮辟佛道,僅從佛道二教的行迹出發,對其義理仍是認可的。陳亮認爲是儒家的“祀禮、饗禮、祭禮”廢壞而導致道家、佛教、巫人盛行,“三禮盡廢,而天下困於道、釋、巫,而爲妖教者又得以乘間而行其説矣”,正因爲官方主持的儒教禮儀得不到倡導而使得民間道、釋、巫盛行於世(78)陳亮《陳亮集》,見《鄧廣銘全集》第5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頁。。陳亮較多的是從國家管理的角度,對影響國家治亂的釋道巫提出了警告,而行之千有餘年的佛道二教僅指出“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者,百家衆説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從現實的角度承認了他們的存在(79)同上,第222頁。。南宋理學家對於佛道諸子的態度,程朱、陸學、吕學等都有不同的看法,婺學承襲吕學、朱學脉絡,但其後學之於諸子的態度已不像宋代那麽門户分明,融合或者説調和之説在學脉發展過程中逐漸取得主流。
柳貫學識淵博,“幼有異質,穎悟過人……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從中可知柳貫於子學諸書不廢研習,且有淵博的學術修養(80)宋濂《浦陽人物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六,第2267頁。。柳貫對老莊之學頗有見地,“老莊之學由天成,大知小知無營營。百嘉於此亦交鬯,衆樂自然同一聲。可能貧病色種噲,不愧繳妙神微明。玄中有物本諸易,我將退密觀其生”(81)柳貫《題虞博士作玄又玄齋銘銘爲吴玄初法師作》,《柳貫集》卷六,第164頁。。
方鳳孫婿吴萊對諸子學的理解尤其值得重視。宋濂曾這樣評價吴萊的諸子之學,“翻閲子書數百家,辨其正邪,駁其僞真,援據皆的切可傳,四方學者一時多師之”(82)宋濂《浦陽人物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六,第2267頁。。吴萊從《春秋》經學的立場反觀諸子,提到諸子學何以發生的歷史背景時説:“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唯磨厲其舌,肆爲讒説,莫之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唯以利害相勝。”這是吴萊沿襲帝制時代儒生的一貫口徑而提出的批評,不僅慨歎“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還將戰國諸子之學視爲儒者所不必學,僅需瞭解其人其文即可,“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立場之鮮明,好惡之明確,可見一斑(83)吴萊《吴氏戰國策正誤序》,《全元文》第44册,第40~41頁。。吴萊在討論帝制時代法律問題時也有一致的説法,“蓋當秦之時,孔子没而異端起,處士横議,而説客妄售其所自爲術,是非矛盾,紛盭相勝”,秦因没能意識到儒者的作用而“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結果導致國家二世而亡(84)吴萊《唐律删要序》,《全元文》第44册,第46頁。。吴萊注意到戰國時期儘管“士多以遊説縱横、攻戰刑法之説行”,但君主卻喜歡士人披着儒者的外衣談論事功富强之術,“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像吴起、荀子後學李斯、韓非之輩,雖以儒服示人,其學卻非吴萊從理學角度認爲的儒學正宗(85)吴萊《孟子弟子列傳序》,《全元文》第44册,第52頁。。
理學觀念下的子學研究在浦江學人身上還有突出表現。宋濂在浦江學脉中實際上是以一代儒宗的面目出現。柳貫對宋濂期望甚深:“吾邦文獻,浙東爲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唯景濂耳。”(86)焦竑《玉堂叢語》卷六《師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2頁。方孝孺曾如此評價其師:“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絶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87)方孝孺《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先生像贊》,見黄靈庚校點《宋濂全集》第5册,第2544頁。宋濂在理學上的造詣遠超其文學上的修養,他以六經爲根本,將性理之學融入著述之中,“吾心與天地同大,吾性與聖賢同貴”,足見其理學修養之深(88)宋濂《自題畫像又贊》,《宋濂全集》卷九十,第2138頁。。
宋濂關於子學的論述的立場是基於性理之學的。宋濂曾批評戰國諸子“各以私説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爲文”,對所謂“聖人之文”亦即自孟子以來“能辟邪説、正人心”之文“不無所愧”。宋濂還指出自孟子以降,經周敦頤、二程、朱熹等人“完翼經傳”才使文統與道統得以彰顯。宋濂立場鮮明地將“立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這一立場宋濂得自黄溍,柳貫、吴萊也不乏此類觀點,可見浦江一脉對此有一貫的認知(89)宋濂《華川書舍記》,《宋濂全集》卷三,第76頁。。實際上,宋濂在子學方面的思想背景相當駁雜,儒釋道三教的影響都曾在其身上留有深刻印記。宋濂認爲道家之學與六經有相合之處,爲自己“頗艷”之“神仙家之説”提供合理依據,宋濂提到“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書》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修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蜎子與夫兵謀之書,咸屬焉”。如果從宋濂當時處境而言,此時正值宋濂有意披髪入山爲道士之時,宋濂在文中所謂“列仙之儒”的説法,以及道士道慶授以“長生秘訣”都暴露這一階段宋濂的精神歷程,但這並非其終身自持的一貫立場(90)宋濂《混成道院記》,《宋濂全集》卷八,第162頁。。儘管宋濂基於生理與性情而有所謂“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的説法,還有仰慕道士吐納修養可以養生延命的目的,這些似乎構成了宋濂“寄迹老子法”入山爲道士的合理解釋。但在戴良看來,如果不能從君子的出處所表現的“行道”與“存道”的角度進行解釋,並不能把握宋濂披髮入山的真實想法。肉體壽命不足以與“施之於功業”“見之於文章”的“君子之道”相提並論,戴良“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而“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老子之道並不是戴良所認可的道,但堯舜周孔之道與老子之道卻是“聖人之道”的一體兩面,“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91)戴良《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戴良集》卷六,第58頁。!恰恰表明宋濂並非全然放棄仕進之路,而是對自己的出處有着深入考慮才有此決定。從中可知,宋濂、戴良在出處進退上有着調和儒道的思想趨向。
從經子關係上,也可得知宋濂的基本態度。諸子之學應在儒家經學之下,“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烏足以爲經哉”,並提出明確的經學作用之説,“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凖”(92)宋濂《經畬堂記》,《宋濂全集》卷十二,第226頁。。宋濂明確經子位次的意圖,正是爲彰顯經學作爲儒家心性之學和匡時救世之道的作用,諸子之學不外是拿來作爲對比的對象,其實貫穿的還是儒者貶低子學的一貫態度。表明這一態度的另一典型例證是宋濂在《諸子辨》中所言: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立其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盭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仿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曷爲辯之?解惑也。
《諸子辨》作於宋濂四十九歲,當時正處戰亂,宋濂妻孥先頭避兵諸暨勾無山,宋濂在完成是書後也走避勾無,命次子璲謄録成稿。《諸子辯》辨析歷代諸子學著作,包括《鬻子辨》《管子辨》《晏子辨》《老子辨》《文子辨》《關尹子辨》《亢倉子辨》《鄧析子辨》《鶡冠子辨》《子華子辨》《列子辨》《曾子辨》《言子辨》《子思子辨》《慎子辨》《莊子辨》《墨子辨》《鬼谷子辨》《孫子辨》《吴子辨》《尉繚子辨》《尹文子辨》《商子辨》《公孫龍子辨》《荀子辨》《韓子辨》《燕丹子辨》《孔叢子辨》《淮南鴻烈解辨》《揚子法言辨》《抱樸子辨》《劉子辨》《文中子中説辨》《天隱子辨》《玄真子辨》《金華子辨》《齊丘子辨》《聱隅子辨》《周子通書辨》《子程子辨》等,對先秦漢魏六朝唐宋這些子書的思想内容都作了獨特的評論,對各著作的真僞多進行了考辨。學界大多將此書視爲辨僞之書,近年有學者將此書作爲宋濂“明道”“存心”的性理著作(93)黄靈庚《宋濂的闡述性理之作——〈龍門子凝道記〉、〈諸子辨〉辯證》,《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詳細分析書中宋濂的意見,辨僞之説僅是表象,實質仍然是宋濂承襲婺學學統的一貫立場,以“正心”“明道”的儒家正統觀念作爲取捨諸子百家的標準。書後序文再次表明了宋濂的立場:
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戲!邪説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爲之志,既各爲之辯,復識其私於卷末。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
藉由對諸子著作的批判,可較爲完整地呈現出宋濂的儒學觀念。宋濂注意到諸子著作的基本定型多在秦漢之時,書中内容有一個層累的加工過程。從文意的角度考察《鬻子》時,宋濂指出漢儒對其進行了“補綴”,一定程度上梳理了《鬻子》因年代邈遠而産生的篇章舛錯的問題。此外,鬻熊弟子也對此書進行了增補的歷史事實,宋濂也有所發現。先秦典籍的漢代生成是一個典型問題,傳世的先秦典籍多數經歷了漢儒某種程度上的“加工”,所以宋濂能通過辨析諸子著作而發現這一問題,着實可見其學識之高。類似例證,書中已明白提及,“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後人綴輯”之語比比皆是(94)宋濂《諸子辨》,《宋濂全集》卷七十九,第1902頁。。宋濂的諸子學研究,上承唐馬總《意林》、宋高似孫《子略》、宋黄震《黄氏日抄》(子部),下開明清人諸子辨僞,是浦江文脉中諸子學一系的重要節點(95)劉思禾《浦江諸子學與重振傳統文化》,未刊稿。。
與宋濂同爲吴萊弟子的戴良,不僅得方鳳詩文一道的傳授,於子學也有獨到見解。從經學角度會通老莊之學,在元末浦江似爲一大學術共識。不僅宋濂在思想上明顯有和會三教的印迹,戴良也有類似言論,“《易》卦有復,所以復乎其本始也。本始也者,樸而未散之謂也。樸而未散是名太素,老子之抱樸見素,莊子之復樸入素,又皆求復乎太素之説也。然則曷爲而復之?復之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唯其一也,故不雜;唯不雜也,故能純。傳曰: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斯言豈欺我哉?”(96)戴良《樸太素字説》,《戴良集》卷十八,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頁。從《易》《老》《莊》三者之間分析得出共同之處,並以《莊子》統籌三者,如果不是學有心得,恐怕很難有這樣深入的認識。
戴良向來以元遺民的角色示人,這種身份令其對老莊之學有更深層次的理解。至正二十一年(1361)起,戴良曾一度任職於張士誠控制下的吴中,但好景不長,至正二十六年(1366)以後,朱元璋陸續占領原爲張士誠所據的高郵、泰州之後,戴良買舟東下,離開吴中,開始了飄零隱居的生涯。戴良借《莊子》文意撰文,以浮萍自況曰:“生獨不見夫萍之樂也。不根以據,不土以著,或依沼沚,或傍溪壑。憑風聚散,挾雨棲泊,就必其深,避必其涸。逐鳬鷺而上下,結萑蒲以隱約,類飛蓬之跌宕,肖浮梗之落魄。此則萍之所甚樂,而余之所托焉者也。”(97)戴良《萍居解》,《戴良集》卷二十六,第298頁。其他引《莊子》内容入文者,如《樗庵箴》中“官道之樗,其材不足以中規矩,匠氏過之,卒棄而馳”的話語正是源於《莊子》(98)戴良《樗庵箴》,《戴良集》卷二十六,第302頁。。戴良會通儒、道與其身世經歷密切相關,藉由老莊文意紓解本懷,足見戴氏儒道之學的修養。
如果從儒學發展史的角度審視,“元明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99)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揅經室一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478册,第548頁。。金華朱學爲明初儒學的主流,而此時金華朱學的主要代表則是宋濂、王禕和方孝孺。宋、王二人在明初政壇與思想界的影響力,使帶有强烈經世意圖和規模恢弘的金華朱學大行於世。不過,由於歷史原因,作爲建文忠臣的方孝孺在義理上並没有對朱學有所推進,在現實政論方面也無多少建樹。反倒因其堅持純粹的朱學,“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100)方孝孺《習庵説》,《遜志齋集》卷七,第229頁。,對來自佛道等方面的學問毫無假借,甚至批評乃師宋濂複雜的思想背景,意圖使朱學一歸於正,提出了一套較爲嚴密且頗具體系性的學道方法。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方孝孺對待先秦子學的態度明顯異於前代學人。
方孝孺曾較爲系統地閲讀過先秦諸子,但其對子書的評價則嚴格以朱學爲立場。如其對《荀子》的看法便很典型。方氏認爲荀子作爲孔子後學,受戰國處士“若楊朱、墨翟、宋鈃、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的學術氛圍影響,“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嵬瑣一曲之偏智”。儘管荀子仍是以儒者自居,但“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蔓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方氏關於荀子的見解沿襲了傳統士人的一般見解,並無多少高明之處,但因其所持堅定的朱學立場,在發表對其他子書的見解時,較之前人更爲嚴厲。如其辨析《子華子》爲僞書,讀《孫子》《吴子》也從儒家仁義角度批判孫、吴二人,指出他們僅是“道德之師”“仁義之師”之外的下下策,“下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談吴起先從天性“固刻忍之人”談起,講其“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子之亞也”(101)方孝孺《讀孫子》《讀吴子》,《遜志齋集》卷四,第112頁。。
對待法家人物,方氏從中選擇契合儒家的内容予以肯定,卻並不接受法家論調,如其《讀慎子》則肯定其中合乎儒家道理的内容,“(慎)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如“立天子”、勞役、用人等,比附儒者所謂“君爲輕”“不違農時”以及“舍己從人”等説法,不過也指出“(慎)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的問題(102)方孝孺《讀慎子》,《遜志齋集》卷四,第112頁。。這種説法也反映到方氏考察戰國名家《公孫龍子》關於“正名”的問題上,方氏認爲公孫龍子一系列的辯駁,不過是“費其辭”而已,甚至有“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學者必務知道”的尖刻判語(103)方孝孺《讀公孫龍子》,《遜志齋集》卷四,第113頁。。從方孝孺對子書的評判來看,明顯有受明初時代背景的影響。他强調儒家的仁義道德之説,儘管有很多論述顯得迂闊,但考慮到元明之際的戰亂以及明初朱元璋的重典治國政策,那麽方氏强調爲政以休養安静爲要就不顯得那麽突兀了。
方孝孺還注意到“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説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部分子書在他看來“遺毒餘焰蔓延於天下”,不得已“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於篇,餘皆焚之”,所選取的諸如“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心欲安静,慮欲深遠”等有助於君主施行與民休息政策的話語,確實符合明初儒者的某些施政理念(104)方孝孺《讀鄧析子》,《遜志齋集》卷四,第114頁。。方氏對子學的實用態度有别於前代學者,一昧的信服朱學,思想上的迂闊在所難免,所以他在面對實際的社會問題時,只知道行《周禮》以復古制,天真地認爲“近者是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幾矣”,與乃師宋濂務實的思想相去甚遠(105)方孝孺《成化》,《遜志齋集》卷三,第83頁。。所以,宋濂思想背景駁雜,卻能使金華之學大行於世,方孝孺之學儘管純粹,卻使金華之學大受政治影響,宋元以來的浦江學脉也因人而終,不得不令後人反思其中的問題。
方孝孺之後,浦江學脉遭受嚴重挫折。此後子部書籍的閲讀雖然不絶如縷,但在明朝理學風氣下並不廣爲接受。我們能找到的明清時期浦江學人的子書閲讀資料相當稀少,很多人如民國學人曹聚仁所言:“我曾經自許爲老莊的門徒,可是,‘老莊’屬於儒家所謂‘異端’。我們浙東山谷地區,雖有小鄒魯之稱,金華學派也成爲理學支流,實在窳陋得可笑,五十方里之内,只有陳姓人家藏有一部洋連紙小字石印本《二十二子》。先父也算承繼金華學派的道統,他一生不曾看到過《老子》《莊子》。他把孟子距楊墨的話説給我聽,卻從來没讀過《墨子》,更不知道有所謂《墨辨》。”(106)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三聯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頁。浦江乃至金華的子學傳統到了晚清竟局限到只有接受新學觀念的青年才能標舉自身學術傾向的程度。曹聚仁對子學有着深度思考,他的一些觀點至今仍不失新意。他對20世紀儒學的衰頹和諸子學,尤其是墨學這類藴含着科學元素的子部之學抱有期待,“大家該明白我們是生在墨學復興的新時代,墨學由於借了西方科學的光而復興了,新的儒墨之争,儒家又已黯然無光了……墨子有着時代的清新氣象,有着唯物論的進步觀點……在這兒,先借時代的光輝,肯定地廢了孔,讓墨家抬起頭來!”(107)同上,第125頁。甚至經過曹氏的論證,“孔墨可以並稱,而大禹乃是墨家的理想人格者”,“先秦諸子中,最幹净的‘顯學’是墨家,不獨墨學富有現代科學精神,墨子那種‘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爲之’的舍己救世精神,比耶穌、釋迦都偉大些,墨家師徒,都是社會革命的戰士!”(108)同上,第139頁。墨學在曹氏看來具備了現代意義上的革新精神,“墨家師徒,也跟如今的社會革命集團一樣,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集團,依他們的政治觀點去實踐躬行的”(109)同上,第141頁。。
曹聚仁站在清末民初盛行一時的進化論角度看待先秦諸子,“我呢,正是站在斯賓塞、赫胥黎的觀點來看老子的”,提出自己的老子觀是在“老氏所説的‘反’字上”,“事物變化之最大通則,則一事物若發達至於極點,則必一變而爲其反面”。老子的辯證法觀點爲曹氏所吸收,構成其老子觀的主體觀念,也正好把握住《老子》一書的精髓。曹氏之於《莊子》,信服蔣錫章在《老子校詁》和《莊子哲學》二書的見解,綜合哲學義理與訓詁文字,“可圈可點,先得我心”(110)同上,第133頁。。曹氏對古人的不同意見並不作評判,而是采取羅素的描述論(The Theory of Description)將種種説法予以描述,供人擇取(111)同上,第121頁。。如其認爲“‘孟’‘荀’不能並稱,以弘通而論,孟子實在不如荀子。荀子乃是儒家集大成的人,比孔子高明得多”(112)同上,第147頁。,“我們尊墨子,重視荀子,有着‘古爲今用’的時代新意義在其中”(113)同上,第150頁。。實際上,曹聚仁對儒家,或者説宋明理學家並無好感,對待主張社會變革的法家則青眼有加,他自己説:“我在道家立場表揚法家的文化史迹,走的還是清末啓蒙期文士,如梁啓超、夏曾佑他們的老路子。”(114)同上,第160頁。
受晚清民國以來新舊、東西文化相互激蕩的影響,曹聚仁有着强烈的疑古精神。他講自己讀了三十年書,自謙没有什麽經驗可説,如果非説不可,他提出三條經驗之談:“時時懷疑古人和古書;有膽量背叛自己的父師;組織自己的思想體系”,還主張青年人“愛惜精神,莫讀古書”(115)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三聯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頁。。曹聚仁從傳統的辨僞、校勘、詁訓三個角度看待古書,受乃師古文經學大家章太炎的指導,對古代文獻尤爲注重去僞存真、辨别校勘的工作,這一態度伴隨其終生。他對諸子學的態度也存在一個文獻整理和學術史梳理的意見,但相比於後來注重諸子學思想的再發掘和諸子學學術體系的現代轉换,曹氏則力有未逮。曹聚仁對待先秦古籍,懷疑大過信任,當然先秦典籍本身就有種種文獻學方面的問題,但針對先秦諸子的研究與復興,曹聚仁則抱持着悲觀的態度,對時人的文化復古不但多有譏刺,對年輕人閲讀和研究先秦典籍也努力的“反對讀經,讀《國學概論》”,畢竟先秦古典的多義和難以達詁本就是學界公認的(116)同上,第6頁。。曹聚仁這樣的態度固然是風雨飄摇、内憂外患下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一般態度,也是20世紀學術思想劇烈變動的真實反映,但結合現代學術體系轉换的時代大勢,一昧地固守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觀點,並對傳統文化畏之如蛇蝎也不符合當下的現實需求。諸子學的現代轉化及其相關理論、方法的升華有待來者。
整個14世紀是浦江文脉的鼎盛時期,出現了許多文化名人,戴良對此也有評論:“浦陽於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鐘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玳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117)戴良《浦陽人物記序》,《戴良集》卷六,第59頁。浦江學人的諸子學研究深受性理之學的影響,同時與其人生遭際密切相關,尤其在元末明初社會大動盪時期,子學著作中關乎性靈安頓的内容尤爲這一時期的學人所注意,但我們也注意到隨着明初社會秩序的重塑與穩定,一套嚴格由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工程重新規制士人的精神世界,元代寬鬆治理下士人豐富的創造力以及對子學的獨特認識也隨之暗淡。直到明中期國家管理日益鬆動,士人在心靈自由與子學研究上才迸發出不亞於宋元的思想創造力。經過傳統學術研究範式的近現代轉化,曹聚仁、方勇等人對子學有着不同於前人的深入思考,浦江子學傳統由此得以新生(詳見下文)。
4. 詩學
元人王禕曾盛贊元朝的文章成就:“於乎!以余觀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謂盛矣。當至元、大德之間,時則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則廬陵歐陽文公之文殿其終。即兩公之文而觀之,則一代文章之盛,概可見矣。”(118)王禕《文評》,《全元文》第55册,第710頁。姚燧、歐陽玄,一先一後,如兩峰對峙,元文之盛可得而知。至於説詩歌成就,楊維楨則云“我朝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不無溢美之詞(119)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63頁。。元人關於有元一代的詩文成就有如此自信,實際情況如何,窺一斑而見全豹,以浦江文脉爲中心進行考察,或能得窺宋元以降詩學的發展脉絡。
宋亡入元,詩風復盛,浦江文脉至方鳳發生了轉變。有别於宋代濃重的理學色彩,元代浦江學人的文人化色彩日趨明顯,“婺中之學……漸流於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義烏諸公(黄溍、柳貫等人)師之,遂成文章之士……至公(宋濂)則漸流於佞佛者流”。清人全祖望從清學背景角度,批評元代婺學的流變,語帶譏諷,黄百家也有“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輩而下,多流爲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道薄耳”之論(120)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第2801頁。。這實際上是不瞭解元代婺學風氣轉變的時代促因所致。南宋末年的詩歌,衰弊已極,究其原因,南宋政府科舉取士重明經、詞賦,“以詩進者”,“謂之雜流,人不齒録”,“人不攻詩,不害爲通儒”,風氣使然,南宋詩歌成就可想而知,隨着宋元鼎革及元初數十年不行科舉,“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121)戴表元《陳晦父詩序》,《全元文》第12册,第122頁。。元代詩風之盛,遠超前代,詩歌成爲元人寄托性靈的載體,寫詩品詩成爲元人日用常行的必備,士人之間約爲詩會,“每爲會期,遠者二三歲一聚,近者必數月,相見無雜言,必交出近作,相與句字推敲,有未穩處,或盡日相對無一言,眉間鬱鬱,參差倚闌行散,饋食不知,問事不應”(122)劉將孫《蹠肋集序》,《全元文》第20册,第164頁。,以詩宣洩心中七情,甚至到了不知老之將至的地步,“脚跟不識青雲路,頭髮空成白雪絲。怕醉有時曾止酒,遣閑無日不吟詩”(123)謝應芳《生日口號二首》,《龜巢稿》卷十六,《四部叢刊》本。。
遺民方鳳、謝翱、吴思齊受宋亡刺激,詩風一變爲慷慨沉鬱,浦江詩風也在他們影響下異於前代,“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浦江士人多好遊歷,方鳳自宋亡後,“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淚如霰”,飽覽山川,詩歌“音調淒涼,深於古今之感”,宋濂曾評其詩風極肖杜甫,與南宋江湖派士人大爲不同,“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即杜甫)者非耶”(124)宋濂《浦陽人物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六,第2265~2266頁。。方鳳也由此被視爲遺民詩風的典型代表。
方鳳過世於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浦江文脉的第二代學人已開始活躍於文壇,但此時的文壇風氣已不同於元初,遺民風格的詩文陸續退出舞臺,盛行的是一種雍容和緩、平易正大的“盛世之文”。這是一種以元一統爲時代背景而形成的所謂“盛世”,融合了理學的思想觀念,以平易、正大爲主要特徵的文風在元中期得以展開,理學由此“流而爲文”,以理學爲精神底藴的文風正是元代文學思潮的典型體現(125)查洪德《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8頁。。元代詩風大振,是文統與道統在元代士人身上合一的典型表現。理學精神滲透至文學創作,大量文人以經學爲底藴,肆志於詩文,理學的各派傳人轉而成爲文章之士。這一轉變完成於元中期,如果按照浦江文脉的發展而言,恰是方鳳的弟子輩,如黄溍、柳貫、吴萊等人在文壇發揮影響力的時候。
隨着元朝在江南統治秩序的穩固,浦江詩風逐漸由遺民詩向所謂盛世詩風轉變。其中的代表是方鳳的弟子如黄溍、柳貫、吴萊等人。考察浦江學人在詩歌方面的内在修養,漫遊山水以增長詩思才情是方氏後學的一個典型特徵。方氏門人多好遠遊,以此壯氣填胸,行諸筆端。柳貫得仙華山、浦陽江山水滋養,“學文於方鳳、吴思齊、謝翱”,“以文學知名”,詩文成就與虞集、黄溍、揭傒斯並稱“儒林四傑”;吴萊爲方鳳孫婿,年少明敏,“好遠遊,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絶處及昔人歌舞戰鬥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遊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磐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遊。由是襟懷益疏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由此“工詩賦,尤善論文”,於詩文一道有獨到見解,“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門人宋濂從吴萊處習得作文之法,在“篇、段、句、字”方面都有深刻見解,宋濂文風的養成,吴萊在其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126)宋濂《浦陽人物記》,《宋濂全集》卷九十六,第2266~2270頁。。
黄、柳、吴等人都曾北上大都,在與北方文人集團及江西籍文人集團的接觸中,他們所秉持的南方文風也獲得了認可。他們提倡自吕祖謙以來便强調的文與道的合一,詩風崇尚雅正,貼合正統,他們的文學理念在北方得以展開。黄溍“之所學,推其本根則師群經,揚其波瀾則友遷、固”,學術“精明俊朗,雄蓋一代,可謂大雅不群者”,其文則“上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屬,其生色之融液,至今猶津津然”(127)宋濂《金華先生黄文獻公文集序》,《宋濂全集》卷三十二,第705頁。。再如柳貫,他的思想很活躍,這與婺州地區多種學派之間相互競争密切相關。柳貫“丱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奥義,多所發揮。繼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栝吴先生思齊、粤謝先生翱。三先生隱者,以風節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絶出於流俗”(128)柳貫《柳貫集》附録《翰林待制柳公墓表》,第563頁。。柳貫受朱熹傳人金履祥教授,爲朱學四傳,後受陳亮龍川學派吴、方、謝等人的古文詩歌方面的教導,由此可見,柳貫身上道與文達到了某種程度上的統一,符合元代“道統與文統合一”的主導性思潮。梳理柳貫的生平,宋元之際東南詩文各派文學思想對他的影響相當明顯,如方回、戴表元、牟應龍、胡純、胡長孺等人,都在柳貫早年遊歷杭州時有過接觸。這些前輩學人給予柳貫的影響,讓我們不難看出柳貫文學思想所具有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柳貫强調他的理學背景,指出從事詩文創作,不僅要“求之群聖人之經以端其本”,還需參考“孟、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重點還需將創作理念歸之“周、程、張、邵、朱、陸諸儒之論”,從而表現“義理之真”與“性情之正”(129)柳貫《答臨川危太樸手書》,《柳貫集》卷十三,第363頁。。柳貫的這一主張將理學與詩文創作進行融合,並進一步提出近乎心學的那種貼合自然、無多雕飾的“出諸余心,宣諸余口,無雋味以悦人,無鴻聲以驚俗……以足吾之所好而已”的詩文創作理念(130)柳貫《自題鍾陵稿後》,《柳貫集》卷十八,第489頁。。柳貫的詩文創作理念是複雜和矛盾的,在道統與文統之間徘徊,受到世風影響,時而以理學道統正傳的面目示人,時而以追求自然心性、嚮往山林的詩人角色出場。實際上,柳貫扮演了浦江文脉之中一位捏合宋元之際遺民文風與元中期所謂盛世文風的角色,他處於承上啓下的過渡時期,與時代的脉搏與個人的命運相頡頏,努力尋求個人生存與心靈發展的平衡。但是,這種平衡是難於掌握的,柳貫更適合做一位優遊林下的士人,其精神屬於山林而非廟堂,他常年偃蹇的鄉居生涯便透露了此番消息。
柳貫、吴萊等人對浦江第三代學人的影響較爲顯著。以宋濂爲首的浦江學人,他們的文學理念繼承了前輩師長們的某些原則和觀念,但有所不同的是,宋濂等人關於詩學的論述更爲注重道統之於文統的整合。宋濂承認詩歌“發乎情性者也”(131)宋濂《王氏夢吟詩卷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二,第436頁。,“乃吟詠性情之具”(132)宋濂《答章秀才論詩》,《宋濂全集》卷二,第59頁。的内在屬性,强調“無背於經”才“可以言文”,詩文創作要根基於六經,這點與柳貫有意消解道統與文統之間差異的觀點有别。宋濂將詩能否合於“古道”,即合乎理學家所秉持之道作爲審視詩歌内容的標準。詩不僅要音韻和諧,辭氣暢達,還要合乎格律,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義”(133)宋濂《霞川集序》,《宋濂全集》卷三十三,第714頁。,以儒者之詩的立場品評詩文,以理學家的態度堅持詩文的聖賢氣象。但宋濂身處元末,詩風、文風已然不同於元中期的盛世文風而流於“棄道”而以“吾心”爲師。宋濂曾對此深爲不滿:“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倡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134)宋濂《答章秀才論詩》,《宋濂全集》卷二,第59頁。詩文風氣到了晚元,確實發生了轉折,即便是最能堅守文道傳統的金華學脉,理學道統“流而爲文”並參合釋道已經相當明顯,宋濂文風合三教學問爲一爐的博大氣象在元末可以受到推崇,但在嚴明理學藩籬的明初則已得到批評和修正。對比宋濂高徒方孝孺的文章和生平志業就可明顯得到這樣的認識(135)方孝孺著,徐光大校點《遜志齋集·前言》,寧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頁。。這種文風因世事政教變遷而作的改變不僅難以避免,也正是這種變化才使得區域性文脉傳統呈現複雜多面的特徵,這是區域性文化研究不能忽視的問題。
浦江文脉的學術底色源自金華之學,被視爲最能堅守婺學底色的一支。如以元代文統與道統合一的趨勢而言,相比於元代其他區域性學術團體,宋元時期浦江文脉雖迭經變遷,但屬於最後文人化的一支。對於道與文的兩相關係,浦江學人在整個元代學術共性的背景下,有自己的學術堅持,也有自身的學脉傳承與理念更新。在政治因素左右下,浦江文脉雖在明初大放光彩,但也因爲政治集團的利益衝突而陷入四世而斬的文化困境,不過來自學脉本身的文化影響力,自明中期以後,學術思想的回潮,浦江文脉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其影響力,宋濂在言及當時吕學境況時曾説“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也即所謂“托物引類”的道理(136)宋濂《思人辭》,《宋濂全集》卷八十六,第2035頁。。這一論説對於理解浦江文脉的延續頗有啓發,思想觀念的相感相生,僅僅局限於時代和代際傳承不免視野狹隘。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能作爲區域性文化集團特異性傳播的一個特徵。
照顧到明清屬於科舉社會的發達階段,從對浦江科舉人物産生的量化統計,觀察當地區域文化的氛圍,或能透露區域性文化的延續情況。明初浦江有大量人才通過薦舉的方式進入明朝政壇,爲數多達60人,成爲浙東士人群體在明初官僚機構的重要組成。另舉明朝浦江科第人物爲例,有明一代浦江産生進士9人,舉人32人,這一數字的獲得,在科第艱難且有解額限制的明代實屬不易,甚至超過了北方某些州府在明朝科第人物的總和(137)何保華校注《明清浦江縣志兩種》,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632~634頁。。從中也可解釋浦江文風不墮的歷史原因。
二、 當代浦江諸子學研究對傳統文化的振興(138)這一部分獲允參考劉思禾《立乎其大——淺談方勇教授之治學》及《現代諸子學發展的學科化路徑及其反省——從胡適、魏際昌到方勇》(《諸子學刊》第十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92~316頁),特致謝忱。
宋濂有感於吕學之不傳而有言,“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學術脉絡的不絶如縷有待於後世學人的賡續與發揚(139)宋濂《思人辭》,《宋濂全集》卷八十六,第2035頁。。明清浦江科舉場屋之學盛行,學人思想被束縛於程朱理學、四書章句之中,經世之學罕有人言,諸子之學不顯於世。清代諸子學研究作爲經學研究的拓展,立身於傳統的四部之學,與經子關係、今古文等問題糾纏混合。晚清民國學制改革,王國維、梁啓超、張百熙、章太炎等人並未給予經學、諸子學合理的學科地位。這些傳統學術門類被分解於現代大學體制中的不同學科,被中文、哲學、歷史等學科吸收、轉化(140)劉思禾《現代諸子學發展的學科化路徑及其反省——從胡適、魏際昌到方勇》,《諸子學刊》第十九輯,第292~316頁。。受西學影響下的現代學科體系,認爲傳統且混雜不清的經學、諸子學、佛學、理學等内容不符合所謂現代化的學科轉型需要,將其納入分工明確的現代學科進行分解、吸收,一個後果便是原有的經學、諸子學等傳統學術整體、學術脉絡被拆分和消解,不同學科基於本學科的研究傳統形成方法各異的學術研究路徑。這些原本有着自身整體特徵的學術傳統已然不復其本來面目。回溯明清以至當代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化歷程,浦江學人之中有能力推動諸子學發展且有所成就者,則要從方勇教授談起。
(一) 方勇的學術歷程與治學脉絡
方勇,浦江人,故宋遺民方鳳第二十四世孫,現任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方勇先後就讀於河北大學、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及博士後經歷,先後師從魏際昌、吴熊和、褚斌傑三位先生。方勇繼承了胡適的古典研究思路並爲其再傳,又有獨特的研究進路與格局,不僅開拓了宋代遺民文學的研究領域,還創造性地拓寬了莊子研究的路徑,建立起諸子學術史研究體系,以大型諸子學文獻叢書《子藏》爲文獻基礎,推動當代諸子學發展,留心地方文獻的整理工作。一言以蔽之,方勇以重振諸子學傳統爲要旨,包括推動諸子學史研究,創建諸子研究中心,創辦《諸子學刊》,彙聚培養諸子學研究人才等工作,爲推動諸子學的當代復興做出了重大貢獻。
方勇在其研究領域與整體格局上,在不同時期有着調整與變化,但其治學理念則是一以貫之的。從方勇的成長歷程而言,早期在河北大學學習、工作到完成博士論文,時間跨度從1983年至1997年,期間有《論先秦小説》(碩士學位論文)、《莊子詮評》(與陸永品先生合作)、《方鳳集(輯校)》及博士論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等作品。隨後爲寫作《莊子學史》階段(1997—2008年),近十年則爲推動諸子學發展而傾注心力(2008年至今)。
儘管方勇在早期研究階段所形成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還基本屬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範疇,但其中所凝練出的研究路徑已與前人有所區别。如其《莊子詮評》一書,本爲注解莊子之作,但與廣爲流傳的陳鼓應先生所作《莊子今注今譯》的研究路徑有所區别。《莊子詮評》書中廣收歷代莊學注疏數十種,排比歷代莊學著作,分析得失,不僅有集成文獻與梳理學術史、便於學人掌握歷代莊學發展脉絡之功,還可從中得窺方勇此後治學之一般輪廓: 基於文獻和學術史的研究方法,重視思想創獲的發掘。此外,方勇有感於地方文獻歷經朝代更迭、天災人禍而大多散佚不傳,不僅將浦江方氏二十四世祖方鳳存世著作進行輯録、點校,出版了《方鳳集》,還擴大搜集範圍,將浦江一地歷代存世文獻搜集整理,數百巨册的《浦江文獻集成》業已成書(141)方勇先後整理出版《方鳳集》《存雅堂遺稿斠補》《存雅堂遺稿集成》《浦江文獻集成》等地方文獻,又着意呼吁恢復月泉書院,籌建“方山子國學講堂”等地方文化事業。目前而言,《浦江文獻集成》是浦江歷史上最大的地方文獻搜集整理工程,網羅歷代浦江文獻共計700餘種,合爲250巨册,與《金華叢書》《紹興叢書》相近,不僅是地方文獻整理的重要成果,歷史上瀕臨失傳的浦江文獻也賴此得以保存。月泉書院因爲得到浦江縣委縣政府的支持和幫助而得以恢復。“方山子國學講堂”也在多方支持下成立並展開活動,浦江當地傳統文化的建設已然步入快車道,浦江文化的歷史内涵也會在新時代迸發勃勃生機。。至於説方勇博士論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則是其於1997年完成後,200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是書增訂版自序提到,“我原來的學術志趣是在先秦文學上”,後來一系列的因緣變化,在吴熊和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借《方鳳集》的點校之功,從先秦文學轉移到宋元文學上,但其方法仍是“閲讀和梳理宋元文獻資料”,憑藉“搜集鑽研前人的研究成果”,三年下來,完成了這篇博士論文(142)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是書研究宋元之際故宋遺民的歷史與文學,書中所融合的家國情懷與細密研究的治學風格令人印象深刻,傅璇琮認爲此書的突破點在於“以地域分佈與互動相倚網絡來凸顯南宋遺民詩人各種複雜心志”,注意到“具有共性的民族危機感和悲憤意識,又反映出某種不均衡的生活方式和心理追求”,因而對此書作出“這就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擴寬、觀念更新所帶來的極有現代意義的成果”的評價,足見其在遺民文學領域的典範意義(143)同上,第8頁。。
《莊子學史》是方勇奠定其學術地位的扛鼎之作。方勇於1991年完成《莊子詮評》之後,受胡適古典文獻整理的研究思路的長久影響和啓發,有意從文獻和學術史角度通盤研究莊學,力圖寫就一部莊學通史。1997年以後的十餘年,方勇將全部心力投注於《莊子學史》的研究之中,期間雖經歷了博士後出站、到華東師範大學任教等人事變動,但爲此書的撰述,宵衣旰食,不休不怠,歷十餘寒暑,完成《莊子學史》計三卷二百餘萬字(後增補爲六卷三百一十多萬字),依時代劃分有戰國秦漢編、魏晉南北朝編、隋唐編、宋元編、明代編、清代編、民國編,並有導言與綜論,另附《一百年來莊子研究論文輯目》和《主要徵引書(篇)目》。書中歷述莊子思想與莊子文本的流衍變化,將歷代莊學作者一百五十餘人予以詳盡叙述,評述莊學著作數百種。全書鋪陳開來,氣度恢弘,不僅是莊學研究的指引與路標,還爲後來諸子學史的研究奠定學術範式。其中無論是從方法上注重原始資料與原始語境,表現出有别於哲學史化的莊學研究的治學理念,還是在諸子學研究學科化方面,方勇對諸子學現代學術形態,尤其是哲學史模式下的諸子學研究予以充分反思。在這一思想理路下,方勇指導其弟子不斷在諸子學史領域拓展陣地,先後將《莊子》《論語》《孟子》《老子》《列子》《韓非子》《論衡》等子學著作納入到整個諸子學研究領域,成立了系統的、分工明確的專業諸子學史研究團隊。
近代學術與時代發展的脉絡昭示,一種有别於傳統儒學一元獨尊且更具靈活性、適應性的學術取向,或能更有效地應對東西方文化交流與時代挑戰的需要。在原有諸子學研究基礎之上,方勇反思諸子學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歷史問題,提出以“新子學”觀念爲中樞推動諸子學傳統的發展與創新。爲此,方勇積極參與諸子學著作的推廣與傳播,推動中華書局出版《諸子集成現代版》(亦即《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後爲北京商務印書館籌劃出版《諸子現代版叢書》。2007年,方勇在華東師範大學建立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創辦《諸子學刊》,這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以諸子學研究爲刊行主旨的學術刊物。2017年,《諸子學刊》進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系列,得到學界的進一步認可。2010年起,在華東師範大學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聯合支持下,啓動迄今爲止最大規模的諸子學大型文獻叢書《子藏》工程,搜集影印自先秦至民國末年所有存世的先秦漢魏六朝諸子白文本及歷代諸子注釋、研究著作,分門别類,以《老子》《莊子》《管子》集成的系列形式,結集出版,著述多達5000種,並爲每種著作撰寫提要。整部《子藏》,預計總册數多達1300餘册,現已出版三批,492册,1500餘種。可以預想,《子藏》工程作爲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文獻集成工作,不僅爲未來諸子學各項研究工作的順利展開提供了豐厚且珍貴的文獻資料,還爲“新子學”理念的提出奠定堅實的學術支撐。
2012年10月22日,方勇在《光明日報》國學版發表《“新子學”構想》,引發學界熱烈討論,文中正式提出“新子學”理念和在此理念下復興和重建諸子學學術體系的理論構想。隨後分别發表《再論“新子學”》《三論“新子學”》等系列闡述文章,“新子學”理念逐漸得以清晰明確地呈現: 即批判性地反思現代學科體系下,尤其是以哲學史書寫方式爲背景的諸子學研究模式,力圖還原諸子學原有的學術脉絡,透過細緻的文獻整理與學術史梳理,尋找到元問題和元方法,從而進入諸子學本身的文化精神世界,對當代文化價值進行獨特解讀(144)劉思禾《立乎其大——淺談方勇教授之治學》,未刊稿。。
“新子學”理論的創獲得益於文獻、學術史和思想觀念等三個層面的不斷深入研究。在當代學術體系的語境下,文獻、學術史和思想創造如諸子學研究的鼎之三足,不可偏廢。子學的創造期在先秦,先秦典籍問題最突出的也在文獻。中華基本典籍幾乎都有非常複雜的文獻問題,而且面對大量出土文獻,缺乏文獻意識和文獻訓練必然會使諸子學的學術研究無法進行。梳理學術史是新子學的重點問題之一,諸子之間複雜的學派關係、彼此間的影響、思潮的流變以及歷代諸子學的演變,無不昭示學術史在諸子學研究中正本清源的作用。另外,僅僅着眼於文獻與學術史的研究並不足以反映“新子學”的學術構想和價值主張,還需要深刻的思想研究。當代多元的文明形態必然要求古典研究走向多元,需要就文明的最一般的問題展開討論,在古今語境中回環往復、比勘對校,從而有符合現代思維、現代語境的真知灼見。諸子學傳統的重振,或者説新子學思潮的興起,作爲崇尚多元争鳴而非一家獨尊的“子學精神”的具體顯現,不但可視爲由傳統文化資源向現代社會轉化而來的一種新思想,更是在古已有之的叢林中獲得了現代技術的“新的樹種”(145)曹礎基《新子學懸想》,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學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頁。。
(二) 方勇對諸子學現代學術形態的研判
方勇在其研究領域和整體格局方面的一系列調整變化,有着基本的脉絡和特點。他的問題意識始終圍繞着文獻、學術史及思想創造三個部分構建諸子學的研究框架,倡導回歸諸子學自身傳統,從而在接續胡適從文獻角度建立諸子學學科化範式的同時,對諸子學如何回歸自身傳統及現代轉型問題予以反思和修正。這不僅需要重新思考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現代重構問題,還需要針對現代學術體系中諸子學的身份及諸子學進入現代中國學術體系的形態等問題進行厘定和選擇。
方勇對諸子學回歸學科化有着充分的自覺意識。他肯定“現代學科體系推動了諸子學長足發展”,但指出作爲中國古典學問的諸子學,有其自身屬性與特徵,那麽將之進行學科化分解研究,能否適應現代學科體系,值得存疑。爲此,方勇從現有學科框架下的研究成果、諸子學研究隊伍、所屬學科的專業訓練以及諸子研究的固有模式等角度,提出在目前學科分立、專業受限、“不同領域之間的研究成果缺乏共用機制,學者之間也很少聯繫”的情況下,學者們在諸子研究上囿於固有模式,無法突破,“表現爲研究對象歸於集中,研究的方法歸於單一”,“這些都不利於諸子學發展”。在與學界同仁不斷交流後,諸子學研究的共性問題浮出水面,“大家都認爲諸子學要發展,就要突破現有的學科限制,擴大學界的交流,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綜合性,作一種跨學科的研究。諸子學要發展,諸子學界迫切需要一個穩定、多元的學術群體,在相互溝通之中凝聚共識”(146)方勇《2014年“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言稿》。。期待綜合性、跨學科、全方位的諸子學研究新格局,成爲目前諸子學研究需要努力爲之的方向。
“新子學”理念的提出,其“新”在何處,從哪里可以獲得思想資源回應“新”的問題,這是構建“新子學”理論亟需解決的問題。方勇分别從諸子學與西學的關係,由諸子學的原生中國意識導出其問題意識與方法,解決具象化諸子研究的方法問題以及建立系統的“新子學”學術體系等角度,較爲系統地論證諸子學學術體系建構的理念與方法,回應諸子學要以怎樣的形態自立於現代中國的學術體系的問題。
方勇着意立足回歸諸子發生的原生思想形態,歸諸史源,重新發掘諸子學原本的問題意識和思想綫索,將諸子學定位到原生的中國意識,從而反思受西方哲學史脉絡影響下諸子學趨向行上學的研究路徑,對近代以來子學“淪爲西學理念或依其理念構建的思想史、哲學史”的文化“附庸”表示不滿(147)方勇《“新子學”構想》,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學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三論“新子學”》,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二輯)》,學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頁。。當然,“新子學”也非簡單的文化保守主義的話語,而是注意到諸子傳統形態與現代化學術理念之間的融通,承認諸子學作爲中國“軸心”思想元典的文化價值,不帶偏見地正視和發展其文化智慧,“面對現代學術中世界性與中國性的衝突,‘新子學’的主要構想是以返歸自身爲方向,借助厘清古代資源,追尋古人智慧,化解學術研究中的内在衝突。所謂返歸自身,就是要平心静氣面對古人,回到古代複合多元的語境中,把眼光收回到對原始典籍的精深研究上,追尋中國學術的基本特質”。這是“新子學”研究的旨歸。不過,方勇對簡單的中西比較研究持有疑慮,指出應以冷静的態度對待中西結合的相關研究。那種中西結合的簡單研究,“結果卻往往導致不中不西的囫圇之學”,根基淺薄卻貿然從事的中西比較之學,對任何學問都是一種傷害,“任何真正的學問都有堅實的根基,没有根基的綜合從來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48)方勇《再論“新子學”》,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21頁。。
但是,面對西學盛行的當代社會,西學能給“新子學”帶來什麽,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方勇指出,“新子學”當然不會忽略西學,但也表明“我們的工作重心還在中國性的探索上,在中國學術的正本清源上”的學術立場。對待西學,首先應將諸子各家的研究“回歸原點”,采用原理化的研究方法,“以問題爲中心,做一種會通的研究。要抓住核心觀念疏通古今,融入現代生活中加以討論”,將諸子對中國文明所洞見的基本史實作最切近中國社會的闡釋。高度“人工化”的現代社會“需要社會科學的視角才可以理解”,因而采用西學之中社會科學化的種種方法,“諸如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的方法來闡釋”古典文本,或能有更爲實際的解釋力(149)方勇《三論“新子學”》,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二輯)》,第7頁。。
諸子學曾得益於現代學術分科的影響,不同學科湧現出大量的、看似輝煌的學術成就,但哲學史話語下的諸子學卻往往被詮釋成帶着西方哲學話語的另類面孔,本是中國的傳統學問卻讓國人難以理解而紛紛卻步。學術分科本是讓學者儘快進入諸子學研究領域的捷徑,在此時卻歷史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成爲制約諸子學研究的窠臼。“新子學”試圖擺脱近代以來加諸其身的現代分科體系的束縛,目標“建立以諸子傳統爲研究對象,具有相對獨立研究範式的現代學術體系”。“‘新子學’需要破除歷史上的種種偏見,也需要反省現代學術的盲點,其要點就是探索中國文明形態的基本特徵。這很可能顛覆我們以往對諸子學、經學以及對先秦時代的一般看法,從而在思想的層面上對於‘何者爲中國’做一個回答。”(150)方勇《新子學: 目標、問題與方法》,《光明日報》2018年4月7日。方勇對自胡適以來所謂諸子學學科化範式進行反思,倡導回歸諸子學的自身傳統,回應“何者爲中國”的問題。
實際上這仍是回應諸子學現代價值的一種嘗試,將諸子學研究直接用於“對治現代性,而非論證現代性”,“從哲學史的範式中走出來,把重點從知識構造轉出,重新唤醒傳統資源的價值意義,讓經典回到生活境遇中……唤醒價值,是指在傳統價值中找到適應當代的形式,並與現代價值做有效溝通”(151)方勇《三論“新子學”》,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二輯)》,第7頁。。還諸子學以本來面目,將分列開來的諸子學研究予以統合,唤醒諸子學自身的問題意識與價值場域,將諸子學研究内在思想的原發性與表達方式的現代性有機結合,不僅是“新子學”理念提出的棘手問題,也恰是諸子學回歸自身“恰切的理論性”的關鍵點(152)劉思禾《現代諸子學發展的學科化路徑及其反省——從胡適、魏際昌到方勇》,《諸子學刊》第十九輯,第292~316頁。。
當代諸子學研究如何沖出一條新路,尋找到某種更好的形態或範式論述諸子之學,從而實現諸子學現代轉型的文化訴求。這不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自我認同,解決自身問題,解決現代生活困境的需要,同樣是文化適用性的體現,古典學術的新生能否爲當下提供某種思考或解決方案,能否適用於當下,也是“新子學”理念進一步發展的題中之義。
餘 論
浙東自古以來學術昌盛,名家輩出,舉凡吕祖謙、葉適、方鳳、宋濂、黄宗羲、全祖望、章學誠等輩,皆爲一時之選。整體而言,儘管浙東歷代以來没有形成綿密有序的學派組織,但區域性學術集團卻在浙東屬於較爲典型的文化現象。若以金華地區而論,自兩宋之交中原文獻南渡,金華便逐漸成爲一個重要的學術區域化發展重鎮。梳理宋、元、明初三個時段金華地區的文化人物,不難發現以師緣紐帶聯繫起來的浦江學人,其代際嚴明、傳承有序、理念合轍,雖有時代遷轉之影響,仍不失爲金華地區文脉傳承的典範地域,同樣也是江南文化轉爲中國文化重鎮不可或缺的貢獻者。宋元浦江學術的底色帶有濃厚的婺學色彩,後隨着朱學的傳入而匯流,藉由浦江學人與明初政治的結合,開出有明一代的文章之派。由此可見浦江文脉對明代文化走向的影響力不可謂不深。至於説浦江學人在理學影響下的經子觀念,不僅是整個社會思潮疊相作用的産物,亦是元代中後期士人的離道傾向和文人化趨勢下文學自由思潮衝擊的結果,吴萊、宋濂師徒恰可拿來對比二者子學觀念的變異。
近代以後,帝制時代儒學獨尊的經學化傳統不復存在,傳統經學轉而成爲經學史,離經還子的呼聲高漲,即强調重新回歸因爲被政治收編而趨於模糊的子學原初性格,承認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内在多元性和互文生長的特點,提倡異於傳統諸子學研究的“新子學”研究理念。浦江學人的子學觀念發展到了近代,方勇教授不僅接續浦江文脉傳統的子學觀念,並將諸子學研究納入現代學術體系,形成以文獻、學術史及思想研究包納並舉的“新子學”理論研究架構,以此適應當代文史哲研究交錯紛争的動態變化。2017年10月27日上午,方勇教授在臺北“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既可作新子學研究通古明今、觀其會通之目標的清醒認識,也可作爲浦江文脉承前啓後、開新啓昧的預告——“縱觀數千年來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之發展,譬猶不同大陸板塊之間經由獨立漂移轉而互相碰撞衝擊,原先的矛盾只發生於板塊内部,新的矛盾則會從板塊内部擴張至板塊之間,由單一之個體超越至彼此之關聯。百年以來,中西文化之碰撞交流亦復如是……‘新子學’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試圖努力尋求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