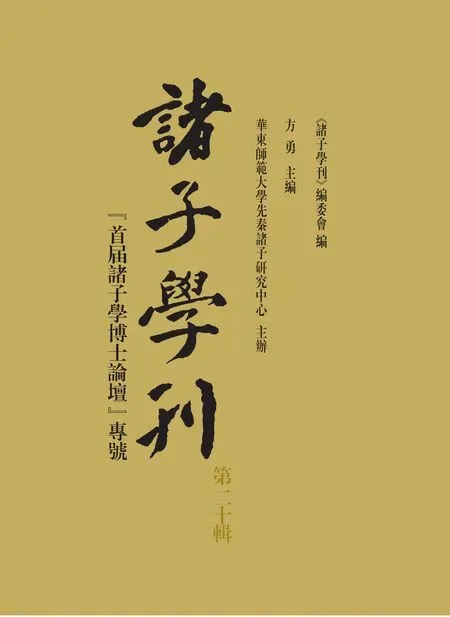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名與實
劉曉軍
内容提要 《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得名緣於文獻著録的需要,主要依據是學術思想體系的分類,凡授受不明、學無家法又妄加附會古人者即爲小説家。這決定了小説家文本内容駁雜、體例繁蕪與價值卑微的文類屬性。小説家以闡述思想學説爲主,説者爲闡明己意,會使用説理、叙事、博物等方式,遂衍生出後世小説文本的三種文體形式,即論説體、故事體與博物體。《漢書·藝文志》對小説概念的界定、小説價值與地位的評估以及小説文本的確認等諸多方面,一直影響着古代的小説觀念與小説生産。直到晚清民初西方小説理論傳入中國,這種影響才逐漸式微。
關鍵詞 《漢書·藝文志》 諸子 小説 文類 文體
作爲現存最早著録小説的書目文獻,《漢書·藝文志》無疑是中國古代小説最基本的“法典”。它對小説概念的界定、小説價值與地位的評估以及小説文本的確認等諸多方面,一直影響着古代的小説觀念與小説生産。降及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我們仍然能够看到《漢書·藝文志》的遺響。這樣一部反映中國小説原貌與主流小説觀念的書目,理應在古代小説研究方面擁有足够的話語權。20世紀以來,在中國文論研究集體患上“失語症”的大環境下,小説理論研究難以獨善其身,包括《漢書·藝文志》在内的小説目録總體處於“失位元”的狀態。現代小説觀念與小説理論移植於西方,與《漢書·藝文志》對小説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今人大多不願承認《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爲小説。加上《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基本上名存實亡,今人無從窺其堂奥,於是這部本應成爲評量中國傳統小説準則的史志目録,逐漸被世人遺忘。它給古代小説研究留下的遺産,除了後人據此生造的作爲現代小説參照物的“目録學小説”這個概念,似乎再難發現可以利用的價值。然而《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畢竟屬於歷史存在,不會隨着時代變遷而改變它的屬性。在漢人的觀念裏,這種文獻就叫做“小説”。無論今人是否承認其爲小説,此類文獻作爲“小説”被著録、被認可甚至被仿作了上千年,這是無法抹殺的歷史事實。我們認爲,《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及其體現出來的小説觀念,是中國小説古今演變的邏輯起點。本章將首先回到漢代的歷史語境,剖析《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命名立意;再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還原《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的本真面目;最後再綜合各種因素,論述《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文類屬性與文體特徵。
一、 《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立意命名
《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産生出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需要,這種分類思想始自劉向、劉歆父子對書籍的分類整理。
劉向校理群書時,爲每書撰寫叙録,叙述學術源流,辨别書籍真僞。阮孝緒云:“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本書。”(1)阮孝緒《七録序》,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編《目録學研究資料匯輯》第二分册《中國目録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42頁。劉向的校理以學術思想爲依據,按照學説體系編定群籍。余嘉錫云:“劉向校書,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學,出於某子,某篇之簡,應入某書。遂删除重複,别行編次,定著爲若干篇。……蓋因其學以類其書,因其書以傳其人,猶之後人爲先賢編所著書大全集之類耳。”(2)余嘉錫《古書通例》,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75頁。劉向又將所有叙録結集成書,是爲《别録》。劉歆以《别録》爲基礎總括群篇,撮其指要,撰成《七略》。姚名達認爲《七略》開啓了古代的圖書分類,他以《漢書》卷三十六載劉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群書,種别爲《七略》”爲據,認爲“所謂種别者,即依書之種類而分别之”,故《七略》爲圖書分類之始。(3)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臺灣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65年版,第52頁。所謂“略”者,即簡略之意。《七略》摘取《别録》以成書,《七略》較簡,故名略;《别録》較詳,故名録。參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第51頁。《七略》的分類標準較爲駁雜,但總體上仍然以學術性質與思想派别爲標凖。班固删節《七略》舊文,參以己意,略加注釋,遂成《漢書·藝文志》。其中“諸子”一略,包括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小説家共十家。
“諸子略”的設立,是典型的學術系統分類。班固認爲,儒、道等九家的學術思想出於王官,“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4)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第40頁。;而小説家“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説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5)同上,第39頁。。學術淵源不同,價值地位也存在巨大差别。關於小説家的設立,吕思勉的解釋較爲通俗,他説:“蓋九流之學,源遠流長,而小説則民間有思想、習世故者之所爲;當時平民,不講學術,故雖偶有一得,初不能相與講明,逐漸改正,以蘄進於高深;亦不能同條共貫,有始有卒,以自成一統系;故其説蒙小之名,而其書乃特多。”吕思勉進而指出,小説家之所以位列諸子之末,是因爲“徒能爲小説家言者,則不能如蘇秦之遍説六國,孟子之傳食諸侯;但能飾辭以干縣令,如後世求仕於郡縣者之所爲而已。”(6)吕思勉《經子解題·論讀子之法》,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第93~94頁。
然則“小説”一詞究竟有何含義?班固爲何要以“小説”之名爲學術派别立目?這兩個問題看似尋常,卻都有深研的必要。
“小説”一詞,較早見於《莊子·外物》: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没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盪,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説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説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7)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925頁。
莊子此文屬諸子常用的“譬論”,即以“釣魚”譬“得道”——“鯢鮒”譬“小道”,“大魚”譬“至道”。經世之才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故能於東海之中釣得大魚,即“至道”;輕浮之徒只會諷誦詞説,只能於溝渠中釣得鯢鮒,即“小道”。由溝渠中不可求得大魚的小道理,莊子又引申出了“飾小説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的大道理,即成玄英云“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説,以求高名令聞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8)同上,第927頁。。
莊子所言“小説”意有所指——不通“至道”的學説即爲“小説”。其與“大達”對舉,價值判斷的意涵非常明顯,“大達”既爲“至道”,“小説”便成“小道”。《論語》云:“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正義曰: 此章勉人學,爲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説,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9)何晏等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531頁。可見在儒家看來,“小道”亦指與己意不合的“異端之説”“百家語”,雖肯定其“必有小理可觀覽”,但也不諱言“君子不學”。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小説”幾乎成爲不本儒家經典學説的代名詞。《漢書·宣元六王傳》載,東平王劉宇上疏求皇帝賜予諸子書,大將軍王鳳認爲不可,奏稱:“《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10)班固撰,顔師古注《前漢書》卷八十,武英殿本。王鳳雖未明言“小説”,但他所言“小道”“小辯”與《五經》相對,正泛指包括“小説”在内的諸子學説。後漢徐幹《中論》提出,人君之大患莫過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所謂“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便包括“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説之文”(11)徐幹《中論·務本第十五》,《四部叢刊》本。。徐幹所言“小説”,即指遠離治國大略的街談巷語、道聽塗説。晉郭璞認爲《爾雅》“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12)郭璞《爾雅·序》,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頁。,於是“綴集異聞,會稡舊説,考方國之語,采謡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群言”(13)同上,第5頁。。邢昺疏云:“群言,謂子史及小説也,言非但援引六經,亦博通此子史等以爲注説也。”(14)邢昺《爾雅疏》卷一,《四部叢刊續編》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409頁。邢昺所言“小説”,同樣與“六經”相對,指“異聞”“舊説”及“方國之語”“謡俗之志”之類。以“小説家”稱引文獻類目,並非班固首創,至少桓譚已著先鞭;且班固對“小説家”的界説,幾乎未脱桓譚窠臼,故要明確《漢志》“小説家”的内涵,先要瞭解桓譚對“小説家”的認識。桓譚《新論》云:“若其小説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15)桓譚著,吴則虞輯校《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除了從理論上總結“小説家”的形式與價值,桓譚還以實例爲證,進一步明確了“小説家”的内涵:“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維絶,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虚誕,故當采其善,何云盡棄耶?”(16)同上。吴則虞認爲,桓譚這兩條論述文氣似相連接,疑出自一篇。此説頗有見地,且前後連讀,桓譚所言“小説家”便有了實指對象,即莊周寓言與《淮南子》中的神話故事之類。桓譚認爲,《莊子》中“堯問孔子”之類寓言與《淮南子》中“共工争帝”之類神話皆不本經傳,乃虚誕妄作,故皆屬短書,即小説也。然此類文獻亦有可觀之處,不可盡棄。桓譚對“小説家”的理解,乃其學術立場使然。《後漢書·桓譚傳》言桓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17)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75頁。。世祖時,桓譚官拜議郎給事中,上疏力陳時政,其學術立場於此可見一斑: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虚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李賢注: 伎,謂方技醫方之人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李賢注: 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説,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18)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76頁。
不難發現,桓譚固守儒家學説,以尊經明道爲要務,諫言皇上遠離黄白之術與讖緯之説。所言“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即方士與史卜之官,是“小説家”的主要來源;所言“群小之曲説”“雷同之俗語”,指“奇怪虚誕之事”,是“小説家”的主要内容。桓譚要求皇上遠離的,正是儒家强調的“君子不學”的“小道”,此一觀念,又是漢人對“小説家”的普遍認識。桓譚與揚雄過從甚密,服膺揚雄,曾言:“通才著書以百數,唯太史公爲廣大,餘皆藂殘小論,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19)桓譚著,吴則虞輯校《新論》,第79頁。其持論以五經爲本,視他説爲“藂殘小論”的立場,與揚雄幾乎一致。揚雄《法言》云:“或問: 五經有辯乎?曰: 唯五經爲辯。説天者莫辯乎《易》,説事者莫辯乎《書》,説體者莫辯乎《禮》,説志者莫辯乎《詩》,説理者莫辯乎《春秋》。舍斯辯亦小矣。”宋咸注曰:“舍五經皆小説也。”(20)揚雄撰《法言·寡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頁。所謂“藂殘小論”即“叢殘小語”,指不本經傳的“街談巷語”與“道聼塗説”,價值低下,時人視爲“短書”。王充《論衡·書解》云:“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之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 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論衡·謝短》又云:“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21)王充著,陳浦青點校《論衡》,嶽麓書社2006年版,第363~364頁、164頁。王充以“蕞殘”“短書”指代“小説”,並非指小説書籍的形制短小,而是指此類文獻内容穿鑿失經,有違聖教。荀悦云“又有小説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22)荀悦《漢紀》,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37頁。,則稱得上是對桓譚、班固的附議。作爲一種學説或觀點,“小説”是形而上、抽象的;作爲學説或觀點的表達,“小説”又是形而下、具體的,呈現爲某種獨特的載體。周秦時期,“小説”一詞主要指不合己意的學説或觀點,立場不同,對象便各異;到了兩漢時期,“小説”一詞已有明確的指稱對象,指那些不本經典、價值低下、品格卑微的書籍篇目,“小説”至此已成一個文類概念。
二、 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的小説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小説家著録了十五家小説:
《伊尹説》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依託也。)
《鬻子説》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因以託之。)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黄帝説》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説》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師古曰: 劉向《别録》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 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黄車使者。應劭曰: 其説以《周書》爲本。師古曰: 《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説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説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據書後班固注釋可知,自《伊尹説》至《黄帝説》等九家爲周秦時書,自《封禪方説》至《百家》等六家爲漢代時書。這十五家小説全本早已亡失,但經過歷代學者的努力,除《周考》《務成子》《宋子》外,其他十二家小説已有輯佚的傳世文獻可供參考。近年來又發掘了不少出土文獻,其中部分簡牘文本完全符合《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規定的特徵。藉此我們可以管中窺豹,大致還原《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的本真面目。以下按照先傳世文獻後出土文獻的順序,分别舉例言之。
《伊尹説》二十七篇。伊尹爲商湯賢相,周秦典籍多有提及“伊尹相湯”事,如“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顔淵》),“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墨子·尚賢上》),“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莊子·庚桑楚》),“湯問伊尹曰”(《逸周書·王會解》),“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晏子春秋》),“伊尹説湯是也”(《韓非子·難言》)。《吕氏春秋·本味》詳細記載了“伊尹以至味説湯”一事,一般認爲即《伊尹説》佚文(23)詳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説湯”條、梁玉繩《吕子校補》卷一“本味”、袁行霈《漢書藝文志考辨》等。。原文如下:
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
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知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歡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黄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説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禦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咸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 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 洞庭之鱄,東海之鮞。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 昆侖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余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 陽檏之薑,招摇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 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 三危之露;昆侖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 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人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24)吕不韋著,陳其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44~746頁。
《鬻子説》十九篇。鬻子名熊,“鬻”亦作“粥”,二字古通。芈姓。《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亦著録《鬻子》二十二篇。今人認爲唐逄行珪注本《鬻子》乃“小説家”《鬻子説》的殘篇(25)詳見鍾肇鵬《〈鬻子〉考》,載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頁。又見鍾肇鵬《鬻子校理·前言》。。試舉兩例:
政曰: 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臣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
政曰: 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26)鍾肇鵬《鬻子校理·撰吏》,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頁。
《青史子》五十七篇。青史子未知何人,史無可考。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佚本《青史子》一卷。賈誼《新書·胎教》與《大戴禮記·保傅》均引“青史氏之記”,一般認爲此即《青史子》佚文。《新書》卷十《胎教》:
青史氏之記曰: 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隱之道也。(27)賈誼撰,盧文昭校《新書》,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06頁。
《大戴禮記》卷三《保傅》前亦引“古者胎教之道”,只是較《新書》甚爲簡略;後引“巾車教之道”則爲《新書》所無:
青史氏之記曰: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此所以養恩之道。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環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28)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9~62頁。
《師曠》六篇。師曠事,廣見於《逸周書》《左傳》《吕氏春秋》《韓非子》《汲冢瑣語》,以及《史記》《新序》《説苑》等周秦兩漢間典籍,故其書雖亡,而殘編尚夥。《逸周書·師曠見太子晉》,一般認爲即《師曠》佚文:
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其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
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
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
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
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如周,行不知勞。”
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悦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咫。”
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
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與不好取,必度其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反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謂義。”
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異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
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爲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
師曠罄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於初,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能?”
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
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
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
師曠曰:“天寒足跔,是以數也。”
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
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
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絶境越國,弗愁道遠。”
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木當時而不伐,夫何可得?且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
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
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
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29)盧文暉輯注《師曠——古小説輯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頁。
《天乙》三篇。天乙即商湯,《史記集解》引譙周語曰:“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30)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3頁。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認爲《新書·修正語》與《史記·殷本紀》等所引“湯曰”均出自《天乙》。今舉《新書·修正語》爲例:
湯曰: 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静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淩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也。
湯曰: 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虚成也,顯榮不可以虚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也。(31)賈誼撰,盧文昭校《新書》,第98頁。
《黄帝説》四十篇。《風俗通義》卷六、卷八各引《黄帝書》,一般認爲此即《黄帝説》。《文史通義》卷六《聲音》“瑟”條曰:
謹按: 《世本》:“宓羲作瑟,長八尺一寸,四十五弦。”《黄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32)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5~286頁。
卷八《祀典》“桃梗 葦茭 畫虎”條曰:
謹按: 《黄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郁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閲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33)同上,第367頁。
《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朱右曾以爲《逸周書》中“羿射十日”等四條記載或出自《虞初周説》,姑録如下:
日本有十,迭次而出,運照無窮。堯時爲妖,十日並出,故爲羿所射死。
岕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神經光之所司也。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
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34)朱右曾云:“《文選》注十四卷。案穆王之書並無闕逸,且其文亦不類本書,李善引此。古文《周書》下,又引《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跱衡,馬驚觸虎’云云,則亦非出於《汲冢瑣語》也。考《藝文志·小説家》有《虞初》九百四十篇,應劭曰‘其言以《周書》爲本’,然則此文(指‘穆王田’條)及上三條出於《虞初》乎?網羅散佚,寧過而存之。”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77~178頁。
《百家》百三十九卷。《風俗通義》“門户鋪首”與“城門失火,殃及池中魚”條均引《百家書》。又《史記·五帝本紀》云“太史公曰《百家》言黄帝”,《甘茂傳》云“學《百家》之説”,《范雎傳》云“《百家》之説,吾亦知之”,王利器認爲應劭所言《百家書》與太史公所言《百家》皆指《漢書·藝文志》“小説家”之《百家》(35)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第578頁。。今以《風俗通義》所引《百家書》爲例:
門户鋪首。謹案: 《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上,見蠡,謂之曰:‘開汝匣,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户,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户,欲使閉藏當如此周密也。”(36)同上,第577頁。
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俗説: 司門尉姓池,名魚,城門火,救之,燒死,故云然耳。謹案: 《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見,但就取之,喻惡之滋,並中傷良謹也。”(37)同上,第608頁。
除了傳世文獻,出土文獻中也有不少篇目可歸入小説家類。我們從放馬灘竹簡、上海博物館藏竹簡、北京大學藏竹簡與清華大學藏竹簡中選取了若干篇目進行分析,以期與傳世文獻中的小説相互印證。需要説明的是,我們對出土文獻中小説文本的認定,完全基於《漢書·藝文志》對小説的界定以及前人對小説的認知,即以儒家學説爲鏡鑒,凡來源爲“依託”或“後世所加”,内容“淺薄”“迂誕”,不本經典、價值低下、品格卑微的篇目則視爲小説。
《志怪故事》。1986年,甘肅省天水市放馬灘一處戰國晚期秦人墓葬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簡360—366號記載了一個叫“丹”的人死而復生的故事: 丹因傷人而棄市,屍體葬於垣雍。三年後丹死而復生,爲世人講述了死者的種種忌諱。整理者原定名爲《墓主記》,後改爲《志怪故事》。釋文如下: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謁御史: 大梁人王里樊野曰: 丹報: 今七年,丹刺傷人垣雍里中,因自刺殹,棄之於市,三日,葬之垣雍南門外。三年,丹而復生。丹所以得復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論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當死,因告司命史公孫强,因令白狐穴掘出丹,立墓上三日,因與司命史公孫强北之趙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聞犬吠雞鳴而人食,其狀類益處、少麋、墨,四支不用。丹言曰: 死者不欲多衣。死人以白茅爲富,其鬼薦於它而富。丹言: 祠墓者毋敢哭。哭,鬼去驚走。已收腏而厘之,如此鬼終身不食殹。丹言: 祠者必謹掃除。毋以淘灑祠所。毋以羹沃腏上,鬼弗食殹。(38)甘肅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編《天水放馬灘秦簡》,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07頁。簡文由何雙全整理,本釋文參方勇、侯娜《讀天水放馬灘秦簡〈志怪故事〉札記》,《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3期。爲行文方便,釋文用通行字,通假字直接讀破,以簡體録入。下同。
《泰原有死者》。與放馬灘竹簡《志怪故事》類似的是,北京大學藏秦牘中亦記載了一個人死而復生的故事,整理者定名爲《泰原有死者》,釋文如下:
泰原有死者,三歲而復産,獻之咸陽,言曰:“死人之所惡,解予死人衣。必令産見之,弗産見,鬼輒奪而入之少内。死人所貴黄圈。黄圈以當金,黍粟以當錢,白菅以當。女子死三歲而復嫁,後有死者,勿並其塚。祭死人之塚,勿哭。須其已食乃哭之,不須其已食而哭之,鬼輒奪而入之廚。祠,毋以酒與羹沃祭,而沃祭前,收死人,勿束縛。毋決其履,毋毁其器。令如其産之臥殹,令其魄不得落思。黄圈者,大菽殹。剺去其皮,置於土中,以爲黄金之勉。”(39)李零《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簡介》,《文物》2012年第6期。
《彭祖》。上海博物館藏楚竹簡,簡文假託耇老與彭祖討論天道與人倫、休咎與禍福等問題。整理者認爲其乃最早的彭祖書,定名爲《彭祖》,釋文如下:
耇老問於彭祖曰:“耇氏執心不妄,受命永長。臣何藝何行,而舉於朕身,而毖於帝常?”彭祖曰:“休哉,乃將多問因由,乃不失度。彼天之道,唯亟□□□不知所終。”耇勞曰:“眇眇余沖子,未則於天,敢問爲人?”彭祖(曰):“□□□。”(耇老曰):“既榰於天,又潛於淵,夫子之德,盛矣何其。宗寡君之願,良□□□。”
(彭祖曰):“□□□言。天地與人,若經與緯,若表與裏。”問:“三去其二,幾若已?”彭祖曰:“籲,汝孳孳博問,余告汝人倫,曰: 戒之毋驕,慎終保勞。大往之衍,難以遷延。余告汝□,(曰): □□□之謀不可行,怵惕之心不可長。遠慮用素,心白身懌。余告汝咎,(曰): □□□,父子兄弟,五紀畢周,雖貧必修;五紀不彝,雖富必失。余告汝禍,(曰): □□□,□者不以,多務者多憂,惻者自賊也。”
彭祖曰:“一命二俯,是謂益愈。二命三俯,是謂自厚。三命四俯,是謂百姓之主。一命二仰,是謂遭殃。二命(三仰),(是)謂不長。三命四仰,是謂絶世。毋逐富,毋倚賢,毋易樹。”
耇老三拜稽首曰:“沖子不敏,既得聞道,恐弗能守。”(40)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8頁。簡文由李零整理,本釋文參周鳳五《上博楚竹書〈彭祖〉重探》,《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81頁。
《殷高宗問於三壽》。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末簡簡背有篇題“殷高宗問於三壽”。簡文假託殷高宗武丁與三壽(少壽、中壽與彭祖,主要是彭祖)對話,以此論述作者的思想觀念。釋文如下:
高宗觀於洹水之上,三壽與從。
高宗乃問於少壽曰:“爾是先生,爾是知二有國之情,敢問人何謂長?何謂險?何謂厭?何謂惡?”少壽答曰:“吾□□□”(高宗乃問於)中壽曰:“敢問人何謂長?何謂險?何謂厭?何謂惡?”中壽答曰:“吾聞夫長莫長於風,吾聞夫險莫險於心,厭必臧,惡必喪。”
高宗乃又問於彭祖曰:“高文成祖,敢問人何謂長?何謂險?何謂厭?何謂惡?”彭祖答曰:“吾聞夫長莫長於水,吾聞夫險莫險於鬼,厭必平,惡必傾。”
高宗乃言曰:“吾聞夫長莫長於□,吾聞夫險必矛及干,厭必富,惡必無食。苟我與爾相念相謀,世世至於後嗣。我思天風,既回或止。吾勉自抑畏以敬,夫兹□。”(彭祖乃言曰):“君子而不讀書占,則若小人之聾狂而不友,殷邦之妖祥並起。八紀則紊,四岩將行,四海之夷則作,九牧九有將喪。惶惶先反,大路用見兵。龜筮孚忒,五寶變色,而星月亂行。”
高宗恐懼,乃復語彭祖曰:“嗚呼,彭祖!古民人迷亂,象茂康懋,而不知邦之將喪。敢問先王之遺訓,何謂祥?何謂義?何謂德?何謂音?何謂仁?何謂聖?何謂智?何謂利?何謂信?”彭祖答曰:“聞天之常,祗神之明,上昭順穆而警民之行。余享獻攻,括還妖祥,是名曰祥。邇則文之化,曆象天時,往宅毋徙,申禮勸規,輔民之化,民勸毋疲,是名曰義。揆中水衡,不力,時刑罰赦,振若除慝,冒神之福,同民之力,是名曰德。惠民由任,徇句遏淫,宣儀和樂,非壞於湛,四方勸教,濫媚莫感,是名曰音。衣服端而好信,孝慈而哀鰥,恤遠而謀親,喜神而憂人,是名曰仁。恭神以敬,和民用正,留邦偃兵,四方達寧,元哲並進,饞謡則屏,是名曰聖。昔勤不居,浹祗不易,供皇思修,納諫受訾,神民莫責,是名曰智。内基而外比,上下毋攘,左右毋比,强並糾出,經緯順齊,妒怨毋作,而天目毋眯,是名曰利。觀覺聰明,音色柔巧而叡武不罔,效純宣猷,牧民而禦王,天下甄稱,以誥四方,是名曰叡信之行。”彭祖曰:“嗚呼!我寅晨降在九宅,診夏之歸商,方般於路,用孽昭後成湯,代桀敷佑下方。”
高宗又問於彭祖曰:“高文成祖,敢問胥民胡曰揚?揚則悍佚無常。胡曰晦?晦則□□□虐淫自憙而不數,感高文富而昏忘訽,急利囂神莫恭而不顧於後,神民並尤而仇怨所聚,天罰是加,用凶以見訽。”(彭祖)曰:“嗚呼!若是。”(高宗曰):“民之有晦,晦而本由生光,則唯小心翼翼,顧復勉祗,聞教訓,余敬養,恭神勞民,揆中而象常。束簡和睦,補缺而救枉,天顧復之用休,雖陰又明。”(彭祖)曰:“嗚呼!若是。”(41)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149~161頁。
《赤鵠之集湯之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内容爲與伊尹相關的一個故事: 湯射獲一隻赤鵠,令小臣伊尹烹做羹湯。湯後妻紝巟與伊尹偷嘗羹湯,被湯發現,伊尹逃亡至夏。湯震怒,施咒於伊尹。後伊尹得巫烏之助,治癒夏后之疾。末簡簡背下端有篇題“赤鵠之集湯之屋”。釋文如下:
曰古有赤鵠,集於湯之屋,湯射之獲之,乃命小臣曰:“旨羹之,我其享之。”湯往□。小臣既羹之,湯后妻紝巟謂小臣曰:“嘗我於爾羹。”小臣弗敢嘗,曰:“后其殺我。”紝巟謂小臣曰:“爾不我嘗,吾不亦殺爾?”小臣自堂下授紝巟羹。紝巟受小臣而嘗之,乃昭然,四荒之外,無不見也;小臣受其餘而嘗之,亦昭然,四海之外,無不見也。湯返廷,小臣饋。湯怒曰:“孰調吾羹?”小臣懼,乃逃於夏。湯乃□之,小臣乃眛而寢於路,視而不能言。衆烏將食之。巫烏曰:“是小臣也,不可食也。夏后有疾,將撫楚,於食其祭。”衆烏乃訊巫烏曰:“夏后之疾如何?”巫烏乃言曰:“帝命二黄蛇與二白兔居后之寢室之棟,其下舍后疾,是使后疾疾而不知人。帝命后土爲二陵屯,共居后之床下,其上刺后之體,是使后之身屙蠚,不可及於席。”衆烏乃往。巫烏乃歝小臣之喉胃,小臣乃起而行,至於夏后。夏后曰:“爾唯誰?”小臣曰:“我天巫。”夏后乃訊小臣曰:“如爾天巫,而知朕疾?”小臣曰:“我知之。”夏后曰:“朕疾如何?”小臣曰:“帝命二黄蛇與二白兔,居后之寢室之棟,其下舍后疾,是使后棼棼眩眩而不知人。帝命后土爲二陵屯,共居后之床下,其上刺后之身,是使后昏亂甘心。后如撤屋,殺黄蛇與白兔,必發地斬陵,后之疾其瘳。”夏后乃從小臣之言,撤屋,殺二黄蛇與一白兔;乃發地,有二陵屯,乃斬之。其一白兔不得,是始爲陴丁諸屋,以禦白兔。(42)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第166~170頁。
《湯處於唐丘》。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簡文記載湯得小臣(伊尹)的故事以及湯問小臣有關謀夏、爲君之道等方面的對話。本篇與下文《湯在啻門》的形制、字迹相同,内容相關,當爲同一抄手所書。釋文如下:
湯處於唐丘,取妻於有莘。有莘媵以小臣,小臣善爲食,烹之和。有莘之女食之,絶芳旨以粹,身體痊平,九竅發明,以道心嗌,舒快以恒。湯亦食之,曰:“允!此可以和民乎?”小臣答曰:“可。”乃與小臣基謀夏邦,未成,小臣有疾,三月不出。湯反復見小臣,歸必夜。方唯聞之乃箴:“君天王,是有台僕。今小臣有疾,如使召,少閒於疾,朝而訊之,不猶受君賜?今君往不以時,歸必夜,適逢道路之祟,民人聞之其謂吾君何?”湯曰:“善哉!子之云。先人有言: 能其事而得其食,是名曰昌。未能其事而得其食,是名曰喪。必使事與食相當。今小臣能展彰百義,以和利萬民,以修四時之政,以設九事之人,以長奉社稷,吾此是爲見之。如我弗見,夫人毋以我爲怠於其事乎?我怠於其事,而不知喪,吾何君是爲?”方唯曰:“善哉!君天王之言也。雖臣死而又生,此言弗又可得而聞也。”湯曰:“善哉!子之云也。雖余孤之與上下交,豈敢以貪舉?如幸余閒於天威,朕唯逆順是圖。”
湯又問於小臣:“有夏之德何若哉?”小臣答:“有夏之德,使過以惑,春秋改則,民人趣忒,刑無攸赦,民人皆瞀偶離,夏王不得其圖。”
湯又問於小臣:“吾戡夏如台?”小臣答:“後固恭天威,敬祀,淑慈我民,若自事朕身也。桀之疾,後將君有夏哉!”
湯又問於小臣:“古之先聖人,何以自愛?”小臣答:“古之先聖人所以自愛,不事問,不處疑;食時不嗜饕,五味皆,不有所;不服過文,器不雕鏤;不虐殺;與民分利,此以自愛也。”
湯又問於小臣:“爲君奚若?爲臣奚若?”小臣答:“爲君愛民,爲臣恭命。”
湯又問於小臣:“愛民如台?”小臣答曰:“遠有所亟,勞有所思,饑有所食,深淵是濟,高山是逾,遠民皆極,是非愛民乎?”
湯又問於小臣:“恭命如台?”小臣答:“君既濬明,既受君命,退不顧死生,是非恭命乎!”(43)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第134~140頁。
《湯在啻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簡文記載湯問小臣伊尹古先帝之良言,伊尹答以成人、成邦、成地、成天之道,由近及遠,由小及大,比較系統地闡述了當時的天人觀。釋文如下:
正月己亥,湯在啻門,問於小臣:“古之先帝亦有良言情至於今乎?”小臣答曰:“有哉!如無有良言情至於今,則何以成人?何以成邦?何以成地?何以成天?”
湯又問於小臣曰:“幾言成人?幾言成邦?幾言成地?幾言成天?”小臣答曰:“五以成人,德以光之;四以成邦,五以相之;九以成地,五以將之;九以成天,六以行之。”
湯又問於小臣曰:“人何得以生?何多以長?孰少而老?固猶是人,而一惡一好?”小臣答曰:“唯彼五味之氣,是哉以爲人。其未氣,是謂玉種,一月始揚,二月乃裹,三月乃形,四月乃固,五月或褎,六月生肉,七月乃肌,八月乃正,九月顯章,十月乃成,民乃時生。其氣朁歜發治,是其爲長且好哉。其氣奮昌,是其爲當壯。氣融交以備,是其爲力。氣促乃老,氣徐乃猷,氣逆亂以方,是其爲疾殃。氣屈乃終,百志皆窮。”
湯又問於小臣:“夫四以成邦,五以相之,何也?”小臣答曰:“唯彼四神,是謂四正,五以相之,德、事、役、政、刑。”
湯又問於小臣:“美德奚若?惡德奚若?美事奚若?惡事奚若?美役奚若?惡役奚若?美政奚若?惡政奚若?美刑奚若?惡刑奚若?”小臣答:“德濬明執信以義成,此謂美德,可以保成;德變亟執譌以亡成,此謂惡德,雖成又瀆。起事有獲,民長賴之,此謂美事;起事無獲,病民無故,此謂惡事。起役時順,民備不庸,此謂美役;起役不時,大費於邦,此謂惡役。政簡以成,此謂美政;政禍亂以無常,民咸解體自恤,此謂惡政。刑輕以不方,此謂美刑;刑重以無常,此謂惡刑。”
湯又問於小臣:“九以成地,五以將之,何也?”小臣答曰:“唯彼九神,是謂地真,五以將之,水、火、金、木、土,以成五曲,以植五穀。”
湯又問於小臣:“夫九以成天,六以行之,何也?”小臣答曰:“唯彼九神,是爲九宏,六以行之,晝、夜、春、夏、秋、冬,各司不解,此唯事首,亦唯天道。”
湯曰:“天尹,唯古之先帝之良言,則何以改之。”(44)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第141~148頁。
《融師有成氏》。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内容爲上古傳説人物祝融之師有成氏,涉及蚩尤、伊尹等人。簡文以較大篇幅描述了有成氏的形狀。由於是殘簡,有成氏的形狀剛剛講完,蚩尤、伊尹等人的事迹亦僅有開頭,不見下文。整理者定名爲《融師有成氏》,釋文如下:
融師有成,是狀若狌,有耳不聞,有口不鳴,有目不見,有足不趨,名則可畏,實則可侮。我曰虘茖乎,□□猷;我曰虘喬乎,弗飲弗食。物斯可惑,類獸非鼠,察後伺側。蔑師見螭,毁折戮殘,唯兹作彰,象彼獸鼠;有足而縛,有手而梏,沈跪念唯,發揚騰?楎?。昔融之氏師,訮尋夏邦,蚩尤作兵,囗聞適湯。顔色深晦,而志行顯明。不及遇焚,而正固(下缺)(4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329頁。簡文由曹錦炎整理。本釋文參禤健聰《戰國竹書〈融師有成〉校釋》,《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第88頁。
上述七篇出土文獻中,《志怪故事》《太原有死者》與《赤鵠之集湯之屋》側重於叙事,《彭祖》《殷高宗問於三壽》《湯處於唐丘》與《湯在啻門》偏重於論説,《融師有成氏》爲殘篇,據現有文字判斷,叙事、論説皆有可能。誠如余嘉錫所言,論説者“託之古人,以自尊其道”,叙事者“造爲古事,以自飾其非”;其所表達的思想學説,也恰如吕思勉所言屬民間思想,乃習世故的平民所爲,以儒家學説爲參照,同樣應當歸入“淺薄”“迂誕”之列。
三、 “小説”的文類屬性與文體特徵
以上臚列了傳世文獻中《伊尹説》《鬻子説》《師曠》等八家小説,以及出土文獻中《太原有死者》《志怪故事》《赤鵠之集湯之屋》等七家小説。按照《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命名立意,再順着《伊尹説》《鬻子説》《黄帝説》之類的命篇思路,我們擬從三個方面入手分析《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文類屬性與文體特徵: 誰在説——考察小説的來源;説什麽——考察小説的内涵;怎麽説——考察小説的形式。
首先考察小説的來源。班固認爲前九家周秦小説來歷不明,多爲“依託”。九家小説中,班固注明“依託”者有《伊尹説》《天乙》《黄帝説》三家;未注明“依託”,但實際是“依託”者有《鬻子説》《師曠》《務成子》三家,前者注明“後世所加”,後二者注明“非古語”,意即此三家小説皆後人所撰而依託古人(46)《漢書·藝文志》“兵書略”中注明“依託”者還有“兵陰陽”之《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等。。何謂依託?余嘉錫從學術發生與傳承的角度作了解釋:
況周、秦、西漢之書,其先多口耳相傳,至後世始著竹帛。如公羊、榖梁之《春秋傳》、伏生之《尚書大傳》。故有名爲某家之學,而其書並非某人自著者。唯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託。如《藝文志·文子》九篇,注爲依託,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時代不合,必不出於文子也。(47)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管子》,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08頁。
余嘉錫指出,後人著書立説,或“託之古人,以自尊其道”,或“造爲古事,以自飾其非”,至“方士説鬼,文士好奇,無所用心,聊以快意,乃虚構異聞,造爲小説”(48)余嘉錫《古書通例》,第253~263頁。,便有了《伊尹説》《黄帝説》之類小説。爲何依託?梁啓超從古書辨僞的角度進行分析:
研究漢志之主要工作,在考證各書真僞。……雖然,本志自身,其所收僞書正自不少,其故,一由戰國百家,托古自重,(例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炎黄伊吕,動相援附,二由漢求遺書,獎以利禄,獻書路廣,蕪穢亦滋,三由輾轉傳鈔,妄有附益,或因錯糅,汩其本真,四由各家談説,時隱主名,讀者望文,濫爲擬議。以此諸因,訛僞稠疊,辨别綦難。志中本注言“似依托”言“六國時依托”之類,頗不少。(49)梁啓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梁啓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8頁。
由此可知,“依託”既是小説發生的重要動因,又是劉、班等人辨認小説文本的重要依據。又“周秦古書,皆不題撰人。俗本有題者,蓋後人所妄增”(50)余嘉錫《古書通例》,第203頁。,故周秦九家小説題爲《伊尹説》《鬻子説》《黄帝説》等,實皆後人所作而附會於伊尹、鬻子、黄帝等人。以《鬻子》爲例,《意林》卷一引《鬻子》云:“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51)王天海、王韌《意林校釋》(上),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頁。《史記·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52)司馬遷《史記·楚世家》,第5頁。《漢書·地理志下》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53)班固《漢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82頁。據此可知周文王時鬻子年事已高,不久即逝;周成王時鬻子已卒。而《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著録《鬻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云“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54)班固著,顔師古注《漢書·藝文志》,第26頁。,賈誼《新書·修政語下》亦引有鬻子與文王、武王、成王的問對七則,與班固自注相合。則依常理可知,無論是道家《鬻子》還是小説家《鬻子》,皆爲依託,故黄震認爲“此必戰國處士假託之辭”(55)黄震《黄氏日鈔》卷五五“讀諸子”,錢塘施氏傳鈔小山堂本。,嚴可均認爲“蓋康王、昭王後周使臣所録,或鬻子子孫記述先世嘉言爲楚國之令典”(56)嚴可均撰,孫賓點校《嚴可均集》卷五“文類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頁。,四庫館臣認爲“不出熊之手。流傳附益,或構虚詞,故《漢志》别入小説家”(57)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七子部雜家類一《鬻子》。。正因爲周秦九家小説爲依託之作,缺乏可信度,實乃“街談巷語,道聼塗説”之類,故班固定性爲“淺薄”“迂誕”。
後六家漢代小説,班固大多注明何時所作,源自何人。如《封禪方説》《待詔臣饒心術》《虞初周説》皆云“武帝時”,《臣壽周紀》云“宣帝時”;饒爲齊人,壽爲項國人,虞初爲河南人。時年既晚,作者已明,小説真假不成問題。但據作者身份來看,小説内容皆不本經傳。六家小説,除《百家》爲劉向自撰(58)詳見劉向《説苑序奏》。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説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其他作者可歸爲兩類: 方士與待詔臣。虞初爲方士侍郎,《封禪方説》雖未明言何人所作,但既言“方説”,或即方士所説,當亦方士所爲。沈欽韓云:“此方士所本,史遷所云‘其文不雅馴’。”(59)轉引自張舜徽《廣校讎略·漢書藝文志通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頁。楊樹達云:“方説者,《史記·封禪書》記李少君以祠社、穀道、卻老方見上;亳人謬忌奏祠太乙方,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膠東宫人樂大求見言方之類是也。”(60)楊樹達《漢書管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頁。饒與安成爲待詔臣,“臣壽”位次“待詔臣饒”“待詔臣安成”之後,或爲承前省所致,亦可作“待詔臣壽”(61)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之下諸子略小説家曰:“案此次待詔臣饒、臣安成之後,或蒙上省文,亦官待詔者,當時皆奏進於朝,故稱臣饒、臣安成、臣壽。”。方士本指自稱能尋訪仙丹以長生不老之士,後泛指從事醫、卜、星、相等職業者。漢代以才技徵召士人,使隨時聽候皇帝詔令,謂之待詔。《漢書·哀帝紀》云:“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應劭曰: 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62)班固撰,顔師古注《前漢書·哀帝紀》,武英殿本。漢代自武帝迷信神仙方術,方士大行其道,多有待詔乃至身居高位者。《後漢書·方術列傳》云:“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届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争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内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奸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63)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第1021頁。所謂“懷協道藝之士”即方士,如王梁、孫咸、鄭興、賈逵諸輩。又《漢書·郊祀志》記載,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議精簡祠置,“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 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64)班固撰,顔師古注《前漢書·郊祀志》,武英殿本。故《漢書·藝文志》“小説家”中,方士與待詔名雖有異,實則相同,方士即待詔,待詔即方士。换言之,漢代六家小説,除《百家》外,皆出方士之手。方士爲干謁人主而“奸妄不經”,迂誕怪異之詞充斥其間。王瑶先生説:“他們爲了想得到帝王貴族們的信心,爲了干禄,自然就會不擇手段地誇大自己方術的效益和價值。這些人是有較高知識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對地增高;於是利用了那些知識,借着時間空間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傳説,援引荒漠之世,稱道絶域之外,以吉凶休咎來感召人;而且把這些來依托古人的名字寫下來,算是獲得的奇書秘笈,這便是所謂小説家言。”(65)王瑶《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頁。從這個角度來看,出自方士的六家漢代小説與出於依託的九家周秦小説性質一樣,皆“淺薄”“迂誕”,不本經傳。
接着考察小説的内容。傳世文獻中的小説,《吕氏春秋》所引《伊尹以至味説湯》與《逸周書》所引《師曠見太子晉》兩篇篇幅較爲長大,結構也頗爲完整,當能較好地體現《伊尹説》與《師曠説》的原貌,故本文稍加詳叙;出土文獻中的小説,我們將重點分析放馬灘秦簡《太原有死者》與北京大學藏秦牘《志怪故事》。
《伊尹以至味説湯》開篇闡述了一個道理: 賢主要想建立功名,必須得到賢人的幫助;而要想讓賢人盡忠職守,賢主必須待賢人以禮。爲了讓説理更加形象生動,説者以“湯得伊尹”這個故事爲例説明賢主與賢人之間的傾慕;以“伯牙與子期”的故事爲例説明賢主與賢人之間的契合。表述這層意思之後,説者開始闡述另外一個道理: 要想成就偉業,賢主必須成爲天子。爲了説明這個道理,説者借賢人伊尹之口以“至味”之道爲例,鋪陳天下至美之物,如肉之美者、魚之美者、菜之美者、飯之美者、和之美者、果之美者、馬之美者等,闡明只有成爲天子,方才具備享受天下至味的條件。篇末再次闡述道理: 要想成爲天子,必須修成“聖人之道”。在這篇文獻中,闡述道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全篇的靈魂;叙述故事乃爲闡述道理服務,是全篇的血脉;伊尹爲“至味”鋪陳的名物長單,則是全篇的肌肉。《師曠見太子晉》全文設置了一個簡單的故事框架: 叔譽在與太子晉的論辯中落荒而逃,建議晉平公臣服於周,歸還聲就及與田兩地;師曠不信邪,決定親自去見太子晉一決高下。師曠與太子晉你來我往,坐而論道。兩人一見面便唇槍舌劍,長達五個回合的辯難之後方才落座。(“師曠……稱曰”與“王子應之曰”凡五見)入座之後,兩人又注瑟放歌,仍然暗藏機鋒,之後師曠開始服軟,主動告退。告退之前師曠投石問路,想探尋太子晉是否有光復周王朝的野心,卻得到了太子晉明確的否認。篇末話鋒一轉,以師曠給太子晉卜命而結束全篇,頗具戲劇性。不難看出,“師曠見太子晉”這個故事本身不是全文的中心,兩人之間的論難才是全文的重點,説者借叙述故事以闡述道理的思路清晰可辨。傳世文獻中,寓理於事的小説還有《百家》。“門户鋪首”條叙述的是公輸班因見蠡之伸縮頭頸而發明門户鎖扣的故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條叙述的是宋國因汲水救火而使池水乾涸,導致池中魚亡的故事。但兩者的最終目的是説理,前者闡述“閉藏周密”的道理,後者表明邪惡可能傷及無辜。這幾篇小説具備一定的共同性,即在故事的包裹下表達説者的觀點。爲了生動形象地闡述觀點,説者無一例外地藉助於叙述故事的手段,在娓娓道來的叙事中讓觀點自然呈現。
同樣是闡述道理,也有不藉助於故事而直接陳述的,《鬻子》兩則“政曰”,引用古代政典説明選舉官吏的道理。前者説民衆是衡量賢或不肖的尺度,賢人能得到百姓擁戴,不肖者則被廢除;後者説民衆的地位是最低下的,但民衆可以用作選擇衡量官吏的標準,即官吏必須受民衆喜愛。《天乙》兩則“湯曰”也是如此。前者闡述了明君與君子貴“學道”而賤“獨思”、明君“慎其舉”與君子“慎其與”的道理;後者闡述了君主應廣開言路,用心求道、取道、致道、入道、積道、樹道的道理。兩則文獻都没有藉助於故事,而是直截了當地闡述説者的主張。
除了爲闡述道理而叙述故事之外,也有爲考辨名物制度而作的叙事。《風俗通義》卷六所引《黄帝書》,叙述的是泰帝因見素女鼓瑟而悲,故改變了瑟的弦數的故事。卷八所引《黄帝書》,叙述的是門神荼與鬱壘的來歷。《新書·胎教》與《大戴禮記·保傅》所引“青史氏之記”,記叙古代的幾種禮儀: 胎教之道、養隱之道和巾車教之道。胎教之道,重點在於諸官各司其職,叙事非常詳細;養隱之道,重點在於懸弧之禮,名物非常瑣細;巾車教之道,重點在於養成教育,鋪叙相當完備。《逸周書》所引《虞初周説》“羿射十日”“岕山”“天狗”“穆王田”四條,全爲遠古神話故事。這幾篇小説中的叙事,目的不在於闡明何種道理,而在於解釋某些事物的由來,考證考辨名物制度的真相。
以上是傳世文獻中的小説。接下來再看出土文獻中的小説。
《志怪故事》與《泰原有死者》記載的是人死而復生的故事,反映了周秦時期的宗教信仰與方術習俗。《志怪故事》中的“司命史”“白狐”“白茅”與《泰原有死者》中的“黄圈”“黍粟”“白菅”等名物以及死人的好惡與祠墓者的禁忌等行爲,體現了周秦時期的喪葬制度。司命是掌管人的生死壽命的神祗,《莊子·至樂》篇中莊周問骷髏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66)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19頁。可見司命具有使人死而復生的能力。《志怪故事》中的司命史公孫强不是神祗,應當是一個欲自神其説而依託爲司命的人,他熟知方術神迹或自稱有通靈的本領,乃巫師或方士之流。白狐是古代靈獸,也是祥瑞之兆。《穆天子傳》云:“甲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於河宗。”(67)郭璞注,洪頤煊校《穆天子傳》卷一,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頁。白狐打通洞穴進入墓室,使丹重返人世,寓意着白狐具有溝通冥界與人間的神力。白茅是古代喪葬常見的祭品,周秦祭祀禮制中大量使用白茅獻祭禮神,方士亦將白茅視爲召神降真與驅鬼除邪的法器。《晏子春秋》記載柏常騫替齊景公施展法術時“築新室,爲置白茅”(68)晏嬰《晏子春秋》卷六,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3頁。,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詰”篇亦曰:“人無故室皆傷,是粲迓之鬼處之,取白茅及黄土而灑之,周其室,則去矣。”(69)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頁。黄圈即黄豆芽。東漢靈帝熹平二年(173)張叔敬朱書陶否鎮墓文記載了類似的助葬之物:“上黨人參九枚,欲持代生人;鈆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70)轉引自陳直《漢張叔敬朱書陶瓶與張角黄巾教的關係》,陳直《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頁。説明黄圈可供死人在地府中繳納賦税之用。白菅即白茅,《志怪故事》説“死人以白茅爲富”,説明白茅是財富的象徵。“”即繇,即徭役。《泰原有死者》説“白菅以爲”,是説白菅可以抵充徭役。據此可知,“黄圈”“黍粟”“白菅”等物品,均具有象徵財富的意義,死者擁有這些物品,便可以在冥間過上富足的生活,還可以繳納賦税,抵充徭役(71)參姜守城《放馬灘秦簡〈志怪故事〉中的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姜守城《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考釋》,《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3期。。除了涉及喪葬儀式中的名物,兩篇小説還談及祠墓的行爲規范與禁忌事項。值得關注的是,二者有不少相同之處,除前面提及的死人都以白茅(白菅)作爲財富的象徵外,都忌諱祠墓者在祭祀前哭泣(《志怪故事》“祠墓者毋敢哭”,《泰原有死者》“祭死人之塚,勿哭”),都忌諱祠墓者把湯羹澆灌到祭品上(《志怪故事》“毋以羹沃腏上”,《泰原有死者》“毋以酒與羹沃祭”)。《志怪故事》出土於西北,《泰原有死者》則可能出自南方(72)李零《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簡介》:“種種跡象表明,這批簡牘中的地名多與南方有關。如果這批簡牘真的是從南方出土,則文中死者不一定是隨葬簡牘的墓主。”,不同地域中的復生故事有着如此衆多的巧合,這是否恰好説明此類文獻都出自相同身份、職業的説者——方士或巫祝之手?《文選·西京賦》“小説九百,本自虞初”薛綜注云:“小説,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73)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二《西京賦》,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5頁。這兩個復生故事顯然屬於“醫巫厭祝之術”,是地地道道的小説。
《赤鵠之集湯之屋》没有出現“伊尹”之名,但簡文情節與“伊尹以滋味説湯”“伊尹去湯適夏”等傳説相符,又與《楚辭》“緣鵠飾玉,后帝是饗”(74)《楚辭》:“緣鵠飾玉,後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朱熹注曰:“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此即《孟子》所辨‘割烹要湯’之説,蓋戰國遊士謬妄之言也。”參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頁。的記載吻合,故整理者認爲簡文中的小臣即伊尹。又,本篇與《湯處於唐丘》《湯在啻門》出自同一批簡,都是依託伊尹表達説者的思想學説,或許即《漢書·藝文志》所録《伊尹説》二十七篇之軼文。本文有兩個顯著的特點,體現了小説“街談巷語,道聼塗説”的特徵。一是濃厚的巫術色彩。赤鵠做成的羹能讓紝巟與小臣視通萬里;小臣被湯詛咒之後便昏睡路旁,口不能言;烏巫能知天命,可治療疾病,這些情節同樣屬於“醫巫厭祝之術”,因此簡文開頭“曰”前省略的説者身份當爲巫祝。二是鮮明的民間色彩。商湯貴爲君王,伊尹亦是大臣,但簡文中的湯與小臣完全没有爲君爲臣者應有的格調,充滿着十足的世俗氣,如君王之小氣與暴虐,王后之貪吃與狡黠,小臣之卑微與怯懦,這比較符合民間視野中的君臣形象;小臣悲慘的遭遇與喜劇性的結局,也是民間喜聞樂見的格套。
上博簡《彭祖》與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都是有關彭祖的早期文獻。《彭祖》記耇老與彭祖對話。耇老本泛指長壽之人,並無確指,簡文作爲專名,顯系依託古人。耇老的身份似乎是大臣,奉“寡君”之命向彭祖請教治國方略。彭祖先答以“天道”,耇老以“未則於天”爲由避談天道,而“敢問爲人”,請談人道。彭祖認爲天、地、人三者彼此關聯,互爲經緯,意即天道與人道密不可分。耇老堅持“三去其二”,只談人道。於是彭祖分别“告汝人倫”“告汝□”“告汝咎”“告汝禍”,從人倫、□、休咎、禍福等方面系統闡述了他的人道思想。《殷高宗見於三壽》記殷高宗與三壽的對話。“三壽”本來指三個不同的年齡階段,《莊子·盜蹠》有上壽、中壽與下壽之説。簡文中的“三壽”指三個具體的人物——少壽、中壽與彭祖,顯然又係依託。全篇主要寫殷高宗與彭祖的對話,並通過對話闡述彭祖的思想學説。殷高宗首先就“長”“險”“厭”“惡”四個理念發問少壽與中壽,是爲鋪墊;接着繼續發問彭祖,在得到彭祖的回答之後,殷高宗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彭祖接續殷高宗的話頭,又進一步補充了自己的主張。殷高宗在領會了彭祖的觀點之後,又追問“祥”“義”“德”“音”“仁”“聖”“智”“利”“信”九個理念,彭祖一一予以闡述。最後,殷高宗闡述了自己對“揚”與“晦”兩個理念的理解,並得到了彭祖的認可。值得注意的是,全篇充滿着濃郁的巫術色彩,尤以“君子而不讀書占”一段最爲明顯。《融師有成氏》對有成氏的描述同樣充滿着神話色彩,部分内容與《山海經》的記載非常類似。
最後考察小説的形式。總體而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的分類標準偏重於文獻的思想内涵,形式特徵非其關注的重點。但“説什麽”往往會影響到“怎麽説”的選擇,所以“小説家”的歸類,理應也有其形式特徵的趨同性。梁啓超就主張“小説之所以異於前九家者,不在其涵義之内容,而在其所用文體之形式”(75)梁啓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梁啓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6頁。。他指出,“諸書與别部有連者,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鬻子》二十二篇,此復有《伊尹説》《鬻子説》;兵陰陽有《師曠》八篇,此復有六篇;五行家有《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房中家有《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此復有《務成子》十一篇,考其區别所由,蓋以書之内容體例爲分類也……道家之《伊尹》《鬻子》蓋以莊言發攄理論,小説家之《伊尹説》《鬻子説》,則叢殘小語及譬喻短篇也”(76)同上,第4726~4727頁。。梁啓超此説的確能啓人深思,考察《漢書·藝文志》所録小説的形式,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根據前文可知,《漢書·藝文志》小説家所録小説大致包括説理、叙事、博物三種類型,而《伊尹以至味説湯》三者兼而有之,且篇幅頗爲長大,結構亦相對完整,故下文以此篇爲主,分析小説的形式。
從文體屬性來看,這是一篇論説文。全篇共四段,進行了四層論述。第一層,説者提出賢主建立功名的根本在於得到賢人。第二層,説者首先叙述賢人伊尹的出身以及賢主湯得到伊尹的經過,然後進一步深化前層觀點,强調賢主與賢人之間“相得然後樂”是建立功名的關鍵。第三層,説者進而以伯牙與子期的故事爲例,强調賢人與賢主的關係應當像伯牙與子期,賢主應當禮遇賢人。第四層,説者首先叙述湯在朝禮遇伊尹,接着伊尹爲湯講述天下最美的味道,並乘勢提出,只有做了天子才能享受天下最美的味道;最後更進一步,强調要想成爲天子,必須修成聖人之道。不難發現,四層論述步步爲營,層層遞進,從第一層闡述賢主求得賢人的重要性,到第四層强調天子修成聖人之道的必要性,境界與格調已有很大提升。再從論述的手段來看,説者融説理、叙事與博物於一爐,而將三者統攝成一個整體的方式,便是桓譚所言“近取譬論,以作短書”的“譬論”。所謂譬論,指用打比方的方式説理,使道理明白易懂。説者在論述事理的過程中,采用切近事理内涵的道理、故事或事物作比,以期形象生動地闡述事理。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云:“譬,諭也。諭,告也。凡曉諭人者,皆舉其所易明也。曉之曰諭,其人因言而曉亦曰諭。諭或作喻。”(77)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頁。王符《潛夫論》云:“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78)王符《潛夫論箋校正》,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26頁。諸子説理,大多以譬論方式,舉具有關聯性的道理、故事或事物類比。《管子》云:“召忽曰:‘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79)房玄齡注,劉績補注,劉曉藝校點《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頁。《墨子》云:“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税,弓張而不馳,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80)畢沅校注《墨子·三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頁。前者以鼎之三足譬管仲、鮑叔與召忽三人對於齊國的重要意義,後者以馬駕而不税、弓張而不馳譬聖王不喜好音樂的不良後果。就論述的策略而言,《伊尹以至味説湯》通篇采取了譬論的方式,且使用了兩層譬論,層累推進。外層的譬論是説者以湯得伊尹一事譬賢者得賢人之助,裏層的譬論是伊尹以天下之至味譬聖王之道。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説者借助於叙事,叙述了湯得伊尹的經過及伯牙與子期的相知;伊尹則借助於博物,鋪陳天下至美之物。就論述的效果而言,經過兩層譬論,原本抽象的道理(如功名與賢良的關係、天子與聖人之道的關係),借助於叙事(如湯得伊尹、伯牙與子期)與博物(如肉之美者、魚之美者),變得形象生動,明白易懂。
實際上“譬論”是《漢書·藝文志》小説家普遍使用的論述方式,除《伊尹以至味説湯》外,其他篇目中亦有迹可循,如《師曠見太子晉》師曠云“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王子云“夫木當時而不伐,夫何可得”;《天乙》云“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獨居,譬其若火”;《百家》以“城門失火,殃及池中魚”的故事“喻惡之滋,並中傷良謹”的道理等。其他幾篇小説因不見全帙,只剩殘篇,無從判斷總體的形式特徵,但據現存的條目來看,也大致可以歸於論説體(如《鬻子説》“政曰”論民與吏之關係)、故事體(如《黄帝説》記“泰帝破瑟”與“荼與鬱壘執鬼”,《虞初周説》記“羿射十日”等,皆屬神話故事)與博物體(如《青史子》所記胎教之道、養隱之道與巾車教之道皆屬名物制度考辨)。
以上我們從來源、内涵與形式三個方面考察了《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的名與實,現在稍作小結:
首先,“小説家”的得名出於文獻分類著録的需要,主要依據爲諸子學説的區劃,凡不便歸入九流者皆入小説家。這造成了小説雖位列諸子十家,卻不登大雅之堂的尷尬,“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81)房玄齡等撰《晉書·藝術傳序》,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67頁。。如《百家》是劉向編校《説苑》等書的副産品,因品質與《説苑》不符而被剔除在外,别集爲一書。姚振宗以爲《百家》“蓋《説苑》之餘,猶宋李昉等既撰集爲《太平御覽》,復裒録爲《太平廣記》”(82)轉引自楊樹達《漢書窺管》,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18頁。。這決定了小説家來源多樣、内容駁雜與體例繁蕪的本質特徵。明乎此,方可談小説。
其次,班固以“小説家”作爲文獻類目,承續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九流的分類思想。余嘉錫云:“若夫諸子短書,百家雜説,皆以立意爲宗,不以叙事爲主;意主於達,故譬喻以致其思;事爲之賓,故附會以圓其説;本出荒唐,難與莊論。”(83)余嘉錫《古書通例》,第253頁。這決定了小説以闡述思想學説爲主,説者爲闡明己意,會使用多種表達方式,如説理、叙事、博物,後人著述輯録,各有偏重,遂衍生了小説家的三種體例,即論説體、故事體、博物體。
第三,“小説家”的作者身份卑微,如稗官、方士、待詔臣之流,不爲世人所重,不比九流作者身份顯赫,多爲王官,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小説内容淺薄、迂誕,不本經傳,不比儒家、道家等高文典册可以“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爲“君人南面之術”,故人微言輕,價值低下,被視作小道,君子不爲。
第四,“小説家”雖是君子不爲的小道,但也有其價值功能。王者借助小説,可以觀風俗之盛衰,考朝政之得失。歐陽修云:“《書》曰: 狂夫之議,聖人擇焉。又曰: 詢於芻蕘。是小説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雍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於路,采其風謡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84)歐陽修《崇文總目叙釋》,《歐陽修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1004頁。歐陽修將稗官采集小説比諸采詩官收集民情民意,大體不差,傳統小説也的確仰仗這種實用的價值功能才得以厠身於歷代官私書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