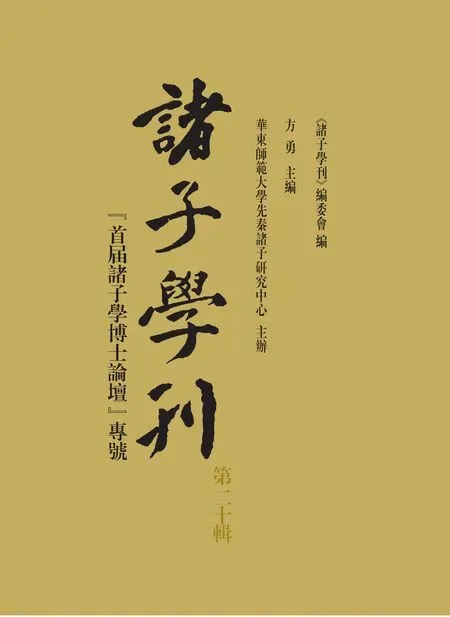言説觀念與文本生成
——論《韓非子》“言説之難”意識及其文本意義
張 安
内容提要 言説觀念是韓非思想中的重要部分。《韓非子》中多有關於言説問題思考的記載,《難言》《説難》即是《韓非子》中專門論述“言”與“説”的文章。韓非對於言説問題的思考串聯着《韓非子》諸多篇章,可以分爲兩個層面,這兩個層面基於人主和人臣之間的話語關係,意圖爲君主如何聽言、辨言提供幫助。同時,韓非的言説觀對《韓非子》的文本也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 《韓非子》 言説觀念 文本意義
春秋諸子能言巧辯,遊説君王,立言後世。韓非處於諸子之末,遍覽群書,以法爲綱,針砭時弊,向君王提出切實可行的治國之道。同時,他撰寫文章,將自己言説以文字的形式記録下來,流傳後世。“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1)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引,張守節正義《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46頁。言説不便和對世間百態的洞察,韓非意識到言説之間有諸多困境。廟堂之上的國家治理,江湖之遠的人心交際,都需要巧妙的語言來進行溝通。細讀《韓非子》,有關於言説的言論在其中俯拾皆是。如《難言》《説難》兩篇文章,就是專門論述韓非的言説觀念。《韓非子》一書包含多種文體,書表文、政論文、對問體等兼備其中。韓非的言説觀念無疑也影響了他的文章形式以及内容。本文不揣譾陋,妄提拙見,試圖梳理清楚《韓非子》中的言説觀念,以及從言説觀念出發,提出這種觀念對於《韓非子》文本生成的一些看法。
一
《韓非子》中,“言”與“説”的含義有所不同。《難二》有云:“辯,在言者,説,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2)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99頁。本文以下所引《韓非子》原文,皆出於此書。《難言》《説難》兩篇是《韓非子》中有專門論述“言”與“説”的文章。仔細梳理兩篇文章,可以發現它們從“言”與“説”的角度出發,表達出對如何有效地進行言説的兩種不同思考。馬世年先生在《韓非子的成書及其文學研究》中將《難言》歸入書表體,屬於臣子向上進言;將《説難》歸入一般政論文,則是就時事發聲言論,這種分類方法也恰如其分地將“言”與“説”這兩種概念區分開來。
《説文》在解釋“言”字時云:“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的表達需要“直言”。“直”,《説文》解釋爲“正見也”。這種正見往往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向上推溯,言在《尚書》中常指君王的教令(3)丘淵《言、語、論、説與先秦論説文體》,華中師範大學2008年博士畢業論文,第45~46頁。,同時,春秋時期的言也是輔佐政治的一種行爲(4)同上,第56頁。。《難言》中的“言”,主要講述的就是輔政之言。韓非子的言説觀有着極强的功用性,從“言”方面來講,主要表現在他對於言和行的認識上。《問辯》有云:“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説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外儲説左上》:“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説者多‘棘刺’‘白馬’之説。”《難言》的功用性考慮就是臣子的進言是否得當,最終能否爲人主所采納,並且進言者是否可以全身而退。《難言》言辭懇切,向人主講述“進言”之難。整篇文章的論述要點是“君子難言”,通過兩個層面的思考來展開論述。首先,對臣子進言的論説言辭進行剖析。分析進言的言語風格實用亦或華麗,言語的表達形式是“連類比物”,或是“徑省而不飾”,言語的内容“閎大廣博”,或是“家計小談”,言説内容的時間範圍的“近世”或是“遠俗”,言説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最終得出臣子進言“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的結論。其次,提出“至賢説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以智説愚必不聽”,並列舉出伊尹説湯、文王説紂等事例來論證。
説,《説文》云:“説,説釋也。”又解釋“釋”説道:“釋,解也。”議論諸事,解釋道理。戰國時期,説在文體上的表現也是類似於“經”“注”之類的解釋典籍之文。《説難》一文,不僅在文體上不同於書表體的《難言》,而且面向的讀者是進言的臣子、遊説之士而不是帝王,論述内容自然也與《難言》迥異。梁啓雄在《韓子淺解》中注釋此篇時云:“韓子指出遊説之士發言之難,及其遭遇之險,是一篇反映出人情世故和君主心理的作品。”(5)梁啓雄《韓子淺解》,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9頁。《説難》一文,先詳説種種處下者如何向在上者進言,再論在上者對進言者的不同態度,然後又告訴進言之人,“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讓遊説之士明白言語的慎重與否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息息相關。所以,“此説之難,不可不知也”。那麽,進言的核心,在於“飾其所説之所矜而滅其所恥”。讓言説之人明白如何用言語巧妙地在維護在上者尊嚴的情況下,同時也完成其不可明言的事情。最有用的言説應當是“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係縻”,然後進言者才可以“極騁智辯焉”。宋人高似孫《子略》卷三“韓非子”條云:“《説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唯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説而後説於人。”(6)高似孫《子略》,《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9頁。
將“言”與“説”有所分别,並非只出韓非一家。郭店楚簡《尊德義》:“教以禮,則民果以勁。教以樂,則民弗德争將。教以辯説,則民勢陵長貴以妄。……教以言,則民訏以寡信。”(7)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頁。劉釗釋“言”爲言辭,侯文華釋之爲“指出使對應的外交辭令”(8)侯文華《論語文體考論》,《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3期。,相比之下,李零未釋“言”,而是釋“訏”爲“詭詐之意”(9)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頁。,既符合《説文》對於“訏”的釋義,也符合具體語境。李零進一步解釋道“‘訏’與‘信’相反……也是與‘忠’相對”。“信”《説文》訓爲“誠也”。不信之言即爲不誠之言。《韓非子·難二》有云:“夫言語辨,聽之説,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言語辯,聽之説,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所以,郭店楚簡的“民訏以寡信”,是與《韓非子》的“窕言”極爲相近的。“教以辯説,則民勢陵長貴以妄。”辯説是韓非極爲反對的一種言説行爲,《八奸》中有一奸行爲“流行”,“何謂流行?曰: 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説。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説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虚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郭店楚簡言辯説會“民勢陵長貴以妄”,韓非言辯説之士因巧言利勢患害,最終虚辭壞主。二者是對於辯説的批評態度是一致的。
二
韓非對於言説問題的考慮,可以分爲兩個層面。這兩個層面都是基於人主和人臣之間的話語關係。人臣如何向在上人主言説,屬於上行進言;人主如何辨别人臣的進言,避免陷入言説困境,而後以法爲綱,以刑、賞來掌握人臣的行爲,這屬於對下辨言。這兩個層面的思考串聯了《韓非子》諸多篇章。在這其中,韓非對於人主如何對待言説的論述,尤其是如何明辨臣子的言説,在全書中多爲“顯現”出現;而對於處於下位的人臣如何言説,除了《説難》專門論述以外,多“隱性”在《韓非子》的《説林》《内外儲説》中。
雖如《説文》釋義,“正見”謂之“言”,而“論”即爲“説”,但梳理《韓非子》全書,除了《説難》《難言》對“言”“説”涇渭分明地有所論述,其餘各篇中“言”與“説”時而有所混淆,時而涇渭分明。但是“言説之難”的意識,貫穿《韓非子》始終。歸結起來,之所以出現“言説之難”,是因爲言説皆可辯。言可辯,就會使得奸臣“取資乎衆”,使人“信乎辯”,達到其“以類飾其私”的目的。所以,韓非在基於“言説之難”考慮之上的言説觀,首先就是旗幟鮮明地反對辯言辯説。言説可以辯,就會出現“飾言”“窕言”“壅於言”的情況出現。這幾種情況正是韓非認爲會擾亂朝政,危害國家,因而極爲反對的。韓非明確反對“棘刺”“白馬”之辯説,“堅白”“無厚”之詞。《外儲説左上》云:“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説者多‘棘刺’‘白馬’之説;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問辯》云:“人主者説辯察之言,尊賢扛之行……‘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 上不明,則辯生焉。”“白馬”“堅白”出自名家,“無厚”出自莊子,都屬於言辯範疇。韓非拒絶辯言,同時也斥責“不言”,《南面》云:“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
基於對言説之辯的排斥,韓非的言説觀尚簡尚直,功用性極强。《問辯》云:“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説也。”《五蠹》云:“今人主之於言也,説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這樣的言説觀也直接反映在《韓非子》提出的治國策略。《外儲説左上》中,楚王問田鳩“墨子……其言多而不辯,何也?”韓非借田鳩之口回答道:“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説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説,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這種實用性言説觀念的核心在於“務本”,“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而好末事,知道虚聖以説民,此勸飯之説,勸飯之説,明主不受也”。韓非强調治國之用言,勢必不能爲“辯説文辭之言”,不可“以文害用”,否則極有可能爲害國之舉。輕者如《問辯》所述,導致“耕戰之士寡”“憲令之法息”,重者則可能如《亡徵》所言,導致亡國之禍。
臣舉言以議政,君納言以任事。在韓非看來,君臣之間的言語往來,微妙深遠,無論臣子進言,亦或是君主納言,都要謹慎小心。言説與治國的關係密不可分。在《二柄》中,韓非説道:“故世之奸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説疑》中又云:“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所以,在韓非心中,明主必須能明白言説中的是非,進而審核臣子所進之言與所行之事是否得當。《奸劫弑臣》云:“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韓非子》關於言説困境的思考,因言説可辯而起,具體在對人主如何明辨臣子進言的問題提出見解。言説具有不確定性和易被修飾性,都容易讓人主陷入言説困境,從而被左右其治國策略。韓非總結以下幾種情況會讓人主陷入言説困境,進而危害國家正常運轉:
第一,奸臣朋黨比周,以言惑衆惑上。《孤憤》中説“朋黨比周以蔽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人臣結黨營私,謀一己之私利,向上用言語來蒙蔽人主,“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説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虚辭以壞其主”,向下則“爲人臣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散公財以説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騙取民萌,最終獲得重用,奸害朝堂、百姓。在韓非看來,言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成“勢”的一種。《孤憤》云:“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朋黨比周,言曲取私,終將導致人主失勢而人臣得國。
第二,文學害法,政令不行。韓非認爲,文學與法,水火不容。《六反》中明確將“文學之士”定義爲“學道立方,離法之民”。《八説》有云:“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民尚文學文,追隨能言巧辯的文學之士,就可能棄耕,如《外儲説左上》所説:“利之所在民歸之……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韓非言説觀重功用性,言行與法令勢必要合一,才能有效治理國家。《問辯》中有韓非關於法令與言行的思考: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説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説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别辭争之論,而莫爲之正。
在這樣的思考下,韓非甚至深惡痛絶予民以智。《揚權》言“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顯學》言“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民有智,以文學修飾其言,狡辯其行,離群犯上,終爲《五蠹》所言“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第三,言不當事,事不稱功,奸行不止。韓非對於言説功用觀念的態度,極爲嚴苛。韓非認爲言必須當事,才能使人主不被迷惑。《八奸》中,他提出了“(明君)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説議也,稱譽者所善,毁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群臣相爲語。……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其所論述的能使人主亡國的八種奸行,一半需要人主明辨“左右”“父兄大臣”“説議”“諸侯”所述之言是否與實情相符合。再者,一言對一事,一事論一功,韓非認爲言必須當事,才能符合法治的要求,從而合理分配功賞。《八經》中談及“有道之主”的作爲,韓非就提出“有道之主”需要“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二柄》中更是對此展開了詳細論述,其云:“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説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爲矣。”從某種程度來説,這也是出於禁奸、防止朋黨比周現象的考慮。
三
韓非對於“言説之難”的考慮,貫穿《韓非子》全書,最顯著表現就是“説”體文在《韓非子》全書中所占比重較大。韓非善於以事喻理,因事論人,“説”體文是《韓非子》這一特點的體現。學界認可《説林》《内外儲説》的故事性質。馬世年先生認爲《説林》是原始資料彙編的故事集,《儲説》是韓非學派内部的教學資料(10)馬世年《韓非生平與〈韓非子〉文體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第32頁。。廖群先生認爲:“在《韓非子》中,《説林》《儲説》顯然不是一般的故事集,而是韓非闡發理論學説的組成部分。”(11)廖群《“説”“傳”“語”——先秦“説體”考察》,《文學遺産》2006年第六期。《内外儲説》《説林》,占去《韓非子》全書幾乎三分之一,故事性極强的“説”體文在《韓非子》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讓人深思這與韓非“言説之難”意識的關係。吕思勉在《經子解題·韓非子》中云:“(《説林》)此篇列舉衆事,藉以明義……此可見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義。”又云:“《内外儲説》,皆言人主禦下之術,乃法術家言之有條理者。”(12)吕思勉著《經子解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65頁。“列舉衆事,藉以明義”即是《韓非子》“説體文”的意旨所在,而這樣的意旨,即用寓意極强的故事來説事論理,是韓非建立在對如何進行有效言説的思考之上的。此外,韓非還在《説林》《内外儲説》中記録了大量的巧辭妙言的故事,這也是韓非利用故事和言説的巧妙關係,來達到言説最優效果的例子。這些故事或彰顯言説之善,或彰顯言説之惡,或顯言説之變幻多端,無一不是通過故事來表明言説的力量。如《説林》上中的“湯使人説務光”“子圉恐孔子貴於君”“子胥出走”“温人之周”“子皮事田成子”等。可以説,《説難》向言説者論述、闡釋言説的不易之處,而《説林》《内外儲説》作爲《韓非子》的重要内容,是韓非以故事形式向言説者説明“故事”在言説活動中的重要性。
韓非尚簡尚直,功用性極强的言説觀,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韓非子》的文本生成。《韓非子》就篇名來説,有相當部分篇目是以數字命篇,如《二柄》《八奸》《十過》《三守》《六反》《八説》《八經》。這些篇目無一例外,都在開篇時不多贅言,直接解題,再往下就是分條叙説,闡明己意。這些文章或提出治國的規則,或指出需要防範的奸行,都與人主治國有關,旨在幫助君主建立世間秩序,是典型的政論文。韓非的這種言説觀是建立在他的法治思想之上,在他的法治思想中,一切的社會關係都是利害關係可以闡明的,因此,他的言説觀與思想同軌,思想不需要感性考慮,直切要害,言語不需要過多修飾,乾净利落,這也影響到了這部分文章的寫成。
四
韓非的言説觀念雖然服務於封建統治,但是其本身仍有可取之處。陳啓天闡發新法家理論内涵時認爲可以將舊法家思想中適用於現代中國的成分,酌情考量,審時度勢,從而形成一種新法家理論(13)陳啓天《中國法家概論》,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20頁。。反觀韓非的言説觀念,其所倡導的“言當事”理念,對待言説的辯證態度,旗幟鮮明地反對“飾言”“窕言”“壅於言”,都是韓非言説觀念中值得我們汲取的合理成分。
首先,韓非提倡的“言當事”理念,值得當代人們學習。雖然韓非的這一理念建立在監督下臣所言與所做之事相符,方可量言定功的基礎上,但這一理念最終旨在杜絶臣子的種種“奸行”。法家治國的治國理念,是從人性的惡作爲出發點,試圖建立有序的社會秩序,且保證秩序不受破壞,來達到萬世大治的目的。基於這樣的治國理念,韓非常着眼於人性的黑暗,將人際關係等同於利害關係,“言與事當”就是他用來衡量利害關係的一個準則。這個準則古今皆可通用。人性善惡没有定論,但是社會動物需要合理的秩序來規範行爲,確保社會的正常運轉。言不當事而導致宦官當道,佞臣横行的例子在古代不可枚舉;當代社會因爲言不當事而導致人們不守誠信,喪失道德底綫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長春長生的假疫苗事件,演藝圈金額驚人的陰陽合同,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僅僅造成極惡劣的社會影響,同時也阻礙着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因此,普及韓非“言當事”理念,爲當代人樹立講真話,講實話的觀念是極有必要的。
其次,處於新媒體時代的人需要學會“辨言”。媒體技術飛躍式的突破,使得社會中的個人隨時隨地都能成爲話語中心。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真假信息裹挾而來。因此,對信息進行“去僞存真”的處理極爲重要。韓非在《難二》解釋“夫言語辯聽之説,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時説到:“辯,在言者;説,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這揭示出言説活動中主客雙方的特點。説者擇言以語人,勢必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話;聽者擇言而信,剔除“窕言”,就會讓話語活動的雙方得到平衡。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帶來大量的信息,如何讓信息接收者辨别謡言,拒絶傳謡,是當下網路環境净化工作的重點之一。韓非的“辨言”觀念雖然有拒絶“民智”的成分,但其對於言説的辨認態度值得人們去學習。
總之,韓非强調功用的言説觀是他以法爲綱思想的反映。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言説既可以作爲得“勢”之“術”,建立秩序,治理天下,同時也可讓言説者懂得言説之道,實現言説價值。這種過於强調目的性的言説觀念的産生,既是韓非個人經驗的總結,也是戰國末年亂世背景下的結果。韓非的這一觀念,在現在看來過於嚴苛,不近人情,但在當時背景下所産生,也是必然之事。習近平同志曾指出:“我們決不可抛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恰恰相反,我們要很好傳承和弘揚,因爲這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論群衆路綫———重要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頁。。傳統文化是“中國故事”的根基所在,韓非的法家思想作爲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社會的法治規範。在此基礎上,對韓非的思想價值進行深度發掘,可以更好地實現社會的“法治”,再配合“德治”,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