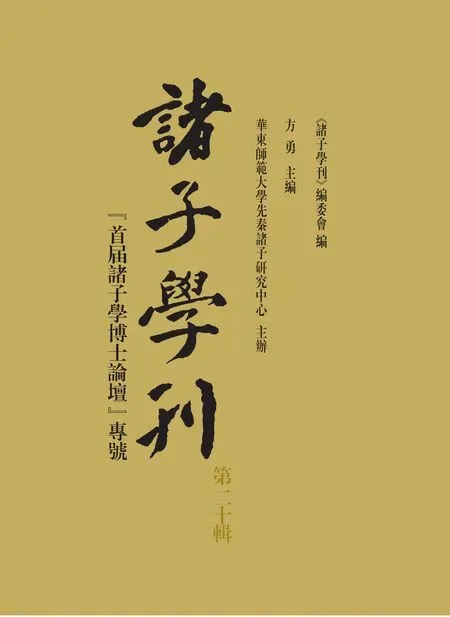錢穆荀學研究芻議
張 泰
内容提要 錢穆對荀子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先秦諸子系年》《中國思想史》以及文集未刊佚文《荀子篇節考》《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等。在考據方面,受疑古學風影響,錢穆對荀子其人其書均進行了考證,尤其對《荀子》篇節的重新考訂頗具新意;在義理方面,受“明體達用”的宋學精神影響,錢穆既肯定了荀子思想的經世精神,又站在正統儒學的立場對其提出批評,並指出荀學的政治性傾向導致學術附庸於政治的局面,進而造成先秦學術的中絶。
關鍵詞 錢穆 荀學 考據 義理 宋學
自清代以來,荀子研究成爲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乾嘉考據成績斐然,晚清至民國義理的研究又達到新的高度。錢穆先生是我國著名學者,一生治學範圍廣博,著作豐碩,其著作彙編爲《錢賓四先生全集》,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於1998年出版,後來大陸又由九州出版社重新校訂於2011年出版《錢穆先生全集》。子學研究是錢穆先生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先秦諸子系年》《中國思想史》等書中均有創見。錢先生早年撰寫的兩篇論文《荀子篇節考》與《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未收入其文集,而又與其荀學研究相關,可與其文集相參證,頗具學術價值,故今以此兩篇文章爲切入點,結合錢穆先生對荀子的其他論述,分析錢穆先生荀學研究的特色與價值。
一、 疑古學風影響下的荀學考據
20世紀20年代,胡適先生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主張,在全國範圍内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整理國故”運動,對宋儒“疑古”的精神大力發揚,采取“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針,對大量史料進行整理與考辨,形成了以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爲首的“新考據派”。這一時期,錢穆的考據成果影響也很大,《劉向歆父子年譜》經顧頡剛推薦刊發於《燕京學報》,《先秦諸子繫年》被陳寅恪稱贊爲“自王静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矣”(1)錢穆《師友雜憶》,《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162~163頁。。他與新考據派關係匪淺,30年代初錢穆得以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便與傅斯年、胡適等人的推薦有關。但錢穆並不屬於新考據派,他對新考據派的態度也經歷了從肯定到否定的轉變。
錢穆在治學中向來主張考據與義理並重,反對不以義理爲終極歸宿的考據,他認爲,“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理爲歸宿,始知其所當考據之真意義,與真價值”(2)錢穆《〈新亞學報〉創刊詞》,《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1955年。。新考據派的學者在實踐中將乾嘉學派爲考據而考據的態度發揮到了極致,疏於對義理的研究,這是錢穆所不能接受的。他在《國史大綱》中有這樣一段批判:
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爲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爲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唯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3)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7册,第24頁。
從這裏便可以看出錢穆與新考據派的分歧所在。徐國利認爲:“錢穆的獨特貢獻則在於從保存和發展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視野下系統論述考據及其與義理的辯證關係,並以之爲準繩對清代、特别是近代以來的新考據學作了全面批判。”(4)徐國利《錢穆的考據學思想》,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6届年會論文,2005年10月。錢穆自己所做的考據工作,就在竭力避免清儒及新考據派的舊路,而是以考據來打通學術史,解決因史料的錯訛、殘缺造成的學術史錯誤(5)由於歷史的局限與方法的限制,錢穆的考據學成果也存在一些錯誤,比如他缺少對出土文獻的關注,而很多新出土的材料證明了他的一些考據成果是錯誤的。。他對考據與義理的關係進行了重新界定,認爲考據也包括義理,他曾説“考據應是考其義理”(6)錢穆《學與人》,載《歷史與文化論叢》,《錢賓四先生全集》第42册,第152頁。。在諸子學研究中尤爲重視這一點,認爲“他們(指先秦諸子)的思想言論,也各有來歷,各有根據,都不是憑空而來。那亦即是考據”(7)錢穆《史學導言》,載《中國史學發微》,《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2册,第44頁。。以荀子爲例,錢穆對荀子的考據包括對荀子生平事蹟的考證和對《荀子》篇章的考訂兩方面,對荀子其人其書均進行了細緻的考辨,爲闡發荀學義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 對荀子生平事蹟的考證
錢穆考據學的代表作《先秦諸子繫年》對先秦諸子的生平事蹟、學術淵源、各家思想流變等一一加以考定,其中專論荀子的有卷三《荀卿年十五之齊考》、卷四《荀卿自齊適楚考》《春申君封荀卿爲蘭陵令辨》《荀卿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考》《荀卿赴秦見昭王應侯考》《荀卿至趙見趙孝成王議兵考》等篇,基本囊括了荀子生平的重要事件。錢穆的考證主要以典籍中的文獻互見爲手段,輔以學理,從而博綜典籍,梳理綫索,還原歷史的真相。
據司馬遷《史記》與劉向《孫卿叙録》等記載可知,與前輩儒者一樣,荀子的一生也到過許多國家。他曾於齊國講學、於楚國仕宦、於趙國議兵、於燕國議政、於秦國論風俗。其中的時間問題歷來爲研究者所重視,錢穆認爲劉向和司馬遷的説法均有矛盾之處,難以確信。
荀子與齊國的關係十分密切,他一生中曾三次到齊國。齊國的稷下學宫對於荀子思想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意義。據錢穆考證,荀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十五歲時遊學之齊;第二次到齊國是從燕國到齊國,爲稷下列大夫;第三次是齊襄王時,從楚國到齊國,此時稷下之士皆已散亡,荀卿“最爲老師”,自襄王六年至襄王十九年,荀卿“三爲祭酒”。關於荀子遊學於齊時的年齡問題,史料中存在“年五十”與“年十五”兩種記載。司馬遷《史記》與劉向《孫卿叙録》記爲“年五十”,而應劭《風俗通義》、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王應麟《玉海》等記爲“年十五”,孰是孰非,衆説紛紜(8)據梁濤《荀子行年新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贊同“年五十”説的有胡適、羅根澤、蔣伯潛等,贊同“年十五”説的有梁啓超、錢穆、梁啓雄、游國恩、劉蔚華等。。錢穆主張“年十五”之説的原因有三: 其一,遊學是從學於諸先生,是年輕時所做的事。年五十之後荀子已爲師,遊學的行爲與其身份不符;其二,劉向《孫卿叙録》提到的荀卿“有秀才”,是“年少英俊之稱”,並非“學成爲師之事”(9)錢穆《荀卿年十五之齊考》,載《先秦諸子繫年》,《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册,第387頁。;其三,“始來遊學”與“最爲老師”相對,指的是時間的先後,因此遊學當爲年少時所爲。以考據的視角來看,距離荀子年代更近的司馬遷與劉向均記爲“年五十”,而“年十五”之説爲後出,或是後人以爲年五十與遊學的經歷不符,遂妄自改爲年十五,錢穆的推斷有可能是後人改“年五十”爲“年十五”的原因,並不能確定“年十五”爲真,今人也多認爲錢穆此説不足爲據,如林桂榛就認爲錢穆以“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稱”證“年五十”當作“年十五”,“此謬甚”(10)林桂榛《荀子生卒年問題新證——以〈鹽鐵論〉兩則記載爲中心》,《邯鄲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關於荀子自齊適楚的時間,錢穆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當在湣王十五六年間”,“是時荀卿年當五十五六”(11)錢穆《荀卿自齊適楚考》,載《先秦諸子繫年》,《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册,第491頁。,這次自齊適楚,是他第二次到齊國之後再次離開,並因受讒而作《成相》。關於荀子與春申君的關係,歷來人們都以《史記》所述爲本,認爲春申君曾封荀子爲蘭陵令,春申君死後荀子終老蘭陵。錢穆列舉了大量文獻,結合荀子生平經歷的考證,推翻了這一説法。證據如下: 第一,荀子去齊適楚在湣王末世,距黄歇爲春申君尚二十餘年,時間不符;第二,荀子當時已經年過八十,年齡不符;第三,荀子書中並没有關於蘭陵令與春申君的記載。經錢穆考證,荀子確曾爲蘭陵令,然而並非在春申君爲相之後,而是在荀子遊趙聘秦之前。這一説法爲荀子與春申君關係的考證提供了新的思路。
關於荀子入秦、至趙的時間先後問題,也存在争議。孔孟都未曾入秦,而據《儒效》《强國》等篇記載,荀子曾入秦與秦相范雎問答。錢穆根據范雎爲相的時間來推算,荀子入秦當是秦昭王四十一年至五十二年之間,據此而知,一些人將荀子入秦的經歷置於入趙以後是錯誤的。錢穆根據之前的考證否定了劉向對於荀子“避讒適趙”的説法。他認爲,荀子至趙當在去秦國之後不久,長平之戰前。由《臣道》篇稱頌平原君與信陵君之功可知,荀子在邯鄲解圍之時身在趙國。當時荀子已經年過八十,錢穆推測荀子有可能終老於趙國。
錢穆對荀子生平的考證基本勾勒出了荀子的行年,因而將荀子的生卒年定爲約公元前340—前245年(12)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附《諸子生卒年世約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册,第697頁。。他結合大量的史料文獻,通過旁證,對不同文獻進行對比分析,對史料進行了大膽的質疑與推斷、猜想,雖然個别地方帶有一些主觀痕迹,但依然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功底,他在致余英時的信中也毫不吝嗇對此書的自得之意,“唯《諸子系年》貢獻實大,最爲私心所愜”(13)錢穆《致余英時書》,載《素書樓餘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3册,第413頁。。
(二) 對《荀子》篇節的考訂
錢穆的荀學研究最具特色之處在於對《荀子》一書所做的是正篇節的工作,主要見於論文《荀子篇節考》。該文刊載於《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學術”欄,同時刊載的還有《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及《墨辯與邏輯》。這三篇文章不見於《錢賓四先生全集》和《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一直未爲人所重視。錢穆先生本人對《荀子篇節考》頗爲得意,其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序中寫道:“又曾撰《荀子篇節考》,乃在蘇州中學任教時所成,曾刊載於吴江某生所編某雜誌中,自謂昔人治荀書,獨未於此有注意,惜行篋中缺此篇,附識於此,志弊帚之自珍焉。”(14)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8册,第1頁。錢穆先生自認爲此文發前人之未發,頗具學術價值,卻未將其刊録於《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究其原因,其在《師友雜憶》中自叙“余有《荀子篇節考》一文,刊《原學》之第一期。自謂有創見,言人所未言。但今無此雜誌在手,因此亦未能將此刊文入余近所編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15)錢穆《師友雜憶》,《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册,第145頁。。乃是其自己記錯發表刊物,由此造成此文數年來不爲人所知,實屬遺憾。
這篇論文在考據上的最大成就在於對傳統考據方法的反動,不對字詞章句進行訓釋,而是着眼於篇章的起承轉合,評估《荀子》一書中可能出現的錯簡問題。在文章中,錢穆首先肯定荀子“在先秦最爲能持論”(16)錢穆《荀子篇節考》,《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但是讀《荀子》書卻發現一篇之中時常出現“自爲出入”的情況,原因就在於今本《荀子》存在錯節脱簡的問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錢穆懷疑劉向負有一定責任,“向以三百二十二篇勒定爲三十二篇,期間不能無離合從違。有離合從違,即不能必其爲荀子原書之真也”(17)錢穆《荀子篇節考》,《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他還舉了《三年問》《禮三本》篇出於《禮論》,《宥坐》“見大水”節附《勸學》篇中,《哀公》後“定公問於顔淵”節本不在此篇等例子,來説明劉向整理荀子書的時候采用的“歸併”“轉移”“連綴”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荀子書的原貌。此外,他還懷疑劉向校書時所去除的篇節,未必是重複的篇章,而只是“重複之文”,但自劉向校定後唯有此本流傳下來,荀子書原貌已無從考。劉向的校書在歷史上影響深遠,《漢書·藝文志·總序》云:“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18)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01頁。“當時古書多篇章卷單行,各本篇章多異,他合校衆本,互相補充,删除複重,編定篇章。”(19)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10頁。劉向所校爲其精通的經傳、諸子、詩賦三大類書,其他專書皆由專家完成。以劉向的學識,校書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的篇章排列錯誤問題似不太可能,況且他在校書中廣備衆本,他所做的“編定篇章”也並非對原來各篇進行重新的排列組合,而是去重補缺,將原來散見的各篇章歸爲一書,均稱“新書”。因此,經劉向整理而錯簡的觀點難以成立。
錢穆還從子部著述的一般規律來分析《荀子》錯節脱簡的原因。他將子部著述分爲“集語”與“造論”兩種形式,“集語”是經後人采集編校而成的書,如《論語》《孟子》,即今所言語録體,多見於早期子學著作;“造論”是專題論文,以論述要旨命名而成的書,即今所言論辯體著作,這種形式在戰國後期才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錢穆指出,《荀子》一書是“集語”與“造論”並存之書,像《性惡》《天論》《正名》《正論》《非十二子》等篇,本爲“造論”體,而後人以集語題名之法誤解之,因而出現了以篇中出現題名者爲篇首的情況,造成“篇末與前文若不類,而與下篇之首則緊相銜接”(20)錢穆《荀子篇節考》,《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這也是造成篇節錯亂的原因。
在分析了現象與原因之後,錢穆也將其認爲的《荀子》中的錯節脱簡處一一列出,並做了是正篇節的考訂。大致可歸納爲以下幾類:
第一,以文章的主題或特點來判斷。這種情況在分析中是最多的,也是最容易判斷的一種,如《不苟》篇“皆以君子二字發端”,《儒效》篇“同論君子小人”“同辨安危榮辱”“同謂君子小人之分起於智愚”“同謂宜重師法、尚積習”“本篇各節皆言治”,《非相》篇末與《非十二子》篇首“一意相承”,《王霸》篇“各節皆引成語,‘此之謂也’作束”(21)同上。,錢穆先生正是通過總結這些特點來判定一些屬於或者不屬於此篇的文字。
第二,以文章的結構層次來判斷。如《榮辱》“知之不若行之”,“蓋承尚更進一層言之”,《非相》與《非十二子》關於“辯”的討論是“上下照顧”(22)錢穆《荀子篇節考》,《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這種錯簡的情況比較普遍,由於竹簡繁重,經常會有脱落的情況,後人不清楚它的原本位置,造成錯亂,所以根據文章的結構層次大致可以將其歸位。
第三,以“文氣”來判斷。如錢穆認爲《非相》後段應爲《非十二子》開篇,原因是“文氣相貫”,與荀子他篇“血脉貫通,劃而分之,則精義散失”(23)同上。。這種從文章整體來判斷篇節歸處具有一定難度,由於荀子書並非一人獨立完成,其中包含弟子後人集體編的作品,即使荀子本人寫作的文章風格也不一定統一,甚至一篇文章中面對不同的問題也會采用不同的論述方式,因此錢穆用這種方法來判斷篇節歸處也是比較謹慎。
第四,以《荀子》書本身特點來判斷。如《非相》自“人有三不祥”以下爲《非十二子》文,原因是“《荀子》書容有單篇短論,而今則連筆相次,絶無一節自成一篇者。後人怪其短,遂以下篇前半割而歸之”(24)同上。。再如,《非十二子》“兼服天下之心”以下爲《仲尼》篇文字,後人以“集語”的題名方式,將“仲尼之門”定爲《仲尼》篇首,這是没有搞清《荀子》書是“集語”與“造論”並存之書的緣故。又如,《王制》篇分爲五項,每項均有標題,錢穆認爲《王制》篇也是雜綴“集語”而成的。因此,錢穆才會在文中數次强調“集語”與“造論”的區别,以區分不同篇章的文體特點。
還有一些判斷證據不足或没有闡述理由,可能是出於治學的敏感將其列出,但又苦於找不出確鑿的證據,只能暫時擱置。
錢穆先生對《荀子》篇節的考訂,其實還是爲了對荀學義理的闡發打好文獻基礎。清儒雖然精於校勘,他們對《荀子》的校勘也堪稱精良,但卻很少有人關注篇節的問題,只有盧文弨有寥寥數語論述(25)盧文弨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90頁。,這正反映了清代漢學發展到後來“爲考據而考據”的狀態,而錢穆先生用了一整篇文章來論述這個問題,足以看出他的考據學思維與清儒的不同。
二、 “明體達用”立場下的荀學義理闡釋
錢穆先生的諸子學研究一方面精於考辨,另一方面更注重對義理的闡釋。這與他對宋學的推崇是密切相關的。他曾多次表達自己的宋學觀,如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開篇便提到: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爲判。”(2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6册,第1頁。
在錢穆看來,清代學術也是承襲宋明而來,學術本就是“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27)錢穆《清儒學案序目》,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92頁。,各時代的學術之間必然存在内在的關聯,而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産生新的變化。他對於宋學的推崇主要就在於宋學所藴含的精神乃是清代“爲學術而學術”的漢學所欠缺的,即“宋學派的精神在明體達用”,而“體”便是儒家的綱常名教,“宋儒主張存天理去人欲,修齊治平之總綱即天理,亦即聖人所謂之體,由體便可達用”(28)錢穆講,劉大洲記《漢學與宋學》,《磐石雜誌》1934年第2卷第7期。。由“明體”到“達用”的過程就是儒家思想的經世化過程。
錢穆對荀子的研究也站在“明體達用”的立場之上,他在1977年出版的《中國思想史》中總論中國歷代思想,其中“荀卿”一節專門論述荀子的思想。此外還有發表於《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學術”欄的論文《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通過對荀子與韓非思想的比較,分析其思想對先秦學術所起的作用。與其他思想史著作將荀子思想分類論述不同的是,錢穆先生主要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即通過荀子對諸子的批判來闡發荀子的思想主張。
荀子所處的時期,在錢穆看來是屬於“先秦學術之歸宿期”(29)錢穆將先秦學術分爲四期,分别爲萌茁期、醖釀期、磅礴期、歸宿期。參見《先秦諸子繫年·自序》,《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册,第47~48頁。。《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對荀子著書立説的時代背景是這樣描述的:“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30)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348頁。這就説明,荀子著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對當時諸子學説的不滿。從《荀子》一書來看,其批評諸子的内容確實占了很大篇幅。他對諸子的批判集中於《非十二子》一篇,此外還有零散見於《不苟》《儒效》《天論》《正論》《樂論》《解蔽》《性惡》等篇。荀子對諸子的批判,從整體上看是站在是否有志於經世,是否有利於王道政治的立場,這與後世的宋學精神不謀而合。因而,錢穆在闡釋荀學義理時,便采用了比較的方法。再者,通過對諸子的評價,荀子批判其弊端,吸收其精華,進一步豐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主張,所以,通過對比來研究荀子的思想無疑具有其合理性。
荀子對墨子、莊子、惠子批評的要點在於他們所主張的僅僅是“道”的一個方面,而則不僅僅着眼於這一隅。對於墨子與荀子的比較,錢穆站在“群”的立場肯定荀子對禮義的重視,相對於墨子只重視外在的物質,荀子“外面注意物質經濟條件,内面注意情感需要條件”(31)錢穆《中國思想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4册,第57頁。,因此二者才會産生“隆禮”與“非禮”的矛盾。但錢穆認爲,荀子只能稱作智者,不能稱作仁人,原因就在於荀子所講的禮是從社會經濟生活出發的,成爲一種功利性的手段,而忽略了儒家所講的仁。筆者以爲,荀子强調禮,是其理論與現實結合的必然選擇,他在堅持儒學本位的前提下,擴大了儒學的生存空間,這是荀子比孔孟高明的地方。荀子自始至終以儒門正派自居,將孔子奉爲聖人,只是他着重發展了外向一路,並不能稱他忽視了儒家仁的宗旨。
對於惠施所代表的名家,錢穆認爲荀子與其根本的不同在於對道的獲取方式,荀子“主從人生實際經驗中求道,不從名與辭之辨析理論中明道”(32)同上,第59頁。。在儒家看來,名家過於重視名與説,做了很多無用之功,對於社會、政治均没有益處。
對於莊子所代表的道家,荀子批評的焦點在於對天與人的理解上,稱其“蔽於天而不知人”。錢穆認爲,道家重視自然的弊端就在於對社會歷史文化的群業過於看輕,從這一角度來看荀子的批判不無道理。但荀子似乎走向了“不求知天”的極端,他認爲“荀子把天、人界限劃得太清楚了,遂變成天、人對立,變成‘制天命而用之’了”(33)同上,第60頁。。可見,錢穆是反對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觀點的,他的天人觀與宋儒保持了高度的統一,主張天人合一,“宋、明儒喜講‘天人合一’之學,要‘存天理,滅人欲’,最後進至‘天人合一’之境界”(34)錢穆《學術思想遺稿》,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頁。。因此,他也將荀子“天人相分”的觀點視作儒學的異端,雖然在客觀上給予了一定的肯定,但還是從内心排斥它。
對於荀子與儒家内部的批判,錢穆對荀子“性惡”的主張評價不高,“荀子主張人類性惡,這也没有真認識人類歷史文化群業的真相”(35)錢穆《湖上閑思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9册,第2頁。,“謂人性中有惡,固屬不可否認。但謂善絶非自然,全出人爲,此見實太狹窄”(36)錢穆《中國思想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4册,第55頁。。這也是荀子“性惡”的觀點没有得到後世廣泛認同的原因。在錢穆看來,荀子與孔孟之儒的不同在於他的理論太偏於重智,而忽視了人與人的關係,“他講人心功能,也看重思慮(即智),而忽略了情感(即仁)”(37)同上,第61頁。。在荀子與孟子的比較中,他也是更偏向孟子的,“儒家又可分兩支,孟子比較重古代,迹近‘理想主義’,荀子比較重現代,迹近‘經驗主義’,但講現代,仍須探本於古代。講現實,仍須歸宿到理想。此乃荀子之不如孟子處,故後代儒家亦多偏向孟子”(38)錢穆《四部概論·下篇: 子學與文學》,載《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35頁。。這一觀點筆者雖不能苟同,卻還是認爲很富有創造性。錢穆先生以學者的姿態,站在孔孟傳統儒學的立場上對荀子的學説進行審視,既肯定了荀子對儒學發展的積極意義,也指出了相較於孔孟的不足,難免具有歷史局限性。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錢穆對荀子的總體評價是不高的。這與宋儒對荀子的貶斥有很大的關係。二程認爲,“荀子極偏狹,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39)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伊川先生語五》,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2頁。,“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40)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第十《大全集拾遺》,第403頁。。朱熹也説:“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4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戰國漢唐諸子》,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254頁。宋儒尊孟貶荀的態度顯而易見,這種態度貫穿整個宋代,並延續到明代。錢穆站在“明體達用”的立場之上,肯定了荀子思想中經世的精神,然而從内在理路上,他還是延續了宋明儒學“體”的根本,從人性善的角度出發建立儒家仁與禮的倫理綱常,站在了荀子的對立面。更有甚者,他將秦朝焚書坑儒的根源追溯到荀子處,將其視爲先秦學術中斷的關捩。
三、 先秦哲學中絶與荀學價值判斷
錢穆發表於《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學術”欄的論文《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與《荀子篇節考》一樣未收入其文集,其文對於焚書坑儒的史實及韓非、李斯與荀子的關係等問題做了深入的探討,對先秦哲學的中絶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韓非與李斯都曾學於荀子,而其二人均背離儒家,成爲法家的先驅。荀子是戰國儒學的集大成者,而韓非則將其轉化爲一套更適用於政治統治的理論,並由李斯付諸於實踐。錢穆認爲:“秦人焚書坑儒……其説已先極論於荀卿、韓非之書,秦皇李斯特本其説而實施之也。”(42)錢穆《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這種觀點依然來源於宋儒,如蘇軾有言:“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43)蘇軾《荀卿論》,《蘇軾文集》卷四,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01頁。朱熹曾説:“如世人説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它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4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戰國漢唐諸子》,第3255頁。在明代已經有學者指出這一觀點的偏頗,如楊慎認爲:“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吴起亦可以累曽子矣。”(45)楊慎《宋人譏荀卿》,《升庵集》卷四十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58頁。錢穆將焚書坑儒的根源追溯到荀子的主張,其依據在於他歸納的荀子之學的本旨“政學一本,君師一貫,而重治”(46)錢穆《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
錢穆從七個方面論述了荀子的主張與政治的密切聯繫。第一,“重分”。爲政者治國應“各當其分”,職責分工確定,社會才會井然有序。第二,“重化其言”。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大道之不存,唯有通過辯説來使感化人民。第三,“重勢臨刑”。荀子“化”的手段之一便是通過刑罰,這是由於人性惡的緣故。第四,“以君爲師”。荀子試圖通過政治的方法,最終實現教化人民的目的。第五,論學“尚效”,“效以往之成績,而不敢任人爲自發之創造”,《荀子》書中多次提到的“聖”,即“以往之成績”,也是“效”的内容。第六,“法後王”。錢穆認爲,這是荀子“自負以大儒之姿,師聖人而得其道貫”(47)錢穆《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後王之法乃是其提出的治理天下之法。第七,“正名”。由於有墨家這樣的儒家反對派的存在,荀子需要用“正名”來確立道的合法性,在學術上就是辨同異,在政治上就是明貴賤。錢穆對這一觀點的評價也不高,認爲“其意蓋注重於政治而極於民之循令,此所以言之多弊也”(48)同上。。
在錢穆看來,荀子的學説是“臣學”,是由學術向政治的進階。這些思想主張對韓非影響很大。韓非進一步發展了荀子的理論,將其變爲“君學”,本質便是爲政之道,成爲爲政治服務的載體。
韓非的理論是導致焚書坑儒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現在: 第一,“政學合而辯息”,政治與學術合爲一體,思想學術失去了自由生存的空間,日漸萎靡,因而“百家争鳴”的盛況也不復存在。第二,反對文學,主張“以法爲教,以吏爲師”,控制思想來源,導致了嚴苛的社會環境。第三,斥遊學,禁私學。遊談文辯,不利於社會生産;私學盛行,不利於法令的推行。韓非希望以這種理論治國,達到“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49)司馬遷《史記》,第255頁。的效果。
面對秦統一之初的社會現實,爲了鞏固秦的統治,李斯上書諫言焚書。此後又有坑儒之事。錢穆對焚書坑儒的史實做了一些考證,對康有爲、胡適、崔適等人的説法進行了辨析,最終得出結論爲“秦政皆源於荀韓”,荀韓的理論必然會導致焚書坑儒現象的發生,而“焚書坑儒爲實行斥異端、尊一主之手段”(50)錢穆《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在這篇論文中,錢穆探討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關於先秦學術的中絶。從戰國晚期開始,一些總結性的學術思想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荀子的出現便對戰國學術做了系統的總結,集諸子之大成。秦的統一,將法家推向主導地位,焚書坑儒更使儒家和其他各家失去了生存發展的空間。到了漢初,黄老道家一度興盛,好之者衆多。隨着漢朝統治的逐漸鞏固,到漢武帝時期,終於形成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爲社會統治思想。然而此時作爲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已非先秦學術之風貌,因而有“先秦學術中絶”一説(51)關於先秦哲學中絶,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有“古代哲學之中絶”一章,論述詳盡,可備一説。參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87頁。。
錢穆指出:“學術附庸於政治,此誠我國哲學中絶之真因,焚書亦其實行方法之一端耳。”(52)錢穆《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求是學社社刊》1928年第1期。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百家争鳴”的盛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學術環境比較自由,各學術團體相對於政治勢力是獨立的,士人擇木而棲,合則留,不合則去。秦統一之後,無論是統治者的政策還是社會環境,都扼殺了學術獨立自由發展的可能,只能附庸於政治,成爲統治的工具。一些無所依附的學説,如名、墨,便逐漸消亡,所僅存的幾家,如儒、道、法,也失去了其原初的面貌。錢穆認爲這都是秦政影響的結果,而“秦政源於荀韓”,矛頭便指向了荀子。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荀子的思想在戰國中後期無疑是先進的,是理論與現實結合的産物,也成功爲儒學拓展了生存空間,尋得與政治的關聯,最終經過一批儒者的提倡而成爲社會獨尊。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儒學作爲學術的發展空間,使儒學的發展陷入停滯。因此,錢穆的批判也不無道理。
四、 錢穆荀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荀學研究在歷史上長期處於低迷的狀態,自楊倞爲《荀子》作注以來,直到清代,學者才開始系統研究並發現荀子思想的價值。錢穆的荀學研究在民國學術史,乃至荀學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錢穆的荀學考據爲荀學提供了新的考據視角。清代的《荀子》考據呈現出異常繁榮的面貌,尤其是清中期之後,王念孫《讀書雜志》、俞樾《諸子評議》等一大批考據成果問世,他們對《荀子》一書用力頗深,將荀學考據推向了頂峰,但這一時期的考據依然是沿着漢學的理路所做的極致化努力。錢穆的考據一反清代以來的考據傳統,將詞章的訓釋降到次要地位,他曾説“至於書本子的訓釋與考據,亦學者所應有的工作,唯非學者主要之急務”(53)錢穆《漢學與宋學》,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79頁。。他從篇章的錯節問題入手,來分析《荀子》文字中存在的邏輯關聯不暢、義理闡發不順等問題,這在荀學史上也具有開創意義。錢穆雖然不善於使用出土材料,但辨錯簡的方法在他的治學中卻很常見,他在《論語新解》中也常常懷疑《論語》存在錯簡的問題,如《鄉黨》“席不正,不坐”一則,他認爲“此句孤出,於上下文皆不得其類,疑是錯簡”(54)錢穆《論語新解》,《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册,第365頁。。這一考據方法貫穿於錢穆的治學始終,體現了他爲探求古書的真實面貌,對古書做出最合理的解讀所做的嘗試。
錢穆對荀學義理的解讀延續了近代以來重義理的風氣,他曾批評清儒治諸子的方法不當,“諸子則專家之學,不能通其大義而徒求於訓詁名物,無當也”(55)錢穆《國學概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册,第361頁。。爲了改變這種情況,自晚清以來,章太炎、胡適、梁啓超等人開始探索以西學詮釋經典,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標誌着現代諸子學的起步。而錢穆在治學中卻少見西學,而更重傳統,他在臺灣演講時針對輕視傳統的風氣講道“文化必然有傳統,無傳統就是無文化”(56)錢穆《中國文化精神》,《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8册,第4頁。。從錢穆對荀子的義理研究來看,一方面,他對荀子學術的理解受宋儒影響頗深,對荀學價值的判斷依然延續了宋儒的觀點;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宋儒所謂的“道統”説,而主張從歷史文化的大傳統來構建“道統”,比宋儒的眼界要更開闊,這反映了錢穆學術學宗傳統的特性與現代色彩,他曾説“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57)轉引自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自序》,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錢穆將荀子思想的政治性與先秦學術的中絶聯繫起來,從學理上來看具備一定的合理性。自先秦伊始,學術與政治就具有相當的關聯度,諸子百家争鳴的最終目的乃是爲自家學説尋找政治依靠,兩漢經學本身就是學術政治化的産物,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都曾爲統治服務,至清代雖然出現了“爲學術而學術”的考據學,但很快便被經世致用的學問所取代。錢穆所謂的“學術附庸於政治”從學術史上來看,並不能算作由荀子思想的政治性而導致的,且在荀學史上,荀子的思想並未得到統治者的重用。但在晚清,政治家的“排荀”基本都是從荀學的政治性上考量的。譚嗣同稱:“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58)譚嗣同《仁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頁。梁啓超説:“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59)梁啓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1頁。這些思想雖然不免具有宣傳的誇大性,但確實成爲荀學史上重要的觀點,錢穆“先秦哲學中絶”之論的可貴性在於其避免了思想中摻雜政治因素,而是從學術的角度來分析這一問題。
綜上,錢穆先生的荀學研究一方面精於考據,另一方面重視義理闡發與價值判斷,尤其是兩篇未收入文集的佚文《荀子篇節考》與《秦人焚書坑儒本諸荀韓爲先秦學術中絶之關捩論》從新的維度對荀學展開研究,應成爲荀學研究的重要材料。錢穆由焚書坑儒的史實出發,强調了荀韓學説在政治上的共通性,而這種學術的政治化傾向最終導致了學術附庸於政治,造成了先秦學術的中絶。錢穆受宋學影響,對荀子多批評之語,而從學術史的角度考量,錢穆也並没有肯定荀子的貢獻,而是將學術中絶的矛頭指向荀子。從這一角度來看,錢穆的荀學研究又有一定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