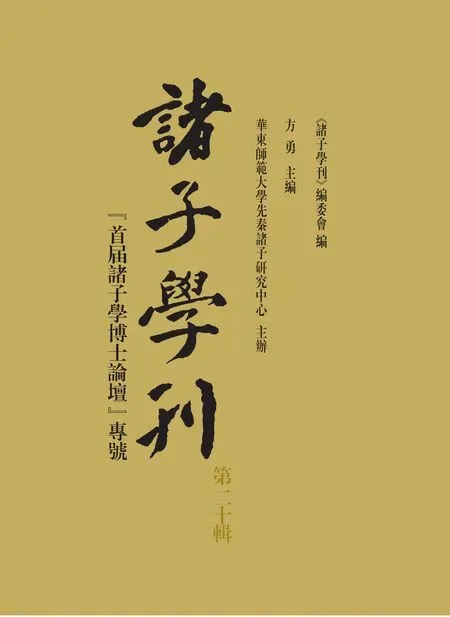作爲過程論的“成人”
——荀子人性論新釋
王國明
内容提要 荀子人性論實質上是一個過程論,而非本質論。性惡並不意味着人性本惡,荀子所謂性有廣、狹義之分,所謂惡也有美惡之惡、與善惡之惡之别。荀子從未直言人性本惡,其所謂“人之性惡”,實指狹義的情性,它並不能涵蓋荀子人性論的全部内涵。廣義的人性還包含心性或知性等内容。“化性起僞”的實質正是不斷發用心性以化情性,從而以後天人爲實現人的本質——義與辨,這一動態過程亦即荀子所謂“成人”。
關鍵詞 人之性惡 過程論 化性起僞 “成人”
荀子人性論素爲荆棘密佈、疑竇叢生之大問題,自古及今,聚訟紛紜,幾爲荀學史一大公案。其因以“性惡論”標識,所以人們通常認爲其内涵即人性本質爲惡,可是細加考索,又會遭遇困惑: 若人性全爲惡,則善從何而來?若人性全爲惡,則荀子所倡禮樂教化又如何可能?若禮樂教化能使人向善,則人性又豈能説惡?再者,荀子説“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辨也”,又説“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如此豈不與“性惡論”自相矛盾?事實上,這些質疑恰恰反映了這種將“性惡論”視作本質論的常識看法,並不能有效理解荀子人性論的完整面目和真實内涵。荀子性惡論實質上是一個過程論,言“性惡”只是其人性論的邏輯起點,而最終通過“化性起僞”,實現人的本質——義與辨,完成禮義化的塑形,才是其人性論的終點,亦即荀子所謂的“成人”。
一、 美惡與善惡:“性惡”的雙重意藴
荀子素以“性惡論”標識,然而通觀《荀》書,言“性惡”者唯《性惡》一篇,初思或令人駭怪,若“性惡”是荀子人性論之核心觀點,理當彌散全書,爲何單單只見於《性惡》一篇呢?更有學者以此篇所主“性惡”與《禮論》等其他篇所主“性樸”不相協調爲由判定《性惡》爲僞作(1)近年來,周熾成、林桂榛等先生重新發掘劉念親、兒玉六郎有關荀子“性樸論”的見解,并努力倡導,使之成爲荀學領域的一大熱點,突破故識,確有創見。而隨着對“性惡論”質疑的深入,有關荀子《性惡》篇的文獻問題亦再度陷入争論。歸納前人時賢的有關探討,約分三派:第一派是僞作説,主張《性惡》非荀子作。如劉念親《荀子人性的見解》,《晨報副刊》1923年1月16~18日;金谷治《〈荀子〉の文獻的研究》,《日本學士院紀要》1951年第9卷第1號;周熾成《荀韓:人性論與社會歷史哲學》,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荀子:性樸論者,非性惡論者》,《光明日報》2007年3月20日第11版;《〈性惡〉出自荀子後學考——從劉向的編輯與〈性惡〉的文本結構看》,《中山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等;顔世安《荀子人性觀非“性惡”説辨》,《歷史研究》2013年第6期;王澤春《〈性惡〉非荀子所作新證》,《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等。廖名春則以文獻學和漢語史的證據質疑了僞作説,堅持《性惡》爲荀子作,見氏著《由〈荀子〉“僞”字義論其有關篇章的作者與時代》,《臨沂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由〈荀子〉書“僞”“綦”兩字的特殊用法論〈荀子·性惡〉篇的真僞》,《邯鄲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第二派是訛誤説,以林桂榛先生爲代表,主張《性惡》篇爲荀子所作,但其中“性惡”實“性不善”之訛。見氏著《揭開二千年之學術謎案——〈荀子〉“性惡”校正議》,《社會科學》2015年第8期。第三派是調和説,既承認“性樸論”,也以《性惡》文獻爲真,并在義理上調和“性樸”與《性惡》的矛盾。如兒玉六郎依性僞之分的理路,將《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句釋爲“人之本性易爲惡,其善者乃是矯性”,核心意涵即“人之本性乃是素樸而毫無修飾”。見氏著,刁小龍譯《論荀子性樸説——從性僞之分考察》,《國學學刊》2011年第3期(原刊《日本中國學會報》1974年第26集)、路德斌《“性樸”與“性惡”:荀子言“性”之維度與理路——由“性樸”與“性惡”争論的反思説起》,《孔子研究》2014年第1期;《荀子人性論:性樸、性惡與心之僞——試論荀子人性論之邏輯架構及理路》,《邯鄲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綜上可見,即使在同樣承認“性樸論”的前提下,對《性惡》的文獻問題也各執一詞,同樣用文獻實證或義理闡發的方法,得出的結論也不盡一致甚至相反。這既説明《性惡》是否爲荀子所作,並不構成荀子“性樸論”成立的必要條件,也反映出以思想判準確定文獻真僞的局限性。今本《荀子》經歷了長期曲折複雜的歷史過程,是目前我們唯一可確定的客觀存在,也是對後世思想史産生真正形塑的文本。在没有充足鐵證的前提下,我們還是以尊重現有文本爲宜,或者視作思想史上的“《荀子》”文本。。不過《性惡》的文獻真僞是另外一個問題,兹不具論。在没有足够充分證據的前提下,我們姑且相信《性惡》爲《荀子》之真文獻,抑或説是思想史上的“《荀子》”文獻。《性惡》篇中反復申説“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之理,據鄧小虎統計,“‘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以及類似的用語在《性惡篇》共出現了九次,‘人之性惡’單獨出現的次數則有七次”,他還敏鋭地發現“荀子從來没有使用‘人性’一詞,它用的是‘人之性’”(2)鄧小虎《〈荀子〉中“性”與“僞”的多重結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2008年第36期,第5頁。。言“人之性惡”,是否就意味着説廣義上的“人性惡”或“人性本惡”呢?“人之性惡”與“人性惡”,一字之差,是否藴涵着義理上的重要差别?林宏星先生提供了一種推測意見,他認爲“人之性惡”或只是荀子人性論中的一種特定的“性”,“或僅僅只是其‘人性’論中的其中一義”(3)林宏星《荀子精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頁。。此説可从。“人之性惡”與“人性惡”並不能劃等號,乃在於“人性”的外延要大於“人之性”,説“人之性惡”並不意味着“人性惡”,那麽,更不能説明“人性本惡”,誠如前面的質疑,“人性本惡”,則禮義無所施設,教化自無可能,顯然不合荀意。
依荀子,性有廣狹二義分,廣義之性包含情性與心性諸端,情性、心性均屬於性,所謂“血氣心知之性”,即性有“血氣”與“心知”之别,前者即情性,後者即心性或知性;狹義之性指情性。那麽,被荀子指斥爲“惡”的“人之性”顯然是狹義的情性。荀子説“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惡》)。平情而論,渴求衣食温飽,好利避害,本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維持生命活動的基本生物屬性,荀子自己也坦承:“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4)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49頁。(《王霸》)那麽,此種情性又何以能説“惡”呢?此處須特别注意的是,《荀》書中的“惡”字義項頗爲複雜,兹特拈出兩個最易混淆的義項: 一是言美惡之“惡”,二是言善惡之“惡”。前者語例如“惡願美”(《性惡》),“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王霸》),“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儒效》)等,後者語例如“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 是善惡之分也矣”(《性惡》)(5)同上,第519、259、145、519頁。案美惡對舉,在先秦文獻中頗爲常見,如《老子》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美(王弼本作“善”,郭店本、帛書本、北大漢簡本作“美”)與惡,相去何若”,《莊子·人間世》“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管子·白心》“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等。。從自然層面言,性天生而成,本始材樸,或曰“性樸”,只可謂“美惡”之“惡”,而無所謂“善惡”之“惡”(6)徐克謙師在譯荀子的“性惡”時,不同於“human nature is evil”的習慣譯法(如John knoblock),而將其譯作“human nature is bad and rude”,“bad and rude”顯然更接近“性樸”義,這裏的“惡”是粗駁不好之意,而非像“evil”帶有强烈的倫理意義。見Keqian Xu: Ren Xing: Mencian’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 and Human Becoming, Dialogue and Universalism, Vol.xxv, 2015.2, p.34.。《荀子·禮論》云:“性者,本始材樸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郝懿行注:“‘朴’當作‘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爲絢’也。‘僞’即‘爲’字。……《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即此所謂‘性僞合’矣。”(7)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432~433頁。《説文解字》云:“朴,木皮也。”“樸,木素也。”(8)許慎撰,徐鉉校定《説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14、115頁。喻指樸拙鄙陋,不加修飾之意,正合“美惡”之“惡”義。因之荀子才謂“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人之性正是須“僞”(即禮義師法)的文飾方能使之美。《荀子·性惡》亦云“人情甚不美”,“惡願美”,“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樸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9)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525、519、516、531頁。。即使性質美尚且須賢師良友的薰染,何況“今人之性惡”,故更須禮義教化以美。梁啓雄亦云:“荀子把‘本性’或‘材性’看做質樸的、原始的素材,而稱這種質樸的素材是粗惡的而不是美善的。又把加工於性的人爲後果稱爲‘僞’,這種‘僞’是‘善的’、‘美的’、‘文理隆盛’的。”(10)梁啓雄《荀子思想述評》,見廖名春編《荀子二十講》,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頁。此説不無道理。毋庸諱言,此所謂“性惡”,乃是一般粗駁不純義,並無善惡之惡的倫理義。那麽,倫理之惡又是從何而來呢?荀子言善惡之惡實際上是從社會現實層面講的,在荀子看來,善惡並非先驗概念,乃據社會治亂之後設概念,誠如王陽明《傳習録》所云“荀子性惡之説,是從流弊上説來”(11)王陽明《傳習録》卷下《黄省曾録》,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録〉詳注集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頁。路德斌先生亦嘗指出,與孟子將“善”視作先天具足於個體的“獨善”不同,荀子乃是將“善”視作關係範疇,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約束,共同建構起來的一種和諧狀態。見氏著《荀子與儒家哲學》,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209頁。。且看荀子對善惡的定義:“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 是善惡之分也矣。”(12)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519頁。(《性惡》)如上所揭,自然情性本無所謂善惡,但倘若放縱欲望,順任情性發展,必然導致争鬥,“凡有血氣,必生争心”,引發淫亂、殘害等邪僻之事,出現“犯分亂理”的局面,而這正符合荀子對倫理之惡下的定義:“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從這種意義上説,因情性易引發欲望,而欲望的放縱又容易導致倫理之惡。荀子説: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争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争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13)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513~514頁。
可見倫理之惡實源於“順是”而爲,放縱情性,因之,荀子性惡之内涵,主要分以下兩層:
第一,未加“順是”條件的情性本無倫理意義上的善惡,本始材樸,或曰“性樸”,只能説是美惡之惡,粗駁之惡,而非倫理之惡。
第二,附加“順是”條件後的情性易生倫理之惡,且荀子所謂“善惡”乃是就社會現實效果而言的後設概念,並非孟子所謂先驗的善惡(14)孟子言善惡乃先驗概念,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42、360頁。後句朱熹注云:“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系於人。’”,而放縱情欲,超過禮之限度便是惡,因之逆推情性有趨惡傾向,或如梁濤先生所言“性有惡端可以爲惡”(15)梁濤《荀子人性論辨正——論荀子的性惡、心善説》,《哲學研究》2015年第5期。。
二、 義與辨: 荀子對人的本質界定
無論是從自然層面上講的美惡之惡,還是從社會層面上講的善惡之惡,卻都指向了“性惡”,只不過惡的具體内涵不同罷了。有趣的是,荀子從社會層面談人之性惡,卻也是着眼於人性的自然屬性或生物本能。這説明荀子對人性的現實狀態之論述恰恰是着眼於人性的自然屬性。今天對人性的一般意義上的理解,常表述爲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有機統一,且以人的社會屬性作爲人性的主體論述視角。可見荀子的着眼點和我們今天對人性的主體論述並不盡相同。但這並不意味着荀子未嘗措意人的社會屬性,與我們今天一般意義上的人性論相同的是,荀子也將人的社會屬性作爲人的本質特徵。《荀子·非相》云: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 以其有辨也。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16)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第92頁。荀子這一説法,與亞里士多德的看法頗爲接近,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並非如其師柏拉圖所説是“兩脚而無羽毛的動物”,而是“社會的動物”(social animal)、“政治的動物”(political animal)。
荀子在此將“辨”作爲人禽之别的標誌,用以界定“人之所以爲人者”的根據,那麽,“辨”之了義究竟爲何呢?事實上,“辨”正是心的功能,即“知仁義法正”與“能仁義法正”,其實質就是心之思慮而見諸行動者,是“心爲”與“人爲”的統一。李滌生先生嘗謂:“‘辨’,辨别,辨别是非善惡、邪正等,即孟子所謂‘是非之心’。《解蔽》篇云:‘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心的作用曰意識,有意識才‘有知’,‘有知’才‘有異’。‘異’者,辨之謂也。辨别白黑美惡是感性之知,辨别是非善惡是理性之知。辨是心體的理性功能作用而見諸於行事的,存於心就是判斷力,形於外就是辨説(辨通辯,包括語言、文字)。這是人類異於禽獸先天所獨具的特點。人性惡而能‘化性起僞’者以此,荀子勸學所欲發揚者亦此。”(17)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版,第79~80頁。此誠“辨”之的論。荀子以“有辨”來界定人之本質屬性,“有辨”,簡言之,即有分辨,有禮義道德。《禮記·冠義》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18)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411頁。此即一證也。
值得注意的是,有論者(如Munro. Donald,楊向奎(19)楊向奎《荀子的思想》云:“(荀子)他説人生而有義,這也不是可以解作性善嗎?”原載《文史哲》1957年第10期,收入廖名春選編《荀子二十講》,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頁。等)即據此認爲荀子人性論存在矛盾,指出這並非“性惡”論,更似“性善”論,其實,事情並非如此簡單,這裏的“辨”實際上接近於荀子所謂的“僞”,它的産生固然有賴於先天之性的質具條件,但並非内在於“人之性”(亦即情性)中,實乃後天之“心爲”與“人爲”的努力,這從《非相》後文“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的言説也可得到印證,“辨”並非人性中所固有者,實乃有待於後天禮法之教與聖王之化方可生成。與之相關聯的還有《荀子·王制》一段記載:“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這段引文也常被人視作是荀子認爲人性本善的“證據”,然而這一説法同樣難以成立。何艾克(Eric Hutton)以“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式對其中的關鍵詞“有義”做了頗有啓發的解讀,他認爲“有義”之“有”不能釋作“天生的有”(Having innately),而是“占有”(possess)或“擁有”(own),是一種外在的、後天獲得的“有”,並且爲此種釋讀提供了一條旁證——“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王制》)。他表示這裏的“得”字與“義”相聯用正“暗示着這個‘義’是在人性之外的”(20)何艾克(Eric Hutton)《荀子有一致的人性論嗎?》,見[美] 克萊恩、[美] 艾文賀編、陳光連譯《荀子思想中的德性、人性與道德主體》,東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頁。英文本爲Eric Hutton:“Does Xunzi Have a Consisten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T. C. Kline Ⅲ, P. J. Ivanhoe. Virtue, in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Hackett Publishing, 2000.。我們當然贊同這一解讀。事實上,我們聯繫荀子的“義外”説,也可對這一問題進行通貫的解釋。“義”和“禮”關聯緊密,從某種程度上説,“義外”其實也可視作“禮外”,《荀子·大略》云:“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左傳》桓公二年云:“義以出禮。”《荀子·議兵》云:“義者循禮。”《禮記·樂記》云:“禮近於義。”《禮記·禮運》云:“禮者,義之實也。”在先秦思想史上,“仁内義(禮)外”是一個重要命題(21)相關研究可參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8~389頁;劉豐《從郭店楚簡看先秦儒家的“仁内義外”》,《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王博《論“仁内義外”》,《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2期;李景林《倫理原則與心性本體——儒家“仁内義外”與“仁義内在”説内在一致性》,《中國哲學史》2006年第4期;徐克謙師《孟子“義内”説發微》,《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在孔子那裏,此思想已有所萌芽,《墨子·經下》和《經説下》更是明確提及“仁内義外”説,只不過是對其持批判的態度,尤以《經説下》敘説得最爲詳贍:“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内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内。其爲仁内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後來的竹帛《五行》也接受了這種思想,其開篇就揭示了仁義禮智聖“形於内”的“德之行”和“不形於内”的“行”之分野,郭店簡《六德》云:“仁,内也。義,外也。禮樂,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婦也。”郭店簡《語叢一》亦云:“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禮、樂、刑〕。”“仁生於人,義生於道。或生於内,或生於外,皆有之。”(22)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209頁。至孟子那裏,關於這一問題更是出現了孟、告之争。告子主張“仁内義外”:“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與之針鋒相對,提出“仁義内在”説。綜上可見,“仁内義外”説是當時非常普遍的一種學説,大多是持認可態度,像孟子如是截斷衆流,特表“義内”説者反倒在少數。迨及戰國末世,天下岌岌,荀子爲重樹禮義權威,確立其外在客觀標準,又重新光大“仁内義(禮)外”説,在荀子看來,禮義生於聖人之僞,而非生於人之性,故而“義(禮)外”,這和孟子“義内”説形成區别。因之,《荀子·王制》此處的“有義”亦當放在荀子“義(禮)外説”的思想脉絡中加以理解,並非人性中先天“有義”,更不能以此誤認爲荀子主張人性本善。誠如廖名春先生的論斷:“‘義’‘辨’‘知’不是指‘性’,而是指‘僞’,這並不是説它們與‘性’無關。”“概括荀子‘性’‘僞’關係的理論,就是‘性’中無‘僞’,‘僞’中有‘性’;‘性’中無善,‘僞’中有善。看到‘僞’中有‘性’,就以爲荀子‘性’中有善,其實是‘性’‘僞’不分的結果。因此,絶不能把荀子的人‘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辨也’‘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等‘僞’善説當成其‘性’善説之證。”(23)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1~82頁。
由上討論,“義”與“辨”並非人性所内在固有,即在人性之外,那麽,“人之所以爲人”,雖是荀子對人的本質定義,卻非對人性之“性”的定義(24)需要特别强調的是,此節所言荀子對人性之“性”的定義,是指《荀子》文本中荀子對人性之現實屬性的看法,亦即“今人之性惡”的“人之性”,並非今人語意中廣義的人性概念,或者説是對廣義人性概念中“情性”的定義。因爲如前所述,廣義的人性除了情性外,還包括知性或心性等内容。依荀子,人的本質定義正要靠發用心性以化情性(亦即此處荀子所謂人性之“性”或曰“人之性”)來實現。孟子以心言性,并以此善性爲人之性,故只需“盡其心”“知其性”即可實現人之本質,而荀子以情言性,并以此情性爲人之性,故須以心性化情性,即化性起僞實現人之本質。因此,從廣義的人性論或人論而言,荀子並没有否認人實現本質定義的可能。。孟子所謂人性之“性”的概念即從“人之所以爲人”“人之異於禽獸者”的層面而言,亦即人性之“性”的定義與人的本質定義是一致的,即認爲人的社會屬性才是人的本質屬性,這和我們今天普遍對人性概念的理解也是一致的。但荀子對人性之“性”的定義與對人的本質定義其實是有差異的。荀子所謂人性之“性”的概念不是從“人之異於禽獸者”的層面而言的,恰恰是從“人之同於禽獸者”的維度來説的,即從人的自然屬性來定義的,而他對人的本質定義才是從“人之所以爲人”“人之異於禽獸者”的層面而言的。因之,在荀子看來,“有辨”“有義”是人的本質屬性,但並非人性的現實屬性,“性惡”是人性的現實屬性,但並非人的本質屬性。换言之,人的本質定義與人性之“性”的定義在荀子這裏發生了分離,荀子所謂人的本質定義是從人的社會屬性而言,這和孟子及今人普遍看法較爲接近,而荀子所謂人性之“性”的定義則從人的自然屬性而言,這和孟子及今人普遍看法就涇渭分明。依照邏輯學關於定義的公式:“被定義項=種差+鄰近的屬”,荀子所謂人性之“性”相當於今之人性概念中的鄰近的屬,而非種差。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對“本質”和“存在”的區分或許能爲我們理解荀子的這種定義方式有所助益。在阿奎那看來,“本質”指定義所指示之内容,人的定義中包涵了人性,而“人之所以爲人”就是指人性,從這一層面説,人性即人的本質。但是,他又提出“存在”的概念,“存在”是一切事物的現實,它説明的是一種現實狀態,並進一步提出“純粹的現實”和“複合的現實”兩個概念,前者排除一切可能性與潛能,是絶對化的現實(在阿奎那看來,“絶對現實”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上帝),後者是包含可能性與潛能的現實,是充滿可能性變化的現實(25)劉素民《阿奎那》,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3頁。。荀子所謂“人之所以爲人”是從人的“本質”,人性的應然狀態(“應然”)來定義的,荀子所謂“今人之性惡”是從人性的“存在”,人性的自然狀態或現實狀態(“實然”)來定義的,人性是“複合的現實”(26)徐克謙師嘗言及先秦諸子論“性”的複義性:“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ussion on human nature or ren xing among pre-Qin scholars is not only the inquiring of what human naturally is, but also the inquiring of what human potentially could be and should be. Of course, both are always interwoven with each other and cannot be easily separated. Yet there is always a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and it has perplexed many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Keqian Xu: Ren Xing: Mencian’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 and Human Becoming, Dialogue and Universalism, Vol.xxv, 2015.2, p.30.。如勞思光言:“荀子之論‘性’,即純取事實義。”“乃指人生而具有之本能。但此種本能原是人與其他動物所同具之性質,決非人之‘essence’。”“荀子所言之‘性’,並非孟子所言之‘性’也。”(27)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248頁。我們用孟子或今人對人性的看法與定義去套荀子對人性的定義,實際上已經犯了“以孟套荀”“以今律古”的弊病,並不能真實理解荀子對人性之“性”的看法。
事實上,回到思想的歷史現場,我們不難發現,從鄰近的屬理解“性”是先秦語境的約定俗成義,荀子對人性之“性”的看法非但不是標新立異,反而正好符合當時人們普遍對人性之“性”的看法。“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正名》),倒是孟子違反了當時流行的“性”概念(28)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言:“荀子之論學,雖與孟子相違,然並非超脱於儒家之外,而實爲孔子之正傳,蓋孟子别走新路,荀子又返其本源也。”見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0頁。。先秦人性論的主流實爲自然人性論,如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告子言“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莊子言“性者,生之質也”(《莊子·庚桑楚》)。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禮記·樂記》言“人有血氣心知之性”。此外,《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提及的三種人性論:“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及《論衡·本性》所提及的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的“性有善有惡”等,雖具體説法各異,但都接近於自然人性論,都是以生之自然爲性。這些都是從人性的現實狀態,或曰從“實然”角度來定義“性”的,像孟子那樣從“應然”角度定義“性”者,反而是獨樹一幟,截斷衆流。《孟子·盡心下》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2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77~378頁。孟子坦承“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亦是一種“性”,是人性的“實然”狀態,是關於人性的事實判斷,可見,他對當時普遍流行的對“性”的看法也並非無所知曉或是完全漠視。然而他又説君子並不將其看作是性,而把“仁義禮知”視爲性,這顯然是從人性的“應然”角度與社會屬性出發,是關於人性的價值判斷(30)參見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第343頁。。
因之,上述如公都子所提及的或世碩、宓子賤等人所謂的“性善”和孟子所謂“性善”並非一回事,實際是從“性”的兩個不同層面而言的,前者是從自然屬性而言,從“實然”角度講,後者是從社會屬性或形上意義而言,從“應然”角度講。而前者才是先秦人性論的主流,荀子對“性”的看法無疑接受了這一主流看法(31)參見陳來《竹帛〈五行〉與簡帛研究》,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9~31、88~92頁。路德斌《荀子“性惡論”原義》,《東嶽論叢》2004年第1期。。我們再以此檢視上述所引《荀子·非相》文本,前文説“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依照荀子對“性”的定義——“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性者,天之就也”,“性者,不可學,不可事”,可見“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言人之性,“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這正符合荀子對“性”的定義,“性”是天生而就,“無待而然”的,“是禹、桀之所同也”,這與荀子所謂“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榮辱》)、“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性惡》)的説法也是一致的。因之,前文才是荀子對人性之“性”的定義。而後文“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實際上是荀子對人的本質定義。
三、 人之維度: 作爲過程論的“成人”
如上所揭,性惡並不能完全涵蓋荀子人性論的全部内容,“人之性惡”實指情性趨惡,非謂人的本質爲惡,且情性本身可以被塑造或遷化,它並不妨害人們向善,人可以“化性起僞”,積習師法,最終積善成聖,而“積善成聖同時又展開爲一個化性的過程”(32)楊國榮《善的歷程: 儒家價值體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頁。。荀子説:“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性惡》)“化性起僞”,意味着人憑藉先天質具,將對於“仁義法正”的“知”與“能”由“可能”轉變爲“實能”,由“潛能”轉變爲“現實”,其間存在着不可小覷的間距(33)關於“化性起僞”説或荀子關於善之來源的具體探討,參見筆者《善之歷程: 荀子“化性起僞”説的三重原理》,《邯鄲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兹不贅述。。而這段間距的跨越,於人而言亦有着同樣不可小覷的意義,它意味着人從“自然人”到“文化人”,從“本始材樸”到“文理隆盛”,從野蠻粗陋到道德文明的轉變,無疑是一種“質”的飛躍(34)之所以説是“質”的飛躍,緣於最終所成之“善”並非人性所先天固有者,而是通過後天發用心之知能質具或曰認知功能與理性能力而生成的,這和荀子將“善”定義爲社會“正理平治”的後設概念是一致的,心雖趨善而非等同於善,荀子所謂心只是具有認識善、選擇善之能力的虚心,因之此成善過程非純粹内發式、從小到大的生長,而是内外互動式、從無到有的生成創造。也正因此,在荀子看來,化性的最終完成當是不可逆的,如《荀子》所言“情安禮”(《修身》)、“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不苟》),甚至可以説,是人之爲人得以奠基的必經之途。换言之,荀子人性論實質上是一個過程論,而非本質論。有論者將此軌跡概括爲“性樸(不善不惡)→性趨惡(人之多欲,化性起僞)→性善(以禮分欲,積善成德)”(35)陳光連《論荀子爲性趨惡論者,而非性惡論者——兼論人性發展三境界》,《新疆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第6頁。。這一路徑和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郭店簡《性自命出》所謂“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頗爲相近,都反映了人從“自然人”向“文化人”“社會人”的轉變,只不過荀子强調“性惡”來凸顯禮義教化之重要性與必要性,此亦時勢使之然也。Roger T. Ames嘗指出“人之爲人”(Human Beings)與“人之成人”(Human Becomings)兩個概念的差别,前者是“個體化了的、離散的‘人類’”,後者是“情境化的、關係化的‘成人’”(36)安樂哲(Roger T. Ames)《行於五常: 人之爲人(Human Beings),抑或人之成人(Human Becomings)?》,王中江、李存山主編《中國儒學》第三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筆者以爲,依照儒家的立場,人之所以爲人(Human Beings),正在於人在不斷地試圖成爲人(Human Becomings),或曰人在過程中實現了人本身。因之,從現實層面講,“人”的概念在儒家視域裏其實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同樣,人性也是一個多層次,不斷發展的概念,從實然到應然,從“自然人”向“文化人”或“社會人”(亦即“真正的人”)的運動過程。荀子也認爲人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静止的、完成的概念,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不斷完善的概念。在荀子看來,天生而就的“自然人”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人,這和“二足而無毛”的動物並無太大差别,只有經過了禮義教化成爲“社會人”,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人,這一過程就叫作“成人”,即成爲“完人”(Consummately human),完全之人。當然,“成”本身就藴涵有“完成”之義。《説文解字》云:“成,就也。”古代又以樂曲一終爲一成。《孟子·萬章下》云:“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朱熹注:“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3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20頁。“成人”之“成”不僅是一個昭示結果的形容詞,表示“完成的”人,更是一個昭示過程的動詞,表示不斷“變成”人,不斷成爲“人”,或曰不斷變成“全人”,不斷“成人”。即使聖人亦概莫能外,所以孔子自述其學思歷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38)同上,第54頁。
儒家哲學是一種過程式哲學,儒家智慧是一種重始終的智慧,凡事須講求有始有終,慎始善終。《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經》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戴禮記·保傅》云:“《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馬王堆帛書《五行》云:“君子之爲善也,有與始,有與終,言與其體始,與其體終也。”《荀子·禮論》亦云:“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這在修身層面體現得較爲充分。《荀子·勸學》云: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39)王天海《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頁。
荀子在此展示了人通過全粹之學的誦習而成人的過程。所謂全粹之學,即是禮法。“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楊倞注:“内自定而外應物,乃爲成就之人也。”熊公哲注:“定,謂定力;能應,謂能以有定應無定,以禮法所有,應禮法所無。”(40)同上,第45頁。荀子意謂真正的成人乃是通過禮法的學習達到能定能應,周遍萬物的境界,此與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有相通之處。真正的成人,乃是“全人”,完全之人,成就之人,故曰“君子貴其全也”。《論語·憲問》云:“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朱熹注:“成人,猶言全人。”(4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52頁。在荀子看來,所謂“成人”實際上就是通過積習禮義,最終達到一種“美身”的境界:“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此即一種“禮義化的身體”,亦即修身之最終旨歸,如此情性皆合於禮,能定能應,所以《禮記·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42)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第651頁。
綜言之,荀子人性論實質上是自然人性論,因而也是一種中性的人性論,此點雖爲學者所注意(43)據李哲賢先生的梳理,關於荀子性惡説之意義,中外學者主要有三種意見: 一是“人性本惡説”,二是“人性向惡説”,三是人性是中性的。支持第三種意見的學者主要有鮑國順、徐復觀、韋政通、王邦雄、李哲賢、劉殿爵、陳漢生、Hutton等,詳見氏著《論荀子性惡説之意義與定位》,《邯鄲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另有池楨《荀子性惡論的中性色彩》,《史學月刊》2015年第5期。,但筆者所要强調的是,這種中性並非一潭死水、風平浪静的中性,它充滿張力與變數,動輒有“吹皺一池春水”的可能,因其同時藴含了趨惡的情性與趨善的心性。情、心作爲天生而成的“天情”“天君”,本無善惡,只是荀子以社會效果(“度量分界”)後設善惡概念,故相較而言有了分野,情因有貪利好欲之特徵而易逾越社會規則,故而趨惡,心因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與“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而能使情合於社會規則,故而趨善。合言之,情不謂惡而趨惡,心不謂善而趨善。情中節則善,情過度則惡;用心則善,不用心則惡。情勝於心則惡,心勝於情則善。其關鍵在於以心治情之成敗,而化性起僞的實質正是不斷發用心性以化情性,從而以後天人爲實現人的本質——義與辨,而人的概念亦得以挺立,這一動態過程即荀子所謂“成人”。而“義”與“辨”並非現成,只是善的實現,是化性起僞,以心治情的結果。荀子言化性,而不言變性,意在此過程實系漸變,“狀變而實無别而爲異者,謂之化”(《正名》),“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不苟》),“變言其著,化言其漸”(44)張載撰,章錫琛點校《横渠易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198頁。,故荀子特重“積”,積者亦漸也,所謂“積善成德”(《勸學》)、“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性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