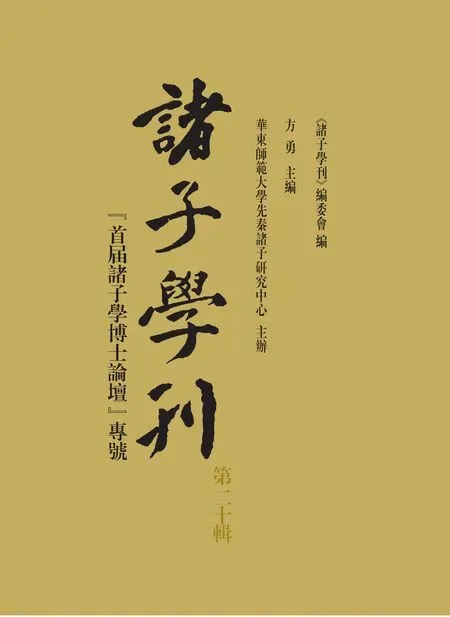性 本 “無 知”
——《莊子》内七篇的人性思想
黄子嫦
内容提要 《莊子》内七篇中並無一“性”字,而外篇開篇即論“性”,且外雜篇中多“性命”“性情”並舉。一般公認内七篇爲莊子本人所作,而外雜篇屬於後學所爲。雖然莊子没有提出明確的人性理論,但其人性思想卻是有跡可循。本文以《莊子》内七篇爲依據,試圖探明莊子所論人性的内涵。
關鍵詞 莊子 人性思想 無知 是非
一、 “生” 與 “性”
《莊子》内七篇中確無一“性”字,但有多處“生”字可以看作“性”字理解(1)下文將提及具體的例子,論證亦隨見下文。,因“性”字本來就由“生”字孳乳而來,且在先秦時期,“性”字和“生”字乃通用字,兩者的概念内涵也有相通之處。
《説文解字》釋“生”的本意爲“進也,象艸木出生土上”(5)許慎撰,徐鉉校訂《説文解字》,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127頁。,用作動詞則爲生長、生育之意,用作名詞則指出生以後的生命。“性”爲“生”的孳乳字,其最初的字義與“生”密切相關,至於具體爲何,這在春秋戰國並不清楚,而告子所謂“生之謂性”,便是嘗試認識“性”爲何物的著名例子(6)參看勞悦强《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9年3月第2期,第 12頁。。諸子百家對“性”的認識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人性的善惡上,孟子與告子,荀子與孟子,分别有一番辯論。
在戰國文獻中,“性”字不但用於指人之性,還用於指物之性,如“水之性”“山之性”“馬之性”“牛之性”等。人之性固然不同於馬之性、牛之性,但人也屬萬物之一,諸子所言的人之性和物之性的“性”,雖然具體的内涵不同,但應該指同一個概念範疇。我們可以從對物之性的論説中求得“性”的基本概念。孟子説:“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7)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見《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37頁。牛山上的樹木因臨近大國而遭到砍伐,失去了原本的蒼鬱之美。雖有日月雨露的滋養而長出幼苗,但又爲放牧牛羊所害,最終整座山草木不生,光秃秃的,人見了以爲從來没有長過樹木。那麽,“寸草不生”是山的本性嗎?此處,孟子所言的“山之性”是指山林在陽光、雨露的滋養下,自然會萌生草木的潛能,可視爲一種“天生而能”,即“本能”。而之所以呈現光秃秃的樣子,則是受到了人爲的干預,以至於使“牛山”失其本性。這樣的推論,同樣適用於水,孟子説:“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8)同上,第331頁。“水之性”是指水之就下的自然本能,而水激而起的狀態則是由人爲的“勢”造成的。這樣的“天生而能”,在人的身上,則表現爲“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9)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上》,第360頁。,孟子稱人這樣的道德本能爲“良知良能”,且以爲“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10)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第331頁。,人性都是傾向於善的一邊的。但是,正如“勢”能改變水的流向,“勢”也能够改變人性向善的傾向,從而使“不善”得以産生。但無論如何,只有向善的一邊發展是更屬自然的,因此孟子説:“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11)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第334頁。錢穆先生説:“人性之趨惡,是外面的‘勢’。人性之向善,則是其内在之‘情’。”(12)錢穆《中國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頁。此處,他注意到了“性善”根植於人心,是屬於内裏的實情。事實上,“性”的字形之所以從心,表示人們言“性”之時不再單純談論物質層面和生理層面上的屬性,而擴展到心理上的本能和精神上的面貌。因此孟子才説:“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13)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上》,第362頁。隨着思想的演變,心靈的作用逐漸被發現和重視。到了荀子,他説:“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又説:“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14)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12頁。喜怒哀樂之謂情,而情爲性之質,則性之中有心理和精神的因素已經很明確了。與孟子將“愛”與“敬”當作人之内裏的實情不同,荀子所謂的“情”指的是喜怒哀樂等情緒,且這些情緒是與欲望相連的,兩者相應而生。在荀子看來,“性”是“天之就”的,自然而“不可事”,因此作爲“性”的實質的“情”和伴隨“情”應運而生的“欲”的存在,也是自然的、必定的,且不可人爲逆轉的,那麽,人所能做的,便是製作禮樂來限制欲望,從而維持社會的和諧,這即所謂的“化性起僞”。孟子主張“仁政”,以爲這是人心之所同的天生的“善端”的擴充和及其在政治上的應用;而荀子主張“禮治”,從而偏向抑制欲望,制天而勝之的一端;不難看出,孟子、荀子的政治主張都是根據不同的人性論基礎而闡發的,也可以推測説,他們對人性的種種論説,或多或少都有爲其政治論説而服務的意圖。
勞悦强先生在《善惡觀以外的孔子性論——一個思想史的探索》一文中談道:“先秦時代的性論,雖然衆説紛陳,言人人殊,但其中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特點,就是有關學説都異口同聲,以‘善惡’這一對道德範疇來認識人性的内容。……戰國後期的儒門弟子無疑都傾向於以善、惡論性。”(15)勞悦强《善惡觀以外的孔子性論——一個思想史的探索》,收録在鄭吉雄主編《觀念字解讀與思想史探索》,臺北學生書局2009年版,第73~124頁。上述孟子、荀子對人性的討論,尤其可以佐證勞先生的觀點。但是,人性畢竟有善、惡以外的内涵,勞先生論文中對孔子性論的闡發,充分彰顯了這一點,當中提及孔子所論人性中還有知性、才性和德性的内容(16)同上。。莊子雖然也是戰國時代的人,但他對人性的論説,似乎也不和孟子、荀子在同一語境中,即他也不從善惡的道德層面談論人性,反而更近似於孔子,沿着孔子性論中知性一面,去闡發自己人性論説,而下文將詳之。
二、 “人而無情”即“人而無是非”
《莊子》外篇《馬蹄》中云:“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17)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31頁。馬的蹄、毛是自然賦予之物,而吃草喝水,舉足奔跑乃是天生之本能,此處的“馬之真性”一如前文孟子提到的山之生木、水之就下,可以推知外篇中所談的“性”也是指不受人爲干預的一種天生且自然的本能和傾向。外篇和雜篇中還談及了人之性,如“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馬蹄》)(18)同上,第334頁。;“請問: 仁義,人之性邪”(《天道》)(19)同上,第478頁。;“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盜跖》)(20)同上,第1010頁。。推之,外篇和雜篇談論“性”,無論是物性還是人性,都將“性”理解爲一種天生的自然本能。然而,在内篇中,莊子卻罕言“性”字,因此莊子有無談及人性思想,若有,則其具體内容爲何,便成爲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勞悦强在《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一文中認爲“内七篇屢言萬物之性,儘管不見‘性’字”,並舉數例爲證,如“惠施所種之大瓠,‘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逍遥遊》),這是大瓠之性。”(21)勞悦强《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第11頁。大瓠外殼之堅硬度不足,與其剖開爲瓢後的容量平淺,無非都是天生如此的一種特性,與上文《馬蹄》中所言馬之“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相比較,無疑二者所指都是物性。因此,“傳本内七篇雖無‘性’字,但‘性’之概念無疑已經出現其中,而且還有相當關鍵的地位”(22)同上,第12頁。。
莊子既然談及了物性,那麽談及人性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同理,莊子談人性,也可以不著一“性”字。至於他爲什麽不使用“性”字的原因,今日已難以知曉,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他曾使用與“性”字密切相關的“生”字來談人性。《德充符》中載常季問仲尼:“彼(兀者王駘)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回答:“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他還舉了兩個例子來進一步説明:“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23)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92~193頁。王駘之學,要在爲己,即“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是一個内自修的過程,那麽常季疑惑,既然要在自得,那麽學者們何必要聚集在王駘的周圍跟從學習呢(24)錢穆云:“常季之意,殆如陽明之倡良知,人人皆可反己自得,則不必聚於王駘之門也。”見氏著《莊子纂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頁。?根據仲尼的意思,唯有静止不動的水才能清晰照物,就如同要知道什麽是“正”青色,就必須去參照無論冬夏變换都不改其“青青”的松柏。同理,要知道何爲“正性”,就須去參照天地間獨一無二的舜的“正性”;要知道何爲“常心”,則必須到王駘的門下,去參照他的“常心”。此處,“正生”解釋爲“正性”,理據有二: 其一,“正生”的“生”是一個名詞,應當作“生命”解。雖然没有從“心”(忄)字偏旁,但若將其純粹理解爲一肉身的生命,即具體説法爲“身”,亦稱“形”(肢體)的生命狀態(25)參考勞悦强《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第12頁。,那麽“正身”或“正形”當作何理解呢?似乎與莊子不甚看重“形骸”的觀念相悖。因此,此處的“生”不應當只從生理的層面上去理解,而應該考慮心靈的因素而解釋爲“性”;其二,“正”字作“性”字解在義理上是通的。鍾泰先生説:“‘正生’猶正性……言舜能正其性,而衆物之性亦正。”(26)鍾泰《莊子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頁。勞悦强先生也持此説,“冬夏長青,是松柏在植物中的獨特之性,對比而言,舜與衆不同的‘正’自然也是他的‘性’,‘正生’無疑即是‘正性’。舜之‘正性’可以正衆人之性,猶如衆人鑒於止水,以顯現其真性。”(27)勞悦强《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第12頁。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用“止水”而不是“流水”來譬喻松柏之“冬夏青青”(即長年保持青色)、舜之“正性”和王駘之“常心”,意味着此三者都具有穩定恒常乃至不變的性質,其中,“常心”之“常”字也能輔助説明這一點。此外,“正性”和“常心”之間有着難以否認的某種關聯性。方潛曰:“以知得心,明心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見性也。”(28)錢穆《莊子纂箋》,第46頁。按方潛的意思,得所謂的“常心”則能够見性,那麽“常心”是穩定恒常的,“性”也便是穩定恒常的。此觀點推諸外、雜篇亦凖。雜篇《庚桑楚》曰:“性者,生之質也”,以“性”爲材質,似乎暗示“性”具有穩定不變的特性(29)《荀子·禮論》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勞悦强先生認爲荀子説法與《庚桑楚》同,見勞悦强《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該文首次宣讀於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七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下册,第529頁。。外篇《馬蹄》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30)郭慶藩《莊子集釋》,第334頁。,此處的“常性”指的是民所受於天之“性”,一個“常”字即説明“性”是穩定恒常的,並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一方之民,有其一方之“性”,並因之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禮記·王制》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31)鄭玄注《禮記》,收入《四庫備要》第四册,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版,第45~46頁。由此可見,“性”之穩定而恒常,是莊子對“性”的認知之一;“性”與心密切相關,是莊子對“性”的認知之二。
根據第一節所論,孟子、荀子都認可人性中固有心理和精神的因素,在孟子處爲“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亦即所謂的“四端之心”。在荀子則處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情”爲“性”之質。而荀子所謂“情”,是“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在荀子看來,喜怒哀樂等“情”是天生而自然的,爲“性”中所固有的内容。可是,在莊子看來,雖然“性”與“心”緊密相關(32)勞悦强認爲:“‘性’是材質,心是材質化爲材用的樞機。”參見勞悦强《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第2頁。,但他卻説“人而無情”。《德充符》中有一段記載他談“人而無情”,莊子似乎認爲“情”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内容: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無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33)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20~223頁。
惠施之所以問莊子“人故無情乎”,是因爲“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34)同上,第320頁。,原文並無提及惠施所言“情”的内涵。但惠施擅長名理之學,他對“情”的理解,很有可能從名理論説的角度出發的,而他的言論似乎也佐證了這一點。他説,既然有了人這個稱謂,必然有與之對應的人的實情,所謂“名者,實之賓也”(35)同上,第24頁。。一般先有了物實際存在的實情,再産生指稱它的名。倘若這世上本就無這一物,又怎會有與之對應的名呢?所以,既然有了“人”這個指稱,就必有與這個指稱所對應的實情(36)西方的分析哲學認爲名是可以没有與之對應的實指的,與惠子想法不同。。若没有與“人”這個指稱所對應的實情,那怎麽可以稱之爲“人”呢?
站在惠施的立場和角度,他的推論似乎無可指摘。然而莊子不同意於惠施,並不是因爲他反對惠施的觀點,相反,他是認同惠施的觀點的,因而他説“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便可“謂之人”,人確實有與生所俱來的實情,至少莊子認同人的肉體生命中的“形”(肢體)與“貌”(相貌)是與生俱來的一種實情,亦是無可否認的一種非常直觀的實情。但是,莊子説“人而無情”,及他對“情”的理解,並不是從名與實的角度出發的,他自有他的語境而别於惠施。莊子所説的“情”,是“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中的“情”,是與“形”相對而言的“情”。而惠施所談的“情”是與“名”相對應的“情”,這個“情”可以指人之情,也可以指物之情,不管人或物,只要有“名”的存在,便有其“情”的“情”。
對比之下,莊子關心的問題與惠施不同。莊子説“道”賦予了人“形”與“貌”,但卻一丁點也没有提及“道”同時賦予了人“情”,即從人之所以爲人的形上角度説,“情”固屬於“人”這一點並不是天理所當然的,即有關於人的實情中,客觀存在的形與貌是無法否認的,但莊子所談的“情”的存在,並不像形與貌的存在一樣不可置疑。他本人便置疑“情”是人生而固有的這一點。因而莊子關心的問題是,人性中是否固然有“情”的存在?我們知道,他的主張是“人而無情”,那麽他所談的“情”到底是什麽呢?
他説:“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主流看法,“非”字連下讀,但根據郭象及成玄英的看法,“非”字是該連上讀的,讀成“是非”,於是,莊子所説的“情”,便指的是“是非”。郭象云:“以是非爲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成玄英疏云:“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若無是無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37)郭慶藩《莊子集釋》,第322頁。郭象和成玄英將“非”字連上讀,從文法上來説並無大問題。但只有文法上的支持是不足够的,“非”字能不能連上讀,“情”能不能解釋爲“是非”,關鍵還要看將“情”解釋爲“是非”這一觀點是否能够在内七篇的整體思想系統中成立。
根據郭、成二人的説法,“是非”可延伸爲“彼我”“好惡”“憎嫌”等對立的範疇,那麽此時莊子所謂的“情”,便有點類似荀子所謂的“情”了,但區别在,荀子是直接以“喜怒哀樂”等情緒爲“情”,而莊子是以“是非”爲“情”,因“是非”的存在,才産生的“喜怒”“好惡”等情緒,意即若没有“是非”,便没有“喜怒”與“好惡”了,如此,才可以做到“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勞悦强先生認爲,此處的“生”當作“性”解。他説:“莊子此處所言,同樣身與生分言,益生實即益性。好惡本身並非不可取,但執著好惡,心未能虚若明鏡,應而不藏,不合自然之道,則内傷其身,亦增益其性。”(38)勞悦强《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第13頁。既然好惡不但傷身,而且益性(39)有關好惡傷身、益性的更詳細論證請參看上文。,似乎“情”更不應該是“性”所固有的内容了,即“情”爲“性之質”這個説法在莊子的理解中的不成立的。如此説來,爲什麽荀子所認爲的喜怒哀樂等“情”爲“性”的固有内容在莊子的思想系統中卻不成立呢?若將“情”解釋爲“是非”可以成立,莊子爲什麽會認爲“是非”是“情”呢,以及“是非”爲什麽不是“性”中固有的内容呢?
既以“是非”爲“情”,且“是非”“彼我”這些概念都曾在《齊物論》中被詳細論説過,如果我們認爲内七篇是同一人所爲,且能構成一思想連貫且互通的整體,那麽,“人而無是非”這一觀點是否成立,還應該回到《齊物論》的語境下去更進一步理解。
三、 “人而無情”即“人而無知”
在《齊物論》中,莊子疑惑喜怒哀樂等情緒的生發來源,他説:“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種種情緒更迭,旦暮不同,代變之快,實在讓人摸不着頭腦。因此莊子説:“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胡遠浚曰:“自‘大知閑閑’以下,言心之種種名言狀態,皆如幻而有,生滅變異,更歷旦暮,而卒莫得所由起。今欲追變異生滅旦暮之故,其乃由心生乎!所謂‘自心還取自心’也。”(40)錢穆《莊子纂箋》,第12頁。胡遠浚直接將“種種名言狀態”的生滅變異推導到“心”的發用固然是正確的,因莊子最後確實説“爲使者”即“真宰”也,且下文緊接着就談“真宰”(“真君”)與百骸、九竅、六藏等的關係,即“心”與“形”的關係。需要註意,種種情緒的萌發固然與“心”有關,但其生滅變異之快,連莊子都覺得它們的存在只是些夢幻泡影,似乎很難與上文提及的“常心”或者“常性”對等起來。此外,胡遠浚的推導跳過了“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這一“是非”(即“彼我”)影響情緒的關鍵一環。若非先得了“此”,則不會有與“此”相對立的“我”,若非有“我”,則心無所取,即心不會産生是非,也不會因是非産生好惡與喜怒等。在莊子看來,荀子所認爲的喜怒哀樂等情緒,其實是因是非而産生的,看似天生而自然固有,然而,若無是非,則喜怒哀樂亦不復存在。因此,與其以喜怒哀樂爲情,倒不如以是非爲情。
“是非”屬於莊子所言的“小知”裏的範疇,而“小知”是會損害人的心性的。莊子説:“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41)郭慶藩《莊子集釋》,第51頁。成玄英疏云:“閑閑,寬裕也。閒閒,分别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虚淡,無是無非,小知狹劣之人,性靈偏促,有取有舍。有取有舍,故閒隔而分别;無是無非,故閑暇而寬裕。”(42)同上。“大知”是無是無非的,而“小知”則有取有舍。莊子説,事“小知”的人其實都在“司是非”:“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與心鬥。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若一直生活在這樣充滿“小恐”“大恐”,且争强好勝的“心鬥”狀態,那麽人的心性將受其害。莊子言:“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43)同上。若主是非,並執著於爲其争强好勝上,那麽便會勞神損精而使得心神日漸消殺,沉溺於此更是會使之無法復原,最後所剩的便是一顆“近死之心”。
既然如此,“小知”或者“是非”是“心”所固有的嗎?是屬於“常心”的一種情況嗎?由此可以見到人之“性”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是非”屬於“知”的一種,而“知”的産生離不開“心”的運作。莊子説:“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44)郭慶藩《莊子集釋》,第56頁。有成心才有是非,没有成心就不會有是非,若没有成心,卻有是非,就如同今日出發去越國但昨天就已經抵達了一樣是絶對不可能發生的事。人的成心就像《齊物論》開篇南郭子綦所提到的天地間千差萬别的或自然形成、或人爲開鑿的不同的孔洞,“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45)同上,第46頁。,風一吹過,就各因其孔穴形狀的不同而發出不同的聲音。類似的,對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因各自成心的不同,便會投射出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就像不同的聲音是不同的孔洞所“自取”的一樣,不同的意見和觀念,乃至“是非”(即互相對立的觀點),也是不同的成心所自取(46)言論與“人籟”的隱喻關係可見於“夫言非吹也”一句。王闓運曰:“言,人籟。吹,天籟。”見錢穆《莊子纂箋》,第14頁。。莊子説:“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即便是愚妄之人,也有成心,也不例外地會師其成心而形成“是非”,“心以爲是,則取所謂是者而是之,心以爲非,則取所謂非者而非之,故曰心自取”(47)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2頁。。然而,卻不醒悟“是非”本非實有,固執於“是非”,此便是“以無有爲有”。即便是聰明睿智的大禹,若執著於是非,也不可能得到真知,又何況是普通乃至愚笨的人呢?錢穆按曰:“世人皆堅執有是非,而不悟其生於各自之成心,我無如之何也。”(48)錢穆《莊子纂箋》,第14頁。
是非産生於成心,是成見的一種。莊子説:“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成玄英疏曰:“於此爲成,於彼爲毁。如散毛成氈,伐木爲舍等也。”(49)同上,第17頁。將散亂的毛髮編制成氈,既是一種“成”,也是一種“毁”,因成了氈就意味者無法再成任何别的物,比如説毯。同理,執著於“是”,則於“非”爲毁,執著於“非”,則於“是”爲毁,二者都已經偏離了事物的本真模樣,於是乎“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50)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4頁。。因此,“是非”是“道”之“成”與“毁”,而非“道”本身。同理,“成心”是“心”之“成”與“毁”,而非“心”(常心)本身;對“性”的善、惡道德判斷(此即一是非)亦是“性”的“成”與“毁”而非“性”的本真。“是非”並非“道”所固有;“成心”亦非“心”所固有,“善惡”的分辨也非“性”所固有。那麽,按照莊子的思路,因是非分辨而産生的喜怒哀樂、怨恨憤怒等多種情緒,自然也非“性”所固有了。
根據上兩節的論證,莊子以爲人的本性其實是“無情”,即“無知”的,也就是説人生之初所固有的智識,本來便没有那麽多的細緻的分辨和是非判斷及取捨,而處在一種“混沌”的狀態。莊子對人的“無知”而“混沌”的狀態的第一次正面描述見於齧缺和王倪的對話: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51)郭慶藩《莊子集釋》,第91~92頁。
齧缺的第一個問題,你知道物與物是混然無分的嗎,王倪反問道:“我怎麽知道?”人是有了知以後,才知道何爲物,何爲我,何爲物和我的區别。若物與物果真混然無分,那麽這一狀態下的人,是不知有物,不知有己的,分辨物與我的意識則根本不存在,更不會去判斷物我是否“同是”。若一旦有了分辨的意識,那麽物我便不再是混同一體的了。因此,若物我果真“同是”,那麽王倪是根本不會有分辨物我的意願的,没有意願則自然不會去判斷,自然也不會有能够回答齧缺第一個問題的“知”(小知)。齧缺能問出這個問題,就已經證明,他並没有處在一個物我混同無知的狀態而逐漸開始進行分辨、判斷和取捨。因而王倪的三問三不知,似乎是在嘗試阻止齧缺這種偏離本性的認知趨向。接下來,王倪用“孰知正處”“孰知正味”“孰知正色”三組例子來説明,其實人也一樣,“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對於仁義、是非的判斷,各人無非都是“自我觀之”,都是從各自成心的孔洞出發,那麽孰能知道其“正”呢?無非勞神損精,傷身益性罷了!由此,不難想到“混沌”被開了“七竅”卻最終死亡的故事,莊子以這個寓言的方式來告訴我們,認知上執著於是非,而脱離了“混沌”的狀態,對性命之保全是有害無益的。
四、 減殺: 對“無知”的養護
在莊子與惠施圍繞“人而無情”的對話的結尾,莊子批評惠施説:“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52)同上,第222頁。按莊子的意思,惠施以辯堅白爲事,無疑是“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而“以好惡内傷其身”。成玄英曰:“惠子未遺筌蹄,耽内名理,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説,是以形勞心倦,疲怠而瞑者也。”(53)同上,第223頁。惠施勞神損精所從事的,是分辨名理之事,如對堅白的辨析,且他以之爲志業,連行走、坐臥都不離對名理的言談和辯説,因此不但形勞,而且心倦。惠施之辯堅白,是執著於是非的表現,莊子在《齊物論》中就曾批評他道:“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54)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4~75頁。蓋昭文、師曠、惠子三人各以其説爲是,而欲明己説於持異見的人,從而證己説之爲是。但他們並没有意識到,己説便已是“成説”,本身就“不明”,又如何能以“不明”去明另一個“不明”呢?因此,“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55)同上,第56頁。,此外還勞神損精,内傷其身。
由此,莊子在《養生主》開篇即談正確求知對“全生(性)”(56)此處“生”讀作“性”,主要原因是前文已有“保身”,“身”即指人的肉身的生命,而後一個“全生”所言應該不與“保身”所言重複,因此很有可能讀爲“性”。更具體的義理上的論證,請參考勞悦强《虚體與德性——〈莊子〉内篇之内聖思想》,第12~13頁。的重要性:“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知是無窮無盡的,但人的生命卻是有窮盡的。若貪得無厭,以多爲得,那麽便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此外,在内七篇中,他還談及以“減”爲“益”的修行方法,如顔回之坐忘:
顔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57)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82~285頁。
顔回以每一次的忘卻爲己身的進益,最先忘的“仁義”可理解爲就名或物而言的“仁義”(58)胡遠浚言,見錢穆《莊子纂箋》,第68頁。,因此“忘仁義”,即是忘物。“禮樂”重在身體力行,因而“忘禮樂”,可以理解“忘身”(59)同上。,而最後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則是脱去形體,及泯滅一切的與形體有關的感官知覺,即是“忘我”。“身”若指形體,即生理上的自我,那麽“我”便指的是形體之内的心靈和精神上的自我,此處類似於《齊物論》開篇南郭子綦所言的“吾喪我”中的“吾”和“我”之别,後者的“我”偏重於指“心如死灰”的心靈層次上的“我”而言。成玄英疏言:“墮,毁廢也。黜,退除也。雖聰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聰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毁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60)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85頁。此處,成氏言“聰明之用,本乎心靈”,因此“墮枝體,黜聰明”,實際是指停止妄用心智之聰明。這與莊子在《齊物論》所談的“吾喪我”,《養生主》所言的“官知止而神欲行”,以及《人間世》所言的“心齋”皆能匯通吻合。南郭子綦正因“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才能超越感官之聽覺,而聽到使萬物得以自己的“天籟”(61)同上,第49~50頁。;庖丁正因能够止官知而目無全牛,才能看到牛之内理,從而使刀刃“以無厚入於有間”(62)同上,第119頁。。
孔子教導顔回“心齋”的方法,説: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63)同上,第147~152頁。
此處的“齋”,不同於祭祀中“不飲酒、不茹葷”這樣針對人的生活飲食行爲的齋戒,而是一種針對人心的智識的齋戒,其目的在使人之心能够“以虚待物”,從而“虚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64)同上,第148頁。。虚者,不是實有,也不全無,是介於有無之間的“似有若無”。然而,與其説“虚”偏向於“有”,莊子更願意説“虚”偏向於“無”,因而他説常人只知道“以有翼飛”和“以有知知”,而不懂“虚”的道理,即“以無翼飛”和“以無知知”。耳朵、心知的功能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我們一味信任它們,便是不知道其有所止,也不可能真正地利用好它們。因此莊子才説,我們要“無聽之以耳”,也要“無聽之以心”,而要“聽之以氣”,只有氣才是虚的,這就類似於上文顔回坐忘一則中所言的停止心知之聰明的使用,亦此處的“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李頤曰:“率其聰明而通於内,屏其心知而外之,虚之至也。”(65)李頤語,見錢穆《莊子纂箋》,第37頁。
此處的“虚心”,可與莊子在《齊物論》中所言的“有蓬之心”“成心”和“近死之心”相對而言。心中無知之時,一切渾然無分,此爲真正的融合而無有間隙;當心中有知,而有言“萬物一體”之時,已是自覺“萬物”而有間隙,知我和外物有天然之别,所幸心還無成見,還能不離萬物。而當心有成見之時,已是去“無”遠矣。正如莊子所言:“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66)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9頁。一有成見,便有成心,成見還會再生成見,無窮而無休止。此外,“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67)同上,第51頁。這些情緒和作態也會隨之而生。莊子一開始並不明白這些情緒和狀態從何萌生,但隨即他了悟道:“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有了“彼”,便有“我”,“彼”和“我”皆是已成之見,皆是“有”,自“有”則可“適有”,且無窮無盡的,無所可止。所一開始便没有“彼”,也便不會有“我”,自然不會自“有”生“有”,從而使得意見紛繁而複雜,而充塞於心。
莊子在多處提到人心若充塞是非及好惡的不良影響。他在《齊物論》“朝三暮四”的故事中説道“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68)同上,第70頁。,因有了好惡的判斷,才有了喜、怒情緒的濫用。《人間世》中談起溢美和溢惡之言時,也説“忿設無由,巧言偏辭”(69)同上,第160頁。。過實的巧言和失當的偏辭本身就已經包含了是非、好惡的判斷,由此才引發了忿怒之作。可見,情緒的失控往往是由是非好惡的分辨所造成的。有了成見而不自覺,才有了成心,有了成心故不能“和之以是非”,從而生發了喜怒哀樂等情緒而最終“内傷其身”。
歸根結底,問題的弊病在偏離了“無知”的本性,所謂“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心知愈來愈複雜,煩惱越來越多,因而莊子説:“以刑爲體,綽乎其殺也。”(70)同上,第234頁。王闓運曰:“殺減之乃寬綽也。”(71)錢穆《莊子纂箋》,《錢賓四先生全集》(6),臺灣聯經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頁。陸長庚曰:“老子云:‘爲道日損。’”(72)同上。當去除了不必要的是非好惡的分辨,正如顔回那般忘仁義、忘禮樂,離形去知,才能最終停止使用心知的聰明而回歸與萬物一體而不自覺的“無知”狀態之中。
結 語
本文先從文字學的角度,説明了《莊子》内篇中釋“生”爲“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這是支持莊子雖無明確提及“性”字,但確實有在談論人性内容的訓詁證據。再者,從梳理春秋、戰國時代諸子談論人性的思想脉絡來説明,莊子思想雖不主善、惡的分辨,但這並不影響他對人性的理解,因其人性論説可以存在善惡以外的人性内涵。接下來,筆者從人性的内涵、養護本性的修養方法兩個方面,論證了莊子所持的性本“無知”這一觀點。
莊子以“無知”爲人性之本,因看到心知的複雜發展、使用對人生所帶來的危害以及在社會層面引發的争鬥與混亂,從而主張保守人性“無知”的本真狀態,這也是他“養生”論説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