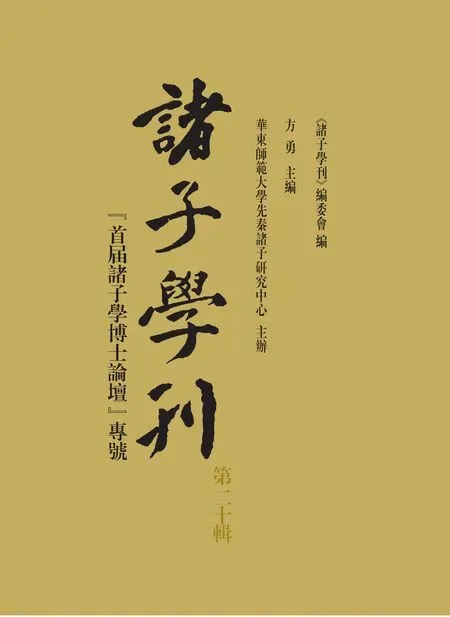楊慎《孟子》學述論
孫 廣
内容提要 楊慎以考據著名,但其考據方法尚不成熟,因而他對《孟子》文本的考據得失相參,還存在抄纂前人成果的情況。在義理闡釋方面,他對“配義與道”的論述,體現了他的“理氣一元論”,且相比同時的“理氣一元論”而言,楊慎的説法將這一理路追溯到了程朱本身,爲“理氣一元論”的廣泛接受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合性情論”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提出了“情”由“外染”造成的説法,既爲晚明肯定“人欲”的價值開闢了先河,也爲黄宗羲、顔元等注重“習染”埋下了伏筆。他對孟子的評論,與宋代“非孟”學者的言論極爲相似,顯然是深刻地受到了“非孟”思潮的影響。不過,他論李覯並非不喜孟子,似也有爲自己的“非孟”言論辯護的原因。
關鍵詞 楊慎 孟子 考據 理氣一元論 合性情論 非孟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是明代最爲博學之人,《明史》本傳謂:“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1)張廷玉等《明史·楊慎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083頁。楊慎是明代學風轉變的關鍵人物,其學術方法、思想,既有對前代的繼承,也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研究楊慎的《孟子》學,不僅可以瞭解楊慎本人的學術思想,更可以窺見明代《孟子》學發展的進程。他對《孟子》的研究,集中於《升庵經説》中涉及《孟子》39條,其他地方也有零散的條目,但比較少見。林慶彰先生説:“楊慎於《論語》、《孟子》二書,闡述義理的條目甚多,如〈夫子與點〉、〈齊桓晉文〉、〈用我吾爲東周〉、〈予欲無言〉、〈立賢無方〉、〈論性〉諸條皆是,唯皆無新意。考證性的條目,則頗能糾正朱子之錯誤。”(2)林慶彰《楊慎之經學》,林慶彰、賈順先編《楊慎研究資料彙編》,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598~599頁。標點以原書爲凖。林先生“一言以蔽之”,自有依據,卻使得後來者不再研究楊慎的《孟子》學,不能不説是一個遺憾。以筆者所見,僅陳育寧《明前中期孟學研究》一文中辟有“楊慎的孟學研究”一節專論楊慎的《孟子》學研究(3)陳育寧《明前中期孟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然該文較爲簡略,許多論述未及深考。職此之故,本文擬對楊慎的《孟子》學研究情況作一番探討,庶幾有愚者千慮之一得。
一、 得失相參: 楊慎對《孟子》文本的考據
楊慎是明代考據學的先鋒人物,對他的考據學的評價,明清學人注重其考據成果是否有價值,近幾十年來的學者則注重其考據方法對清代考據學的影響。職此之故,自陳耀文《正楊》始,對楊慎的考據評價都比較低,以其考據成果多舛誤也;自林慶彰先生《明代考據學研究》始,對楊慎的考據評價都比較高,以其發後世考據學之端也。從其對《孟子》的考據情況來看,不論是成果還是方法,都可謂是得失相參,無可厚非,亦未足過許。而且,楊慎的一些考據,還存在因襲前人成果的情況。
(一) 考 據 有 補
楊慎家學深厚,又穎悟博學,他對《孟子》的考據,有一些頗能够“發前人所未發”,對於《孟子》研究來説,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最能體現楊慎《孟子》文本考據工夫的,莫過於他對“氓”字的解釋。“願受一廛而爲氓”條云:
氓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反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新氓之治。”《注》: 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甿之癡癡,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於外州者也。《孟子》:“許行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悦,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4)楊慎《升庵經説》,王文才、萬光治主編《楊升庵叢書》第1册,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頁。按,此書句讀多有錯誤,凡可讀者一仍其舊,如不可讀則徑改,下文不復説明。
楊慎此處説“氓”爲流亡之民,一是據字形從亡從民,二是據《周禮》《詩經》《孟子》等經典中“氓”字出現的語境分析其義,可謂有理有據。段玉裁注《説文》,亦據《孟子》“天下之民皆悦而願爲之氓”謂“‘氓’與‘民’小别異。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故字從民亡”(5)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633頁。,與楊慎之説如出一轍,而反嫌例證略少。梁啓超謂博證之法,“乾嘉以還,學者固所共習,在當時則固炎武所自創也”(6)梁啓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然則如楊慎等明代學者,實早已發其端倪,只是尚未能如顧炎武一般有自覺的方法論意識罷了。除此之外,如“梁惠王遺事”一條,雖未發表己見,卻有助於人們瞭解梁惠王發問的語境,更可以據此考證孟子適梁的具體時間。又如“庸字解”條:“附庸之國: 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 庸,廧也。杼,亦廧也。”(7)楊慎《升庵經説》,第393~394頁。雖然“庸”訓爲牆早有明文,但將其與“附庸”聯繫起來,卻是楊慎首發,對於闡明經旨,亦有幫助。
(二) 考 據 疏 漏
《升庵集》提要謂:“慎以博學冠一時……至於論説考證,往往恃其强識,不及檢核原書,致多疎舛。又恃氣求勝,每説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8)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39頁。這句評語,可謂正中楊慎之弊,在他對《孟子》的考據之中,也多有體現。
首先,楊慎對《孟子》的考據錯誤,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爲他没有核對原書。如“置郵傳命”條,楊慎引《説文》作:“驛,置也。”(9)楊慎《升庵經説》,第384頁。因以爲有遲速之别。然而《説文》實際作:“驛,置騎也。”段注:“言騎以别於車也。”本是指車馬之别。楊慎未細考本文,漏去一“騎”字,因而致誤。其“一夫”條引尹焞事,作:“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10)同上,第382頁。考諸《和靖集》,此句實作“德壽問某”,非宋高宗所問,後文才是宋高宗所問。楊慎之前,未見誤引者,而楊慎之後,如陳耀文《天中記》、郭良翰《問奇類林》、孫奇逢《四書近指》、黄宗羲《宋元學案》均引作“宋高宗”,其貽誤後學,亦可謂深遠。
其次,楊慎“恃氣求勝”,因而他的一些考證,顯得過於“好爲異見”。如其謂“略”字義乃“聚土爲封”,以趙岐注《孟子》“大略,大要也”爲謬,殊爲舛誤,陳耀文《正楊》已駁之,甚明。又如“七十而耡”條,楊慎云:
《説文》引《孟子》“七十而耡”。《周禮》:“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鄭玄曰:“耡,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録·街彈碑跋》云:“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耡,音助。又《周禮》:“以興耡利甿。”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又《齊民要術》引諺云:“濕耕澤鋤,不如歸去。”(11)同上,第386~387頁。
按,“起民人令相佐助”本是杜子春解《周禮》之説,並非楊慎發明,楊慎的創造在於將這一説法移植到《孟子》“七十而助”之上。這一説法對《周禮》來説是否準確,姑置不論,但對於《孟子》來説,卻顯然是不對的。《孟子》原文“徹”“助”“貢”並列,均指税法,其義甚明。且也,雖然《説文》引此作“耡”,但其義仍是“耡,耤税也”。楊慎之説雖有其依據,但完全不顧《孟子》文本,故致此誤。又如“轉附朝儛”條云:
轉附、朝儛,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即此地與?(12)楊慎《升庵經説》,第383頁。
轉附、朝儛,趙岐注云:“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13)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819頁。朱子《集注》與絶大多數的注本均作此解。另因顧野王《輿地志》云:“,水名。”亦偶有引此以解“朝儛”爲水名者。淳于髡語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云:“綿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綿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14)同上,第5999頁。朱子並同。歷來注家,皆以轉附、朝儛爲山名或水名,並未見有論其爲郡邑者。楊慎徑指轉附、朝儛爲邑名,並無任何依據,不過據“朝歌”想當然爾。如此之類,其“恃氣求勝”之態畢見矣。
(三) 抄纂前人成果
張仲謀先生明確指出:“楊慎的《詞品》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因襲前人著述的現象。”(15)張仲謀《楊慎〈詞品〉因襲前人著述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4期。不僅僅是《詞品》,楊慎對《孟子》的一些考據也存在因襲前人著述的情況。其“變置社稷”條云:
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杜,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故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自齊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爲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方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16)楊慎《升庵經説》,第398頁。
然考之《孟子注疏》,僞孫奭疏云:“犧牲既成以肥腯,粢盛既成以精絜,祭祀又及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爲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亦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17)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第6037頁。僞孫奭疏認爲“變置社稷”是“更立有功於民者爲之”,並舉了商湯“以棄易柱”而變稷神之事來證成之。對比楊慎之説,不僅僅是在觀點上相同,就連論據都同樣拿“以棄易杜(18)按《左傳》,“杜”當爲“柱”,點校者失之。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503頁。”之事爲證。所不同者,僞孫奭疏乃舉其事,而楊慎則徵引典籍原文耳。楊慎《升庵經説》中有“孟子注”一條,還在其中調笑僞孫奭疏寫的西施是“摇錢樹”,可見他確實是讀過《孟子注疏》的。然而此處如此雷同,卻毫不提及孫奭之名,實在難免剽竊之嫌。另如“舜避堯之子”條,也是因襲李覯《常語》(詳見下文)。如此之類,雖然主觀上可能是由於偶然遺忘、混淆,但所呈現的結果,卻不能不引人訾議。
二、 “理氣一元”與“合性情”:楊慎對《孟子》義理的闡發
楊慎少王陽明十六歲,正當陽明心學對程朱理學發起挑戰的時代,學術界、思想界的狀態非常活躍。楊慎在參加“大禮議”時,還號稱“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説也”(19)張廷玉等《明史·楊慎傳》,第5082頁。,但被貶雲南之後,他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其著作中屢見抨擊程朱的言論。當然,他也不是陽明的追隨者,其著作中也有不少訾詆陽明心學的言論。他的學術思想,是非常具有獨特性的。這一點,通過他對《孟子》義理的一些闡發,也能够看出來。
(一) 理氣一元論
朱熹“是正式提出和全面系統討論與解決理氣關係的第一人;他比前人更清楚、更明白地論證了理與氣的區别”(20)郭淑新《論朱熹在理氣論上的創造和貢獻》,《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2期。,朱熹在理氣關係上“建立了一套以理氣二元論爲核心的哲學體系”(21)高海波《宋明理學從二元論到一元論的轉變——以理氣論、人性論爲例》,《哲學動態》2015年第12期。。在朱熹的語境中,實際上是“理”附着於“氣”,雖然不可偏廢,但二者仍然是不同的事物,因此朱熹説:“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22)黄宗羲《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512頁。在明代中晚期,例如王守仁、羅欽順等學者,已經在質疑“理氣二元論”了,並嘗試提出“理氣一元論”。劉宗周就評價陽明是“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静,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絶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23)黄宗羲《明儒學案·師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7頁。。
楊慎所持,也是“理氣一元論”,但與同時代的王守仁、羅欽順等人不同,楊慎將“理氣一元論”追溯到了程朱,認爲程朱原本就是持“理氣一元論”的。“配義與道”條云: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卻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説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滚出來。”“一滚出來”之説,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説,欠瑩。文公《語録》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滚發出來。”此説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並取“補貼”之説,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滚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説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剩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庵云:“不謂理氣交相爲暢如此。”嗚呼!是即“合而有助”之説之病也。(24)楊慎《升庵經説》,第385頁。
通過楊慎所引余祐《性書》和羅欽順之言可以看到,楊慎認爲對“配義與道”的理解,實際上是理氣關係的一種表達。他認爲,張載、程子對理氣關係的認識,都是“理氣一元論”。而李侗對理氣關係的論述則並不統一,既説過“襯貼起來”這樣的“理氣二元論”,也説過“一滚出來”這樣的“理氣一元論”。朱熹對“配義與道”的解釋選取了“襯貼起來”的説法,因而添了“有助”這樣的字眼,而在别的地方又説了“一滚發出來”,顯然是受李侗的影響。如此,則所謂的“理氣二元論”,只不過是宋儒論述“欠瑩”時的誤解,程朱本身實際是持“理氣一元論”的。通過楊慎的論述,“理氣一元論”的説法,不但不是對權威的程朱的挑戰,反而是對後儒誤解的匡正和對程朱精義的繼承。如此一來,“理氣一元論”也更能爲篤信程朱的士人所接受。這也可看作是楊慎早年篤信程朱的一個側面的反映。
(二) 合 性 情 論
《孟子》所説的“人性論”本是限定在“人”的範疇,所以他説“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極嚴“類”之别,後來黄宗羲“類同則性同”(25)黄宗羲《馬雪航詩序》,黄宗羲著、陳乃乾編《黄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64頁。之言深得其旨。至宋儒以《中庸》“天命之謂性”爲綱領,遂將“性”的概念延展成一種“泛性善論”(26)牟宗三將傳統的人性論分爲以《易傳》《中庸》爲代表的“宇宙論”和以《孟子》爲代表的“道德論”兩種進路。(參見牟宗三著,羅義俊編《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據此,則宋儒所奉行的,實則是《中庸》一路,與《孟子》並不相同。李存山也説:“傳統儒家的性善論是講‘人性之善’,而宋代新儒家在接續性善論傳統時則已發展爲‘凡物莫不有是性’的泛性善論。”(李存山《從性善論到泛性善論》,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三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56頁。)。楊慎論“性”,與同時期的陽明心學一樣,都將“性”的討論限定在“人”的範疇之内,與《孟子》論“性”實乃同一進路,而不是宋儒的“泛性善論”。
司馬光質疑“性無有不善”,楊慎“論孟子”遂條予以反駁,可見楊慎基本上是認可孟子的“性善論”的。不過,在具體的論述上,楊慎卻不同於《孟子》,因而“論性”一條,又説《孟子》論“性善”,“其蔽也,或使人驕”(27)楊慎《升庵經説》,第394頁。,還一起批評了荀子的“性惡”、揚雄的“性善惡混”、韓愈的“性三品”之説。那麽,爲什麽要否定他們呢?楊慎《性情説》云:“《尚書》而下,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28)楊慎《升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册,第66頁。而《廣性情説》又説孟子言性而不及情,荀子言情而不及性,揚雄、韓愈雜性情而言(29)同上,第66~67頁。。可以看到,楊慎這兩處對孟、荀、揚、韓四者論性的評價,頗有矛盾之處。這一細節姑置勿論,綜合起來看,他始終在强調孔子的“合性情”之説。那麽,“合性情”是怎樣的呢?《性情説》云: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於《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鈎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性生於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 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於《易》者也。(30)同上,第66頁。
如所引李善之言,“性”是本質,而“情”是外染,楊慎説“情生於性”,則“情”乃是“性”遭遇“外染”的結果。而所引許慎、班固、《鈎命決》皆以陰陽論“性情”,以爲“性”屬陽而“情”屬陰。《鈎命決》所謂“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其“性善情惡”的意味已經非常明顯了。對此,楊慎基本上也是接受的,故楊慎説“害性者,情也”。通過這段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楊慎對“性”“情”的理解具有四個鮮明的特徵: 一是“性”“情”不離,遺“情”則爲死灰,忘“性”則爲禽獸。二是“合性情”不是“一性情”,二者有不可混淆的區分,因此他説“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31)王安石的“性情論”乃“性情爲一論”,其意以“性”爲體而“情”爲用,皆無所謂善惡,善惡乃對“情”的發用是否合理的評價。(參見姜國柱、朱葵菊《中國人性論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6頁。)而楊慎的“合性情”乃是“性情俱”,所謂“性”“情”仍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但不能缺遺其一。二者不同如此,不可混淆。。三是“情生於性”,“性”受外染而生“情”。四是雖然“情生於性”,但“性”没有絶對的決定作用,如果“情”熾盛,也會反過來擾亂“性”。
由此看來,楊慎對“性情”的認識,與同時代羅欽順以“性”爲“道心”、“情”爲“人心”,其基本的取向是非常一致的。更進一步,羅欽順和楊慎都認爲不能“去人欲”“遺情”,肯定了“情”“欲”存在的意義。這一説法,爲明代晚期李贄等人認可“人欲”開了理論的先河(32)溝口雄三先生認爲,對“人欲”的認可是晚明思想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徵,而李贄則是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參見溝口雄三著,索介然、龔穎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華書局1997年版。。只是相比於羅欽順,楊慎對爲何不能“遺情”的論述較爲缺乏。從另一方面來説,“性”受外染而生“情”,將“惡”排除在“性”之外,否定了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的説法,維護了“性善論”。而這“外染”的提出,爲後世如黄宗羲(33)黄宗羲《陳乾初墓志銘》云:“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見黄宗羲撰,陳乃乾編《黄梨洲文集》,第167頁。、顔元(34)顔元《存性編》“借水喻性”條與楊慎此處非常相似,其言曰:“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見顔元《顔元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頁。等所直接繼承,是則楊慎“合性情論”有别於羅欽順之處,也是楊慎對人性論的貢獻。
三、 “非孟”餘緒: 楊慎對孟子的評價
早在元代,孟子就取代顔回而成爲了“亞聖”(顔回稱“復聖”),而《孟子》一書也在元代被作爲“四書”之一列入了科舉考試的科目。明承元制,除了洪武朝有短暫的波動(如罷孟子配享、修《孟子節文》)之外,在對待孟子其人其書的問題上,還是延續了元代的制度。到楊慎的時期,孟子已經歆享了數百年的尊榮,其地位可謂不容置疑。即便抛開制度,在學術界中,理學也好,心學也罷,都是非常尊崇孟子的。可以説,到楊慎的時代,整個社會的主流都是尊孟的。但是楊慎不僅不尊孟,還對孟子多有抨擊。細究其故,楊慎是受到了“非孟”思潮的影響。
(一) 楊慎受“非孟”思潮影響
首先,當時“非孟”思潮似乎頗有復活的跡象,楊慎或亦受此影響。與楊慎同時代的吕柟,乃是關學巨擘,《明史·儒林傳》稱:“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唯柟與羅欽順云。”(35)張廷玉等《明史·儒林一》,第7244頁。今觀吕柟《四書因問》,吕氏弟子顓、九霄、九式、官(36)未知具體何人,此處但以《因問》所書標示之。其“非孟”言論,觀書即見,此處不贅。等人,均曾以“非孟”言論請教於他,其中有引前人“非孟”者,也有自己質疑《孟子》之處。吕柟一一爲之辨明,因而感慨:“余隱之及朱子辨之,又弗能究焉,宜乎至今而人猶議於斯也。”(37)吕柟《四書因問》卷五,吕柟著、劉學智點校整理《吕柟集·涇野經學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48頁。以吕柟一人之門下,已有這麽多弟子“非孟”,雖未足據此而言整個社會如何,但亦可概見當時“非孟”思潮頗有一些影響力了。楊慎之“非孟”,或亦受此影響。
其次,楊慎讀過余允文的《尊孟辨》,對前人“非孟”的情況非常了解。宋代的“非孟”思潮,在當時影響甚巨,但相關著作卻大都失傳。只有余允文的《尊孟辨》和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録》收録頗多,並流傳了下來。而楊慎是明確表示自己讀過《尊孟辨》的。“論孟子”條云:“温公《疑孟》謂‘性無有不善’爲失,引朱、均爲證。余隱之《尊孟辨》云:‘犧生犁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38)楊慎《升庵經説》,第394頁。由此可見,楊慎讀過《尊孟辨》,對司馬光等人的“非孟”言論是非常清楚的。
再次,楊慎“非孟”的言論,與《尊孟辨》中所載的内容頗有相似甚至雷同者。“舜避堯之子”條云: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於文祖”,“受命於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 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39)同上,第393頁。
而《尊孟辨》載李覯《常語》之言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於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於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歷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欷。”(40)余允文《尊孟辨附續辨别録》,《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0頁。兩相對比可以發現,二者都引用“受終於文祖”“受命於神宗”“歷數在躬”三條引文,以論證受禪的舜、禹乃是必須即位,不可以避讓推辭;而李覯以王莽爲例,楊慎以曹操、司馬懿爲例,均用以説明舜、禹並非作僞竊國之人。在這兩個方面,可以説完全相同。又如“瞽叟殺人”條所言,雖非抄纂,卻也是《尊孟辨》所載司馬光《疑孟》所批評過的内容。前文所引“論孟子”一條中,楊慎已明確舉出“温公《疑孟》”,此處討論同一個問題卻反而不提及司馬光,其中緣由亦頗耐尋味。
(二) 楊慎爲李覯辯護
北宋的“非孟”思潮,即是李覯發其端。李覯作《常語》,其中頗多訾詆孟子之言。受李覯影響,其好友陳次公、顧野又分别作了《述常語》(從題目來看,當是申論李氏《常語》之作,其中也頗有訾詆孟子之言,均有一條見收於邵博《聞見後録》)。至王安石變法,正式升《孟子》爲“兼經”,安石又頗以孟子自比。受党争影響,司馬光作《疑孟》,蘇軾作《孟子辨》,以質疑孟子,遂掀起了一股聲勢頗大的“非孟”思潮。然而,楊慎“李泰伯不喜孟子”條卻説:
小説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子也。何以知之?曰: 考其《集》知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剿小説,以爲無根之遊談,故詳辨之。(41)楊慎《升庵經説》,第399頁。
楊慎的這段論述,依據有二: 一是“李泰伯不喜孟子”乃是“小説家”所載,本不可信;二是從李覯的文集來看,其中多有徵引和闡發《孟子》之處。如果單純地看這兩點依據,楊慎之説是可以成立的。一方面,所謂“小説家”,據胡應麟考證:“宋小説載一士人聞泰伯非孟子,撰二絶句投之,李遂罄家釀與飲,酒盡,迄不復來矣。”(42)同上。則此事出於《道山清話》(43)《道山清話》載:“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好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駡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駡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絶倒。”見《道山清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7册,第668頁。,《四庫全書》歸之於子部小説家類雜事之屬,確實不具有多大可信度。另一方面,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李覯文集,當是成化間左贊所編之本(44)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盱江集》、民國《四部叢刊》所影《直講李先生文集》、中華書局標點本《李覯集》,均係此本。,而這一本中的“非孟”言論僅有三條,“蓋贊諱而删之”(45)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册,第114頁。,已很難考見李覯的“非孟”言論。因此,陳育寧《明前中期孟學研究》未及深考,遂徑將此條作爲楊慎博學、求實的例證(46)陳育寧《明前中期孟學研究》,第77~78頁。,其失誤也可以理解。
但是,如前所述,楊慎讀過《尊孟辨》,並受到了《尊孟辨》中所載“非孟”言論的影響,特别是“舜避堯之子”一條,與《尊孟辨》所載《常語》之言相差無幾。而且,楊慎讀《尊孟辨》,也當在其作《升庵經説》之前,理由有二: 首先,《尊孟辨》自明中葉以後就已無完本,《尊孟辨》提要云:“朱彝尊《經義考》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注‘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其《尊孟辨》及《續辨》《别録》之名,亦厘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47)余允文《尊孟辨附續辨别録》,第1頁。如此,則楊慎所處的時代,除了存於《永樂大典》及《朱子全集》之中者,單行本的《尊孟辨》的流傳必然是較少的,否則不至於此後便無完本。以雲南之偏遠,很難見到流傳較少的單行本《尊孟辨》,而《永樂大典》更是絶不會有。因此,楊慎當是被貶之前讀的《尊孟辨》,而其作《丹鉛餘録》等書乃在被貶雲南之後,其先後明矣。其次,即便楊慎寫作之時偶然“遺忘”,但丘文舉輯録《升庵經説》是在“丹鉛”諸録完成之後,《升庵經説》完成時,楊慎作有序,此時當有所檢核。而“李泰伯不喜孟子”一條在論《孟子》之末,也是比較醒目的。綜上所述,楊慎是在讀過《尊孟辨》,明知李覯乃“非孟”的代表人物的情況下寫下的“李泰伯不喜孟子”條的。
那麽,楊慎爲何要這麽做呢?楊慎自己並未解釋。但結合其他方面來看,仍可作出一些合理的推測。首先,李覯的學説不同於朱熹,爲李覯辯護,有利於李覯學説在當時的接受,進而從側面達到楊慎反理學的目的。其次,如前所述,楊慎對“舜避堯之子”的質疑,在很大程度上因襲了李覯的《常語》。楊慎爲李覯辯護,透露的信息是他未嘗讀到《尊孟辨》,有可能是有意掩飾他對李覯的因襲。再次,楊慎本身便對孟子頗有訾詆,他爲李覯所作的辯護,實際上也是爲自己所作的辯護。楊慎並非全然訾詆孟子,其文集中也多有稱引《孟子》之處。需要注意的是,“李泰伯不喜孟子”條,正好是《升庵經説》論《孟子》部分的最後一條。而這一條中的辯護方式,是列舉李覯文集中稱引《孟子》之處。如果以這種方式來反觀楊慎,那楊慎自然也可以説是“深於《孟子》者”了。
結 語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對楊慎的《孟子》學作一個整體性的把握。
在考據方面,楊慎頗有一些“發前人所未發”的觀點,對理解《孟子》本身頗有裨益。但與此同時,楊慎的考據方法尚不成熟,常常因爲疏於核對原書而致誤,又頗“恃氣求勝”,背離文本。在個别的考證之中,還存在抄纂前人成説的情況。
在義理方面,楊慎對“配義與道”的論述,體現了他的“理氣一元論”思想,並且將這一理論上溯至程朱本身,爲“理氣一元論”的廣泛接受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而他的“合性情論”雖然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論”,但是爲明代晚期肯定“人欲”奠定了理論基礎,對“習染”的提出也對黄宗羲、顔元等人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對孟子的評價方面,楊慎深受“非孟”思潮的影響,他對孟子的評價,頗與前人的“非孟”言論相似或者雷同。他還特意爲“非孟”的代表人物李覯曲爲辯護,既可以由此反對程朱,又可以掩飾自己對李覯的因襲,還可以爲自己的“非孟”作出辯護。
總的來看,楊慎的《孟子》學研究是多方面的,在各個層面均有其獨到的特色,也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果。不過,他的缺點也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當盡可能地客觀,不應該過度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