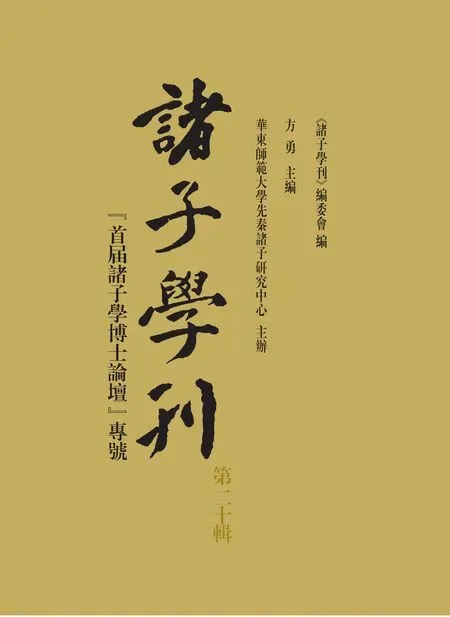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雍也可使南面”
——出土文獻與仲弓爲政思想探微*
鄧國均
内容提要 在孔子弟子中,仲弓是“孔門十哲”之一。《論語》載其與孔子的對話,主張“爲政”當“居敬行簡”,與《上博竹書·仲弓》篇所載内容可以相互印證,顯示其爲政思想包涵重“敬慎”、尚“寬簡”兩大要點。仲弓的政治思想,與《論語》及《上博竹書》所載孔子“爲政以德”“五德”“仁之以德”諸説高度相通,反映了孔子和仲弓對先秦諸子共同關註的“君德”“王道”等問題的獨特認識,也應是孔子稱許仲弓“可使南面”的重要原因。孔子和仲弓的“爲政”思想,與“秉要執本”“清虚自守”的《老子》等道家“君人南面之術”亦有不少相合之處,反映了早期儒、道思想的深入交流,及其對某些政治理論問題的共同認識。
關鍵詞 《論語》 孔子 仲弓 爲政
“爲政”是孔子與其弟子及時人經常討論的話題。但在孔子弟子中,由於相關史料有限,仲弓及其言論所受關註相對較少。本世紀以來,隨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以下簡稱“《上博竹書》”)等一批簡帛文獻的面世,才使這一局面有所改觀。學者們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對仲弓的家世里籍、政治活動,仲弓與《論語》的編纂及早期儒學的傳承等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但另一方面,作爲“孔門十哲”之一,仲弓儒學思想的特點,仲弓與孔子思想的異同,孔子對仲弓的稱許及其與所謂“南面之術”的關聯等問題,又似乎尚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筆者不揣淺陋,將對上述問題的思考述之如下,以就正於方家。
一、 《上博竹書》與仲弓的爲政思想
冉雍,字仲弓,魯國人。《論語·先進》載:“德行: 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 子游、子夏。”(1)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98頁。可見仲弓被列爲“孔門十哲”之一,是“孔門四科”中“德行”科的代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云:“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2)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190頁。早期典籍有關仲弓的記載雖然不多,但卻爲我們考察其思想學説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論語》所載有關仲弓的内容,分别見於《公冶長》《雍也》《顔淵》《子路》等篇。仲弓向孔子“問仁”“問政”等,體現了其對早期儒學核心問題的關注。雖然這些對話相對較少,但由於《論語》一書在編訂過程中,編纂者對相關材料進行了較爲嚴格的選擇(3)趙貞信《〈論語〉究竟是誰編纂的》,《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1年第4期。,因此所留下的内容大多值得予以探究。如《雍也》篇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4)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477頁。
對於“南面”一詞,何晏《論語集解》引苞氏説云:“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5)皇侃《論語義疏》,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24頁。朱子《論語集注》亦云:“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3頁。由於兩章編次相鄰,因此有學者認爲,仲弓之“問”與孔子的稱許,可能具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如漢代劉向所編《説苑·修文》就説:“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7)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説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99頁。漢代以來的學者,亦多聯繫“南面”一詞的涵義,而對仲弓的政治思想進行解釋。
仲弓“問子桑伯子”,實則是“問爲政”。孔子和仲弓由對“子桑伯子”的討論,進而論及了“爲政”的一個基本原則和總體方略問題。對於“居敬行簡”的涵義,漢代孔安國解釋説:“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8)皇侃《論語義疏》,第125頁。梁代皇侃則聯繫“禮制”爲解:“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如此者乃爲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9)同上。兩説均注重“爲政”者之“居身”與“臨下”兩方面的聯繫。朱子則又兼及“行簡”的社會影響而釋之:
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1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83~84頁。
可見朱子是將“居敬”理解爲一種“自處”“自治”之道,突出了“爲政”者“修養心性”的重要性。明人鹿善繼則又結合“心學”之理而解釋説:“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衆寡小大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遍,洞察情形,而挈其綱領”,“如此行簡,民安可知”(11)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64頁。,指出了“居敬行簡”的要義在於敬慎爲治、提綱挈領和簡政安民。程樹德《論語集釋》引《四書翼註》亦云:
居敬之簡,見識精明,當務之爲急,器量威重,執要以御繁,如是則民受和平安静之福。居簡之簡,得一遺二,精神不能兼顧,貪逸憚勞,叢脞而不自知,如是則民受其苟且率略之弊。此言不但判斷伯子人品清楚,實天下後世南面者之圭臬也。(12)同上。
所謂“執要以御繁”,也即鹿氏所説“挈其綱領”之意。此説將“居敬之簡”和“居簡之簡”兩種“爲政”方式進行比較,尤其將前者視爲“天下後世南面者之圭臬”,充分肯定了仲弓政治思想的意義。此外陳震《筤墅説書》亦云:“以不擾於外者爲簡,子所以僅可伯子也。而以貫攝於心者爲簡,雍所以可使南面也。知簡之可以祛繁,再知敬之可以運簡,則仲弓之可使,伯子之僅可,已判然矣。”(13)同上,第365頁。將“敬”“簡”“繁”三者作動態化解讀,有力地突出了此章的社會實踐價值。
從上引各家的解釋,可知仲弓“居敬行簡”之論,實具有較高的政治理論價值和較强的社會實踐意義。聯繫《論語·顔淵》和《子路》等篇所載仲弓與孔子的對話,對其政治思想的淵源及其義理指向,或許能有一個更爲全面的理解。尤其是學者整理出版的《上博竹書》等簡帛文獻,爲考察仲弓政治思想的具體内容提供了更爲豐富的信息。
《論語·子路》所載孔子和仲弓的對話,則涉及“爲政”的一些制度創設和具體措施問題:“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14)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506頁。對於孔子所説的“先有司”,學者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分歧。魏王肅注説:“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15)皇侃《論語義疏》,第324頁。梁皇侃亦云:“言爲政之法,未可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16)同上。由此而言,則所謂“先有司”,似是包括了制度創設和人事任命兩個方面。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則云“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17)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16頁。如此而言,則“先有司”即爲“委任有司”,“赦小過”則爲赦免“有司”之過。但如果參考《上博竹書》的相關内容,對於此章内容的理解則可能會有所不同。
《上博竹書》中有一篇被學者命名爲《仲弓》的,共計二十八簡(另有附簡一支),五百餘字,内容頗爲豐富。其篇首爲“季桓子使仲弓爲宰,仲弓以告孔子曰”(18)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頁。,可與上引《論語·子路》内容相印證。從簡文首段看,仲弓並不太願意擔任“季氏宰”,孔子則對其予以勉勵。下文内容則依次圍繞“敢問爲政何先”“敢問民務”等問題而展開:
仲弓曰:“敢問爲政何先?”……(5)[曰]:“老老慈幼,先有司,舉賢才,宥過赦罪,(7)政之始也。”仲弓曰:“若夫老老慈幼,既聞命矣。夫先有司,爲之如何?”仲尼曰:“夫民安舊而重遷,(8)……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仲弓曰:“雍也不敏,雖有賢才,弗知舉也。敢問舉才(9)如之何?”仲尼:“夫賢才不可掩也。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之者?”仲弓曰:“宥過赦罪,則民何懲?”(10)“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猶差,民無不有過。賢者……”(19)(19)同上,第266~277頁。本文所引《上博竹書·仲弓》釋文參考了楊懷源《讀上博簡〈中弓〉札記三則》(《古漢語研究》2005年第2期)、陳劍《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11頁)的整理研究成果。引文括弧内數字爲原簡序號,簡文上下文有殘缺者,用省略號連接,異體字、假借字等均用今字寫出,不再另外注明,下同。
仲弓向孔子請教“爲政何先”,孔子則向其提出了“老老慈幼”等“爲政”理念和措施。對於“爲政”須“先有司”的原因,孔子的解釋是“夫民安舊而重遷……有成”。陳劍認爲,這裏的“遷”字“可能是‘變化’之意而非‘遷徙’(居處)之意”(20)陳劍《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戰國竹書論集》,第107頁。,“安舊重遷”即思想守舊,不願改變現狀的意思。廖名春根據上下文認爲,“先有司”當指“有司”應起“率先垂範”的作用(21)廖名春《楚簡〈仲弓〉與〈論語·子路〉仲弓章讀記》,《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 1期。。對於“宥過赦罪”,孔子的解釋是“日月星辰猶差,民無不有過”,可見寬赦的對象是“民衆”。這正與學者多將仲弓“居敬行簡”之論,理解成“爲政”尚“寬簡”之義相合。
《論語·顔淵》所載另一則孔子和仲弓的對話,則涉及“居敬”之説的來源及其意義問題。其文云:“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22)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502頁。《論語集解》引孔安國説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23)皇侃《論語義疏》,第299頁。朱子《論語集注》則云:“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2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3頁。可見《論語》此章所載孔子對“仁”的解釋,是將其與“敬”相結合,把“敬慎”看作“爲政”過程中達至“仁道”的一個途徑。《上博竹書·仲弓》亦有與此相關的内容:
仲弓曰:“[敢](27)問民務。”孔子曰:“善哉問乎!足以教矣。君(15)子所竭其情,盡其慎者三,蓋近□矣。(20)雍,汝知諸?”仲弓答曰:“雍也弗聞也。”孔子曰:“夫祭,致敬之(6)本也,所以立生也,不可不慎也。夫喪(23B),致愛之卒也,所以成死也,不可不慎也。夫行,旬年教……”(23A)(2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67~282頁。引文對原簡的編連和文字的釋讀,參考了陳劍《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陳劍《戰國竹書論集》,第106~111頁)的整理研究成果。
從簡文可以看出,孔子和仲弓所重視的“居敬”原則,實源自上古以來的“祭祀”“喪葬”具有一定宗教性的禮儀活動。“祭祀”是“致敬之本”,“喪葬”是“致愛之卒”,其作用在於“立生”和“成死”,因此是“君子”所應“盡慎”的事項。《論語·學而》載有子之言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26)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457頁。同書《顔淵》篇亦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27)同上,第2504頁。由此而言,《上博竹書·仲弓》所載孔子和仲弓有關“民務”問題的討論,實可以看作是孔子對“仁道”及其政治功用的一個頗爲具體的解釋。這也應是《論語·顔淵》載“仲弓問仁”,孔子爲何要側重論述“居敬”的重要原因。
從上引《論語》和《上博竹書》的内容,可知《雍也》篇所載仲弓的“居敬行簡”之論,實顯示其政治思想包涵重“敬慎”、尚“寬簡”兩大要點。就其實際内容而言,則可能包括對“祭祀”“喪葬”等禮儀文化制度的重視,以及孔子所説“老老慈幼,先有司,舉賢才,宥過赦罪”等具體政治措施。清代劉沅《四書恒解》説:“自古聖王不過居敬行簡而已。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無爲而治,恭己南面’,皆是義焉。”(28)程樹德《論語集釋》,第365頁。由此而言,則仲弓的政治思想,實與孔子的“德政”理論和“王道”學説具有較深關聯。通過對《論語》及《上博竹書》所載孔子“爲政以德”“仁之以德”説的考察,可以更爲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二、 仲弓思想與孔子“爲政以德”説
《論語·先進》所載“孔門四科”以“德行”居首,表明其在早期儒學思想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皇侃《論語義疏》解釋説:“德行爲人生之本,故爲第一以冠初也。”(29)皇侃《論語義疏》,第267頁。程樹德《論語集釋》引韓氏之説則云:“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乎言也。”(30)程樹德《論語集釋》,第744頁。聯繫《論語》等所載孔子的“德論”及相關内容,對於孔門“德行”科的意義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孔子思想體系中,“德”爲最高範疇之一,是具有統率性的哲學概念。《論語·述而》載:“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31)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481頁。同篇亦載:“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32)同上。同書《里仁》篇亦載:“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33)同上,第2471頁。可見孔子曾以“修德”爲務,並將“德”看作立身行事的依據,以及對“君子”的内在要求。《爲政》篇則云:“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34)同上,第2461頁。《季氏》篇亦載:“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35)同上,第2520頁。由此而言,則“德”又是“爲政”“化民”的一個重要原則。《爲政》篇首章所載孔子的“爲政以德”説,尤爲明確地論述了“德”的政治意義: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36)同上,第2461頁。
雖然歷代學者對此章的解釋有所不同,但大都將其與“無爲而治”“君德”“王道”等問題相關聯。如漢代鄭玄説:“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也。”(37)皇侃《論語義疏》,第23頁。皇侃《論語義疏》亦云:“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衆星共宗之以爲主也。譬人君若無爲而御民以德,則民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衆星之共尊北辰也。”(38)同上。《論語集注》引程子之説亦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3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3頁。同書引范氏之説亦云:“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静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40)同上。可謂從不同角度指出了“爲政以德”的實際效用。朱子則又結合早期儒家對於“政治”涵義的認知而爲解: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4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3頁。
清人宋翔鳳亦承此軌轍而發揮:“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璇璣,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42)劉寶楠《論語正義》,第39頁。所説與朱子略同,均認爲“爲政以德”與“政者正也”及“無爲而治”之旨相通。朱子及宋氏所引“政者正也”之説,見於《論語·顔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43)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504頁。從上引范氏“以簡御煩”“以静制動”“以寡服衆”諸解,朱子“無爲而天下歸之”之論,以及宋氏“王中無爲,以守至正”等説,可知孔子“爲政以德”的主張,實包涵一種“無爲”“尚簡”之義。《論語·雍也》所載仲弓“居敬行簡”之論,正與其思想義旨相合。
對於學者多以“無爲”之義解釋孔子的“爲政以德”説,亦有少數學者持不同意見。如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説》曰:“極論此章,亦不過《大學》‘以修身爲本’之意、孟子‘至誠動物’之旨”,“若更於德之上加一“無爲”以爲化本,則已淫入於老氏‘無爲自正’之旨”(44)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06頁。。程樹德《論語集釋》亦云:
此章之旨,不過謂人君有德,一人高拱於上,庶政悉理於下,猶北辰之安居而衆星順序。即任力者勞,任德者逸之義也,與孔子稱舜無爲而治了不相涉。郭象以黄老之學解經,必欲混爲一談。朱子不察,亦沿其謬,殊失孔氏立言之旨。(45)程樹德《論語集釋》,第64頁。
然而仔細考察,可以發現程氏所謂“一人高拱”而“庶政悉理”,以及“任力者勞”“任德者逸”之説,與上引范氏“以簡御煩”“以寡服衆”等解説,其實並無根本區别。清代李允升《四書證疑》説:“既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並結合儒家思想的“仁”“義”等概念而解釋説:
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46)劉寶楠《論語正義》,第39頁。
可見“無爲”並非“無所作爲”,而是注重對某種基本原則和總體方向的把握,可稱之爲“有限作爲”或“有效作爲”,實際上奉行的是一種“簡德”。就其邏輯思路而言,王氏和程氏對上引諸説的批評,一方面是出於儒、道異軌的派别之見,另一方面也可能與其對“無爲”的不同理解有關。
《上博竹書·從政》及《季康子問於孔子》等篇,亦載有不少孔子對“德”“政”關係的論述,比上引《論語》内容更爲具體,但其思想主旨則基本一致,實可以看作對孔子“爲政以德”説的重要補充。其中《從政》“甲篇”的第五、六、七號簡,較爲詳細地論述了所謂“五德”的内容:
聞之曰:“從政,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五德: 一曰寬,二曰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寬則無(5)以容百姓,不恭則無以除辱,不惠則無以聚民,不仁……(6)……則無以行政,不敬則事無成。……”(7)(47)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21頁。
《上博竹書·從政》的内容,多以“聞之曰”開頭,其來源不很明確。簡文整理者將《上博竹書》與《郭店楚墓竹簡》等簡帛文獻相比較,認爲應是聞諸“古先聖賢”或“夫子”(48)同上,第215~216頁。。從内容上看,《從政》篇所説的“五德”,與《論語·學而》載子貢所云“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以及《陽貨》篇“子張問仁”章所載“恭、寬、信、敏、惠”之説有相合之處(49)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458、2524頁。,因此應是“聞諸夫子”的可能性較大。《從政》篇將“寬”與“敬”納入“五德”之中,尤爲引人注意,可見二者均是孔子“德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上博竹書·季康子問於孔子》,對“敬”與“仁”“德”之關係亦有論述:
孔子曰:“仁之以德,此君子之大務也。”康子曰:“何謂仁之以德?”孔子曰:“君子在民(2)之上,執民之中,施教於百姓,而民不服焉,是君子之恥也。是故,君子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3)德以臨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謂仁之以德。……”(4)(50)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7頁。
從簡文可知,孔子將“敬”“慎”看作“德”的核心要素,並將“德”與“仁”聯繫起來,與《論語·顔淵》所載“仲弓問仁”,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實則重點闡述“爲政”的“敬慎”原則基本一致。《上博竹書·從政》篇言“不敬則事無成”,《季康子問於孔子》篇則言“敬成其德以臨民,民望其道而服焉”,可見所謂“敬慎”的作用,主要在於“成事”與“服民”,其實質是將一種宗教倫理轉化爲政治倫理,實現對民衆的道德教化和社會風俗的引導。
《上博竹書·從政》所載“五德”之一的“寬”,亦見於《論語·八佾》《陽貨》等篇。《八佾》篇載:“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皇侃《論語義疏》説:“此説當時失德之君也。”(51)皇侃《論語義疏》,第80頁。其内容正與《上博竹書·從政》“五德”説相合,可見“寬”亦是孔子所倡導的“君德”之一。《論語·陽貨》“子張問仁”章,對於“寬”的作用有頗爲具體的論述: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52)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524頁。
對於“寬則得衆”,宋代邢昺解釋説:“言行能寬簡,則爲衆所歸也。”(53)同上。《論語·堯曰》亦云:“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邢疏亦曰:“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54)同上,第2535頁。由此可見,“寬”“簡”涵義有相通之處,《論語·雍也》所載仲弓的“行簡”之論,實與《上博竹書·從政》所載孔子的“五德”説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將《上博竹書·仲弓》《從政》《季康子問於孔子》等篇與《論語》對讀,可以發現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實貫穿着“敬慎”和“寬簡”兩大原則,二者均是其“德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的“爲政以德”“五德”和“仁之以德”諸説,非唯關涉社會個體一般性的修身養性實踐,實亦指向先秦諸子哲學最高層面的“君德”“王道”等核心議題。《論語·雍也》所載仲弓的“居敬行簡”之論,不但表明其對孔子“仁道”“德政”思想的深入領會和準確把握,實亦反映其政治思想與孔子學説一脉相承的關係。仲弓對於“君德”“王道”等問題的獨特認識和領會,及其與孔子思想的上述聯繫,應是其被稱許“可使南面”的重要原因。
《上博竹書·仲弓》的第三號簡,所載内容亦爲孔子對仲弓的勉勵和贊許。其文云:“子有臣萬人道,汝思老其家夫!”(5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65~266頁。正與《論語·雍也》所載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相合,可見孔子對仲弓的期許之高和寄望之重,在孔門弟子中除顔回外,似未有能出其右者。如此均表明孔門“德行”之科,與“言語”“政事”之科實有較大區别,其在很大程度上寄托着孔子對於政治人才培養和學術思想傳承的深切期望。孔子和仲弓對於先秦諸子共同關註的“君德”“王道”等問題的深刻認識,不但反映了早期儒家思想在這方面的成就,亦表明早期儒、道政治思想有不少相通之處。將兩者進行適當的對比,或許有助於深化對所謂“南面之術”的認識。
三、 孔子、仲弓思想與“南面之術”
歷代學者對孔子和仲弓政治思想的解釋,多將其與道家的“無爲而治”等論説相聯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學者對此問題的某種共識。證之於《論語》和《老子》二書,確實可以發現其包涵着不少共通的思想觀念和理論原則。
《論語·衛靈公》所載孔子對舜的贊述,是考察其政治思想與道家學説之關係的一條有力綫索。“無爲”本是貫穿於《老子》全書的一個重要原則,如該書第二章説“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56)高明《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31~232頁。,四十三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57)同上,第38~39頁。,四十八章“無爲而無不爲”(58)同上,第54~56頁。,六十三章“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59)同上,第131~132頁。,等等。《論語·衛靈公》亦載: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60)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第2517頁。
何晏解釋“無爲”涵義説:“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61)同上。皇侃《論語義疏》亦云:“既垂拱而民自治,故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正南面而已也。”(62)皇侃《論語義疏》,第395頁。可見此章内容,實與《爲政》篇所載孔子“爲政以德”説,在思想主旨上有較爲明顯的聯繫。朱子之解釋,即將帝舜之“恭己”,視爲其“敬德”的體現: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跡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6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62頁。
孔子將“無爲”與“恭己正南面”相聯繫,顯示“無爲而治”應是所謂“南面之術”的一個較爲突出的特點。如將此章内容與《論語·雍也》所載“仲弓問子桑伯子”章相比較,便可以看出仲弓的“居敬”之説,實與孔子所説“恭己”略同;仲弓“行簡”之論,實與孔子“無爲”之説相合。兩章内容在思想主旨方面的此種聯繫,既是仲弓思想與孔子學説一脉相承的又一個明證,同時亦表明孔子對仲弓“可使南面”的稱許,或許正是因其思想中包涵着某些“南面之術”的内容。
孔子與《老子》思想的相通之處,尤其表現在對“德”的論述上。《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德”是貫穿全書的哲學概念。從《論語》及《上博竹書·從政》等篇看,孔子的“德論”體系,大體包括了寬、恭、惠、仁、敬等方面的内容。《老子》的“德”論,則多以“無爲”作爲貫穿其中的基本原則,某些篇章還論及儒家的仁、義、禮等概念。如三十八章説: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64)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1~6頁。
《老子》崇尚“道”“德”,主張本道、德之義以治國,故而對儒家的“禮治”説多有批評,但對於“仁”“義”等思想概念及其價值,仍予以較高程度的肯定。該書五十一章,還對“無爲”與“德”的關係作了較爲詳細的論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65)同上,第69~73頁。
此章通過對“道”“德”與“萬物”關係的闡發,對執政者提出了“爲而不恃,長而不宰”的“玄德”標準和要求。《論語·述而》載孔子自述其以“修德”爲務,《老子》五十四章亦云:“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66)同上,第86~88頁。這種對於執政者“修德”重要性的論述,與孔子的“爲政以德”説是基本一致的。
仲弓的政治思想,及其與孔子“爲政以德”説的關係,上文已作了較爲詳細的辨析。仲弓主張“爲政”當“居敬行簡”,證之於《老子》一書,亦可發現其思想與道家學説多有相合之處。《老子》認爲,“善爲道者”在政治活動中,大都保持一種“敬慎”“恭肅”的態度,如十五章説:
古之善爲道(“道”王弼本原作“士”,據帛書《老子》甲、乙本改)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客”王弼本原作“容”,據帛書《老子》甲、乙本改)。(67)同上,第290~293頁。
所謂“善爲道者”,其實也就是“善爲政者”。此章所説的“猶”和“豫”,都有“小心謹慎”之意,“儼”則多理解爲“恭敬”“嚴肅”的意思。此外如六十四章説:“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68)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135~139頁。。其所謂“民”,實際上也是指執政者。《老子》尤其强調“敬慎”原則在軍事活動中的重要性,如三十章説:
以道輔佐人主者,不以兵强於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者”王弼本原作“有”,據帛書《老子》甲、乙本改)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69)同上,第381~385頁。
三十一章也説:“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70)同上,第387~391頁。。六十九章亦云:“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71)同上,第171~173頁。可見《老子》是以極爲謹慎的態度來看待軍事活動的,與《論語·顔淵》所載“仲弓問仁”,孔子答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所體現的“敬慎”原則基本一致。
與此種“敬慎”態度相聯繫的,是《老子》書中多處對“儉”“嗇”之旨的論述,體現了一種較爲明顯的“尚簡”思想傾向。如六十七章説:“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72)同上,第160~162頁。此處所謂“儉”,固然可指對一國財物的“節用”,但實亦包含一種“爲政”尚“寬簡”、重“清省”之義。同書五十九章亦云: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73)同上,第114~117頁。
所謂“嗇”,從字面看是强調“爲政”者對自身精力的愛惜,實則是提倡一種“清簡”“無爲”的政治風格。六十章也説:“治大國,若烹小鮮”(74)同上,第118~119頁。,强調政治的要義在於尚清静,不繁擾、不多事,與上述“儉”“嗇”之旨相合,均包含有崇尚“簡約”“無爲”之義。
從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孔子和仲弓的爲政思想,與《老子》等道家學説確實具有較多的相通之處。《老子》的“玄德”“不言之教”“兵者不祥”和崇尚“儉”“嗇”等思想,大都貫穿着“無爲而治”的原則,體現出一種重“敬慎”、尚“清簡”的價值取向。此種價值取向深爲漢代學者所推許,如西漢時期曾經“習道論於黄子”的太史公司馬談,在其《論六家要指》中就説: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75)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3289頁。
可見他認爲,道家政治思想具有簡約易行、因時而變、切於世用等長處。班固本於劉向、歆父子《七略》而作的《漢書·藝文志》,亦總結道家思想的特點説: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76)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32頁。
所謂“秉要執本”“清虚自守”等,與司馬談“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之説大體一致。尤爲值得注意的是,《漢書·藝文志》明確指出,具備此種行爲和功用特徵的道家政治思想,正是古來所謂“君人南面之術”。孔子贊舜“恭己正南面”,又稱仲弓“可使南面”,顯示了他對此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其“無爲而治”“爲政以德”“仁之以德”説以及仲弓“居敬行簡”之論,則確切地表明孔子和仲弓的政治思想,確實有不少與古之“南面之術”相合的内容。
孔子和仲弓政治思想與道家學説相通,既有共同的歷史背景、文化淵源等因素,也與春秋時期儒、道思想的深入交流有關,在《論語》中我們即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條件。《論語·微子》載孔子及其弟子所路遇的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等人,大都是具有道家思想傾向的隱逸之士。《論語·雍也》載仲弓所問之子桑伯子,又見於《莊子·大宗師》《山木》等篇,或稱子桑户,或稱子桑雽(77)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64~266、684頁。。此外《楚辭·涉江》亦云“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東漢王逸注説:“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78)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1頁。《涉江》不但將桑扈與接輿並舉,還將其視爲“忠”“賢”一類人物。清人劉寶楠考釋“子桑伯子”之名説:“‘雽’、‘户’、‘扈’音近通用”;“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例”(79)劉寶楠《論語正義》,第210~211頁。。由此看來,子桑伯子與子桑户、子桑雽、桑扈等應爲同一人,其人亦是一位具有道家思想傾向的隱逸之士。孔子及其弟子與這類人物既有直接接觸,尤其是仲弓對於子桑伯子其人的關注與問詢,足以表明其政治思想與道家學説具有某些相通之處,並不是偶然的。
對於諸子思想的主旨及其共通之處,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概括總結説:“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80)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3288頁。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亦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81)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6頁。。早期儒、道思想既“各推所長”,而又能對所謂“南面之術”,實即對於“君德”“王道”等問題獲得一些共同的認識,正是其百慮一致、殊塗同歸的突出體現,由此也更可以看出這種共識的可貴之處。
結 語
通過對《論語》及《上博竹書·仲弓》《從政》《季康子問於孔子》等篇内容的比較和研究,可知“德行”作爲“孔門四科”之首,實寄托着孔子對於政治人才培養和學術思想傳承的深切期望。仲弓作爲“孔門十哲”之一,其“爲政”思想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 《論語·雍也》所載仲弓“居敬行簡”之論,可與該書《顔淵》《子路》等篇所載“仲弓問仁”“仲弓問政”以及《上博竹書·仲弓》篇所載其與孔子對於“爲政何先”“民務”等問題的討論相印證,顯示其政治思想包涵重“敬慎”、尚“寬簡”兩大要點。(二) 仲弓的政治思想,與《論語》及《上博竹書·從政》等篇所載孔子的“爲政以德”“五德”“仁之以德”諸説高度相通,反映了孔子和仲弓對先秦諸子哲學最高層面的“君德”“王道”等問題的獨特認識,也應是孔子稱許仲弓“可使南面”的重要原因。(三) 孔子和仲弓的政治思想,與《老子》等道家的“君人南面之術”亦有不少相合之處,反映了早期儒、道學派對某些政治理論問題的共同認識,這種認識似乎可以初步概括爲以下兩點: 即“君德”重“敬慎”,“王道”尚“寬簡”。這種政治思想的産生,固然因其植根於春秋時期及其以前的文化傳統,而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其對於此後的儒家、道家思想所産生的影響,仍然是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