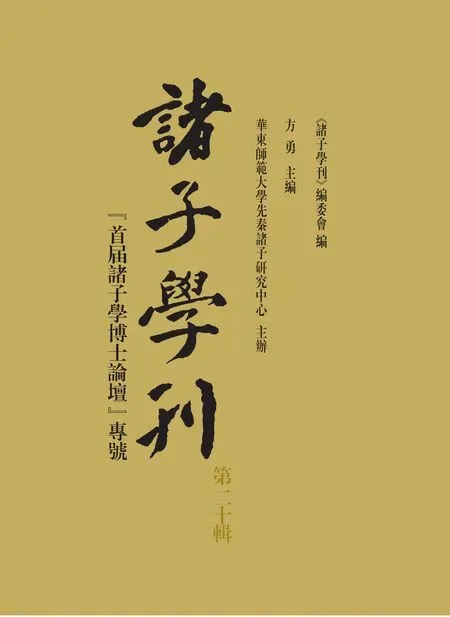禮學視域下諸子哲學發生學
——對先秦諸子思想淵源的重審
陳 雄
内容提要 中國哲學的正式成型以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争鳴爲標志,但它的發生與西方哲學發生的“突破性”相比表現得更加“温和”。上古及三代以來宗教文化的積澱、西周禮樂文化的“郁郁乎文哉”、東周社會的情勢,它們與諸子百家的争鳴呈現出一種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關係。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對於諸子哲學發生學的研究可從“源”“因”“緣”三個方面展開,即: 諸子哲學“源”於西周的禮樂文化,“因”於東周的“禮壞樂崩”,而諸子的分途發生則“緣”於對即將崩壞了的“禮”的不同態度和方法。
關鍵詞 諸子 發生 禮
一、 諸子哲學發生學引論
“發生學”最初是應用於自然科學領域的一種研究方法,與“遺傳學”相類,研究生物的發生和演變。上世紀中葉,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傑發表了關於“發生認識論”的系列著作,他解釋道:“發生認識論旨在説明知識,特别是,它要根據知識的歷史、知識的社會發生以及作爲知識的基礎的那些概念和運算的心理學起源,來説明科學的知識。”(1)[瑞] 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頁。不過這種方法在皮亞傑這裏比較具體,且無法脱離其心理學的背景,但卻可以以此爲基礎,賦予它更廣泛的意義,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發生認識論”提出後不久,發生學方法很快被應用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研究領域(2)參考張乃和《發生學方法與歷史研究》,《史學集刊》2007年第5期。。而隨着1981年《發生認識論原理》的譯入,發生學方法逐漸引起了國内學者的注意,樓培敏曾介紹了發生學方法的特點和一般步驟以及所應遵循的方法論原則(3)樓培敏《發生學方法》,《社會科學》1986年第10期。,俞吾金則首次提出了“哲學發生學”,並認爲開展此項研究除了可以推動人類學、民族學、傳記學等學科的發展外,還能對藝術、宗教、倫理等意識形態的研究提供啓發,它將大大擴寬哲學研究的領域並能够在研究中導出一些有重要價值的結論(4)俞吾金《論哲學發生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我們基本同意這個觀點,進一步,沿着這個思路,對中國哲學的研究引入發生學的方法亦將具有重要的價值和廣闊的前景。
研究中國哲學的發生學,首先也是最基礎的,就是要確定“中國哲學”這個對象於何時正式成型?這個問題的解決繞不開“軸心時期”與“哲學的突破”兩個理論。前者由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提出,其最爲精闢的論述是:“我們可以把它簡稱爲‘軸心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奥義書》和佛陀……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這數世紀内,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5)[德] 卡爾·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後者由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提出,他説:“第二個基本進步,一般被認爲是‘哲學的突破’。由於這一過程,在公元前第一個一千年中的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至少是部分各自獨立地和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爲人類環境的宇宙性質的明確的概念化,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伴隨着這一過程,也産生了對人類自身及其更大意義的解釋。”(6)[美] 塔爾科特·帕森斯《“知識分子”: 一個社會角色範疇》,《文化: 中國與世界》第三輯,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55頁。雅斯貝斯着重强調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幾乎同時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批哲學家;而帕森斯强調的則是“事件”,一次中西方幾乎同時實現了“哲學”上的“突破”事件。對於這兩個理論,陳來説:“無疑,帕森斯所説的‘哲學的突破’即發生於雅斯貝斯所謂軸心時代,二者並無不同。”(7)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 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4頁。如此,總體上可以表述爲: 在“軸心時代”,中西方文化的思想界實現了“哲學的突破”。
胡適説:“中國哲學到了老子、孔子的時候,才可當得‘哲學’兩個字。”而在此之前的兩三百年則是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8)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6頁。。馮友蘭也把“子學時代”作爲其《中國哲學史》的開篇。張岱年説:“中國哲學之創始者,當推孔子。”(9)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緒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頁。勞思光也説:“孔子於周末創立儒學,方是中國最早的哲學。”(10)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頁。余敦康則説:“中國的哲學開端於春秋末年的孔子和老子。”(11)余敦康《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頁。這樣,可以基本上得到一個共識:“哲學的突破”在中國表現爲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争鳴,而這也標志着中國哲學的正式成型。
但這裏存在一個被掩蓋的事實,即: 諸子哲學的發生並不完全是突破性的。“突破”一詞的使用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無疑是得當的,當我們回顧西方哲學史時,古希臘哲學的發生確實會給人一種“忽然”産生的“驚異”感覺,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説:“在全部的歷史裏,最使人感到驚異或難以解説的莫過於希臘文明的突然興起了。”(12)[英]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3頁。這是因爲在希臘古典哲學之前存着一個文化的“斷層”,雖然古希臘青銅時代的米諾斯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異常發達,但卻隨着多利亞人的入侵被徹底毁滅了,希臘歷史進入了“荷馬時代”,整個社會文化全面倒退,直到公元前8世紀“黑暗時代”結束之後便出現了一個哲學家“蜂起”的時代,從而給人一種“突破”的印象。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也出現了斷裂,原因同樣是遭遇了外族的入侵而導致本土文化的絶跡。但是,與上述兩類在文化斷層之後重新發展起來的“次生道路”的文化不同,中國是一種“原生道路”的文化(13)鄒昌林説:“世界文化可以看作兩大單元: 一是原生道路的文化單元,一是次生道路的文化單元。”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博士科研成果通報1991上》,宇航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前者表現爲“斷裂”“偶然”與“突進”,後者則表現爲“連續”“必然”和“温和”。
所以,諸子哲學給人的是一種“突破”的錯覺,雖也存在有思想“哲學化”的“飛躍”的成分,但皆有其立論的文化傳統,即如余英時所説的“諸子立言所採取的‘托古’的方式”(14)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頁。。畢竟中國文化没有斷層,在諸子哲學出現之前,有着雄厚的積累。對此,吕思勉的論述甚確:“先秦諸子之學,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興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鬱積,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時勢,乃如水焉,衆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積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偉,而影響於人必深。”(15)吕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世界書局1933年版,第2頁。那麽,我們研究中國哲學的發生學,首先要做的就是追根溯源的工作,即中國哲學源何而生?其基礎或曰諸子哲學之前的雛形又是什麽?其次,諸子哲學緣何從之前的雛形演變過來?造成這種“演變”的原因又是什麽?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中國哲學的諸多流派是怎樣形成的?由大致相同的時代和社會背景爲何産生了不同的哲學流派?也就是説,諸子的發生緣何分途而行?
二、 關於諸子哲學起源問題的論辯
關於諸子百家起源問題的探討古已有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漢書·藝文志》的“諸子出於王官”説。劉歆認爲,諸子有十家,其中儒家出於“司徒”,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縱横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説家出於“稗官”。這種思路被歷代學者所推崇和吸收,成爲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影響至今。如章學誠認爲諸子百家之學皆本源於“周官之典守”(16)章學誠《文史通義》,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頁。。章太炎也説:“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17)章太炎《諸子學略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馮友蘭則謂古代“官師不分”(1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3頁。。當然也有不同意見,如柳詒徵認爲“諸子之學發源甚遠,非專出於周代之官”(19)柳詒徵《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521頁。。胡適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專對“王官”説提出質疑,或許是受《淮南子》影響,他認爲諸子的出現是“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救之”,與“王官”無關,諸子皆是“應時而生”(20)胡適《中國哲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頁。。他甚至認爲,儒是殷商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他們的宗教是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他們的職業是治喪相禮。他還認爲老子才是真正的“儒”,是“正宗老儒”,孔子則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爲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21)胡適《説儒》,《中國思想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頁。。
劉歆以降的“諸子出於王官説”雖不盡全面,卻有其深刻的歷史依據,其所據的史料、文獻頗豐,且劉歆所處的時代畢竟距諸子較爲接近,完全否定不可取。況且胡適之言雖有一定道理,卻未免偏頗,其所論證的老子是正宗的老儒,儒學出於殷士,實難令人信服。勞思光説:“一學派之所以成爲一學派,乃在於其確定主張及理論,而不在於在組成方面與某社群間之外緣關係。”認爲胡適只是解釋了周初以下有一禮生社群之形成與殷士有關,而所論孔子及儒學之立場,則與事實不符,所以儒學出於殷士之説不能成立(22)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76~77頁。。
除了《淮南子》與《漢書》,與諸子哲學起源相關的材料最早可追溯至莊子學派,《莊子·天下》認爲諸子哲學的共同淵源是“古之道術”。侯外廬結合“王官”説,認爲莊子所説的“古之道術”就是西周的宗教王官之學(23)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頁。。余敦康在此基礎之上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從顓頊“絶地天通”的宗教改革論起,經堯舜夏商時代宗教文化的發展,又對周代國家宗教進行了詳細論述,並最終清理出了一條從宗教到哲學的發展脉絡,提出夏、商、周三代宗教是中國哲學思想發生的源頭(24)余敦康《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頁。。葛榮晉也認爲“中國哲學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崇拜中逐步孕育出來,經過夏、商、周發展到春秋末期。”(25)葛榮晉《先秦兩漢哲學論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與此類似的,劉緒義認爲先秦諸子導源於巫術,而“王官之學”便是由巫術而來的“禮”學,是巫術文化的高級階段,諸子就産生於巫術文化向人文文化悄然轉移的大背景之下(26)劉緒義《巫: 天使在人間——關於先秦諸子的發生學思考》,《廣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諸子争鳴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照劉氏所説,向人文文化轉移的巫術文化,當是指西周,但西周是否爲巫術文化似可商榷。殷商確乎是一種巫術文化(或曰宗教文化),我們也同意西周繼承了夏商以來的宗教傳統,但有一個基本事實不可忽略,即周人的天命神學較之於殷商明顯的理性化了,其“人文”色彩顯得十分的濃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的諸多制度不可能全部納入“國家宗教”的體系之中,所以,相比於夏商的宗教文化,西周應被稱爲“禮樂文化”爲確。
吴淳將中國哲學的發生發展分爲坡狀或梯狀形式呈現的“五個臺階”,而諸子哲學可視爲第六個臺階,起於老孔,也即儒道,後又有墨家。他認爲,這“不是一個時代的開始,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是對前五個時期哲學發展的一種總結(27)吴淳《中國哲學的起源——前諸子時期觀念、概念、思想發生發展與成型的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6頁。。吴氏將中國哲學的源頭追溯至非常久遠的年代,但他還是承認中國哲學範型的基本確立是在周代後期,與前述馮、胡、張等人的觀點仍是一致的。不過,吴先生所做的工作明顯是以中國哲學相關概念爲對象的,這當然是中國哲學發生學的内容,然而,中國哲學的發生學與中國哲學相關概念的發生學究竟有别。吕文郁對自先秦以降的諸子百家起源論作了總結,認爲主要有五種: 諸子緣於王官説、百家緣於“六經”説、百家緣於史官説、百家緣於政治説、百家緣於諸因綜合説(28)吕文郁《春秋戰國文化史》,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86~104頁。。但這個總結是有問題的,如章學誠是“六經”説的代表,但卻可歸爲其“王官”説的框架之中,而“六經”之學在西周本就爲“王官之學”,“史官”更是“王官”之一隅,所以,吕氏所總結的前三者“百家起源論”可統歸爲諸子出於“王官之學”。“百家緣於政治説”其實就是“應時”説,至於“諸因綜合説”則駁雜重複,亦不足爲據。
也就是説,關於諸子百家起源問題的探討,實可歸結爲兩類,一是“王官”説,一是“應時”説,兩説各有所據,亦各有局限。顧士敏認爲《莊子·天下》《漢書·藝文志》和《中國哲學史大綱》關於中國哲學起源的探討,其結論都是一致的(29)顧士敏《“中國哲學起源”新説》,《思想戰綫》2001年第1期。。王叔岷則於此二説均持批判態度,認爲任何學術的産生都有淵源和時代兩個方面,不能片面强調其一。他認爲劉歆、班固只是從淵源方面看,《淮南子》則只知道從時代方面去看,而胡適從之,只有《莊子》能從淵源、時代兩方面去看(30)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講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頁。。吕思勉試圖調和二説,認爲兩者一個是“因”,一個是“緣”,他説:“凡事必合因緣二者而成。因如種子,緣如雨露。無種子,固無嘉穀;無雨露,雖有種子,嘉穀亦不能生也。先秦諸子之學,當以前此之宗教及哲學思想爲其因,東周以後之社會情勢爲其緣。”(31)吕思勉《先秦學術概論》,第2頁。
三、 諸子哲學發生學新論
上述吕思勉先生“因”“緣”之説是解決諸子哲學發生學問題的關鍵,但不能同意將西周的宗教、哲學思想看作“因”,更不同意將東周社會的情勢看作“緣”。我們認爲,西周社會的意識形態當爲“源”,而東周社會的轉型是爲“因”,諸子應對這個“因”所産生的不同“反應”是爲“緣”。試論如下:
前已提及,中國哲學的發生是以諸子百家的出現與争鳴爲標志的,胡適説:“大凡一種學説,絶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如果能仔細研究,定可尋出那種學説有許多前因,有許多後果。”(32)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5頁。發生學要做的就是尋找“前因”的工作。若將諸子哲學作爲一個整體看,它們的“前因”可分爲兩個方面: 一個是“淵源基礎”,一個是“直接原因”。前者指的是社會的意識形態,即西周以降的文化積澱,實質上也就是它們的思想的“源”;後者指的是當時社會的現狀,即東周時期的社會轉型,這是觸發諸子哲學産生的直接動力,這才是真正的“因”。若把它們分開來看,在發生的過程中,它們的思想各具特色,並最終形成了不同的學派。譬如植物,只有種子具備了適宜的土壤、光照、水分等環境條件才有了生長的可能,而不同地區具體的環境條件造就的植被卻有所不同,如針葉林生長在寒帶而闊葉林則在熱帶,沙漠中有仙人掌和胡楊,水中則有蘆葦和浮萍。這便是它們的“緣”,也即諸子分途發生的“特因”(相較於“因”而言)。
(一) 諸子哲學發生之“源”
在人類社會形成之初,當他們開始相信有靈魂的存在時,便出現了巫術,同時也産生了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顓頊之前,這種宗教崇拜的存在是一種自發、無序的狀態:“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國語·楚語》)而顓頊最大的貢獻就是“絶地天通”,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宗教性質的改革,將“家爲巫史”的家庭宗教上升成爲“國爲巫史”的國家宗教,而自發性質的原始崇拜也上升爲國家性質的信仰體系。而且,除了爲維護社會穩定而將神權收歸政權的動因之外,更重要的,顓頊的宗教改革“是爲了適應部落聯合體的需要,來營造一個爲各個宗族組織結構所普遍認同的宗教文化體系,以加强部落聯合體的凝聚力”(33)余敦康《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第19頁。。中國古典哲學及其所賴以存在的宗法社會的濫觴,最早可追溯至這種“宗教文化”。
唐虞時,由宗教傳統中的祖先崇拜衍生出了倫理道德觀念,《尚書·堯典》載有堯的“欽明”“允恭”“克讓”等德行,他能够以美德修身使得九族和睦,以致“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些修身之道簡而言之就是“允執其中”,蔡元培説這是“當日道德界之一大發明”(34)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5頁。。舜帝“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孟子·離婁下》),是中國孝道文化的始祖,“孝”是父系社會人倫觀念的核心,孟子稱贊説:“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離婁上》)《漢書·蓋寬饒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從堯舜時宗法觀念的萌芽到夏代把公共權力據爲己有、世代相襲,標志着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的出現。夏啓時有伐有扈之戰,其理由就是因“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所以“天用剿絶其命”(《尚書·甘誓》),這是一種早期的天命神學思想。同樣的,這種思想爲殷商所繼承,《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在“君權神授”觀念的支配之下,殷商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國家宗教體系,從衆多的文獻和考古材料看,殷商的宗教文化達到了一種高度發達的水準。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同意王國維所説的中國政治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35)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53頁。,但文化則不必然,因爲“小邦周”在文化上大大落後於“大邑商”的事實以及在建國之後大量承襲、改造殷文化的“制禮作樂”是顯而易見的,這是王氏理論的“不合理”之處。不過,在損益前代宗教文化基礎之上所造就的禮樂文化,確乎是一種“超越”和“變革”,這又是王氏理論的“合理”之處。
如果説在商代,禮文化是從屬於宗教的話,正所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禮記·表記》)。那麽,西周則恰恰相反,“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是爲宗教文化從屬於禮文化。他們將“德”融入了君權神授的觀念世界,在此基礎之上又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全新而複雜的禮樂制度體系。牟鍾鑒説:“禮樂文化脱離了巫教的初級階段,也超越了神道獨尊的中級階段,而達到了人神一體的高級階段,形成一種文明程度很高的東方文化傳統,並從這個文化傳統中孕育出儒學,爾後影響了中國數千年。”(36)吕大吉、牟鍾鑒《概説中國宗教與傳統文化》,《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卷二,第126頁。不僅儒學,諸子百家哲學皆是在這個文化傳統中孕育出來的。正如余英時所説,哲學的突破在古代中國有它獨特的文化基礎,那便是“禮樂傳統”(37)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92頁。。因此,西周完成了一個由宗教神學之禮到人文理性之禮的轉變。而只有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發達了,才具備哲學産生的條件。
一般認爲,哲學的最初源頭發端於宗教,中國哲學也不例外,也正是因此,諸多前輩學者對諸子哲學與宗教傳統的關係給予了較大的關注。但他們似乎忽略了一個介於二者之間的“承上啓下”的角色。因爲,諸子哲學並不是直接由宗教演變過來的,它們之間存在有一個“橋梁”,那就是“禮”,即西周的宗法禮樂文化,這才是諸子哲學所能産生的直接原因和基礎,也是中國文化暨中國哲學區别於其他民族文化和哲學的根本特徵,更是中國哲學之所以“合法”的原創性所在。
(二) 諸子哲學發生之“因”
馮友蘭論子學時代哲學發達的原因説:“自春秋迄漢初,在中國歷史中,爲一大解放時代,於其時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及經濟制度,皆有根本的改變。這是一個大解放、大變動、大過渡的時期,所以出現了諸子並起的哲學發達時代。”(3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3~28頁。張岱年也説:“至春秋時,社會的經濟基礎起了根本的變化,社會組織隨而發生動摇,於是舊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陷於崩潰,人民生活亦不安定起來。社會制度的變動,乃震醒人們的意識,遂引起了種種的哲學思潮。”(39)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緒論》,第9頁。誠然也,多元、開明、活躍的文化多産生於政治動蕩、社會紛亂之時,春秋戰國正是這樣一個“禮壞樂崩”時期,這是諸子生活的時代背景,更是諸子哲學發生的總原因,分述如下:
1. “儀”“義”分離後的論禮精言
凡事發展都有一個規律——“始簡而後巨”,禮制也是如此。西周後期,“郁郁乎文哉”的禮樂制度行之久遠,逐漸地繁瑣化和形式化,而禮儀内在的“禮義”卻喪失了。面對着“儀”與“義”嚴重分離,人們紛紛發表自己對“禮”的看法: 如對魯昭公“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左傳》昭公五年)一事,晉國大夫女叔齊認爲這不過是“儀”,是禮的末梢,不是真正的“禮”。再有鄭國大夫子大叔也認爲揖讓周旋之類的只是“儀”,真正的“禮”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這些重“義”輕“儀”的言論是後來文質之辯、德禮之辯的先聲,而七十子後學所著《孝經》更是直接套用子大叔的話説“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再如晉國大夫師服,認爲“名”是用來表達“義”的,“義”是“禮”的基礎,“禮”可以“體政”,而“政”是要“正民”(《左傳》桓公二年)。類似的,春秋時人們關於“名”“義”“禮”“政”“民”的關係討論是後來儒家“正名”學説、名家“名實論”等的思想來源。它如關於禮德關係、禮法關係,以及相關的天人關係、宗教倫理等方面的討論,這些都是東周時期“禮壞樂崩”的産物,也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的直接來源之一。
2. 西周官學的崩潰
西周之時,學在官府,官師合一,教師由官員擔任,這是西周教育制度的最大特點。其有大學和小學之分,大學設在都邑,小學設在鄉邑。《禮記·王制》曰:“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宫。”這些都是培養貴族子弟的官學。教育的内容,以鄉學爲例,《周禮·地官·司徒》載:“一曰六德: 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
東周時,伴隨着禮樂崩壞,宗法制瓦解,周天子地位下移,官學隨着王權的衰敗而没落。《論語·微子》載:“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何晏引孔安國注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40)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頁。因爲西周時樂官同時擔任着“樂教”的任務,“樂人皆去”標志着王官之樂散落民間,這正是整個西周官學體系崩潰的一個縮影。王官之學散落民間,使得原本只能貴族學習和討論的知識得以在民間傳播,私學便發生了。私學的實質就是西周官學的下移,所以,私學的内容大都没有脱離“六德”“六行”“六藝”的西周官學框架,不過是結合時代需求而做了一些創造性的損益、轉化和發揮。恰恰是這些損益、轉化和發揮,構成了東周時期百家争鳴的思想準備。
3. 各文化圈的交流互動
東周時期,分封制名存實亡,西周時大小千餘諸侯國,春秋時只剩百餘,兼併戰争此起彼伏,柳詒徵對此進行了概括:“魯兼九國之地;齊兼十國之地;晉兼二十二國之地;楚兼四十二國之地;宋兼六國之地;鄭兼三國之地;衛兼二國之地;秦有周地,東界至河;吴滅五國,北境及淮,越又從而有之。”(41)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那麽,衆多的小國併爲一個大國之後,由於它們之前的國家組織、社會狀況、政治、文化等均不相同,它們在新的國家内相互交流、碰撞後融合,也就逐漸産生了新的、獨具特色的思想文化。
各地文化的興盛最終形成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四個文化圈: 中原文化圈(即周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和秦晉文化圈。由於宗周文化與三晉、齊魯、荆楚等各地文化差異較大,隨着政治的多元化出現,它們之間再次的相互交流、碰撞,促使了文化的創新。這是諸子哲學産生的文化基礎。如此,結合上文私學的産生,我們可以總結出一條由西周王官之學到諸子百家争鳴的綫索: 王官之學—(散落)—私學—(交流)—地域文化—(融合)—四大文化圈—(交流)—諸子百家争鳴。
4. 士階層的崛起
西周社會的文化階層大概是巫祝卜史這一群體,但他們是上層貴族的附庸,具備的只是文化傳承而非創造的能力。隨着貴族人數的增長、禮樂制度的崩壞,矛盾衝突加劇、王官失守,社會上下流動頻繁複雜,而士階層正處於上下流動的中間環節,所以,包括巫祝卜史在内的一部分貴族下降成爲士或庶人,而一些庶人也有了上升的機會,“士的人數遂不免隨之大增”(42)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12~13頁。。文化傳播的力量是巨大的,原來的巫祝卜史在下層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帶動了士庶人群體的整體素質。而相反,貴族中的上層管理者在權利下移的同時,知識素養也下移了,楊寬説:“到春秋後期,上層貴族已腐朽無能,只有士還能保持有傳統的六藝知識。”(43)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頁。
本來,士是貴族中的最末一等,而正是因爲社會的轉型,使得“士”在禮樂詩書方面接受了長期的訓練而成爲博文知禮的專家,所以“當時對禮樂有真認識的人則只有向‘士’這一階層中去尋找”(44)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89頁。。也就是説,“士”已開始崛起並成爲社會的知識分子階層。君主們需要這些知識分子爲自己服務,目的自然是功利性的,但卻在客觀上促成了戰國時期的“養士”之風,總體呈現出“禮賢下士”的社會環境。换言之,士階層人數的壯大與社會職能的變化反過來使得“士”在戰國時期的地位得到提升,這正是諸子哲學的人才準備。
5. 政治環境寬鬆
東周時期社會大轉型,制度要變,新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運行模式等正在探索,總體趨勢是由之前宗法控制的國多邦小向中央集權的統一大國邁進,如何治理這個集權性質的大國?用何種制度?在“争於力氣”的國際環境中如何生存、發展、强大?這些便成爲當時的新的知識分子階層即“士”思考的問題,也是各國君主們所需要的在競争中生存下來的理論指導。這種局勢導致了一個客觀事實: 即學術和政治的某種程度的對等關係,也即知識和權利之間形成了一種相對平衡的關係。
讓我們來做一個假設: 使百家之説出現在那禮樂文化蔚然壯觀的西周鼎盛時期,它們勢必會被判爲“異端學説”而被無情地打壓下去,絶無争鳴之可能。同理,當統一的王朝到來之後,知識分子的遊學與争鳴對集權社會的穩定將造成威脅,於是有了“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的文化政策,百家争鳴的土壤便消失了。錢穆所説甚確:“蓋諸子之興,本爲在下者以學術争政治。而其衰,則爲在上者以政治争學術。”(45)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5頁。誠然也,政治愈穩固,文化越專制。正是由於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的用武之地大大提升,各諸侯國争相籠絡人才,政治空隙增大,知識分子在各國之間的流動變得更加的自由,學術的創造没有被過多的約束,思想的大迸發便成爲可能。也就是説,學術没有被政治勢力控制,思想家們的思想一旦自由,就意味着百家争鳴即將“水到渠成”。
(三) 諸子分途發生之“緣”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將先秦諸子分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劉歆《藝文志》則分爲儒、道、法、墨等“九流十家”,這爲我們研究諸子哲學提供了一個框架。但從胡適開始,學界多有反對之聲,認爲“六家”“九流”是漢人創的,不是先秦的真實情況。他們大致認爲: 先秦並未形成明確的學派,師承關係除儒墨之外並不明顯,對一些人物、子書的分類也不太確切。我們認爲,完全否定《史記》《漢書》對學派的劃分太過武斷,誠然,先秦確實没有明顯的學派之分的“名”,但卻有着儒墨道法等學派之“實”,每個學派的特色以及學派之間的争辯還是很明顯的,最重要的,各學派成員也有學派之分的自覺,這一點在《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書中均有體現。況且,學派的劃分絶不僅僅是爲了“敘述的方便”,而應該是對一種既定事實的肯定。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各國之間的戰争此起彼伏,原本禮樂和諧的穩定局面被打破,從中央到地方處處“君不君,臣不臣”,社會“禮壞樂崩”。由和諧到失序,失序要重建,處於不同地位和階層的人都在思考社會的重建之方: 有主張維護,有主張改良,有主張返歸,有主張變革,由此便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傾向。通俗地講,究根溯源,先秦諸子的思想學説皆是針對當時的社會所下的一劑藥,有温、有寒、有熱、有涼、有猛、有緩,出發點都是社會這個“禮壞樂崩”的病體,尋了各不相同而又相互關聯的路徑,最終的目的和歸宿又都是“把病治好”,期望重新走向“和諧安定”。
儒家的淵源可追溯至殷商甚至更久,但儒家作爲一個學派的開創則是由孔子開始。先秦雖無儒家之名,卻有儒家之實,不可一棍子打死;正如西周禮制雖無“成文法”之名,卻有“自然法”之實一樣。儒家無疑是要“復禮”的,孔子曾不止一次的表示“吾從周”。也有學者認爲儒家哲學的核心或實質是道德哲學或倫理學,而倫理道德的具體踐行則須以“禮”爲規範,比如“克己復禮爲仁”(《論語·顔淵》),再比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論語·泰伯》),如此之類不勝枚舉。
道家最是棘手,從他們的著作來看,他們對周禮的態度似乎是無情的抨擊。老子説:“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在這看似“反禮”的背後隱藏着道家復歸遠古質樸之禮的真相。也就是説,他們所反對的是當時社會那種變質了的“禮”,對原初的“禮”的本質卻是認可的,這在他們的著作中通過種種不明顯的方式反應出來。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人們自覺行“禮”之“實”而不知“禮”之“名”,這才是真“禮”,也即“道”。不過,到戰國末期,社會形勢大爲不同,先秦後期道家也逐漸轉變了態度,他們吸收儒家之禮入道,以“道”統禮,這也是戰國後期學術發展之趨勢所然。
法家最爲複雜,它有三個發展階段,經歷了一個對“禮”由“重”至“輕”、對“法”由“輕”到“重”的過程。早期法家以管仲、子産等爲代表,他們在看到禮樂制度衰微之後引“法”入“禮”,將原本從屬於“禮”的“法”單獨提出來,擺在輔助“禮”以治國的位置。中期法家以李悝、商鞅等人爲代表,他們將“法”從屬於“禮”的地位進一步提升,“禮法並重”,但他們的思想傾向又有不同,可分爲“法”“術”“勢”三派,商鞅便以“重法”著稱。後期法家以韓非、李斯爲代表,“禮”在他們那裏成爲了“法”的附庸,他們的思想帶有明顯的法治極端主義的傾向。
墨家也是崇禮的,與儒家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義利觀”,他們重“實功”,其思想學説透露出一種實用主義的禮學觀念。名家的“名實論”與“禮壞樂崩”關係密切,如“離堅白”“白馬非馬”等命題所體現出的名實相分的邏輯學無疑在“禮”的“儀”“義”相分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加速作用。兵家的思想來源與西周軍禮淵源頗深,他們在損益軍禮的過程中更爲注重“禮義”的發揮。如“上兵伐謀”便是對“大師之禮”中“宗廟謀議”這一項目的發揮,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則體現了軍禮“恤民”的禮義。
綜上所述,將諸子哲學的出現放在整個東周時期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之下,通過對諸子思想淵源的重新思考和審查,發現它們“源”於“禮”、“因”於“禮”更“緣”於“禮”,因此,對諸子思想的研究應該引入禮學的視野,這有助於我們更全面、更深刻、更系統地理解諸子、理解中國文化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