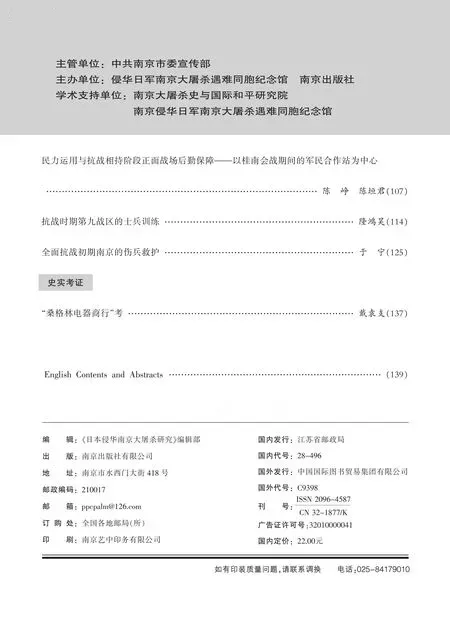图像与记忆: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中的南京大屠杀*
沈 俊 林敏洁
德国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在《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中提出,文学记忆包括三个层面的功能:存储、传播和暗示,文学作品可以根据不同的回忆方式来重构过去、传播不同的历史观、寻求各种记忆话语之间的平衡以及反思记忆集体的过程和问题。(1)冯亚琳等编,余传玲等译:《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246页。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通过真实世界与绘画空间的交织,将“德奥合并”“水晶之夜”“卢沟桥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及其记忆进行文学的重构。作品中出现的画作并非局限于艺术本体论的元隐喻,(2)元隐喻(meta-metaphor),隐喻研究术语之一。英国学者M.J. Reddy在论文The conduit metaphor: 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1993)提出“元隐喻”的概念,即“隐喻”在语言学意义背后所隐藏的人类思考和交际方式;在张锐、李劲辰的论文《论中国传统哲学隐喻化的语言观》(2009)中论述,当语言系统对真实世界进行逻辑化隐喻时,“元隐喻”便被制造出来,它是语言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L. David Ritchie在论文A note about meta-metaphors(2017)中指出,元隐喻就是对隐喻的隐喻,是对“隐喻”理论的实际应用;但汉松在论文《历史阴影下的文学与肖像画》(2018)中认为,《刺杀骑士团长》中大量对肖像画的描写是作者在“艺术本体论层面的反思”,是一种“元隐喻”,本文沿用这一说法。图像中一以贯之的是村上春树对战争记忆的伦理责任和美学阈限的深刻思考。
实际上,村上作品中有关战争历史记忆与主体意识话题的讨论早已引发学界关注。桥本牧子以1990年代日本围绕“历史”展开的讨论作为考量,认为村上的文本“对日本共同体的创伤记忆的恢复”以及“历史记忆主体性的再构造”具有“卓越贡献”;(3)橋本牧子「村上春樹『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論――「満州」と「トラウマ」」、『プロブレマティー ク』(別巻 2 越境の比較文化·比較文学)、2006年、80-95頁。刘研则认为在村上作品中“潜藏着一个在代际间传承战争记忆的叙事结构”,并“借此论述了战争记忆在当代日本自我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以及民族与战争历史情感记忆方面的复杂性”;(4)刘研:《记忆的编年史: 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叙事结构论》,《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林敏洁在论文“村上春树文学与历史认知——以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为中心”中论述了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思考,认为“画中及故事中蕴含着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代、国家与个人、政治与艺术、精神与肉体、强权与自由、人性与疯狂、地狱与人间、加害与被害等各种看似矛盾的种种因素”。(5)林敏洁:《村上春树文学与历史认知——以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那么在《刺杀骑士团长》这部小说的画作中究竟存储着怎样的南京大屠杀记忆?作者是如何对这段记忆进行提取、还原与再构的?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采取文本解读的方法,探析《刺杀骑士团长》中几幅画作的符号意义以及作者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历史反思。
一、肖像画:暴力记忆的导入与存储
作为后现代风格明显的作家,村上春树作品中对图像多有指涉,《刺杀骑士团长》主人公“我”的身份设定为中年职业肖像画画家,关于肖像画艺术价值的思考贯穿了全书,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这部作品中作者对“肖像画的本体论和再现理论所进行的自觉反思”(6)但汉松:《历史阴影下的文学与肖像画》,《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4期。。笔者想从书中两幅颇有深意的肖像画入手,展开对重要人物“免色涉”肖像画与“白色斯巴鲁森林人”肖像画中蕴含的主体与暴力记忆的讨论。
遭遇婚变的“我”在外游荡了一个半月后,应好友雨田政彦之邀住进郊外山间其父雨田具彦的旧居兼画室,其间接到神秘邻居“免色涉”为其作肖像画的委托。起初,“我”认为画肖像画不过是受雇于人、令人倍感厌倦的商业行为,实际与他见面之后,“我”便感到自己不得不为他画肖像画,体会到肖像画乃是将“画主”在画布上再现的过程。在叙事进程中,作者多次暗示“我”与“免色涉”的主体关联性:“他的人格——无论其内容如何——在我的画作融为一体”“我自认成功地使‘免色涉’这一存在跃然纸上”“那基本是为我(自己)画的画”“将表层意识和深层意识得心应手地交织起来”。当画作完成后,“免色涉”称赞道:“完美,这正是我想要的画”,还说这幅画代表画家与被画者“成功地交换了彼此一部分”。“我”与“免色涉”的关系也从一开始的亲近感,上升为“连带感”。(7)[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98页。这里的肖像画作为隐藏着主体性理念的显形之物,成为画家的某种自我投射,将“我”与被画者“免色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记忆的层面来看,笔者认为“免色涉”肖像画被作者赋予了两个重要功能:首先,“免色涉”肖像画具备导入暴力记忆的功能。村上春树出生于二战以后,毫无战场经验,对父辈历史记忆的梳理与还原开启了他探索历史的真相之旅,正如《且听风吟》《东尼泷谷》《1Q84》中的父辈形象都有对于中日战争历史的指涉。《刺杀骑士团长》中第一次出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叙述与讨论,便是在“我”为“免色涉”完成肖像画的过程中,可以说,正是通过“免色涉”肖像画,村上为读者导入了南京大屠杀记忆。生于战后、不了解战争的年轻人“我”与存储着暴力记忆、父辈形象的“免色涉”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符合村上文学惯有的叙事模式,而“我”与“免色涉”的主体关联性也是对暴力记忆在代际间传承的隐射。其次,“免色涉”肖像画具备揭露真相的功能。“免色涉”在“我”的眼中,为人慷慨、温文尔雅、格调不俗,对历史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理想的“肖像画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发现与画中的人不同,真实的“免色涉”身上隐藏的暴力倾向开始慢慢浮现:他为了接近秋川真理惠,不惜用强硬手段买下她家对面的豪宅,并想方设法弄到军用望远镜,目的就是为了随时监视她。在解救失踪的真理惠的高潮段落,“我”发现最危险的人物原来就是“免色涉”。“骑士团长”说,“免色涉”是“危险的、非同寻常的存在”,并暗示真理惠的母亲是被“免色涉”毒杀致死。村上隐晦地表达了“免色涉”这个人物在其完美的画像外表之下隐藏着某些“恶”之记忆,正如他家中密室里的衣柜,还收纳着秋川真理惠母亲生前穿过的衣服,“这个秘密他决意不向任何人揭示”。(8)[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20页。“免色涉”这个形象在村上文学谱系中,对应的是带着战争暴力记忆存活下来的父辈形象。村上曾这样描述日本二战时期对亚洲各国犯下的暴行,“那是我父辈和祖父辈的罪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9)Rubin Jay.Murakami Haruki and the War Inside. Imaging the War in Japan: Repres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Trauma in Postwar Literature and Film. Ed. by David Stahl,Mark Williams. Singapore: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0:P.63.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二战历史欲盖弥彰的暧昧态度,使得具有战争记忆的父辈们变成了“免色涉”,他们将暴力记忆藏入“衣柜”,从不示人,隐蔽性很强且具有传承性,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与“恶”再度显形,成为“既是‘免色涉’,又不是‘免色涉’”(10)[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第220页。的危险之物,这也是村上通过“免色涉”肖像画想要表达的担忧。
如果说“免色涉”肖像画象征的是隐藏着暴力记忆的父辈形象,那么,“白色斯巴鲁森林人”肖像画无疑是“我”内在暴力倾向的强烈隐喻。“我”第一次出现便是“我”与一夜情女子偶遇之时。与这名女子的危险性行为引发了“我”内在暴力的释放。其后,当“我”与雨田政彦聊及军队暴力体制以及南京大屠杀时,“我”的眼前都会出现与该女子暴力性行为的画面,可以说,这是村上以性暴力为基础,展示暴力的不同表现方式及其多重结构,而“白色斯巴鲁森林人”即是暴力的见证物,同时也象征了“我”心底深层的愤怒与暴力。作者通过一个梦境直接挑明了“我”与“白色斯巴鲁森林人”的关系:梦中的“我”在宫城县海边一座小镇握着“白色斯巴鲁森林人”方向盘(现在它是我拥有的车)。“我”身穿旧的黑色皮夹克,头戴带有尤尼克斯标志的黑色高尔夫帽。“‘我’身材魁梧,皮肤黝黑,花白头发短短的硬撅撅的”。(11)[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如果把梦境理解成人的潜意识的话,“我”在潜意识中就是“白色斯巴鲁男子”。这里“花白头发”与“免色涉”最重要的特征“银白头发”呼应,暗示了暴力性的传承。当“我”意识到自己即是“白色斯巴鲁男子”,也意识到暴力记忆复苏导致的恶劣后果时,“白色斯巴鲁森林人”明确地拒绝“我”:“不许把我画成画!”(12)[日]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林少华译,第105页。换言之,“我”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暴力记忆分离,这也呼应了小说引言中所述,“迟早总会画出无面的肖像,如同‘刺杀骑士团长’(画像)一般,我必须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13)[日]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林少华译,第3页。暗示着“我”需要时间对暴力记忆进行梳理并克服。那么,对完成“自我像”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刺杀骑士团长”究竟是怎样一幅画呢?
二、雨田之画:南京大屠杀记忆的还原与再塑
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提出,图像存在着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记忆媒介的图像”,是“被观察的客体”;另一种则是“作为回忆的特殊形式的图像记忆”,或者说是“幻想”。(14)アライダ·アスマン『想起の空間――文化的記憶の形態と変遷』、水声社、2007年、18-58頁。“免色涉”以及“白色斯巴鲁森林人”的肖像画属于前者,这些记忆媒介的图像唤醒了主体“我”的暴力性;而雨田具彦所作之画“刺杀骑士团长”(15)小说主人公“我”受好友雨田政彦之邀请,住进其父雨田具彦(著名日本画画家)的旧居兼画室,意外在阁楼发现了一幅雨田具彦不为世人所知的大师级作品,名为“刺杀骑士团长”。,既是作为记忆媒介的图像具有唤醒功能,又是作为回忆的特殊形态的图像成为某种特异力量的象征,召唤尘世之外世界的经验,而这与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联,需要将“刺杀骑士团长”之画存储的记忆取出,并解读出村上对这种记忆的想象、修复与建构。
“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作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第一幕第一场唐娜·安娜的父亲骑士团长被唐璜所刺杀的情景,画面中共有5个人:穿着飞鸟时代(16)飞鸟时代约始于公元593年,止于公元710年,因政治中心奈良县的飞鸟乡(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的服装,一个年轻的男子把剑刺入了年老男人的胸膛,一旁站立着一位放声大哭的年轻女性和一个单手拿着账本的年轻男性,画面左下角有一个男人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男子把地面上的封盖顶开一半,从那里伸出脖子,露出长长的脸(17)即后文的“长脸人”。。这个奇妙的目击者也引发了“我”的思考,“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了什么而如此潜入古代地下的呢?”村上继续给出暗示,“是雨田出于某种意图将此人补画在画面中的。”并且,(此人)出于慎重而在确认事件的细节。(18)[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第187—188页。至此,读者大概能猜到“长脸人”是通过记忆之穴穿越到了古代,来目击和核实这场决斗的记忆,在后续的情节中,“长脸人”撕开画面,“我”由此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可见,“长脸人”扮演着导引记忆的角色,象征着唤醒记忆与读取记忆。果然,雨田具彦的记忆通过其他人的讲述,逐渐在“我”面前拼贴成完整的画面:在西洋画领域被寄予厚望的雨田具彦留学维也纳,在此期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合并,希特勒的暴力统治越来越激烈,雨田具彦参加了反纳粹的地下抵抗运动,和同伴一起计划暗杀纳粹高官。可是,计划泄露,同伴们相继被盖世太保逮捕杀害,在维也纳的恋人也被强制送往集中营,只有雨田具彦一人活了下来,被遣返日本。作者暗示,之所以能独活,是因其家族费尽周折,更重要的背景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其结果,日本和德国进入明白无误的同盟关系”。(19)[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第226页。可以想象,对这样一段记忆,雨田家族一定是噤若寒蝉,雨田具彦本人也根本无从诉说,“他因此怀有的愤怒和哀伤想必是极为深重的。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抗世界巨大潮流的无力感、绝望感。其中也有单单自己活下来的内疚”。(20)[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第226页。画作“刺杀骑士团长”可以理解成是原本要发生的暗杀纳粹高官事件在断裂的记忆空间里的修补,弥合他内心暗杀未遂的悔恨和独活的罪恶感,于是“我”在文中推想,“唐璜”是雨田具彦,“骑士团长”是那个本该被刺杀的纳粹高官。
雨田具彦悲惨的战争记忆与《刺杀骑士团长》小说第一部中其胞弟雨田继彦的遭遇有类似的地方。继彦作为音乐系在校学生,阴差阳错被征兵送往中国战场,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并参与虐杀,这样的战争体验令其心理受到重创,最终在回国后无法释然,自杀身亡。但他的死被家族封锁,是由于“在那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社会,trauma(创伤)这样的单词与概念毫无用处。一句性格懦弱,没有骨气,缺乏爱国心的话就可以打发了。当时的日本,既不去理解,也拒不接受这样的‘懦弱’。它只能作为家族的耻辱,被暗中埋藏”。(21)[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第99页。在这里,作者无需再暗示什么,对军国主义的暴力本质以及对战后记忆策略的批判昭然若揭。与哥哥留下画作相似,继彦将这段记忆通过遗书的形式保留下来,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可谓惊心动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在各地历经激战,杀人行为、掠夺行为一路反复不止”,进入南京后被上级命令用军刀砍杀俘虏,“若是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可以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扫射。但一般步兵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使用刃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扬子江有很多鲶鱼,一个接一个把尸体吃掉。听说靠吃这些死尸,当时的扬子江里有些鲶鱼肥如马驹”。接下来,这段转述继彦遗书中被迫砍杀俘虏的记录最为暴虐:上级军官递刀给继彦,要求他砍掉俘虏的头。继彦“并不想做这样的事。可是倘若违背上级的命令,事态就严重了。单单接受惩罚是不能完事的,因为作为帝国陆军,上级的命令便是天皇陛下的命令。他颤抖着举起了军刀。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大力气,那军刀也只是那种批量生产的便宜货,人头没能轻而易举地斩断。而他也没能紧接着补刺一刀,令其断气。四下一片血海,俘虏痛苦地满地打滚,那光景悲惨至极”。(22)[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第99页。村上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表现备受日本右翼攻讦的“南京大屠杀”,这其实是与试图淡化和掩盖战争记忆的暧昧言论的一种决算。他在展现战争记忆对人内心造成的摧残的同时,将战争责任直指天皇以及天皇制度下麻木不仁的军队,不得不佩服村上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尊重历史记忆的良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村上笔下,雨田两兄弟并非完全是受害者的形象。哥哥的独活、弟弟在南京的虐杀,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加害者的行为,这种加害与被害相互交织的设定是作者让罪责和良心在记忆空间发挥审判功能,在(日本)集体记忆的受害者身份认同中撕出裂缝,成为记忆带给他们在战场之外严重且隐秘的创伤,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日本直面战争责任并深刻反省战争发动机制的根源性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有了进一步的解读空间:“唐璜”代表的是热爱艺术、本性纯真的年轻人,“骑士团长”代表的是“恶”“暴力”的体制,雨田具彦创作这幅画实际是通过想象的“刺杀”对过去经历的记忆进行再造,从而治愈时间的创痛。至此,村上通过传统的“导入、储存、取出”的回忆范式,实现了某种“过去经历记忆的再造”(23)アライダ·アスマン『想起の空間――文化的記憶の形態と変遷』、水声社、2007年、18-58頁。,完成了个体记忆的修复,但这些尚不足以构建一个新的记忆空间。
三、隐喻空间:大屠杀记忆的反思与重构
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指出,新的记忆空间的形成有别于“感知、回望、反应”,不再指向事件的重复,而是建构一种具有“反思性”以及“情感可重复性”的记忆空间,而这样的建构“需要某种灵光闪现的时刻”。(24)アライダ·アスマン『想起の空間――文化的記憶の形態と変遷』、水声社、2007年、61頁。村上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安排了这样“灵光闪现的时刻”:为了找回失踪的秋川真理惠,“骑士团长”主动请“我”将其刺杀,通过重演画中场景,引出画中另一人物“长面人”,即前文提及的记忆的导引者,“我”得以进入“隐喻世界”,在这个空间中,作者对记忆进行了重构并解开了一系列主体隐喻的谜底。例如,“骑士团长”说:“诸君杀的不是我,诸君此时此地杀的是邪恶的父亲。杀死邪恶的父亲,让大地吮吸他的血。”(25)[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第234页。如前文所论,在作品中“父亲”具体的投射人物是“免色涉”,“骑士团长”进一步提示,“免色君本身不是邪恶的人……但与此同时,他心中有个类似特殊空间的场所,而那在结果上具有招引非同寻常的东西、危险的东西的可能性。”(26)[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第354页。这再次呼应了村上文学系谱中带有邪恶记忆的父辈的形象,也明确了作者一直以来的焦虑:这些被封闭在常人看不见的“特殊空间”中的战争记忆将会导致极其危险的结果;“免色涉”与秋川真理惠类似父女的关系,可以对应画作“刺杀骑士团长”中“骑士团长”与少女的关系,而“我”将真理惠视为妻子与已故妹妹的综合体,“我”可以视为“唐璜”的替身,刺杀完成后,真理惠被救出,印证了“免色涉”即是“邪恶的父亲”,但前文也分析了“我”与“免色涉”的连带性、继承性,杀死他,意味着对自我历史的清算与断裂。
在“隐喻空间”中,“我”通过刺杀“邪恶的父亲”制造了与暴力记忆的断裂,这是村上对父辈们屠杀成千上万平民战争记忆的揭露与反思,除此之外,“隐喻空间”中还包含有作者对暴力发生原因更深层的思考。如前文所论,一直说着“你小子在那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并拒斥被“我”画出来的“白色斯巴鲁森林人”,其实是“我”的“本我”。而在“隐喻世界”中,他变成了危险的“双重隐喻”,“某个扁平的什么在黑暗中往我这边爬来”,(27)[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第277页。试图吞噬正在洞中爬行的“我”,这说明“我”警觉于欲望之本我对“我”的控制;按照唐娜·安娜的说法,“双重隐喻”“早就住在人体内深重的黑暗中,捕食人的正确情思,吃得肥肥大大”(28)[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第273页。,这暗示着村上意识到“暴力”的产生糅杂着各种政治、环境因素和人性因素,如同本我的邪恶潜伏在任何人身上,属于集体性、无意识记忆的范畴,这也是村上对当下日本社会的警示,如不吸取教训必将重蹈历史覆辙。
四、创作动机:对日本战后记忆危机的指涉
以上通过分析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几幅图像的内涵,解读了村上春树围绕南京大屠杀记忆展开的提取、还原与再构的过程以及作者对于这段记忆所进行的历史反思。村上曾经被批评不关心政治、历史问题,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关于战争记忆的作品?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日本社会愈演愈烈的记忆危机有关。
长期以来,日本官方主流媒体刻意强调日本二战受害者的身份,而遮蔽战争中日本作为加害者侵略亚洲各国的记忆。1990年代,关于二战中对亚洲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记忆叙述问题成为日本各界的争论焦点(29)成田龍一『「戦争経験」の戦後史―語られた体験/証言/記憶』、岩波書店、2010年、254頁。,历史修正主义、历史自由主义伺机而动,大肆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否认日本战争责任,压制受害者的声音。事实上,依据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审判结果,南京大屠杀史实是在国际社会法律层面得到确认的。尽管铁证如山,战后日本并没有形成承认并反思的历史共识,“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美化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行,受到进步人士的谴责和批驳,形成了肯定派、虚构派、中间派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论争史”。(30)徐志民:《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来自中国学界的观察》,《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到21世纪初,右翼学者、政客与某些主流媒体合流,出版著作,拍摄影片,不遗余力地宣扬“南京事件虚构论”,试图从日本“国民的记忆”中抹除南京大屠杀。例如,2010年,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公布前后,日本媒体大肆宣扬中日双方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上的“鸿沟”,试图抹杀双方共同认定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实这一重要成果。(31)[日]笠原十九司著,高莹莹译:《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与南京大屠杀论争在日本的终结》,《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这样的争论和舆论导向,“使得大多数日本人逐渐退缩,最终成了旁观者。这也是南京事件的历史认识难以在日本社会形成固定共识的巨大障碍”。(32)[日]笠原十九司著,罗萃萃、陈庆发、张连红译:《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序言第5页。在这样的背景下,村上春树毅然拿起笔参与了战斗。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他明确写到了南京大屠杀并表达了他对大屠杀人数争议的看法。相关记述出现在第二部《流变隐喻篇》第三十六、三十七章,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是的,就是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杀人。有同战斗相关的杀人,有战斗结束后的杀人。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把投降的士兵和市民的大部分杀害了。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33)[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第81页。。村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大屠杀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对数字的争执不过是极右翼分子与政客们转移视线的惯用伎俩,侵略暴行不容置疑。
在《刺杀骑士团长》写作期间,村上春树在安徒生文学奖颁奖礼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影子的意义》的获奖演说,主张人和国家都要学会与痛苦的记忆共存,而不是强行改写历史,“只顾自己利益来改写历史,结果仍只会伤害自己。”(34)环球网报道记者 余鹏飞:《村上春树获安徒生奖 演讲对修改历史者敲警钟》。 全文参照:May 13 2020 〈http://news.cri.cn/20161031/48ae1a18-79a9-76de-db60-a966a7411a58.html〉《刺杀骑士团长》发表后,村上接受媒体采访,当记者问由于《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背景有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阴影,他对该画怀有怎样的想法时,村上回答:“历史乃是之于国家的集体记忆 。所以,将其作为过去的东西忘记或偷梁换柱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同历史修正主义动向)抗争下去。小说家所能做的固然有限,但以故事这一形式抗争下去是可能的。”(35)林少华:《刺杀骑士团长:置换,或偷梁换柱》,《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27日第8版。这些都表达了村上春树对战争记忆与日本主体性倾向的深刻思考与担忧,《刺杀骑士团长》可谓是村上对日本战后记忆危机现实的指涉。
结语
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的那样,在“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堪为典范的自杀、令人悲痛的殉难、暗杀、处决、战争以及大屠杀……这些激烈的死亡必须被记忆/遗忘成我们自己的”。(3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在统合日本国家记忆时,本文所论及的南京大屠杀记忆会成为被销毁的历史而被遗忘,这是集体记忆策略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战争已经是上一辈人(甚至是上上辈)的经历,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无甚兴趣也无从考量。然而,这些战争的真相却是关乎日本、亚洲乃至全世界和平发展的命运所在。尽管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70余年,战败的日本既没有对它所发动的战争承担足够的责任,也没有对这段记忆做正确的梳理,而只是将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记忆传递给后代,这种对战争记忆歪曲与捏造的企图只会加剧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不确定性。值得庆幸的是,包括村上春树在内的很多战后出生的作家们能正视这个问题,并主动了解、梳理、还原、揭露日本二战时期有关战争暴行的历史,通过文学的创作参与重建历史记忆叙述的真实。正如有学者指出,“以《刺杀骑士团长》为契机, 村上春树引导读者重温历史, 并通过战争记忆呼唤和平友好。”(37)林敏洁:《村上春树文学与历史认知——以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纵观《刺杀骑士团长》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写,恐怖、残暴、荒谬、丧心病狂的图景只是其表象的呈现,作者真正想展现的是暴力记忆带给受害者乃至加害者长久的创伤体验以及蝴蝶效应般的持续影响。对于日本战后那些为了将暴力正当化、合理化而产生的荒诞怪论,村上坚决予以回击,用文学表达的方式与官方刻意回避、弱化的记忆策略展开了搏斗,以其高超的艺术技法打破遮蔽、还原过去、建构起新的记忆空间、拓展历史记忆的话语和范畴。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言,盼望子孙后代幸福的心愿和有关“天使获得自由”的理想只能来自过去,“以无数被屠戮”和“被奴役的祖先的名义”。(38)[德]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著,金寿福译:《关于过去视域的建构》,《文汇报》2015年12月1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