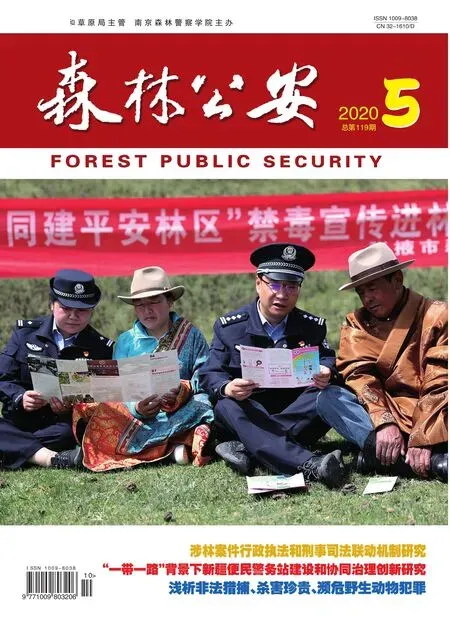涉“异宠”类野生动物犯罪的特点、成因和治理对策
薛 培 马文涛
2019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野生动物异域宠物全球贸易报告指出,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年交易额300亿~400亿美元,其中200亿美元为非法贸易,而“异宠”贸易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之一。据前瞻产业研究院行业报告称,早在2016年中国就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大宠物消费市场,预计2023年宠物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而其中以鸟类、两栖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为主的“异宠”占市场规模的2.2%,比例不高但呈不断增长的势头。互联网贸易的爆发式增长,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显著加剧了依托“互联网+”的野生动物犯罪愈演愈烈之势,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治理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现阶段加入的国际公约、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野生动物资源的所有权制度与管理体制的局限性,成为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有效规制的障碍。
一、当前非法买卖“异宠”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特点
(一)“产业化”趋势凸显
大多数以养个性宠物而引发的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均呈现出“产业化”发展态势。涉案人员中,既有以贩卖野生动物为业的走私商、进口商、源头经销商、分销商,也有不直接经手野生动物(或经手少)靠串联上下家供需信息促成交易并抽佣渔利的中介、代理人以及单纯的“异宠”爱好者、玩家,形成了庞大的非法买卖网络。办案中甚至发现,部分涉案人员还是动物园或者公园内动物表演展示场所的承包者、经营户、从业人员,或是曾从事野生动物救助工作,熟悉野生动物品种、品相、价格、稀奇度。如2018—2019年四川省成都市森林公安局查办的“4•21”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系列专案,反映出销售地域广、贩卖数量大、涉案人员多、销售转卖环节复杂等特点,涉案人员几乎涵盖了从走私商、源头经销商到玩家的所有身份,涉案动物1000余只,销售去向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犯罪低龄化及社群化
由饲养稀奇古怪的“爬宠”等“异宠”类野生动物热引发的涉野生动物犯罪,与传统的食用或者制作动物制品的涉野生动物犯罪相比,前者低龄化犯罪趋势明显。通过检索裁判文书网发现,青少年“异宠”消费者因此而遭受刑罚的情况逐年增多,比重也越来越大。此外,涉案人员多因共同的喂养、把玩“异宠”兴趣聚合于论坛、QQ群、微信群进行交流,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发布广告或者寻找货源,以自己的微信、支付宝或者以非法渠道购买的他人微信和支付宝账号作为支付手段,形成较为固定的同好圈,具有很强的内向性、隐蔽性,不太为圈外人所知。
(三)“网络+快递+网约车”成为非法交易常态
近年来随着涉野生动物犯罪执法力度不断加大,线下实体及大型电商平台非法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随着电商渠道微商化,犯罪分子依托网络社群的“异宠”同好圈,摆脱了对大型电商平台的依赖,形成了个性化的隐秘网络销售渠道,加之快递业和网约车的快速发展,“网络+快递+网约车”成了非法交易常态,有的多次转手后难以查清微信、QQ昵称对应的涉案人员。有的案件还反映出,“异宠”类野生动物案的源头经销商,依靠在论坛和公众号发布科普软文引流,筛选出异宠爱好者加为好友,并从中培养一批分销商、中介、代理人,然后在每次货物走私入境前,提供“异宠”视频图片供中介、代理人在微信朋友圈投放广告,收集市场需求信息,并根据客户需求个性化定制选购,到货后再由源头经销商或分销商直接通过异地快递物流加同城网约车匿名、谎报品名配送发货,从而大大降低被查处的风险。
二、“异宠”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现象的成因
(一)猎奇消费引发产业化犯罪
强烈的消费需求和巨大的经济利益是“异宠”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高发的根本原因。末端消费者出于猎奇、追求个性化等心理需求喂养“异宠”,在青少年群体中日渐成为潮流,引发了上游大量违法动物交易。某些所谓的珍奇动物几次转手可以从数百元加价到上万元人民币,而上游经销售一批次可以出货数百只,巨大的利润催生了野生动物境外盗捕盗猎、人工繁育、走私进口、国内养殖场“洗白”、分销直销等职业化、产业化犯罪的出现。同时,上游经销商为开拓销售渠道,又利用论坛、公众号、朋友圈等渠道普及、推广异宠知识,引诱更多看客入场消费,“异宠”同好圈群体越滚越大,引发的非法动物交易就越来越多。“异宠”猎奇消费无形中催生和助长了非法动物交易产业链,造成全球野生动物资源破坏,外来生物入侵等生态灾害(如绿鬣蜥在我国台湾地区泛滥成灾),甚至有可能带来新的疾病、疫情及公共安全健康问题等。
(二)“互联网+”犯罪致使打击处理困难
一方面,该类犯罪分子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交易中频繁更换账号,交易账号与收支款账号不同,商谈使用暗语代称,寄收件使用虚假信息等情况,甚至找人代为收(提)货和利用网约车同城送货,发现犯罪难度大。另一方面,由于此类小众爱好群体以网络聚合,人员遍布全国,圈内信息传播快,一人落网,立即全网皆知,交易上下家可以立即销毁交易证据、丢弃涉案动物,导致侦查取证被动。再一方面,涉案“异宠”类动物多为非原产于我国的境外动物,饲养环境要求高,容易死亡,据统计,至少四分之三的宠物蛇、蜥蜴、陆龟和海龟会在家庭饲养一年内死亡,客观上造成交易实物查获不易,使得无法获取定案所需的司法鉴定。
(三)快递行业监管失守失范
我国《邮政法》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邮政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并执行邮件收寄验视及实名制度,禁止寄送活物等。但在实践中,通过非法运输这一环节查获的案件占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件的比例超过50%,凸显出落实快递实名制和开箱验视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将对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的打击放在与猎捕、杀害同等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凸显出我国对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刑罚的严厉。但部分快递业从业人员受利益驱动为了扩大业务量,为犯罪分子寄送动物提供便利,违反邮政业相关管理法规规定,违规寄送活物、不履行快递实名制、执行收寄验视规定不严、发现问题不及时向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等监管失范情况突出,有的快递人员甚至还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侦查人员调查动向。
(四)法律滞后导致定罪量刑难
一方面,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对象涉及的范围较窄,特指的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但并没有将所有野生动物涵盖进去,且社会价值这个概念过于宽泛,界定过于模糊,使得法律在实践应用方面很难开展。另一方面,目前市场上的热门爬宠,包括平原巨蜥、高冠变色龙、泰加蜥蜴、绿鬣蜥、球蟒、红尾蚺等物种在内的多数“异宠”,属于非原产于我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保护动物,虽已纳入刑法保护,且最高法《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买卖此类动物“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需参照该司法解释附表内的国内同属或同科重点保护动物的数量来确定量刑幅度,但该附表并未涵盖所有重点保护动物纲目科属,实践中因查处的涉案物种往往找不到对应的参照动物,或者即使找到对应的参照动物但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划定的动物保护级别不同,贩卖数量再多也只能以一般情节量刑处罚,造成量刑偏轻缓,甚至有贩卖数百只“异宠”动物判缓刑的案例,犯罪嫌疑人即使被查处,也很容易在高额利润驱使下再犯。
此外,“异宠类”野生动物交易产业化分工明晰,有分销商、代理人和中介参与其中。货物拥有者、实际发货人、洽谈交易者可能并非同一人,也并非在同一地,一次交易中可能有多层中介参与介绍。案发多因单个交易环节疏漏,很难同时查获上下游多层级涉案人员及货物,此类案件多出现“有交易记录但未查获实物、有查获实物但无交易记录”的证据困境。由于刑法未规定野生动物“持有型”犯罪,即使现场查获大量野生动物也无法直接定罪,而查获交易人员、交易记录未查获实物又面临无法认定交易动物物种和保护级别的难题,普遍存在公安机关查获笔数多,但是审查起诉、审判环节认定笔数少的情况。
三、推动解决涉野生动物社会治理问题的具体路径
(一)完善立法是根本
一是改变现有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思路,从分级分类重点名单保护,向全面保护加例外清单思路转变。二是推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同步修订,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中增设野生动物及制品“持有型”犯罪,以节省司法资源,加大野生动物犯罪打击力度。三是对司法解释关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保护动物的犯罪情节认定标准进行修订,明确找不到国内同属同科参照动物或参照动物保护级别不同情况下的犯罪情节认定规则,并改变司法解释中唯以数量作为涉动物活体犯罪情节是否严重标准的弊病,以平衡司法解释滞后与社会治理、办案现实需要之间的不匹配关系,从源头上控制野生动物走向市场。
(二)强化共治是关键
一是在法律及司法解释未进一步修改之前,司法机关应加强合作,加大对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形成协同治理机制和体系,必要时可组织联合开展打击快递企业、从业人员参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专项行动;推动建立野生动物资源类或自然资源类刑事案件集中管辖制度,由专门的检察院、法院或专门的内设机构集中办理,提升司法专业能力。二是深化两法衔接运行机制,监督行政案件办理并及时移交刑事司法,着力推动野生动物行政执法权统一行使,改变公安、林业、水务部门多头管理的现状,提高执法效率。三是积极探索拓展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研究跨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公益诉讼提起方式、异地检察机关协同提起公益诉讼的可能以及非我国原产野生动物犯罪的受损生态修复方式,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及单独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穷尽一切手段,让涉案人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三)落实责任是基础
一是落实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及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杜绝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广告,同时建议通过设置关键词、暗语监控等手段,加大查处打击力度。二是落实快递企业的主体责任、法律责任,坚决落实快递行业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执行收寄验视、寄递实名制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安、邮政、工商等主管部门报告,相关主管部门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引导、规范快递行业发展。三是落实公众社会责任,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宣传、法律宣讲、以案说法等,探索建立非刑事、行政惩戒机制,积极引导不滥杀、滥捕野生动物,不购买、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规范饲养宠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