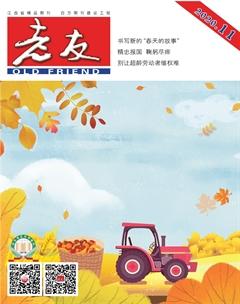穿着的变化
陈孜
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与穿衣有关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一是1968年1月我结婚时,用5尺购布证、7元多钱买了一块红灯芯绒布料,请老裁缝为妻子缝制一件外衣,衣服因布而得名“灯芯绒”。新婚妻子穿着“灯芯绒”出门,村里人羡慕极了,都说:“他的老婆穿得这么洋气,家里肯定很有钱。”殊不知,妻子的这件“灯芯绒”,算是当时说亲时媒人提出的“最高彩礼”,也是最高档的婚衣。我讨这门亲,总共花了将近500元钱,不仅花光了家里人全年在生产队劳动得到的分红,还背了一身债。
二是1978年冬天,我带女儿去表婶家做客。一进门,表婶双眼紧盯女儿穿的棉袄对我说:“缝补破衣裳的布料,颜色要一样啊!”这时我才注意到女儿衣服上的补丁形状各异,且有红、蓝、白几种颜色,乍一看就像几何拼图。女儿的这身穿着,让我既尴尬又难受!表婶是个热心肠的人,当即将女儿的棉袄脱下,在衣橱里寻了一件小表妹穿过的衣服给女儿换上,虽大了点不是很合体,但总算遮了“羞”。事后,妻子告诉我,女儿穿的衣服都是用老大老二两个儿子穿旧了的衣服改的。因无钱添置新衣,孩子们穿衣都是大的穿了给小的,缝缝补补凑合着穿。破了也找不到合适的布,只好拿几块不同颜色的破布缝补上。女儿走亲戚都不能穿件好衣服,对此我心中一直深感愧疚!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贯彻落实分田到户的政策,我也参加了工作。几年过去,家里很快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穿打补丁衣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改革开放仅几年时间,尽管生活逐步改善,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够开放,穿着比较单一。1987年,台湾当局迫于形势,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那年年底,一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的姓彭的先生携妻子回大陆探亲,一时间在家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天,我妻子从集镇买东西回到家,一脸诧异地告诉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一男一女,穿着打扮得像妖怪,引得许多赶集的人围观。”事后得知,其实那位彭先生穿的只是一套深灰色西装,他妻子也就是一身红绿相间的外套。我笑了笑对妻子说:“你这是少见多怪。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那样时髦的穿着。”妻子听了却一本正经起来:“我才不信。能有今天这没缝缝补补的衣服穿,也就不错了。人家那种‘洋衣服,莫说没有,就是有都穿不出去!”
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亲们生活迅速改善,穿着越来越讲究,色彩也从单一变得五颜六色。我们全家的穿着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儿女们办婚事,彩礼根本不提穿着。按照他们的说法,时代在变,穿着也要随着变,款式一时一个样,头年买,第二年就跟不上潮流了。最可喜的是,老伴看着村里老年人穿着花样不时翻新的漂亮衣服,思想观念也转变得“老来俏”了。她穿的每件衣服,都要到高档服装店去挑选,不光布料质量要好,而且衣服颜色要艳丽光鲜,四季服饰的搭配讲究得体。每当我和老伴走亲访友或外出旅游时,老伴对穿着就更为讲究,从壁橱里拿出一件又一件不同色彩的衣服比比试试,还不无得意地问我:“老头子,你看哪件穿得更好看?”看着老伴对穿着也如此讲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总是顺着她的心意说:“好看!你穿哪一件都好看!”
穿着的变化,更引起台湾同胞的密切关注。随着两岸“三通”的正常化,家乡人到台湾旅游已成时尚,每到一处,高档的穿着、多彩的打扮,都会引得台湾同胞的啧啧称羡。20世纪90年代后期,村里一位陈姓台湾退役军官,向往祖国改革开放发生的巨变,决定回家乡定居养老。当他踏上故土,乡亲们对西装革履不再有看“西洋镜”的感觉了,倒是乡亲们绚丽多彩的穿著令其耳目一新。他不无感慨地说:“台湾当局的报纸电台,都在宣传大陆生活贫困,人们缺衣少食。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我总算亲眼看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责编/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