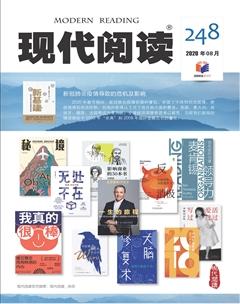汉武帝盛世的军事改革
汉武帝承接文景之治,改弦更张,不再无为而治。他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然后征战四方,尤其是北伐匈奴,经过几次阶段性战役,在漠北决战中重创对手,迫其西迁,充分显示了军事改革的成果。
汉武帝刘彻是个不甘心守成的皇帝。在诏书中,他不止一次表达改革的愿望,并寻找各种“借口”。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他从自然界找理由:“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公元前122年(元朔六年),他又从历史上找依据:“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当然了,这些都是包装,褪去外套,最本质、最核心、最真实的东西显露出来了——汉武帝内心难以遏制的扩张欲望。
汉武帝摆出对匈奴开战的理由,重点说到世仇。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御驾亲征匈奴,不料在白登山(今大同市东马铺山)陷入匈奴30万骑兵四面围困,险些创造开国皇帝被俘的尴尬纪录。经此大挫后,西汉一直对匈奴采取守势战略,并以“岁岁纳贡”为代价换取对方不内侵。匈奴对西汉“孝敬”的礼物照单全收,不够用时还在边境侵掠,每年杀掳的汉人达1万多人(仅辽东和云中地区),甚至有一次打到离长安仅200公里的地方。匈奴气焰嚣张到什么程度呢?刘邦死后,冒顿单于致信调戏吕后,要吕后去做他的妃子。吕后尽管气得不行,回信却尽是软话,称配不上冒顿。为此,吕后不惜自毁形象,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
汉文帝和汉景帝虽然也曾反抗过,不过均以失败告终。例如,公元前166年,文帝拒绝和亲,竟引来匈奴14万大军。汉军受命迎击,结果竟是惧而不战。到最后,文帝只能屈辱求和。这种情况持续了近70年之久!
有条件、有愿望、有理由,汉匈大战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不过,汉武帝身边的人,绝大多数还在紧紧拥抱过去,包括太子。太子劝谏不要兴兵杀伐,汉武帝的回答是:“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在卫青面前,汉武帝说得更明白:“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即位时年仅16岁,一段时间内尚不能亲政,而由窦太后主政,继续执行和亲政策。7年之后,西汉国力更盛,已具备与匈奴一争高下的资本。于是,23岁的汉武帝决定不再忍受下去。
不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还有最重要的东西没准备好——军队。
汉初对匈奴采取战略守势,军队也被塑造成一支战略防御型军队。要消灭匈奴,显然要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造,打造成一支战略进攻型军队。这需要进行方向性军事改革。
一是抓“权”。
汉初,搞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不主动求战。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军队居然没有常设的专职最高首长,军务由丞相兼管。只有打仗时,太尉(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长)才临时出来代管几天,打完仗又把军权还给丞相。丞相一系的文官,不喜欢打仗,除非对方要自己的命,否则绝不主动开战。
汉武帝要对匈奴用兵,不管是决策还是执行,都得绕开丞相这个障碍,这意味着得把军权从丞相手中拽出来。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汉武帝任母舅田蚡为太尉。没有战事,却恢复太尉一职,自然不寻常,目的就是要丞相交出军权。这只是第一步,过渡一年后,汉武帝又迈出了第二步——撤销田蚡的“太尉”职,从此不再设置。不过,军权并没还给丞相。那么谁来管呢?漢武帝自己。
这样一来,汉武帝想升谁的官,升多高,完全自己说了算,随心所欲,不必先经过丞相点头。现在,将军们只需要对皇帝负责,政府被晾在一边。也就是说,汉武帝可以甩开膀子干一票了。
二是换“将”。
汉武帝从父亲景帝那里继承了一批将军,知名的如韩安国、李广、公孙敖、公孙贺,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致命缺陷——只愿意也只会打战略防御战,不擅长主动进攻。
汉武帝并非完全不信任父亲留给自己的军事人才,也给了他们机会,但发现他们不堪所望。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汉武帝派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等率领30万大军,准备在马邑(今山西朔县)诱歼匈奴军臣单于(冒顿之孙)。不料,单于看出破绽,还没到伏击区就撤了。匈奴没有进入伏击圈,但负责断其后路的王恢一路还是有机会截击,竟未敢出击。马邑伏击战,汉军出动30万人,对付单于率领的10万人,本是个很好的机会,居然无功而返,而且还暴露了战略企图。汉武帝非常恼火,把王恢杀了才解气。于是,汉武帝得出结论——老将们不中用了,必须从青年才俊中选拔新生代将帅。
如何观察和发现人才呢?
汉武帝决定亲力亲为,办法是在宫廷和宫城近卫军中新建几支部队,并且多从“名将多出焉”的北部边郡挑人。若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汉武帝时期的名将大多具有相似身份——宫廷侍卫武官出身。最典型的莫过于卫青与霍去病:卫青出身羽林(增设的宫廷近卫军,约2000人);霍去病,侍中出身。
三是崇“武”。
前面说到,太尉变成了时有时无的职位。军队统帅都混得这么差,其他人更不用提了。这种状态,要让军人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进攻如狼似虎的匈奴,谁会有干劲儿呢?
所以,汉武帝决定提高军人地位,而且速度要快,步子要大。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汉武帝将卫青提拔为大将军。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呢?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丞相,军政大权一把抓,不仅管分内的军事,连属于丞相的政事和民事也可以插手,弄得宰相越来越没事可干,成了闲职。丞相府门前以前车水马龙,门槛都要被踏破,这以后就不行了,门可罗雀。史载:“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为了刺激普通军人的积极性,汉武帝还设立了“武功爵”。这个点子,商鞅已经试过了,效果很好。汉武帝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总原则不变——杀敌数量越多,斩首级别越高,获得的官爵和赏赐越好。在汉武帝手里,受封侯爵共98人,其中将军为侯者53人,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汉者29人,两者所占比例为92%,靠亲戚或世袭关系而非军功封侯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可怜的7人。立下军功,除了官爵,还有银子。漠北大战获胜后,汉武帝掏出50万金用于奖赏。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西汉一年的财政收入!
四是增“马”。
据军事学家研究,一个骑兵的战斗力相当于50个步兵!汉武帝要摆平匈奴,没有足够的马是不行的。尽管汉武帝继承了30万匹马的丰厚遗产,但由于只有5~16岁的中龄马才适合做战马。这样一排除,可以用来对匈奴作战的马就不多了,必须增马。
养马是哪个衙门负责呢?太仆寺。养马只是太仆寺分管的众多事务之一。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汉武帝新设水衡都尉一职,把太仆寺所属的天子六厩划走,使太仆寺能够专心发展军马。此举效果明显,仅边境36个马场的马匹数量就增加了10万之多。
除了太仆寺这个“国营单位”,汉武帝还积极鼓励民间养马。《汉书·武帝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马少,平杜马匹二十万。”啥意思呢?西汉前期已经在用价格杠杆刺激马匹私营,一匹马的价格涨到过1万钱,但到了汉武帝这里,一下子提高到20万钱!既然养马这么挣钱,老百姓当然趋之若鹜,根本不需要进行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动员。这么好的政策,居然还有“刁民”不满意。怎么回事?有人说了:俺不想要钱,俺想当官。但这种事要是应下来,那就是卖官鬻爵,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马匹对付匈奴,汉武帝一咬牙——准了!
汉武帝多管齐下,使养马在西汉成了一项全国、全军、全民运动。史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
汉武帝军事改革的成效如何?用事实说话:经过14年(公元前133年—公元前119年)的7次大小战役,特别是漠北决战,西汉大败匈奴,占领并巩固了河西、河南、漠南数千里的国防线。匈奴受到沉重打击,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被赶到更北的漠北,没有水草,无法生存,被迫远迁西北。
(摘自现代出版社《兵道:这些军队如何改写历史》 作者:许述 罗耳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