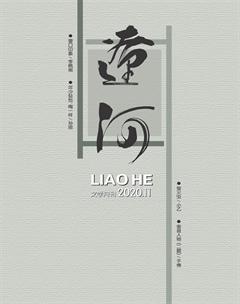井台会
冯伟
在蒲草,到了腊月廿三就算是进年了,一家家杀猪宰羊做着过年的准备。好在小年的前一天落了一场大雪,北风也飕飕地刮个不停,每家准备的年货还能放得住。这一天,蒲草的何三赖家也杀年猪,他大清早就担着两只空水桶到大队部来挑水。
当时蒲草大队就这么一眼井,在大队部的院外。离井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又粗又高又大的槐树。这树有些年月了,看上去很有风骨。虽说冬天树冠已经没了叶子,枝丫却依旧在那儿迎风傲雪,很是强劲地支撑着一片蓝天。那较粗的枝丫直挺挺地伸展着,像一只手,迎客松般托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在一根树枝上,用铁线吊挂着一截被称为“钟”的有些生了锈的钢轨。在悬挂钢轨的连接处插着一根手指粗细的铁棍,是用来敲“钟”的。在井的北侧,正对大队部的院门是个大大的场院。这个季节是没人打场的,场院的西侧有四堆小山般大小的玉米秸垛。那玉米秸儿已经不是绿色的了,黄得发黑,此时已被大雪给封了个严严实实。
何三赖挑着水桶,空水桶被北风刮得左右摇摆不停。当然他何三赖也被风吹得觑眯着眼,一只胳臂压着扁担,攥着拳,捂着嘴,挡着风;另一只手放在裤兜里,腋下还夹着一柄小洋镐。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腰间还勒了一截麻绳。棉鞋也是黑的,却不是那么干净,落着灰土和斑斑点点的污渍。帽子是狗皮的,护耳没有放下来,在头的两侧,翅膀般随风呼耷着,像是要飞。
何三赖来到井台,放下两只空水桶,將扁担戳在院墙旁,拿过小洋镐,先将亮滑的结冰井台刨出一片供人站脚打水的麻面儿来,免得打水的人滑倒或是掉进井里。这是蒲草人不成文的习惯,只要到了冬天,只要有冰雪,最早来井台挑水的,必须将封冻了的井台刨出一块能站稳脚的空地儿。何三赖今天不仅起得早,心情也很好,他家终于也能杀一头猪过年了。何三赖很是认真地一镐一镐地刨着井台上的冰面。那尖硬的镐尖儿和厚厚的冰层撞击着,绽放出美丽的冰花儿来,刹那间在他觑眯着的眼前一开一灭,一灭一开,亮晶晶的,如同一束束颜色相同大小不等的烟花燃放在井台上。也就几分钟的光景,何三赖将井台走人的地方刨出一条梯形的过道来,然后开始打水。
井台很亮,结着厚厚的冰。那本是很宽阔的井口,被渐渐封冻了的冰给遮掩得有些窄小。井台上的冰是亮的,井口处的冰却亮得发白,并有冰柱悬挂在井口的井壁上,看上去让人谨慎。何三赖小心翼翼地走上来,站稳脚,想用手去够缠在辘轳上绳头处的铁钩子,这时才发现,那井绳并没有在辘轳上缠着,而是垂直掉进了井里。何三赖便伸过右手抓住冰凉的辘把往上摇。开始还很轻松,可越摇越沉,仿佛有个很重的东西挂在了上面。何三赖纳闷儿,什么东西这么沉?他觉着一只手很难将重物提起,便怀疑着,抻着脖子往井里看。井太深,井口窄小,黑咕隆咚看不见。只好又伸出左手,用双手奋力继续往上摇。摇着摇着,终于摇上来了。何三赖一看,竟是一具尸体。何三赖大吃一惊,吓得立刻松了手,辘轳便以极快的速度往回转,直到他提上来的尸体又沉落到了井里,那旋转的辘轳才戛然而止。
何三赖惊恐着,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心狂跳不止。他在井口边呆愣了一会儿,猛地缓过神儿来,慌忙离开井口,不小心绊倒了一只水桶,将水桶踢得老远,自己也随之摔滚了出去,又不顾一切地爬起来,跟头把势地跑到那棵槐树下,拿过那根铁棍用力敲钟,声嘶力竭地喊,不好了!死人了……
这时的太阳刚刚出来,整个蒲草被朝霞笼罩着。由于前一天下了雪,四野洁白一片,一家家烟囱冒出的烟在静静的村庄上空袅袅地升腾着。也说不清是谁第一个听到何三赖敲的钟响。可随着一声声急促的钟声传来,整个蒲草的人也就听到了。听到了就纳闷儿,这是干啥呀,这么早,敲什么钟?可钟声仍然不绝于耳,而且一声紧跟着一声,便觉着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了。村民们赶忙扔下手中的活,或是从被窝里爬起来,向大队部奔去。
蒲草村形同巨掌,大队部正设在掌心的位置。大队部的后身是座被称作“奶头山”的山。山不是很高,却很宽长,有四条山沟,像从“奶头山”流下的奶痕。山沟的两侧稀稀拉拉坐落着百十户人家。只要有人敲钟,那钟声便流水般漫向山沟,再从山沟的上空溢出。离大队部约二百米外是一条叫响水的河。河的腰身很细,很圆润,酷似女人的腰姿,没头没尾地舒展在奶头山脚下。水很清澈,由东向西潺潺而去。
随着急促的钟声,村民们大多都到了。来到了槐树下,村民们见是何三赖在敲钟,难免有些失望。何三赖的敲钟并没有停,只是速度放慢了,力气也小了,钟声也没那么大了。大队长杨广轩也来了,见是何三赖在敲钟,上去一脚将何三赖踢倒在雪地上。何三赖戴的狗皮帽子滚得老远,露出光秃秃的头来。大队长杨广轩吼道,何三赖,敲什么敲?这钟是你敲的?何三赖坐在地上,脸色是青的,双手冻得通红。他喘着粗气,惊恐着,不说话。杨广轩又踢了下何三赖的屁股问,谁让你敲的?敲钟干啥?何三赖坐在地上,咽了口唾沫,然后一口寒气从嘴里喷了出来,瞅着大队长,用手指着井,结巴地说,井……井里有人!在场的人听了猛地一惊,呼啦一下,涌向井口。
当尸体再次从井里被提上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人们在晨光的照耀下,看着被打捞上来的人,不禁又是大吃一惊,这不是李美芳吗?
在蒲草大队,甚至在整个黄岭公社,可以说没有不熟悉李美芳的。李美芳是上海知青,不仅人长得漂亮,品行也很端正,深受村民的爱戴。李美芳出生于医生世家,父亲母亲,包括她的爷爷奶奶都是行医的。要不是上山下乡,她可能也跟着行医了。李美芳小的时候就跟在爷爷奶奶身边,耳濡目染,日久天长也就学了一些给人看病的本领。原本是想考医学院的,赶上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也就来到了蒲草。开始李美芳和那些知青们一样每天到地里干活儿,后来村民知道了李美芳有给人看病的本事,大队长杨广轩就在大队部设了个医疗站,让李美芳专门负责给村民和知青们看病。村民和知青们有个头痛脑热小病小灾,省得跑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了,到李美芳这里都能得到解决。李美芳也就成了村医,不用再下地干那些农活儿了。
李美芳的死,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么好个姑娘怎么会死呢?可知青死了,不同于村里老百姓,人家是城里人,是响应号召来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不是小事情。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特别是大队长杨广轩更不敢隐瞒,只好上报公社。公社听说知青死了,这还了得?立刻上报县里,县里上报市里,然后和公安机关成立联合调查组,来蒲草调查。不曾想的是,很快调查明白了,他们在李美芳的医书中发现一封遗书,大概意思,是蒲草大队长杨广轩的儿子杨天下强奸了她。
蒲草大队是由黄岭、茅崎、蒲草三个小队组成的,大队长是蒲草的杨广轩。在蒲草,杨姓占村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还多,属于大户人家。杨广轩能当大队长,源于他的父亲是老革命,加上他是村里的唯一党员,接父亲的班,当上了大队长。已经干二十多年了。杨广轩的儿子杨天下自然是根红苗正,在公社的人保组工作。
杨广轩的儿子杨天下被公安局的人带走的那一天,轰动了整个蒲草。那是腊月廿六的下午,村民们正忙着准备过年。有人看到蒲草大队长杨广轩家来了两辆警车,把杨广轩的儿子杨天下给带走了。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知道杨天下出事儿了。杨天下被带到公安局,经过审讯,承认是自己强奸了李美芳,可不承认李美芳是他杀害的。公安机关只好把案子移交给了检察院,检察院经过重审,依然没有效果。没办法,案子被移交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核实,杨天下强奸罪名成立,害人致死没有证据。合议结果,李美芳属于自己将自己拴到井绳上,然后投井自尽的。
消息传到了蒲草,蒲草的村民并没感到意外。大队长杨广轩的儿子杨天下喜欢李美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杨天下是个有家室的人,儿子都十几岁了。杨天下有事没事经常到村医疗站来看李美芳,今天说头痛,明天说肚子痛,后天就说屁股痛,反正他病的位置是从上身到下身,最后疼到了那个位置。杨天下那种自上而下的病把李美芳弄得很尴尬。李美芳明白杨天下是什么意思,得罪不起他,人家是公社人保组的人,只能是见他来了就躲,或是去青年点,或是上谁家串串门儿,不想见杨天下。可杨天下是个厚脸皮的人,不厌其烦地往医疗站出溜,弄得李美芳很无奈。时间久了,村民们也就知道了。李美芳一个下乡知青,不仅不敢得罪杨天下,也不敢得罪大队长杨广轩,只能是偷偷地跟一些人诉苦。村里人听了,便在背地里议论,说杨天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李美芳死了。李美芳的家人从上海来到了蒲草。不仅父母和亲属来了,相关的领导和家乡的公安人员也来了,来这里查事情的真相。最终的调查结果是相同的,被害人属于遭强奸后自杀。李美芳的家人只能在无比痛苦中将女儿接走了。临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来相送。村路上,山坡间,河两旁,送行的人胸前戴着白花儿,排着长长的队伍,流着泪,挥着手,跟李美芳告别……
年,照常过,村民们该吃肉吃肉,该包饺子包饺子。可他们的内心并不是那么快乐,他们想念李美芳。
这个年,大队长杨广轩也没有过好。儿子杨天下被抓走了,儿媳妇羞愧难当,领孩子回了娘家,而且扬言要跟丈夫离婚。家里只剩下杨广轩老两口和一个闺女。这一年,村里请他这个大队长吃饭的人也少了。杨广轩心里很憋屈。以往过年,村里的哪一家杀年猪不得请他吃一顿?不仅吃,还要带回家来一些。今年却大不相同了,即便有人请,他杨广轩也没脸去。他把一切怨气都归罪到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杨天下身上。原本儿子在公社人保组工作,是他杨家的荣耀,做梦也没曾想能惹出这么大个祸来。是儿子把这个不愁吃,不愁穿,风光无限的家给毁了。不仅把他这个做爹的毁了,也把他老杨家的大家族的名声给毁了。还没到过年,在腊月二十八这一天,大队长杨广轩就病倒在炕上。
村民们虽说没有忘记李美芳,可日子还是要过,年还是要过。他们穿新衣,放鞭炮,茶余饭后免不了提到死去的李美芳。想李美芳的音容笑貌,念叨李美芳活着的时候对他们的好。大年三十,在吃年夜饭之前,个别村民还到井台上给李美芳上了供,烧了纸,然后把那些能吃的东西都扔到了井里,让李美芳去吃。要说蒲草最想念李美芳的有那么几个人,何三賴、蒋琴和蔡庆,都是受恩于李美芳的。李美芳不仅给他们的亲人治过病,在经济上还有多多少少的帮助。特别是何三赖,把整个猪头、四个猪蹄儿,还有一个猪尾巴都拿到井台上来,边上香嘴里边念叨着,说我不应该第二次把你丢到井里,可我确实吓坏了。自从何三赖发现井里的李美芳,就常常做噩梦。他总是能梦见李美芳被从井里捞上来的情景,一身女军装,胸前佩戴着毛主席的像章,乌黑的秀发,衬着一张苍白的脸。蒋琴也来到了井台,她也摆了供品。她不能忘,她的胃寒病就是李美芳给治好的。蔡庆也来了,他领着自己的母亲,来看李美芳。老太太的哮喘病也是李美芳给治好的。老人家边烧着纸边说,姑娘,一路走好啊……
蒋琴在公社的成衣铺上班,这里每天都有村民们来来往往,闲坐闲聊。在蒲草,每逢夏天,村民们喜欢到村部的老槐树下乘凉,玩耍;冬天太冷,他们就要聚到成衣铺这里来,东家长西家短,唠起来没完。自从李美芳死后,话题就转到了李美芳的身上。人们带着惋惜,带着想念,也带着对大队长的儿子杨天下的憎恨,来议论李美芳的死。有的说杨天下活该,判他死刑也不为过。有的说,媳妇要跟他离婚了,这个家妻离子散了。有的说,他不仅败坏了他自己家的名声,也败坏了他们杨氏家族的名声……于是,杨氏人听了就跟着脸红。
杨广轩勉勉强强过了个年,在正月十六的这一天,从炕上爬起来,来到槐树下,又敲响了那个象征着权威的钟。杨广轩站在树下,两脚叉开,披着衣服,一手掐腰,一手敲钟,那有些尖刻、刺耳的钟声带着他大队长的威严传得很远很远。他想给全村人开个大会。
村民们在年味儿还没有完全散尽的气氛中,听到了钟响。这是李美芳死后的第二次钟声,也是新一年开始的第一次钟声。村民们听到钟声,立刻想起了李美芳,心惊了一下,想,还没出正月,又敲钟干啥?村民们知道他们的大队长很喜欢开会,而且每次开会必须自己敲钟,每一次敲得都很卖力。他觉着钟声就是他的权威,就是他老杨家在蒲草的大家族的象征……村民们便在一种抱怨和无奈中来到了槐树下的井台旁。
会计杨立志见村民们来得差不多了,就说,大队长让你们到村部的屋里开会,你们都站在井台上干啥?村民们看了一眼杨立志,没动,依旧围着井站着。杨立志重复道,天太冷了,队长让你们到大队部的屋子里去开会。只听有人说,你让他出来开吧。会计杨立志没明白,问,为啥?没人搭理他。杨立志只好又返回大队部,对杨广轩说,他们要求在井台上开会。大队长杨广轩看了眼会计杨立志,将手中的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踩了一脚,走了出去。
还是在正月里,外面依旧很冷。杨广轩来到大队部院墙外,看了眼站在井旁的村民,就明白村民是什么意思了。这是他杨广轩从李美芳死后第一次来到井旁。他先是干咳了一声,然后又将自己披在身上的大衣往肩上耸了那么一下,上了井台。
杨广轩站在井台上,先是往井口里望了一眼,然后看着村民。村民们也看着杨广轩,这才几天的光景,队长就瘦了一圈儿。心想,这个年他是不会舒服的,儿子被人抓走了,儿媳妇回了娘家,他这个平时极要面子的人怎么会好过?只听杨广轩说,我先给大家拜个年吧。本应该是过年了,去各家走走,可家门不幸啊,出了个逆子,败坏了我老杨家的名声,也败坏了咱蒲草的名声……说着又干咳起来,而且咳起来没完。村民们在一旁看着,觉着大队长怪可怜的。蒋琴说,有啥事儿你就说吧,那些事儿都过去了,大冷的天儿,又敲钟干啥?杨广轩脸咳得通红,缓了缓,又说,今天就一件事儿,我想问问大家,这口井的水你们吃不吃了?如果吃,请不要再往里扔东西了。村民们互相看了看,没有谁回答。杨广轩又说,按说这井从前也是淹死过人的,大伙都知道,可也没耽误大伙吃水呀。人捞上来了,把井淘一淘,该吃吃,该喝喝嘛,水不黵人。干啥都要到那么远的河里去挑水?何三赖说,一挑水就想起了李美芳,心里不好受。这句话让杨广轩很尴尬。杨广轩就看了眼何三赖,心说,就你引起来的,你要不发现井里有人谁知道?可又觉着这话有些说不通,他何三赖不发现井里的人,别人打水也会发现的。这时,会计杨立志说,不是都过去了吗,过去了就过去了。明天把井淘了,该吃水吃水。有人又说,过不去呀,心里这道坎儿过不去。会计杨立志说,人不是捞上来了吗,人也不在井里,有啥过不去?蒋琴说,不是喝水过不去,是感情过不去。李美芳的魂儿还在井里,我们不能打搅她,让她好好安息在这儿吧。村民们突然议论起来,是,不能惊动李美芳的魂儿,就让她好好安息吧。杨广轩突然说,你们要是不喝这口井的水,我就把井填了。村民们听了杨广轩的话都愣了。他们相互对望着,然后去看他们的大队长杨广轩。蒋琴说,你要是敢填井,我就敢把你家房子给点了!你信不信?又有人说,你要是敢填井,我们就去公社告你。就这么一眼井,你还给填了,让我们吃啥?会计杨立志说,你们不是不吃吗?蒋琴说,吃不吃是我们的事儿,填井不行!对,不行!众村民异口同声。这时,妇女主任杨美娟在大队部门口喊,队长电话。杨广轩听罢,看了眼村民,手一扬,说,散会!
大队长杨广轩想填井的事儿,引起了村民的高度重视,也是村民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做梦也不敢想大队长要把井填了。村民们散会往回走,纷纷议论个不停……
有些村民开完会没有回家,来到了成衣铺,继续说大队长填井的事儿。何三赖说,咱们绝不能让他们把井填了,那样的话咱对不起李美芳。蒋琴说,他不敢,他只是吓唬咱,让咱吃井里的水。何三赖说,杨广轩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还是小心一些好。蒋琴说,你们可是亲戚,怎么向着咱们外人说话?何三赖说,人得讲理,不讲理,天王老子也不行。有人说,你不怕大队长给你小鞋儿穿?何三赖说,吹牛,他当这么多年大队长,也没说照顾过我。有人说,咱们还是成立个护井队吧,晚上轮流值班,看着点儿。蒋琴说,怎么看呀,大冷的天儿。何三赖说,咱们可以去大队部住,反正大队部晚上也没人。蒋琴说,大队部不安全,容易让人发现,要我说你们就藏在场院的玉米秸垛里,离井还近。有的说,我看行。于是,村民们自发地找了几个年轻人,成立了护井队。
护井队由十四个人组成。村民们推荐何三赖为护井队长。何三赖当仁不让,把十四个人分为七组,每组两人,七天一轮。
第二天,大队长杨广轩找人开始淘井。由于过年时村民们祭奠李美芳,上完供,有的把祭品扔到了井里,肉、白菜、豆腐、粉絲、馒头,还有酒,有的把烟也扔了进去。井水就很脏,什么东西都有。水泵抽、人淘,弄了大半天才算淘干净。淘井的时候,有的村民在一旁看着。他们把从井里淘出来的给李美芳的祭品都放到一起,埋到了老槐树下。
杨广轩看着村民的举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仅想起了李美芳,也想起了在蹲监狱的儿子。他想,这回井淘干净了,村民们该吃井水了。不曾想的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井里挑水。杨广轩就很生气,找来会计杨立志,问,你看这眼井怎么办?井都淘了,他们还不吃井里的水。舍近求远,吃河里的水,也不是个事儿呀。我想动员一下咱们老杨家的人先来吃井里的水。时间长了,大伙也就都来吃了,事儿也就过去了。会计杨立志说,管他呢,不吃就不吃,神不知鬼不觉,把井给它填喽,他们知道也晚了。杨广轩还是有些犹豫,说,我怕激起民愤,这个时候填井,容易引起众怒,还是先开个家族会议吧。
当天晚上,大队长杨广轩在自己家,给他们老杨家偷偷开了个全族会议。
一家一个代表,七十几个人挤了满满三屋子。虽然都是杨姓,但是辈分不同,年龄差异自然也就很大。按辈分,年长的在炕上坐着,年少的在地上站着。杨广轩坐在自家的炕头上,披着棉袄,抽着烟。会计杨立志挤上炕,对杨广轩说,叔,人来得差不多了,啥事儿,你说。杨广轩像是有些难以启齿,说,井都淘干净了,我就问你们都吃不吃那口井里的水?在场的人谁都不说话。杨广轩扫了他们一眼就明白了。又说,不就是掉里一个人吗,以前又不是没掉过,该吃水吃水呗。还是没人说话。杨广轩又说,说白了吧,这不是简单的吃水问题,是涉及到我们老杨家的声誉问题。难道那口井就成了我们老杨家的罪证不成?咱们越不去吃水,村里人就越忘不了我儿子这件事儿。我儿子的罪证,也是我们整个家族的罪证,一旦因为这件事儿我这个队长被拿下去了,落到了外姓人手里,对你们还有什么好处?凭良心说,自从我当队长,对你们都怎么样?当兵、盖房、要房基地……处处照顾你们,要不是我当这个队长,谁能办了这些事儿。这时一家的侄子说,叔,不是不想吃井里的水,就是感情过不去。一到井口就想起了那个李美芳。不忍心打井里的水,怕惊了她的灵魂。李美芳救过咱家孩子的命,那次咱家孩子把一玻璃球卡在嗓子里,要不是李美芳救得及时,孩子就没命了。又有人说,就是,我妈的肺气肿都是李美芳给治好的,要不早就死了……屋里所有的人都骚动起来,说起李美芳的好。杨广轩听了,也知道李美芳活着的时候给他们一家家做了不少的事情。屋内乱了一阵,然后又静下来。房间里人多,抽烟的人也多,满屋子烟气罡罡的,看人很模糊……
会,不欢而散。最后大队长杨广轩把会计杨立志留了下来。
风轻云淡,正是阴历二月份的日子。这一季节,晚上天黑得早,护井队的人按部就班地护着井。这一天正赶上何三赖和蔡庆在护井值班。他们猫在大队部场院的玉米秸垛里,闲聊着,听着井旁的动静。上半夜一晃儿就过去了。两个人开始聊得挺欢,可聊着聊着就困了。蔡庆说,都几天了,也没人来填井,他们不会来了。何三赖说,万一要来呢?昨天晚上他们老杨家开了全族会议,就是研究吃井里水的事儿。谁都没说吃不吃,杨广轩很生气。蔡庆问何三赖,那咱们就这么天天守着,得守到啥时候是个头?何三赖说,守到他们来填井的时候。又说,这才几天,你就屁了?我当兵的时候,站岗放哨,侦查敌情,家常便饭。蔡庆说,你不困呀?何三赖说,困也得忍着。他们一旦把井填了,咱对不起死去的李美芳。于是,两个人又开始回忆李美芳活着时对他们的好。何三赖说,我从前不刷牙,是跟李美芳这些知青们学的怎么刷牙。蔡庆说,这些城里人给咱们带来了好多乐趣。他们会唱会跳,会穿会戴,我穿红腿裤就是跟他们学的。何三赖说,我穿的红腿裤就是李美芳给做的。她不仅心眼儿好,手还巧。蔡庆说,她还送给我妹妹一套军装呢……
大队部很静。老槐树在月光下是一个庞大的剪影。四野没有虫鸣,更没有犬吠,仿佛一切都死去了。
何三赖和蔡庆又聊了一会儿。蔡庆咧开大嘴,困顿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说,咱们抽根烟吧,我困得受不了了。何三赖说,找死呀,把玉米秸垛点着了怎么办?再说,咱这一抽烟,还不得让人发现?蔡庆问,应该是下半夜了吧?何三赖看了看月亮,说,差不多,两点多吧。蔡庆说,不能来了,要来早来了。我眯一会儿,有事儿你叫我。何三赖说,长一身肥膘,就知道睡。你睡吧,我盯着。蔡庆迷糊了。何三赖警觉地窥探着外面。
又过了一阵子,何三赖也有些迷糊了。他刚刚打了个盹儿,便听见有声音传来。何三赖就是一惊,他捅醒蔡庆,说了声,来人了!蔡庆立马精神起来。两个人从玉米秸垛里往外望,果然看见五六个人,推着三辆手推车向井旁走来。何三赖和蔡庆警觉起来,悄悄地观察着。只见六个黑影,推着车来到井前,正在要往井里扔石头的时候,何三赖大吼一声,住手!便从玉米秸垛中冲了出来,边跑边对蔡庆说,我去敲钟,你阻止他们!
“当当当……”,悦耳的钟声划破夜空,惊醒了酣睡的人们。村民们听到钟声,感到大事不妙,慌忙地从被窝里爬起来,穿上衣服,冲出家门。
一会儿工夫,大队部,槐树下,井台旁都站满了人,村民们议论着,指手画脚……
大队长杨广轩和会计杨立志也来了。他们听到钟声,从梦中醒来,第一反应就是出事儿了。还没等杨广轩从家里出来,会计杨立志已经破门而入了。楊广轩看着杨立志问,怎么回事儿?会计杨立志摇头说,不知道呀!杨广轩问,我让你安排的事儿呢?杨立志说,安排完了,说是今天晚上办。杨广轩气愤道,糊涂!走出家门。杨广轩来到大队部,只见人头攒动,手电的光亮闪闪。他走上前来,问,又是谁在敲钟?妇女主任杨美娟跑上来,说,是何三赖敲的。杨广轩气愤道,怎么又是他?敲钟干啥?死娘了!杨美娟说,有人要填井!杨广轩问,填井?填什么井?谁让填的?杨美娟说,不知道,人跑了。杨广轩这才松了一口气,对会计杨立志说,查!一定把人查出来!
真正的春天来了。人们怀着对春天的渴望,开始种地,期待着秋天的收获。当然,也过着跟前一年大致无二的日子。可在大队部的井台上仍然没有人在这里挑水。队长杨广轩每次到大队部,都要向井台的方向看上一眼,心事重重。
杨广轩的儿媳妇是在杨天下被判刑后离的婚。杨天下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罪名有两个,强奸罪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对于李美芳是自杀,还是被别人拴到井绳上再推倒井里,始终是个谜。离婚的时候杨广轩硬是把孙子要了下来,儿子不行了,孙子他一定得要,他把希望寄托到孙子身上。他杨广轩不能后继无人。儿媳妇先是不同意把孩子留给杨家,后来娘家人做了工作,说年纪轻轻的,带个孩子还怎么嫁人?儿媳妇虽说舍不得孩子,最终还是放弃了。
大队部外的井台上仍然无人打水,就是杨姓的人也不来。全村人都去离村部二百米开外的响水河里挑水吃。这么一弄,杨广轩家也没法吃井里的水了。杨广轩一家是很难将井水吃干净的。无奈,也得去吃响水河的水。从表面上看,村部的井没人动了,杨家的那块“疮疤”似乎也被封存了,没人再看了。可在响水河这里打水的人,是每每都要想起或是提起李美芳的。他们每提起一次,老杨家的伤疤就被掀开一次,那种疼痛永远都不会愈合。
清明节到了,村民们没有任何组织地又来到了井旁。他们拿着祭品来看李美芳,整个井台上摆满了鲜花和供品。杨广轩家被逼无奈也来了,是杨广轩的老婆来的,摆了供品,还上了香。杨广轩在大队部看着,心情很不好。突然对会计杨立志说,我想把大队部搬了。
正在杨广轩想搬大队部还没实施的时候,公社赵书记把他叫去了,让他把蒲草书记兼大队长的位置让出来。杨广轩问,为啥?赵书记说,不为啥,就因为你那个儿子,影响太坏。杨广轩说,可他已经伏法了,和我没什么关系。赵书记说,怎么没关系,他还是你的儿子吧,你再干下去,工作还怎么进行?也不服众呀。杨广轩心里恨着儿子,也恨着眼前的赵书记,可又不能反驳,就在那默不作声。赵书记又说,你推荐一个人选吧,你们村不能没有队长。杨广轩说,党员没有了,蒲草就我这么一个党员。咱们的党支部是由黄岭、茅崎、蒲草三个小队的三个党员凑成的党支部,你们不让我干了,就少一个书记。赵书记说,那你就推荐一个小队长,有能力,群众基础好,有工作经验的,不是党员也行。支部书记可以让公社的组织委员先兼着,将来有合适的人选再补上。杨广轩就推荐了现任大队会计杨立志。
这一天杨广轩回家喝了酒,边喝边骂自己的儿子,还骂公社的赵书记,说赵书记卸磨杀驴,他忘记了他的父亲当年从战场上是被他杨广轩的父亲给救回来的。可骂归骂,事情终归出现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便又开始骂自己的老婆,骂老婆养了个败家儿子。老婆也不敢言语,一个劲儿地在厨房炒菜。杨广轩骂够了,又让老婆去找会计杨立志。杨立志来了,见大队长在喝闷酒,就问,叔,咋了?杨广轩说,没咋的,我推荐你当咱们村的小队长了。杨立志看着自家的叔叔杨广轩,说,叔,你是不是喝多了?杨广轩说,多什么多,我那个儿子不是出事儿了吗,我这个大队长让人给撸下来了,推荐你了,当蒲草的小队长。杨立志说,叔,这怎么成,我当个会计还凑合,当队长不行。杨广轩说,怎么不行,难道你还想把这个队长让给外姓人吗?杨立志便不再说话。杨广轩说,赶紧上来喝酒!
三天后,公社的组织部门到蒲草给全体村民开会,宣布杨立志正式上任。
蒲草的村民对杨广轩从大队长的位置被拿下来,和杨立志任蒲草的小队长并没感觉出什么惊讶。无论是杨姓的人还是其他村民,对杨广轩和杨立志的评价,一个五八,一个四十,没什么大的区别,是那种豺和狼的关系。当公社的领导宣布完的时候,村民们在“换汤不换药”的谩骂声中散去了。他们又来到了成衣铺,把话题从杨广轩的身上,转到了杨立志身上。全村人都知道杨立志是杨广轩的亲侄儿,四十三岁,原本是中学的地理老师,因猥亵女学生,被学校开除了。又因为人精明,会精打细算,写了一手好字,杨广轩就让他到大队部当了会计,一干就是十七年。杨立志人聪明,鬼点子也多,人送绰号“杨小鬼儿”。
杨立志上任第一天就来到了杨广轩的家,请教叔叔这个队长应该怎么干。杨广轩见侄子没有过河拆桥,还念着自己的好,就说,不需要你干别的,把我没完成的事儿完成就行了。杨立志是聪明人,当然知道杨广轩想干什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青年们陆续回城。蒲草剩下的知青也是寥寥无几。杨立志借此机会把青年点儿挪到了大队部,把大队部挪到了青年点儿。本是不合情理的事情,可青年们都急着回城,没心在这鬼地方待下去,别说换个住处,就是把行李扔了才好。
杨立志把大队部搬到青年点儿的这一天,全体村民自然也就知道了。有人问,大队部好好的为啥搬家?杨立志理由充分地说,知青马上都回城了,用不了那么大的地儿。我们大队部办公的地方小,串一下。让那几个知青住到大队部去,换换环境。
杨立志把新大队部收拾得很漂亮。不仅贴上了毛主席的像,还挂上了一面党旗。把原来在槐树上的那个“钟”也撤了,换成了大喇叭。那大喇叭绑在新大队部院内的一根高高的旗杆上,逢年过节旗杆上还要飘扬着一面红旗。
原来的大队部一下子冷清下来了。除了几个还没有来得及回城的青年,极少有人还到老大队部来闲逛。只是那眼井还在,那棵槐树还在。村民们虽说不到原来的队部,槐树下却总是有人来的。春天闲坐,夏天乘凉,秋天打场,只有冬天这里是空旷、冷清的。去新大队部的人依然不多,除了他们杨氏一家当族的个别人去,其他村民很少去。村民依然恋着那棵树和那眼井,纳凉、聊天,有的还在平平的井台上下棋。那井已经好久没人打水了,里面的井壁和水面上生满了苔藓,井口旁的石缝间也长的全是蒿草。
村民们并没因大队部的搬迁而忘了那棵树和那眼井。正是天儿热的时候,闲暇时总是有人到槐树下乘凉。他们一到这里,就看到了井,就能想起李美芳。想起了李美芳,也能想起那个把李美芳害了的杨天下。人们的嘴就像一只只手,把他老杨家的伤疤又给掀开看了一遍。
杨立志当小队长后干的第二件事就是想锯掉井旁这棵老槐树。
杨立志上任后一共开过两次会,本想在新队部开,可都没开成。一次是春季播种派活儿,一次是修堤坝开动员会,是用新大队部的大喇叭喊的。村民也都听到了,听到了就来开会,可就是不到新大队部来,依旧是去了老槐树附近的水井旁。来新大队部的也不是一个人也没有,三三五五的,都是他杨姓的人。杨立志无奈,只好来到槐树下的井台旁开会。当然,杨立志是很别扭的,新队部是他弄的,可村民们不愿来,就证明了他这一举措的失败。于是,他就把村民们不来新大队部的罪过强加在那眼井和那棵老槐树上。他想,如果没了井和树,村民们就没了念想,没了念想就没了那么多的能聚到一起的眼睛和嘴,没了那么多的嘴和眼睛,他们就无法说三道四地看他老杨家的笑话、揭开他们的伤疤了。只要那块伤疤不被人常常掀起,总是会有愈合的那一天……
秋天到了,这一天杨立志来找杨广轩,说了自己的心事,想把老槐树弄死。杨广轩立刻精神起来,对杨立志的想法很赞同。只是这件事非同小可,老槐树可是蒲草大队唯一的标志了,全村人对这棵树的情感和依赖,远远超过对他们当队长的情感和依赖。别看它是棵树,它承载和见证着蒲草大队的历史和风风雨雨。那是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栽下的,多少年了,是那么的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说心里话,杨广轩也有些舍不得这么做。可为了他个人的名声,为了这个家族,他杨广轩是要忍痛割爱的。杨广轩看了眼杨立志,觉着砍掉这棵树也确实是砍掉了村民的主心骨。于是说,这件事不能明干。杨立志冷冷地笑了一下。
秋天转眼过去了,冬天接踵而至。队长杨立志这一天下午来到了供销社,买了一包花椒、一瓶白酒、还有一包花生米。他回了家,喝了酒,吃了花生米,把自己弄得醉醺醺的。见天黑了,从家里出来,口袋里揣着那包花椒和一棵钉棺材用的大铁钉子,怀里抱着一把铁锤,穿着大衣,来到了井旁的老槐树下。这个季节,知青点儿的青年们没事可干,早已經放假回城了。杨立志先是在知青点的附近转了转,确认没人,便来到了井旁。朦朦胧胧,井台是荒芜的。当然,这个季节井台的周围已经不是绿色的了,花枯了,草黄了,井口的苔藓也不见了。杨立志站在井台上看了半天,也想了半天。他先是想起了淹死在井里的村里人,然后想起了死去的李美芳。李美芳的音容笑貌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要说他杨立志对李美芳的印象也是不错的,一个知书达理的城里姑娘,不仅长得漂亮还会给人医病,在乡下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死了就是死了,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现在是队长了,他要为他们家族的声望负责。他不可以让这个阴魂不散的人战胜了自己想除掉这棵树的决心。他不仅想起了李美芳的死,自然也想到了还在监狱里蹲着的堂弟杨天下。于是,心一横,将井台上村民下棋的石子一脚给踢到了井里。
杨立志来到槐树下,围着槐树转了一圈儿。他用手抚摸着,这是棵近百年的老槐,高大魁梧,苍劲有力的腰身支撑着头顶上的那片天。杨立志看着,他想起了曾经在这棵树下斗过地主,打过土豪,自然也分了那些人的田地。他想起了在树下放过无数次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开过无数次的会议。那时虽说他不是队长,可是他老杨家的人说了算。老杨家的人说了算,就是他说了算。他通过杨姓的权力送儿子当过兵,也给女儿安排到公社的卫生院当了保管。当然还有很多说不清的好处……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正是初冬,槐树的叶子已经被秋天的冷风蹂躏得凋零了。村子里寂静无声,不仅看不见人走动,连狗都看不见。杨立志俯下身,拿出铁锤和铁钉往树根上钉。一连串钉了十几个钉子粗细的小孔,然后往里放花椒。他想,这棵树将永远没有春天了。
这一年很快过去,村民们在寒冷的冬日里,盼着春季的到来。他们想到老槐树底下纳凉的惬意,想看着那眼井对李美芳的回忆和想念。可夏天的到来是先要经过春天的。这一年在蒲草只有两个人对春天的到来有些忐忑,那就是杨广轩和楊立志,他们唯恐那棵树不死。
春天终于到了,不曾想的是老槐树该绿还绿,还是那么枝繁叶茂,蓬蓬勃勃。杨广轩和杨立志站在井旁,看着老槐树纳闷儿。杨立志说,不应该呀,整整一包的花椒都让我放里了,没有不死的道理。杨广轩说,这棵树近百年,已经不是简单的树了。杨立志看了眼杨广轩问,你舍不得了?杨广轩叹了一口气。
杨立志没有死心,就在当天的晚上,他偷偷摸摸从外地找来一伙人,将老槐树锯掉了。第二天,有的村民来老槐树下纳凉、闲聊,发现场院光秃秃的,像是少了什么,猛地发现老槐树没了,只剩下一段白呲拉的树根。村民们当时就炸了,树怎么会丢?就来大队部找杨立志,问老槐树没了,怎么回事儿?杨立志装糊涂,问,老槐树怎么能没?那么大的一棵树,谁偷它干啥?村民们说,只剩个树根了,整个树冠树干都没了。杨立志假模假式地来到了井旁,果然那棵树没了,整个场院只剩下一眼孤零零的井。
当然,老槐树没有找回来,锯掉老槐树的人也没能抓到。老槐树就这么不翼而飞了。村民们在怀疑、谩骂、不解中渐渐地也就把这件事放弃了。
一晃又过了一年,从老槐树的根部又生长出很多嫩嫩的枝条,将那个平坦的树根围上了一层新绿。村民们在想,用不了多久,这里还会长出一棵大树。
自从老槐树被“偷”,队长杨立志很是得意。得意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原大队长杨广轩想干没干成的事儿,让他给干成了。再是,村民们没地儿可去了,来新大队部的人也渐渐地多起来。换了队部,丢了老槐树,村民们也没能把他怎么样。他从内心有一种成就感。杨立志经常到老队部来转,看看这些青年们住的地方。此时的老大队部青年们已经走光了,青年点儿空空落落的。杨立志在青年们的住处转了一圈,只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的标语还在墙上贴着,剩下的是一片狼藉……
杨立志来到了院外,看了眼破败的老队部,又一个念头产生了。
自从村民们看不见老槐树,听不见钟声,始终觉着很别扭。这种别扭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都很快过去了。可村民们并没因为树的丢失而忘记那眼井,也没因树的丢失而忘记李美芳。
村里有了大喇叭,每天早上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响起《东方红》,那庄严而舒心的旋律随着太阳的升起,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也唤醒了沉睡的村民。他们可以在做早饭的忙活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那是首都北京的声音,这种声音更加增强了村民们对李美芳的想念。只要大队一开会,村民们还是要到井台这里来,并没因老槐树的丢失而忘记那眼井。
一晃又一年,杨立志给村民们开会,当然这次会依旧是在井台开的。杨立志宣布一件事情,想把老大队部扒掉翻新重盖,然后搬回来。村民们没有多想也就同意了。
这是杨立志当小队长之后,得到全村人拥护的唯一一次会议。杨立志自然很高兴。杨立志扒旧房盖新房,没有找本村的人,就连本家的人也没找。他找的是外村人,先是扒的老大队部,然后盖五间楼座。楼座盖完了,杨立志站在屋里往外望,觉着院墙太老旧不好看,就一声令下把墙拆了。拆墙的时候有人问,墙外的那眼井怎么办?杨立志说,那是眼废井,没人吃水,填了!干活的人就用拆墙的石头将那眼井给填了。第二天,村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何三赖、蒋琴,还有蔡庆带领一些村民来找杨立志,问,为啥把井填了?杨立志并不回避,说,那是眼废井,好几年没人吃水了,都臭了,影响村里的环境,不填干啥?村民们愤怒,可又没办法将井里的石头重新挖出来。于是,他们从家里拿来了锹镐,将那眼井的井口又填了很多的新土,做了个大大的坟包。然后,在坟旁,在正对着新盖的大队部的方向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李美芳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