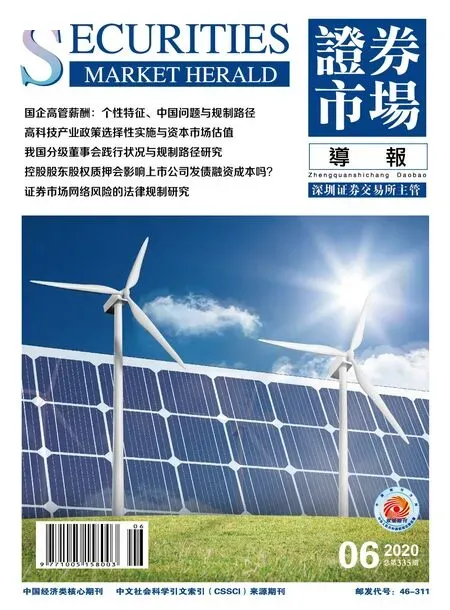国企高管薪酬:个性特征、中国问题与规制路径
楼秋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29)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未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当完成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此种具有鲜明“市场化”特征的改革理路,不仅是对建立“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再强调,也有助于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回应竞争中立原则以适应国际竞争。其中,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高管薪酬的合理确定对于市场化改革意义重大。一方面,与公司业绩挂钩的高管薪酬,可以促使高管自觉追求“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目标的实现。在内外部治理机制均有所欠缺的背景下,可以“自我执行”的薪酬激励是市场化改革不可多得的制度资源。另一方面,不同形式、结构的高管薪酬,对于高管回应市场竞争需求、不当政治干预的行为模式亦有不同影响。例如,当经济收益而非政治晋升构成高管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时,政企不分问题便可能迎刃而解。
然而现阶段,国企高管薪酬却不断暴露出“无效率”和“不公平”的问题:第一,高管薪酬涨幅超过公司业绩提升,存在“过高”之嫌;第二,高管攫取“灰色收入”、进行高额“在职消费”的新闻屡见报端,薪酬激励未能抑制贪腐现象;第三,高管薪酬与职工工资差距拉大,给人“不公”之感。可见,就国企公司治理而言,高管薪酬有其两面性:用之得当,国企改革事半功倍;用之失当,则反而加剧“内部人控制(分享)”问题。2001年安然丑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针对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问题,在公司、证券和税收等层面重拳出击,所采行的诸多改革政策已经或可能为我国所借鉴。然而,中国国企的高管薪酬有其独特的“制度背景”和“问题表现”,若无法对此加以精准认识,则任何原创或舶来的改革举措都无法做到对症下药。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梳理中国国企高管薪酬之“制定与规制特征”“特殊问题表现”入手,结合比较法、实证研究的知识启示,提出符合深化改革之方向的政策建议。
一、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与规制特征:以美国为参照
(一)薪酬制定:最优合同v.董事会俘获
尽管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已经将“过高”的高管薪酬纳入法律规制的视野之内1,有关高管薪酬的学术讨论却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才逐渐饱满起来。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提出,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公司法的最大任务则在于减少乃至消弭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2Jensen and Murphy(1990)主张公司应“按业绩付费”,亦即将高管薪酬与某些客观标准挂钩。31993年,美国进行税法修改,高管薪酬超过100万美元且不与公司业绩挂钩的部分,不得用以抵扣税负。4这一规定使“按业绩付费”成为通行做法。
然而,“按业绩付费”迅速拉大了高管与普通职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飞速增长的高管薪酬促使学者反思其正当性。部分学者认为,飞速增长的高管薪酬是公司与高管之间签订“最优合同”的结果;最优合同促使薪酬安排最大化股东利益。5其他学者则主张,公司董事会实际为高管所“俘获”,飞速增长的高管薪酬是由高管自己决定的,既无效率也不公平。6迄今为止,究竟何者更为准确地描述了美国高管薪酬制定现实的问题,仍无定论。
然而,就中国国企而言,“董事会俘获”理论更贴近有关其高管薪酬制定的实践。《公司法》第46条规定,(国企)经理、副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的报酬事项应由董事会表决通过。《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更是要求,国企法定代表人/其他负责人的年度薪酬方案应交国资委批复/备案。从应然视角出发,通过国资委和监事会的治理制衡,董事会与高管达成的薪酬安排会是“最优合同”。但是,至少由于以下原因,应然与实然有所疏离:
第一,由于所辖企业数量庞大、事务千头万绪,国资委难以对待批复、备案的薪酬方案进行精密管理。截至2019年底,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共有96家。以每家中央企业设置1名董事长、1名总经理、5名副总经理、1名党组纪检组组长、1名总会计师计算,国资委所需受理的央企负责人薪酬方案至少为864份。每份方案又包括“应付年薪”“其他货币性收入”“年度任期激励收入”等6项子内容,所需受理事项其实至少达到5190项。在尚需处置国企其他重大事项、人力和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资委难以对董事会与高管的薪酬协商进行精密监管。
第二,由于“地位低下、资源匮乏”“缺乏适当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受制于高管/控股股东”等因素7,监事会(独立董事)在现实中大有沦为鸡肋之感,难以发挥《公司法》所托付的监督职能。
第三,国企董事会缺乏进行“最优合同”协商所必需的“独立性”和“信息流”。尽管国企董事会遵循一人一票的表决原则,但实践中董事长往往居于支配地位。一方面,董事长可以利用其“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形式”职权,决定决议的“实质”内容;8另一方面,董事长由于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且一般兼任党委书记,在董事会中享有高度权威。若此,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或CEO职位时,董事会对其薪酬难以进行公平协商。而当董事长不兼任其他执行职务时,高管又可以通过扭曲或者隐藏薪酬制定必要信息的方式,使其个人利益的满足凌驾于公司价值最大化之上。
由此可见,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具有明显的“董事会俘获”特征。而此种“程序性”缺陷,使得针对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无需进一步考量高管薪酬的“实质”合理性,即是否确实与公司业绩挂钩。
(二)薪酬规制:程序正义v.实质公平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1世纪接连发生的安然丑闻和金融危机,都被认为与过高的高管薪酬有着内在关联。危机的扩散和民众的不满,使得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在美国成为当务之急。一系列旨在矫正高管薪酬畸高问题、实现薪酬安排“实质公平”的改革举措被相继提出。其典型代表有以下两项:第一,在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试图建立、运用“浪费”规则,以宣告过高的高管薪酬无效。在“Rogers v. Hill”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当公司的奖金支出与高管工作价值缺乏关联时,该项奖金支出构成对公司资产的浪费,应为无效。9第二,在三次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均曾考虑通过“惩罚性税收”和“工资帽”实质性地调整高管薪酬。例如,1932年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曾提议对高管薪酬超过75000美元的部分额外征税80%,并不允许公司就此项薪酬支出申请税收抵扣;罗斯福新政时期,国会要求对接受联邦援助的行业、公司的高管设置工资帽,比如铁路行业为6万美元、航空邮递业为17500美元。10
然而,这些强调实质公平的改革举措并未成为主流。一方面,浪费规则在大萧条之后便极少为法院所使用。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Brehm v. Eisner”案中指出:法院不会对包括薪酬制定在内的董事会决定展开合理与否的实质判断;与之相反,法院的判准在于其决策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11另一方面,出于保护自由市场竞争的考虑,惩罚性税收从未转化为立法;而工资帽则始终仅对接受联邦援助的公司适用,并在援助结束之后自动失效。真正得到广泛支持的,是有关加强薪酬信息披露、董事会独立性和股东决策参与权的法律变革。由此可见,有关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在美国呈现出强调“程序正义”的特征。
与之相反,受多重因素制约,中国有关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更多地着眼于“实质公平”,其突出表现即在于对国企高管薪酬进行封顶。而这种强调“实质公平”的法律规制的成因,则至少可归结为以下两个维度:
一方面,自1993年《公司法》通过以来,国企改革便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全新阶段。然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等现代企业之“形式”要素的引入,并不必然形成制约平衡的公司治理“实质”。公司治理存在的形式化倾向,与“所有者缺位”一经结合,便会由于“内部人控制”引发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基于此一现实,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便难以依托于对“程序正义”的强调,否则,无异于在沙滩之上建造城堡。
另一方面,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手段的选择,还受到“人事管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双重约束。首先,尽管监管者一直力主对国企“去行政级别”,但现实中,国企高管往往仍按部、厅、处等级别享受待遇、评价职务调动。与此同时,为增加工作激励、加强国资委与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国企高管往往存在向党政机关“晋升”、进行“挂职锻炼”和“岗位轮换”的情况。受此种行政化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影响,国企高管的薪酬便应当在“实质”数额上加以限制,否则,无法与其他行政职位进行有效衔接。其次,由于市场化改革前国企内部的薪资分配较为强调平等性,厂长、干部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因此,高管薪酬的过快增长可能会对既存的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产生冲击。另外,高管薪酬的快速增长、与企业职工或者社会公众平均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也与消除两极分化、解决分配不公的和谐发展观念有所抵牾。正是受以上收入“平等”“公平”观念的影响,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也必然更加倾向于对“实质公平”的强调。
综上所述,与作为参照的美国不同,中国国企的高管薪酬实践在“制定”和“规制”特征上均呈现其个性。此种个性特征,不仅形塑了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的“特殊问题表现”,更成为对既存法律规制手段所展开的一切检讨反思、未来改革方案构建所不容忽略的起点。
二、国企高管薪酬的特殊问题表现
1978年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的经济活动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调控。彼时,由于高管(厂长、干部)和普通职工(工人)之间的薪酬差距甚微、以物质奖励引导生产的观念尚未普遍化,针对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并不必要。1978年之后,包括“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利改税”等在内的政策举措相继推出,政府开始使用薪酬激励的手段推动国企改革。然而总体而言,由于尚未采取包括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权在内的“激励薪酬”,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并不显著,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问题仍不突出。1990年代开始,为满足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要求,更好地在香港、纽约等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国有控股的“红筹”公司开始对其高管提供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权在内的激励薪酬。12伴随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入、与国际接轨以便参与全球竞争的需求加强,原本仅在境外上市的国企中采行的股权激励,开始向在境内上市的国企开放。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股权激励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国企高管的薪酬,拉大了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在同一时期,国企的经济绩效虽有所提高,但却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上全面落后于私人企业。自此,高管薪酬的“不公平”和“无效率”问题,使得针对其的法律规制变得极为必要。然而,高管薪酬在国企实践中呈现出远较“不公平”和“无效率”更为复杂的“特殊问题表现”。
(一)漂浮的高管薪酬:零薪酬与被压抑的股权激励
1.零薪酬
“过高”或者“过快增长”的高管薪酬是法律规制的典型对象。然而,在中国国企实践中,却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现象,即高管“零薪酬”。一份针对约3400家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有近300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2015年的薪资为0”。13但是,零薪酬并不意味着高管确实提供了无偿劳动。就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而言,其事实上或者兼任其他关联公司的高管职务,或者本身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收入。此种薪酬安排至少从两个方面扭曲了国企的公司治理:
第一,国企往往处于企业集团这一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以中央企业为例,由国资委控股或全资持有的控股公司往往延伸出3~9个层次的子、孙公司,形成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企业集团往往通过剥离(注入)不良(优质)资产的方式,助推部分公司上市;并在之后,从控股公司或关联公司中派遣人员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管,以便进行控制。在这一背景下,上市公司高管不从本公司、而从控股公司或者关联公司领取薪酬的安排,可能模糊其信义义务的承担对象。由于薪酬多少并不与本公司业绩挂钩,高管更可能从企业集团的整体利益而非本公司利益出发作出决策。
第二,本身具有政府官员身份的高管,其收入、职业前景不与本公司业绩挂钩,可能加剧“政企不分”问题。一方面,其在进行公司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所在地方或者部门的利益,促使本公司进行无效率的地方性投资或者为社会稳定雇佣冗员,从而加重国企的社会、政策负担;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官员,其往往更加看重政治晋升而非经济激励,因此其企业家角色淡化而更不易于抵御不正当的政治干预。
2.被压抑的股权激励
包括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权在内的股权激励的引入,往往被认为是高管薪酬飞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有关股权激励无法切实促进公司业绩增长、易于引发高管财务造假的研究,亦不断揭露其可能产生的无效率和不公平问题。然而,在国企实践中,股权激励还另外呈现出两副面孔:
第一,尽管按照《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等文件的要求,国企高管的薪酬组成应当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中长期激励”,但实证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年初,开展股权激励的国企上市公司有21家,仅占总体的11%”。14近年来,在国资委的重点推进下,“双百企业”(国资骨干企业)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比例也仅达到19%。15由此可见,即便股权激励确实在美国引发了严重的高管薪酬无效率或不公平问题,这些负面影响在中国国企中其实并不显著。
第二,在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国企中,还可能由于“行权禁止”和“行权收入交公”等因素的存在,股权激励的制度功能大打折扣。在一项针对“红筹”公司(前任)高管的采访中,受访者表示:其薪酬构成中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权,其实并不能由自己决定行权;即便行权,行权收益也需要上交控股公司。16此种说法,还可以从其他轶事证据中获得支撑。例如,中海油前任董事长傅成玉便表示,自己并未真正行使过作为高管拥有的股票期权;17中海油控股股东亦曾澄清“有关薪酬只是‘名义收入’,且会全数捐赠予母公司”。18
股权激励在国企中的“低采用率”和“名实不符”,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扭曲了公司治理:一方面,大量国企甚至国有上市公司,可能仍然未为高管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从而不利于国企对经济目标的追求;另一方面,名实不符的股权激励,减损了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进一步削弱了中国资本市场本就孱弱的监督功效。
(二)另类的锦标赛:在职消费和政治晋升
尽管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容易造成直觉上的“不公平感”,但这种不公平有时却是实现经营效率的必要代价。除去“按业绩付费”这一种解释之外,为实现效率而容忍不公平还可以从“锦标赛理论”中得到说明。该理论提出:对企业内部不同层级的员工设置较大的工资差距,并使员工事先无从得知谁会最终得到提拔,可以对其提供努力工作的激励;19另外,伴随晋升空间的不断缩小,高层级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应当进一步扩大。20然而,在国企实践中,锦标赛很大程度上不以工资差距的方式展开,转而以“在职消费”和“政治晋升”的方式呈现。这种另类的锦标赛同样会削弱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并最终扭曲公司治理。
1.在职消费
所谓在职消费,是高管凭借其特权在工资之外所获得的“非货币性”收益。21尽管部分在职消费属于高管履行职务之必需、外国/私人企业高管亦享受较高的在职消费,但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构成其主要收入的现象则颇为反常。一份针对处于垄断性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绝大多数为国企)的实证研究显示:高管在职消费的均值是货币性薪酬均值的50.6~79.2倍。22高管在职消费金额高企的成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司为内部人所控制,资源被任意挥霍以满足高管个人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股权激励受抑制等因素,国企高管自认薪酬并未达到市场价格,出于“嫉妒”心理通过在职消费抹平差距。无论基于何种成因,国企高管所享受的高额在职消费都必然溢出于履行职务之必需的范围。此种不合理的、仅能为高管所获取的非货币性收益,虽然也能在企业内部促成锦标赛,却会严重败坏公司治理。
第一,与货币性薪酬不同,在职消费的合理性难以被查验、纠偏。以股权激励为典型代表,货币性薪酬总是需要与公司业绩相挂钩。如此一来,高管的货币性薪酬总是能够借由“客观指标”进行查验、纠偏。与此不同,在职消费的合理性则体现出需要主观判断的特征。对于高管使用的50平方米办公室是否过于豪华、出席会议是否必须乘坐头等舱等问题,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答案。即便股东、监管机关有所不满,亦很难证明其不合理性。第二,超出合理范围的在职消费,会为高管的不正当行为提供“正当化”激励。当高管出于嫉妒心理,利用不合理在职消费消除与外部同行的薪酬差距时,其往往认为此种不正当行为是“本质正当”的。此种“道德”正当化过程可能促使高管进行更多不正当行为——因为其可以借助“消除(不正当的)薪酬差距”这一理由对之加以正当化。
2.政治晋升
在国企内部,政治晋升亦能通过引发锦标赛向高管提供工作激励。一方面,伴随政治级别的晋升,不仅高管的货币性薪酬获得提升,而且其享受在职消费的机会、规模亦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国企高管向党政部门的晋升可以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地位和声望。将政治晋升纳入锦标赛范畴,有其积极效应。如何向最终获胜者(如CEO)继续提供有力的激励,对于锦标赛理论十分重要。在一般企业中,可选的方式只能是向其提供更高的经济报酬。然而,由于效用边际递减,经济报酬的激励作用终将消退;而向党政机关的政治晋升,则为锦标赛提供了另一种激励形式。然而,政治晋升引发的锦标赛亦可能产生严重的负作用:
第一,重视政治晋升而非经济报酬,可能加剧国企的政企不分问题。当政治晋升成为主要激励,国企高管不仅会更加愿意接受政治干预,从而维持与上级之间的良好关系,为未来的晋升创造条件;甚至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自觉注意迎合地方或者部门利益,从而加重国企的社会和政策负担。第二,重视政治晋升,还可能不利于国企内部管理模式的转变。例如,对于处在充分竞争领域、重视创新和员工积极性的企业而言,强调去等级和速决策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可能更有效率。然而,由于过分重视政治晋升,该种企业反而可能更愿意保留“等级式”的内部管理模式。
三、既存法律规制手段的反思
针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无效率和不公平问题,一系列法律规制手段被相继推出。这些规制手段,或者聚焦于“实质公平”,例如《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高管薪酬进行(有弹性的)封顶,《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下简称《八项规定》)则对高管的在职消费提出限制;或者聚焦于“程序正义”,例如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并“强制”要求公开薪酬安排的详细信息。然而,就严厉程度和实际效果而言,聚焦“实质公平”的规制手段,在当下显然仍处于核心地位。就国企高管薪酬的特殊问题表现而言,以上规制手段似乎可谓对症下药:薪酬封顶直击“过高”和“过快增长”的高管薪酬问题;《八项规定》约束高管进行不合理在职消费的攫取之手。但事实上,既存的法律规制手段,不仅不能有效回应国企高管薪酬的特殊问题表现,反而可能使之进一步恶化。
(一)“一刀切”:“意外推高”与“逆市场化”
根据《意见》的规定,国企高管的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年薪以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为限,绩效年薪以基本年薪的“2倍”为限,任期激励收入以年薪总水平的“30%”为限。考虑企业所处行业和规模、高管岗位职责和风险承担等因素,《意见》允许国企根据实际情况“在限额内”进行自主安排。例如,副职负责人的基本年薪按主要负责人的“0.6~0.9倍确定”,以此在企业内部形成经济激励方面的锦标赛。“一刀切”的高管限薪自然有其优势:一方面,“一刀切”的法律规制可以最快速度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一刀切”的法律规制还可以节约国资委本就有限的“执法”资源。自2003年成立以来,针对国企的公司治理问题,相较于通过股东会或董事会机制行使“股东权”,国资委仍更多使用“红头文件式”的行政管理手段。这其中自然有“政企不分”的缘由,也内涵着“执法”效率的考量:与强调一企一策、精准施策的股东权行使不同,面向全体国企的行政权行使可以通过形成“规模效应”节约“执法”资源。然而,“一刀切”的高管限薪却可能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
第一,高管限薪可能意外地推高高管薪酬。限薪的本意在于抑制“过高”和“过快增长”的国企高管薪酬。根据《意见》的规定,国企高管的年薪最多不能超过普通员工年薪的8~9倍。对于原本薪酬差距超过这一限制的国企而言,《意见》当然可以起到降低高管薪酬的作用。然而,对于其他国企而言,《意见》反而可能推高高管薪酬。其原因在于:《意见》在限薪的同时,也正当化了高管薪酬与员工年薪之间8~9倍的差距;原本薪酬差距未达这一限制的国企,反而可能以此为依据为高管加薪。如此一来,《意见》便可能意外地促成更多“过高”和“过快增长”的国企高管薪酬的出现。
第二,行政管理色彩浓厚的限薪,还可能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有所违背。一方面,高管薪酬的快速增长,不仅有董事会俘获的原因,也有管理人才供不应求的正常市场因素。在这一背景下,限薪可能导致国企高管薪酬“过低”,而“过低”的高管薪酬在加剧国企高管嫉妒心理的同时,也不利于招揽市场化的管理人才。现有的折衷方案是允许通过市场招聘的高管不受《意见》约束,但由此导致的内部薪酬差距亦可能借由“嫉妒”和“不公平感”而影响公司经营管理。另一方面,“过低”的高管薪酬亦将使高管收入与公司业绩发生“脱钩”,此时,包括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在内的薪酬安排便无法发挥其促使高管为公司利益最大化而努力的目的。
(二)“两头堵”:“薪酬补偿”与“挤出效应”
限薪虽然在“表面”上降低了高管的货币性收益,但并不会使高管自愿接受“过低”的薪酬安排。与之相反,高管可以通过享受更高的在职消费的方式进行“自我补偿”。事实上,在《意见》出台之前,国企的高管薪酬便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限制及其所造成的高管薪酬的“外部不公平”,使得国企高管转而将在职消费作为“薪酬补偿”。若此,随着限薪的进一步收紧,薪酬补偿造成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恶化。正因如此,中央试图通过落实《八项规定》限制不合理的在职消费。然而,同时实施限薪令和八项规定的“两头堵”策略,亦有其副作用:
第一,如前所述,在职消费的“合理性”极难查验、纠偏。《八项规定》所提出的“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在执行中亦面临相同难题。尽管包括“住房、车辆配备”等在内的部分“工作和生活待遇”确实可在事前进行精细界定,但在职消费的形式多种多样,难以全部客观化、指标化。《八项规定》在实际落地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问题,恰为这一判断的最佳注脚。例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便指出,在国企对《八项规定》的落实过程中,不仅违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而且“一些‘四风’问题改头换面、潜入地下,呈现出由明转暗、逃避监管等隐形变异现象”。23
第二,“两头堵”策略,还可能产生不利于国企市场化改革的“挤出”效应。假设《八项规定》在实践中确能得到完全落实,则“两头堵”策略将会限缩锦标赛的开展形式。一方面,限薪可能造成高管薪酬“过低”,从而导致以工资差距为内容的锦标赛无法进行或效果不彰;另一方面,严格受限的在职消费使得高管进行薪酬补偿的努力无从实现,导致以享受在职消费为内容的锦标赛失去意义。此时,锦标赛仅能围绕政治晋升而展开,国企的高管职务亦将因此对重视政治晋升而非经济报酬的人员更具吸引力。伴随时间的推移、人员的更替,市场化人才将被逐渐挤出国企。若此,则前述“逆市场化”问题亦会有所加剧。
(三)缺乏实效的程序性构建
除聚焦“实质公平”的规制手段外,我国近年来亦借鉴美国经验,引入了一系列提升“程序正义”的政策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薪酬委员会”和“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然而,从实践来看,这些政策措施或者本就存在设计缺陷,或者并未切中肯綮,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1.没有“牙齿”的委员会
尽管《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仅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设立“薪酬委员会”,但由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准则第2号》)的规定,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已是一项“硬性”要求。在上市公司中引入薪酬委员会,并要求其多数成员由独立董事担任,自然是希望通过提升高管薪酬制定程序的“独立性”来克服其无效率和不公平的问题;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一制度目的并没得到完全实现。一方面,就整体而言,“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并没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24;另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较,国企薪酬委员会的治理能力较弱。25制度目的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疏离,显然可以被归结于薪酬委员会的力量缺乏。
第一,根据《准则》的规定,薪酬委员会虽有“研究和审查”高管薪酬方案的权力,但该方案的最终批准权仍为董事会所掌握。如前所述,国企存在突出的“董事会俘获”问题,此种权力分配难以解决高管“自定”薪酬的问题。第二,与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薪酬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不同,《准则》仅要求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占多数”。若此,内部董事亦可以充任委员会成员,并可能对委员会决议施加影响。第三,薪酬委员会为董事会的“下设机构”,其成员在实践中往往由“董事长、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或者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提名”,并最终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考虑到突出的董事会俘获问题、委员会成员当选或连任与否系于董事会意志等因素,薪酬委员会难以发挥实效也就完全可以预见。
2.不充分的信息披露
有关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在过去十余年间已大有完善。2003年修订的《准则第2号》仅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和前三名高管的“报酬总额”;而2017年修订的《准则第2号》则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每一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报酬总额及其全体合计金额。此种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细化,当然有助于提升高管薪酬的透明度,增强资本市场和高管声誉机制的监督作用,然而,既存的信息披露制度其实尚难以回应国企高管薪酬的特殊问题表现。
第一,高管“零薪酬”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未得到消解。尽管根据《准则第2号》第55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需说明其高管“是否在公司关联方获取报酬”,但上市公司无需进一步披露高管在关联方所获报酬的具体情况。就国企而言,这一规定不仅继续认可了其高管在关联企业甚或政府部门获取报酬的实践,更使其实际所受激励的结构和数额无法为外部市场所知。第二,资本市场无法借助信息披露对不合理的在职消费进行监督、纠偏。根据《准则第2号》第55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虽然需要披露“每一位”高管的薪酬,但亦仅需披露“总额”;至于构成总额的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形式、数额究竟如何,仍不为公众投资者所知。如前所述,在高管薪酬受到“限薪”和“八项规定”的“两头堵”时,其往往通过在职消费进行“自行补偿”。若上市公司无需详细披露高管的非货币性收益信息,则因不合理的在职消费所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无法得到缓解,更遑论消除。
四、国企高管薪酬规制路径的再构建
(一)思维转换:从“一刀切”到“精准施策”
根据《意见》的规定,国企高管薪酬被“一刀切”地限制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9倍之内。对于此种规制手段在实践层面所可能引发的负作用,前文已有所论及。然而,其作为一项规制手段在应然层面上的“不可欲性”,则仍有待进一步检讨。
第一,无论立法抑或司法机关,均难以为“过高”提供精准界定。“一刀切”的规制目的在于抑制过高的高管薪酬,其正当性必须建立在对如下两个问题的回答之上:其一,5~6倍甚或3~4倍的薪资差距,何以不构成过高;其二,9~10倍甚或10~11倍的薪资差距,又何以构成过高。对于以上两项问题,其实均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意见》出台之后,关于国企高管薪酬究竟“过高”抑或“过低”的讨论持续发酵,为其注脚之一。而“一刀切”的规制手段在美国法上的式微,则可以提供另一种视角的参考。如前所述,在三次危机时期,美国均曾提议或者采纳“一刀切”的规制手段,然而这些措施最终都没有成为主流。至于其原因,则可以从美国法院对“浪费规则”的态度中窥见一斑。在“Rogers v. Hill”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过高的”薪酬属于无效。但是,其并没有就如何判断“过高”设置明确的标准,而是将案件发回重审交由下级法院解决。该案最终以原被告和解而结案,法院也因此无须提供标准。而在“Brehm v. Eisner”案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则拒绝对高管薪酬的实质合理性进行讨论,而强调对“商事判断规则”的坚持。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法院根本无法对何谓“过高”进行精准界定。
第二,由于所处行业、发展战略、管理人才稀缺度等因素,高管薪酬的确定本就因公司而异,无法在事前进行“一刀切”的法律规制。对于这一点,针对《意见》实效而展开的实证研究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撑。一份针对2007~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意见》对“成长性较好样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其原因即在于该类公司更需要通过高薪酬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26另一份针对《意见》之前其他限薪政策的实证研究指出:对垄断性的国企进行限薪,可以在不影响公司业绩的前提下提升内部公平感;然而,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则可能因此遭受效率减损。27事实上,《意见》及其他限薪政策并非对该问题全然没有体察。例如,根据《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负责人基本年薪的确定应考量“企业经营规模”和“经营管理难度”等因素,但此种“弹性”为国企适应个性需求预留的空间仍然太小,不足以克服“一刀切”式法律规制的弊端。
若此,针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应当完成从“一刀切”到“精准施策”的转变。至于精准施策的含义,必然是要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在充分考量“个体”国企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其薪酬安排作出“个别”回应。若此,则各级国资委必须借助“股东会”和“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制,而非“红头文件”对高管薪酬进行监管。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如前所述,红头文件式的行政管理可以节约国资委的“执法”资源;则“精准施策”是否会导致国资委力有不逮?事实上,在“一刀切”的规制思维得以转变后,法律规制的重点亦必将从实质公平转向程序正义;此时,借助内部治理和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国资委反而可以依托其他制度资源更好地履行其出资人职责。
(二)侧重转移:程序正义及其保障
既然国企的高管薪酬不应进行“一刀切”的事前封顶,则其具体数额、结构、形式便应交由公司自己加以确定。此时,国企高管薪酬制定所呈现的“董事会俘获”特征,便成为必须克服的障碍。而此种克服又主要可以借助“薪酬委员会”和“信息披露”两项机制加以实现。
1.为薪酬委员会“赋权”
若欲使薪酬委员会制度克服“董事会俘获”问题,并最终达成关于高管薪酬安排的“最优合同”,便需要赋予其充分的“权威”。此一赋权至少需从如下方面进行:第一,薪酬委员会的职权,应从“研究和审查”薪酬政策与方案,扩充至“制定和批准”薪酬政策与方案。若认为这一方案过于激进,则至少应规定由薪酬委员会拟定的薪酬方案,董事会无正当理由不得修改。第二,薪酬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应从“独立董事应当占多数”,改变为“应当全部由独立董事担任”。尽管《准则》规定应当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主席),从而对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有所帮助,但内部董事兼任委员仍然能对决策过程、结果直接施加影响,有损委员会的功能发挥。第三,薪酬委员会成员的选任方式,应由“董事会选举产生”改变为“全体独立董事选举产生”。另外,还应当对薪酬委员会成员的解任设置“有因解除规则”,以避免其在行权过程中遭受不当干预。28第四,鉴于独立董事的选任本就受制于高管的客观现实,似乎还应考虑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储备库,从中随机抽取独立董事以组成薪酬委员会的方案。
在权威赋予之外,还必须给予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方案所必需之信息,否则,其权威无从真正实现。而当薪酬委员会成员完全由独立董事担任时,其信息匮乏问题便更加严重。此时,存在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允许高管参与薪酬委员会讨论,以向后者提供与其薪酬制定相关之信息,但禁止其参与薪酬的最终制定;二是设置可以行使(1)接近公司各类职员、(2)调查公司各类内部文件、(3)参加各种董事会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各项职权的“监察使”(Ombudsperson)一职29,为薪酬委员会提供必要信息。
2.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再细化
第一,尽管“零薪酬”在国企大多以“企业集团”形式构建,在政府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现实下无法被直接禁止,但其可能导致的信义义务承担对象的错位问题,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大意义,必须予以详细公开。《准则第2号》应进一步要求上市公司说明该高管在关联方取得报酬的数额和具体构成形式,并披露该关联方的实际控制人等。通过此种详细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可以提前获知高管信义义务承担对象的可能错位问题,并做出不购买或者折价购买股份的决定。
第二,在职消费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分,然而其边界、查验和纠偏却较难进行。此时,通过信息披露施加“声誉”惩罚比诉诸正式的法律诉讼程序更有效率。根据《准则第2号》的规定,上市公司仅需公开每一位高管从公司中所获取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总额”,而不必就各项内容的个别数额进行详细披露。若此,则高管是否、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在职消费的情况,根本无从为公众投资者所知晓。《准则第2号》应当在未来进一步要求上市公司详细公开高管所享受的所有无法被划归为基本年薪、年度绩效和中长期激励的货币或非货币性收益,而无论其数额。
在法律规制的侧重从实质公平转移至程序正义之后,国资委仅需关注国企是否搭建了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了足够的信息披露。此时,国资委可以借助独立董事、证监会、资本市场和声誉机制等制度资源辅助其履行出资人职责。若此,则国资委的“执法”资源不会由于需要进行“精准施策”而捉襟见肘。
(三)结构优化:股权激励和绩效年薪
第一,股权激励的“广泛化”和“真实化”。自20世纪70年代 Jensen and Meckling提出公司治理的“代理成本”范式以来,以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权为典型形态的激励薪酬便被认为是一项可能的治理机制。尽管过去实践已充分暴露出其弊端,但其促成高管与公司利益连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应然)功能亦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上,伴随内外部公司治理的不断完善,股权激励的优势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前所述,就现阶段而言,股权激励在国企中存在“低采用率”和“名不符实”的问题。因此,与美国正在经受的股权激励的巨大负作用相比,我国国企的股权激励尚需首先完成“广泛化”和“真实化”的制度创设工作。这一创设工作的总体方向自然应以“分类改革”为基础。至于股权激励在个别国企高管薪酬中的具体比例,则一如前述,应交由该国企通过内部程序加以决定,并依托信息披露等制度设计接受监督。
第二,绩效年薪的“去中心化”。根据《意见》的规定,国企高管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三个部分组成。按照中长期激励不超过年薪的30%、绩效年薪最多为基本年薪2倍计算,高管薪酬中的“绩效年薪”最多可占年薪的46.7%。若此,则绩效年薪这一“短期”激励在国企高管薪酬中占据“中心”地位。尽管存在“延期支付”和“薪酬追索”等约束机制,但是绩效年薪的中心化,仍可能造成严重的“短视”问题从而损害国企长远发展。其原因至少可被归结为如下两点。一方面,相较于公司的中长期表现,与绩效年薪相挂钩的公司年度业绩数据更容易被伪造、篡改;另一方面,相较于中长期激励,绩效年薪的兑现更快,从而具有更高的“现值”。考虑以上因素,未来的国企高管薪酬应当完成绩效年薪的“去中心化”,而放开对中长期激励比例的限制。至于中长期激励,尤其是股权激励所可能带来的无效率和不公平问题,则应交由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加以解决。
五、结语
就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而言,其高管薪酬的合理确定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有效率的薪酬数额、结构可以为高管自觉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动力;另一方面,无效率、不公平的薪酬则不仅有损国企利益,更削弱、动摇民众对国企乃至公有制的信心。尽管在过去四十余年,尤其是近二十年里,一系列旨在解决国企高管薪酬之无效率和不公平问题的法律规制手段被相继提出,但这些规制手段,或者由于本身存在设计缺陷,或者对国企实践中呈现的“本土化”问题缺乏回应,不仅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高管薪酬的不公平和无效率。未来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必须进行整体性调整:一方面,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应当完成从“一刀切”到“精准施策”的思维转换,并由此应当更加关注包括薪酬委员会赋权和信息披露细化在内的“程序正义”构建;另一方面,在摒弃对高管薪酬数额、形式的硬性限制的基础上,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应同时关注薪酬结构的优化问题,以避免短视主义的危害。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9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公司股利分配法律制度研究”(19SFB3032)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See Rogers v. Hill (Hill III), 289 U. S. 582 (1933).
2. See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3(4): 305-360.
3. See Jensen M C, Murphy K J. CEO incentives—it's not how much you pay, but how[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 (May-June): 139-140.
4. See Stout L A. The toxic side effects of shareholder primacy[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2013, 161(7): 2009.
5. See Core J E, et al. Is U.S. CEO compensation inefficient pay without performance?[J]. Michigan Law Review, 2005,103(6): 1142-1185.
6. See Bebchuk L, Fried J.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参见郭雳. 中国式监事会:安于何处,去向何方——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再审思[J]. 比较法研究, 2016, (2): 76-78.
8. See Kershaw D. Company law in context: text and material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250-251.
9. 同注1。
10. See Wells H. “No man can be worth $1000000 a year”: the fight ove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1930s America[J].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2010, 44(2): 751-754.
11. See Brehm v. Eisner, 746 A. 2d 244 (Del. 2000).
12. See Chen Z, Guan Y, Ke B. Are stock option grants to directors of state controlled Chinese firms listed in HongKong genuine compensatio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5): 1555.
13. 参见2136家企业高管薪酬上涨 近300位高管“零”年薪[EB/OL].[2020-04-11]. http://finance.sina.com.cn/trust/xthydt/2019-04-30/doc-ihvhiewr9038961.shtml.
14. 参见王勇, 邓峰, 金鹏剑. 混改下一步: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思路[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172.
15. 参见杜雨萌. 国资委:央企所属“双百企业”19%已实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EB/OL]. [2020-04-11].http://www.zqrb.cn/finance/hongguanjingji/2020-04-03/A1585885812375.html.
16. 同注12。
17. 参见傅成玉回忆在中海油年代:千万年薪一分没动 都上交了[EB/OL].[2020-04-11].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3lian ghui/20130308/7747017.shtml.
18. 参见中海油称所有执行董事自愿放弃去年薪金及奖金[EB/OL].[2020-04-11]. http://news.cntv.cn/20120415/120358.shtml.
19. See Bognano M L. Corporate tournament[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2): 290-315.
20. See Rosen S. Prizes and incentives in elimination tournamen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4):701-715.
21. 参见万林华. 国外在职消费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 (9): 39.
22. 参见杨蓉. 垄断行业企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 基于在职消费的视角[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 139.
23. 参见通报数据显示国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仍有短板——对症下药,释放监督刚性力量[EB/OL].[2020-04-14].http://www.ccdi.gov.cn/toutiao/201810/t20181011_181221.htm.
24. 参见高文亮, 罗宏. 薪酬管制、薪酬委员会与公司绩效[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8): 84.
25. 参见姚成. 薪酬委员会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影响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19, (17): 176.
26. 参见黄贤环, 王瑶. 国有企业限薪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吗?[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 (1): 35, 45-46.
27. 参见潘敏, 刘希曦.“限薪令”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 71-72.
28. 参见楼秋然. 董事职务期前解除的立场选择与规则重构[J]. 环球法律评论, 2020, (2): 102-117.
29. See Dallas L L.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 the dual board and board ombudsperson[J].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1997, 54(1): 13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