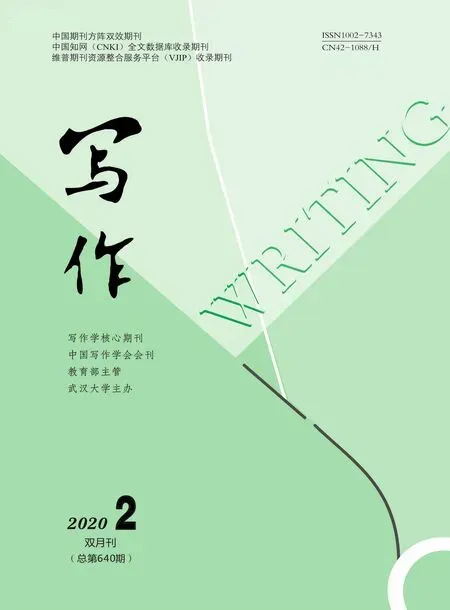镜与灯:接通“内外宇宙”的当代大陆儿童诗形态表征
刘 慧
一、生命的温情:对社会现实的深度观照
儿童诗是一种有生命温度和人性温暖的诗歌,“儿童的心灵、儿童的世界、儿童所具有的清纯的天然性又对成人的心灵和世界具有反哺的功能”①刘晓东:《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它不回避社会现实的问题,但展开的书写维度却是更能给读者以信心和希望的“暖心”诗歌。它对于社会现实的观照并不浮泛,而是在痛彻心扉的深度下另辟蹊径,探寻着心灵的救赎方式。
叶延滨的诗《信仰——夸一夸我的小弟。1967年深秋》写了在那个黑白颠倒、道德沦丧的社会畸形时期一家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他们用爱维系家庭,用“信仰”支撑生命:“牛棚里出来,/爸爸失去健康。/妈常担心地想,/又不敢讲:/‘他,他的肝硬化咋样?’/爸在梦中疼醒,/却安慰她:/‘老毛病,天阴,枪伤……’//一张造反派的通告贴在门上,/一家人被赶进一间小房。/妈把两床褥子都给我们:/‘孩子,睡在地板上凉……’我却笑着回答:/‘这下,别担心小弟弟滚下床!’//失去的就失去吧,/咱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想唱一家人来个 ‘四重唱’!/爸爸摸着小弟的头问/‘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嘿,小弟说:/‘有信仰!’//啊,信仰就是明天希望,/啊,信仰就是空气、太阳。/信仰里有同志和朋友,/信仰带来笑声和欢畅!”面对丑恶,善良之花仍然会悄然绽放,这才是人性得以保存余温,社会能继续发展的力量。儿童诗正是这种给人希望的文学存在方式。“我曾遇到过一双眼睛,/那是一双女人的眼睛/——她说钱丢净了。/她的家在W城。/家里在有个两岁的孩子在等。/她的眼睛里好像有泪,/我仿佛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于是我掏出兜里所有的毛票,/心里想着她平安的归程……//在另外一天的另外一个胡同,/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的那双眼睛!/也是一个少年,/也是我那天经历过的情景!//为此我像得了一场病。/病好了许久以后,/我仍害怕一类人的眼睛。/我也因此而感到庆幸:/我既有过一次轻信的经历,/又看到了别人与我同样的真诚。”薛卫民的《眼睛》写出了一位少年儿童人生中面对第一次欺骗时内心的波澜,欺骗使得真诚的少年心灵受到伤害。但在这次轻信的经历后,少年的辨别力得以提升,内心也更加强大,真善的良知并没有因被骗而失掉,反而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真诚存在,从而弥合了心灵的伤痛。
面对惨绝人寰的战争和自然灾难,儿童诗并没有回避和远遁:“把教室/搬到/帐篷里/一边听/老师的谆谆教诲/一边听/战争的肆无忌惮//把家园/挪到/墙洞里/一边在/黑暗里摸索/前进的路/一边看/洞外的天空/是否有忧郁的/阴云。”巴以冲突中,一名巴勒斯坦儿童在加沙地带一所学校的墙洞里往外看,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学校被毁后只能在帐篷里上课。何腾江用《撞击心灵》记录了这一切,触目惊心的战争还在继续,而人类对于知识的渴望以及和平生活的向往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谭旭东《流泪的课桌》、张品成《这一张奖状》等大量书写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学生的儿童诗,读来痛彻心扉。自然灾难往往使人类重新意识到自我的渺小。而黄亚洲《用我们的人体,连续射击》(组诗)又揭示着人类在大灾大难面前守望相助的人性伟力,“军队用淌血的手掌/托出了一代人/这一代人的书包里/永远有瓦砾、沙土、发黑的雨水,以及士兵的血……”军人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以及对于“下一代”生命的无限珍视构成了最为动人心扉的人间真情。“世界上,/有一种烛光,/永不会熄灭,/靠无畏精神的培植,/这个烛光,/长在人的手心,/一代代,在风里,雨里,/烛光也依然摇曳,/啊,南丁格尔,/是第一个燃烛的人,/她创造了世界上,/一种,特殊的蜡烛,/这种蜡烛,/永远燃在人的心里,/爱,是它永远的能源。”正如商泽军的儿童诗《南丁格尔的烛光——致获南丁格尔奖章的中国战士》中表达的一样,爱是代际传承的能源,爱是人类更迭繁衍的力量,爱是世界发展的动因,爱也是儿童诗观照人类社会现实的情感基调。这种爱是博大的、众生平等的,这种去除世俗功利的真纯之爱,是独属于孩童真纯的灵魂和儿童诗的表达的。“你挂在长安街上,/你不是五星红旗,/你的汗水却把红旗浸染,/没有你的劳动,/长安街不会如此光鲜。”徐德霞的《长安街上的洗楼工》混合着温情的关爱,以儿童之口道出了洗楼工的价值所在,并对其劳动给予赞美。
姚业涌《致慢班的一位同学》是对现实应试教育的学校分班制度下儿童心理的刻画和抚慰:“凭着一张考卷的成绩,/就把你和我分离/——一个在‘快班’,/一个在‘慢班’,/同桌的回忆分成两半,/熟悉的话语从此消失//分离就分离,/请你把低垂的头颅抬起//我和你依然生活在,/同一片阳光下面,/站立在同一片土地,/依然在老师身边,/吮吸知识的乳汁//分离就分离,/生活没有把你抛弃,/同一个目标,召唤,/你和我飞翔的双翼,/不要把分数看得太重,/看得太重就不能起飞,/请在自己脚下打好,/奋飞的地基//分离就分离,/成功不喜欢怨叹,/只相信汗水和足迹。”诗中的主人公“我”虽然对被分配到“慢班”的同桌有万般不舍,但更多的是积极的自信心鼓励,夯实学习基础,共同奋飞翱翔。事实上,分快慢班这种教育管理机制曾经挫伤过很多少年儿童的自信心和学习热情。这首诗没有采取控诉的角度来体现这种教育管理机制的片面性和危险性,而是从儿童正面、阳光的立场出发,选用了鼓舞劝慰的书写角度,但成人读者是能读出对于功利的教育管理制度的反思意味的。
而对于当下依然存在的贫穷和城乡差异导致的留守儿童现象,儿童诗从儿童的角度给予书写和自我关注,其间,底层民众的生活之艰难和骨肉分离的无奈也跃然纸上:“孩子叫作故乡,/父母叫作异乡,/父母变成一张车票,/父母变成一趟火车,/父母变成一座工厂,/异乡在父母身上流汗,/流出的汗都叫作泪,/汗水其实想,/浇灌成长,/孩子想学变魔术,/把车票变成父母,/把火车变成父母,/把工厂变成父母,/把异乡变成父母,/把父母变回自己身边。”张绍民的《把异乡变成故乡》写出了转型变革时期孩子们的现实疼痛,诗中九个“变”字传递出了孩子渴盼父母陪伴的急切心情,等待遥不可及,“变”立竿见影。诗人把儿童的幻想和父辈艰辛讨生活的现实结合了起来,彻底地改“变”成为了在异乡工厂打拼,想要努力改变下一代命运的底层人民的心音。
当代大陆儿童诗对于社会现实的观照不同于成人诗的直指当下,它更多的是温暖人心,以柔克刚,以真纯荡涤丑陋甚至卑劣。它的方式是委婉而动人的,它的情感宣泄是有节制而内敛的,“向光性”仍然是它的主要诗学特征,而它本身也是温情的自发热体。相较于成人诗歌对社会现实的显“危”镜功能,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成人诗歌构成了一种互补和互动,发挥着显“微”镜的作用。通过对微物的温情书写而反观出阔达的社会人生不同的侧面,丰盈着整个的诗学体系建构,使其更加张弛有度,磁力场平衡和谐。
二、对历史文化的“轻盈”审视
儿童天然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成人的待物态度,也存在着一种与成人对历史文化迥异的思考和审视方式。因而,在当代大陆儿童诗中,关于历史文化的内容出现之时,往往是诗思出人意表,四两拨千斤的“轻盈”表达使得既定的成人观念下的历史文化“面目全非”,从而也拨开既有的历史文化烟云,呈现出儿童视角下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景。
一类是在对古典文学、民间故事传说的“轻盈”审视中创造性的诗思诉诸笔端。王立春的《老秋翁》就是重新演绎了冯梦龙“三言二拍”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而王立春的《七月七》是在“牛郎织女”传说原有寓意基础上,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把牛郎织女的相思之情做了淡化和弱化处理,延展强化出的是孩子对母亲的想念之情。“这是一年中/惟一的一次相会/你看那两个孩子/就要/见到自己的妈妈了”。而诗人笔锋突转穿越回到当下现实,末尾一节中将儿童对远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的想念也寄寓在了七夕之夜中:“这七月七的夜晚/妈妈/在我们睡着之后/你会/带着我们的梦/去和城里的爸爸相会么”,如此精心的构思把传说故事与现实相勾连,更具神话传说的现代意义。高洪波的《都江堰的二郎神》是以儿童视角为神话传说中曾经的反面人物二郎神重塑形象:“你拿着铁锹劳动,/比握三尖两刃枪更威风!/你制伏了江水,/还驯服了凶龙,……你是凡人,/也是英雄。/像齐天大圣一样,/屹立在我的心中。”敢于大胆质疑经典的勇气是儿童独具的思维习性和思想魅力,他们的思想还暂时没有受到拘囿,是发散型并自成体系的,也因此有别于成人的思维套路,而使儿童诗的主题思想呈现别有洞天。
一类是在对西方经典童话借鉴与创造转化时,不为原作所束缚,给西方童话经典赋予了崭新的生命面貌。例如,圣野的《竹林奇遇》中,故事接续着著名的西方童话《皇帝的新衣》,第二天,那个说了“皇帝根本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被皇帝依然信任的两个骗子追踪,他逃跑到了密密的竹林里,就再也找不到了。“他的妈妈很担心,/到竹林里找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孩子,出来吧,出来吧,/骗子已经回城了’/忽然,妈妈听到,/一根竹子里有声音。//妈妈连忙请篾匠来,/破开那根竹子,这个说真话的小孩,/果然从竹节里跳出来了!/妈妈惊奇地问他:/‘你躲在这里干什么?’/孩子认真地回答:/‘这里叫虚心国,/安全地住着,/不说谎的公民。’”这首儿童诗虽是西方童话故事的延伸,但更多寄寓的是中国的民族文化智慧,从竹子这一中国典型的“君子”风范代表物,到虚心国的营构,匠心独运,在奇思妙想中对说谎的国家和大部分说谎者以及用缄默变相地维护了说谎行为的人们进行了辛辣地讽刺。再比如王立春充满异国情调的“欧洲童话”系列中的《真孩子匹诺曹》和《小美人鱼》等儿童诗,都注重将西方童话与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相融合,诗思轻盈跳跃,与儿童读者的想象力与趣味性相投合,使读者有种穿越了中西童话王国的时空之感。
还具代表性的一类是对历史文化人物的大胆审视及反思。例如,高洪波的《致鲁迅》:“……鲁迅爷爷,/你真了不起!/你这当年‘教育部’的官员,/却诅咒那老中国的教育/——扼杀儿童的天性,/禁锢孩子的生机。/你希望中国儿童,/坦率、真诚,充满活力,/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虚伪和俗气!……//当然,你不是神,/你有你的偏激,/你恨猫,恨得十分彻底;/你讨厌京戏,/讨厌得不可思议;/你轻信,过后又追悔莫及;/你又那么喜爱香烟,/全不顾烟雾,/污染着空气!……”伟大的文学巨匠,民族精神之魂鲁迅先生就这样出现在了儿童的视野里,被儿童视作一个普通人来点评优点和不足,儿童的真诚和可爱,坦率和勇敢使鲁迅走下被众生膜拜的神坛,褪去被历史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完美形象,回归自我,但这形象反而更加可亲可敬,跃然纸上。儿童诗在坚守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同时,始终关注中国精神、民族性格和文化精华,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精粹中汲取营养,化作当代大陆儿童诗的创作精髓,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这也成为了当代大陆儿童诗的一个特色。
当代大陆儿童诗对历史文化的“轻盈”性来自于其特有的“儿童性”和要弘扬的“儿童精神”,而穿越中外历史文化的“审视”中更多折射着现实主义文学性的光芒,儿童性的天马行空造就了儿童诗独特的审美眼光。这也成就了另一种维度的对历史文化洞察的视野,使当代汉语新诗的表现力更加丰富而多元。
三、“直达本质”的哲思
周国平在《女儿四岁了,我们开始聊哲学》中曾说:“儿童是天生的诗人和哲学家。他们对这个世界,甚至对自己,总是充满着好奇;他们有问不完的问题,他们在不断地探索着。”①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这正道出了儿童诗的哲思属性,儿童态与原生态的宇宙万物特征相类。因而,儿童诗诗人寻着这一质朴真纯的样态书写着宇宙万物,这是一条不用弯弯绕绕却可以直达事物本质的便捷之路。古语说“大道至简”,儿童诗化繁为简的哲思同样具有穿透真理和人心的力量。
诗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文学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思考题,一千个人心中可能会有超出千种答案,“诗是什么/一个盲孩子/用心中温暖而明亮的阳光/雕塑出/想象中的/花朵的微笑。”(何鲤《诗是什么》)然而,儿童诗的回答却是这般出其不意而又充满爱的温度和感人的力量,诗就是心中的希望之光。儿童诗中的哲思不是故作高深的玄妙,而是大道于简和真的美好。当然,其中也有自然语境下对生命真谛的思考:“昨天,/当你还属于天空,/你是夜色中闪光的星星。//走上一条坠落的路,/坠落中耗去了光和热情。//于是,/你死了——成为陨石,/成为一块冰冷的石头。//于是,/我懂了,/一旦背离了天空,/星星就不再是星星。”(刘丙钧《陨石》)通过自然物的消殒而生发出了如何正确选择人生道路的启示。“在草地上,花儿自由舒展。/你采摘花儿编织花环:/花儿用一生的美丽,/装点你一时的心愿。”(明照《编织花环》)对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喜好需求,却以其他物种的美好生命为代价的行径进行深沉的反思。
大和小是看似最简单但又最复杂的充满思辨关系的哲学问题,儿童诗中对其进行了有趣又生动的呈现。“我问妈妈,/世界有多大,/妈妈拿出一个小球,/说,这么大//我对妈妈说,/奶奶家种的西瓜,/比小球大得多,/那到底是西瓜大,/还是世界大//妈妈反而说,/这么小的孩子,/胆子真大。”(庞敏《大和小》)从具象到抽象的思维转换过程中,虽然母亲没有揭示出明确的答案,但辩证的哲思已经存在于孩童脑海中。哲学不在于去观察人们尚未见到过的东西,而是去思索人人可见却无人深思过的东西。王宜振《春天很大又很小》是把哲思在美妙的童话般语境中具象化:“春天到底有多小,/问问小花朵,/也许会知道,/花朵说:/它常站在我的花瓣上跳舞,/跳完舞,又钻进小小的花苞里睡觉//春天到底有多小,/问问小燕子,/也许会知道,/燕子说:/我衔着它从南方飞到北方,/它嘛,同一粒小豌豆差不了多少//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那棵树,/也许会知道,/大树说:/春天是一只大鸟,/一棵树只是它的一根羽毛//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小朋友,/也许会知道,/小朋友说:/我们都被春天含在嘴里,/远山和草地也陷进春天的怀抱……”春天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季节,而是一个有了大小形状的具体物,物态的变化多端也证明着儿童诗的世界里想象力的奇妙和思辨性的生动。
“下雪了,下雪了,/奶奶带我到郊外赏雪。/她的头上落满了雪花,/我的头上也落满了雪花。/回到家中,/奶奶给我拂扫着/我的头上雪花没有了,/奶奶的却留在头发里,/那是好多冬天留下的雪花吗?”(逍遥《岁月》)经年岁月的雪花浸染了奶奶的头发,因而由黑变白,这岁月更迭、生命演进的人生哲学就蕴藉在了简短的诗行当中,看似清浅和不经意的表述却揭示出了生命的轨迹。顾城的《小花的信念》是一首充满象喻性和童话意味的儿童诗:“在山石组成的路上,/浮起一片小花/它们用金黄的微笑,/来回报石头的冷遇/它们相信,/最后,石头也会发芽,/也会粗糙地微笑,/在阳光和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牙齿。”美善的人性有着最坚定的信念力量,终究能营造美好的人间。童话诗人顾城正是借助于小花的信念力量来鼓励世人,在充满清逸之美的事物中浸淫着人类与自然“万物归一”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的存在,这种直达“本质”的哲思是简单、纯粹的,也是明丽而充满生趣的存在,它既符合小读者的具象感官体悟特点,同时也给潜在的成人读者以诗写哲思的另一种启示。
“儿童文学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一种简易的文学,而是要用单纯有趣的形式讲述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深奥的道义、情感、审美、良知。”①秦文君:《漫谈儿童文学的价值》,《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如果说诗歌是烛照人类灵魂之灯火,那么儿童诗就是原发性的火苗,有了这星星之火,整个世界就会溢满希望的灯火通明。儿童诗的优秀作品以思想的力量穿透童年经验,突破生活原貌,获得人类共通的儿童性、人性、社会历史的思索,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儿童“并不只是想从中看到自己,而是文学中的未知因素激发了他的阅读兴趣,他把文学阅读当成一次愉快的探险、旅行,他希望从作品中读到新鲜的,他在现实中力所不能及的事物,这从童话比儿童生活故事更能吸引儿童这一事实便可见出……因此,儿童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种‘体验生活’的要求”②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这就给儿童诗的成人创作者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优秀的诗人是不能造就的,而是天生的,在无比深刻的层次上,这与在难以接近的灵魂幽深处形成的诗性直觉有关。这种带有诗性直觉的不可遏止的力量和自由的创造性天真,正是天才诗人最深刻的方面。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如果说,成年诗人对儿童天性的彰显是一种自觉的回归,那么,儿童诗诗人对于正处于当下的童心感受则是一种自发的启程。相比之下,他们更多地具备不事雕琢的朴质和圆润,即使是那些深蕴哲学意味的言语,也是属于内心自然喷涌的原始智慧,难以复制。儿童诗中“互促性”的双向生命价值取向,其中包含了贯穿诸如人类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等的理性和感性在人的完整存在与自我实现中的各自地位,两者之间微妙复杂又深入的互相交缠,以及二者互动协作过程中理性与感性之间恰到好处的交汇融合,使寻求人类的精神性充分发展的更高可能性,成为了儿童诗乃至整个儿童文学所要积极探究的课题。
“诗是精神的食粮。但它却不能充饥。相反,它只能使人更加饥渴。然而这正是它的崇高之处。”①[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刘有元、罗选民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8页。儿童诗是一个具有特异性的诗学宇宙空间,它的儿童性与成人性的二维交互存在又使得这个宇宙空间的涵养度和能量释放愈发地充满生机,受众群体的精神给养日益充盈。但在看到当代大陆儿童诗所囊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一面的同时,儿童诗生态失衡状况也是存在的。在大量的当下大陆儿童诗中,“城市性”已成为主流,更多的是倾向于书写“城市属性”的儿童诗作品,描摹城市儿童的喜怒哀乐的心情故事以及城市背景下的世态人生。当下的乡村儿童及其生活被遮蔽,“乡村属性”的儿童诗歌中大量涉及农村题材的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例如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一批粗糙的伪儿童诗中大量涌现外,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的被发觉而少量出现。当代大陆儿童诗的总体属性仍是“城市性”的,书写乡村儿童生活、学习、内心情感状貌的具有“乡村性”特征的儿童诗还是凤毛麟角。乡村儿童是一个更加需要诗歌雨润身心的庞大群体。以儿童诗的生态失衡状况投射整个儿童文学和审美教育的生态发展状况是令人忧心的,这也是文学和教育资源的一种失衡状况的写照。而以民族性、地域性为书写范畴和特色彰显的儿童诗创作与研究也还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