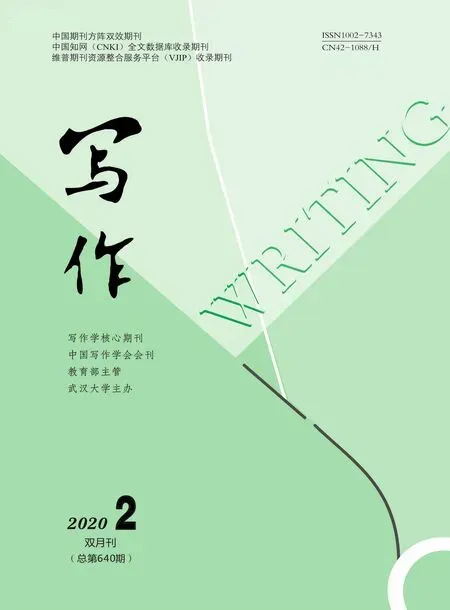宏大叙事与中国故事的书写
——何建明访谈录
王冰云 何建明
在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何建明先生应邀来澳门做关于长篇报告文学新著《大桥》创作的主题演讲。笔者利用演讲前后的空隙时间,围绕在宏大叙事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主题,请他提供个人化的写作经验和思考。现整理出来,与更多的读者、报告文学写作者、研究者分享。
一、“宏大叙事”的多种形态
王冰云:何老师,您好!首先谢谢您在繁忙的演讲间隙接受我的访谈。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在多种场合都提到当代报告文学作家要讲好中国故事。在我看来,您的中国故事书写是以宏大叙事(或称是“国家叙事”)为特征的。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宏大叙事”的呢?
何建明:你提出的问题,也有不少专家与我探讨过。确实有人认为我的报告文学题材,大多写的是重大历史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其特征是所谓的“宏大叙事”,如近期出版的反映浦东开发开放进程的《浦东史诗》和反映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大桥》。我认为,及时书写当下生活中标志性的历史和重大事件,是报告文学作家为后人研究当代史提供史料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去及时记录,随着当事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乃至离开这个世界,有很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可能就会被永远遗忘。这一类选题的创作,确实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特征。但我对宏大叙事的理解,还不仅仅停留于此。我认为,对很多做出不平凡业绩或创造出这个时代奇迹小人物的书写,也可以看作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个“大”,不是事件之大,而是“精神”之大。小人物的传奇性创造,只要折射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可以纳入到“宏大叙事”的范畴。后人在重新审视今天的历史时,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具有当代史意义的。诸如我前不久出版的讲述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特殊贡献山村老书记黄大发的故事的《山神》,还有我早期反映贫困大学生群体的《落泪是金》,当然也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作品。
二、“等米下锅”不会有出息
王冰云:有写作者认为,报告文学作家选对了题材,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我很好奇,您的这些带有宏大叙事特征的中国故事,是如何捕捉到的呢?有很多人,苦恼于不知道写什么?是不是您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外在条件,想学也没有办法学。比如说将港珠澳大桥列入写作对象,不是人人都能获得受邀写作这样的资质的。
何建明:有些重大题材的写作,确实是因为某些主管部门的信任,受邀从事写作,而我也对这类题材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一种双向选择。但这并不是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常态。尤其不可能成为许多进入这个领域不久的写作者的常态,“等米下锅”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觉得当代报告文学作家,要学会用心肺去呼吸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独特的新鲜空气。只要你有一双敏锐好奇的眼睛,一颗与时代脉搏共振的心,一支记录这个时代足迹的充满激情的笔,中国好故事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你的视野。
比如说这次我到澳门来,澳门本来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当我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宝库。我对澳门的历史和现实都感兴趣,是不是能写?怎么写?我的脑子里有很多问号。因为我不是澳门人,我要到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人提供方便,中间给我搭个桥,像一个跳板式的,有了这个桥,我走过来了,这样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去做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跟澳门正好有一个相逢的机会,什么机会呢,那就是澳门回归20周年,由于澳门方的邀请,我来到这里。澳门进入了我的视野,给了我选择、思考的可能。关于“一国两制”的推行和实践,现在看来,澳门做得比较好,上上下下,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整个世界都在看澳门的发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特殊的参照。这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作家要有这种敏感性。从这里辐射出去,可以思考更多的问题。不仅看表面现象,你还要看它本质的东西,另外还要看它的前瞻性。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自身的问题和民族自身的问题,实际上在世界上经常会碰到,美国也有美国的后院,就是古巴。俄罗斯边境上也有一个老闹事的地方,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国能不能给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版本,实际上是很重要的。而这个世界又非常复杂,许多势力在针对我们中国,因为你强大。如果你是一个弱者,就没有人会管你。一个人也是这样,你特别有名气的时候,人家就给你找毛病,找个事儿,给你出点什么洋相,都有可能,但如果你是弱者,那谁会关注你呢?
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时代课题,而这个课题,作为文学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它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用的,或者对我来说,它是有用的。你看我今天介绍澳门那些最古朴的东西、地方,依然觉得它还是美的。但如果我是一个本地人,住在那个地方,我可能对它是反感的,但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然后再看澳门这块土地,我发现所有的一切都给我提供了极大的资源。如果说要用书写的话,这种资源是非常丰富鲜活的,它让我直接感受到,让我产生了书写澳门的冲动。
看到葡萄牙殖民者他们留下的那些东西,我就会想这些人当年带着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跑到这个荒山野岭里来,在这个地方能呆得下去,而且把土地一步一步地建造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来,我们自己能做得到吗?未必做得到。所以我们作为文化人,要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我们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只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是真实的,才具有世界意义。我们既要尊重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但更多的要尊重历史事实。另外就是我们要把澳门放在一个大的世界坐标上看,大的人类的概念上看。每到一地,我都会不停地思考与国家、民族发展相关的问题。因此选题就会从我的大脑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一个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必备的素质。
三、捡到篮子里的不全是“菜”
王冰云:有人说,报告文学是用“脚”跑出来的,也就是说,确定了描写对象,如何获取故事的细节和感人的情节素材,就显得非常重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要求,决定了您必须贴着写作对象,真实地呈现它本来的面貌。您的写作效率非常高,其中包括了快速获取故事素材的能力,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秘笈么?
何建明:报告文学写作中,写作时间与采访时间应该各自占多少比例,并无一定之规。可能因人而异,因题材而异。总的来说,要学会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去获取更多的素材。采访效率高与低,与报告文学作家获取素材的能力密切相关,而且这种能力不是天生具备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感悟、摸索。同样一次采访,有人去采访了半天,或许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就白走了一趟。或者觉得太平淡了,没有什么价值。我采访非常重视的是:第一,我必须想办法与被写作者面对面交流,获得直接的感受。采访前就知道这个人非常了不起,手中也有一大堆书面材料,或他人间接的介绍,但我仍然必须要跟他见面,因为见面了,即使对方提供的材料与已经掌握的材料重复,但肯定感觉不一样了,会有很多新的发现。被采访者本人,在我的不断追问下,也会给我讲出新的东西来。经过我的挖掘、诱导,就会涌现特别出彩的故事细节。别人没发现的事情,我发现了。
另外,我为什么一定要到现场?我要直接用双眼观察。因为在现场,不仅有了直接感受,而且我会产生很多联想,这就是作家的一个本事。比如说在创作《爆炸现场》的时候,当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爆炸早已经发生过了,但我必须还要赶到现场,我要去感受一下,那个烧焦的味道是怎么样的。然后咱们也没看到死人,但是我必须要感受到在那一刻,那么多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因为我当时看不到,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已经打扫完的废墟当中,还有很多那些死去的消防队员的帽子、手套、衣服等等,还有零零散散的一些东西在那个现场,这些遗留物让我联想到第一现场会是什么样,有了这个直接的观察与感受,再来梳理已经掌握的资料,资料就开始有鲜活的现场感,让你觉得如同身临其境。资料就与现场对应了,这种亲身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必须要到现场去,到了现场你就会产生新的东西。比如你想了解何建明,你只有跟我接触了,你才能真正知道我这个人的优缺点,才可能最准确地进行把握。其实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做出对一个人的基本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善良的还是丑恶的,他是那种有激情的,还是那种文静的,只有直接接触了才能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这次我来澳门,特地去了黑沙湾。我对黑沙滩充满了好奇心,就想到现场了解那里的沙到底为什么是黑的?我还想它黑沙里边含铁量是不是特别高?有可能很早的时候,那个地方海底里原来是一个火山,才有可能产生一种不同的物质。我会思考这些问题。如果从生态角度思考,那个地方可能是风水不太好的,老百姓可能会离得远远的。到了现场,我看到了出乎意料的黑沙湾。这里经过建设,风景优美,人气很旺,还有很多别墅。不到现场,就没有这种观感。所以,一切外在的环境,只有通过人的心灵的过滤、感官的触碰、目光的扫描,才能产生文学书写所需要的毛茸茸的质感。为什么有的人写得好,有的人写得不好,这种感觉是特别重要的。我为什么要到现场,我发现我的感觉是特别独特的,这就是一个经验。再有一个就是要看写作者对生活中的事物,有无特别细腻的感知天赋。有的人可能书读了很多,但他就做不到,他缺少这种瞬间激发的那种化学反应,我是可以这样的,这就是我能够走上这条道路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有的人他没有,单靠硬功夫不行,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有这个本事。同样去采访,我肯定用很短的时间,收获最多的材料。对于我来说,迅速地抓住那几个点是很重要的。
四、处理好“硬”和“软”的关系
王冰云:您在讲好这些中国故事的时候,是如何寻找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的呢?由于您选择的题材大多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工程,或者是与主流时代氛围相契合的人物,掌控、驾驭这样的描述对象困难很大。在很多作者的笔下,这类题材写出来往往会如同工作经验总结材料那般枯燥乏味。您是如何将看起来“硬棒棒”的书写对象“软化”,让人读起来生动形象可感,富有感染力和征服力的呢?
何建明:你提出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读者并不因为你写的题材的重要,就特别高看一眼。你给读者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文本至关重要。我觉得,让宏大叙事式的中国故事成为接受度很强的真实性和文学性高度融合的作品,对于我来说,首先要燃烧自己,然后用生命的激情,让那些原本冷冰冰的素材飞翔起来,充满生命的温度。当你完成一部作品以后,你的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是对应的,甚至还超出了你的想象,那种激奋也是特别强大的。人都有一种虚荣心,但当我们自己的劳动或者创造的东西获得了社会肯定,或者多数人的肯定,这种动力也是非常强大的。这种强大就不断地把你推到一定的高峰和高度,所以你就会觉得活得既充实又有成就感!还要继续往前走,咱不是说干完了就不干了,每一次创作一部作品,都是带有点试验性的探索性的或者说重新开创性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想写好,每一次都是一种挑战,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你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本出来,不管是开头还是标题,如果你负责任的话,都是要下功夫的,而下功夫的时候都是要动脑筋,动脑筋的时候必须十分专注。刚才那个刘会长(澳门新媒体会长)问我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说我固定下来以后,每天我都会给自己一个规定,必须完成多少字。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会完不成,如果拖拖拉拉的,那就会拖完了。我就是这么一次一次的一年又一年的这么重复着在做,我才走到今天这个份上,所以这是一个强迫性的东西。而且写作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痛苦并不是工作累,而是有的那个地方卡住了,或者是材料不行,大部分都是没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一些材料。凡是得到好的材料,我书写的时候都是非常开心的。今天如果写七千字或八千字,心里特高兴,明天稍微轻松点,继续奋斗,我一直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激情和活力,驱使着我一直往前走,而且脑子越活跃创造性就越强,就像你越是跟我对话,我可能越来劲,脑子全部开动了,那种创造性的东西就“嚓嚓嚓嚓”迸发出来了。有时我的助手就跟我说,今天你又比上一次好,今天最出彩。其实弄完了以后,我实际上很累,因为我处于开足脑筋、精神和思维都达到极端的状态。有时一部作品写完以后,就特得意地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如何表达,发现当自己精神燃烧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或者说把自己的心力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传递出来的感觉也是最好的。自己认为最好的,给人家看也是最好的。处于激情和动力巅峰状态创造出来的文本,才有可能感染更多的人。
激情是让题材“软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将激情喷射出来,需要整合素材的强大的思想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有人经常问我是如何构思和组织材料的?比如说我跟你同样出去一次,我装了一麻袋回来,你可能什么都有没找到,这很正常。这里有一个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提炼能力的问题,这种能力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实践与修炼。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吧,或者男人与女人之间,有时可能之前接触不多,但见面之后却可以很快成为朋友,这就源于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非常重要,同时,这种感悟和感觉也具有先天性。
创作《大桥》的时候,我看到这大桥就是林鸣(《大桥》里面的工程师),而林鸣是代表着中国工人、中国工程师、中国科学家和当代中国人的形象。我把这些东西赋予到他一个人身上,然后再寻找有关他的材料。果然如此,超出我的预料,他的个人的经历,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那是我最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书写起来很舒服,也可以完全进入我想达到的那种境界,甚至于超出我的境界。所以你看我在《大桥》的最后的描述,多么富有诗意富有人情味呀!他们夫妻俩看到这段文字都感到特别高兴。尽管他的爱人出场很少,但是这个戏,画龙点睛点到了极致。这样的结尾,既具有人情味,又不是胡吹乱侃,是很真挚的一个情景,谁看了谁都会感动。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文字洋溢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七情六欲,你对书写的人物就必须具有同样的情感温度。你别看黄大发(《山神》里的主人公)没有什么文化,但我们之间的交流,眼神的交流就达到了一种默契,默契了以后他才握着我的手。我也算是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了,他是一个普通农民,为什么握着手,我们有某种天然的默契和感觉,这就是情感,这就是作为人的情感。我跟吴仁宝(《精彩吴仁宝》里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握手就知道我应该从何处切入去写他。这就需要特殊的感知能力,这一点很多写作者做不到,这种特殊的人与人的感觉,不是想学就学到的。
在我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人都是让我十分感动的。黄大发是这样的,林鸣也是这样。你不知道,第一次见到林鸣,我都没心思去写他,奇怪他年龄没有我大,看起来怎么比我还老。但交谈后就觉得他了不得。比我还小一岁,居然成为创造了多种世界性记录的这座大桥灵魂性人物,这么了不起的人,我不写他写谁呀?让我感觉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他写出来。黄大发这个破老头小小老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着村民,为了吃上一顿白米饭,花了那么多代价,这些都是让我感觉到这就是金子,就是黄金,我必须把它挖出来,传达出来。
我的写作与我的性格一样,似乎从青春年少至今,从未衰老过,曾经有人评论说我是“永远青春”,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这个人的基本人生观与事业观,同时也是说明了我的创造格调。其实,作为一名作家,没有激情几乎是不可能成就什么的。写好一部作品,最起码的首先是要感动自己,不管是喜还是悲,不管是歌颂还是批判,对作家而言,都需要动情,动情才会使文字有温度和热情。
五、“宏大叙事”与“时代意识”
王冰云:我印象中您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必须要具备政治家的高度,二是要有社会学家的知识,三是必须有思想家的认识,四是必须具备普通人的情怀,最后他才应该是一名作家,有文学修养,不断进取,善于研究文体。在您看来,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讲好中国故事,对优秀报告文学作家有什么特殊要求么?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何建明:我认为通过宏大叙事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对于一个优秀的书写者来说,特别是一个纪实报告文学作家、非虚构作家,第一个就是他应该具有政治家的素质。所谓的政治家素质,我主要指的是作家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时代意识,擅长把握全局。举例来说,这次来澳门,对于澳门实践“一国两制”这样一个重大题材,该如何把握书写呢?很多人可能围绕澳门回归20周年写写就可以了,这是简单的呈现历史,但我会从更高的时代角度、更广的地域范畴,来观照和思考这段历史。我会思考,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给我们、给世界提供了什么启迪和经验。现在因为香港的问题,造成了很多人对“一国两制”的质疑。通过澳门这件事情,我们把它做好,说明“一国两制”共存是可行的,不是没用的,它具有世界意义,未来怎么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模式,我也会思考。然后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组成了香港澳门的发展史,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实际上我们写好了,对葡萄牙也是有意义的,你看我们原来占领的这个地方,交还给中国人后,他们管理建设得比我们还要好,他们心里也会感觉到自豪。我们通过自己的笔来书写我们的历史,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但我们也不否认葡萄牙人曾经做出的历史贡献,这就融通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这就是我要写的。如果我写的话,我要看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跟整个时代合拍,第二个层面是全社会的,第三个层面是未来和世界的。通过宏大叙事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具有这样的高度,这是一般作家很难做到的。
第二个是要当社会学家。你看澳门是一个海岛,是一个殖民地海岛,我们自己都没这个经历,通过这个写作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岛。你看今天咱们走了三个岛,这岛与岛之间的认识让我们得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包括黑沙滩等等。还有,你会发现通过这一次我又获得了关于海洋知识、岛屿知识等等,这是要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我走了这么多年,每到一个地方,如果写散文的话,我也可以写得很美。这种观察社会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有了丰富的社会知识,作家对书写题材的把握就会更加客观、可信,信息量就会更大。
第三个是思想家的认识。我们思考的这些问题,像“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这看起来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它是人类共有的。我刚才讲的任何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跟澳门“一国两制”共存这件事写好了,它可能对其它国家也很有借鉴价值,比如说南苏丹与北苏丹,比如说越南,无论是哪儿的,都是有民族自身的问题,我们把它写好了就是一种版本,人类文明的版本。这样,思想的高度、深度也就出来了。
第四个我认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怀。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们一个文学作品更根本的就讲人的情感和人的行为。你把人做好了,你的文章也就做好了。做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做人的范围有很多,情感道德什么的等等。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人的缺点我也有。但是在某一刻某一件事上,我的情感投入是最深的。比如写浦东史诗,那个时候我对上海的感情和浦东的这种发展史实,我是最有感情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我。
如果写澳门,我也是这样,尽管我不是澳门人,但是我用的情感用的思想用的才情,我会尽我所能,我才可能把它写好。写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比如说黄大发,我也得站在黄大发的立场上,我去用尽我的所能。黄大发自己都讲不出来,我把它讲出来,包括他对着你,他对着乡亲们,他对着自我,这种感情是我要投入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黄大发,这就是普通人的情怀。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这种普通人的情怀,你见了一个老太太见了一个高官,对不同身份职业的人,都要给予足够的尊重,都应该不卑不亢。见了高官,我们有面对高官的方式,见了普通老百姓我们有普通老百姓的方式。但我自己本人始终保持着普通人的情怀,这特别重要。不是假心假意的,而确实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真诚,好与坏,你自己判断。我自己也有好与坏,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人要真诚,要表露出自己的本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我现在呈现的创作风格,当然不是为了创作风格,是说这一点作为人的本色非常重要。你有一天当了一点官,有了一点名气,把自己架在中间,那不行,我也受不了,或者说我认为真正一个大作家,他不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拥有普通人的情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个就是一个作家的本事。作家的本事是我们的专业的本事,专业本事非常重要,但没有前面这几个基础,专业本事也就做不大。简单来说,这是我实实在在总结出来的,没有教科书给我讲,光这一个就可以做成一个大的论文,但没有人帮我去做,所以觉得很着急,实际上这是经典的经验写作。你在上海大学访学是不会学到这些东西的,因为有些老师没有这样的体会,只有我才感受得到。
为什么我说必须具有政治家的这种素质呢?那是因为写报告文学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站在一般作家的角度,可能很难抵达书写对象可以达到的应有的深度和高度。你有可能只是站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局部在思考一些问题。当我们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就会从宏观去思考题材给我们提供的各种书写的可能性。思想家不用说了,有了思想家的那种穿透力,那是更加了不得的,想得很远很深刻。社会学家那种丰富的知识,可以丰富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能力,你明白吗?所以他们是互补的。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是一个作家,就要努力把它写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王冰云:聆听了您的这些非常具有“实战”价值的书写经验,收获良多,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访谈!真诚期待未来您能创作出更多更加精彩的文学作品。
何建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