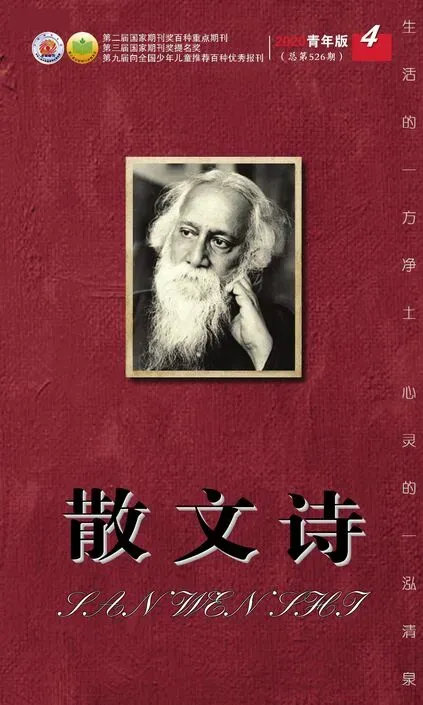湖水收藏一天的故事
张梦真
蔷薇穿过身体
夜幕垂下帘栊,万物合拢双手。虔诚如夜,吞没一座坚硬的城,吐出一半炽热的火。在一只飞虫的指引下,顺势划向季节边缘,飞蛾扑向火,蔷薇扑向一个蓬勃而略带灼热的时令。五月泥沙俱下,夹杂着时光流动的颗粒感,磨砺身体某处旧疾,隐隐作痛。
黑暗,让微小的光不断放大,也让瞳孔不断放大。无数星辰,在蔷薇浓密的叶子间,和粉色花苞里,飞进飞出。立夏的枝头,草木葱茏,一个念头在雨水中应声开放,缓缓而行,然后戛然而止。
静止唤醒一部分疼痛,年久失修的病灶,不断挤压着生命潜伏的隐喻。黑暗借着夜无限生长,蔷薇,粉色的香,穿过身体里的稀薄,迸射着星星般明亮的眸子。
无名之辈
告别刀枪剑戟的东风恶,收起为一朵花提心吊胆的害怕,连同那些尚未表达的悲喜,刀枪入库,封存。五月,众多无名小花,夹杂于芸芸众生之间,零星,散落,原野式地开放。相比于以佛的视角照看众生,我更愿意化身为眼前的事物,比如阳光、雨水、栅栏,以一己之力去温暖一朵花,或者干脆做一朵花的容器,取出身体里小而精致的部分,重新放入一朵花苞,借助一朵花,开出一个又一个崭新的自己。
清 明
四月眉头紧锁,午后阳光一如往常,被黄土尘封已久的称谓,拂过树梢,拂过原野,拂过高高的坟茔。一只鸟,轻轻飞起,盘旋片刻,又轻轻坠落。如同记忆中的自己,结束一次飞行,收拢羽翼,准时抵达。此刻,生与死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日渐消瘦的骨头,等待一次雨水的洗礼。
泥土依旧沉睡不醒,空留一朵白色小花,向人间传递,起死回生的念头。一只蚂蚁缓缓经过,精心梳理着,草木葱茏,试图驮住一个春天。无休无止的风,紧紧包裹着知名或不知名的草木,偶尔掠过一两声鸟鸣,试图接住一些信息。有些茅草开始变得坚硬,轻而易举引燃一簇明火。我小心翼翼,摘下一个春天,又小心翼翼,捧回一个自己。
一只潜伏深夜的蝉
在一片杨树林中寻找一只蝉,于黑暗中,寻找明亮的切入口。于在场的仪式中,寻找缺席的部分。夏夜,带着泥土的黑暗,偷偷爬过人间,剥开一棵树的伤口,干瘪的蜗牛,新鲜的蝉蜕,深深嵌入年轮,潜伏着永恒的微光。
黑暗是一场预谋,再次尝试展翅,欲飞是危险的行动,向上的危险。遥想那些年,没能遏制住一只蝉蠢蠢欲动的心,如同未能及时悬崖勒马,大声喊住一个误入歧途之人。
一粒蝉鸣,是一个古老的象征,葬身于漫无边际的丛林,跟随石头坠入谷底,难起回声。把天空归还给天空,把泥土归还给泥土,把自己归还给一只鸟或者飞蛾的前世,空荡荡的夜,只为再次确认,树叶是绿的,白色是纯的,飞翔是透明的。
湖水收藏一天的故事
湖堤没入湖水,连同一天中尚未发生的部分,一同沉入湖底。恰巧,一阵鸟鸣经过,把可能发生的部分,顺势带入山林。这时,指针扣动夕阳,向晚的时辰,横亘于指缝与指缝之间。水落石出,初夏,悄然莅临枝头。一段故事讲完,一行人远去,几朵清荷含苞待放,追随远去的踪迹,微微晃动,留下一池湖水,动荡不安。鸟鸣隐入山林,一些低矮的灌木,在风中穿行,斜阳被一尊石头遮住,又被湖水完全裹住。湖水,平如明镜,清可见底,收藏亭亭玉立的身躯,也收藏一整天的故事。
雪是一场宏大叙事
雪来了,冬天开始有了诉说的欲望。雪越来越近,脚步越来越轻,大地仿佛被月光圈养,越来越安详。雪有妙笔,落地生花,一片接着一片,纷纷的意象,目不暇接。雪渐渐落下来,大地渐渐升起来。水落石出,雪落松出,都是人世间的真相。
青松高得突兀,落光叶子的银杏树,重新焕发生机。旧年的光景,被重新梳理、擦拭,愈发明亮起来。观雪之人,在身后,看一片小小的雪花,旋转着玲珑身姿,飘落于窗前。转瞬间,一片雪覆盖另一片雪,白雪把白雪覆盖,大地与大地重叠。
下雪天,适合一个人,静静看一粒雪,如何从微观世界,走入无我之镜,写就一篇宏大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