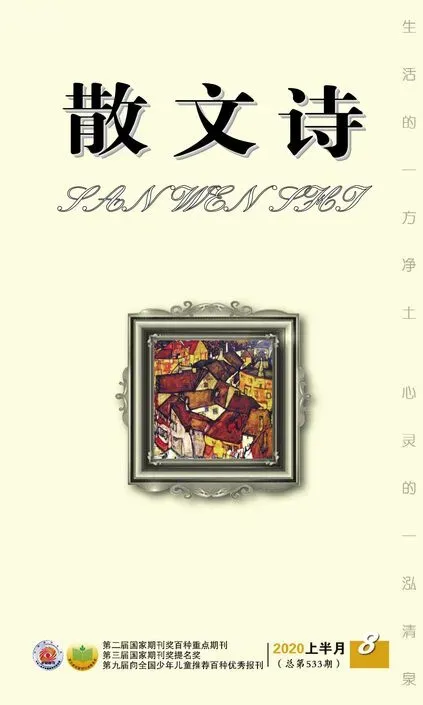风把我慢慢吹软
◎刘怀彧
阴影里
此刻有大面积阴影。绵延的屋檐,高大的树木,婆娑的藤蔓,家禽和畜类,都有鲜活的阴影。芭蕉叶的阴影,房子那么大,墨汁一样浓。鸟雀飞出好远,阴影还在轻盈地跃动。
凡有阴影的物事,都有超负荷的阳光,灵动而深刻。此刻坐在池塘边,黄色的蝴蝶,捉住黄色的菊花。而我仿佛就是,另一个人的阴影。
内心的安宁,海一样,泛着蓝光。
有客来
无须电话约,估摸着就来了。主人不在,打个回车就是。反正时间够用。无需按门铃,狗一叫就起身。哪怕只是过路人,迎上去,就成了座上宾。无非茶时节喝茶,饭时节吃饭。
一张桌子,添套碗筷。五人可坐,十人也可坐。
来的都是客。一早来了四只鹅,接着三条狗。然后是一大群鸭子,嘎嘎嘎,满院子招呼不赢。而满园桂花,有最广大的朋友圈。蜂来蝶往,如芳香的集市。
夜深人静,听得狗叫。披衣开门,四周虚静。只听得母亲在房里念叨:老头子,你要回来,还是先托个梦吧。免得惊吓了,你家孙子。
老样子
一件带条纹的旧衬衣,丢在老家,多年忘了穿。
乡下住着,忽然就凉快了。旧衬衣,太花。穿上去,有点扭捏。像儿时新衣加身时的那种拘谨。母亲却很是惊喜:“咦?还是老样子嘛。”老样子,是原来的样子,还是老了的样子呢?
不管怎样,我终归还得像脱下旧衬衣一样,脱下故乡,回到让人接受的,该有的样子。
老黄鸡
儿女回乡,母亲高兴地指给我们看她养的鸡。
我家的鸡,个个都肥。五只黑的,三只白的。只有一只黄得油亮,像个皇帝。领着一群爱妃,四处啄虫啄粒。
日之夕矣,撒把碎米。黑的白的,纷纷围拢。那只黄鸡远远张望,很生分地,在家门前走走,踱进了邻居的窝。
母亲笑着说,这老家伙,我就多看了它一眼。
风细软
风吹午后竹林。一会给她梳头,一会胳肢她修长的细腰。蝉噪掩口,守着机密。
风吹门前池塘,水面百般模样。挺着胸脯,向上。
风吹野外稻田,禾穗千里急电,一浪一浪,翻转。
风吹万物像耳语,白鹅外泄了春光,蜻蜓立不住舞步。
而我一人独立,也慢慢地被风,吹软,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