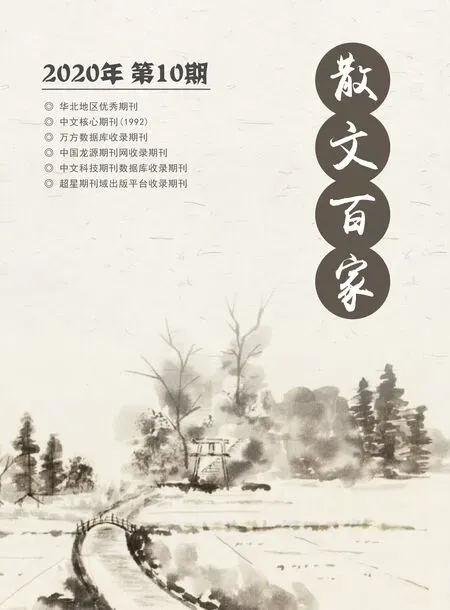鲁迅作品中的特殊语法现象研究
——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作品为例
王美桐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又辛在《六十年来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发展》中指出“六十年来围绕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发展方向问题,曾经发生过三次斗争。第一次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斗争;第二次是提倡大众语,反对文艺八股的斗争;第三次是反对党八股的斗争”。[1]现代汉语在形成初期发展到现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鲁迅作为现代白话文初兴时期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为我们了解现代汉语形成初期的语言面貌以及语言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语法具有稳固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缓慢的变化当中。我们在阅读鲁迅作品时,会发现有许多与现在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书面语不同的特殊语法现象,这些特殊语法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过渡状态。
一、助词“得”的特殊用法
我们阅读鲁迅著作,往往感到某些虚词的用法有些“特别”,其中有的就是受了古白话的影响。例如助词“得”。
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藤野先生》)
例句中的“得”与现代汉语中的“得”用法不同。现代汉语中,“得”多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连接程度补语或结果补语,如“长得漂亮”、“解决得好”,用作结构助词。例句中的“得”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后面多跟表示处所的成分,多由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
“动+得+名”这种用法常见于古白话中,鲁迅作品中的这种用法可以看作是由此承袭而来。如:
1.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旁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得过来,靠了门。(《水浒传》)
2.三人入得门来,悄无人声。(《警世通言》第三十卷)
3.两公子过得桥来,看见杨家两扇板门关着。(《儒林外史》第九回)
二、“将”的特殊用法
“将”在现代汉语中用作副词,例如“我将离开这里”,有时用作介词,相当于“把”,例如“将革命进行到底”。鲁迅作品中的“将”有时用在动词后面,作助词,表示动作、行为的开始,后面跟趋向动词。例如:
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阿长与山海经》)
“动+将+补”结构基本不出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书面语中。但是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出现的频率很高,鲁迅作品中的这种用法可以看作是由此承袭而来。例如:
1.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扒将起来。(《水浒传》)
2.把破设设地偏衫揭将起,手提着戒刀三尺。(《西厢记诸宫调》卷二)
3.您两个恰便似一个印盒脱将下来。(《谢天香》)
4.韩翃拾了金钱,又听见了她的话,便不顾生死,不问哪里,拼命赶将去。(《金钱记》)
三、特殊的第三人称代词“伊”
古代“伊”作代词有多种用法:可以表示远指,相当于“那”,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可以表示第三人称,相当于“他”、“她”,如“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可以表示第二人称,相当于“你”,如“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到了宋代,“他”在口语里应用的更加普遍,“伊”的使用已经不多见了。现代白话文初兴时,“伊”曾被作为第三人称女性代词使用,今已罕见。鲁迅作品中常用“伊”来指代女性。
1.母亲便宽慰伊,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社戏》)
2.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社戏》)
3.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故乡》)
4.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故乡》)
四、特殊的倒装句
倒装句又叫“易位句”,是相对于常式句的一种变式句。有的倒装句是应语法结构的要求而倒装,有的是为了达到某种修辞效果或是受作者的个人风格影响而倒装。黄琼英在《鲁迅作品语言历时研究》中将这两种倒装分别称为“强制性倒装句”和“非强制性倒装句”。她在讲到鲁迅作品中的倒装句中提到“鲁迅作品中的倒装句除了一些‘强制性倒装句’外,还有着大量的非强制性倒装句”。[2]这种“非强制性倒装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现代汉语还处于形成阶段,语法位置还没有固定造成的。语言是用于交际的,句式的选择和运用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要受制于语用条件。一般来说,变式句更多受到语用的影响。鲁迅作品中的那些“非强制性倒装句”则语用理据性较弱,很多都是一些非常规的用法,是创作过程中无意识而为之,正因如此,鲁迅的作品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
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祝福》)
例句中倒装句补语“不过”和宾语“他”位置与现代汉语的规范用法不同,相同的语义,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应表述为“拗不过他”。“动+宾+补”这种格式在近代汉语中较为常见,例如:
1.我自小靠爹娘过活,没处赚得一文半文,家中来路又少,也怪爹娘不得。(《醒世恒言》卷五》)
2.张胜提刀,绕屋里床背后,寻春梅不见,大拔步径望后厅走。(《真本金瓶梅》第99 回)
3.你若果然做出这事来,莫说他财大势大,我敌他不过,就是敌得他过,他终没有偿命的理!(《醒世姻缘传》第9 回)
4.这课象似你在那女人身上要做一件瞒心昧己的勾当,必定瞒他不过,还要吃场好亏。(《醒世姻缘传》第65 回)
5.小孙一人敌他三个不过。(《西游记》第89 回)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语法现象大多是对旧有的语法规则的承袭。提倡白话文必然存在白话文怎样写的问题。我们现在写文章已经有了明确的规范,而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创作是没有成系统的规范的。因此如何创作白话文学作品是该时期作家所面临的问题。钱玄同在1918 年曾提出过一套办法,即“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由此可见,创作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文言、古白话色彩。可以说,鲁迅的语言是雅俗兼具的语言,是现代汉语形成期的典型作品,为规范的现代汉语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语法具有稳固性。但是,通过对这几篇作品中的语法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法虽然稳固,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缓慢的变化当中。
五、结语
本篇论文从语法层面,分析了助词“得”的特殊用法、“将”的特殊用法、特殊的第三人称代词“伊”、特殊的倒装句这几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前两种语法现象是对旧有的语法规则的承袭,第三人称代词“伊”是现代白话文初兴时期常见的用法,体现了过渡时期的语言特点。鲁迅作品中还存在一些“非强制性倒装句”,受到的语用制约较小,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非规范性的用法,也体现了鲁迅独特的语言风格。
从以上几方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鲁迅作品有着不同于文言文也不同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独特之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必要指出这些特殊现象并作必要的说明,不但不会影响鲁迅先生的伟大,而且还可以使学生更明确地了解这些语言现象的演变情况及现在的规范化要求,这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教学或许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