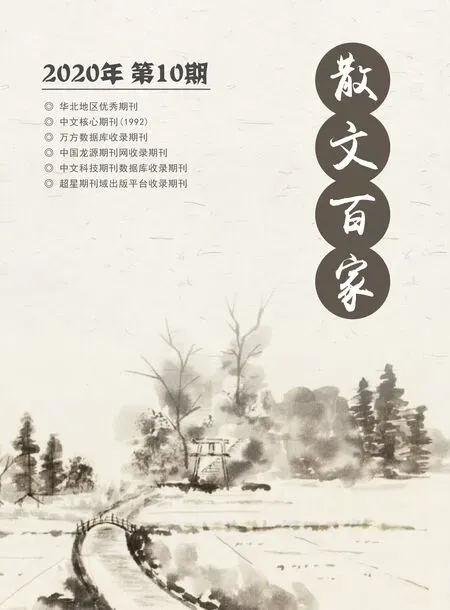望 乡
刘宏韬
广西罗城公路养护中心
被囚禁的河流
几年前开始对故乡那条河的河岸进行改造,花了两三年的时间,用两道几公里长的坚固堤岸把河水围了起来。在河堤上面建成了人行小道。每到傍晚,居民们就成群结队地到那里去散步。
有人说修建河堤那是为了保护河流和土地,防止洪水来临时造成水土流失。但是这条河千万年来一直这样流淌,期间也经历过无数次洪水的冲刷,原先沙土的两岸,为什么就能够坚持下来?而我们人类才生活了多少年,反而就产生了危害呢?
建国后为了水利而在这条河上兴建起来的拦河水坝,只不过是利用河水自己的力量把它们送到田野当中。如今在水坝的下方又建起一座水电站,老水坝被淹没了,河水也被“电”控制了。枯水季节,电站的大坝会把河水拦住,拦得高高地再把它们放下来。因为,只有高水位才能带动电机,电机发动了才能产生电,电生出了钱。经济效益比河水重要得多。
我记得,在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经常在河里撒欢,我就没有看到过河水枯竭的样子。当时河里的水草丰富,鱼儿满江,从没听说过河水伤害了两岸的泥土。现如今,每到了枯水季节,它甚至可以露出水底的鹅卵石,就像是老母亲那被吸吮得干瘪的乳房一样,沧桑而惊心。只是没有人为她的苦难哀伤,也没有人想念她曾经风姿绰约的年华。
人是聪明的,发明了农药,发明了炸药,发明了电……鱼儿被毒死了,被炸死了,被电死了,被吃到人的肚子里去了。我曾经想过,是什么让人类比其他生灵更聪明的?只不过这种聪明,也让人们生成了残忍这种思想,而且根深蒂固。我们往往会代替大自然去想去做,根本没有想到那是不是它们想要的、需要的。
人类用钢筋水泥去爱护河流,但是他们不知道河流是需要自由的。河水没有了自由,那些靠它养育的鱼虾龟鳖也就失去了自由,甚至因此而绝了种。
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囚禁”!
河流被我们囚禁起来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也是被囚禁的人。
母亲的菜地
也就是在前几年,因为单位要建集资房,于是父母原先住的老屋被推倒了,院子里全部被硬化了。就这样,母亲多年以来坚持种菜的习惯被终止了,因为水泥地代替了黄土地。
自打小学记事开始,母亲就有两块菜地。一块在我们的老屋后面,一块在单位大院的围墙外面。母亲在菜地里种着应季的蔬菜,有茄子、西红柿、辣椒、白菜等等。在八十年代里,我家的青菜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我小学的时候,经常在晚饭后陪着母亲去菜地给青菜浇水施肥。夏季的温度比较高,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浇水容易伤着叶子;秋冬季的时候就要改在中午时间浇水,这样就不会冻伤菜根。
两块菜地都不大,只是浇水施肥的话,十来分钟也就完成了。我曾经问过母亲,老屋后面的那块菜地有多大。母亲告诉我有一分多。我问母亲一分地有多大,母亲也说不上来。于是,母子间的问答也就戛然为止了。
围墙外面那块菜地是长方形的,就在单位的肥料仓库之外,需要从单位的后门出去,再绕上一个弯经过一片田地后才能到达。母亲在那里种植红薯和南瓜为主,因为那块地距离家里稍微远了一点,打理起来有些不便,于是只能种植那些长远的东西。
在外面的那块菜地边上有一丛洋芋,我跟姐姐去那里摘瓜割红薯藤的时候,她会把洋芋的花蕊抽出来。把它们放到嘴里用力地吸吮,就会有一股甜蜜的汁水流入嘴里。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零食少得可怜,就靠品尝大自然的恩赐来解解馋。
关于围墙外的那块菜地,我还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那是在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夏天,我照旧是在放学后陪着母亲去浇水,母亲为此奖励我五分钱买一根雪条。我向母亲撒娇,希望能够多拿到五分钱,以便可以将雪条的规格提升到有奶味的雪糕。没想到母亲以一种坚决的态度拒绝了我,让我的心情顿时坠入冰窟,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母爱,一瞬间就决定要离家出走。
那是个与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的仲夏夜,一个少年在镇上转了几圈之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怎样也走不出黑暗。于是,故事就以我被父亲找到之后带回家给母亲痛殴了一顿结束。这样的情节在二十多年后被我写成了人生的第一篇小说,还换得了几百块的稿费,让当年的五分钱升值近万倍。
再后来由于改革开放浪潮带来的冲击,父母的单位业务萧条了,成了近乎破产的状态。单位只能通过出卖土地来偿还一些债务,母亲的菜地也被压缩了,最终只能在老屋门前重新整理出一小块。这块菜地,从九十年代一直延续到2010 年。在最后的菜地上,母亲种植的菜品比以前的要多得多。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地边的一兜佛手瓜,密密麻麻挂满了架子。在我的印象里,每次回家都能见到上面挂着嫩绿嫩绿的瓜,摘下来炒了,清甜爽口。那个时候,走出家门几步就有辣椒西红柿,葱花老蒜,方便得很。
现如今,父母住上了钢筋水泥的楼房,楼下就是市场大街。没有了菜地,他们依然是出门几步就能买到青菜。堆在高摊上的青菜,绝大部分都不是在小镇的土地生长起来的。它们都是远道而来,镇上的人甚至无从得知它们的来处。
它们从远方来到小镇上,而我又是从小镇走向远方。我怀念我踏足过的那些菜地,就如同我怀念我走过的生命一样。它们都已经不可重来了。
当年我为了五分钱就想逃离这个小镇,犹豫着走了一个晚上也走不出去。如今我拼命地想要回去的时候,却再也进不去了。
消失的树
那天晚上,我钻进了蚊帐,打开小台灯看着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没想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虫落到书页上,我猛地把书合上,将它的生命凝固在书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杀生,但它却的确是走错了路。
我想起故乡小学后面路边的一棵柿子树来。
很多年前,我还上小学的时候,它就已经老态龙钟了,但是每到成熟季节的时候,它上面都会挂满了红柿子。它不是黄澄澄的硬柿子,而是那种软柿。大孩子们可以麻溜地爬上去摇一摇树枝,或者是用石头把柿子砸落下来。我没有这些本事,以至于每次都是流着口水看别人吃。
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又到南京读大学。虽然每个假期都回家乡,但是却一直没有再留意柿子树的样子。某一次我突然记起它来,再用目光去寻找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它的踪影。
它是什么时候被砍掉的?我问了几个人,都说不清。
小学里原来有三棵巨大的参天古树,现在也只剩下一棵了,剩下的这棵畏畏缩缩地窝在校园的一个角上,或许正是因为它的“懂事”,才避免了被毁灭的命运。
消失的仅仅是这些树吗?不!还有我家的菜地,还有田间地头的潺潺溪水,更甚的是还有那些年轻人……这些消失的东西还不是最紧要的,最令人绝望的应该是思想。
走错路,站错地方,都是会送命的。所以,留下来的,都是屈服。
蒙蒙躲
很多孩子都玩过一种游戏,叫捉迷藏,叫躲猫猫,叫摸瞎子。这种游戏很简单,就是其他人藏,一个人找。
在我的故乡,这种游戏叫做蒙蒙躲。
我年幼的时候,跟着哥哥姐姐们做过这个游戏。当时我父母是有单位的,住在一排泥瓦房里。三兄妹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我们在晚上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也还有街坊的哥哥姐姐一起来。捉的人到门外去等着,藏的人就藏在那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
房间里面对面摆放着两张木床,上面挂着蚊帐。躲的人要么躲到门背后,要么躲到床底下,还有的就是躲到蚊帐后。我每次都躲到蚊帐后,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当时骄傲地想着自己躲藏得太好了!后来长大了,再回头想一想,无非就是哥哥姐姐们让着我罢了,难道他们进门后会看不到蚊帐后那个笑嘻嘻的小男孩?
这些年来,故乡的山渐渐地被挖掘机挖出一条条的小路,蜿蜒在各种种植基地之间,那些白花花的沙石实在是碍眼。我记起在电视剧里,那些威武不屈的革命先烈被绑在刑架上受刑的时候,身上会被折磨出一道道血痕。
我想,故乡的山也如同那些先烈一样。
那些山和革命先烈一样咬着牙,一声不吭。他们都有相同的性质,都是为了人的幸福。
我们看不出来吗?
只不过我们道理堂皇,然后心安理得。
后来我知道,玩蒙蒙躲是有很多方式的,甚至是可以成为故事的。
成人的游戏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有人也希望这样,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那样。
夜来香和玉兰花
我一直分不清夜来香和玉兰花的区别,只知道它们都能散发出让人沉醉的香味。
在我现在住的大院里就有两棵树,它们的花和叶子都有所不同,但是都香味扑鼻。我有时认为高大的那棵是玉兰花,另一棵是夜来香。有时的想法又恰恰相反,总之我自己也懵里懵懂分不清。
记得我还小的时候,老家的乡政府大院里也有两棵这样香味扑鼻的树。那个时候的我一样也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品种。有人告诉我说晚上开花的是夜来香,白天开花的是玉兰花。我似懂非懂地记住了这个分辨的规则,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晚上去看那些树有没有开花,只是每天距离它们很远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现如今的乡政府大院比以前宽敞明亮,但是那两棵树很多年前就在锯子吱吱呀呀的声音中轰然倒下了。
不单单是树名的问题,就是家乡的人名我也不太记得。那里很多的人我都认识,但是绝大部分都叫不上名字。有时候跟家人或者同乡聊天时说到“某某某”,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表示我也是认识这个人的,然后心里却是忐忑的,生怕人家再问下去。
也不单单是人名的问题,家乡的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比如村庄,比如道路方位。算得近一点,老街里的一切我都很陌生。
故乡在我的心里很亲,但是在我的眼里口中却很远。于是现在我说起故乡,觉得很亲切。但是用心一想,却又觉得太多太多的陌生。我想回去,但是能去哪里?我说不上来,反正它也不主动张开怀抱热烈欢迎我。这是我的错。
我怎样才能扎下根来?这个问题就像院子里的两棵树一样,我害怕得不到答案,也就懒得再费心思去刨根问底了。管它是夜来香还是玉兰花,我每天一醒来就能闻到它们的香味,那就足矣。反正都是鸡蛋,谁又会去纠结是花母鸡下的,还是黑母鸡下的呢?
人啊,别想太多,郑板桥老先生在两百多年前就说了,难得糊涂!
老呇
镇上的小学边上有一泓呇水。
它比地面要低四五米。
它的四周被用青石条砌了起来,高出地面差不多一米。四四方方的呇水躲在里面,就像是坐在天井里一样。
它的历史很悠久,有人说跟小镇的年纪一样。但是小镇的年纪是多少,谁也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哪怕是大概的数字,也没有人说得出来。
我上小学的时候,这口呇水是老街里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人们踏着石阶上上下下,挑着空桶来,担着清水回。就那么二三十级的青石台阶,被鞋底磨得幽幽发亮。
那时候上学放学,老街里的孩子们都要经过它的身边。我家不在老街里面,但还是偶尔要路过那里。当时的围墙,约莫跟我一样高。我从不敢爬上去往下看,因为我担心我掉下去。呇水幽幽的颜色几乎发黑,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这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我曾经认为它是个无底洞,一旦掉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说句实在话,我甚至从未走下那几十级台阶,对它只是远观而不敢近看。
小学毕业后,我跟它的交织就更加少了,它在我的印象中一度迷失得仿佛不存在一样。等到后来我有胆子敢于直视它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影子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也快要老的时候。我第一次沿着青石台阶来到它的面前,它已经如风烛残年的老妪一般,再也看不出曾经的美丽容颜。人啊,年纪越大就越容易怀念从前。
我看到水面上漂浮着垃圾,那里也不再是青幽幽的样子了。当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后,谁还会去记得这样一个需要手提肩挑的老呇?
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这是它的使命,或抑是它的宿命?
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
我只踏进过这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