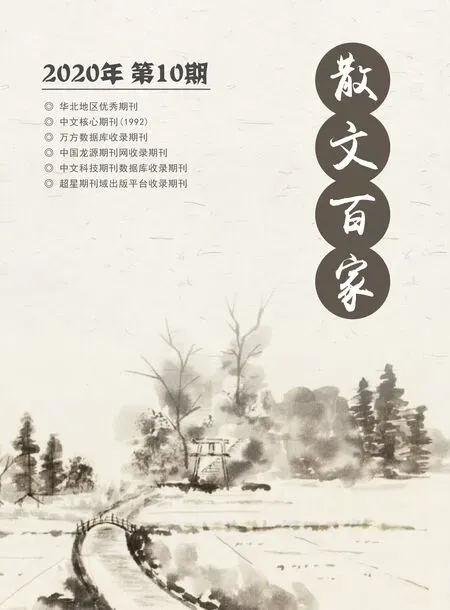外公,你是一条长河
荣 蕾
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外公,你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长河用爱,智慧和善良滋润着耄耋之年却依然内心清澈的外婆,滋润着您那些出走半生,仍是少年的儿女们,也滋润着我们这些二十余岁,初谙世事的孙辈们。
题记
深夜无眠,冬风凛冽,泪眼朦胧中幻化出了一个老人的身影,从五十多岁鬓发乌黑只是眼角有些皱纹的他,到六十余岁鬓染微霜面色依旧红润的他,再到七十余岁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的他。泪水中老人的形象真实又不真实,直到我眼前出现了那个衰老病弱如同秋天一片枯叶的他。是的,这个老人是我的外公。是那个刚刚在今年三月去世的他。他是个平凡善良的老人,他的离去并不会给这个快节奏的城市带来一丝丝波澜。然而对于至亲来说他的离去就如同身体中失去了重要的一部分,疼痛锥心刺骨。
我的外公大我55 岁。我没有亲眼目睹过他青年时期的英俊挺拔,壮年时候的意气风发,亦或是中年时候的功成名就。这些只能从外婆嘴里听到,从前来看望外公的学生嘴里听到。而我亲眼目睹的是外公的老年时代。老年时代的他,只是一个慈祥和善的老人。
一,记忆是一条长河,随着时光不断流淌
回忆起人生的头几年,我还是个三四岁孩子的时候。年纪尚幼的我早已经记不得那些细节,只记得一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子乌黑头发的老人常常把我高高举起,用他长着胡子的脸贴我的小脸。而我每每在幼儿园得到奖励也总是要第一时间分享给他,无论是话梅糖大白兔奶糖还是漂亮的本子。年幼的我还不懂这些东西对于外公这个年纪的人并不需要,然而外公每每拿到都会特别惊喜地亲亲我,说蕾蕾最棒。春天温暖而花香弥漫的夜晚,夏天凉风习习的夜晚,秋天落叶沙沙响的夜晚亦或是冬天阴冷的夜晚,幼小的我常常会依偎在外公怀中,听他抑扬顿挫地读古诗词,那声音仿佛是在讲述一个无比幸福的往事。或者听他声情并茂地讲述历朝历代的故事,而我小小的脑袋里就好像真的出现了刀光剑影,耳畔也好像真的响起了鼓角争鸣。那个时候的外公身体很好,会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而我是他最小的啦啦队员,竭尽全力地叫着喊着仿佛我的外公是我最大的英雄。
小女孩一天天的成长直到读了小学。幼儿时期的积累让我进入小学后就一直成绩优秀。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不能自己上下学,学校离家不远,又不方便坐公交车,是鬓角微霜的外公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走在上学亦或放学的路上。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路边传来湿漉漉的青草香,或是茉莉花氤氲的香味。我每每去寻找那些花朵和小草,却发现一无所获。直到三年级时候我能够自己上下学才发现原来那香味竟然是源于亲人对自己最真挚的爱。不是花香,不是草香却是亲情的香。小时候的我擅长写作,拿到过好几次全国征文一等奖,学习奥数也拿到过海淀区智慧杯数学比赛一等奖,英语也早早以接近满分成绩通过剑桥少儿英语三级。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让家人自豪的孩子。而外公也总是和他的朋友骄傲地提起我。
骄傲聪明的小女孩一点点长大,长成了少女。在海淀激烈的小升初竞争中我胜出考进了清华附中最好的两个实验班。只是在实验班里我的成绩不再优异只是普通一员。我彷徨,我痛苦,我找不到方向,而七十多岁的外公常常会说人只需要和自己比较。而那个无法承受心理落差的少女恰恰是听了这句话才放平了心态,最后被学校保送到了本校高中部。平静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高三,我因为太过紧张焦虑抑郁,整日哭泣。而那个时候是已经头发花白的外公每天中午来到学校陪伴我,陪着我说话解闷儿。那一年倏忽而过,我把高三完整坚持下来。还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沉浸在痛苦中,未能考取名校的失落让我无法面对自己。是外公陪着我一次次地聊天告诉一个个意味深长的人生道理。我渐渐明白了许多,我相信自己的努力终归会在某个时候给予回报。
读大学后我的专业成绩优秀,参加学校翻译比赛演讲比赛商务谈判比赛都有获奖,一不留神还拿了个校级人文知识竞赛冠军。几乎每年我都会拿到奖学金,被评为三好学生。几个月后我成为了班级唯一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而此刻外公面对得意的我却说孩子你需要平静。别人的看不起抑或嫉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并且为之努力。而年少轻狂的我似乎还不理解这句话背后沉甸甸的力量。
读研后的我成为了著名作家梁晓声的学生。而此刻的外公却已经须发皆白了。那时候的我不知天高地厚,自认为自己很优秀。那个时候年少轻狂的我每每与人发生矛盾总是认为问题都在别人而不在我。自己以非英语专业学生身份通过了专业八级,以优秀毕业生身份本科毕业,又以专业第一名身份考入名校研究生。这些成绩足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姑娘。我开始逃课开始沾沾自喜。而此刻,外公告诉了我两个道理:(1)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内省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成熟。(2)客观地讲蕾蕾你的确优秀,但比起卓越人才你还差得很远。尽管不是所有人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都可以变得卓越,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因为仅仅是比平均水平高的能力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而不幸的是那个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并没有听进去这些话,而等到我真的听进去这些话的时候,我亲爱的外公却已经在2015 年,在他78 岁的时候患上了绝症。
二,生命的河水渐渐干涸,爱却奔流不息
还记得那是2015 年的6 月,外公告诉我胸口发疼,喘不上起气来。我心下顿觉不妙,于是便请假带外公去看了医生。做完X 光片后医生悄悄告诉我外公有可能得的是肺癌。在那一刻,我感觉悲伤如同一块千斤重的巨大石头填满了我的整个胸腔.我强忍住泪水走进了医院的女厕所,如同一只将要失去至亲的小狼一样放声大哭了整整五分钟。然后我面对着女厕所的镜子尽自己所能地擦干脸上的斑斑泪痕,勉强挤出一个并不自然的微笑。我带着这个不自然的微笑走出了厕所,看到了外公一个人坐在医院长椅上,表情凝重。我没有多想,对外公说:“姥爷,医生说你肺纹理增厚了,可能有轻微的纤维化。没有啥大事但是我还是不很放心,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可是不知怎么我还是压不住自己的情绪,说话时候忍不住有点想哭。外公对我说:“蕾蕾你怎么不高兴。没事的,外公到这个岁数有那么孝顺的儿子闺女第三代,有那么好的儿媳妇女婿,没啥不满足的。”一丝闪念在我脑海中划过,可能外公已经知道了。但我马上撒娇说:“是啊,蕾蕾除了妈妈爸爸就最喜欢外公了。”
我在外公面前极力保持平静,却在当天的晚上默默流泪一整夜。是的,我爱我的外公,我愿意拿我二十年安康的寿数来换取外公一辈子的平安健康。那个仲夏的晚上,窗外是悠长又幽怨的蝉鸣,室内却是面色惨白的我跌坐在坚硬的地板上,渐渐感到自己滂沱的泪水打湿了胸前。这是我22 年的生命里第一次彻夜不眠,也是第一次觉得夜晚是那样的漫长。滴滴答答不停作响的钟表如同房间里另一个在抽泣的我。空空的屋子里仿佛不再有那些家具,那些书本,却只剩下了我和悲伤。我轻手轻脚走到桌子前,拿出佛经。我泪流满面地祈祷,佛祖啊,倘若自幼要强的我犯下了什么罪过,也请你降罪于我。请你大慈大悲,莫要为难一生忠厚善良的外公,让他可以平安健康地度过晚年。大地的黑暗逐渐被清晨的阳光所取代。新的一天来到了。我收拾好全部的悲伤,强迫自己精神饱满地来到厨房,为父母和外公外婆准备好一天的早餐。在母亲送我去上研究生课程的路上,我告诉妈妈这个我们极难接受的消息。听完我说的话,母亲的身子立即被悲伤狠狠击打,似乎变得无力而孱弱。但悲伤过后我和爸爸妈妈都恢复了理性。我们和舅舅姨妈一起讨论如何做进一步的检查,如何选择医院,选择医生,选择治疗方案,让外公的生命可以得到尽可能长的延续。我们带着外公去做进一步的病理分析,确认了外公目前处在肺癌II 期,预期寿命还有两年左右。而这时候外公刚刚度过他的78 岁生日。我们尽己所能为外公求医问药,无论是中药还是西医,无论是细胞免疫疗法还是基因靶向治疗。尽管外公在2019 年的3 月1 日溘然长逝,但他被诊断为肺癌后的生存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权威医生所判断的预期寿命。这也是爸爸妈妈、舅舅姨妈和我们这些第三代孩子们努力的结果。
回想起久病床前漫长的灰色岁月,记忆却并不全是悲伤的。在外公最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依然深深爱着外婆,深深爱着他的儿孙们,当然也被他教过的学生所关心着敬爱着。
在外公身患绝症的四年里,他的学生屡屡带着昂贵的特效药和爱戴来到医院和家里看望他。很多学生是在他大学刚刚毕业不久时候教过的,因此他们和外公年龄差距并不大。那些须发皆白的学生们依然会在外公面前恭恭敬敬喊一声张老师。这些都已经步入晚年的老人们和外公谈着他们的少年时光,外公的青年时代。他们会想起刚刚毕业,身上满是朝气的外公和他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听评书,看电影,师生亲密无间,宛如哥哥和弟弟妹妹一样;他们会想起当时收入依然微薄,还要养着几个孩子的外公会拿出自己的钱请贫困的学生吃饭,给他们购买习题集,语重心长地叮咛嘱咐他们,最后他们赶上文革前高考的末班车进入了名牌大学,至今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院士或者市长、厅长;他们会想起二十出头,自己还是个孩子,稚气未脱,才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外公会时不时板起脸来,刀子嘴豆腐心地教训着那些十来岁正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们。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当年十多岁的叛逆少年和天真少女,现在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老太太,而当年意气风发的外公也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了。岁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习惯,却没有改变师生之间浓烈如醇香老酒、长久如奔流江河的情谊。我和外公一样也是一名中学教师。在被外公和他学生之间情谊感染之余我也暗暗许下心愿。我要做一名让学生毕业之后还会思念还会爱戴的教师。外公做了将近四十年的教师,虽然作为五十年代大学生的他有着高学历,多才多艺,博览群书,但他却一生清贫。外公临终之前一个月退休金也只有六七千块钱。但他却拥有天下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不会随着时间逝去、距离变远而褪色的情谊。凭心而论,教师的收入待遇实在算不上好。但为什么还有那样多德才兼备的人选择这一工作并且兢兢业业地去做呢?我想这些人恐怕和我外公的想法一致。他们的心中一定是这样想的:唯愿桃李满天下,不求荣华加己身。
外公外婆自1961 年成婚,五十余载如一日,恩爱有礼,相濡以沫。他们共同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熬过了外婆的难产大出血和儿女的夭折的痛苦。外公为外婆和儿女们做了三十余年的饭菜,外婆为外公和儿女们洗了三十余年的衣服,收拾了三十余年的屋子,直到儿女们长大后为长辈负担起了做饭洗衣的家务。外公生病之后,外婆常常和儿孙辈一起照顾他。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在一起却总是有说不完的情话。有时候外婆用轮椅推着外公在花园里看春天的景色,外公会冷不丁地摘下一朵花插在外婆已经发白的鬓角上。已经快八十岁的外婆会娇嗔道:“老头子,你做什么?”外公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爱意满满地说:“逗你玩儿,老太太!”我们儿孙辈看到这些,真的被外公外婆之间历经五十余年而不褪色的爱情深深感动。
舅舅姨妈和爸爸妈妈都已经年过五十,身体逐渐衰弱,因此彻夜陪护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这些孙辈身上。记得在外公生命的最后半年里,有一天,我刚刚和外公的管床医生沟通过就匆匆去饭店买外公喜欢吃的笋炒肉丝、清蒸鲈鱼。因为时间匆忙,我没有来得及吃饭就连忙赶到外公所在的病房。我走进病房后,连忙打开饭盒准备一勺一勺喂外公吃饭。可我却没有想到虚弱的外公伸出干枯如同秋天树杈的手抚摸着我的头,问道:“嫣然,你吃饭了吗?”外公病情的加重并没有让我泪如泉涌,可听到这句话我的泪水却决堤了。我泣不成声地说:“外公,我刚刚吃了我最爱吃的酸汤鱼。”我眉飞色舞地和外公描述着酸汤鱼的爽口美味,外公听完我的描述后说道:“好孩子,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此刻,他才一口一口地吃下。而我也收起了泪水,望着外公如同幼年时候一样天真地笑了。
外公病了以后性格越来越像孩子,原本记得清楚的事情好多也忘了。就像文章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小时候的我常常依偎在外公身边听他读古典诗词,听他讲历史故事。而如今由于外公的肺部肿瘤已经转移到脑部,那些古典诗词、历史故事外公似乎已经不记得了。而这时的我还清晰记得外公给我讲过的那些优美婉转的千古绝唱,那些胸怀天下的国家栋梁。我把外公教给我的这些故事又重新讲给外公听。乌鸦反哺,小羊跪乳就是如此这般吧!外公病重后越来越任性,有时候晚上突然惊醒说要吃什么玩什么,我和表哥表姐们便拿起手电筒在黑夜中去寻找24 小时便利店去给他买食物。彻夜不眠,满街寻找,伺候大小便,讲故事,读诗词固然辛苦,然而我和表哥表姐们却丝毫不抱怨,因为能够在外公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他就是我们儿孙辈最大的幸福。
三、长河干涸,生命逝去,然而爱却永不停息
2019 年3 月1 日,一个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那一天,是我的表哥和舅舅陪伴着外公,那天晚上,我彻夜不眠,胸腔里像有一只小猛虎一样坐立不安。也就是在那天的深夜,外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生善良正直的外公经过病痛的数年折磨,终于撒手人寰。记得最后一次照顾外公,他衰老枯弱如同秋风里一片摇摇欲坠的树叶一般。那时的我欲说千言万语却悲极思滞。外公五十年代毕业于师范大学,一生从事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他在校亦师亦父,深受学生爱戴;在家勤劳坚定,慈祥幽默,乃全家之天。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天是明朗的天。而今天塌了,我心有所思却欲语还休。他从教四十二年,享年八十三岁,带着眷顾和不舍离开了我们。暂借挽联表达我的哀思:经寒暑不惑倍双桃李遍大地,历春秋耄耋繁三风范感苍天。“40+2<40×2”是科学,“80+3<80×3”更是规律。虽说理想替代不了科学,然“已遍天下”足矣,亲情也受限于规律,但“苍天已泣”足矣!
外公是一条长河。长河虽然总会干涸,生命固然总会逝去。但是被长河滋润过的土地上长出的花花草草、树木森林却赋予了长河以新生。被外公教导过关爱过的儿孙辈会带着刻入我们血液里永不停息的爱,满怀着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和热爱昂首挺胸地活下去。而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善良,我们的努力也会赋予外公新生!
是的,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