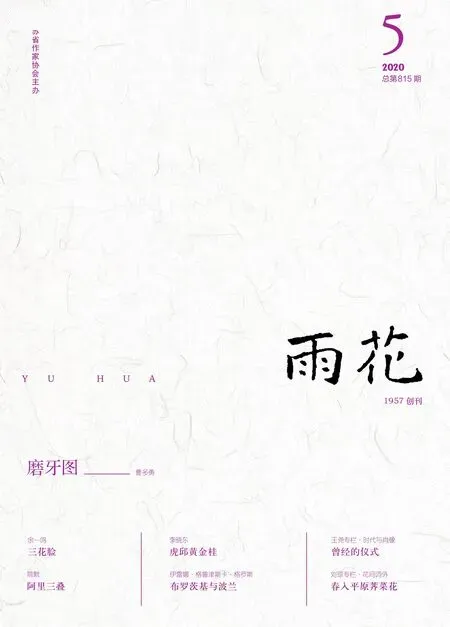刀光
赵 雨(浙江)
推开库门,我半身浸在阳光中,阳光从南窗斜射进来,仓库里的货品浸在阳光中。阳光有灰尘的味道、包装纸的味道、拖把的味道、石灰的味道,我关上库门,往前走,前方是北墙,北墙照不到阳光,堆着一些杂物。我不确定那东西在不在,如果它在,我的判断就是正确的。我起码有五年没看到它了,把它放在仓库,就是为了遗忘,像遗忘一条僵死的狗。但现在我得找到它,将它从遗忘的时光中剥离出来,重见天日。我在杂物堆里翻找一番,它很快显露了出来,如此显眼,任何东西都不能遮蔽它,灰尘不能、包装纸不能、拖把不能、石灰不能。一块牛皮纸包裹着它,纸张泛黄,褶皱不堪。我捧起来,慢慢摊开,它暴露无遗。它是一把刀,刀背厚实,刀刃寒光闪闪,刀柄精雕细琢,握在手里我感到热血蹿上脑门,手心渗汗,凭空挥舞两下,空气仿佛一匹布被从中撕开,当年的我又回来了,当年的生活又回来了。仓库外,肖玉还坐在我的店里等我回话,刚才就是他让我来找这把刀的。他说,找到刀,一切就都回来了。
我离开仓库,回到店里,我的店是家小型超市,一百五十平,六排货架,摆着各种物品,前门有个玻璃柜,出售香烟,柜台后是收银台,收银台后横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肖玉此时就坐在其中一把上,桌上放着一瓶牛栏山、两个酒杯、一只果碟,花生壳满桌都是。
二十分钟前,他进来找我,一坐下就说先喝两杯。他来找我肯定是有事,没事我们现在几乎不见面。果然他两杯没喝完就把事说了出来,他说他妈的王思出事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说让人算计了。“算计”是我们的行话,意思是被人陷害了,我问具体的过程。
他说,前天晚上王思出门散步,来到玉门小区和柳条街交接的巷子,一伙早埋伏在那里的人出来将他包围住,对他拳打脚踢。一开始王思还还击,没过一会儿就寡不敌众,败下阵来。王思躺在地上,一声不吭,那伙人将他往死里打,如果不是两个同样也在散步的人经过,冲散了那伙人的杀气,他可能就没命了。
我说,肖玉你每次都说得绘声绘色,好像你就在现场似的,你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别将自己搞得像目击证人一样。肖玉将酒杯往桌上一掼说,他妈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王思被人算计了,后果非常严重。我问什么后果?他说,那伙人离开后,两个散步的好心人叫了辆救护车,把王思拉到医院,外表看不出什么大伤,可惜脑子估计是打坏了,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医生说,他可能就此醒不过来了,可能就此变成一个植物人。我大惊,植物人?肖玉说,对,我们最好的兄弟王思居然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狗屁植物人,这种事真不可思议,所以我就来找你了。我说,找我能干什么呢?肖玉说,给王思报仇。我说,你知道是谁动的手?肖玉毫不迟疑报出一个名字,是李大富。我问,北街李大富?肖玉说,对,就是北街李大富。我问,你怎么知道是他?肖玉说,一个礼拜前,王思和他结了梁子。
为了一个女的,肖玉舔着嘴唇说。
年过四十的王思还会为了一个女的跟别人结梁子,这大出我的意料。
肖玉接着说,王思很喜欢那女的,那女的是银河KTV的陪唱小姐。正好李大富也喜欢她,王思和李大富彼此都知道对方喜欢那女人,但找不到时机过招。我说,肖玉你等等,什么陪唱小姐那么稀罕,全世界的男人都围着她打转?肖玉说,是刘恬。我问,哪个刘恬?肖玉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刘恬,就是我们以前初三(2)班的语文课代表,刘恬。我问,她怎么会做了陪唱?肖玉说,妈的,陪唱是正当职业!我说,那倒也是。
肖玉接着说,那天晚上,王思把车停在银河KTV门口,等刘恬下班,刘恬每天两点下班。两点一过,和她一起出来的就是李大富,李大富搂着她的腰,把她送到门口,正要跟她说再见。李大富搂着她腰的那只手还没放开,王思就从车里跳下来,故意把车门关得很响,然后走到李大富跟前,拍拍他的肩,说,兄弟,早点回家吧。李大富人称“北街第一霸”,并非浪得虚名,他显然已喝下不少酒,那些酒都是刘恬陪着喝下的,但他看人的眼神还是直、准、狠。他看着王思说,兄弟,得罪了。说完,放开刘恬的腰,摇摇晃晃走了。
肖玉说,李大富为什么不当场发飙和王思单挑,却说了句“得罪了”?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自己动手,而是委派自己的手下行凶,这是老江湖的惯用手段——对于肖玉这样的说辞,我事后向刘恬求证过,那时刘恬还处在王思被打的悲痛之中,她矢口否认李大富现场说过“得罪了”三个字,她说,李大富对王思说的是,兄弟,我知道你喜欢小恬,我知道你知道我也喜欢小恬,那么我们两个男人就来一场公平的竞争吧。如此甜腻无聊的话出自李大富之口比“得罪了”更让我不能相信,所以他们当时究竟说了什么就成了一桩悬案。
肖玉喝了口酒说,没过几天,王思就遭了暗算,所以你说这不是李大富报复是什么?李大富居然敢明目张胆把我们最好的兄弟打成植物人,这笔账我们再怎么样都是要算的。我沉默良久,肖玉当时还没提到那把刀,我内心其实是退缩的,自从盘下这家小型超市后,我就退出他们那个腥风血雨的圈子了。肖玉见我面有难色,问我是不是有别的想法。我说,你知道我现在是个安分的店主,再干这种事有点不大习惯。他又把酒杯往桌上一掼,这次玻璃杯脚被掼断了,牛栏山洒了半桌。他厉声道,你这混蛋,你忘了这个店是怎么来的!你可以忘了我和王思我们三人以前的交情,可如果连王思对你的恩情都忘了,你就太不是东西了。
这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没错,没有王思的帮助,就没有我这个店。那正是五年前我对江湖产生倦意时,也是像今天这样的一场酒局,我对王思和肖玉说,我不想混了,想干一份稳定的工作,肖玉没理会,王思问我想做什么,我想了想说,最好是开一家店,当一个店主。王思说,想做就去做,当店主蛮好的。我说,但我没钱。王思说,钱我借给你,等回本了再还我。我说,如果回不了本呢?王思说,那就不用还了。这家店就是这么开起来的,到现在我还不相信我这种人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坐在一个柜台后,拥有六排货物架和一个收银台,这一切都是王思给我的,我欠着王思的人情。
肖玉说,你再想想,想想我们结拜的场景,想想我们三人横行南北两街,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情景,想想我们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情景,你想想这些,再想想王思现在躺在床上可能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你还坐得住吗?这次轮到我往桌上掼酒杯,我说,我确实坐不住了。肖玉情绪越来越亢奋,像在演讲,他说那就对了,最后你再想想那把刀。我说我还藏着那把刀。肖玉说把它找出来,带着它,我们去为王思报仇。说到这里,他从腰间拔出一把刀,拍在桌上,这把刀和我的那把一模一样,王思也有这样一把,这三把刀是当年镇上最有名的吕铁匠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我们就靠这三把刀成为让昀镇人闻风丧胆的“三刀客”。
现在我把刀找出来了,它一如当年,渴望血的滋润。我坐回肖玉面前,把刀拍在桌上,和肖玉的那把躺在一起。肖玉看看我说,你答应了?我点点头说,我不能成为一个无情无义的人。肖玉问,什么时候行动?我说,听你的。他说那就明天晚上,我们直捣黄龙,做了李大富那混蛋。
李大富的老巢在北街,去找他前,我决定先去看看王思,看看他到底被打成了什么样。第二天,一过午,我跟着肖玉去了医院。王思躺在病床上,像睡着了一样,除了额头有一块淤青,脸上没一处伤,身穿大一号的蓝色病服,一根管子从鼻孔伸出来连到一旁的机器上——十年后,他忘记了自己的这副形象,他连自己曾经被打,有可能成为植物人这件事也忘了,人总是会忘记很多事情,说不上是好是坏。十年间,他把业务越做越大,最终成为昀镇最成功的企业家。他会每天傍晚牵着自己和刘恬的儿子阿亚的手在玉明街散步,有一天过马路时,父子俩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救护车撞飞,当场丧命,出事地点就是当年医院住院部的旧址,这是他一生的蓝图——现在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病床上的他给我永远醒不过来的假象。我久久望着他的脸,十多年前歃血为盟的记忆在脑海中翻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后来开始怀念那段岁月。那时的昀镇还没有购物中心、没有广场、没有轻轨线、没有汽车阵、没有几十层高的小区楼。我久久望着他的脸,俯下身,趴在他耳边说了句,兄弟放心,我会为你报仇。
离开医院,我们正式踏上前往北街的路,上世纪,北街和南街所在的北镇和南镇没什么区别,过了二十年,区别可大了。南镇成了经济开发区,北镇像个被丢弃的孩子。从南跨到北,像是跨过一条国境线,北镇的标志性建筑百货大楼一过,就是北街地界,这栋大楼曾红极一时,如今关门落锁,窗户残破。
我们在百货大楼前停留片刻,我分了支烟给肖玉,说有件事我得搞清楚,你说王思被四个打手围着打这消息究竟是哪里来的?肖玉吸了口烟,若有所思,然后正儿八经对我说,为了劝你一起来为王思报仇,我对你隐瞒了实情。我大吃一惊问,这是他妈的什么意思?他说,其实我正是这次打架的目击者。
你在现场?我问。
是的,他点点头说,那天晚上,我出门散步,沿着柳条街走,经过巷口,听到异样的声响,一听就知道是打架。巷内没一盏路灯,黑灯瞎火,只能听到打架的声音,五条模糊的人影,四人在打一个人,看不清人脸。他说,我发现是打架,全身血液都亢奋起来,那种感觉你现在还有没有?这几年过的日子实在无聊,逮到机会,我就观看起来,观看四打一的场面,打人者出拳的速度,被打者无力还击的软弱。当时我不知道那个被打的人是王思,否则不可能袖手旁观。打完后,四个人离去,我也准备离去,这时趴在地上的人艰难撑起上身,摸出手机打电话,我的手机就响了,传来的是王思的声音,说自己被人打了。我像做梦一样,他趴在地上的样子像一只大蛤蟆,整个影子都黑乎乎的。我跑过去,扶起王思,王思已昏迷,我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所以根本就没有两个刚好散步路过的好心人,救护车是我叫的,是我把他送到医院的。
我问,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跟我说实话?肖玉说他觉得愧疚,当时王思离他不足百米,他兴趣盎然地目睹了王思被打的全过程,虽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还是无法原谅自己,这事差不多成了他的心病,他恨不得抹去在场的记忆,怕告诉我实情我会觉得他冷酷无情,会觉得王思的不幸有一半是他造成的。我说,你想得太多了。他丢掉烟蒂说,反正他现在只想找到李大富,洗刷他和王思的耻辱。两年零四个月后,王思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从植物人状态苏醒,连医生都觉得是医学上的奇迹,归因于那些日子刘恬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真情感动上苍。我第一时间去看望他,他坐在病床上,神采奕奕,微笑着招呼每位来访的朋友。我和他谈了半小时,趁机问他两年零四个月前的那个夜晚,是谁打了他。他一脸疑惑,盯着我看了十秒钟,然后说:“不,没人打我。”
“那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问。
“是一辆电瓶车,”他说,“那辆电瓶车在漆黑的柳条巷撞倒了我,停都没停就逃逸了。”
虽则说法不一,但这不重要,我在这里要说的唯一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那天我和肖玉去找李大富寻仇。
肖玉在百货大楼前抽完烟,丢掉烟蒂,我们继续前进。
北街此时整个展开在我们面前,它的一侧有一条河,北街是一条临河街,河水在我小时候是很清澈的,夏天傍晚来河里洗澡,我会从家那边的河段一路游过来,游到北街,看到在临河房子里晒衣服的妇女、在河埠头淘米的老太太、吃过晚饭在桥上赤膊摆龙门阵吹大牛的闲汉,街上店铺的样子也能窥见一二。听长辈说,这条街历史悠久,南宋时就有了,南宋的街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这副鬼样,年代那么久远的东西到今天居然还在,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它可不是什么值钱古董,街上脏水横流,坐在家门口洗菜洗衣服洗袜子什么鬼东西都洗的妇女把洗完的水直接往街上倒,更壮观的是含有金属味道的水,那是街面上的小五金作坊生产的,有一种油腻的颜色,太阳一照,五彩斑斓。
李大富的网吧位于北街尾端,分外扎眼,二层钢结构房,窗户光洁,玻璃上贴着游戏海报,外墙褐色,墙砖整齐划一,像是贫民窟里的大户人家。我们可不是来欣赏人家房子的,肖玉自从在网吧门口停住脚,眼神就充满战斗的力量,他摸了摸佩戴在腰间的刀,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只剩下两件大事:第一件,五分钟后,他会和我走进网吧找到李大富,十分钟后,他会把李大富宰杀在后门一条死巷中;第二件,他会被逮捕,半年后没有任何悬念地被判故意杀人罪,坐在一辆囚车中由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押到行刑场,被一颗滚烫的子弹射碎头颅,结束年仅三十六岁的生命。
现在,他摸了摸佩在腰间的刀,我也摸了摸佩在腰间的刀,刀柄的棱角透过衣料格外分明,刀身用牛皮纸包裹着,硌在右屁股蛋上,佩刀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名古代的侠客,即将闯入仇人之家,斩获他的首级,但我感觉不到荡气回肠的侠客激情,反倒觉得眼前这一切挺荒唐的。如果现在手上有一把枪应该会更省事,街上的热浪将我搞得头晕眼花,我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
我们推开网吧的门,肖玉在前,我在后。网吧里坐满人,二十出头的小年轻戴着耳机,坐在一个个用带格的板材隔开的座位上,盯着眼前的电脑屏移动鼠标打游戏。现在这世道全是这样的人,他们好像可以腐烂在座位上,对门外的世界毫无兴趣。空气里充满烟味、方便面味、湿纸巾味,还有一股尿味,我们沿着过道来到柜台,一个女的坐在那里,我们问她,你们老板在哪里?女的问我们找老板有什么事。我们说我们是他的朋友。女的往右指一指说进门第一间房。我们走了进去,房内很宽敞,李大富坐在办公桌后玩手机,他大概四十出头,头顶秃了一大块,耳朵上的头发很长,盖住耳廓,嘴唇厚实,鼻子硕大,下巴宽阔,穿着黑色西装。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立刻就认出来了。
没错,我们和他是认识的,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了。
他是90年代第一批进入昀镇的外地人,操着一口纯正的外地口音,刚在混道上崭露头角时才二十岁,我和肖玉、王思“三刀客”已经成名。作为后起之秀,他借着那个年代新生的舞厅、卡拉OK厅、台球厅等娱乐场所一步步稳固自己的势力。跟着他混的哥们都是外地人,以打架抱团著称,若得罪一个人,叫来的同伙都是一车车的,颇遭本地人侧目,昀镇历史上颇为著名的一场群架事件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冲突,而根源正在李大富和肖玉身上。原因很简单,有一次肖玉在一家台球厅打台球,和一个外地小混混打,输了几局,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小混混把李大富叫来,李大富倒挺客气,笑着对肖玉说了两句话,不知哪里说得不好,肖玉把一杯啤酒泼到李大富脸上。李大富一抹脸,居然还在笑,他说,想打架这里施展不开拳脚,约个时间地点。这架就这么约下了,整个打架过程肖玉只找准李大富一个对手,刀光剑影,两人居然都没受伤,是件稀奇事。
老仇人见面没有分外眼红,李大富先招呼道,哟,稀客啊。时过境迁,我总结这次惨案,认为李大富其实不至于落得死的下场,关键在于他的态度,不知他对别人讲话是怎样一副腔调,对肖玉,语气中透露出难以遮掩的轻蔑和打趣,肖玉天生敏感,最忌恨对方那种吊儿郎当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样子。
李大富说完“稀客”,又说了句“何事登三宝殿啊?”肖玉黑下脸,开门见山说,是你找人打了王思?李大富抓抓头皮说,王老板怎么了?肖玉说,别他妈事不关己的样子。李大富站了起来,他站起来比我和肖玉高出半个头,他用手指点点办公桌说,二位如果来做客,欢迎,如果找碴,还是那句话,约个时间地点。肖玉上前一步说,少废话,再问你一句,是不是你干的?这问题完全可以用“是”还是“不是”解释,李大富不这么做,继续绕弯子说,是怎样,不是又怎样?肖玉说,是,老子让你血债血偿,你这外地佬。李大富说,你好像对外地人很有成见,现在大家都为挣钱,哪有什么外地人本地人之说。肖玉就不跟他废话了,像当年突然泼出去的啤酒一样,一个箭步窜上前,隔着办公桌往他脸上就是一拳。李大富倒在椅子上,弹起来,绕出办公桌来和肖玉厮打,我赶紧关上门。
时隔多年,我回忆那场二对一的干仗,自认对李大富是不公平的,论体格、狠劲、打架技巧,李大富不输肖玉,加上我,他就没有胜算,何况我们还带了凶器。我们一开始没亮出凶器,他们几个回合下来,我站在一旁观战,如果肖玉有必胜的概率,我会一直做个旁观者,但他很快被李大富压在身下,拳头如雨点般砸下,我不能再置之不理,上前给了李大富一记闷拳,将他打落在地。他翻身爬起,一抹流血的嘴角,说,很好,一起来,来!
我和肖玉开始合攻,不一会儿把他揍得眼角开花。他冷不防往后退,撞开一扇后门,逃了出去。我们这才发现房内原来还有一扇门,通往网吧后的巷子,我们追出去,这条巷子的一头通向大街,另一头是个死胡同。李大富一出门,踌躇片刻,可能被打得晕头转向,判断不了方向,这一停顿,又被我们逮住,肖玉与他近身肉搏,突然只见他往腰间一掏,单手一挥,寒光一闪,肖玉脸上出现一道口子,血流如注,李大富的手上握着一把短小的匕首。
我们早该料到像李大富这样在江湖上行走的人贴身肯定带有家伙,这一疏忽让肖玉吃了苦头。李大富握紧匕首,又露出轻蔑的笑说,跟老子打,弄死你!你们本地人有什么好牛的?弄死你们!肖玉的怒气至此达到顶峰,他掏出刀,我也掏出刀。李大富战意正酣,丝毫没把我们的刀放在眼里,对肖玉实施挑衅,肖玉持刀逼近,李大富握匕首乱舞,肖玉向他砍去,被他挡掉两刀,第三刀砍在他手腕上,匕首震落在地,他俯身捡,肖玉向他肩膀猛砍一刀,皮开肉绽,他露出怯意,扭身逃跑。
他跑的是大街方向,当时我们三人所在位置是:我在最靠近大街处,李大富在中间,肖玉在最里面,李大富要跑,必然经过我身边。他跑过去,我才意识到他要跑,肖玉大喊一声,拦住那混蛋!我拔腿追,肖玉紧随其后,局面变成了李大富跑第一、我第二、肖玉第三。
好,现在我要说说在这最后几分钟发生的事,跑在第二的我,望着李大富的背影,一股强烈的倦怠感涌上来。仅一秒时间,之前的整个生涯铺展在眼前,那种你追我赶、神经紧绷的岁月。如今我已告别这种岁月,是一个安分的店主,我有一家店,坐在收银台上的时光让我满足。然后我做出一个判断:如果我追到李大富,一场恶战难免,有兄弟在旁,我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我不希望有这场恶战,说白了,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介入这场复仇的把戏,又不能表露出来,最后我是这么做的:一个趔趄,假装在奔跑中不慎跌倒,为了演得像一点,我真把脚踝重重折了折,能听到骨头错位的清脆声,滚了两滚,我捂住脚踝,痛得额头渗出两滴豆大的汗,对肖玉喊出他刚才对我喊的话:拦住那混蛋。
肖玉风一般超上去,我没想到他能跑这么快,他挥出一刀,将李大富砍翻在地。我看到在阳光中翻飞的刀光,刀光一起一落,我没去阻止他的屠戮,我知道拦不住。我不知道他哪来那么一股不顾一切的杀气和怨气,毕竟李大富只是有可能委派打手将我们的兄弟王思打成植物人(有可能王思那晚真的只是被一辆超速的电瓶车撞翻在地),最后的结局不至于在肖玉的刀光中,如一摊烂泥被砍死在地。
——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