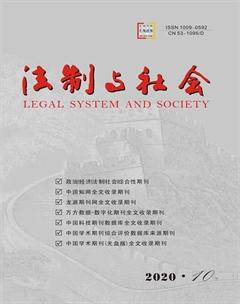论监察调查中律师介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崔宇笛
关键词监察 辩护 可行性 必要性
一、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必要性研究
(一)被调查人在调查程序中处于弱势,需要法律帮助
首先,被调查人一般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在被监察委采取强制措施后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因此,若赋予律师在调查程序中介入的权利,将能平衡被调查人与监察委之间的力量不对等,提升被调查人对监察委的防御能力。
其次,在法律赋予律师介入调查程序之后,律师能够为被调查人申请排非。在仅允许律师介入调查程序且不进行其他立法修改的情况下,律师可以依据《高检规则》第65条“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据”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调查阶段申请排非具有重大意义,其能够尽早地发现并否认通过非法途径收集的证据,防止其流入后续程序对被调查人造成人身、财产的损失。因此,尽早地排非能够预防冤假错案的再现,更好地维护刑事诉讼环境和社会秩序。
最后,目前学界存在调查权即侦查权的学说,如人民大学的陈卫东教授、清华大学的张建伟教授、四川大学的龙宗智教授等,笔者认同并支持此观点,因为二者在时问、目的、手段上存在较大程度的吻合。如龙宗智教授所言:“职务犯罪调查具有犯罪侦查之实,而无犯罪侦查之名。”进而,主张此观点的律师便可以在对《刑诉法》条文解读时将“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与“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办案人员”进行等量代换。再以《刑诉法》第4l条为依据,在调查程序中搜集可能在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检察院补充移送前程序中遗漏的有利被调查人的证据,以此来保护被调查人权利,约束国家公权力。
(二)《监察法》的排非规定存在疏漏,被调查人的权利遭受威胁
《监察法》对于防止监察委非法取证只有第33条后半部分原则性的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和第40条后半段的:“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方法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既有规则又有原则,这看似是很完善的排非规定。
首先,笔者对上述规范的意义表示肯定,因为其对于排除非法供述而言着实完善,但其似乎对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实物证据不太适用。因为若监察委想伪造或者以非法方法收集书证、物证,其无需威胁、引诱、欺骗、打骂被调查人。这就意味着监察委虽然不能以打骂、威胁、引诱等方式收集供述之类的言词证据,但对于搜集其他实物证据而言,当前并没无其他具体的法律规则来制约他,唯有《监察法》第33条后半段的法律原则能够起到较为薄弱的作用。而当这些证据收集完成后,完全可以与其他合法的供述一起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对于被调查人而言是非常大的威胁。
(三)维护刑事诉讼程序正义
程序法治,是指通过构建和完善程序法律制度来实现国家法治目标的模式,其核心是程序正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专家武钦殿法官曾说:“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前提”。笔者认为,当刑诉程序偏离了程序正义,结果正义将失去最基础的制约,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将无法得到保障。在《监察法》出台前,职务犯罪侦查权归检察院享有,且此程序允许律师介入,受律师的监督。但在《监察法》出台后,职务犯罪调查权归监察委享有,律师不再被允许介入,其律师帮助权被剥夺,监察委也失去了来自律师的外部监督,其恶果是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程序不透明,非法取证如刑讯逼供的滋生,甚至最终冤假错案率的升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缺乏律师介入的调查程序会影响监察委员会的公信力,不利于在社会中形成信仰程序正义的良好法治风气。不仅如此,调查程序与侦查程序在法条上存在的明显差异将会影响当前正在进行的两法衔接工程的效率,延缓刑诉体制改革的进程。由此可见,允许律师介入调查程序是一件法治行动,其能够更好地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
二、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可行性研究
(一)现行法条存在律师介入的法理可能性
首先,调查活动应受何种规范调整?通过对比《监察法》与《刑诉法》在职务犯罪刑诉程序中的职能,笔者认为《监察法》规定的调查活动是职务犯罪刑诉程序中的一个子环节,《刑诉法》则是统领整个刑诉程序的母法。因此可以将它们视为调整刑事诉讼的“根本法”和“基本法”,这也意味着调查活动需要受双重约束。同时,《监察法》中有关调查的规定又像是为追诉特定犯罪活动的“特别立法”,《刑诉法》中的侦查章节则是为打击一般罪名而设立的“一般法”。正因为一般法有着为特别法补漏的功能,如《合同法》有着对《海商法》关于海上货运合同权利义务的空白进行补充的作用,笔者便将《刑诉法》第14条中关于公检法三机关保护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法律原则补充到职务犯罪辩护中来了。这样,即使在职务犯罪刑诉程序中不存在公安机关,检察院仍需依据本条保障被调查人的辩护权,并且本条并没有限定辩护权存在的时间,因此律师在调查阶段可向检察院主张此法条,便依法有权进入到调查阶段为被调查人提供法律服务了。
诚然,会有反对聲音基于《刑诉法》第34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予以反驳,但此条是在规定审查起诉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如何保障自己的辩护权,这和审查起诉前被调查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辩护权不冲突。
(二)律师如何介入调查程序的构想
1.关于律师介入时间点的构想
我国《刑诉法》规定,一般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辩护的时间起点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笔者认为若未来《监察法》将律师介入调查程序写入其中,可以规定被调查人在被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有权申请辩护与法律帮助。
首先,基于被调查人的需求而言,在被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之前,被调查人并不需要较强程度的援助。如在谈话、进行自我陈述等程序中,被调查人受到的人身自由限制较少,心理压力较小,被调查人可以通过自身能力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初步保护。然而,若被调查人被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后,其将面临被限制在留置场地的局面,其人身自由将会被较大程度地剥夺,不仅如此,被调查人与外部环境的交流机会和自由度也会被压缩,这将导致被调查人与监察委问的信息不对等逐渐被拉大。监察委非法取证的可能性也会随之被加大。
其次,从实践经验来看,自从2012年《刑诉法》修改以来,增强律师在刑诉程序中的介入对我国人权保护意义重大,在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律师能够在侦查阶段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侦查阶段申请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同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这虽不能让所有委托人都能得到撤案、不起诉或宣告无罪的结果,但这能保障让无罪的嫌疑人尽快得到法律的肯定,让有罪的嫌疑人得到應有的权利保障。律师在刑诉程序中的介入已然成为公平与正义的降临,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时间点的构想同样可以借鉴域外经验,比如。香港《廉政公署(被扣留者的处理)令》第四条中表明:“(1)被扣留者须获给予合理机会,以便与法律顾问通讯,并在一名廉署人员在场但听不见的情况下与其法律顾问商议,除非此项通讯或商议对有关的涉嫌罪行的调查或执法会构成不合理的阻碍或延迟。”香港特别行政区允许律师在当事人被“扣留”后介入程序。“扣留”与“留置”含义近似,皆意在将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在特定时间与地点内进行适当限制。故我国《监察法》在未来修改时,可以此作为参考。
2.关于律师介入内容的构想
(1)会见通信权。不论是在一般刑事犯罪刑诉程序,还是在职务犯罪刑诉程序中,会见权是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基础。假设允许律师介入但未赋予其会见权,律师仍无法了解到侦查机关或是监察委是否存在非法取证的线索,进而无法申请监察委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不仅如此,假如不赋予律师与职务犯罪被调查人会见的权利,律师还无法得知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否存在违反程序正义的情形。再退一步讲,律师若没有会见权,仅凭当事人的电话转述与家属转述,其甚至无法全面了解案件真相,为委托人提供正确、有效的法律帮助。因此,笔者认为,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是架构律师介入内容的首个步骤。
(2)调查取证权。假如仅赋予律师介入的权利但未规定其享有调查取证权。则律师在现行《监察法》创设的司法环境下仍无法获取能够证明被调查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因为《监察法》未规定律师在监察委调查取证时能够在场,进而律师无法发觉监察委是否在收集能够证明被调查人有罪、最重的证据的同时收集了能够证明其无罪、罪轻的证据。因此,律师从而无法预判下一步是否针需要在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检察院补充移送监察委搜集的,对被调查人有利的证据。这不利于保护被调查人的权利,并且会使律师陷入能够介入调查但却无能为力的窘境。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另一方面能够加强被调查人方的力量,使其可以防御监察委的非法取证,并对监察委证明力不足的证据链进行攻击。更深层次地讲,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则可以倒逼监察委强化自身办案质量,确保职务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高效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