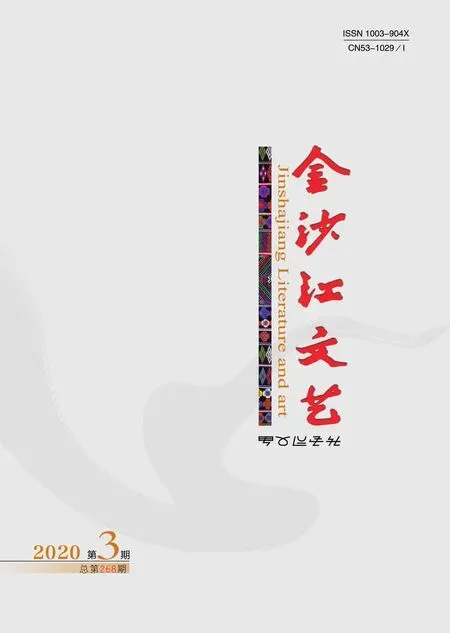钱 事
胡爱玲(广东)
1
汪友金的小院紧挨公路,好处是出门就能招停中巴,四十分钟就能享受县城的繁华和嘈杂了。
他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女孩比男孩大一岁,都在县里读高中。他老婆叫莲,可他喜欢喊她莲花,他觉得这样喊着顺口。有时,汪友金执拗得像一头闷驴。
莲花说,有金呐!随你怎么喊,还怕你改了我俩的关系不成?
汪友金笑而不吭。莲花是在心里把他喊做有金的。有金!有金!她的男人有一个响亮且喜性的名字,叫着都带劲。
莲花是个长得一般的女人,但她精明能干,擅长料理家务,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乡下男人来讲,比家里搁个漂亮的花瓶实用多了。
有一天黄昏,说起来既普通又特别,莲花家的重要成员之一,猪畜生没按时吃上食物,抗议示威般地吸着鼻子,嘴里一边哼还一边乱拱,不料就碰翻了厨房三条腿的桌子,十几只碗碟噼里啪啦摔到地上,再加上自相残杀,瞬间全都变成碎片了。
民以食为天,食以碗为器。后果当然严重,莲花非常生气。猪畜生并不傻,颇会察言观色,也了解女主人的脾性,见她手拿木棒过来,急忙抢先掉头穿过公路,往大青湖那边广阔的田野里逃去。
莲花十分心疼碗碟就追过去,她一心想惩罚这野性十足的畜生,对公路上潜在的危险失去了应有的警觉,刚跑到路中间,一辆大货车就如饿狼般朝她飞奔而来。
老天爷。刹那间,世界无声无息。
汪友金傻了。他正站在院门口闲着,饶有兴致地看莲花追猪。他还想起一部老电影,其中也有女主角撵猪的镜头,女演员头发又黑又长,被风吹得飞扬跋扈。
碗碟经年历月,难免有些磕碰残缺,汪友金早就打算等过年孩子们放假回来,大家一起去镇上购物,顺便再添置些新餐具。可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告诉莲花这些了。时间在那个时刻窒息,汪友金脑子嗡的一声懵了,像遭到最强烈的雷击。
更糟糕的问题接踵而来,司机是个没有品德也或很马虎的人,他肇事后就跟没事似地跑了,好像只是撞到一只猫或狗。
汪友金坐在漆黑的地上,几乎就是个木头人。交通警察非常耐心,问他那辆大货车的号码和特征等等,汪友金对此一问三不知,他甚至不清楚那是辆什么牌子的汽车,他成了只会摇头和只会说不知道的机械人。
这事对汪友金打击很大,半个多月都没缓过气。但事情业已这样,活着的仍得继续过活,一双儿女也还要教育抚养,地里的庄稼仍得照旧侍弄,那头该杀的猪畜生也照样撒野。
也间接刺激了两个孩子,女孩儿不久考到上海,第二年,男孩考到了西安,都是重点大学,这成了当地的文化大新闻。人们都给汪友金道贺,说他以后就等着享孩子们的福吧,汪友金却愁眉苦脸地笑不出来。
他们说,汪友金,我们羡慕你还来不及,你愁个什么呢?
汪友金说,我还能愁什么呢?还不是愁钱的事呗!
他们不吭声了。普天之下,谁不愁钱事呢。
看着愁眉苦脸的汪友金,秋生笑嘻嘻地说,爸,我听说现在的大学生不是谈恋爱就是逛马路,其实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趁早出去打工挣钱呢,家里有姐姐这个名牌大学生就够了。
汪友金不高兴,板着脸说,乖乖!你以为你考上大学就能耐了,你以为你考上大学就有本事了!这不光是你们自个用功的结果,主要还是因为咱家祖坟冒青烟了!你既然考上了就好好上!你什么都别考虑,只要你们将来能有出息,我就是累死也会供养你们的,谁叫我是你们的爹呢!
他那点田养不起两个大学生,汪友金决定去北城打工。他没有什么手艺,只能挣力气钱。这是担负神圣使命的钱,它抚养的可是汪家开天辟地以来的两个大学生呀。一想到这些,他就有使不完的劲。
工友损他说,你不就是两个孩子考上大学了吗?有什么臭美的呢?你还不照样跟我一样累得屁颠屁颠的,像牛马一般地干活!等儿女们什么都安顿好了,你这个老家伙也该完蛋了!
汪友金听了也不恼,还顺手甩给他一支烟,两人坐下有说有笑地抽起来。
汪友金干活实诚,不会偷懒耍滑,本分得就像做自家地里的活。挖沟、抬砖、挑沙、搬家、掏化粪池,只要能挣到钱,什么苦活脏活都干。
北城是个正在茁壮成长的城市,比汪友金的县城大多了。他白天干活省吃省花,下工后就回到郊区的家,一间又矮又小的出租屋,除去一床一桌一凳,几乎就没有挪脚的地了。
夜晚最寂寞难熬,汪友金躺在狭小的床上难免也有失眠的时候,在他有限的生活经验里,只能想想死去的老婆莲花。这个女人不风骚也不灵动,但她却是属于汪友金的实实在在的念想,道理类似于文化人所说的精神食粮。
他是喜欢莲花的,她刚从西庄嫁过来时,也是个娇小害羞的新娘子,这个陌生而新鲜的小女人,弄得汪友金的心扑通了一整天,真等到进洞房面对她时,他倒像个孩子般手足无措了。
从前的夜晚,汪友金把滚烫的莲花搂在怀里,冲她说一些不靠谱的笑话。这对于没有去过北京香港,只去过小县城的汪友金来说,也算是世界上最浪漫最美妙的事了。
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汪友金只身待在北城,白日里干活时,他仍是一个浑身使不完劲的人,但夜晚笼罩下的汪友金却感到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他就像个无家可归游荡在城市的幽灵,身体在北城躺着,魂儿却遛回老家了。
北城是好,却不是他的家,汪友金的根在大青湖边。他的小院里肯定长满了荒草,也肯定开满许多漂亮的小野花。在公路对面苍翠的田野里,流淌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小河,它很像一根被随意扔在大地上的银链。
庄稼深处,就是碧绿无垠的大青湖。干活累了,汪友金就过去蹲在岸边洗洗手和脸,然后坐下来抽一支烟,凝视着水里红艳艳盛开的莲花和浅滩上亭亭的水草,心里就很欢喜。这时候,莲花红彤彤的脸庞,还有她肥硕的屁股似乎就在夕阳余晖中晃荡,还有在空气中飘扬的饭菜的香味。烟一抽完,他站起来拍拍屁股就急急往家赶了。
跟现在比,以前的生活多好。汪友金望着斑驳的天花板,眼巴巴地期待天快亮起来。他希望黑夜永远不要降临,他愿意融入城市汹涌的人流,这样,他就能背对世界上所有的无奈和愁苦了。
2
北城有条叫塘埂的小街,街上净是网吧、电玩厅、小超市、发廊、酒馆和唱歌房什么的。一到晚上街上就喧嚣起来,霓虹灯闪烁着炫目诡异的光辉,吸引着东来西往的人。
这天早晨,汪友金抄近路赶一个工地,从街上一个小超市门口经过,看见一个身穿大莲花图案睡衣的女人,她刚洗好一盆衣服和被单。她的头发中等长度,乌黑茂密地覆盖双肩。她往绳子上晾东西时,雪白的腰身就显露无遗。
女人清新而美丽,像她衣服上的大莲花。
女人蓦然回头,瞥见一个有些苍老且高大的乡下男人,便友善地职业性地冲他笑了一下。
汪友金看见小超市招牌上的莲花二字,心里便蓦然柔软温润起来,仿佛那两个字就是他的老婆,一个叫莲花的精明能干的乡下女人。一阵风吹过来,汪友金眼朦胧了,他心里想,老天呐!我的莲花原来还在,她早就来北城等我了。
这一大朵柔软的莲花,以及那幕回眸浅笑,时常出现在汪友金的梦中,这使汪友金很尴尬。他很清楚自己来北城打工的目的,北城有许多欢娱的场所,但他汪友金可不是来寻欢作乐的,他打工挣钱是要供养儿女上大学的。
他不是没想过再讨一个女人,可一个快五十的乡下人,还有两个上大学的窟窿等他填补,有哪个女人会傻兮兮地跟他过日子。
汪友金就非常自责,深深地自责。别人可以去那些欢娱的地方,但他汪友金不能去,他是个负有特殊使命的乡下男人,他必须得担当起汪家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汪友金想,自己那么辛苦,即使是一头牛、一头驴子,干完了活计,还得给一口水喝,掬一捧草料吃。汪友金既委屈又难过,便在心里暗暗责怪那死去的莲花,或者骂她一句脏话,这样他就好过一些了。
一个傍晚,疲惫的汪友金下工路过莲花小超市,门紧闭着,他失落地坐在台阶上。一支烟的工夫过去了,那扇门也没有动静,他站起来走过去,耳朵贴在卷帘门上。
隔壁发廊门开了,一个男人出来走远。接着,一个短发女人懒散散地走出来,她看见探头探脑的汪友金就问,你干什么?
汪友金指着莲花小超市的门,说,我,我买东西。
短发女人说,买东西?她回老家去了!
汪友金被短发女人的绿眼睛逼视得有些惶恐,然后就转身逃也似地跑掉了。
第二天下工,汪友金又去了一趟“莲花小超市”,它依然没有营业,倒是又看见那个短发女人,好像专门在等他一样。汪友金对她没有什么好感,又落荒而逃,唯恐避之不及。
北城有许多好看的女人,汪友金的眼里只有莲花。
他做苦力活,每月基本上能挣两千元,给孩子们按每天二十元标准,就得一千二百元,女儿是要多给五十的,他就只剩七八百了。还有房租、水电费、伙食费、香烟费,加上老家人情世故的花销,根本没有结余。就这样,他还得在城里打工三年,才能让两个孩子都圆满毕业。挣来的钱就像水,看似抓了一大把,可打开手掌一看,全漏光了,它们只是从手心里过一遍。人一辈子忙忙碌碌的,其实就是为钱的事而忙碌。
汪友金无奈地在心里默默嘀咕,唉!莲花呀莲花,你个臭婆娘!你把两个孩子撂给了我,你解脱倒是解脱了,你清静也是清静了,可你知道我每天有多辛苦吗?
3
一个淫雨霏霏的下午,汪友金去邮局给两个孩子寄下月的伙食费。他对两个孩子很放心,儿子和女儿都非常上进。填完熟悉的单子,办好熟悉的程序,看着业务员把印戳响亮地一盖,汪友金就觉得钱已装到孩子们的兜里了,他也就感到十二分的安心了。
从邮局出来,汪友金抬头望望天色,看雨一时还住不了,瞧瞧行人寂寥的大街,他忽然心里空落得很。北城那么大,却没有他汪友金的去处。除了做工和吃睡,一切都与他无关,他是这个城市的局外人。
汪友金对北城已很熟悉,俨然是个土著了。他左右瞧瞧,这个地方离塘埂街不算太远,从楼群巷道里斜刺一插,二十几分钟能走到。
汪友金无可救药地想起那个不是他妻子莲花的“莲花”,这个乡下女人真不简单,居然能在北城开一个小超市。不知道她从老家回来没有,按道理她应该回来了。这个念头一闪,他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想去看个究竟。
他有段时间没来塘埂街了,看见莲花小超市的门开着时,汪友金心里一喜。
短发女人真是汪友金的冤家,她一看到他就暧昧地笑了。
这一次,短发女人没理睬汪友金,而是冲超市里的邻居喊了起来,哎哎,莲花大老板!你的老乡来了,都来找你好几趟了!
她出来了,看去竟比先前消瘦些,倒显出几分清丽,恰如一朵雅致的莲花。
短发女人说,你人缘真好,看看,生意都自己找上门,前后两不误!
她笑着骂了短发女人一句。短发女人扭着腰进自个屋了。汪友金的心却莫名地跃动起来。
她对他笑着说,听你口音,老家是南安的吧!你买东西?你进来吧。
汪友金说,我南安大青湖边的!
女人就有点愣神,上下打量着汪友金,说,你是大青湖边的!?
汪友金点点头,抬眼看看门楣上莲花两字,觉得亲切而熟悉,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出声音,莲花!
女人脸上露出欢喜,她说,莲花是我的名字,开这间店时,他起的。
汪友金一愣,你真的叫莲花?
莲花说,是呀!怎么了?
汪友金不好意思地说,我,我老婆也叫莲,莲花,不过,她是个短命鬼,两年前在家门口被汽车撞死了。
莲花露出惋惜的眼神说,哟!嫂子可惜了!现在的汽车跑得太快,就跟去抢钱一样,真得小心点!
汪友金选了毛巾牙膏洗衣粉肥皂后,又拿了五块钱两盒的香烟,才来到收银柜前交钱。莲花在电脑里算好账把小票递给他,说,大哥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买的都是日用品。
莲花说,你的孩子真有出息,你是怎么教育的?
汪友金笑着,谦虚地说,我一个小学毕业的粗人还能怎么教育他们呢?都是孩子自己刻苦上进!
汪友金边说边撑起伞出去了,雨打在伞上噼噼啪啪,好像燃放劣质的炮仗。
莲花说,大哥,慢走,再来呀!
汪友金嗯着,一头抵进了雨中。
4
汪友金已经习惯来莲花小超市买东西,就像从前习惯去村里王瘸子家买东西一样。也不知为什么,他每次一看见超市门口的莲花两字,就觉得无比亲切和高兴。那两个字似乎成了他精神的寄托。
有一天傍晚,他像往常一样买完东西刚要走,她对他说,你等等!
他奇怪地问,什么事?
她说,你每次都怪怪地看这个招牌?有什么问题吗?
汪友金不好意思地说,没有没有,我喜欢看这两个字。
她笑着好像懂了他的心一样,说,你是不是把它当成你家莲花了,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呀!
汪友金咧着嘴,嘿嘿地笑,没说话。
莲花见他沉默不语,也不追问了,就转移话题说,这是我男人以前请广告公司做的,字裱得还不错。
汪友金对她男人还是有些好奇的,就问,我怎么没看过你男人呢,他……他是在别的地方做大事吧?
她笑得喘不过着气,说,是是,他是在别地做事!他是给阎王爷做大事去啦!
汪友金有些尴尬,说,你看我老是说错话,真对不起。
这有什么,不要紧!死鬼都走了两年了,要不是为了孩子,哼!
汪友金当然猜不到她“哼”的背后是什么,就跟着瞎嗯。
她转而说,我也有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上大学,不过上的是普通的大学,一年难得回来两趟。唉!做父母的就好像前生欠他们的一样!
汪友金说,也不能这样讲,毕竟是自个的孩子,我们不管他们,谁管他们呢?哟,我得走了。
莲花忽然脸就红了。她看着他,说,你急什么呢,怕我吃了你呀,你进来。
莲花转身把卷帘门拉了下来。
两人没完没了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汪友金走出她的屋子,来到外面宽敞辉煌的街道上,他忽然觉得北城很美很顺眼。他希望将来孩子们毕业了,也能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宽敞的楼房,成家生活,养儿育女。到那时,他还会选择回到老宅子过余下的生活。
5
北城南区建一个商业广场,工地规模很大,遍布许多深浅不一的基础井,很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仿佛在等上天的恩赐。
每口井上有一个三足铁架,井上的人把一只装满土的桶从井里摇上来,井的深度就长高一点了。井底当然也有个人在挖土,人在直径一米多的基础深井里,很像掉在猎人陷阱里的一只困兽。
现在,汪友金就是一只这样的困兽,不过他却很开心。他每天上班都尽可能穿有大口袋的衣服。他是这样想的,如果万一挖到宝贝古董什么的,他可以趁上面人倒土的工夫,把宝贝藏进口袋里,转天偷偷拿到古玩市场里卖掉,卖得好能顶一年半载的打工收入,孩子们的上学费用也就更有保证了。
他这绝不是异想天开,在北城这块土地的下面,曾经埋藏着一个非常遥远的王朝,那是一个被青铜器皿照耀得十分华丽的年代。在北城某一处工地上,曾经发生了一件大事情,类似事情的传播总是很有生命力。工地挖掘机挖到一堆宝贝,在人群愣神的刹那后,欲望就忽然神奇地苏醒了,大家朝宝贝一哄而上。这是一个罕见的陪葬坑,很多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虽然公安局介入调查,但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得到宝贝的人当晚就远走高飞了,他们的发财传奇却留了下来。
憧憬这样的美事使汪友金每天在工地上过得很充实,以至于每一个小时跟井上的人换班时,他总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从而使上面的人更加生疑。
上面的人就喊,汪友金!你怎么还不上来,是不是挖到什么宝贝了?
汪友金赶紧抓住绳子,屁股坐到桶上,上面的人把他摇上来。
他一上来,马上就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地面上的新鲜空气,他觉得站在地面上的感觉真好。
六点半下工,汪友金顺路去菜场买了点便宜的菜,他的脚今天在井里崴了一下,有些酸胀,索性奢侈一回乘公交回家。
汪友金有些累,他刚躺下来两分钟,在旧货市场买的二手诺基亚就响了,坐起来一看,是儿子秋生从西安打来的。接完电话,他眉头紧皱地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好像放一块大石头似的缓慢。
秋生学的是计算机本科专业,这个暑假里,他打算在西安一边做家教一边自学新教材。他很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对学习计算机课程非常重要,可一台最便宜的功能齐全的二手笔记本也得三千块钱左右。秋生说自己攒一千了,但还差两千。按说这钱不算多,孩子买电脑又是为了学习,这真的无可厚非。
汪友金读书不多,只是小学文化,但大道理还是懂的。汪友金搜遍腰包和积蓄,也只凑够一千块,还差一半呢。他郑重地想,无论如何,也得给秋生筹办好买电脑的钱,不能因为几个小钱而耽误孩子的前程。
6
第二天,汪友金整个上午都是在沉默中干活。中午吃饭时,他找到工头,赔着笑脸递烟。工头不大情愿地接过来,皱着眉头叫他有什么事快说。汪友金就吭吭哧哧地说了想提前支下月薪水的事,工头一听眉头立刻就皱紧了。
工头说,汪师傅,有些事你肯定不知道,其实我也有我的难处,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上边结钱也难得像吃屎!话又说回来,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来跟我提前要工钱,那工地还不乱套了!我每月能保证把钱发到你们手里就不错了,何况我现在手里也真没钱!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汪友金也想跟工友去借,可他脸皮薄张不了口,大家的境况也都不好。若为一千块钱回老家想办法,那非让村人笑掉大牙,况且他也没有时间回去。其实,一千块钱对于有钱人不过是一桩小事,可手头一直拮据的汪友金却为此犯了大愁,头都想疼了。
若真说起来,汪友金也算有两个说得上话的工友,可他心里明白得很,在一起喝喝酒吹吹牛还可以,如果真要提借钱的事,可能就会使大家都很难堪。
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小超市找莲花。虽然这一度使他非常犯难,而且,他也觉得一个大男人去跟一个女人借钱,那简直就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可目前的这种情况,使他不能再自私地照顾自己一钱不值的脸面了。
汪友金缓慢地走在街上,不敢看路人的眼神,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了他的心思一样。
在路过北城中心采血站时,汪友金忽然想起一位远房亲戚,他很早就是个卖血的专业户。汪友金以前看不起他,觉得那是好吃懒做的人才干的事。
可现在,他突然碰到困难了。他想,人身上的血就跟水龙头里的水一样,拧开淌出来不就是钱吗?他眼睛亮了,他不假思索地随意钻进了一个房间。
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有一些看着很金贵的仪器,两个正百无聊赖的医生一齐打量着这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男人,其中一个问,你要献血吗?
汪友金说,不,我,我要卖血!
两个医生面面相觑。清瘦些的姑娘尽力克制住笑,说,什么?你要卖血!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肯定搞错了,国家早就废除卖血了,现在提倡义务献血。
汪友金说,什么?义务献血?我还不知道。不过,我急需用钱,我想卖血。你们就允许我卖一回吧!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不是做卖血生意的!我卖血是为了我上大学的孩子能买个电脑学习!
姑娘甜甜地笑了,这是她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她耐心地说,大伯!不是我不叫你卖,现在卖血真是违法的,卖血很容易传染疾病,国家出了政策,提倡义务献血,不允许卖血。
另一个男医生说,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别说卖血,你就是要献血,我们也不会叫你献血的!我们一般提倡年轻的身体好的人适量献血,所以你请回吧。
汪友金非常失望,下医院台阶时差一点踩空。他的嘴巴干得像起了火,他的心里冷得像结了冰。
汪友金的心被烦恼和忧愁填得满满的,他慢腾腾磨蹭蹭地往塘埂街走去。
7
莲花正趴在收银台上,看见汪友金闷闷地过来,觉得有些奇怪,嘻嘻笑着小声说,大上午的,不做正事,你来干什么?
汪友金笑不出来,他望着莲花蓬勃的笑脸更说不出话来。
莲花注意到他脸色,说,老汪呀!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还拉得跟茄子似的,好像谁欠了你多少债一样!
汪友金说,唉!谁能欠我债呢?是我上辈子欠我的孩子们债了!我汪友金算是白白糟蹋自己这个名号了,我汪友金虽然过得不怎么样,但还从没为难到这个地步,这一回,居然就被这狗娘养的一千块钱给难住了!我……
汪友金坐下,说完来意,就不好意思看莲花了,挺高的人低着个头,像做了什么错事的孩子。
莲花说,不就是一千块钱吗!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别说你借一千,你就是借一万,我莲花也会借给你的。
汪友金蓦地抬起头,很冲动地握住莲花的一只手,说,莲花,你!你叫我怎么谢你呀!你我非亲非故的,怎么就敢借钱给我呢?
莲花说,这天底下的平头老百姓,有几个没有被钱的事咬过手呢?不就是一千块钱的事吗?我也是喝大青湖水长大的,别人我不信,我还能不信你吗?何况你借钱办的又是正事!
莲花说完,从柜台里利索地数了一千块钱递给汪友金,说,够吗?
汪友金不接钱,问莲花要笔和纸,莲花一听就明白了,她说,老汪,你要是写借条,那我可就不借了!说完,莲花佯装生气地把一千块钱硬塞到他手里。
汪友金接过钱,身体激动得竟有些抖。他着实没想到,这个令他十分头疼的钱事,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钱事,竟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汪友金说,莲花,太谢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你可别怪我瞎想,我们虽然是老乡,可我却是一个没什么能耐的人,也没帮你做过什么大事,可你却对我这么好?你,你不仅对我……好,现在又借钱给我,你是图我什么呢?
莲花说,老汪呀!你真想知道吗?
汪友金捏着钱点点头。
莲花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她突然有些吞吞吐吐的了。
过了一小会,莲花凝视着汪友金才认真地说,我觉得你不仅是一个好人,而且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救命恩人!特别是你脖子上长的这个黑痣!
汪友金摸摸脖子上这个曾令他烦恼过的痣,很奇怪地说,救命恩人?!
莲花说,是的,你长得的确有些像我的救命恩人!我上初中的时候,暑假有一次跟同村的几个女孩去大青湖边割草,我们热了去湖边洗脸,我想掐一个手边的莲蓬,谁知道没把握好平衡,脚下一滑就掉下了水,我越是扑通就越往深水里滑。她们没有一个会水的,就急得在岸上使劲大喊救命……
也真巧,有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听见喊声,急忙跑过来跳进水把我给救了上来。要不是他,我可能就淹死了。他水性真好,一只手搂着我,另一只手还能划水往岸边游。我当时晕乎乎的,但我能感到他的劲很大,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黄豆般大小的黑痣,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就跟你的这个一样,位置也差不多……
你肯定不会明白,人在临死的时候,其实是最清醒的……
那个小伙子看我只是呛了几口水,没什么大碍,就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
我居然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我后来就常常做同样的梦,梦见他紧紧搂着我,梦见他脖子上的那颗黑痣,我就想,如果我能嫁给他就好了……
汪友金当然对大青湖熟悉,那时他还跟父母住在一起,房子离大青湖也不远。大青湖滩地,土肥草盛,常有近村远村的姑娘来这割草。当年,汪友金确实从大青湖救上来一个女孩,而且,他在听完莲花语无伦次的陈述后,已经完全可以确定,眼前的莲花就是当年被他救上来的女孩。
汪友金听着虽然一言不发,但他的心里却早已澎湃激越,浪花飞溅了。
汪友金沉静下来,他告诉莲花,那一年,他确实知道有人从大青湖里救上来一个女孩,那件事非常轰动,报社都来采访了,却没有找到那个小伙子。有人说那小伙子是南安师范的学生,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游客,是偶然来大青湖玩耍的。
汪友金说,真没想到,那个小伙子救的人竟是你!可我怎么会是救你的那个小伙子呢?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是夏天,大青湖里满是绿色的荷叶,开满了白的红的莲花……
莲花说,是的,就是夏天。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夏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夏天呀!
大青湖有一种莲,叫并蒂莲,开在湖的深处,平常很难见到。大青湖能盛开多少莲花,周边的村子就能有多少叫莲花的女孩子。可见,大青湖畔的人给女孩起名字是很懒的。
汪友金看着莲花眼里的失望,说,那你忙着吧,我走了,我这就给秋生寄过去,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耽误了他的学习。他把钱装进贴身的衣兜,又用手压了压,然后,才在莲花沉默的注视下离开。
汪友金走在去邮局的路上,心里已从早上的冰冷变得温暖起来,脚步也轻盈从容多了,两只手臂有节奏地甩动,好像一双将要振翅飞翔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