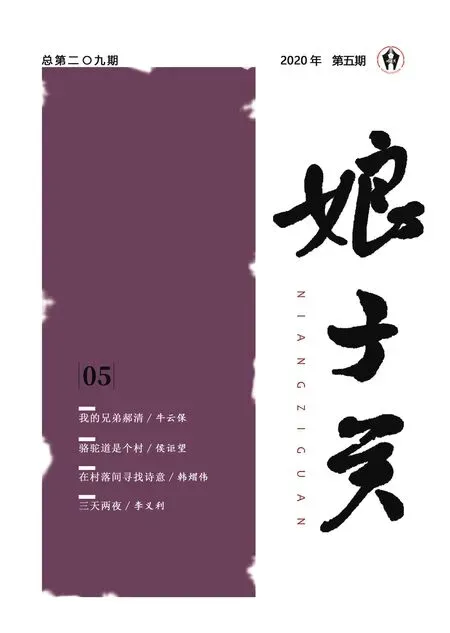父亲是把伞
张青山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天阴沉沉的。大伯说:“赶紧找把黑伞,撑在窗户外”。
按照老家的习俗,家中有人去世,如果遇到雷雨天,是需要在窗户外撑把伞的。至于原因,有的说是怕打雷惊扰了亡灵,也有的说是怕雨水淋湿了亡灵的归程。
“我不怕”
七月初十是母亲的生日。每年我们姊妹几个总是要准备一桌子酒菜,包点饺子来庆贺一番的。但2019 年的这一天,父亲病重弥留之际,实在是没有心情。就在这一天的凌晨两三点,一直处在半昏迷状态的父亲,忽然说了一句:“来,我下去一下”。口齿伶俐,声音还异常地洪亮。我问:“爸,您是要小便吗?您不用下床,给您插着尿管了。”父亲说:“那你扶我起来坐坐”。我就有一种特别不祥的感觉,难道这就是人们说的“回光返照”吗?
父亲坐了十几分钟,又想躺下了。我和弟弟一左一右躺在他身边,竟然聊了半个多小时。我说:“爸,我这几天感冒了,会不会传染给你?”父亲敏捷地回应说:“那谁知道呢。你就躺着吧。传染给我,我也不怕”。
“我不怕”。这是近段时间来父亲说的最多的话。这话,前段时间我一直引导着父亲想让他说出来,更想让他真的不怕,让他坦然面对病情。但此时,他真的说出来而且反复说了,我反倒觉得鼻子发酸,喉头哽咽,泪如雨下。
2018 年秋冬,父亲就常说,最近看着点活就愁得不行。火炉也不待生、饭也不待做。你妈妈老是这个样子,整天喊着嘴疼嘴麻。这光景,愁了。后来他又老说,背痛、小腿浮肿。当时我们害怕是心脏不好,赶紧联系医院去看看。原本我是想联系市立医院的,父亲说,那么远,折腾啥。就近在郊区二院看看吧。如果不严重了,输完液咱晚上还能回家。你妈离不了人。
母亲是2016年正月十六脑出血的,落下了腿脚不利索、面部神经受压迫的后遗症。这几年,白天晚上,生火做饭,洗洗涮涮,伺候病人,全靠父亲。我们兄妹三个,很多时候就是周六周日回去转转看看,帮忙做顿饭,偶尔住一晚上。父亲说,你们都有营生,要先把工作干好。回来的人再多,也替不了你妈的病。我一个人行。每次回去,父亲除了说这几句话,就是埋怨我们买的东西多:“贵巴巴的,花这么多钱,干啥?”
父亲在二院住了一周,背痛有些缓解。眼看着腊月二十了,父亲非得回家:“人家都过年呀,咱老住在医院干啥?”咨询医生出院的事,医生说:“你爸这个血液指标异常,一天和一天的指标都不一样,这应该是还有别的什么病了,要不你们再到市立医院去看看。”
父亲是坚决不去的。他的理由一是要马上过年,二是刚从二院出来再去一院,不嫌丢人?我说服再三,才勉强同意去一院抽个血化验个指标。指标挺正常。我的心里放心了大半。心里还对二院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的看法。
父亲还继续伺候着母亲。村人都说,母亲命好。小时候在娘家,有外婆照顾,我们兄妹三个小时候的衣服,几乎都是外婆来给做的。结婚后,有父亲照顾。家里每次来客人,都是父亲操刀掌厨,母亲也就剥葱捣蒜打打下手。每年过年前家里蒸馒头,母亲只管捏,还只会捏馒头,花糕都是父亲捏。而和面、生火、拾锅等这些既累还需要些技术含量的活儿,都是父亲在干。
六月下旬,父亲突然说肩膀疼得厉害,他怀疑是不是晚上没关窗户伤风了。自己鼓捣着拔火罐贴膏药一周也不见好转,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做饭时锅里加上水都端不动了。这才叫我们回去。
背疼?肩膀疼?食欲不振?身体消瘦?血液指标有过异常?大夫听完这些就说,赶紧住院全面检查。抽血、拍片、心电图、各种的彩超、核磁共振……最后做的骨扫描结果,让我们感觉到了晴天霹雳——骨髓瘤!
刚开始住院,父亲经常问:“检查结果咋样?医生咋说?确诊了啥病?”。过了几天,父亲又说:“如果查出来是大病,不能治咱就不治了。你妈还需要花钱。”又过几天,父亲又说:“如果是不好的病,到时候不要弄那些切气管之类的,咱回家……”每说一次,都使我们心如刀绞。
“瘦了俺孩了”
我们刚开始一再对父亲隐瞒病情,只说是贫血和骨质疏松。但是我们焦急的神态、悲伤的眼神,其实父亲早看出来了,心里也有了些准备,只是没说而已。有一次父亲睡着了,邻床的一个陪侍大哥对我说:“老人心思重了。你们不在跟前的时候常说,我这次看来是大病,我看见孩子们的眼神脸色都不对。”我们一再说是血液科,是严重的贫血加严重的骨质疏松。父亲勉强苦笑说,好吧,就算是吧。
我的心情悲伤到了极点。一方面不断通过熟人朋友咨询最好的治疗方案,一方面也心里嘀咕,父亲还能撑多久。一年?半年?那段时间,我眼睛永远是红的、心情糟糕到极点,食之无味、夜不能寐。勉强入睡,总是梦见小时候的情形。
父亲的勤劳节俭在村里是有名的。十三岁就给生产队放羊,十八岁就赶毛驴车,二十几岁到了大队的副业队挖矾石。三十岁时,顶替在硫铁矿退休的二爷到硫铁矿接班当了矿工。一辈子辛辛苦苦修起了两串院子。第一串是和爷爷奶奶大伯大娘一大家时共同修的三眼窑洞。那段时间生产队下工回来,中午午休时间就拉着平车出去拉石头。第二串是我20 岁的时候修的四眼窑洞两个配房。从打石头、烧石灰、扣砖坯、水磨地,能自己干的都自己干。用村人的话说,就是路上碰见块砖头也要捡回家垒在墙上。
我和弟弟轮流在医院陪侍着父亲。刚用上靶向治疗药物的第一周,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骨头不疼了,肚子也不憋了,食欲也好了。清晨甚至还自己在床头柜里找干馒头片吃。父亲说:“这个科比那个科水平高!有效果。再过几天咱就回家慢慢调理吧。买点牛肉、猪肝,每天吃个三五块。”我一听此话,当即就到超市买了小包装的牛肉回来,每顿吃饭带两块。父亲喃喃地说:“这多少钱?贵了吧。”我们也信心满满,期待着一个疗程治疗结束后可以回家休整一段时间。
我不间断地给父亲打预防针、说宽心话。因为母亲说过,你爸的心太小,只有针尖那么大,凡事看不开,想不开。好长时间以来,我也觉得父亲的节俭近似乎小气。每次切菜都要留一点,说只有讨吃的才不攒余粮。
父亲最奢侈的一次上当消费是在三年前。那段时间他睡眠不太好,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母亲脑出血后,变得很懒惰。凡事都叫父亲。一会要喝水,一会要下地。甚至铺床脱衣服都要叫父亲帮忙。有一次回家我看见了一种保健品,才知道是有人找父亲推销,说是治疗失眠、调节血压、增强免疫力。父亲没有经得起再三忽悠,花了1500元买了三瓶。我就不止一次地劝说父亲以后不能再上当。说的次数多了,父亲终于说了一句:“我也是想好了。万一顶事了?我要是身体好一些,能够单独伺候你妈,你们不也省点心?”
到后来的几天,父亲烦躁得更厉害了,胡言乱语。而且,常用手去拔输液管和氧气管。我们只能在输液的时候紧紧攥着他的手。有一次,我感觉父亲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准备出去打壶热水。我说:“爸,你别动,我出去一下。”父亲说:“你去吧,我不动。”就在我起身的一瞬间,父亲一把拉住我的手腕,眼睛里是那种心疼和爱怜,说:“瘦了俺孩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属于那种比较冷酷的人。母亲也常说,你爸可是凉了。你出生都七个月了,都能在炕角站住了,他都没抱过你一次。这一拉,我才感觉到父爱不仅是经常抱你那么简单。
我想起1992年秋天,村里要选派4人去辽宁鞍山钢铁学院学习耐火材料技术。当时的条件是,不发工资、食宿自理,学费村里出。我当时在矾石矿干活,每月的工资在400 元左右。不发工资加上食宿自理,这一年的收入要差6000 元左右。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我当时就怕一向节俭的父亲不同意我去。不料想父亲的爽快出乎我的意料:“去。去了好好学。今后在耐火厂当技术员,咋不比你在矾石矿拉平车死受苦好。”
“关上窗户,你怕冷”
七月初七那天一早,父亲的状态越来越差,肚子憋得厉害,甚至都不能自主排小便。大夫说,没啥办法了,只能再插胃管。插了胃管下去,立即就看到了吸出来的血。医生说,这种病到晚期就是内脏出血,赶紧回家吧,好让亲戚朋友再见最后一面。
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前几天还指望着父亲能熬到过年。回到家里,父亲牙关紧咬,双目紧闭。我在耳边轻声问:“肚子还憋吗?要不要给您插尿管。”父亲微弱地说:“哦。你出去啊。”
父亲的意思我懂。他同意插尿管。还要我别在跟前。前段时间在病房做穿刺抽骨髓化验的时候,大夫说只能留一个家属。我抓着父亲的手,看着护士在父亲的腰椎部拧进去一个螺丝管,随后又用很粗的针头抽出来骨髓、涂片……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就瘫坐到地下。护士们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脸蛋,我才醒过来。事后,父亲说:“你有这毛病,以后我做检查时候,你觉得害怕就别在跟前了。”
临近晚饭时分,父亲缓了过来。我问:“爸,这是哪里?”父亲说:“这不是咱住的那里?”。父亲没说,家。现在父母住的,是过渡房。村里近年来搞新农村建设,旧村开始拆迁,村里的政策是,谁家愿意先上去住过渡房的,可以报名去。就在2019 年春节前,父亲说,咱也报名上去住几天楼房吧。因为是过渡房,村里不让搞装修,墙是毛墙,地是毛地。父亲前段时间还叨叨,要是铺铺地、刮刮家,置办些新窗帘,这就像回事了。
父亲还坚持要下地走走。我和弟弟一左一右扶着父亲在房间里踱步。父亲一会儿看看厨房,一会儿看看卫生间,一会儿再看看卧室。不说话。呆滞的眼神中更多的是留恋和不舍。我扶着父亲在沙发上坐定。他竟突然抓了一个茶几上摆着的炒豆角,往嘴里塞。二十几天没进食了,他是多么渴望吃点东西了。
父亲还是东张西望。忽然对着坐在身边的母亲说了一句:“关上窗户,你怕冷。”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母亲脑出血后,因为供血不足,老觉得冷。原先在老家院子里住的时候,父亲总是把火炉子生得旺旺的。现在是8 月份,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冷的。父亲的潜意识里,看见开着窗户就首先想到的是母亲怕冷。
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过来探望的络绎不绝。父亲醒着的时候,还可以清晰的叫出他们的名字,虽然声音很微弱。有时候看见来人,也会坚强地微笑一下。那几天,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唉,没办法。”
七月初十中午一点多,父亲好像又睡着了。但我听见他呼吸频率越来越慢,手脚也开始发凉。我赶紧把一家人都招呼过来。我们流着泪,给父亲穿衣服。我还在耳边问“爸,你身上疼不?难受不?肚子憋不?”父亲气若游丝地回答,不。我问,你还有啥交代的?父亲最后说了句:“别让……你妈……受了罪”。
父亲走得很安详,眉头都没皱一下。像一只燃尽的蜡烛,弱弱地停止了呼吸。
守灵那几天,我一抬眼就能看见窗户上撑着的那把伞。伞是挡风挡雨的。没有伞,风雨会直接浇在身上。我忽然觉得,父亲就是那把伞,遮挡了一切压力、痛苦,包括死亡。自此以后,这些,都需要我自己独自面对。
我是无神论者,知道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但面对父亲的去世,每每回想起来,都热泪盈眶。只有在繁忙的工作中才能暂时缓解一些。即便是在工作中,我也常常想起父亲。他曾经说过,你这都是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考上了公务员。你要好好给国家做事情,不要嫌苦嫌累,不要计较得失。要对得起国家每月给你发的工资,不能给家人和亲戚丢脸,不能白活一辈子。
也许,父亲去世的伤痛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弱。但父亲说的这些话,我会铭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