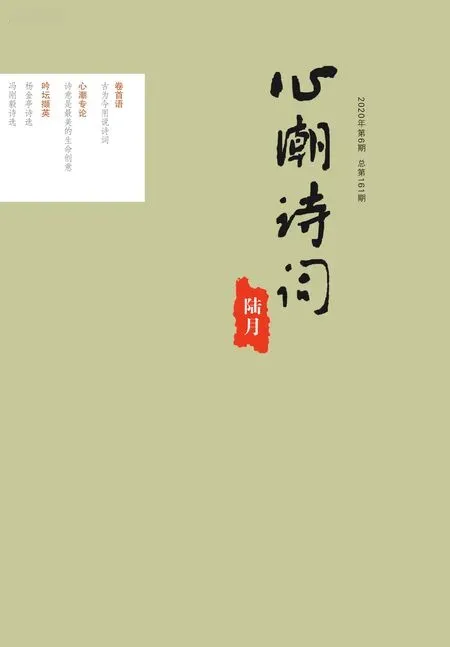经·史·世:劳思光的思与诗
秦燕春
一、经史、经世之思
劳思光(1927-2012)先生不仅是当代具有相当名望的哲学专才,①本名劳荣玮,1950年发表《从文化史上看国家价值》后以笔名“思光”行世。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台湾大学哲学系。曾长期任教香港珠海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台湾清华大学、东吴大学、华梵大学等。劳氏积二十年之力而成《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业内影响昭昭。晚岁荣誉甚多,包括入选台湾中研院院士等。参见《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本文所引劳氏诗词作品均出此书,节约篇幅起见,以下不再一一标注页码。也擅长文艺,善琴能诗,甚至因此被海外学界指为“既能用清晰精严的笔法撰写传世哲学经典,又在诗作中表现敏利的诗作情怀”的近当代中国哲人中的唯一人选。②参阅蔡美丽《百年风雨催诗笔,江湖何处托钓矶——读思光先生诗作有感》,《万户千门任卷舒:劳思光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0页。这首先自然基于家学渊源。劳氏出身世家,母氏亦为衡阳巨族。高祖劳崇光(1802-1867)曾任清同治年间的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代表清廷签署过第一次九龙条约,③参见劳氏1950年存世第一首诗“题解”,《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1页。《清史稿·列传》称其为人为政“沉毅有为,不避艰险”。此所以劳氏自谓“自承庭训,早学讴吟,及长后亲历丧乱,郁郁终年,遂每以诗词自遣”(《韦斋诗存述解新编·序》),故虽余事为诗,却著作颇丰,生前即整理出版了《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其诗作之艺术特色与思想精义亦颇有专文分析发覆。在经由“哲学诠释、文化批判、诗艺探索”三者复合而成的劳氏形象中,④三者正是2007年劳先生八十大寿学术会议命题(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台湾华梵大学哲学系合办)。《万户千门任卷舒:劳思光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中颇有收录,兹不赘述。诗艺不仅占据了三分天下的相当分量,更可能赋予了前两者沛然直呈的生命厚度。诚如劳氏在《思辨录:思光近集》序言中的自我告白:
若就我内在的气质与心态讲,我实在并非一个学究式的人。即以从事哲学研究而论,我并不是像现代学究人那样一味只重视外在表现。反之我所真正关切的是我自己所见到的理境及所达到的自我境界。我治学之基本目的在于自己的所成与所得,至于对外表现只是“余事”。……我所关切的哲学问题,本是哲学现有的危机问题,与未来的希望问题。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转引自彭雅玲《开创诗歌抒情传统的新猷:劳思光先生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思》,转引自《万户千门任卷舒》,第398页。
基于这一旨归,故虽一生多数时间栖身海外,劳思光的哲学理念毋宁仍是非常“中国”的,或者说,亦是颇为“古典”的:从不单纯视哲学为纯智性的概念游戏。而是认为哲学最重要也是最崇高的功能在于达成生命本身的转化。就个人而言,这是成德之路及生命境界的升进跃迁;就集体而言,这是人文建树与文化成果的开拓累积。因此兴趣焦点,劳氏方才特敏于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人文主义者”“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1909-1978)先生于“当代新儒家”中为能“如实完成功夫论的体系,并以成德功夫的境界,视为终身奉行不懈的学人”,①《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337页。唐氏之评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第6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更在唐先生身后以“赤手争文运,坚诚启士林”“平生弘道志,成败莫轻疑”的敬仰恳切之言凭悼之。②《唐君毅先生挽辞》(1978),《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331页。关于唐、劳学术异同,参阅陈旻志《自我境界与“圣”“人”接受模式的贞定:劳思光“文化整体观”与诗学中的文化人格图像》,《万户千门任卷舒》,第514-516页。
也因此,对于劳先生这类气质的哲人,切入其生命内核的精稳之径,可能最佳选择并非哲学表诠,而是诗学表达——后者更直接、更整全、更现量直呈。尤其后者本为作者毫无“立言”“不朽”之显性意识的日常书写、生命实感,③《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共收入劳氏诗作263首。包括挽联5则以及少作数首、新诗一首。即使犹有遗珠,也不会太多。劳氏落笔谨慎,不少年份只有一组诗流传,均衡地分布于其生命自然流程本身,可见对劳氏而言这一诗性书写的本真性,无论从诗词内容还是写作场景,都可看成自我表达的素朴需要,既无“应世”之实用、亦无“名世”之企图,大抵只是基于诗礼传家的古典训练以及劳氏本身颇富艺术气质的生命形构。其得以整理出版基于偶然,所谓“晚年再来台岛,授课华梵,中文系王隆升、林碧玲诸同人以为数十年中感时忧国,言志寄情之作,亦可以持赠后人”。另请参阅王隆升《论韦斋词的生命情怀:以感伤为基调的呈现》,《万户千门任卷舒》,第486页。于中往往更少做作、虚饰之嫌。
一如劳思光《挽殷海光先生诗序》中所叹,“乃值正学之消沉,谁能免弊”,④此文为残稿,约作于1069年,收入《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459页。每个人都未必能轻易冲出自己的思路所限与时代共业,劳氏之思与诗亦如此。其关于中西文化、国运政局的裁断与取态是否有其偏颇,不在本文的关注视域。又如劳思光《挽胡适之先生》联中所称,“肯以大名投世网”者本身就是担当,“莫从细务议清流”于是也往往需成为衡文诛心者的必要的修养。⑤联见《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454页。六尘世界凡有所向、凡有所立,即难免于偏、难免于限。甚至即使作为中国文化基石的六经之学,一旦落于名实亦未免其弊。《礼记·经解》引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此在义理精审的劳先生,自然洞察其微。故《萧箑父自武大寄诗,以二律答之》(1989)中其明言自知“理境无涯”而选择“文章有限”:
平生进学拟登山,踬蹶徘徊只等闲。
残景丘迟空怅望,彩毫郭璞久追还。
无涯理境归言外,有限文章付世间,
成坏华严参胜解,不妨替鸟听关关。
真理如如离言绝思,但仍要有所言说。此正劳氏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中至为关键的“引导”(orientative)意识、“承担”意识。①参阅陈旻志《自我境界与“圣”“人”接受模式的贞定:劳思光“文化整体观”与诗学中的文化人格图像》、黄冠闵《飘零乎?安居乎?——土地意象与责任意识》,《万户千门任卷舒》,第277-308、511页。也因此使得治学特为强调“陆王学上望儒宗”(1960年《春兴》)的劳氏之学同时呈现出奇异的“与世为体”的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性格——“与世为体”本为明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顾先成、高攀龙“东林学风”的裁定,世间俗儒亦颇有以“东林”之学为宗程朱而诋陆王者。此处劳氏之两取,则不仅可以史为鉴,亦可以之鉴史,更两相形构了劳氏之诗的基本特色。
二、经史、经世之诗
劳思光性格中理性很强,②最典型的表现,可谓1957年其父在台去世,劳氏羁留香港未能返回治丧,作为家中独子,其痛可想,是年《丧中作》,其节制力之强,即落实为“伤心无泪无言际,泣涌方知是俗丧”,《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52页。兼之业习所聚,其喜作性理之诗并不意外,但其性理之诗能大体可读、不至沉闷、甚至不乏精彩,原因就值得探究。盖因“性理诗”易落理窟,其头巾气冬烘气、涉典重重常至拒人千里之外,诗家开有此派以来,读者的抱怨可谓史不绝书。何以韦斋诗喜谈性理而能避开理窟,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三。
原因之一,即“经史互映”的诗体结构。韦斋诗整体构成不仅有很强烈的个人自传色彩,而且成功地将此一己悲欢容纳进家国兴亡。正因劳思光系出名门,长于望族,也就最为尖锐地遭受了近代之变中的风吹雨打王谢无家: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毁性转型、甚至沦失。此即频现于其诗中的“兴亡身世两难论,万感茫茫步日昏。同辈宗支余二客,殊方岁月长诸孙”(《己酉初秋,晤伯兄于洛城,共步街衢,闲话旧事,归成二律》)。“曾是重门严戌卫,岂期白首走风尘”(《旧游杂咏》,2002)的隔代衣冠之怅,多少还是深藏于他的生命底蕴,其诗词中与生俱来的清华清贵,大抵也是如此。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原本寥廓杳渺的历史悲欢也因与一家一室的具体遭际融为一体而获得了格外的动人之力。1969年陈寅恪去世于广州,此年初春在美国普林斯顿访学的劳思光很可能听闻了此讯,于是写下《日暮独步忆寅恪先生诗有感》:
昔传陈叟伤春句,灯火英伦感岁华。
我亦孤怀当去国,谁容大难更谋家。
五年奇劫乡书绝,一枕危楼鬓雪加。
兴废待争风雨急,黄昏旷野立天涯。
诗中提到的“陈叟伤春句”,即陈寅恪于抗战胜利后赴海外治疗眼疾写下的《卧病英伦七律二首》之二:“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③转引自《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240页。
《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前有短“序”,据作者自谓作于“辛卯小寒(2012年1月)”的“台北客寓”,距离本年秋冬之际劳氏去世已来日无多。此种终身为“客”他乡的深层悲慨则是涵纳于劳氏作品的普遍之情。在其离开台湾三十三年之后首次返回任教之初,1990年写下《庚午中秋,与清华诸生登人社院高台望月,口占一律抒怀》,此情就溢于言表:
恰似坡公远谪身,随缘樽酒庆佳辰。
讵知入海屠鲸手,来作登楼望月人。
箫管东南天一角,槐柯上下梦千春。
衰颜苦志茫茫意,剩向生徒笑语亲。
台湾不是家乡。他供职与生活时间最久的香港又如何呢?且看2001年的《新正
即事》:
满城火树岁华新,小案瓶兰一室春。
逝去悲欢余自笑,归来花鸟尚相亲。
诗肠久涩无奇句,世味多艰念故人。
万里梦回关塞路,清歌渺渺最伤神。
如何在清醒地认知到“共业”——深察种种现实苦难为我人不可逃避的历史债务之后仍然拥有精神出路的可能,即超越即承当,对于哲人而言,永恒回归往往有着特别的管道。但对于纵横“经史”而又不忘“经世”的劳氏而言,大地上的故乡其实并不遥远,只是拘于现实种种他的“返乡”一直受阻。此即1999年《戊寅岁暮感怀》中道出的心曲:
厌看群儿较重轻,残书高枕度深更。
世途九曲成何事,人海孤行竟一生。
观化夙知身是患,忘言方契道无名。
前宵梦觉中原路,冻雨玄霜满凤城。
又七年之后,写于2006年的《丙戌七月,返港小住,与生徒闲话,偶成一律》,劳氏已经年近八十,却仍然“兴亡”满目:
赵州行脚不知休,且向香城问旧游。
充尔缶鸣谁解事,惊心潮急又临秋。
衰癃久失回天志,客寄还分覆鼎忧。
尚述兴亡供史乘,平生怀抱此中留。
经由劳氏的哲学研究、历史批评、文化论述三者互为犄角形构起来的责任意识,①参阅黄冠闵《飘零乎?安居乎?——土地意象与责任意识》,《万户千门任卷舒》,第277-308页。使得其诗作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兴亡”意象——据统计,劳氏诗作中关怀国族命运、文化前途的词汇,诸如“兴亡”(14出)、“兴废”(8出)、“剥复”(2出)、“剥极”(1出)——之类,②另如出现频率同样很高的“世运”“成败”“是非”等,兹不赘述。参阅彭雅玲《开创诗歌抒情传统的新猷:劳思光先生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思》,《万户千门任卷舒》,第399页。就并非是一种理性的冷眼静观,而是成为一种“继绝兴亡”的行动的导引,并不单纯指向中国文化的路向、更指向世界文化的发展。此即“韦斋诗”虽躬自高标而特能动人的秘籍所在。他到底是热的,尽管是潜流。
劳思光不仅直接创作了大量“咏史诗”,③例如《读宋史绝句》,《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193-194页。在许多表达性理思考的诗中,他亦会直接渗入历史的乃至当下的相关描述。这一书写风格使得他偏好和擅长的性理思考格外有了“道成肉身”的特别趣味。例如《己酉初秋,晤伯兄于洛城,共步街衢,闲话旧事,归成二律》(1969)之二:
未须司马诮形神,讲席消磨十五春。
权实漫为贤首判,圆通差免契嵩嗔。
尚怀饥饿群生劫,肯羡逍遥独乐人。
高歌花灯如此夜,不堪故国正烟尘。
“权实、圆通”一联说的是极为冷僻的华严判教的学术话题,因为揉进个体经历(“讲席消磨”)与家国悲欢(“故国烟尘”),通体即显得颇为圆活自在。1979年劳氏积二十年之力完成《中国哲学史》,该年留诗三组六首。其一即《己未孟秋,史稿既成,夜坐无聊。偶成一律,即柬端正》:
故纸堆中暂息肩,青灯独夜意茫然。
信知正学常违世,坐见横流竟拍天。
牛马任呼随俗例,风云变观感华年。
伊川逝后思杨谢,何日寒斋一论禅?
“端正”即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弟子,亦是曾经全香港最穷的大专院校新亚书院哲学系第一位学生。①所谓“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出薪水,学生缴不出学费”,此正是彼时钱穆、唐君毅等人“赤手争文运”的现实基础,参见《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336页。本为学人书斋论学的“体己诗”,因为作者对于世俗横流的操心与敏感,经由宋儒家风与当代学术的挂搭,其无论历史时间的图像还是现实空间的图像都丰富具体起来,诗,也因此避免了枯槁滞涩。收到唐端正期待其“道义担承仗铁肩,领袖群伦莫恋禅”的步韵之后,劳氏写下了他性理诗中颇为自负的性理境界:“迩来渐证圆通理,万户千门任卷舒。”以及同年《山居即事》中的“频年勘破升沉理,始信伊川境始安”——“礼境”与“乐境”,“理”与“情”,至此豁然贯通。②伊川即宋儒程颐,生平以严谨著称,时人好奇其终生守礼是否劳苦,伊川则以守礼为至乐之境。参见《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345页。
韦斋诗好言理境而能不落理窟的原因之二,笔者认为,与劳思光有意无意间在唐宋之辨中的折中取态有关。
中国传统诗歌现象中的唐、宋之争是显题。大抵而言,劳氏之诗常被归入理则瘦硬的江西宋诗一脉。目前针对韦斋诗的研究基本都保持了这一定位,兹不赘述。劳思光本人在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曾直呈其对两家诗风的断制好尚,兼备“理境与技巧”的宋诗的确更为其称赏。究其极则,劳思光作为甚为看重和追求生命转化的哲学人,看重和追求的诗意同样是“精神意”。唐宋诗间的文学旨趣,可以他经由哲学立场提倡的“情意我”与“德性我”的关系贞定:只有“德性我”重建文化秩序的生命感受,才值得成为“情意我”艺术表现的大宗要点。③林碧玲《劳思光“韦斋诗”的喜情乐境》,《万户千门任卷舒》,第423页。众所周知宋诗的绵密深雅实得益于晚唐不少,但劳思光在同文中不惜贬抑晚唐体的代表作、李商隐的“纯美诗”,认为“只算一种技巧成就,并未表现一艺术精神”,而对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更多推崇肯定,因为后者才能体现“诗言志”的“道德性情意”的悠久传统。此论虽未必能深入玉溪三昧,却颇可备一说。劳氏甚至因此“精神”的不足,而对历史上的词的表现不如诗而另有微词。④劳思光著《中国文化要义新编》,第23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但劳氏于诗艺毕竟有天赋的敏感与体贴,他深知理境亦需要“技巧”来呈现,性理之美如何得以可触可摸的立体表现,而不至流为面目可憎的魔道。笔者以为,劳氏之诗用典绵密而意象丰沛,其实颇得益于晚唐,尤其李商隐。如1954年的《步韵再答闵生》:
兴亡历历问春秋,梦断江南结绮楼。
末世文章哀鹏鸟,中宵风露望牵牛。
共成幕燕谁谋国?辜负沙虫尚荷邱。
却笑张颠非绵句,碧纱满壁转生愁。
无论诗中典故还是结构光色,与其强分唐、宋,不如但赏美文,虽然劳氏更以清通胜出。类似的还有1959年赴港之后的《寄台湾友人》:
次公无酒亦轻狂,囚垢高谈薄玉堂。
十斗分才多白眼,三更得句豁愁肠。
师儒稷下讥荀况,孽子淮南祸辟阳。
日暮浮云莫回首,长安原不是家乡。
殊为有趣的,劳氏惜墨如金的“韦斋诗”中居然保留了十三首《无题》诗。绮情流丽窈眇也是不容遮蔽。“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二),此正劳氏自谓“内在气质与心态并非学究”之佐证欤?
可为这一渊源做一佐证的,尚有劳氏伯兄劳榦(贞一。亦是中研院院士、史学名家)在汉简研究之余,尝于1958年发表《李商隐诗之渊源及其发展》。二劳关系甚密、更多唱和之作,①“庚子冬,伯兄贞一拟过港小留,嗣因签证不顺而作罢,惘然有作”中,劳氏特意提到劳榦的研究“阙文遍注流沙简,逸兴新征锦瑟篇”,《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第117、486-488页。即使劳思光在理性上排斥玉溪体,其风调之潜移默化,却未必无之。对于稔熟玉溪诗的读者,韦斋诗用典乃至用韵的习惯,都与玉溪诗有着频度极高的呼应。篇幅所限,此处暂不展开。
可为这一心性再添冶容的,则与韦斋诗常有心思绵密的写情咏物之作有关。不仅“无题”之情不算稀见,“有寄”之物亦甚可观。例如作于戊申年(1968)的《碧玉》。诗前特有小序以状其情:
寓所不远,有小院植碧桃一株,横枝当风,色作微红,虽秋日无花而风姿可喜,车过见之。明日往寻,则重扉深掩,竟不得复见矣。诗以记之。
碧玉真怜出小家,不披绮绣自风华。
轻车夜过香侵梦,半臂秋寒色映霞。
嫩叶有缘承雨露,坠英无奈辱泥沙。
桃源忽失渔郎路,惆怅长街起暮鸦。
怜花惜玉之浪漫情怀并不常见于一般宋诗派门下。而在劳氏诗笔,这种情调非为仅见,其在早岁亦有同题之作、同类行径。此即作于1958年的《乌夜啼》,词前同样有小序:
儿时居故都,庭中玉兰经雨零落,辄亲拾之,不忍见其委泥沙也。戊戌流寓香岛,忽于友人处见玉兰满枝,感而谱此。
闲庭曲槛流霞,旧时家,记得雨中亲拾玉兰花。 红羊劫,青衫客,负琼葩,一样可怜颜色在天涯。
这一惜怜之情,指向落花,指向流人,更指向“花果飘零”中而能“灵根自植”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因劳思光在宋体唐韵之间无论用典意象还是情意倾向经常都在暗度陈仓,韦斋诗方才具有了虽瘦硬而不干枯,嶙峋之骨常现膏腴之姿的意态风姿。也因此他似乎比号召“宋骨唐面”、兼采“晚唐北宋”的晚清“同光体”的多数诗人,更为入流出色。
三、结语
劳思光个性狷介,亦颇自负,三十而立之年的《答友》(1957)中有谓:
平生学不守常师,少日虚声只自嗤。
稍解诗书于画拙,难争德爵况生迟。
百家出入心无碍,一海东西理可知。
花鸟渐怜催老大,人前何意斗华辞?
对于纳中国于世界、纳中国文化于世界文化,实现“圣人无常师”、出入百家、东西同理意义上的自由愿景,可以说,他坚持了一生。此所以戊子(2008)年集中收入最末一诗,“严寒卧岛城,更休说河清”的暮色垂老中,他犹自矜持于“余年矜大节,垂暮畏浮名”,此正与集中收入最早一诗“书生清节霜为骨”遥相呼应。钱锺书先生尝谓老辈以哲理入诗者,惟静安(王国维)最为如盐入水(其他人则如金屑在眼),一卷韦斋诗,亦可当此语。
——劳氏立克次体的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