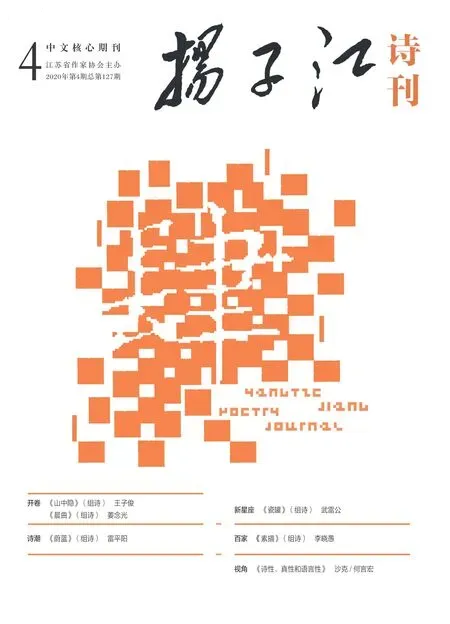旋转木马(组诗)
王彻之
卡吕冬狩猎
来自大都市的希腊神像们
缺少它的幽默。海闪烁釉光,
拉奥孔的蛇缆索般,垂入地平线
拖拽着这颗冰冷行星;
而半裸的维纳斯,如水手观测着风,
通过她在海浪阴影下
咸湿的目光想象群岛有多远,
如何与大陆保持间性联系,
尽管断断续续,风格却必须
连贯;像批评家们对我们的欢乐
呼出的泡沫偏爱泰然处之——
可无论是对你从它陨石般的脸上
瞥见的那无数因狂喜而战栗的流星,
还是在公里的加速消亡中,
对它生活波浪上鱼跃的呼喊
和马刀般弯曲的臀线,以及原始风度来说,
美,和它的悲剧性,一旦被确认,
就必然认同我们既是观众,又是它的发生之地。
旋转木马
虽然圣诞集市结束得
比去年更早,但在集市尽头
小蒙古包似的木马棚下,
几匹错落有致的、上下移动
而彼此沉默无声的马,其感情
似乎全靠轴承相连。在夜晚
鼻翼吐着热气,在上釉的前腿筋腱,
光滑得让人想到爱奥尼式立柱,
与佯作奔跑的后腿间,它们的锁子甲披风
几近溃烂,残破如视力损坏的渔网。
从它们鳕鱼似的小腹刺入
然后冷冰冰地,在既定的法则下
围着星空旋转的遥杆,看起来
就像骑手在风中解绑的心灵
由于战争来得太快,而来不及
与之达成共识的小天使手中抢来的。
而当木马停止了,它们也不肯
在你轻易踏出圆圈半步前失去亮度,
反而在冷风中,让四蹄的黝黑
消耗在激情远超其忍耐的空气里。
激情在这里是无意义的,像海滩的木马。
当习惯这种惊奇,它的感情
仿佛木马里的士兵泄出,
趁夜晚占据你的身体,然后四散奔逃,
以至于许多年后,你走下来,
竟然还可以感到,你的双腿仍然
间或颠簸在它的感性不能持续的天真中。
马戏团
这些天雨大得仿佛
能将日子的牢笼冲毁。
思念像马戏团的野兽退场,
踮脚穿过它尖酸而不熟悉的客厅。
出于对暖气的苍白脸色以及
其合乎礼仪地放弃热情的尊重,
冬天即将过去,但电灯泡的喷嚏
几乎再次让所有的事物变暗。
在比你更好理解的事实中,车站
像一片雪花一样站立,在两座小山间
把窗户的标本,插在河流纵横的
标记灰色心碎和托尔金的地图册上。
幸运的是,它准备好失去的
比已经失去的更多,如同水电费账单。
和圆珠笔滔滔不绝的弹簧类似,
两个月以来,作为自我的售票处,
这仅有的戏剧感并不来自时间
标点似的雨,后者以其击伤大脑的散文
不断敲打我的围栏,而是完全
取决于时间中,雨对自身的厌倦
如何平复,又如何在你的心中化为乌有。
搬 家
再也不会睡在相同的地方,
拥有角度相同的风景,和邻居,
连室内墙壁的白色也不会相同,
但这远非旅行。即使去海边,
或者城堡周围,也用不着
凭意志抛下所有,从一座城市
和自己的咳嗽飞到另一座城市,
并试着接纳新的交通规则,道路,
和以前几乎被你视作野蛮的
凌驾另一种语言之上的语气。
搬家用不着这样枉费心力,
没有什么东西跟踪你,那些杂物
全都没意愿进入你的生命,
尽管你曾经对它们消耗激情。
别去翻那本已然残破,像老奥登
沟渠纵横的脸的诗选,也不用
收起它旁边,撂下农活的打印机,
鲸鱼似的嘴张着,像波士顿
退休的观鲸船拴在码头上
疲惫而无所事事。
每次我去海边,
像跛脚的海鸥,水蚊子般大小,
趔趄在风暴中,我都感到某种
在体内铁索般作响的
同样的疲惫,也许带着怀疑,
将自身置于风浪的中心,
如同码头清洁工,随时准备
弯腰撇清大海的白色浮沫。
我知道,下次冒雨出门的时候
如果我什么都不会带走,
这就相当于说,我没有完成工作,
待在原地,等没人注意我会搬去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