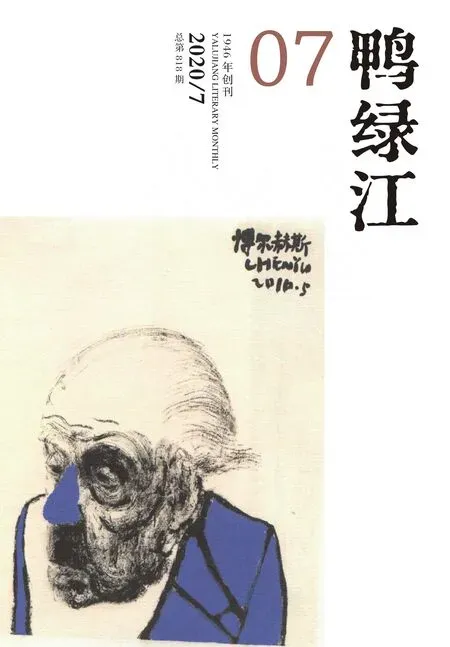倒下还是跳舞?(评论)
——重读邓友梅《在悬崖上》
朱 彤
邓友梅是一位颇具胆识的作家。半个多世纪前,他因在“悬崖”之上跳舞而被铐上沉重的枷锁,历史已然陈旧,但其思想与胆识并未倒下或褪色。时过境迁,以今日之视角回溯历史,记忆与思想重新发酵,这朵“重放的鲜花”或许会呈现出不同的维度与底色。
于是,我回到了那个敏感的历史节点,重返历史现场。我试图同充满矛盾性的“我”一起站在“悬崖”边上,“我”在朴质传统的妻子和浪漫现代的加丽亚两位女性之间徘徊,此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张扬与压抑”,感受到了人性深处与历史根部的痛感。好在作者以“悬崖勒马”“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方式处理了这种痛感,一场“婚外情”的风波就在一个“回头”的“浪子”跳上一辆三轮车中戛然而止。结局似乎令人满意,这个“浪子”倒下了,这阵痛楚也随之破碎、散落。
但是,更大、更深的炽痛刚刚开始。我不想去探讨这位“浪子”未来是否还会继续摘采所谓的“奇花异草”,我更想关注的是通过“浪子”这一介质联结起来的两位女性的命运和个性走向。试想,怀孕后的“妻子”必然要承受双重压力,一面是照顾丈夫、培养孩子,一面是拼命完成革命工作,她这个“贤妻良母”的余生只能在这两种状态之中辗转、腾挪,女性的独立性也只能融化在她沉重的叹息与坚韧的承受里。而加丽亚也无法在设计院继续待下去了,她从美术院被记过后再次失业。那么,以她的个性,再到下一个新环境里工作又会怎样呢?她在享受自由与浪漫的同时,不得不忍受主流的桎梏和世俗的冷眼,沦为传统意义上的异类。在当时的时代精神氛围里,最后的她是否也会倒下?或许,这更值得我们思考。实际上,“我”把“妻子”同加丽亚放在同一空间里对比,来探讨两位女性的是非与高低,这本身就是男性无视女性个体价值的一种强烈表现。我认为,两位女性虽然呈现给我们的是两种互为矛盾的生活观念和态度——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理智与感性、现实与理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但她们最终却指向了相同的结局——丧失女性的独立性。这也是《在悬崖上》的恒久价值之一,它能够带领我们从一个特殊时代的人性内部,尤其是截然相反的两位女性的生命底部,深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根部,从而反思历史的文化传统、政治、规约之于女性的影响,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女性自身的思想与思维方式。
1
不妨先回到文本细部,一起来看一看“妻子”的生活。很多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妻子”是一个怎样勤俭、淳朴、传统,又怎样崇尚革命、热爱集体、遵守国家规范的女性:她“剪着发”,身穿已经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衣,提到“国家制度”这个词汇便立刻严肃;她会帮爱的人洗补旧袜子,上下班很少坐车而是选择散步;她喜欢坚实的木板床和最朴实无华的灯,每天坚持看俄文和政治书;“我”和她在一起谈的是工作、政治、思想、未来……显然,这是一个深受时代政治淘洗的女性代表,她人格高尚,受人尊敬,可以和男性平起平坐,甚至会比很多男性还要“高”一些。建国初期就是这样一个消解性别的时代,“男女都一样”“妇女是半边天”的意识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但事实是,这样的妇女解放仍然是一种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的解放。想想看,女性被动接受男性身份,她们正在盲目赶追集体主义的脚步,“和男性一样”反而更加取缔了女性的主体性,成了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妻子”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在家庭里她既要充当“贤妻”,帮丈夫洗洗补补,又要利用可怜的休息时间学习政治知识;在工作中她严肃、认真,和男性一样地为党和人民做着贡献。她就这样承担着双重劳动,在工作与家庭中间举步维艰。她并未真正获得一个女人的独立性,她不仅性别意识被掩盖,就连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自由也被撕裂。也就是说,“客体性的赋予隐孕着一定意义的主体失落”①刘宁:《妇女权力:转型时期的主体回归与社会实践》,载《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第25卷第3期。。在那样一个极端政治化、道德化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根本不存在自我意识和个人意识,本质上她们还是极其传统的、麻木的,机械地生活在男性制造的集体意志里,女性个体的生命状态如何,就连她们自身也从未思考过。
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奴性”啊!这种“奴性”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几千年来,中国奉儒家传统文化为圭臬,从西周《周易》之中的“乾坤”“阴阳”思想伊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男尊与女卑的关系就被初步建立起来了,他们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系辞上》)②南怀瑾、徐芹庭:《周易今注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页。。这种种原本和谐的元素被男性统治者们强行剥离、对立,最后形成一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二元对立观念,乾坤、阴阳、天地就这样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规约着男性与女性的关系。③南怀瑾、徐芹庭:《周易今注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页。发展到宋代的“太极图说”时,男性统治者们开始以“理”禁锢女性,提出所谓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等,这些程朱理学极其禁锢人性,特别是女性。中国的“文明”时代来临了,女性们顺从地被铐上了枷锁而浑然不知,我们的“奴性”就在这样的背景和制度中逐渐形成了,而我们的独立人格和人身自由也就在这样的习惯和规定中消逝了。不仅如此,儒家文化还从道德层面严格地规约着女性,所谓“从一而终”“三从四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早已深深印刻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里。甚至到了明代时期扭曲地规范女子“无才便是德”,赤裸裸地剥夺了女性的自由与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应该遗忘“五四”这一时期的原因,“五四”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彻底地摒弃封建伦理道德、树立个人独立意识的时期。其中,如何解放女性、启蒙女性、发现女性成为重要问题。于是“娜拉”形象在中国诞生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挣脱家庭的枷锁毅然“出走”。但鲁迅先生以《伤逝》中子君的痛苦告知了我们答案:在20世纪初的中国,“子君”们依然没有一条理想的出路,她们只能堕落或是回到原点。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规约力量的强大所导致的个人意识的幽微和渺小,使五四时期刚刚觉醒、想要起身跳舞的女性们根本无法彻底挣脱枷锁。换言之,“即使是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觉醒和存在的时空也极为短暂和狭小”④丁帆、王世沉:《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唯实期刊,1991年第1期,第59页。。更重要的是,“子君”们虽反抗、逃离了原本的父权制家庭,却仅是为了爱情,这使她们不得不再进入另外一个男性的陷阱之中,又重新陷入“贤妻良母”的泥潭。从这一意义上看,“子君”们的堕落是必然的,而“子君”们的死亡也呈示出反抗“奴性”的深刻价值,死亡,即意味着新生。然而,刚刚想要挣脱枷锁的女性们迎来了“左翼”时期和抗战时期,她们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再次消解于以男性为中心的集体话语之间,这种消解从女作家丁玲前期与后期的创作风格转变之中可见一斑。
我们再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这类女性形象:宗璞的《红豆》中,大学生萧素俨然一个活脱脱的革命者,主人公江玫也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两难中选择了后者;李威伦的《爱情》中,医学院大学生叶碧珍对自己的职业、对祖国和人民那股深厚真挚的“大爱”,使她毅然放弃了个人的“小爱”;丰村的《美丽》中,季玉洁作为外事文化部的女秘书,为他人、为工作先后两次放弃了幸福的机会;甚至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稍有叛逆特质的林道静也是在男性的引导下与自我决裂而走向革命道路的……设想她们婚后的处境与走向会如何呢?或许会与“妻子”大致相同,她们会不断地清理和抛掉自己的自然属性,投入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怀抱,不断增加自己的社会属性,女性个人化的情感特质被啃噬着。如果她们拥有情感,那么也只允许是无产阶级的情感,女性的整体主体意识已经消失。
经过“十七年”与“文革”的沉寂后,“妻子”们集体进入新时期,人性由“失落”转为“复苏”。在这种情况下,以“妻子”为代表的这类女性的精神走向与处境就会有所改变吗?不见得。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让我们看到了“妻子”生命的延续,陆文婷现在的生活正是“妻子”未来的生活。陆文婷是80年代知识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与“妻子”在精神层面上是同质的,即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对祖国和人民饱含深情。与此同时,她也不得不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承担起家庭的一份责任,家庭琐事也在一点一点地吞噬她的身心,她忍受着……终于,双重压力把这个中年女人压垮了,同时压垮的还有“妻子”的未来,以及两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她们的“疲劳”与“断裂”背后隐含的是这一类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与消弭。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我”,《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女售票员”,张洁《方舟》中的梁倩、荆华与柳泉等女性也不得不在家庭与事业中艰难痛苦地徘徊。说到底,即使在80年代的精神氛围里,这一类知识女性的独立性依然没有存在的空间,强劲的外力使女性处于两难与夹缝之间。或者说,这类女性从根本上就没有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独立的“人”在生活,在祖国、人民、家庭这些字眼之下,她们忘记了什么是独立。不幸的是,这类女性在21世纪的今天依旧存在。即便是年轻一代较为开放的女性们,一旦结婚生子,也将面临工作、家庭的双面重担,她们争做一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现代女性。女性们就在这种夹缝中渐渐失去和“妻子”、陆文婷一样的自由。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是怎样影响着这类女性的,即便到了思想大解放的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标志也只是追求爱情而已,这一点中国的“娜拉”“子君”们以出走后奔向男性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三四十年代她们是投向了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怀抱;五六十年代的“妻子”们解放的背后是陷入了更大的不自由;以及新时期的因双重疲劳而“断裂”的“陆文婷”们……这些女性始终没有脱离爱情、男人、家国、他人,而唯独从来没有思考过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如何成为一个不区别于男性的自由的“人”。究其根本,是我们的民族从未这样教育过她们。我们的民族只教会了她们什么是女人的天职,什么是男女有别,什么是无私,什么是奉献。
2
与“妻子”形成鲜明对比的女性形象——加丽亚令人眼前一亮:她有着音乐教授的父亲和德国母亲;她是艺术学校毕业的雕塑师;她秋天穿浅灰色裙子和米黄色毛线衣,有着棕色头发,冬天会戴一顶灰色的哥萨克式羊皮帽,穿紫红色的呢大衣,白色镶红边的毡靴;她喜欢幻想,热爱溜冰、划船、看电影、看音乐会、看《杜勃洛夫斯基》,会到什刹海边散步、去北海看雪景;她和“我”在一起谈的是雪、梅花、鸟……作者试图处心积虑地从姓名、出身、职业、服饰、爱好、谈吐等各个方面将这位女性意识形态化,这些浪漫的元素和符号转而变成了所谓的小资情调,上升到了伦理道德和阶级立场。这位充满现代气息的女性在当时的年代里显得那样刺目,以至于“我”被她的浪漫和理想所吸引,当“我”表白被拒后竟由爱生恨,一切全部成了加丽亚一个人的“过错”。这个追求独立人格、自由开放的女性,却通过科长的叙述、“我”的谴责被铐上了自私、轻浮、作风不良的枷锁。以加丽亚为代表的现代新女性们最终的命运会如何?她们会倒下还是继续跳舞?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一定知道的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伦理道德正在不断地碾轧、毁损她们的自由与个性,表面看,她们具有活泼泼的生气,可有谁能够完全挣脱世俗的锁链呢?从加丽亚最终背靠着树哭泣和“所有人都欺侮我”“我该怎么办哪”“大家更抓住打击我的借口了,设计院我待不下去了”的一系列宣泄中可以知晓,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她并不是完全不在意他者的眼光的,在伦理道德的啃噬之下,她只能黯然离开设计院。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那段历史,政治和伦理对这类女性内在主体性、真实性,以及激情、性情的扼制,在长久的压抑状态里,“加丽亚”们的元气与热力也会日渐萎缩。
以加丽亚为代表的“新女性”诞生于五四时期,这类女性具有现代意义,她们大多受过新式教育,是区别于传统女性的叛逆者。鲁迅《伤逝》中的子君、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是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子君呼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是理智而清醒的,她逃离家庭与涓生自由恋爱、同居,但她在眼看着爱情渐渐枯萎时并没有继续维持这段所谓的婚姻,她的“堕落”是对传统道德最大的反叛。因此,子君的第二次“出走”依旧是女性争取独立、自由的一种表征,而且这次更加坚定、决绝。相比子君精神层面的形而上的觉醒与反抗,莎菲则是女性生理层面的形而下的挣脱与解放。中国传统道德礼教中的贞节观念始终束缚着女性,从孔孟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杂坐”“嫂叔不通问”,到宋代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处女贞操”,据记载,到了明代,一位狱中男子竟在家书中告诉儿子为家中大小女人各买一把尖刀,如遇贼人,自杀守身。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理解莎菲这一女性形象,便能够体会她在文学史上的可贵与价值了。她探索出一条女性自然本性的解放之路,她在与男性自由交往的过程中,那种赤裸的、狂热的、大胆的自然人性欲望正是反抗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她告诉我们,女性不仅要解放思想,也要“回归自己的身体”。亦如凌淑华《酒后》中的妻子采苕,她在醉酒后想要在丈夫永璋面前亲吻其他的男性。此刻,采苕作为“人”的原始欲望被唤醒,充分呈现了女性的“本我”诉求。到了三四十年代,章秋柳、贞贞、蘩漪、三仙姑等形象则把女性的个体意识发展得更为鲜活。章秋柳的强烈的女性道德自信、贞贞在叙述自己被日本人强暴时不显出“悲凉的意味”、蘩漪对继子周萍的情感、三仙姑与女儿小芹的争风吃醋无疑都具有较强的叛逆精神和个人意识,她们意义非凡。当我们撇开她们的母性、妻子等身份,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存在时,便会意识到她们的价值与伟大。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建构根本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女性,她们在追求个人自由、欲望的同时,必然会遭到时代的谴责与鄙视,她们在自由与挤压之中挣扎与变异,最终走向同加丽亚相同的结局。
今天,当我们重返历史场域时,便会发觉,在遍地都是“铁姑娘”的红色时代里,在人性几乎为空白的禁区中,邓友梅能够塑造出加丽亚这一女性形象是多么难能可贵。她拒绝成为他者眼中的好女人、好妻子,她想永远做一个自由的、美的姑娘,当“我称赞她的衣服和身材,她不仅不害羞,反倒爽快地议论起姑娘们的身材特点,以及应该如何打扮之类”①邓友梅:《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邓友梅》,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她与“妻子”是多么不同!其实,从加丽亚与“妻子”两人不同的休闲方式中也可看出两位女性对自我的认识与构建的途径是多么不同。“妻子”的休闲方式是读政治书,加丽亚则是富有现代气息的溜冰、看电影、看话剧等等。从这一意义上,我似乎从加丽亚身上嗅到了一点“狂人”的意味。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是位独战的精神战士,他被那些身处黑暗之中而不自知的麻木的他者视为疯子和异类。虽空间不同,但几十年后的加丽亚并不比狂人所处的环境光明多少,本质上,两者的反抗灵魂与战斗精神处在同一维度上,他们都是时代的清醒者、勇敢者与新生者。然而,唯一的清醒者却被作者有意贴上了“混血儿”的标签,作者告诉我们,她的叛逆意识和异样表现是她的出身和生长环境所致,这就遮蔽了她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这位“狂人”的疯狂是“资产阶级人性”的表现,而不是一位女性作为“人”而独立的表现。这是最可悲的地方。
新时期,这种可悲的禁欲主义也一直禁锢着女性,直到钟雨这一女性形象出现,又重新燃起了“五四”般的烈火。如果说子君争取的是在爱情问题上如何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么钟雨和女儿所追寻的就是在婚姻问题上如何成为一个自由的“女人”。她对子君进行了超越。钟雨接续了加丽亚“第三者”的身份,但这场有爱的“婚外恋”却并不让我们觉得不道德,反而格外真挚,她对爱情的肯定与坚守不仅感染了我们,还深刻地影响了女儿。女儿也在等待一种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②张洁:《张洁文集·第二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370页。。在某种意义上,女儿是钟雨精神的承续者。这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教育与发展。正是这样有着大勇气的两代女性,却被视为“劣等的牲畜”,可见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婚姻的束缚之深。越是压抑,越要反抗。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则通过两性关系的赤裸书写把这种反抗发挥到了顶点,在她笔下的女性们这里,传统的桎梏和世俗伦理已毫无意义,她们以“新”女性的叛逆姿态抵制了传统性欲观念,淡化了传统男性话语权力。沉睡在莎菲身体里的女性欲望苏醒了,原始而纯粹。可以说,新时期散发出的女性个体意识是具有某种先锋意义的,既是对“五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某种回应与超越,又是90年代林白、陈染、徐小斌等“私人化”写作的基础与前奏。庆幸的是,在时代迭变的过程中,加丽亚的生命延续下来了。我们看到了陆芩芩正在追求理想浪漫的北极之光,看到了卓尔那活泼泼的女性原始生命力,看到了倪拗拗、多米迷幻的“身体之思”……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加丽亚。
新世纪以来,以卓尔为代表的“作女”们之所以“作”,“是为了自由的逃亡”,她们“不能容忍任何来自世俗世界的束缚”①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最新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实际上,她们付出的代价和加丽亚等同,极端自由化的另一端是无数个无眠之夜的“独自饮泣”。毕竟,“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同了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一个人在什么程度上进入社会”②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最新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因此,卓尔式、加丽亚式的女性们,只要还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就实现不了完完全全的独立与自由。
我们发现,虽然自五四时期始,女性自我意识就已浮出历史地表,但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伦理道德却彼此连缀,始终缠绕在中国女性的个体生命之中,啃噬着女性的独立性。那么,我们现在便可以重新理解邓友梅在这样一个文本中,精心塑造这两位女性的意图了。首先,两位看似对立的女性,即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却与那个时代的形态、伦理构成统一,其背后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年代,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理应反思一个民族的集体惯性思维对于个体的影响,尤其是女性。亦如西蒙·波娃所言:“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间的所谓‘女性’。”③[法]西蒙·波娃:《第二性》,桑竹影、南姗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页。所以说,到底什么是女性?什么是好女人?什么是坏女人?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女性的判断和认知?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其次,我并不认为两位女性最终的结局是作者向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的妥协,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反讽。一个高扬男女平等、社会解放、妇女解放的年代,作者却在处处显现“解放”之于女性精神和肉体的极度压抑。时代与解放使“人”已变异为“非人”,解放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最后,我们也需要反思女性自身,女性唯有摒弃传统思维,把自己同人类整体的理想联结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独立与解放。
因此,透过“妻子”与加丽亚,我们可以为女性的独立性找寻到一条建构途径。一方面,女性在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时,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独立与自立的人。另一方面,只有女性作为主体的这个个体被主流意识形态真正接受和认同时,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我们应该知道,女性生来便拥有人的权利,无论精神与肉体,都应该自由、独立。而女性的独立与解放也固然不可能逾越自己的时代、民族与人类,女性的独立即是时代、民族的独立,即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实际上,人性与中国现代革命性本不应该放在同一个空间里探讨是非对错,而是要将两者置于平等的层面进行铺叙。正如雨果所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①雨果:《九三年》,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97页。“倒下”还是“跳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唯有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扬起思想与智慧的风帆,透过女性问题关照与反思时代、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问题,才能真正抵达和谐共生、自由理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