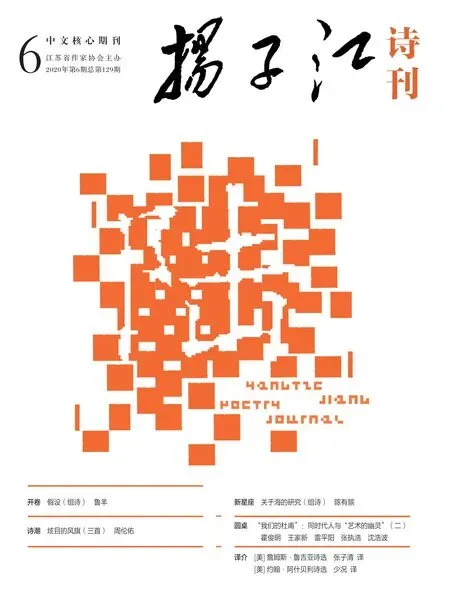隐 忍(外二章)
严琼丽
稻子在我面前生长
稻子在我面前生长,偌大的一片田野,在我眼前发疯地往天空的方向延伸,我坐在田埂上。
河流长在稻田旁边。天渐渐黑了下来,很多人都回家了,我坐在田梗上。
为什么我不是一条没有内容的宽松的皱裙子?
暮色在安静之中被安静蚕食,我早早地将自己归拢在这一片茂盛的生命之中。
这些向着天空生长的稻子,带走我的耳朵,我的皮肤随着我的手指在河里游荡。
人有时要在天黑之前,把自己的神识归还给在流动之中紧抓大地的根须。
我有时会在空虚之中,将自己的肉体置于常规环境之外,让新的、超出自身范畴之外的例外,挤进时空里。
在我仅存的年岁里,我的时空是架在空中的电线。今晚,电线就在我的头顶。
平面危险
柿子红的太阳,挂在西山的山梁上,喂面包屑的人一一散了。抢食了一天的海鸥,在隐秘处,趋于安静。整个湖面,都是我的了。
我坐在你的对立面,将自己堆在岸上的衣服整理平整,等着你急急地涌过来,从岸下站起来,包围我,将我完整地带走。
你来了,带着浪的起落,带着我看不见的微生物,来接我。
我目睹着你,浩浩荡荡地朝我行进,带着千军万马,决不允许它们后退和胆怯。
我想呐喊,想站起来摇臂告诉你:我在这里,在它即将包围的暮色里。
但我,还是按住了自己。
越来越近了,近在咫尺。
我沉默地注视着,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你,缓缓地将自己,连同你的队伍,推向了我,我几近抱住了你的所有的时候,你退下去了,狠狠地,你连同你的将士、长矛、盾牌、弓箭、马匹和干粮,一起撞向了石阶。
我扑下半个身子,还有半个被什么抓住了。
我以跪着的姿态,抱着你零散的部分。
你,立即,以我来不及反应的速度,重整军容,在我什么都看不见的瞬间,头也不回地,朝着来的地方,一沓接一沓,交叠而去。
隐 忍
之于你,我的生命是一个可变换的符号,有时休止,有时截流,有时惊涛骇浪,有时断断续续,有时唯唯诺诺……
之于我,你的生命,是跌宕起伏的剧情,是连绵不绝的清扰,是临近枯萎的倔强,是一言不发的默契……
我曾顺着河流的方向去找你,曾顺着褶皱的脉络去找你,曾顺着冰雪消融的路径去找你,曾顺着保温杯的裂缝处去找你,都寻你不见。
我生气地顺着所有的方向,离家出走一遭,再原途返回。
我将自己关在世间所有的笼子里,再逐一挣脱。
我跑到赤道周围,让那些火焰来煅烧自己,又跑到北极的黑夜里,让寒冷来驱逐自己。
我用尽所有,都无法将你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