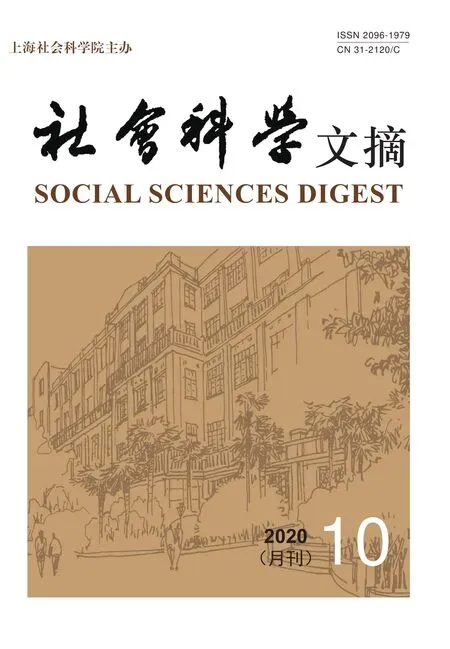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规制
文/姜涛
我国刑法理论目前尚无生物刑法的概念,更谈不上生物刑法的理论建构。在立法上,刑法有关生物刑法的内容分散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投放危险物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之中,并且现有生物刑法体系对新型生物安全风险关注不够。在司法上,由于没有生物刑法的教义学体系,故在遇到诸如疫情之时,往往疲于应对,大量启用刑法中寻衅滋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口袋罪;或者在遇到出售试验动物谋取个人利益之类案件时,缺乏对生物安全的关注(如,该试验动物有无传染病);或者在遇到诸如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案时,病急乱投医,对被告人以“非法行医罪”定罪处罚。本文认为,随着各种生物安全风险的增加,有必要提出并发展生物刑法,明确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规制模式。
生物安全风险的新类型
生物安全涉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传染病防控、基因工程和转基因、食品安全、生物制品、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保护等范畴。结合生物技术、生物法治的最新发展,生物科技发展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目前大致包括如下方面:
1.人类基因安全。一般而言,基因安全是指人体基因处于不受人类不当活动干扰、侵害、威胁的正常状态。基因安全是关乎民族生存的大计,非法的基因改造行为,轻则帮助跨国药企开发药物、独占市场。目前基因技术为发达国家所掌握,极易出现在不知情情况下的泄露或非法采集。从公开的人类基因组数据库和科学文献数据中获得人类生物数据,可以通过发现特定人群基因组特征与病毒感染之间的关系,设计和改造病毒等,增加对特定人群的感染特异性;重则导致“基因殖民主义”或“基因奴隶制”,严重危及人类健康,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2.生物恐怖主义。生物恐怖主义可以定义为故意释放病毒、细菌、毒素或其他有害物质,在人、动物和植物中造成疾病或死亡,其目的是在目标人群中通过恐惧、恐怖和不确定性产生最大的影响。对有潜在生物恐怖风险的抗药性高致病性细菌和真菌的生物防治,已经成为生物安全立法保障的重点。
3.生物保障安全。生物保障安全是国家、企业等主体为避免生物材料泄露或生物材料招致危险而采取的保护与防控措施,这种保护与防控措施可以避免生物材料因泄露、被盗、扩散等而招致对人体的伤害,因此,属于刑法保护的生物安全法益之一。
4.生物资源安全。生物资源是人类可以直接或间接使用的可再生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所组成的生物群落,是生物多样性的实质体现。动物、植物与微生物等生物资源对人类健康、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等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人类的未来也植根于丰富的生物资源。
5.生物资料库安全。人类遗传信息是非常宝贵的生物资源,对其从事科学研究虽可以打开人类遗传秘密,但也带来安全风险。生物资料的滚雪球式采样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成为生物技术公司追逐的热点,但增加了人类遗传物质在未被发现和未经记录的情况下离开国境的风险。
6.生物试验安全。实验室及其设施的安全保护具有重要性,它可以防止未经授权获得和清除微生物、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防止寄生虫的试验感染、真菌的试验感染、伊波拉病毒等试验感染。
7.生物主体资格安全。如果人工智能发展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与人类平等的智能机器的新“种族”,那么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冲突,甚至争夺地球霸权的问题就不可避免,有可能产生潘多拉魔盒的影响。由此带来的担忧是,人类有可能从治理主体变成治理对象,这就是人类的生物主体资格安全。
8.转基因食品安全。现代生物技术,包括合成生物学和经济学,是一种新兴的工具,在改善人类和动物健康、农业和工农业生产以及环境保护方面具有潜力。然而,它的开发和应用可能会对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产生潜在的副作用,包括生物多样性风险,在农业中使用转基因生物具有与自然物种杂交的风险,这可能危害生物多样性;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也存在严重的健康风险。
现代生物安全风险的特点及其控制正当性
(一)生物安全风险的特点
生物安全风险既有一般社会风险的特点,如高后果、低概率,由组织体的严重不负责任而导致。但二者也有所不同,一般社会风险具有局部性,生物安全风险具有整体性,它事关国家兴旺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且生物安全风险的过失判断更加困难。同时,生物安全风险与环境污染风险之累积损害不同,它是一种多样性风险。不少生物安全风险关联的损害具有即时且急迫的特点,且隐蔽性更强。
(二)生物安全风险的控制正当性
在日常用语中,风险被用来表示危险或伤害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风险由三大属性构成:概率、不确定性和未来性。尽管概率评估可以提供关于风险影响的最佳猜测,但在许多情况下,损害的实际表现仍然是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风险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发生,而在于它可能发生的概率,以及破环的严重性。
人类安全是生物安全风险的第一个受害者,其次才是具体个人的生命、健康等法益,前者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假设,关注对集体而非个人的威胁,后者是一个基于自由主义的假设,即个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生物安全风险的核心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极端脆弱性”,国家的责任是保护最脆弱的人,但是国家立法的立足点不能是具体的个人之生命、健康,而应该是人类安全。人类安全的概念意味着从“干预权”转向“保护责任”,这种概念优先考虑人类集体的权利,通过建立和维护可行和合法的国家结构来保障作为集体意义上存在的生物安全,以此来保障具体的个人的生命、健康等权利。毕竟,实现所有人的安全,才是人类最大的自由。
风险社会的正义问题,具体体现为风险分配与组织体的不负责,这种风险分配是跨越阶级的,不以财富的差异为基础。如何避免成为他人风险制造的牺牲者,成为法律正义的内容,并且“失控的世界”不是源于科学的不确定性,而是科学的独断性,或者说组织体的不负责,是一种人造风险,故具有负责的基础。随着社会风险增加,人类开始从追逐财富向回避恐惧转变,避免唯恐不及之风险,成为民众的集体行动,也因此赋予国家新的时代责任——以法律预防和控制社会风险,国家由此也成为了预防性国家。尽管,惩罚并不是预防社会安全风险的唯一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以刑法预防各种导致社会风险的行为,试图在它们发展成为实害之前识别并警告它们,成为当今预防性国家刑法立法的常态,也是一种无奈的积极选择。
生物刑法属于预防性刑法
人类安全范式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推动了刑法上一种新的行动策略——预防性刑法。全球风险社会的特点是犯罪的新型复杂化。基于对犯罪的日益恐惧,风险社会需要实现从传统刑法向预防性刑法的转变。
把生物刑法定位为预防性刑法,这与生物安全风险增加的时代背景有关,其行为规则是从预防范式的视角切入的,它通过对制造生物安全风险之行为作出积极反应,保障人类安全,故构成对古典刑法之范式的突破。
预防性刑法通过刑法保障生物安全,使刑法成为生物安全风险的免疫范式,目标是减少犯罪,它具有法理与现实根据。在法理根据上,安全和自由之间固然存在紧张关系,但是没有安全就根本没有自由,为了安全必定要舍弃部分自由,没有安全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自由危机。预防性刑法的现实根据在于生物安全风险的日趋增加、民众对生物安全风险转为实害的集体恐惧及以刑法保障安全的需要。
从结构上,预防性刑法倚重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和强调“防患于未然”的立法政策等,出现的背景是科技发展等所带来大量不确定的、作用对象无法预知、在未来破坏力极强之不被容许的复杂风险。从功能上,预防性刑法意味着刑法从法治国家到安全国家的渐进结构和文化变化,它是从一种“针对个人罪责的制裁手段”转向“一种通过惩罚被列为危险的人来预防风险”的预防手段,它把刑法由“自由主义静态观念的外壳”,发展成“为了使国家或社会不发生巨大混乱的控制工具”。这与生物安全风险的特点之间具有对应性,生物攻击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恐慌,缺乏经验、群体性后果和恐慌、多变的条件和攻击模式以及相互重叠的责任,都将使生物攻击的事实难以厘清。但是,这种风险必须提前防范,风险防控重于公共事件发生后的惩罚或补偿。显然,胡萨克提出“刑法极简主义”的主张,并不适用于生物刑法。
当然,生物刑法之预防性干预也有限度,并不意味着要牺牲法治国原则,这大致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不能以刑事政策法益概念取代法理法益概念。这涉及法益的理论证成,而不单纯是一种刑事政策上的政治抉择,否则,就会用刑事政策法益概念替代法理法益概念。犯罪化是最具侵入性的国家行动,它需要有力的理由,生物安全的刑事政策,必须以一种既具有重大意义(即潜在的危害程度很大)又具有重大紧迫性(即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超过自由)的紧急情况为理由。第二,预防性刑法也不能突破比例原则,即仍需以一种考虑到个人权利的方式,这种权利并不必然被“公共保护”或“公共危险”的考虑所替代。若缺乏比例原则的限制,刑法会陷入对“嫌犯”的扫荡,强化“又严又厉”的罪刑体系,而不再是将国家置于“权利之眼”之下。就生物刑法中比例原则之实现而言,既可以考虑把企业合规作为免责事由,也不能脱离宪法而扩大刑事法网或加重对个罪的处罚力度等。
生物刑法属于被害者刑法
随着刑法中涉及集体法益的犯罪增多,有必要提出被害者刑法的理论,所谓被害者刑法即从被害者出发,思考预防集体被害的罪刑体系建构问题,它是一个社群主义的概念。简言之,以被害者的保护为立场思考刑法之罪刑体系建构,旨在强化与发展最有利于被害者利益保护的刑法模式,包括从最大限度避免被害、最有效保护被害者的立场出发思考刑法体系建构;赋予被害人在犯罪追诉中的自我决定权;允许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作为特殊情况下的出罪事由;等等。其中,刑法建构一个积极的预防网络,避免潜在的被害者成为现实的被害者,这是被害者刑法最为核心的问题。
被害者刑法的具体实践首先需要对生物安全法益进行分级,针对不同的被害风险等级采取不同的立法技术,然后还涉及把被害者的集体恐惧纳入犯罪判断。
第一,以生物安全法益分级设置犯罪。生物安全可以按照被害者范围、被害的急迫程度等标准分为四级,等级越高相对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及设备要求就更高。
不同等级的生物安全,对刑法的立法技术要求亦不同,其中,涉及四级生物安全的行为,当设置为行为犯,且强调最为严密的刑事法网,即实施某种行为即可构成犯罪,且法定刑最重。涉及三级生物安全风险的行为可设置为行为犯,强调相对严密的刑事法网,且其法定刑次于一级生物安全涉及的犯罪类型。涉及二级生物安全的行为可设置为具体危险犯,不宜强调过于严密的刑事法网,其法定刑当比涉及三级生物安全的犯罪轻。涉及一级生物安全的行为可设置为抽象危险犯,不宜强调过于严密的刑事法网,此类犯罪的利益衡量比较复杂,或涉及科研自由与刑事犯罪的关系。如从事转基因方面的研究自由,只有其滥用这一研究自由的行为才可以被规定为犯罪,或者涉及自由贸易与生物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如“鹦鹉案”中出售人工繁殖的鹦鹉等,且其法定刑当最轻。
第二,把集体恐惧等主观判断纳入犯罪判断。生物刑法有采取主观标准的必要,风险判断的主体间性与风险判断的主观化不同,它是一种合理可识别的某一不良结果实现的事前概率,包括无限复数被害者之间的共同体验与记忆。如生物恐怖主义或疫情带来的集体恐惧等,即因民众对某种生物安全风险的集体恐惧及痛苦记忆作为犯罪认定的标准,包括对因果关系中的不法结果采取主观标准等,这是一种从虚拟的本体论到真实的规范论的转变,这正是生物刑法倚重危险犯之立法技术的重要原因,也是刑法学吸纳心理学之犯罪判断标准的体现。
生物刑法属于关系性刑法
尽管前文强调生物刑法属于预防性刑法,“抓早抓全抓小”是其立法技术的体现,但并不排斥把企业合规作为生物犯罪的免责事由,这是把生物刑法作为关系性刑法得出的结论。
关系性刑法以激励为手段,企业合规是关系性刑法的核心主张,旨在通过促进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来实现预防公司犯罪之目的设定。对于刑法来说,企业合规是以刑罚方式推动公司的自我监管责任,它的基本假设是,法律规则的规定性内容除了任何相应的制裁之外,规则也很重要,“好人”(包括公司)会为了规则而遵守规则,或者说是受激励遵守法律规则。为此,公司应该成为法律规则的认知内化者,以遵守规则的方式来满足它的真实偏好,而不是试图直接满足这些偏好。
以企业合规建设预防企业犯罪对生物刑法具有启发意义。生物犯罪往往是一种产生不必要的生物危害的行为,通过以合规的方式组织生产或研究等可以避免这种危害,任何合规计划的首要目标都是防止公司代理人违法。
就企业来说,如果能够遵循的是对社会负责的道路,这自然是一个比法律道路更高的秩序。与法律制裁的威胁相比,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更有力的合规激励。从反向激励看,如果大多数犯罪不费吹灰之力,被发现的机会低,那么节约守法成本,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有吸引力的奖励,此时,即使事后再为严厉的惩罚,也于事无补。从正向激励看,若能把企业合规作为免责事由,这对企业合规建设是重大激励,即使合规成本很高,也值得去追求。比较而言,法律的反向激励要尽量避免,法律的正向激励需要强化。
生物安全风险控制着人类,人类也会采取法律手段去控制它,在诸多法律手段中,刑法虽然不是唯一也非最有效的手段,却因民众之“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被发展成为一种新期望,成为了能够塑造“新的安全地带”的预防性干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