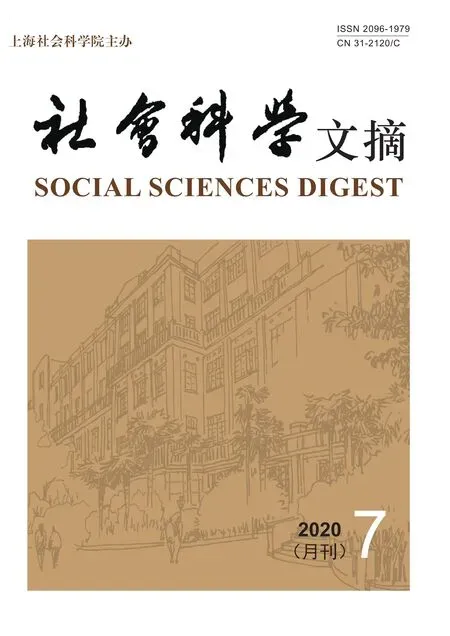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来由、演化与趋势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定义历史社会学,都必须面对历史社会学与历史研究的紧密联系。作为社会学内部兴起的一种反主流的学术运动,在其利用历史学的知识资源的同时,由于历史研究的独特性,塑造了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史料派的“历史性”、实用史学派的“非历史性”以及史观派的“反历史性”,三者构成了历史研究的根本属性,虽然三者是悖谬性的结合。只是由于史料与史观之间、研究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分离,这种悖谬并不影响各行其道的历史议题和历史理论研究。然而,当社会学运用历史学的知识资源时,必然同时遭遇这些悖谬性的研究属性,并引发了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
构成性难题的来由
一般认为,自德国史学家兰克把历史学作为一门职业以来,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是处理一手史料,并以生动的叙事方式将其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回答史料选择标准的前学科问题与史料整理意义的后学科问题。显然,历史研究的这些“非历史性”志向充满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批评的实用主义史学“无历史感”色彩,是为了有效回答史学家所处时代的公共议题,化解公共焦虑,或者为当下时代寻找与建构历史的合法性。当然,历史研究并未止步于此,在“经世致用”的同时,历史研究的“反历史性”假设一直引导其走向更远。其终极目的是,探索并找到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历史规律,以此本质性范畴来引导人类迈向普遍真理的康庄大道。这种历史先验的假设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世界历史是上帝为尘世的人类创造的,呈现出从堕落到拯救的一幅完整画卷。简言之,历史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侧重于史料的“历史性”、历观上的“非历史性”、先验假设上的“反历史性”三种特性。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在19世纪前期几乎是同一时间兴起,也意味着二者开始分道扬镳。一方面,“兰克学派”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与样板,发展出作为学科的历史学。另一方面,孵化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科学,成长于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动荡与危机,提倡无关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致力于化解贫困、犯罪、卫生、司法和经济等问题,成为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从此,在研究策略与实用目的上,历史学的“历史性”与社会科学的“非历史性”之间开始分化。当然,在知识论层面,得益于孔德继往开来的实证主义哲学,社会学的历史意识依然浓厚,但历史研究丧失了独立性,要服务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因果关系和不变法则。显然,历史研究与社会学在先验假设上存在冲突。
从此,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具体研究在对待历史研究方面招致各种争论,逐渐形成几种范式,一直影响到整个20世纪的发展。概括起来,争论主要是围绕历史研究的“历史性”“非历史性”“反历史性”三个层面展开。在“历史性”层面,考古学家抵制兰克的唯官方文本立场,重视非文本和非官方的史料及其背后的立体结构和类型学分析,而倾向于社会学的法国历史学家,如库朗热与西米昂,认为不能过于沉迷文献考证,也不能停留于事实描述。这两种倾向接近孟德斯鸠—孔德—涂尔干的古典社会学传统,关注历史的结构性和普遍性问题及其因果关系的类型分析。
“非历史性”层面体现为兰克唯政治史倾向的批判。到19世纪后期,兰克的传统史学遭到 “新史学”领域的挑战,但“新史学”运动背后的动力是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分化与对峙。19世纪末的社会学似乎包括“新”“旧”两个范畴。“旧”的是指普遍意义上研究人类所有活动领域;“新”范畴是特定意义上研究人类活动的非市场与非政治领域,这恰恰是受学科分化建制影响最小的领域。在“反历史性”层面,19世纪后期整体转向为“进步论”“发展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这在20世纪后期兴起“后现代”思潮之前似乎都是主流的先验假设。当然,在主流之外还有尼采、斯宾格勒等思辨历史哲学对进步史观的批判。
19、20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科学独立于历史研究,历史社会学成为反对学科分化建制的武器,延续19世纪社会科学的历史意识传统,从而成为社会科学家坚持历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当然,历史社会学并非内在一致,而是因受历史研究根本属性的悖谬影响,在历史性、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的侧重点上出现差异,甫一开始就呈现理解性的阐释(interpretation)与说明性的解释(explanation)两种研究范式。
但从20世纪的延续来看,前期成就了法国 “年鉴学派”,战后是英国掀起讨论资本主义起源的热潮,德国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发展出“历史社会科学”。它们都是在这两种范式和“现代化”预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只是现实关怀、主题侧重和问题关注不同。但是,欧洲的历史社会学传统更多是后来者进行回溯而冠名的,只有美国的历史社会学真正是在社会学领域内部发展起来的,并且最早明确提出“历史社会学”的概念表述。
构成性难题的演化
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内部的兴起有其不同于欧洲的独特过程。进入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发展表现出数据操作化与主流理论的概念抽象化特点,与历史研究渐行渐远。但是20世纪30年代,“历史社会学”概念被提出,试图将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弥合在一起。
“历史社会学”最早由班茨(Barnes)和贝克尔(Becker)倡导以此反抗美国主流社会学传统,但由于没有共同的方法与核心议题,且在方法论和数据来源上主要采用人类学方法而无益于后来兴起的历史社会学,但已经初步体现出历史性、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之间的悖谬性结合,在倡导历史意识并对抗主流范式方面奠定了历史社会学传统的学术品格。
20世纪60年代第二代历史社会学开始兴起。由于西方世界频发的社会运动,一大批激进的年轻社会科学家有机会抵制主流研究,反对学科分化和无历史意识。社会学家最主动转向历史研究,由此重启反主流的“历史社会学”。第二代历史社会学更广泛地吸收全球新史学资源。此后,社会学与历史学在形式上出现从未有过的亲密,成为20世纪60、70年代兴盛跨学科学术运动的动力与资源。
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社会学”发展出以宏观(视野)、比较(方法)、历史(证据)三者相结合作为基本特点的研究策略,并形成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议题,包括军事、政治、革命、阶级等主题,围绕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世界性重大问题,由此达成这个学术运动的内部共识。正是因为有共同的方法、主题与问题,历史社会学迅速发展成为社会学的子学科和专门的学术领域,并加以组织化与制度化。与此同时,主流的经济学与政治科学主动把历史研究的传统资源拱手让给社会学,越来越青睐数理统计模型和理性选择理论,陶醉于追求所谓客观规律与价值中立。就这样,社会科学的历史意识一度被“历史社会学”占为己有,因此迎来“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历史社会学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和研究领域,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和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历史社会学家,产生的成果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界都颇有影响。在这些阶段性的变化中,大致可以将美国历史社会学人划分为三代人。
第一代学者的贡献是“批判”,作为抵制功能主义社会学的主要旗手,促成以比较历史分析为标志的历史社会学。当然,有几股力量同时批判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并汇集在一起,助力历史社会学的兴盛。
第二代以“50后”与“60后”为主,贡献在于“建构”。其中,“50后”学者都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社会学成为社会学子学科之后的第一批受益者和亲历者,接受严格的专业培养与学术训练。他们已经不在乎反主流,而是建构自身的学术领地,不局限于第一代学者的物质性主题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而是更广泛关注非物质主题,方法更多元与包容。
历史社会学的第三代学者正在崭露头角,贡献还不明显,主要由“70后”与“80后”的新锐组成。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庞杂,学术训练更规范,研究视野更开阔,不仅仅局限于西方世界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跨区域与全球性的整体关注。在学科上他们并不是局限在社会学学科,而是以比较历史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网络分析、时间系列分析、事件分析等新范式,结合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借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文献、方法、概念与视角。
与这三代学人相对应的,美国历史社会学大致有三个阶段的明显变化,即20世纪60、70年代普遍作为批判的武器(本质论),80、90年代作为子学科的领域(特殊论),千禧年之后,以比较历史分析、叙事分析、过程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为研究方法的形式(工具论),与定量/定性的传统手段结合,广泛应用到历史社会学研究,使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结合呈现多样化。这三个阶段也有大致相对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范式,即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网络主义;在分析层次上也大致呈现出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变化。
三个阶段对历史研究的根本属性也有不同程度的重视。第一个阶段不重视历史性,而是普遍把历史视为社会科学的佐证材料,坚守社会学的“非历史性”传统。但在第二阶段之后,不仅重视一手史料,而且在认知上不完全是“非历史性”,而是更尊重时间次序的历史过程,把史学的“讲故事”与社会学的“讲道理”结合起来。在“反历史”的假设上也有变化。20世纪60、70年代是追求一致的“现代化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但在80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影响之后,90年代之后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主体、叙事、小空间、帝国/殖民、身份、女性等追忆传统、差异化和多样性的主题。但到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连续遭遇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的政治经济大问题似乎又重新受到重视。
这意味着“反历史”的假设、“非历史性”的认知与“历史性”的史料出现多样化的特征,再加上主题与方法趋向于多元化,历史社会学研究开始走向碎片化。同时,历史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也不再局限社会学这个母体学科供给,研究结论也不完全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以至于历史社会学可能成为查尔斯·蒂利所揭示的“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构成性难题的当前趋势
接下来按证据的“历史性”、认知的“非历史性”和预设的“反历史性”三个层面,以部分美国历史社会学家的研究立场为例,展示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在当前的发展态势。
其一是“历史性”的语言与史料问题。社会学家在转向历史时,遇到的最大问题难以得到主流社会学与主流历史学的双向认可,其主要原因有二:历史学家最重视一手史料的搜索、收集与甄别,而社会学家更倾向于重新分析二手史料;与此相关的是,重视一手史料必然涉及到语言、语义与语境问题,背后是必然关联到思想、文化、历史、观念等更为复杂的因素。巴林顿·摩尔指出:语言的丰富与精准是做一流比较与历史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但事实上,历史社会学家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往往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高度重视一手材料及其语言书写,一切根据自己参与收集的档案材料来分析,另一个极端是不喜欢收集一手档案文献,但高度重视历史学家们已经找到的历史数据,大量使用二手文献,并以不同的角度和问题来重新分析这些历史数据,展示长时段背后的“普遍命题”。当然,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个调和以及平衡的观点。比如政治学家西德尼·塔罗与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等人认为,重视语言和一手史料与否,取决于历史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和策略。
其二是“非历史性”的视角、概念、理论问题。如果说对待“历史性”问题有三种态度,那么在“非历史性”问题上的差异就大得更多,而这恰恰是历史社会学家们主要的创新之处。我们可以在两方面来理解其间差异。第一,历史是社会科学的意识和本质,还是发现规律和寻找解释的方法与工具?或者二者是跨学科真正融合的领域?侧重于本质、领域或方法,这是历史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争论议题。第二,历史社会学主导范式出现宏观-结构、中观-文化、微观-网络的分化。
其三是“反历史”的理论预设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名的历史社会学们都深谙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经典社会理论,试图简化历史,旨在寻找总体的结构或普遍的概念,为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轨迹提供“金钥匙”,其背后的历史假设是以“进步论”和“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更强调差异性、多样性,似乎出现逆现代化、多元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的史学观念。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文化、地方性知识、社会性别、宗教,象征、记忆、小空间与小群体等等,强调多重作用力与多重视角是如何整体影响到历史轨迹的变化。
但这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历史社会学的美国化、原子化、碎片化、空洞化,导致历史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陷入低潮,带来诸多方法论争论,但隐藏在方法论之后的实际上是历史观念或者假设的不同。但随着21世纪出现美国的“9·11事件”、英国的“7·7事件”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大问题、大空间结构、长时段的大历史变迁似乎重新回到历史社会学关注的中心地带,宏观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再次受到重视。
结论
历史社会学既不是解决问题的一套理论或者概念框架,也不是一种视角与方法,当然它也很难被视为一个学科领域。相反,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领域一股反主流的学术运动,借用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资源,不断抵制母学科的主导范式与学科之间的沟壑,并不断突破与更新自我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每一代学者的作品都高度关注特定时代的问题,不断平衡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他们一方面展示具体研究的现实意义并推动当下的问题研究;另一方面,了解在不同历史观念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成果。同时,为了更有说服力与可信度,他们还需要亲自投身于历史档案,搜集并解读第一手史料。
但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属性使历史社会学存在与生俱来的悖谬,一直在历史性、非历史性、反历史性的对抗与张力中决断,难以同时满足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认可。他们得有自己独到的学术判断和反思,并不断超越自我的认知障碍。这构成历史社会学领域的斑驳图景。如今,美国社会科学越来越量化和模型化以至于僵化,而历史社会学的扩展与争论无疑是活跃美国社会科学乃至拯救西方社会科学危机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