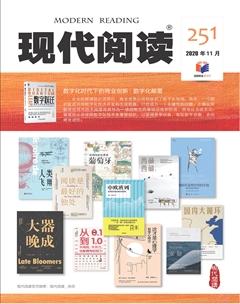活在《史记》中的吕太后

吕雉(前241—?),汉高祖刘邦皇后。她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
《史记》的《吕太后本纪》里,都写了些什么呢?
这篇本纪,虽然题目标的是吕太后,那里面写的,却并不都是吕后生前的事情。它的纪事,很明确地分为太后生前和太后死后两大部分。
太后的生前部分,《吕太后本纪》主要记的,是她做太后以后的事情。这中间有3件事特别突出:一件是对付往日的情敌,一件是控制当今的皇帝,再一件是给娘家人封王。
这3件事,说白了,都是宫斗剧。不过《史记》写法不同:第一件是恐怖片,第二件是伦理片,第三件是纪录片。3个片子还是互相关联的。
恐怖片的主角,是戚夫人,刘邦当年做汉王以后娶的宠妃。因为当年的戚夫人年轻貌美,吕后被高祖冷落了好一阵;也因为这位戚夫人,执着地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代替吕后所生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做太子,虽然没有成功,却让吕后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存危机。结果待刘邦一死,孝惠帝登基,吕太后就把她囚禁到了深宫永巷,最后还残忍地砍去她的手脚,挖掉她的双眼,火烧了她的耳朵,让她喝了永远不能再发出声音的汤药,把她扔在厕所里,还送给她一个极度侮辱的绰号——“人彘”,就是人猪。
伦理片的序幕,是已经做皇帝的孝惠帝被吕太后召去看现场版的恐怖片,得知眼前的人彘就是戚夫人,被吓得大哭,当场把君权拱手让给母后大人,并从此得病,年轻轻的就死了。
于是以眼泪为主题的正片上演了。这回的视角,换成了第三方——年仅15岁的张公子张辟彊。张公子是留侯张良的儿子,年纪不大,看问题很深刻。在孝惠帝的葬礼上,他发现了一件怪事,就跑去和丞相交流。他问丞相:“太后只有孝惠帝这么一个儿子,现在驾崩了,却干哭,不掉眼泪,您知道这事的谜底吗?”丞相反问他:“此话怎讲?”张公子的回答,竟然是:“高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是怕你们这些老臣啊。您如今不妨奏请,让太后的3个侄儿吕台、吕产、吕禄当将军,带兵控制京城的南北军,让其他吕家人都进宫,在中央机关工作,这样太后才会安心,您几位才可能摆脱祸害。”
丞相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照办。伦理片就此转场纪录片。只是下面这纪录片免不了都是给这位封侯,替那位封王,或者搞掉这个王,再让那个上。
讲到吕太后的生前事,还有一件跟控制皇帝有关,就是吕后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时的公开纪年问题。
根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孝惠帝死后,在吕太后的操纵下,先后有两位刘氏小皇帝登基即位,第一位即位时虽然标明是新的“元年”了,还是“号令一出太后”,就是所有的官方命令其实全都出自吕太后;第二位上位时,索性“不称元年”了,因为“太后制天下事也”,就是太后管着天下的事呢。这两段傀儡小皇帝的时间,加起来有8年,后来像《资治通鉴》等史书,就直接把这8年用“高后某某年”来标示了。
“高后某某年”的纪年是真实存在过的吗?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相关学者认为,那个时段吕太后实际掌权,是毫无疑义的,但纪年是很正式公开的大事,吕太后未必会这么做。1980年代前期,湖北江陵的张家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初年的竹简,其
中有一篇历谱,据考古发现简报,是起于高祖五年,终于高后二年的。但事实上,我们看后来正式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一书,这份历谱里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高后”二字,甚至被判定为高后的那两个年份,文字都正好是缺失的。所谓“高后元年”“高后二年”的说法,是通过文献考证获得的。因此,高后纪年是否实施过,至今依然是谜。
吕太后在执掌朝政15年后死了。她一死,《吕太后本纪》的主题和主人公就都变了。这部分也写了3件事:一件是夺南北军,一件是杀姓吕的人,一件是迎代王做新皇帝。掌控局面的主人公,则都是高祖时代的老臣。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那些重新掌握汉王朝实权的大臣,在选择新的汉朝皇帝时,特别注意他们的生母的家庭情况。被提名的代王,不仅是汉高祖活着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而且他的老娘薄氏,做人小心翼翼,个性善良,所以最后取得各位大臣的一致同意,把这位代王推举上去,做新一代的汉朝皇帝——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在《吕太后本纪》的末尾,作者司马迁写了一段“太史公曰”。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孝惠皇帝、吕太后当政的时候,黎民百姓得以远离国家战争之苦,国君和大臣都希望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所以孝惠帝放手不管,吕太后以女天子的身份代行皇帝之职,政令不出房门,天下安宁,很少用到刑罚,犯罪的人因此也很少,百姓们一心一意搞农业,衣食一天比一天丰盛。
司马迁对于吕太后时期的评价,既超越了姓氏,也超越了性别,而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评判国家领导者的指向。在他看来,宫斗也罢,私心也罢,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層面,一切应该以是否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否合乎普遍的人性,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
(摘自中华书局《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 作者:陈正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