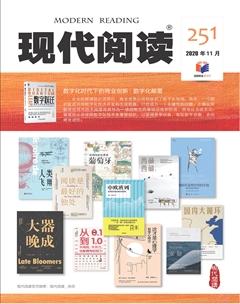出名要趁早——急于求成的社会焦虑
里奇·卡尔加德[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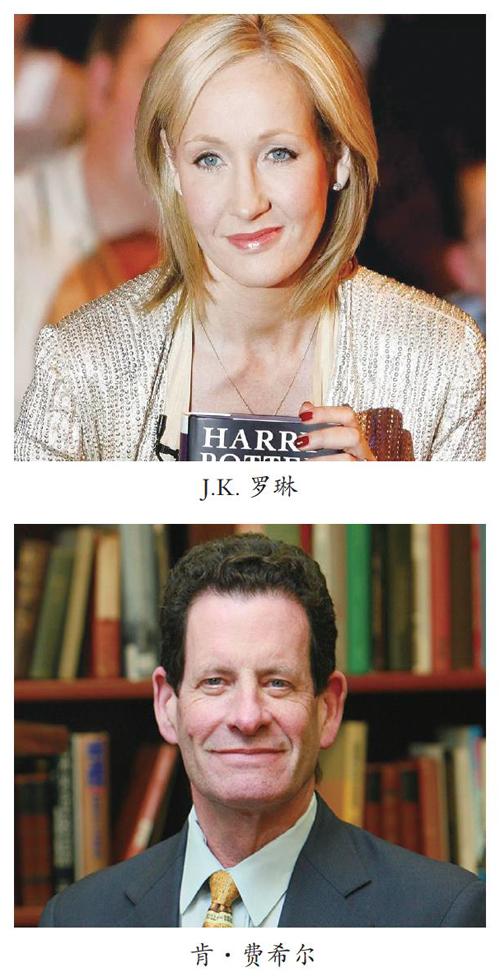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拿到全A,没有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没有进入心仪的一流大学;我们在21岁的时候迷失了人生方向,错过了一份完美匹配自己才华和激情的理想工作;我们没有在22岁时赚到数百万美元;我们没有在30岁时成为亿万富翁,登上《福布斯》封面;我们到35岁时也没有消灭疟疾,解决中东的冲突问题,成为总统顾问,或者第三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在人生刚起步阶段就发光发热,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失败的,这都不是我们的错。我要说的是,父母、学校、媒体和公众都在疯狂追捧少年成才的现象,似乎这种成功才是一流的成就,甚至是唯一的成就。我们如此迷恋这种现象,以至于大器晚成都会变成一种并不光彩的事迹。
但过去好像并非如此。
乔安妮就是一个“大器晚成者”。她少年时期的生活既不稳定,又不快乐。她母亲疾病缠身,她父亲赚的钱虽然够养活一家老小,但他对妻子甚为冷漠,对她的病情不闻不问。乔安妮和父亲之间也很少说话。
乔安妮在学校几乎就是一个无人在意的“透明人”。据一名教授称,她不是太关注自己的学业,对另类摇滚乐倒有几分兴趣,可以一天听好几个小时的摇滚乐。
和许多心智健全但并不引人瞩目的毕业生一样,乔安妮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从事普通的行政岗位。她曾一度在本地商会办公室担任秘书。
厌倦了这种庸常生活的乔安妮,后来与一位她偶然结识的异国男子结了婚。他们生了个女儿。但这只是一段同床异梦的婚姻——乔安妮是个爱幻想的女子,而她丈夫却是个性情多变和隐含暴力倾向的人。虽然有了孩子,两人的婚姻还是不到两年就结束了。他们因家庭暴力问题而分道扬镳。
在年近30岁时,乔安妮仿佛一眼看到了人生的尽头。她没有工作,还带着个拖油瓶一样的孩子。她的人生当然也就开始每况愈下。她被诊断出得了抑郁症,时常会冒出自杀的念头。抑郁症导致她无法卖力地工作。她的生活穷困潦倒,她说:“我只是个还不至于流落街头的穷人罢了。”更糟糕的是,她的前夫开始跟踪这对母女,迫使她不得不向法院申请禁止令,以免前夫靠近她们。
其实,乔安妮并非一无所长。她有一项无人知晓的绝技。在她生活艰难,依靠领取救济金来养育女儿的那几个月中,她开始放飞自己的想象力,书写童年时代的幻想。在社会看来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现实的行为。奇怪的是,就是这种行为让她更贴近自己的天赋。只有在乔安妮放飞想象力时,她的天赋才能够浮现和绽放异彩。
肯是另一個大器晚成者。他是家中3个小孩中排行最小的一个。他的昵称Poco在西班牙语中就是“小”的意思。肯的大哥是一个明星运动员,是老师的得意门生。他不但帅气,而且有一副好口才。他赢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并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而肯却在学校表现平平,他开始认为Poco对他而言就是“渺小的存在”的意思。
肯在加州的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了本地大专院校就读,在那里主修林业学。他发现与林业学专业对口的更多是和造纸有关的工作,而不是那种在森林中徒步冒险的事业。他预感自己的理想又幻灭了。
后来,肯就跟随父亲从商。经过6个月的磨合,肯还是离开了父亲的公司。他自立门户,成了一名财务顾问。在肯20多岁的那几年,虽然他的财务顾问业务发展艰难,但是他通过读书掌握的理论让他在风险投资领域小有收获,其中一笔投资还让他当上了临时CEO(首席执行官)。他觉得自己壮志未酬,所以就继续在这一行努力进取。下面是肯的一段感悟:
这家公司大约有30名员工。我之前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一个人。现在我却不得不担起这个重任。没想到我做得还可以——这远远超过我的预期。你知道我学到了什么吗?我学到了当领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要在场。我发现,领导表现出来的渴望具有感染力。我将CEO办公室迁移到了一个开放式的玻璃会议室中,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在办公室里的情况。我成了每天第一个到公司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我每天都带员工去吃午饭和晚饭。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但可以让他们看到我在此投入的时间和诚意。我经常四处走动和他们交谈,关注他们的想法。
这个举动产生了让我震惊的效果——我的关注点也变成了他们的关注点。我突然就领悟到了身为领导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肯30岁之后才开始挖掘出自己的潜力。
看到这里,你能判断出这两个人是谁了吗?乔安妮和肯都是自力更生的亿万富翁,他们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常客。没错,乔安妮·凯瑟琳·罗琳为人熟知的名是J.K.罗琳,她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肯·费希尔就是费希尔投资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掌管着全球5万多名客户价值达1000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
在这个极具颠覆性和剧烈变化的经济时代,大器晚成的人,你们都在哪里?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像罗琳和费希尔这种成功的大器晚成者,他们都经历了早年的尴尬和失败,起步缓慢,到中年才从容不迫地走向成功。他们的故事与今天崇尚新潮的社交媒体文化并不合拍。罗琳现在已经50多岁了,费希尔也60多岁了。
在这个成功天平的另一端就是少年得志的人,也就是早年走上巅峰的人生赢家。身高1.55米的赖利·韦斯顿就是个奇迹。她19岁时就同沃特·迪士尼旗下的试金石电影公司签订了30万美元的合约,为美剧《大学生费莉希蒂》编剧本。韦斯顿也因为在主流电视领域早早起步的成就而被《娱乐周刊》评选为好莱坞最有创意的人士之一。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赖利·韦斯顿当时其实并非19岁,她实际上已经32岁了,她的真实身份是金柏莉·克雷默,住在纽约州波基普西市。她在为自己辩解时表示:“如果他们知道我已经32岁了,就没人会接受我了。”她说的可能也没错。
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早慧视为一种优势。2014年,17岁的巴基斯坦女生马拉拉·优素福·扎伊成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她还获得了萨哈罗夫奖及西蒙娜·德·波伏娃奖。在科技领域,Oculus VR(虚拟现实设备公司,以20亿美元被脸书收购)的创始人、年仅21岁的帕尔默·洛基变成了虚拟现实的代言人。14岁的少年罗伯特·内伊开发的手机游戏《泡泡球》让帕尔默·洛基在两周时间内就吸金超过200万美元。2017年,应用色拉布开发商公开募股让26岁的埃文·斯皮格尔身价飙升至54亿美元。但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相比,斯皮格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2018年,34岁的扎克伯格已经变成了成熟稳重的企业家,他的身价达到600亿美元。
少年精英是当今杂志百谈不厌的主题。《福布斯》每年都会评选“30位30岁以下”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今天的行业变革者和明日之星。不只是《福布斯》一家杂志在热捧这些少年得志的名人,《纽约客》《财富》《时代周刊》也有盘点青年才俊的榜单。
赞美和鼓励这些少年成名的现象并没有什么错。所有类型的成就都值得大众肯定和称赞。但今天强大的时代思潮让人们认为,仅仅获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过度追捧少年成就——考试分数、光鲜的工作、金钱、名气的风气之下,多少人忽略了在背后不断作怪的虚荣心: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没有在高考中出类拔萃,进入顶尖的十所名校,推动一个行业变革,或者在高大上的企业找到第一份工作,我们就多少有点失败。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造就了一个患上“少年成才狂热症”的社会。
现在这一切有什么不同吗?少年得志者都上了新闻头条,但他们后来真的像媒体让我们看到的那样,一生春风得意吗?事实上,有许多少年得志者并不能承受这一切。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甘恩高中,就有3名学生在2014至2015学年因少年有成的压力而自杀身亡。这3人都是努力进取的好学生。在同一学年的3月份,该校有42名学生因产生了自杀念头而入院就医或接受治疗。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青年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不断攀升。今天,达到重度抑郁或焦虑症诊断标准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数量至少是20世纪60年代的5倍,甚至是8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近发现,在美国高中生中,有“16%的学生曾认真考虑过自杀这个选择,13%的学生制订了一个自杀计划,还有8%的学生在参加调查之前12个月就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些数据真是让人脊背发凉。除了许多美国文化潮流,我们自己似乎也在对外输出自己的焦虑情绪。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抑郁症是导致全球青少年患病或致残的主要原因。
过去如果有人被当成潜在的大器晚成者,就意味着他们的活力、耐性和勇气得到了肯定。如今,人们越发将大器晚成视为一种缺陷(你起步晚肯定是有原因的)及一种安慰奖。这是一种糟糕的趋势,它会弱化那些让我们长大成人的要素——我们的经历、韧性和终身的成长能力。
即使是少年有成者也难免因为遇到挫折而受到质疑。早年出类拔萃的女性尤其容易因为后来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而感受到外界的恶意。卡罗·费曼·科恩就是一个少年有成者:她曾经是波莫纳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后来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了洛杉矶的一家投资银行,在30岁前就成了那里的明星员工。后来她的人生发生了转折——自从生养了4个孩子,科恩的人生就迅速跌落到了低谷。当她试图重返投资银行时,却发现职场的大门已经向她关闭了。经过一周的挫折和抓狂,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感觉自己的信心完全崩塌了。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一切都不同了。”
科恩懷疑自己并不是唯一感受到这种落差的人。她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开创了一家公司 iRelaunch。公司关注的是经历过事业中断期并希望重返职场和开启事业第二春的职业人士。该公司的自我定位是“重返职场”的专家和顾问,面向的客户是有意回归职场的职业人士和打算雇用这些人员的企业。科恩针对这个话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写了许多文章。这位曾经的少年有成者,现在就成了一个重新起步的大器晚成者的典范。
事实上,我们许多人都是某种类型的大器晚成者(或者潜在的晚成者)。我们会在某些节点上进入瓶颈期。我就有许多年一直没有什么成就。25岁那一年,虽然我有名校的本科文凭,却只能干一些洗碗工、守夜人和临时打字员这种工作。那时候的我实在是天真幼稚。这种始终处于人生起步状态的境况,当然也就毫不意外地加重了我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回首那段岁月,我已经能够原谅20多岁的自己。
这是不是也很像你的情况?你家的小孩也是这样吗?如果在学业和事业早期,我们背负了过多成功的压力,我们就会产生恐慌情绪。但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更轻松地前行。大脑的行动能力完全成熟的年龄应该是在我们25岁左右。
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这名大器晚成者,在校期间甚至算不上是个优等生。他告诉我:“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教室窗外。就算你拿一把枪逼我,我可能也还是无法专心听课。”凯利的大脑在那时候还没有作好起飞的准备。
比起马克·扎克伯格,我们许多人更容易在斯科特·凯利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也有一些笨拙摸索的起点,经历过彷徨困惑,跌至事业或教育上的低谷,染上一些坏习惯,撞上霉运,或者缺乏自信。不过我们大部分人很可能因为机缘巧合,获得一些智力或精神上的觉醒。人们无论在哪个年龄或哪个阶段,都应该清楚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
(摘自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大器晚成》 作者:[美]里奇·卡尔加德 译者:范斌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