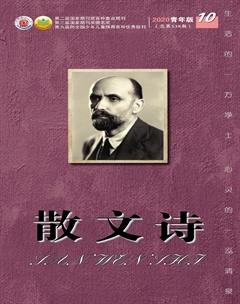羁风之逆
王雪茜:从事散文随笔写作。在《上海文学》《天涯》《鸭绿江》《文学报》《作品》《湖南文学》《雨花》《四川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西部》《朔方》《南方文学》《黄河文学》等国内诸多文学刊物发表大量长篇读书文化随笔及散文,多次入选《散文选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等选刊和选本。
我从未在别处与他相逢。
传记电影《心之全蚀》中,扮演他的演员是颜值巅峰时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不羁的金黄色卷发裹挟着小城夏尔维勒多梦的野风,蓬勃的眼神桀骜中混杂着童真,瞬间点燃了“诗人之王”保罗·魏尔伦那颗驿动的心。
“兰波,你最怕的是什么?”
“我最怕的是别人认为我跟他们一样平庸。”
缺失父爱又被专断母亲管控的少年受够了日复一日的黄昏与白昼、平庸与恶意,他疯狂地迷恋上了“自由的自由”。隔着屏幕,我仍能清晰感受到他梦想拥有改变生活秘诀的庞然决心。
1871年9月,魏尔伦收到了来自外省的8首精彩绝伦的诗,署名皆为一人——阿尔蒂尔·兰波。他立刻回信写道:我亲爱的伟大灵魂啊,到我们身边来吧,我们呼唤你,期盼你。
如白日之火,少年兰波乘醉舟而来。“当我顺着无情河水只有流淌/我感到纤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醉舟》)。此前,羁风之人(魏尔伦对兰波的称呼)已三次离家出走。在边陲小镇舅舅库房中古旧书籍间的冒险,激生了兰波想象中的最初意象,虚拟中的旅行与幻想中漂泊的幸福加速了语言的“炼金术”。“坐在路旁/我凝神谛听/九月的静夜/露珠滴湿我的额头/浓如美酒”(《流浪(幻想)》),露珠刹那而危险的美,正好互文了未来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1871年2月,兰波曾流浪至巴黎。3月,巴黎公社运动爆发,兰波加入了自由射手队,写下了许多同情巴黎公社的诗作,彼时,兰波衣衫褴褛、酗酒、吸食大麻……肆意特立独行的放荡之欢何其淋漓!即便兰波本人,也未料到,日后在法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掀起巨浪的名字,正是不朽的阿尔蒂尔·兰波。
离家冒险时最快乐,怎么走都走不够。兰波,这位发狂,聪明得发狂的履风者,不由让我想起困囿自己人生的无数小黑洞,以及穿梭其中的逍遥自在的风。小时候看过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欢愉的《拉兹之歌》鼓舞了我膨胀的流浪之心——“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既心有所向,何惧素履以往!有谁没梦想过仗剑走天涯?可醒来后忙碌的依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奔向远方的心最终被细密的世俗之网扯回,我们迷途知返,便也泯然如故。
每时每刻,兰波都想重新上路,追逐大海,触碰太阳——“拳头揣在破衣兜里/我走了/外套看起来相当神气/我在天空下行走……”(《流浪》),出发,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中去,虽然他不知道该去哪儿,只是漫无目的地走,去体验从未体验过的丰富多彩的时光。“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感觉》),走,一直走,到非洲,到沙漠,到不确定的远方,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萦绕兰波梦境的是荒漠驼铃与火车的轰鸣,水面下的气泡已缓缓升起,穿过冷漠成为了一个新的体系。即便是梦中呓语,煽动唇舌的也只有一个词语:go(去)。
评论家说兰波是朋克和垮掉派先驱,我倒觉得有点一厢情愿了。兰波可能无意为之,虽然骄狂傲岸,放荡不羁,把流浪当作专业的追随者不乏其人。手持成名魔法棒的兰波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闪闪发光的偶像,他传奇的一生为后来者确立了一种生存和反叛的范式。一串后来在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成了兰波异界表达的接力者——艾伦·金斯堡、威廉·博罗斯、杰克·凯鲁亚克……你看,杰克·凯鲁亚克将破破烂烂的手提箱,又一次堆放在人行道上,“道路就是生活,真正的人都是疯疯癫癫的”。是的。你不妨读一读那名叫詹姆斯·鲍文的流浪歌手与一只叫鲍勃的流浪猫的故事,或者在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追随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的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他认定最勇敢的行为是去新的地方做新梦,而不是在旧梦上缝补编织;曾当过报童、水手、码头小工、纺织厂工人的杰克·伦敦,16岁时便已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流浪,更曾因“无业游荡罪”被捕入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个骑士”的诗人赫尔曼·黑塞为找到自我,踏遍欧亚,创作了著名的流浪体小说《漂泊的灵魂》,主人公克努尔普一生流浪,居无定所,尽管他魅力无穷,所到之处充满欢乐,最终却孤独离世。“我感觉我虚度了一生。”他对上帝说。“你来这个世界的意义在于唤起芸芸众生对自由的一点思念之情。”上帝回他。
兰波不信上帝。这位幼時便写下“上帝去死”的渎神者却想拥有诗人的第三只眼,他如此竭力地想要离经叛道,像文森特·梵高画笔下野蛮生长的鸢尾花,在黑白颠倒的花园里显得格格不入。而离经叛道不过是表层的载体,暗波汹涌的是他咆哮的天赋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择乐之道,莫大乎与浪子同游。1872年,魏尔伦抛妻弃子,与兰波私奔,两人流浪到比利时,从比利时的奥斯当德上船,坐游轮去往伦敦,这是兰波第一次看见梦想中的海。为继续写作或苦于无法继续写作的迷失状态,于是纵酒,醉舟载着两人浪迹天涯。被酒神亲吻的地狱伴侣纵享天堂般的快乐。兰波从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当众朗诵自己的诗歌。
“晚餐后你也许会为我们念一首诗?”
“不,我不念。”
“别的诗人都会念。”
“别人怎么做与我何干?”
他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诗歌有任何的侵入,包括他自己,这无疑印证了兰波最初的孤独。也许,只有通过流浪,不停地流浪,才能体验这种美妙的孤独。他对没有出发的生活感到害怕,对无效而漫长的人生充满恐惧,仿佛复制粘贴的生活是无底的陷阱。
“从骨子里看,我是畜生。”兰波自诩。这话不必当真。半个多世纪后,一位名叫格雷戈里·柯索的街头流浪儿、少年犯,几乎复制了兰波爆炸式的反叛、尖锐的天赋与起伏的人生,后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我的灵魂里面有一个阴影。”柯索大笑着呼应兰波。我仰头,看见天才站在针尖上,拥抱最具煽动性的良知。
在魏尔伦的书房,兰波对着镜子模拟狗吠(他也曾爬在山坡上学过羊叫),偷走魏尔伦岳父的十字架;在公寓楼上,他裸体站在阳台,将脱下的衣服扔到大街上目瞪口呆的人群中(格雷戈里·柯索的同版动作是在旅馆门口掀起大衣扒掉长裤);在诗人聚会上,他打架撒尿,狂言不逊,认为所谓诗歌聚会是对法国诗歌的屠杀……他为放浪形骸而放浪形骸,而兰波反主流的尖锐放浪不过是孤独的另一种声音,是另类的哑默,是无声的喊叫。“我已将泪水流尽,全新黎明”,身为个人已然不够。兰波决定成为所有人,成为诗界的盗火者。而天才少年文思泉涌,绝不想在挣钱上浪费时间,也不在乎作品出版与否,他只在乎写作本身。
“我资助你,你比我超前太多了,我永远也不明白你作品中的深意,我就像是个老古董,而你将重新铸造我铁锈般的陈旧灵感。你的作品一旦问世,读者便会对我魏尔伦不屑一顾。”
“写作改变了我,而我身边是一个奴才——丑陋、谢顶、年老酗酒的抒情诗人,陷于自以为是的忧虑。别指望我忠诚于你。”
像黎明睁开蓝鸟般的眼睛,轻翅无声地飞起。兰波彷徨痛苦,神魂颠倒,单纯又狂躁,睿智又愚钝,他葱茏的天赋异禀被妄图震撼他人的幼稚渴望抵消了。他狂乱地寻找自我,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他觉得必须经历各种感觉长期、广泛、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才有可能成为词语的通灵者,这个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的至高无上的智者,一心想界定未知。未知的创造呼唤着新的形式,当他陷入迷狂,终至失去视觉时,却看见视觉本身,他培育了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灵魂。(参读兰波书信1871年5月15日)在《地狱一季》中,情绪跌宕的兰波饮尽疯狂。而过早沉入玄思冥游,竭尽天赋,终究不过遁入反“常”、反宿命的深渊。
若从艺术观,我觉得兰波的散文诗尤为卓荦通灵,《兰波作品全集》里最让我视如珠玉的便是《彩图集》(另一个中文译名《灵光篇》更贴切)。兰波率性的、完全个人化的性格特征与散文诗的特征不谋而合,散文诗更宽阔的自由度、更丰富的可能性,使兰波在以革新句法、紧凑节奏以及拂乱意识来快意思想、营造新感觉新境界的极端尝试中获得了另一种“和谐的不连贯”(瓦雷里语)。“神奇的花朵嗡嗡作响,斜坡摇晃”,这种语言来自灵魂并为了灵魂,芳香、色彩和音调,通过思想的碰撞放射出闪电般的光芒。他的目光喷火,血液放歌,骨骼膨胀,泪水如红色溪流,他独自掌管着这“野性剧场”的钥匙。“我大概还有一段路程要跋涉,我需要把聚集在我头脑中的魔狂驱散。我爱那大海,仿佛它可以把我一身污秽洗净,我看见给人带来慰藉的十字架从海上升起。”兰波说,“我是被天上的彩虹罚下地狱的。”他将夏日的炎热付与喑哑的飞鸟,凭借死去的爱情和芳香下沉的小海湾上航行的悲悼的小舟来抵御辗转异乡附加的慵倦怠惰。跳跃意象、错位幻想,或至有步骤地打乱自己的感觉系统,让“全部感官按部就班地失常”,以求看到、听到、感到凡人所看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的东西。
与魏尔伦同气同忧的王尔德说,爱始于自我欺骗。1873年7月,在布鲁塞尔,魏尔伦枪击了兰波,被判入狱(此前兰波用刀刺穿过魏尔伦的手掌)。对兰波来说,现实委实太棘手。暮色四沉,世界淹没于黑色的泡沫,梦幻的生路塌陷,虚幻的激情消弭,本以为写作与众不同,可改变世界,非凡无比,未曾想世界太老,万物都已言尽。怀抱绝望写作的他,亦怀抱绝望停止写作。1874年,写完最后的诗篇《彩图集》后,19岁的兰波去往伦敦,从此远离文学。此后17年,兰波在马不停蹄的放射性流浪中度过。
他终于成为了另一个“我”,一个回归到真实尘世的人,一个与文学割断了血脉的人,同时也成为了自己曾最为鄙视和厌弃的人——为了金钱而不断求索。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亚丁……他做过雇佣军、监工、翻译、武器贩子、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他与非洲女人同居,心在双性的腹中跳跃,在最世俗的生活中奋力冲向生命而非文学的未知。他生命中的危险因子在微妙的冒险精神提供的弹性中葳蕤生长,又潜萎暗落。这个一心想通过流浪摆脱孤独的人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孤獨的人。这矛盾不安的灵魂践行着自己悖论中的和谐,在身疲心裂的矛盾中探求存在与超越。“我愿成为任何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神明不佑护流浪者。自入苦圃的兰波不复倜傥,朋友形容他神色冷峻、面貌憔悴。我看过兰波妹妹伊莎贝尔·兰波所画的兰波临终肖像,他蓄着胡须,倔强的蓝眼睛乌青浮肿,似闭非闭,星光熄灭,如落日倾泻下蔷薇花忧郁的阴影。所谓穷途必然末路,而兰波之所以成为兰波,正在于他迷途而不知返。木心评价兰波的天才模式是贴地横飞的伊卡洛斯,以蜡封的假羽搏风直上,逼近太阳,以致灼融羽蜡,失翅陨灭。1891年2月,因非洲的瘴疠溽热和关节炎感染,37岁的兰波腿染恶疾且日益严重,11月10日,做了截肢手术后的兰波悲惨去世。临终之言是对邮船公司的经理说的,“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送到码头?”
在哈勒尔的香蕉园里,兰波拍下了自己双手交叉的照片,“这些相片只是为了记录我的疲惫”。荒谬而累人的工作使兰波想逃离到更远的远方。1880-1881年,位于红海之滨的亚丁港,成为兰波流浪的栖居地。当时的亚丁是个不可思议的熔炉,其中包含了阿拉伯人、印度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中国人、索马里人等。19岁前,兰波热心政治,远离家庭,为发明新的语言付出混乱的代价;19岁后,兰波几年不碰一张报纸,甚至不再阅读,后悔没有结婚成家,决然放弃他认为“不道德”的文学。这一切的冲突在兰波看来,既不可思议又自然而然。
尽管贫穷病痛如影随形,但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别指望我性情中的流浪气质会有所减损,恰恰相反,如果我有办法旅行,就不必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工作,以维持生计,人们不会看见我在同一处住上超过两个月。世界很大,充满了神奇的地域,人就是有一千次生命也来不及一一寻访。”但同时,他又说,“我的生活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我已无力再在这个世界上徒劳奔波……精神上的搏斗和人间的战争一样暴烈。”妙就妙在(不妙就不妙在),兰波是一个说服自己按照自洽法则生存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他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过得顺理成章,并在对自己的否定中完成了对自己的肯定。
“把自己交给上帝请求他的宽恕吧,希望你能找到生命中的方向。”
“可我不需要方向。”
天才不需要经验上的引渡。而今,兰波已成为沉默的大师,没有人能撬开他。
“我死于疲惫。”兰波曾说。可他却以天使般的疲惫启迪了我们。读过兰波,我将重新看待世界与人生,我将焕然一新。
在文学的天空,兰波是“横空出世的一颗流星,毫无目的地照亮自身的存在,转瞬即逝”(马拉美)。他一边毁灭,一边照亮夜空。如果你寂寥落寞、悲观失意,需要重新点燃胸膛,需要一束光击碎潜藏在看似光滑无隙的表象下的恐惧时,我郑重建议你,毫不犹豫吞下兰波酿造的“这一口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