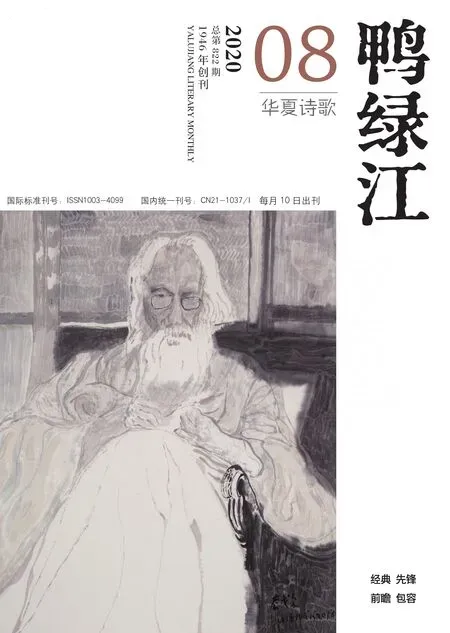江苏南京尘香诗群作品选
组稿:尘子
旧时光
尘子
手风琴是一把梳子,父亲用风梳理顺流年。
那年,我发现父亲抽屉铜制的簧片,会模仿风吹落树梢,模仿猫吃鱼发出的声音。我偷偷把它送给村里的少年。父亲修理手风琴时,得知我拿走了那些簧片,就顺便修理我。他押解着月色,一家家扣开门扉,一枚枚收缴回来。
村头槐树上的鸟儿,依然在啄食自己的鸣叫,一粒粒晶莹剔透。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些吴侬软语,折返时都长成秕谷,如鲠在喉。
我想起了祖父,他挑担稻谷走在虚构的田埂上。返乡的我——可以裹腹,却无法喂养日渐喑哑的歌喉。
祖父像岩石一样迎面遇上风的砂轮。我感觉有一双尖锐的犄角与心里一头看不见的牛,顶在一起。
尘子,本名张国安,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溧水区网络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诗选刊》《星星》《扬子江》《青春》《芒种》《散文百家》等。著有诗集和散文集。
梦中,在鄱阳湖
胡德清
每当忆起家乡,梦中的鄱阳湖就格外“精神”。梦里的事物,仿佛都在沉思。落叶哀叹轮回的无情。我听得到,那些在为轮回的赞歌作曲的人,正在为新的生命挤出最后一滴神液。
那座开满鲜花的殿堂,住着我们的梦境。我在叩问的路上,一直寻找自己多年丢失的钥匙。梦中的鄱阳湖里,每种生物都很忙碌,而我的存在,没有惊扰的意思。世上有比我高的树木,有比我低矮的灌木;有比我高的昆虫,有比我低的人类。我没有彷徨。
鄱阳湖的大小,我无法丈量。走在朝圣路上的我和鲜花、河流,也没人知道大小和深浅。
胡德清,原名洪欧洲,80后,现居安徽六安。诗见于《人民日报》《诗选刊》《诗潮》《星星》《扬子江》等。
他那消失的海
面朝大海
那么久,他在那里没动,站立的姿式如同石头。看到一枚落叶,仿佛一个人,在挣扎。一种不能抵挡的悲凉,叶一样落在他的心上。
“该回家了!”他喃喃低语。那天他把钥匙交给房东,心情就暗了。楼道极窄,刚好适合自己人生的宽度。落魄与潦倒把他挫败得不成人形,他把帽子压得极低,让他只能惊奇地探视别人的一生……
葳蕤的春季过后,充满了谬误。灰蒙蒙的雾里。游若丝线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用手指着村口,在诉说一件没完没了的事……而现在,他像一只犬,四处流浪。把自己丟进黄昏,空荡的街,空荡荡的人生。
面朝大海,本名韦中民,江苏人,70后。诗见于《作家报》《北方诗刊》等并选入多家选本。
荷塘夜色
浮云
把一天的疲劳置于一墙之外。在静静的荷塘月色中,品味月色缥缈。
踱步于池塘周围。夜诡秘而暮气,一座拱桥连接通幽的小路。月光、灯光的余辉交融于半月型拱身,杨柳轻盈的桥下,似画家在镜面上渲染的一幅构图精美的笔墨画。
我偎依在柳枝旁沉思,如果荷塘缺少了柳的妆点,是否缺少了一些柔情和浪漫?绕过一座亭子,是一片空阔之地。瞬时仿佛与天空拉近了距离。星儿低垂,颇有“手可摘星辰”之感。久违的星稀月疏今天都抢眼似的在举头之上,微笑着。
此时,几声鸟啼划破了宁静,不知名的鸟也耐不住寂寞。你猜不出它是什么鸟,夜幕中看不见它,只知它在隐秘的林里,不知它栖息何地?它吼叫的意思是什么?是看我闲适悠然或形只影单吗?哦,我就是那杨柳岸边的倒影,小憩着等待黎明。
浮云,本名曹广杰。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诗见于《中国诗人》《北京诗人》等刊。
心事
阿光
先于雪花抵达内心的,是母亲伫立在家门口的身影。我无法计算出这双目光的密度和重量。黑夜,一再沉默,一朵朵雪花整齐地在屋檐上排列,讲述着季节更迭和天地的广阔。旷野无边,一条通往村庄的小路,露出深深浅浅的脚印,木质大门上挂起的红灯笼透过行云流水的雪花,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味道。
母亲的腊八粥,熬了又熬。
腊月的乡村,雪后初晴的寒冷击溃了灯火阑珊。夜空的弯月像母亲手中磨亮的镰刀,收割着工棚里匆匆收拾行装的身影。这样的场景,只能发生在农村,只有在农村的土地上,才能有更加辽阔的空间来盛放游子的相思。
阿光,本名陈光美,江苏省作协会员。诗见于《扬子江》《星星》《芒种》《光明日报》《诗选刊》《绿风》《诗歌月刊》《人民日报·海外》等,偶有获奖。
洞壁琴音
方述怀
走进秋山时,只见那竹影婆娑而薄雾轻笼,烟雨潇潇且轻柔飘洒。朦胧处的一曲悠扬琴音,不知是谁人弹奏?它若影若现,令人迷醉。这莫不是我梦中的伊人,正拨动琴弦,营造出这古乐仙境……
或许,像父亲那样从前线过来的人们,才更加珍惜如此的和平和安宁吧?比如这个洞壁,我们沿着木栈道一路寻觅着罕见的清静,并且与一座座古采石场不期而遇。石头,是远古的使者,它们充溢着时光的痕迹,被雕刻着历史的浪漫。而雨落石壁似跳动的音符,在心灵深处,谱成一曲天籁之曲。原来,精美的石头真的会唱歌。
琴音悠悠,岁月无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这片沃土也是乡民们用勤劳的双手耕耘出来的。
方述怀,江苏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诗歌散见《青春》《诗潮》《人民日报》等。
雨
毛文文
这雨天好像已进入“复制粘贴”模式,连续几天都这样。雨下大的时候,像我父亲干活时甩出去的牛鞭,劈啪作响,同时也赶走了山谷里的寂寞。
周末,不知如何是好?我赶回老家,惬意地躺在母亲叠好被子的木床上,听着雨声,看着窗外矗立的桃树,上面业已挂满了桃子,它们饱满地在风雨中摇曳……
夏意已浓,我好像还沉浸在春天,迟迟没有回过神来,我依然喜欢那河畔的柳绿。
我又来到瓜地,匍匐的藤蔓,和青葱的夏草似乎有心纠缠。而父亲的咳嗽如同雷声,渐渐逼仄,也像地里叫累了的蛙鸣。父亲经常沉默着,没有多少话说,尤其在落雨的时候,他的眼神如同苍鹰,在地上、院子里、田野,想抓住什么……人老了,是不是他的田野也在缩小?
毛文文,1966年生,南京人。江苏省作协会员。诗作散见《诗潮》《上海诗人》《山东文学》《扬子晚报》等。著有诗集《春天的雨水》。
爱人
剑峰
再见之后,两颗心便席地而坐。我们的幸福像花朵,感觉彼此的倾诉在敞开。我们享受着阳光,明眸里闪烁的光源,源自纯真对纯真的回答。
爱人,你目光柔如太阳之手,御我一生风寒。与你对视,我不知道你潜藏的笑到底有多深?相偎着。任斑斓诉说爱的故事,任冷风涂上暖色的格调。谁用手触摸往事的伤痕?让我感知幸福和温馨。
爱人,记得我第一次拥抱你,是怎样的一种虔诚?那种神圣陶醉的感觉,使我心明如镜。谁用蘸满柔情的爱笔,挥洒不褪色的青春?你曾告诉过我: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我们莲如并蒂,怎样的日子使我们的思念无边?
哦,爱人。我生命中的春天谁热切地思恋过?像河边的芷草一样圣洁。我伸出的手臂一片葱茏。我们彼此打量,几许惆怅算得了什么?
剑峰,本名胡建中。中国作协会员。诗见于《诗刊》《星星》《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散文》等。现为湖南省新化县文联秘书长。
山村里的父亲
杨孝洪
布谷声声,用镰刀割收着夜晚。而老牛与父亲,是两把正打开黎明的钥匙,在新修的柏油路上寻找着锁孔。父亲的背,像一张犁。父亲的犁又像一张背,这并不矛盾与啰嗦,背和犁都在耕耘。它们,在早晨的阳光里结为异性兄弟,在多年的乡村中,延伸着远方和憧憬。
父亲把自己编为牛绳,老牛在父亲的侧身里让路。——这是他们多年以来一直达成的默契。山村歪斜的影子里,装满了小草与野花的笑,也装满了露水和村庄对游子迎来送往的泪水。
岁月在父亲的头上布着霜,盖着雪。有时父亲却有一颗拒绝衰老的心,拒绝平庸的心。他不甘时光在他的怀中慢慢枯竭,所以农活里的每一个动作,都像在抨击与抗拒。
父亲的骨骼深处,有一匹奔腾的马。那匹马,是他永远的图腾。
杨孝洪,笔名杨稀,南京人。诗见于《青春》《萌芽》《扬子晚报》等,偶有获奖。
拖着义肢飞翔的人
朱银梅
每挪动一步,他的义肢与肉体都摩擦出“嘎吱”之声,像一只老旧轱辘,在室内又艰难地转了一圈,衣背早已湿透。曾经奔跑在球场上的身影,如今步履蹒跚,左腿高位截肢,只能靠腰部的力量带动。这或许才是真实的“坐立不安”。
然而,坚持——是对自己的一份尊重,是对教师职业的尊重。
他踱向孩子们,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肩,用目光鼓励每一次举手。他放弃优厚的工伤待遇,放弃学校清闲的岗位照顾,用义肢支撑起高义的灵魂,带着可爱的小生灵们飞向广阔天空。
妻子颤抖的双手,在他浮肿的肢体上摩挲,替代不了的疼痛在心里深藏。
孩子们懂得他每一个缓慢步子里隐藏的寓意。阳光,从生命的裂缝照射进来,引领着人们。
朱银梅,笔名吟梅。诗见于《长江诗歌》《扬子晚报》等,偶有获奖并收入诗歌选集。
母亲
窦玉萍
母亲年事己高,走路需人搀扶。蹒跚的背影,花白的头发。
在水库坝上的休息梯上,汹涌的水流被阻挡在水闸一侧。看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水,一阵心酸:为什么不早点拿自己的人生当回事,非要等到走不动了,才想看看天外的风景?我撑着伞,走在这风雪交加、烟雾迷茫的九孔桥上,有一种事物在牵扯我的心肠,好像千年前我己来过,唯一遗憾的就是这桥上少了一个我深爱的人。
站着,抚摸被风雪打得遍体鳞伤的桥,抚摸桥墩,仰望着桥的那头,看看是否还会有奇迹出现。可这天空,灰蒙蒙的,雪也猛烈地下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桥的那边飘来了音乐声。忽然,眼前浮现出母亲弯腰曲背,走过九孔桥的身影……每一个桥孔里啊,都有一个母亲。
窦玉萍,女,江苏溧水人,诗作散见《扬子晚报》《江苏工人报》《青春》等。
当岁月走不动了
谷玲玲
终有一天,岁月会走不动了。步履蹒跚,而我也会开始回忆,并且成为每日的习惯。泡壶茶,任其慢慢冷却,然后坐在摇椅上看看风景。天空啊那么蓝,阳光明亮,梧桐叶边缘的绒毛清晰可见。而我的记忆摇曳不定,模糊不清。我已变得健忘,等到很多事情都忘记了,连自己的年龄也不甚确切。
终究要别离的,生命的最后也只是单个的自己与事物逐一告别。有些别离隆重,有些别离匆匆,有些别离让我们猝不及防,还有一些别离甚至连告别都没有告别……
我爱的人,那是初识的悸动与欢喜,那是仿若星辰般的光芒万丈。可却忘了后来为什么分开?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决绝地相忘于江湖,老死不相往来?
我仍然记得那明亮的笑容、深情的眸光、优雅的谈吐,还有快乐无比、活泼如兔的青葱年华。
当岁月走不动了,就不要刻意去计较那些得失。
谷玲玲,笔名清影,南京市作协会员。热爱古琴和文学。著有小说集《暗香盈袖》、长篇小说《此去经年》等。
塔尔寺
张友国
计划了很久的远行,可真正坐在高铁里时,我们却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我在想:塔尔寺应该近了吧?其实不然,一切有远近的距离都是人为的划分。我被远走高飞的家乡忘掉了吧?
不敢去寺庙。那里狰狞的金身是一方的神明,不允许我有任何亵渎之意。我不知道神明是由常人无法忍受磨难之后的大悟,还是含着舍利子转世来救赎苍生的?多年之后的此刻,车再次经过莲湖时,我的心开始平静……
湟中的鲁沙尔镇,是个尘土飞扬的下午。我开始祈祷:“多年的打拼,又有何值得炫耀的呢?”正如鲁沙尔的尘土飞扬。
我庆幸什么?多年来庇佑我的除了母亲,还有来自内心的“神明”。塔尔寺,只是我眼中的神,那么,暗中的神在哪儿?
张友国,笔名雨叶脉、半室等。70后,南京人。作品发表于诸多刊报。喜欢文学、摄影以及国画、篆刻。
青海,青海
剑鸿
来这里之前,从未听说过宗喀巴,更不知道因它而建的大银塔。八座白塔,伫立成一列。更让这里多了几分肃穆和庄严。我一遍遍地抚摸转经筒,尽管我不懂“大悲咒”等……从菩提树下觅起一枚飘落的树叶,心底不由得生出幸福和安宁。
白云朵朵,倒映在一片蓝色之中。我分不清哪是湖水哪是蓝天?绿色的地毯和金黄的油菜花融为一体。在西部,在高原,再没有一座湖如此深邃。采一朵湖边的格桑花,心底就升腾起一轮最美的月亮。凄凉的诗歌,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繁华,多少人带着希冀来到这里。这里,早已经不是最后的草原。这里的石头承载着历史,这里的青稞不只属于它自己,德令哈——是“金色的世界”。
不停留是不想触碰诗人心底的伤疤。青海,青海,我一路向西,一路向上。
剑鸿,本名于建宏。江苏省小学“十大书香”人物,江苏省诗教先进个人,盐城市全民阅读优秀志愿者。诗见于《中国诗人》《扬子晚报》《2016江苏新诗年选》《中国诗人年度诗歌选集2017》等。曾获滨海县“政府文艺奖”。
赏雨
许超
被丰沛的雨水充盈。天地间,一张无边巨大的网。但这并不让人窒息。此时的雨,不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那种,天和地在雨中,越来越透明。菊花脑,也在雨中,它呈现亮色,悄悄地从去年的腐败处新生。雨水从瓦当上滴落,清脆的声音足以唤醒我的蒙昧之心。
“草色遥看近却无。”雨后的草窠里,地皮菜想做一回大地的耳朵,它伏在草上,借助草的根系,探听雨水的深度。
雨水,仿佛只是一个人的故乡,朦胧中长长的堤坝、那些少年的身影……在雨后的早晨,鸟站在树上,它凌驾在枝头的技巧同那个滑板少年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不仅仅是在炫耀一种勇气。
空无一人的小巷,一个年轻的女子在远端出现,用曼妙的狐步踏歌,而当我回头,她又用青苔丈量着雨水。这多么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以慢的方式让我心生爱恋。
许超,1984年生于安徽寿县,现居南京溧水。《中国校园文学》签约作家。作品散见《散文》《散文诗》《散文诗世界》《散文百家》《雨花》《滇池》《岁月》《诗歌月刊》《青春》等刊物。有作品入选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