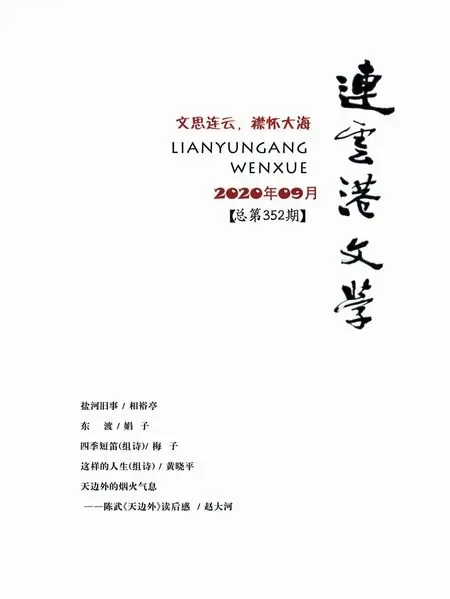邂逅木兰花(外两篇)
王秋侠
那份欲说还休的情怀,是伴着温泉民宿的一株木兰花开始的。木兰花,绿叶、淡黄白色花,清雅,幽香。
秋日的温泉,每一寸时光都有欢喜。在温泉民宿一家小小的院落里,偶遇一株盛开的木兰花。我与木兰花,应该算是久别重逢,内心不胜欣喜。
20 多年前,在赶往南京火车站的路上,第一次见到木兰花。人来人往的石拱桥上,一位老妇人挎着一篮子花,边走边叫卖:“木——兰花!”那叫卖声,好似裹着木兰花的香味,细细的、柔柔的。过桥的女子们,三三两两地走过去,买一朵,别在领下的衣襟上。我急着赶路,隔着那些买花的女子,嗅着从花篮里飘出的缕缕木兰花香,匆匆踏上归途。
一朵小小的木兰花,让我念念不忘。
国庆长假的一天,随一群文人游客前往东海温泉度假区采风。
温泉民宿坐落在温泉度假区驻地,在福如东海大酒店的风景区内,是一个有着江南民居风格的别墅群。两间,上下两层,带一个狭长的院落。
温泉民宿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是天然的温泉了。
“民宿到处有,可是有天然温泉的民宿,少之又少啊!”秋光满院,游客们一步一景,惊喜心动之声不绝于耳。更令他们艳羡不已的是,每套民宿都有天然的温泉管道通进来。院子里有露天的大浴池,可同时洗浴三五人;也有小浴池,满足私人私密的空间需求;还有室内温泉,淋、泡随心所欲,洗浴的时候可以看防水电视。浴罢,K 歌、下棋、打麻将或是会客、谈商务,随客人心情,都有专设的房间。
访客左右观瞻,上下打量,目光深情流连,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本以为随着采风团,闻着热闹声,默默地看个盛景,“到此一游”。没成想,院内一株木兰花探出回廊的窗外,一朵又一朵地出现,让我眼前一亮,心头一热。花似故友,笑容清浅。彼此相对,相顾一笑。
原以为,只有到江南才能看到木兰花。早相识,初相知。木兰花前,俯首拾翠色,扬手嗅幽香。触景生情,一样的花容,不一样的,是我容颜老去,意态萧索,然而心里却是一样的款款依依。
木兰花的主人,是个地道的东海人。上班族,颇有文人雅兴,古玩典藏、琴棋书画,精巧微妙,不一而足。到访的客人啧啧称奇:“这,哪里是民宿啊,一脚进门,分明就是踏进苏州园林了嘛。”
主人为木兰花营造了一个浓缩版的“江南园林”。40 平方米左右的庭院,精巧别致地布置一条回廊,回廊两边的镂空格子上,随意摆放着从各地搜集来的艺术品。回廊折处分隔出花卉区、品茶间、会客间,假山、怪石、鱼池。花花草草点缀假山,池内锦鲤在各类水生植物的根间,成群结队地来回穿梭。
一套温泉民宿,尽是花草、字画、各类水晶摆件等,浓缩江南风情的诗情画意,雅致,有情趣,还有贵气。
出了温泉民宿,走在平整的柏油路上,抬头,有云过天庭;四顾,有凉爽的秋风,带着四周植物的气息,柔柔地吹到脸上。
行程匆匆,木兰花含笑而立,似久违的故人,匆匆一晤,转身一别,就是山长水远,让我久久不忍离去。
一朵木兰花,那份熟悉的心动,牵连着岁月不曾抹去的痕迹,分明就是故地、故人、故情。一念,一生。
红尘细软
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被我视为红尘细软,珍藏。
一双手工布拖鞋,半成新,我不舍得再穿。布拖鞋是姥姥去世前做的,想念姥姥的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手触细密匀称的针脚,感受那份永不再来的温暖和慈爱。
旧时月光里,慢工细活,打糨糊、粘布,划样、裁剪、纳制,紫红的毡绒鞋面、厚薄适中的千层底,70 多岁的姥姥临窗,一针一线,有花香就缝上花香,有阳光就缝上阳光。寂静、寡言,孤独守候的姥姥,心里牵挂的尽是她的那些儿女、孙辈,牵挂他们的衣食冷暖。
幼时,常年住在姥姥家,一直到十多岁才离开。后来,每逢寒暑假就回姥姥家。记忆里,姥姥有一双白皙修长的手,成天忙碌着。冬棉夏单,一家人的四季衣服、一日三餐,几乎占据了姥姥的一生。姥姥心灵手巧,描龙绣凤一辈子,不知给多少人家的新娘子、新郎,做了多少新衣服、新鞋子。那时候的冬夜,透骨的冷,寒风呼呼地刮过来,刮得门窗嘎嘎响。煤油灯的影子在黄黄的泥墙上摇晃。姥姥给我一个玻璃暖水瓶,用絮了一层棉花的花布袋子装起来,放进被窝。我在床西头睡得暖暖的,姥姥在床东头倚墙缝衣裳、做鞋子,一屋子晕黄的光,有暖暖的感觉。
姥姥晚年时,乡村流行做布拖鞋。她就不停地做鞋子,冬季的棉鞋,夏秋的单鞋,各种颜色,大大小小摆满她的房间,等着我们回去穿,快乐地各奔东西。姥姥做的鞋子,针脚细密匀称,颜色清雅,穿起来合脚。疼爱我的姥姥,最后一次给我做了2 双鞋,托人捎给我。一双墨绿色的方口鞋,一双毡绒布拖鞋。那双墨绿色的方口鞋,朋友非常喜欢,恰巧她的脚跟我一般大,她没有姥姥,我当场大方地送给了她,连同姥姥给我的那份脚底的爱和温暖。
晚年的姥姥因白内障,看不见一丝阳光,灵巧的双手再也抬不起来穿针引线。姥姥对子女孙辈的爱,至无力、至临终。
我一直以为四时连绵,花开不败。姥姥会永远在那个院子里,等着我们如小鸟一样飞回来,围着她打旋,享受她给我们满满的爱与宠,再快乐地扇扇翅膀飞走。
暮年的姥姥,犹如一棵经霜的大树,立冬刚过,于寒风中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枯枝淡色,再也不能为她的儿女孙辈遮风挡雨了。最后一次去看姥姥,躺在床上的姥姥浑身疼痛,我坐在床边握着姥姥的手,贴在脸颊上,默默地心疼,流泪。
“乖乖噢,姥姥不能给你做好吃的咯,姥姥还想疼疼你,还没疼够哦……”
清苦的岁月,熬干了姥姥俊美慈祥的容颜。
油尽灯枯,姥姥安详地走了。
我的心里早已一片荒凉。过往的画面一幕幕闪过,姥姥亲昵疼爱的声音远远飘逝。姥姥与我,再不相见。
一双毡绒布拖鞋,是我的珍宝,偶尔拿出来贴着脸颊和胸口,心里瞬间温暖柔软,仿佛梦中的姥姥,风吹蓝蓝的衣裳,从天边走过来……
一件棉布睡衣,蓝底、水红色莲花图案,肩背处早已破旧,不能再穿,可我一直不舍得扔掉,叠放在衣柜里。睡衣是一个好朋友25年前送的。那件睡衣里,有一份柔软亲肤的情意。
红,衣着时尚、知性、优雅,是那种雨后彩虹般的美丽。
25 年前,红在县城工作,鼎鼎大名,得众人仰视。我在乡村,正青春迷茫,前途渺茫。城乡差距显而易见,处境悬殊、天壤之别。红,在我心中偶像一般的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县城认识了红。
故乡偏远,贫困落后。第一次进县城开会,从头到脚仔细收拾了一遍,坐上最早的班车,在砂石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下车就是灰头土脸的模样。会务处的门卫以为我是个上访的,上下打量,再三核对我的身份。那一段时光,觉得浮世苍茫,人生过得颓废而无望,处于无边的黑暗中。
红眼神清澈、温暖。她看我衣着单薄,面有菜色,依然笔耕不辍,就把我带回她家里,给我换上她的衣服。临走,红送给我蓝底、水红色莲花图案的棉布睡衣,那是我的第一件睡衣。
一面之缘,红的关爱像燃烧着的小灯笼,把我暗淡的青春岁月,照得色彩明艳。
买第一部手机,红帮我选的吉祥号,我一直使用至今;在县城买房,她帮我找人给我买性价比高的木地板。工作、生活上遇到了困难和麻烦,第一个给她打电话……
后来,虽然红去了另一个城市,我们很少再见,但我心里一直珍藏着她曾经给过我的那些温暖。
一册简装的文稿,经过千里辗转,再次回到我手上,便有了时间和空间的烙印,记忆和回忆的线索。“萍踪侠影”,有种亲人般的感觉弥漫心间,自然要喜欢,要善待。
在通往暮年的道路上,那些原本不经意的相遇,往事烟云,前尘梦影,常常会不期而至,浮现、盘桓于心间脑际,缭绕不去。在逐渐走向寂静的人生旅途中,却有许多刻意,只为途中,能重逢停在心底的那份温柔。
听梧桐细雨,看月满西楼。孤独寂寞的时候,借着那些旧物件,那些熟悉的身影,就会在我的心里一遍遍走过。
有些人,有些事,可以被时间轻易抹去,犹如草芥随风而散。但也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短暂的瞬间,在我的心中,却漫长成永远。
那些,都是我的红尘细软。
馋痨市
记忆里,乡村集市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吆喝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打招呼声此起彼伏,整整一条街,声音嘈杂,像个劣质、无边的大缸,持续嗡嗡作响。
那样的集市场景、那样的声音,是我少年时光“馋痨市”的背景及背景音乐。
村居平淡,烟火人生,难忘故乡集市上飘来的香味。
30 多年前,乡亲们把卖熟食的地方,叫做“馋痨市”。言下之意,去那里吃东西的,都是些嘴馋爱吃的人。当然,在生活清苦的年代,能去“馋痨市”买吃食的,特别是能坐在那里,拉开架势吃东西的,大多是村里的有钱人。“馋痨市”,只是乡亲们一种亲昵的叫法,并没有什么贬义。类似于村里有好多人家给自家小男孩取乳名叫阿猫、阿狗一样。“馋痨市”在那个年代,相当于时下各地的名吃街。
“馋痨市”,位于集市的中间地段,几条油乎乎、脏兮兮的破旧长条木板,用木架支起来,算是桌子,两边配上长条木凳,也是油乎乎、脏兮兮的。桌子上摆放一摞大黑碗,四五个深咖色的瓷碟子,也看不出干不干净。碟里放的大多是粗盐粒、大葱段、萝卜条、蒜瓣、青红辣椒之类。桌边油煎包锅、油条锅相隔三米左右,架在石头、砖头垒起的风箱灶上,炉火烧红,灶上大锅里油浪翻滚,手指长的面条随手丢进油锅里,“刺啦”一响,打几个滚,转眼黄澄澄的,变成尺把长。
油条的香味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一条街来来回回,在人逢中挤过来、穿过去,好像在热切地寻找着孩子们,把我们一个个拽到“馋痨市”。
手里没钱,衣着破旧,脚上的鞋子“空前”“绝后”。只能高频率地煽动鼻翼,把香味深深地吸进心窝。
一年四季的农闲时节,去“馋痨市”吃东西的,基本上有两类人:小孩和男性老人。没有出阁的姑娘是不会去那个地方的,婶子、大娘、奶奶们去那个地方,大多买了东西,放进篮子里就走开了。在我的记忆里,她们从没有坐在长桌边上,像老爷们儿那样,在众目睽睽下举手投箸。
最让人心动的,是油煎包锅盖一掀开,热气腾腾,半茶缸冷面水,旋转着泼进锅里,锅底立时响起“呲啦啦”的声音,热气再次升腾;盖上锅盖,几分钟过后,“呲啦啦”的声音渐小,再掀开锅盖,长长的铁铲沿着锅边快速地划转一圈,然后快速地平放进包子底部,一铲、一抖,一铲、一抖……给包子全都翻个面,再盖上锅盖,焖一会儿。我们远远地,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身边的堂弟小港使劲地吸着鼻子、抿着嘴,不停地吞咽着口水。
刚出锅的油煎包,两面金黄、酥脆,边缘还有细细金黄的丝,嘎嘣脆。那个诱人的香味,钻到我们心里,一个劲地缠呀,绕呀。堂弟小港下颌微仰,两只大眼微闭,舌头在嘴唇两边,快速、灵巧地摇晃着。两只脏兮兮的小手使劲地扯拽着缺角的衣襟。
刚上小学那会儿,老师要求上课要“认真”。我彼时就想,怎么个“认真”呢,怎样才能算“认真”呢?放学回家,赶紧去问邻居家的三哥。
“小港在‘馋痨市’看油煎包出锅,是啥模样?”
“哎呦喂,他就这样的喏。”我笨拙地学着堂弟小港的嘴馋模样。
哈哈哈!三哥又被我的滑稽模样逗得笑到不行。
“知道不?把小港看油煎包出锅的劲头,用到看老师写的字、说的话上,就是‘认真’的啦。”三哥通过举例子,把“认真”二字,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通俗易懂,但效果不佳。
课堂毕竟不是“馋痨市”呀,黑板上的字跟香气四溢的油条、包子也相差甚远。尽管我上课认真地“认真”了,也远不如“馋痨市”十分之一的专注。有时“认真”过度,黑板上的一个个字竟然变成一根根油条、一个个包子,在眼前飞来荡去。我眼神飘忽,老师一声呵斥:“看哪去了?!认真看黑板!”那些包子、油条在我眼前,应声退去。
在众多的堂姊妹、弟弟中,最招爷爷奶奶待见的是小弟。他脑瓜灵光,在集市上,斜眼看看我们,一个个都像中了法术一样,直直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就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溜走,转身去找爷爷。孙子是爷爷的心头肉,故乡祖辈们赶集回家,常会给孙子买一串油煎包。
故乡有则轶事,说有一位爷爷赶集,临时有事不能回家,就关照村里的另一位爷爷,把一串包子带回村给他孙子吃。带包子的爷爷说:“你孙子长什么样,我也不认识啊。”那位老爷爷很高兴、很自豪地说:“你回村,站在大街上,瞅见最好看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俺的孙子!”带包子的爷爷回到村里,见满大街的小男孩,看过来、望过去,只有自家的孙子越看越好看,而且任他怎么看,都是最好看的!于是,老爷爷按照嘱托,就把那串油煎包,给了他看着最好看的小男孩——他自己的孙子。
那时候,卖包子不用塑料袋,用滑溜溜的高粱秆一个一个串起来。我小弟几乎每个集市,手里都会拿着一个空空的高粱秆回家,悄悄地对我们说,是偷偷从“馋痨市”上捡来的,带回家给我们闻闻那上面油煎包的香味。
起初,我还真信了,也只有我信——他那么小,怎么会骗我们呢?!
“他浑身上下都是包子味,一说话还满嘴的包子香味呢!”堂妹拽着堂弟的前襟,馋猫一样蹭来蹭去地闻着,喊着。
“哎呦喂,我们集集‘干逛’、‘看人’,都‘阅人无数’了,就你那点小把戏……”大弟弟顿了一下,学着爷爷的口吻说,“大的呵,可要让着小的。”
那时候,光顾“馋痨市”的除了孩子们,还有老人们。其实,那会儿长桌子顶头,还有个肚大口小的酒缸,酒缸的缸沿上,挂着类似勺子的“酒端子”,盛地瓜干酒用的。那缸、那酒,对我们小孩子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就忽略不计了。
酒,在爷爷辈那里,在“馋痨市”上,是人生百态的媒介。嗜酒的、解乏的、除忧的,欢聚的、送行的、闲情的,等等。长条桌跟前一坐,酒杯一端,人生百味就在酒花里翻滚。
爷爷辈们在“馋痨”市,只有讲究和将就之分。酒肴丰俭不由人,由口袋里的钱。口袋里有钱的爷爷喝酒,有明显的仪式感。后背挺直坐下来,要上一盘猪头肉,一碟油炸花生米。那时喝酒用的黑碗,口浅、撇沿大,有点像盏。喝酒的时候,左手拇指、中指要贴在黑碗边外,食指捏在碗边沿子内,端起酒凝视片刻,然后仰头一大口。喝过酒,紧闭嘴巴,放下黑碗,赶紧用手捂着嘴,说是怕跑了酒味。等一会儿,才缓缓咽下这口酒,抬起右手用筷子夹起碟里的一粒花生米。
村后的四爷爷嗜酒。用我四奶奶的话说,就是“败家精爷们,无酒,伤心。”四爷爷脖子一拧:“你懂啥,连个崽都不能下,我,越喝越有!”有,在故乡的口语里,是发财的意思。
四爷爷什么酒都行,哪怕是假酒,但不能没有。四奶奶只生闺女,不生儿子。四爷爷人生不满意,借酒浇愁。“馋痨市”上,边喝边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一直喝到不言不语。直到日落西山,还端着一杯劣酒,或烈酒,对着瑟瑟秋风——干杯!
比起嗜酒的四爷爷,村里的刘爷爷一辈子除了苦和累,几乎没有别的了。村里的人说,刘爷爷穷了一辈子,临了都没有坐过“馋痨市”的长凳子。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加补丁,高高的个子,干瘦干瘦的,一年四季都在地里忙活。
有一次,刘爷爷看见我们围在一起,闻串过包子的高粱秆,笑着对我们说:“等爷爷有钱了,一定带你们去‘馋痨市’买峰尖的一大盘油煎包、猪头肉,给你们大吃一顿。”
我们快乐地期待着,刘爷爷能快点有钱,好早点带我们去那个香气四溢的“馋痨市”。
深秋的时候,刘爷爷患病,咳嗽、发热,吃药打针总也不见好,还日渐消瘦,不能吃饭。医生悄悄对他家人说,赶紧准备后事吧。
家人用平板车把刘爷爷拉回家,堂屋的地上早已铺好厚厚的麦穰,上面放上一张旧席子、一床旧褥被。安放好刘爷爷,家人凑在他耳畔,尽量语气平缓地问:“好点儿么?想吃点什么?”刘爷爷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看围在身边的家人,无力地挥了挥手,断断续续地说:“上……上坟的时候,多……多……多带……猪……肉。”
一屋子人戚然敛容,泪如雨下。
少不更事,不知道与世长辞意味着什么,却深深体会到,那个香气四溢的世界离我而去是什么滋味。我汪然出涕,继而失声大哭。
悲哀的事情,却往往历历在目。
刘爷爷去世了,邻居四爷爷一直懊悔,手不离酒瓶。他俩是老弟兄,刘爷爷一辈子好强、要面子,自家穷,干活帮忙,随叫随到。去“馋痨市”喝一盅,不管四爷爷怎么邀请他,他高低不去。
地瓜干酿造的酒,乡亲们俗称为“大头昏”,酒量低的人一喝就头昏。四爷爷酒量大,但架不住无节制地喝,喝得昏昏然,也就暂时不知愁味。四奶奶赶紧找我本家的大爷去劝说,让他戒酒。
我大爷在村里也算个场面人,便直奔“馋痨市”找四爷爷。
喝酒得慢,劝戒酒的话却长,得绕一个长长的大弯子。我大爷先是接着四爷爷的话茬,回顾一年来村里的大事小情,说说来年打算。最后总结:开支都不小呢,您!得戒酒。
四爷爷呢,酒醉心不糊。递给我大爷一杯酒:“喝过酒、吃了猪头肉,你才会知道,做人,还是值得的。等我这手不能端酒碗了,就是你……送我……送我下地的时候喽,到那会儿啊,酒……就彻底……戒喽!”
最后,我大爷、四爷爷相扶起身,离开“馋痨市”。
我大爷这一喝,便喝上了瘾。从此,“馋痨市”非一来再来不可。
多年后,“馋痨市”上,四爷爷坐过的长板凳上,坐着我大爷。与四爷爷不同的是,我大爷并不爱酒,爱的是那一种清绝的酒趣和人生意味。朔风砭骨之时,我会与大爷浅饮低酌,海阔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之后,看着我大爷带着薄醉,踏着一街凉月归去。
少年时光的“馋痨市”,让我无限满足和快乐。那么年轻的岁月,因为那些简朴的美食,而被拉伸得无限长、无限深、无限远……
30 多年过去了,“馋痨市”的规模、吃食种类、灶具、餐具设施以及用餐环境,都处于月月新,年年变的更新升级状态,人们也由当初单一的“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的富足,完成从吃不饱,饱腹到健康饮食的转变。“馋痨市”成为历史的符号,记录着乡亲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人生秋至,念起故乡,,驻足回眸岁月深处的“馋痨市”,那些年、那些月,那些人、那些事,依然是我最清晰的眷恋。